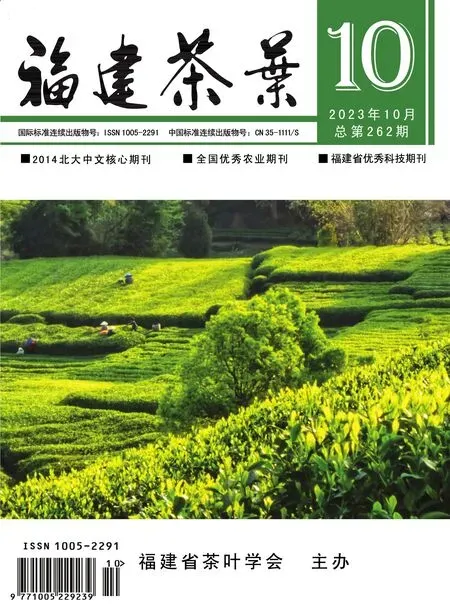宋代点茶的美学特征研究
吴苇菡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00)
茶文化历史悠久,据陆羽所著《茶经》中的说法,它的发现和使用最早可追溯到神农时期:“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作为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的问世代表了唐代茶文化的发展。陆羽将茶学精神与美学精神相结合,茶由食物转变为饮料,使得茶从纯粹的实用性转向品茶的审美性[1],由此一来,茶除了原初的食用价值之外,品茶的过程也提供审美价值。在茶的制作、冲煮、饮用等饮茶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里,对制茶的工具、点茶的技艺、使用的茶具等有其独具一格的判断与选择标准,在保证茶的风味的基础上从色、香、味等角度为感官提供了视觉、嗅觉的享受。
1 茶与生活艺术化
宋代经济文化繁荣,饮茶作为宋代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它的鼎盛时期,饮茶之风日盛,从帝王将相到平民,都把茶作为一种日常饮品,宋徽宗更是作《大观茶论》一书详细论述了点茶之法。这与宋代的休闲审美文化密切相关。
宋代因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另一方面也存在较高程度的边境危机。宋代士人生存的这种特殊环境,使得宋代艺术审美在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一种审美风尚,而宋代美学的突出特征就是艺术的生活化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现象。[2]如果说中国美学的一大特征在于对人生、生活和生命的观照,宋代的这种休闲审美文化可看作中国美学的这个特征体现于生活实践领域的有力证据,饮茶则是最能反映这个特征的文化活动。
由于饮茶在宋代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茶就有了其社会文化功用,参与到居家、待客、婚仪、饮食业等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北宋有客来敬茶的习俗,客来设茶,送客点汤,[3]茶、汤也是宋代士大夫宴饮生活完整程序(酒—茶—汤)的后两个环节[4]。茶肆、茶坊、茶楼、茶店广见于两宋都城汴京和临安,乃至县乡市镇中。宋代墓葬中多处出现茶题材壁画,由北宋早期简单生活器具的雕刻,经中期、晚期至南宋的发展,雕刻更为精美,出现夫妇宴饮图、备茶图、侍奉图、供养祭祀图等多种世俗生活场景。[5]这一方面生动反映了宋代百姓居家饮茶生活的休闲享乐情景,说明当时茶事活动的盛行,浸润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文化的各处。另一方面,由于古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希望墓主人在地下世界也能享尽生前的荣华富贵,因此墓葬中的壁画可看作对文字材料的补充资料。而墓葬壁画作为生前生活的镜像,可见饮茶活动不仅是兴盛一时,并且是一项高雅、考究的文化活动,体现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审美趣味和崇高品格。此外,将品茶这种原本只是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墓葬壁画这种形式表达,实际上也是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来呈现,从侧面呼应了宋代生活艺术化的美学特征。
2 茶艺与审美体验
2.1 唐煮宋点
唐代的饮茶方式为煮茶法,宋代茶饮的特点则是点茶法。
如前所述,茶作为一种日常饮料,在唐之前尚未广泛普及,到了唐代中期才在社会各阶层各地方广泛兴盛起来,饮茶习俗发展为一种特有的茶文化。皇室宫廷方面,唐玄宗明确“茶”的音、形、义。理论方面,陆羽在《茶经》中以嘉木、“精行俭德”对茶之品德加以规定,赋予茶独特的文化意涵。传播方面,饮茶之风在佛寺普遍流行,古寺名刹皆悬“茶鼓”,“茶佛一味”之说盛行,认为“品茶如参禅”,并逐渐形成以茶事佛的风尚[6]。唐代茶事以饼茶为中心,陆羽详细著述了煮茶全过程。用搭配好的木炭、火候、水质等等煮茶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茶之本性。煮茶过程又分为一沸(初沸)、二沸、三沸。每一次煮沸都分别有需要操作的步骤。饮茶实际上引用的是均匀舀出的茶汤与茶之精华沫饽,尤以前三碗为佳。[7]
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与唐代煮茶大不相同,它是将半发酵的茶叶制成的膏饼碾成茶末后,用沸水在茶盏里冲点。这种点茶法虽不是宋代独创,但到了宋代,点茶已发展到一定高度,形成了标准化的规范,它要求极高的操作技巧和文化修养,这也就意味着在制茶工序、茶具茶器的选择、冲煮法等等方面有严格且详尽的要求。
2.2 制茶工序中的感官享受
北宋茶学家蔡襄为了向宋仁宗推荐建安茶,特作《茶录》,分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茶叶的选择标准、烹煮方式和煮茶所用的器具,集中反映了宋人品茶的技艺及其审美特征。
《茶录》上篇论茶,由茶的色、香、味讲起。色:“茶色贵白。而茶饼多以真膏油其面,鼓有青黄紫黑之异。……以肉理润者为上,……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以青白盛黄白。”[8]蔡襄以茶色青白为上,要求茶汤清明,较次的黄白色茶汤则比较浑浊色沉,故青白更佳。宋人追求的这种纯白鲜明的茶汤,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尚白”的审美传统在宋代饮茶活动中的体现,即对茶视觉上的简洁素雅的审美倾向。
香:“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正当不用。”[8]以前的茶中多放入香料提香,却同时掩盖了茶的天然气味。蔡襄主张不应在烹点茶叶时加入任何其它东西,以免遮蔽了茶叶本身的香气,也就是茶之“真香”。他在这里明确指出要品茶之“真香”,即品味茶的自然香味而不以人力修饰或加工,这与宋代崇尚“自然”、天然之美的审美风尚是一致的。
味:“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隔溪诸山,虽及时加意制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损茶味。前世之论水品者以此。”[8]除了作为主要原料的茶叶本身,用于烹点茶末的水的质量也极为重要,好的甘泉水才能冲出清甜爽滑的茶汤,如此一来茶才能充分显其“真味”,品茶之人才有更佳的味觉体验,开启由味觉通往审美境界的道路。
虽然蔡襄作《茶录》的目的是为了进贡他制作的小龙团,但他对茶的色、香、味进行的一系列论述,不仅显示了他对茶事的极致追求,也显示了宋代人对茶汤的要求不仅限于对味道的单一体验,而在于对构成饮茶活动各环节的整体之美的感知。除了对茶之色、香、味的品评,蔡襄还在上篇中对茶的保存、点茶的六个步骤详细探究并规定,可见宋人在欣赏美的同时也在尝试创造美,制茶的过程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2.3 点茶的审美意蕴
点茶是制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蔡襄对当时的点茶技艺确立了标准:“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8]茶与汤需保持一定的比例,以一定的先后顺序和手法,才能得鲜白茶色,而水痕留存时间又是斗茶游戏的一个评判标准。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对“七汤”点茶法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其中技艺之复杂,包含有七次加水的动作:“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砍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周拂,手轻芜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桑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寘,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同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芜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芜著,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悖,饮之宜人,虽多不力过也。”[8]
点茶艺术发展到宋徽宗时已是高峰时期,流行于贵族与士大夫阶层,《文会图》中描绘的就是宫廷大茶会中点茶的情景。由《大观茶论》的这段论述也可看出,赵佶对点茶中的每次注水及要达到的效果有极为严苛的要求。他使用大量自然物象,如调茶膏时“疏星皎月”“灿然而生”,而后“珠玑”渐落,点汤后生出“云雾”,结“浚霭”、“凝雪”,最后茶盏中出现汹涌“乳雾”盘踞等等。经此描述,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单纯的点茶活动,不仅是艺术美的审美对象,用自然的眼光观照点茶法的审美意蕴,则透过点茶艺术自身的美学韵味,更体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本然状态,艺术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在世界大全中臻于更高的人工与天工的统一。
“茶百戏”是点茶艺术中较为独特,也极具表现性的一种艺术形式。茶百戏又称分茶、水丹青、茶戏等等,陶谷《荈茗录》中“茶百戏”一条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8]茶汤在击拂的作用下变幻出各种图样的汤纹,显出一种灵动的美。《大观茶论》中描写的自然美多为茶艺家在点茶活动中静态的审美观照,而茶百戏则是对转瞬即逝的变化着的汤花的直观,汤纹同样多以自然物象为主,更增添自然美的丰富多样,茶百戏又因其艺术形式,展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美、线条美和朦胧美。
2.4 器具之美
宋代饮茶方式的改变,对茶具的使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宋代经济高度发展,海外贸易发达,陶瓷器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是贸易中的重要部分。与唐、五代不同的饮茶方式的变化,透过陶瓷茶器,宋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和美学风尚得以呈现。
蔡襄在《茶录》的下篇分别从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捻、茶罗、茶盏、茶匙、汤瓶几个方面论述,多是对器具的材质作规定,其中茶盏要求:“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胚微厚,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8]宋徽宗《大观茶论》中也讲“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这是说宋代使用黑釉瓷茶盏,以满足点茶、斗茶的需求。宋人对点茶器具的要求包括茶盏的颜色、茶盏的厚薄程度和茶盏的花纹式样,这些详细规定首先是为了满足宋代点茶技艺的呈现效果。与陆羽等人使用青白瓷的茶碗不同,到了宋代使用的茶碗是黑釉瓷。由于对茶汤以纯白鲜明为佳,而斗茶又以咬盏持久、水痕晚现为胜,这种视觉感觉的验证标准,茶盏就必然要易于观察茶色与水痕。黒盏白汤,相得益彰,黑釉瓷茶盏是最适合的。其次,关于茶盏的造型及功用,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讲“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宪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8]可见,茶盏的口、足、宽度与深度都会影响到点茶,因此,根据茶量的多少,需使用不同大小的茶盏。盏壁“微厚”,“久热难冷”也使得汤纹留存时间更久。
黑釉茶盏又有蓝黑釉色的“紫盏”、兔毫盏、油滴釉茶盏、鹧鸪斑纹茶盏、玳瑁釉茶盏、剪纸贴花纹茶盏、木叶纹茶盏等纹样[9]。其中以兔毫盏最为著名,被看作是最理想的斗茶器。其盏身内外皆有黄棕色或铁锈色条纹,尤以闪银光色色细长条纹者为最佳,状如兔毛,故称兔毛盏。兔毛、玉毫、异毫、兔毫斑、兔褐金丝等等都是指的这种兔毫纹。[9]茶盏发展至此,已不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更多的包含有审美享受。许多茶词就提到对茶器的赏玩,如“兔毛紫盏白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梅尧臣),“兔瓯试玉尘,香色两超胜”(陆游《烹茶》)等等。烹茶、茶器、赏玩、饮茶,茶文化的方方面面将饮茶之人升华至美的境界,与有限的茶盏间体味无限的意境。正如蔡襄《试茶》描绘的:“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3 茶与“玩”的休闲美学
如果说上文提到的点茶活动中的茶百戏已趋于更纯粹的艺术美,那么斗茶则反映着宋代独特的“玩”的休闲美学。斗茶又称斗茗,斗茶风尚始于唐代盛于宋代,是北宋时期深受自宫廷至民间文人雅士所钟爱的雅玩。斗茶活动中,茶的色相、茶的香气、茶汤的醇厚程度,甚至于茶具的优劣等等,都作为众人品评的项目,最终以上乘者为胜。如蔡襄在《茶录》中提到的,斗茶以水痕、耐久等因素为标准评判胜负;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提出“茶不问团铤,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8]的观点作为品茶的标准;宋徽宗的“七汤”点茶法也可看作他对品茶的审美倾向。
由于茶艺技术要求极高,这种活动往往是一种雅玩。正如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提到的,“把握‘玩’是理解宋人艺术的一个关键。”这种“玩”,是“以一种胸襟为凭借,以一种修养为基础的”,这也就意味着脱离了对功利的考量,对世俗的追求,对名誉的计较,从而成为一种无功利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玩”的心境,它所追求的,是与“俗”相对的高雅的“韵”。[10]宋人追求的这种“韵外之韵”,通过点茶活动中茶的制作、艺术活动、品鉴等方面,从感官审美(视觉、味觉、嗅觉)、艺术体验、休闲玩乐的角度,全方面体悟过程中的艺术美、自然美,以“玩”的审美心境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观照人生、生命,这种同于大通的审美境界,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和谐交融的“自然”之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