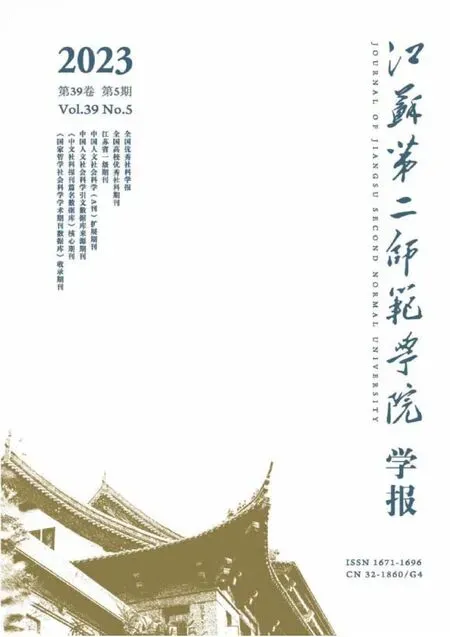精神病态与道德困境判断:共情与工具性伤害的链式中介作用*
云 祥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一、引言
精神病态特质是一组以冷酷无情、自我中心、人际操控以及反社会冲动为核心特征的人格特质[1]。作为一种在广泛人群中连续分布的人格特质[2],即使是那些在临床上未被认定为精神病态但具有较高的精神病态特征的个体也可能表现出缺乏同情、冒险、病态撒谎等典型的精神病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高精神病态特质个体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对社会和道德规范的漠视,导致他们频繁地、刻板化地表现出各种不道德行为[3],这引发许多研究者对精神病态与道德判断关系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探讨高精神病态个体在解决道德困境问题时是否与其他人不同。
道德判断是指个体根据特定标准,对某些行为的是非好坏进行评价,并做出选择和判断的过程[4]。根据道德判断时的依据,可分为道义论道德判断和功利主义道德判断[5]。道义论道德判断强调根据道德原则进行判断,即使某个行为能够给个体带来更大福祉,如果该行为本身违背道德原则,也不可接受;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根据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如果伤害行为能够给总体带来更大福祉,则在道德上可以接受[5]。牺牲性道德困境是用来研究道德判断的主要方法[6]。常见的牺牲性道德困境有经典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在经典的电车困境中,被试必须选择是否扳动扳手,使一列列车改道,从1个人身上碾过,以拯救躺在前面铁轨上的另外5个人。天桥困境要求被试决定是否将1名身材肥胖的男子推下桥,从而使列车停下来,这样可以防止前方铁轨上的5人死亡。在这些情境中,被试都必须做出救1个人还是救5个人的决定。根据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原则,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认可或采取行动都表明一个人偏好功利主义的判断,不认可或拒绝行动则代表一个人偏好道义论的判断[7]。基于这样的研究范式,多数研究发现,与低精神病态个体相比,高精神病态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主义判断而非道义论判断[8-11]。然而,有些研究并未发现精神病态和道德困境判断之间有可靠的关联[12]。Marshall等人的一项元分析综合了相关主题的研究,显示精神病态与功利性道德判断之间存在小幅正相关(r= 0.26),这表明精神病态高的个体比精神病态低的个体更容易接受有利于总体的违反规范的行为[13]。
如何理解精神病态个体倾向功利主义道德判断呢?Gawronski等人认为,人们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的判断偏好受到3个因素的驱动:对行动后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以及自身的行动偏好[14]。个体对行动后果敏感、对道德规范不敏感、自身有更强的行动偏好或者三者的某种混合,都有可能导致其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那么,精神病态的功利性道德偏好是出于上述哪个或哪些因素呢?由于传统道德困境范式在方法上的缺陷,使其难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具体来说,首先,传统道德困境范式将功利主义倾向和道义论倾向视为连续体的两端,接受一种选择意味着拒绝另一种选择。然而,根据道德困境判断的双加工模型,功利主义判断和道义论判断是相互独立的心理加工过程[15],而传统的范式要求个体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就使得功利主义判断和道义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混淆不清。因此,我们无法确定道德困境判断的差异到底反映的是功利主义判断倾向的差异、道义论判断倾向的差异,还是两者的差异[16]。其次,传统道德困境范式中,功利主义判断通常需要采取行动(例如,扳动扳手,推人下桥),而遵守道德规范和义务通常需要不采取行动(例如,不扳动扳手,不推人下桥)。因此,传统道德困境范式中判断为功利主义倾向的结果中混淆了个体自身的行动偏好,而判断为道义论倾向的结果中混淆了个体的不行动偏好[14]。因此,研究者采用能够解离道德困境判断中上述混淆的CNI(consequence, normal, inaction)模型,进一步探讨了精神病态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研究显示,相对于低精神病态个体,高精神病态个体面对道德困境时,表现出对行动结果更不敏感,对道德规范和义务更不敏感,以及较强的行动偏好的特点[14][17-18]。这说明精神病态个体做出的行动并非出于对总体福祉的考量,而是出于对道德规范和义务的漠视以及自身的较强行动偏好。
为什么精神病态的个体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忽视道德规范和义务,偏好采取行动呢?精神病态个体的共情缺乏可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缺乏共情是精神病态中冷酷无情维度的核心特征,是将精神病态与其他反社会人格类型相区别的关键[19]。研究显示,共情缺乏与功利主义道德判断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1][20-21]。有研究者认为,精神病态功利主义偏好的增加是由于其对伤害厌恶的减少,即由于情感加工上的缺陷,在对道德困境做出判断时,精神病态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对处于情境中的受害者共情,进而难以对功利主义选择所引发的伤害行为产生道德上的厌恶[22]。也就是说,精神病态做出功利性的选择并非出于强调成本—收益以提升总体福祉的考量,而是因为其由于缺乏共情导致对伤害行为厌恶的减少,削弱了“不伤害他人”的道德规则的约束。所以,这里我们假设精神病态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影响其道德判断。
除了共情,传统道德困境判断研究所使用的道德困境本身的特征也可能是导致精神病态与功利主义偏好正相关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牺牲性道德困境的结果不能反映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全貌,功利主义哲学核心在于不偏不倚地实现更大的利益[21]。采取彻底不偏不倚的道德立场,就是将每个人的福祉视为同等重要,不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也不应该将家人、朋友、同胞的利益置于他人之上[23]。Kahane等人认为功利主义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积极的维度体现为无偏的善行(Impartial beneficence),强调将每个人的福祉视为同等重要,采取不偏不倚的道德立场去实现更大的利益;消极的维度被称为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即愿意为实现更大的利益而伤害他人[23]。牺牲性道德困境仅仅测量了功利主义的工具性伤害维度[9][23]。而相关研究显示,精神病态特质与工具性伤害倾向呈正相关[18][23],所以,我们推测精神病态可以通过工具性伤害的中介影响道德判断。
由于共情强调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和理解,共情水平高的个体更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所以共情一般被认为是伤害行为的重要抑制因素[24]。虽然功利主义框架下的工具性伤害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总体的福祉,但是要通过伤害行为来实现,所以这种工具性伤害的倾向也可能受到个体共情的抑制。也就是说,如果考虑杀死1个人来拯救另外5个人,个体的强烈的共情反应可能会阻碍这种工具性伤害。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Kahane等人研究显示个体的共情关怀与工具性伤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3]。因此,我们假设精神病态还可能通过共情—工具性伤害的链式中介来影响道德判断。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包括3条中介路径:路径一,精神病态→共情→道德判断;路径二,精神病态→工具性伤害→道德判断;路径三,精神病态→共情→工具性伤害→道德判断。

图1 链式中介模型示意图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在南京两所高校选取大学生588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由于研究所使用的材料阅读量较大,为保障数据质量,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一个注意检查项目,以确认被试在完成测试过程中是否认真阅读了材料。最终有61名被试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另外还有5名被试未完成测试,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22份,有效率88.78%。其中,男生347名(66.48%),女生175名(33.52%)。年龄范围在17—22岁之间,平均年龄18.78岁(SD= 0.88)。
2.研究材料
(1)道德困境判断材料
采用改编自Gawronski等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14]。整套材料由6种基本的道德两难情境构成,每种困境包括4个平行版本(禁止型/倡导型道德规范乘以行动收益大于/小于成本),共24个道德两难情境。被试需要判断道德困境中道德主体的行为是否可以接受(不可接受 vs. 可以接受)。
(2)注意检查任务
采用Oppenheimer等设计的注意检查任务[25]。该任务由1个项目构成,项目题干要求被试在3个选项中选择指定的选项,如被试未按照要求做出选择,则表示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
(3)精神病态特质
采用Levenson精神病态自评量表的简体中文版中的原发型精神病态分量表[26]。该分量表共有16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精神病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α=0.82 。
(4)工具性伤害的道德倾向
采用牛津功利主义量表(Oxford Utilitarianism Scale)中的工具性伤害分量表测量被试的工具性伤害道德倾向[23]。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分量表由4个项目组成,反映了是否接受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而伤害他人(例如,“如果伤害1个无辜者是帮助其他几个无辜者的必要手段,那么伤害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在本研究中,工具性伤害分量表的信度α=0.75。
(5)共情
采用中文版人际指标反应指数量表中的共情关怀分量表[27]。该分量表由7个题目组成,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共情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信度α= 0.72。
3.施测过程
被试分批在教室集体施测。所有被试首先完成道德困境判断和注意检查任务,然后完成Levenson精神病态自评量表、牛津功利主义量表和共情量表,最后填写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数据。
4.数据分析
对于每一个道德两难情境,选择“不可接受”赋值为“0”,选择“可以接受”赋值为“1”。由于Gawronski等提出的基于24题的道德困境分析CNI模型法只能计算出群体水平的CNI参数,无法可靠计算出每个被试的参数,且会高估代表道德规范敏感性的N参数,使代表一般性行动/不行动倾向的I参数不可靠[28-29],所以本研究采用Liu 和Liao 提出的修正上述方法局限的CAN 算法来计算代表结果敏感性的C参数、代表道德规范敏感性的N参数和代表无论受何因素影响总体上倾向于行动的偏好程度A参数。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考Liu 等人的文章[28]。
所有的数据分析都在SPSS 25.0及其PROCESS 4.0中完成。
三、结果与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9个,能够解释59.74%的方差变异,并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1.49%,小于40.0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描述型统计和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对精神病态、共情、传统道德困境判断分析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基于CAN算法的道德困境判断C参数、N参数和A参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一览表(n = 522)
基于传统方法分析的功利主义倾向与精神病态特质、工具性伤害显著正相关,与共情显著负相关,与C参数和A参数显著正相关,与N参数显著负相关。精神病态特质与共情以及N参数显著负相关,与工具性伤害显著负相关;共情与N参数显著正相关,与工具性伤害显著负相关;工具性伤害与C参数和A参数显著正相关,与N参数显著负相关。
3.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精神病态、共情和工具性伤害与道德困境判断的3个参数的关系,所以,不对传统方法计算的功利主义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精神病态只与道德判断的N参数存在相关,因此,之后的分析只探讨精神病态与N参数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采用SPSS 25.0及其PROCESS 4.0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精神病态得分作为自变量,道德判断N参数作为因变量,共情倾向和工具性伤害作为中介变量,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根据PROCESS模型六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精神病态能显著预测共情水平,精神病态和共情水平能显著预测工具性伤害,精神病态、共情水平和工具性伤害能显著预测道德判断N参数。在加入共情水平和工具性伤害后,精神病态依然能显著预测道德判断N参数,表明共情水平、工具性伤害在精神病态和道德判断N参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变量间的回归分析一览表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共情水平和工具性伤害的中介作用显著,总中介效应值为0.15。具体来看,中介效应通过3条中介链产生:第一条为由精神病态→共情→N参数组成的路径,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共情的中介作用显著;第二条路径是精神病态→工具性伤害→N参数,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工具性伤害的中介效应显著;第三条路径是精神病态→共情→工具性伤害→N参数,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共情和工具性伤害的链式中介作用存在。3条路径对总效应的占比分别为12.57%、21.20%、4.45%。另外,精神病态除了通过上述3个路径对道德判断N参数产生作用,还可以直接对道德判断N参数产生影响,其产生的直接效应值为-0.24(t= 4.99,p<0.001)。

表3 共情和工具性伤害在精神病态和道德判断N参数间的中介效应值和效应占比一览表
四、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精神病态和道德困境判断的关系以及共情和工具性伤害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精神病态、共情、工具性伤害和道德困境判断N参数存在显著的相关。精神病态对道德困境判断N参数有直接负向的预测作用,共情和工具性伤害在精神病态和道德困境判断N参数间既存在独立的中介作用,也存在共情—工具性伤害的链式中介作用。
1.精神病态与道德困境判断的关系
基于传统道德困境分析方法显示,精神病态特质与功利主义道德判断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我们进一步基于CNI模型并使用CAN算法来具体考察精神病态是通过影响个体道德困境判断时的C参数、N参数还是A参数导致上述结果时,结果显示,精神病态与C参数相关不显著,与N参数显著负相关,和A参数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略微存在差异[18][28]。具体来说,Körner等人基于48道道德困境题目的CNI模型法计算出每个被试的C参数、N参数、I参数(I参数的方向与A参数相反),显示精神病态与3个参数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8];Liu和Liao使用CAN算法重新计算了Gawronski等研究4a和4b的数据,结果显示精神病态与N参数显著负相关,和C参数关系不确定(研究4a显示相关不显著,4b显示负相关),和A参数相关不显著[28]。综合本研究和上述两个研究,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精神病态与N参数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精神病态只显著负向预测N参数。这表明高精神病态个体之所以在牺牲性道德困境中存在功利主义偏好,主要原因是高精神病态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对道德规范不敏感,做出道德决策时不容易受到道德规范的驱动,而与道德选择的结果以及自身的行动偏好关系不大。
2.共情、工具性伤害在精神病态与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精神病态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影响道德困境判断的N参数。这一结果说明在传统的牺牲性道德困境研究中,精神病态之所以表现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精神病态会通过减少共情,进而削弱道德规范对自身的影响,从而更少做出道义论道德判断,相应地也就表现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判断。以往研究认为精神病态在进行道德困境判断时,由于缺乏共情,对受害人的情感卷入程度较低,较少产生对伤害行为的厌恶情绪,从而促进了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10]。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精神病态通过共情影响的道德困境判断的另一条路径,即共情的缺陷削弱了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已有研究认为道义论判断依赖直觉性的情绪加工[15],精神病态个体由于情绪加工上的缺陷,不易产生直觉性的情绪反应,难以激活启发式的道德规则,因而更少做出道义论的判断,在传统范式下,较少的道义论则意味着更多的功利主义。
研究结果显示,高精神病态个体有更强的工具性伤害的倾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8][23],这表明高精神病态个体更愿意接受牺牲少数以获得更大利益的行为。本研究还显示,工具性伤害偏好与道德判断N参数显著负相关,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同,为了更大的福祉而去伤害他人本身就是对“不伤害他人”这样的道德规则的违背[18]。所以,精神病态还可以通过工具性伤害间接影响道德判断N参数。因此,我们又多了一条解释精神病态的功利主义偏好的路径,即高精神病态个体有更强的工具性伤害的倾向,而对工具性伤害的偏好减少了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表现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倾向。
3.共情和工具性伤害在精神病态与道德判断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共情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工具性伤害,且精神病态可以通过共情—工具性伤害链式的中介对道德判断N参数产生间接效应。这表明精神病态不仅可以通过共情、工具性伤害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道德判断N参数,还可以通过减少共情促进工具性伤害的提高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所以,高精神病态个体的共情水平更低,而共情的缺乏除了减少个体对伤害行为的厌恶,还增加了个体对工具性伤害行为的偏好,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导致道德规范对个体约束的削弱。
总之,本研究系统分析了精神病态与道德困境判断的关系,以及精神病态的共情缺陷和功利性偏好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道德困境判断的3个决定因素与精神病态的心理特征联系起来,这不仅可以为理解精神病态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缺陷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还对道德困境判断心理机制的探讨具有一定的价值。另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的研究样本为大学生样本,通过自我报告测量的所得结果大部分达不到临床精神病态标准,虽然精神病态特征在人群中是连续分布的[2],但我们在当前研究中获得的结论是否能够代表临床标准的精神病态个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本研究所使用的道德困境材料多是关于生死的极端和不寻常的主题,没有涉及日常生活中在个人利益和他人福祉之间的选择或者对他人道德义务的履行等方面的道德问题[30],后者恰恰是精神病态容易卷入的道德越轨行为的道德问题[9]。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日常道德困境材料来研究精神病态的道德选择。
五、结论
本研究发现,其一,精神病态特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困境判断的N参数;其二,精神病态特质能够分别通过共情、工具性伤害的中介作用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N参数;其三,精神病态能够通过共情—工具性伤害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N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