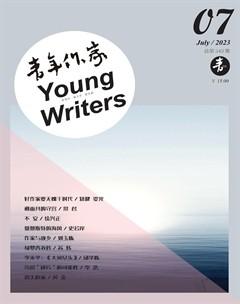盗果记
“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那时,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意思是说,小孩子小偷小摸,长大后就定是一个钉在耻辱柱上的大盗。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孩提时代,我就是个偷摘水果的“小毛贼”,从七岁一直偷摘到十三岁,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园艺场、上学路上私家院落的小果园,都留下了我匆匆的脚步。当然,偷东摸西,不论是在哪个年龄段,都是不光彩的行为,那是用别人的手打自己祖宗的脸。十三岁以后,我彻彻底底明白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把黑色的过往压在了箱底,不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只不过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会把它拿出来晾晒晾晒。
一
1970年代初期,一个稻花飘香的早晨,我走进了大队小学,开启了读书生涯。刚开始,听课、做作业、做游戏、打球,校园时光把我紧紧地包裹着,幸福洋溢心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慢慢退潮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厌倦和饥饿。我家离学校有四五公里路。为避免第二天早课迟到,母亲在头天晚上就给我备好了次日的早餐。黎明刚把黑夜撕开一条口子,母亲就叫醒我,一边给我烧火热早餐,一边给我讲上学的注意事项。早餐非常简单,除了酸菜红苕,见不了几个“米花花”,更不用说“油星星”了,反正稀汤波浪一大碗。这样草率地对待肚子,肚子是有意见的,一到上午十点多,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默默地做两件事情,一是畅想中午的午餐是什么样子,尽量把它想得美好些、丰盛些,比如说米饭下面卧着一块巴掌大的腊肉;二是拼命地转移注意力,把注意力牢牢地拴在学习上。放学铃声一响,我和同学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教室,无论是烈日,还是雨雪,都火速奔跑在回家的路上。
一天中午,太阳像个大火球悬在天上,世界像个大蒸笼,赤裸的脚踩在地上,像踩在滚烫的钢板上。为了尽快地赶走饥饿,我拼命地在这个大蒸笼里奔跑,直到顽皮的小石头把我的脚趾教训得皮开肉绽。我正准备到一棵桐麻树下处理伤口的时候,突然发现树下坐着一个小男孩,走近一看,是比我低两个年级的邻居唐家贵。他脸色苍白,一只手按着肚子,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我问明情况后,估计他中暑了,连忙背起他回家。那棵桐麻树虽然离他家不是太远,但饥饿、暴晒死死折磨着我,我费了洪荒之力,才把唐家贵背回家中。
放下唐家贵,我一下感觉四肢疲软,头昏眼花,站立不稳。
唐家就住在我家坎下,两家交往不少,我对大多数唐家人印象不错,唯独对唐父有点小意见,他见人就笑,总觉得他笑里藏着沙子,不纯净。但那天我突然感觉他变了,变亲切了,变可爱了。他把儿子扶进屋后,二话没说,就直奔院坝边的李子树,跳起,拉下一根枝条,摘了一捧李子,塞给我:“没啥好招待的,解解渴。”当我把李子放进嘴里时,劲儿立即从每个毛孔里冒出来,人也有精神了。
后来,这棵李子树就站在我心里了。它顶着绿油油的树冠,远看像团厚实的绿云朵。它不仅外表朴实无华,还给人们奉献了许多爽口的果实。我每天上学放学路过唐家时,都要一遍一遍地深情凝望那棵李子树。
一天下午,我在学校学农基地参加完劳动,夕阳像面大铜锣立在山尖。我披着暮色,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跳着舞的炊烟放大了我的饥饿,牧童的笛声喂胖了我的困乏。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唐家院子外的一块坡地上。站在坡地看唐家,烟雾缭绕中,李子树若隐若现,一片飘渺,宛若仙境,我仿佛看见那些胖嘟嘟的李子正唱着歌,扭着腰,欢迎我去检阅。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辜负了李子们的一片心意呢?
我先规划路线,到达李子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大路到院子,二是绕苞谷地到达。如果走大路,目标太大,唐家人多,老老少少十多口,还没走拢,就可能被发现了。苞谷林是天然屏障,走苞谷地,不易被发觉,风平浪静时,走快点,有风吹草动,停下来看看,收放自如。如此一番盘算后,我便迅速走进苞谷林。苞谷林似乎不喜欢我,它们使劲地用叶片割我的手臂,我的手臂上,好像有无数毛虫在吞吻。不过这些都难不到我,因为我心中有一束燃烧的火苗,火苗的名字叫李子。
我轻手轻脚地来到李子树下,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夜幕已经拉下来了,水牛正在不远的牛圈里动情地吃草,猪圈里的猪似乎打起架来,广播里传出沙哑的声音,说的什么听不清楚,唐家人都在屋里忙碌着。我判断这是和李子约会的绝好机会,连忙顺着树干往上爬。这是棵大树,爬到树干顶,树干又分出几个枝丫,枝丫像几支巨大的手臂向黑压压的四周伸展开去,大枝丫上又长出一些小枝丫,那些顽皮的李子才居住在那里呢。突然间,我感到那些可爱的小李子在和我捉迷藏,故意长在那些遥远而危险的地方,惹我不高兴。
我开始犹豫起来:是继续前行,还是打道回府?如果前行,很快就能摘到李子,但问题是小枝丫同意吗?如果小枝丫不同意,发起脾气来,会把我狠狠扔到地面上。如果回去,这一夜的辛苦岂不白费了?我决定试试,我选择沿着伸向苞谷地那个枝丫爬去,因为即使枝丫“献身”了,我被摔到苞谷林,也能减轻伤害。我双腿夹紧枝丫后段,两手抱紧枝丫前段,缓慢地向前移动,爬了约两米,枝丫开始晃动起来,我惊出一身冷汗,忙停下来,还好,伸手就能摸到一根小枝条。我把小枝条拉过来,一串胖胖的李子被抓住了,我慌忙地把它们摘下来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的,没吃几个,肚子就饱了。吃完后,我又摘了一些装在书包和裤兜里。
刚走出苞谷林,就听见母亲在家门口叫我的乳名。
二
我的老家川北苍溪,山川扶與,清气磅礴,是声名远播的水果之乡。我们那个大队里,苍溪雪梨树漫山遍野,集体有好几个大的园艺场,大的有好几十亩,有专业队伍管理,我二舅就是专业队负责人。苍溪雪梨理所当然是我的心爱之物。除苍溪雪梨外,我心心念念的还有附近贵阳大队的苹果。
贵阳大队有一个苹果园,横卧在一个叫尖包梁的山梁一侧,大约有二十亩,春天满园一片春色,夏天碩果压弯枝头。真正吸住我眼球的是我读初中一年级的那个夏天。
一天早上,一轮火红的朝阳从容地在东边山巅上燃烧,万千条金线抛落而下,铺展在大地上。我迎着朝阳,搭着书包,和邻居杨德武一起行走在上学的路上。
尖包梁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它像一条鲤鱼的脊梁横亘在两片田园中间。站在尖包梁,举目四望,远处一棵棵秧苗站成嫩绿的诗行,正在孕育丰收的希望,近处,苹果园里的苹果压弯了树梢,微风一吹,手舞足蹈的,惹得我心里痒痒的。
再往上走,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头发凌乱,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边吸着烟,一边专注地扫视着苹果园。
走过尖包梁,我和杨德武有个想法,几乎同时从心底飞出:想办法尝尝尖包梁园艺场里苹果的味道。
小时候嘴馋,又性急,有了这个想法,恨不得马上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对园艺场地形情况、安保情况一概不知,稍有不慎,就会吃不到羊肉惹一身膻。
晚上放学后,我们又来到尖包梁附近,仔细打量起苹果园来:苹果园内,除大片苹果树外,还有个简易茅屋,屋外有只大黑狗,警惕地盯着四周。通往苹果园的路有两条,一条从尖包梁的顶部直插下去,另一条从尖包梁的底部平行伸入。如果悄悄进入园内,相比之下,走底部那条路比较隐蔽。
来到尖包梁的顶部,早上见过的那位男子好像还在那里闲逛,时而盯盯这,时而盯盯那,莫非他是苹果园的守护神?试试看:
“老叔贵姓?在忙啥?”
“我姓何,在看园子呢。”
一试,果真如此。如果要进入园子,还得把“功课”做深做细:
“老叔,您一个人看这么大个园子,太辛苦了。”
“下面屋子里还有人看,我主要看外围。”
“那整天这样,也太无聊了。”
“也不完全是这样,有时还看看书。”
“叔,您喜欢看哪些书?”
“《红岩》呀,《西游记》呀,不过这些都看过了。一直想找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看,就是没找到,小朋友们,你们有吗?”
“叔,我们没有。但我们可以帮你找找。”
那时,我爱看一些文学书籍,结识了一些书友。第二天,便很快从书友那里借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午放学后,我和德武慢腾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精心酝酿“送书计划”和“采果行动”。想来想去,“计划”和“行动”同时进行,德武负责制造阅读氛围,把老何引入忘我境界,让老何忘记苹果园,腾云驾雾,到乌克兰谢佩托夫卡镇去,和保尔倾心长谈,我趁机进入苹果园。
接下来的一切按计划进行。没有想到的是,老何,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竟是一个超级书迷。他胸中装着的,不仅有土地和粮食,还有文学和精神!不到十分钟,他就被保尔那苦难的童年所感染,完全沉浸在故事情节中。
几块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辉,天色开始暗下来。距园艺场不远处是贵阳大队学校。学校操场挂起了白色的银幕,听说晚上要放映电影《洪湖赤卫队》,各家各户的男女正兴高彩烈地往学校聚集。
我不忍心打扰老何,给德武使了个眼色,沿尖包梁往下走。走到园艺场接口处,一下子把我难住了,只见几丛干刺手挽着手,站成一堵墙,有半人高,把路口堵得严严实实。要进园,须搬动刺丛,徒手是拿它没办法的,要用工具,铁制的最好,挪动力强,没有铁制的,找个木棍、竹棍也可以。
我在路口方圆五十米的范围内找了好一阵,什么棍都没有找到,正准备给德武发信号撤离的时候,一个小孩滚铁环用的铁钩走进我的眼帘,我眼睛一亮,如获至宝,拾起,回到刺丛处。有了铁钩,掀动刺丛易如反掌,没几下,就把刺墙弄了一个大口子。
夜色,像张宽大无比的幕布,悄悄拉上了,天上现出半个月亮,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苹果园,苹果园里的苹果树好像都睡著了。苹果树矮矮的,枝丫像伞一样张开,苹果就像它们可爱的小宝宝,躺在它们温柔的怀里。
那时,我营养不良,个子矮,走到苹果树下,那些顽皮的苹果冷不防敲敲我的小脑袋。我“生气”了,谁敲我,就把它“请”到我的书包里,一枚、两枚……很快地,书包鼓胀起来,衣服上的口袋鼓胀起来。我带着“丰收”的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匆匆离开苹果园。
我和德武踏着夜色,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边分别讲述着刚才发生的故事,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噬着美味的苹果,月光给我们铺展道路,青蛙给我们送来伴奏,萤火虫也出来凑热闹,在树上一闪一闪的,朦朦胧胧中,我看见了站在家门口的父亲。
回到家中,我先给父亲母亲讲了苹果的来历,当然不能照实说,重点环节必须“偷梁换柱”,否则屁股上马上要长出几个包块,然后把书包里的苹果拿出来,给家人分享。父亲吃着香喷喷的苹果,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人家送的,倒没有什么,要是偷的,我绝不饶你!”
三
我小时候还摘过橘子。
深秋时节,橘子就像一个个红色的小灯笼挂在树上,钓着人们的馋虫,尤其是小孩,怎么挡得住橘子的诱惑呢?
有一次摘橘子的经历还清楚地记得。
我刚上初中时,家离学校远,走公路,有二十多里,山路近一点,也有十多里,山路坑洼不平,崎岖难行,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往,感觉很累,所以每天下午放学后,总要和德武一起,到公社粮站、供销社等车辆出入重点地方去看一看,看有没有车辆回大队或附近的大队,哪怕能搭一段也行,多数时间是去了也白去,那时车辆少,何况小孩子又没有几个熟人,谁愿意拉你?但偶尔也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和德武像往常一样快速赶到公社粮站收公粮的地方,碰碰运气。刚到粮站大门口,就远远地看见一群人正围着一辆东方红牌拖拉机忙前忙后。我们连忙靠近拖拉机,在人群中寻找认识的人。我的目光很快地落到一个熟悉的中年男人身上:那不是我二姑父吗?他家住在贵阳大队,是生产队长。他正抽着烟,指挥大家搬运公粮。我上前一步,叫了他一声,他向我笑了笑,顺口说了声:“等会儿搭拖拉机哈。”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过了一会儿,老天爷突然变脸,天上乌云滚滚,地上狂风大作,四周鸡飞狗跳,拖拉机和交公粮的人火速撤离。二姑父也跟他们一起撤离了,离开时扔给了我们一条麻袋,说是大雨来了,可以挡挡雨。我们也想撤离,可撤到哪里呢?撤回学校,校门已经关上了,回家,又没带雨具,大雨来了怎么办?我们只能靠在墙角静静地等待。很快,指蛋大的雨点倾斜而下,砸在地上,开出朵朵水花。大雨像根绳子,死死地把我们绑在那里。雨小下来的时候已是街灯初亮,我们还在原地一动不动。有一个陌生人给我们送来了两个大馒头,说是二姑父安排他送的,还说下大雨了,机耕道坏了,拖拉机就不去贵阳大队拉粮食了,叫我们自己安排。
我们的肚子早已“闹革命”,接过馒头,狼吞虎咽起來。肚子问题解决后,我们一起商量晚上怎么办,我和德武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的共同意见是等雨停下来,然后沿着公路回家,因为公路路面宽,没有灯也可以走,顶多就是走慢点,反正明天是星期天。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我和德武坐在墙角处,每人轮流讲五个故事,轮了三轮,雨还是不听话地下着,浓浓的凉意向我们袭来,我和德武不得不钻进麻袋里,后来就在麻袋里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树上的鸟雀把我们叫醒,我们从麻袋里钻出来,踏上回家的路。
离开粮站没多久,肚子开始“造反”了。我们一边走,一边寻找着可以吃的食物。走到一个山嘴时,我们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大院子后的台地里,长着许多橘树,树上挂着许多橘子,便加快脚步赶到树下采摘。
这个时候的果子是不好摘的,一拉动树枝,树上的水滴就联合起来抗议,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把衣服弄个半湿。
刚摘下几个橘子,突然院子里的狗叫个不停,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拿了根扁担,边走边骂从院子里冲出来:“两个龟儿子,胆子太大了,大白天敢偷老子的果子!”我和德武吓得屁滚尿流,箭一般地逃离现场。我们在前面猛跑,那个男人在后面死追。突然,身后传来“咚”的一声,我们转过头去一看,只见那个男人仰面朝天,滚到烂泥里。我们扭头继续奔跑,到了安全地带才停下来。
那次盗果经历,后来在我脑海里反复上演,挥之不去。我想,假如那个中年男人把我们追上了怎么办,会让我们去“游街”吗?会把我们交给学校处理吗?假如那样的话,一切美好不都葬送了吗?一连串的问题,终于让我在盗果的路上停下了脚步。
记得智利诗人巴勃罗· 聂鲁达说过这样一句话:“漫长的童年时代,收纳了世间所有的现实和所有的奥秘!”盗果故事是我童年王国中的一座大厦。成年之后,我一不小心,就走了进去,进去时,有点雾里看花,出来后,正是霞光满天。
【作者简介】赵天秀,四川苍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作品;现居四川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