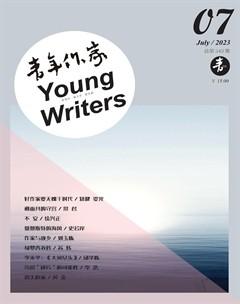姚美君
一
今早,我送孩子去上学,转向小学大门的马路口被堵成一片。阿女坐在后座,我没有望向她,但她一边很焦虑地踢着前座的背,一边气呼呼地噘起嘴,发出一些我不能忽视的声音。
我讲:“刚刚顾着玩贴纸不刷牙的是谁?”
阿女讲:“要是我的小红旗没了,就同你死过。”
这句搏命的话从女儿嘴里说出来,我很惊奇,觉得她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难道真的“女大女世界”?
我讲:“生得你出来,就不怕死。你怕迟到就跑过去喽,反正离得也不远。”
话音还没落下,阿女突然拉开车门,让本来缓慢行驶的车,不得不被我踩下急刹。
我骂她:“命都不要啦?”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而已。
她未必听得到。阿女试图大力地摔上门,来展现她的决绝和脾性,但毕竟个头不大,又不常运动,车门并没有关紧。她一脸错愕,又摔了一次,车门这才发出沉闷的声音。我看着她跑远,书包在她背上一颠一颠的,像颗傻乎乎的气球。我心想,她到底还是个孩子。
不遠处,两位交警站在马路上疏解交通,前头有两辆车发生摩擦,一个男人开着车门,与一个女人对骂。学生们赶着跑进校园,跟守在闸门的教学主任或校长一类的人物,机械地问好,一边又回头望那对吵架的车主,或许他们在观察陌生的中年男女,吵起架来和自己的父母究竟有什么区别?车龙仍然缓慢地行进着,喇叭声时不时响起,空气是微凉的,是那种属于清早的微凉,与拥堵嘈杂的情景极不相称,或许是我们做家长的,总要承担烦躁的生活,把琅琅书声留给儿女们。
就在此时,我收到了姚美君的回讯,她讲:“有空的话来找我吧。”我拉上去看聊天记录,有半个月,竟然都是我单方面问候她。我回复她:“好,我这就去找你。”我看了看时间,这么早起床,不是她日常的作息,她通常都是睡到吃午饭的时间。我只能猜测,或许她一晚上没有睡。
姚美君是我在新加坡读书时认识的女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克拉码头的酒吧。她坐在卡座里,很文静的样子,别人不问她话,她不会主动开口。我见她双手隐隐抓着沙发,可能对环境感到不舒服,就经常引她讲话,让她尽量多地介绍自己。然后知道她原来是潮州人,在我们一帮澳门人当中显得突出。为了照顾她,我们切换成普通话交流,结果一个个讲出来都是“煲冬瓜”,难听死了。她摆了摆手,用很僵硬的广东话讲:“真的不用迁就我。”她说自己从小就看TVB,也会讲一些广东话,再说了,她的普通话也不算好听。
我们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让她教潮州话,还说新加坡也有好多潮州人的,你优势更大。她也稍微兴奋了点,真的教起我们,先是“食饭”的读音,后来是对女性外貌的夸赞,然后是一些不能入耳的粗口,真可谓有求必应。但当她一字一句很认真地教我们粗话时,我就知道,她是毫无娱乐天分的,是那种适合一起做小组作业,而非玩大话骰的人。
带她来赴场的是朋友杨仔,他是酒场的熟客,经常打电话喊我们出去喝酒,留学生当中流传他是夜店之王,花花公子。我们一帮人和他算是老友,都知道他并非那类人,因为他从不带女仔来,甚至每次主动组起酒局后,他也不太招呼朋友们聊天、举杯或者玩游戏,属于很不称职的主持人。甚至夸张地说,他总是派对里最沉默的那一个,我们都笑他扮忧郁。
正是这样别扭的两个人,此后在我们的见证下,谈了八年的恋爱,还结了婚。显然,那时的我们预料未及,但与世上许多事一样,真正发生的时候,又是顺其自然合情合理的。他们的婚礼选在了澳门举办,我们一班老友当然出力相帮。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祝福贺卡上写的不是“百年好合”,也不是“修成正果”,而是“世界和平”。
二
姚美君和杨仔结婚多年,都没有生孩子。他们于婚宴上已经昭告众人,不必祝福“早生贵子、三年抱俩”,他们要丁克一辈子。当天话口一出,隔壁台上的四位长辈的面色都很难看,一副不知道该不该附和鼓掌的样子。倒是我们这一桌伴娘伴郎们,相视而笑。我心里暗暗佩服,唉,真就没有这对奇侣做不出来的事。
早在试婚纱的时候,我就听姚美君在抱怨讲:“如果要生孩子,我怎么甘心嫁入他们家?”
“也不能这样讲吧,你阿爸阿妈难道更开明吗?”我帮她拉上拉链,听她这么一说,想起了她那对父母——那对差点因为八字不是上吉,就反对这桩婚事的“老潮州”。
姚美君一边望向镜中的自己,一边把手抬起来,摸了摸上面的订婚戒指,讲:“天高皇帝远,我的手指都管不到,还想管我的肚。”
我笑了笑,赞叹她的广东话真是越来越熟稔了。她讲:“都是杨仔将我教识的。”我讲:“他可不单教你广东话。”
自从他们在一起之后,姚美君的作息也跟了杨仔走,终日陪他打游戏机,打到日夜颠倒,酒量也水涨船高,很快就练成千杯不醉的好本事。当然最明显的是,她的口齿越来越伶俐,越来越会交际,像是在填补杨仔的沉默,撑起一副女主人的派头。我们当中一些人还很嘴贱地说:“可能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日久天长,原形毕露罢了。”
姚美君突然转过身,牵起我的手,包进她的手里。她问我:“不生仔,很好啊,两人世界,多自由。不是吗?”她把我的手向下顿了一顿,像是在确定什么。
“你自己钟意就得啦!”我想,她其实不确定,但这是杨仔的意思。实话实说,杨仔怎么看都不是做爸爸的材料,虽然他工作起来,比以前读书勤力多了,但创业这事,本就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从毕业算起,他赔了多少钱我们都私下计算过,那笔数至少可以在横琴多买一套房了。况且他投资的都是一些游戏公司、网咖、手办,可见贪玩的生性还没有沉淀下来,要做父亲,是勉强了点。
“是喽,我钟意,最紧要了。唉,我将来要是变得和我爸妈一样,”她打了一个夸张的冷战,“想都不敢想,所有剩下的几十年生命都围着孩子转,太可怕了。”
“那你公婆他们怎么讲?”我刚生阿女一年,还处于母爱泛滥的时期,才不想顺她的话讲。
“他们也不愿意啊,吵了好几次架,不过杨仔还是争取到了他们点头。”她突然凑近我耳边讲:“有一次差点都要分家了,还是杨仔够狠,你知道的啦,他脸一塌下来,就跟杀手一样。”
姚美君得意洋洋地把拉链一拉,抖了抖,整件婚纱的上装就跌了下来,露出她上半身的裸体。她的皮肤在非自然的光线下,显得干净白皙,几近于透明,只有乳头那里贴着两片白色的乳贴,明晃晃的,像止血胶布一样。
犹记得读书时,有一次玩俄罗斯转盘,杨仔输了,喝了两杯“子弹”鸡尾酒,还要接受真心话挑战,我指着姚美君问他:“你最喜欢她什么?”他眯着眼端详,很严肃地讲:“身材……吧?”我们即时惊呼:“肤浅!”我讲:“人家堂堂才女,你居然就喜欢身材!”姚美君也脸红,但不是那种害羞的红,而是那种出热汗、有点生气的红。她反问杨仔:“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我们都着急地追着问:“是什么?”杨仔却一声不吭。她摸着杨仔的头发,从头摸到脸,又到胸膛,讲:“我最钟意你扮抑郁。”我们正想嘘她无聊,殊不知她又笑着讲:“但又真饥渴。”对于这个答案,我们当然心满意足。这时杨仔冷冷地讲:“你又没输,干嘛回答他们?”他一讲完,就环抱住站着的姚美君,示意她坐下来,那模样,就像小孩抱住了仅属于他的大型毛绒公仔。所以我们经常说,他们这对是孩子和玩具,一个贪玩,一个贪他的贪玩,绝配。
三
姚美君的身材确实很好,她自己也知道。她曾经给艺术系的学生做人体模特,倒不是缺钱花,只是觉得为艺术献身,是一件挺美学的事。所以当她在婚纱店的更衣室里,赤裸着上身,转过来跟我讲“真想这样站在婚礼门口迎宾”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意外,只是嘴上不忘骂她一句:“黏线!”骂完又捏了她一下,她倒是很开心,笑得发出类似鹅的叫声。
姚美君和杨仔结了婚以后,就住在氹仔一个房价不便宜的小区。我开车过了大桥,找到那个小区,又受了门卫的核查,才得以进去。小区的景观明显是欧葡式的风格,该有的雕塑、喷泉、科林斯式的立柱一件不少。楼栋下正好有一个喷水池,中间安置着一位裸露的女神像,不知是维纳斯还是谁?我估计,这套房的位置肯定是姚美君挑的,她最喜欢这些无用的艺术了,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她就总是拉我去看展。
上电梯的时候,我發了语音告知她我快到了,按下电梯楼层键,发现旁边那道划痕还在,它就像一根白色的头发,挂在那片棕金色的漆膜上。两年多前的一天,阿女被她爸带过海去香港迪士尼玩,我就约了一帮姐妹晚上出来喝酒,顺便讲讲各自男人们的坏话。结果那晚我被委以开车的重任,她们倒是杀了个天昏地暗,我却只是喝了几樽气泡水,还得一个个将她们送回家宅,安顿好。
姚美君是最后一个,她喝了很多,基本上我的罚酒都让她承受了,倒不是我狠心,只是我相信她千杯不醉,将她留到最后,也是想着或许还能帮我收拾其他醉鬼。谁知她后劲强大,发起酒癫来像巫婆作法,一边哭喊,一边挥着手,我扶着她进升降机,她却扒着门,死活不愿意进去。我只能哄阿女一样地哄着她:“乖啦。入来啦。”
我连拉带拽,把她拖进电梯厢,她一进去就用那双下午刚做好的“九阴白骨爪”,从上到下将楼层键按了个遍。我去抱她,她试图挣扎,一下就把那块漆膜划出细痕。我求她:“发个好心啦,你们小区很贵,我赔不起的。”
她倒是放弃了般坐在地上,慢慢抬起头看着我,讲:“你的样子好妈妈款,好贱格啊。”我不知道她这话什么意思,只当她是在开玩笑,一边伸手去捞她起身,一边反问她:“好,算是我贱格啦。妈妈款又如何啊?大小姐?”
“为什么你们今天都在聊育儿经?为什么啊。欺负我咩?”听出来她的声音多了哭腔,我只好拍起她的背,心想今天确实冷落了她一点,我们唾骂各自丈夫的时候,难免总会聊到子女。她三番两次想岔开话题都没有效果,我们也不如以前灵敏,根本察觉不到她隐约的失落。
我在玄关见到门口没有男人鞋,就按了门铃,却见到她家门上的艾草已经枯黄,发黑,想起她半个月前发的那条讯息:“死了。”我胸口一阵发闷。姚美君打开门,或许是见到我,微微笑了一下。我这才放心,问她:“怎么样,缓过来了吗?”
她又笑了笑,讲:“还好吧。”
我一边脱鞋,一边讲:“一个月时间都差不多到了,你从此就要解放啦。”我脱好鞋走进去,才发现她身上穿的,是我之前送给她的哺乳裙。裙子是粉色的,上面有小熊的卡通图案,最特别的是在胸脯前有一个帘扣,可以方便妈妈们翻开来哺乳。其实她穿起来挺适合的,衣服很宽大,能笼罩住她过度滋养的身体。好看归好看,我可不敢夸她。
“我婆婆要我养足四十天,讲这样保险一点。”她突然问我:“怎么啦?看着我干什么?”
我讲:“没有,哪有看着你?”我扯开话题,看向她家的电视墙。“你怎么看起《侏罗纪公园》了?你不是应该看《师奶唔易做》咩?”
“你才是师奶啊!”她将音着重于“师”字上,听上去就和“C”一样。
“知道啦,你是E奶。”我反击。
她低下头看,讲:“你羡慕不了的。”
“好好好,你最大。”
正当我为了她还有心情开玩笑而感到安慰时,她就叹了一口气,猝不及防。我只好讲:“来时买了两盒蓝莓,吃不吃?”
四
我先生问过我,为什么要在姚美君结婚贺卡上写上“世界和平”四个字?我跟他讲:“如果你见过她公婆就知道了,她们要是能相处得好,那就是世界和平,相处得不好,自然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不明白,这是最高祝愿。”
姚美君和杨仔在婚宴上说要丁克,引起了家族遗老的不满,即便他们未必一下就懂得这个词的含义,但要搞清楚也不难。席后还没送完所有宾客,姚美君就被拉到化妆间挨训,我作为伴娘,也只能在一旁看着。她婆婆讲:“有些事情焖在锅里,煮生煮烂都无所谓,反正时间消磨,得过且过;但要是捅开了戳破了见天光了,那就不好意思了。”
彼时新郎官已经醉倒,被人抬去婚房。姚美君只能孤身作战,乖顺地被指教了快半粒钟,虽然频频向我示意,表明自己的礼貌已经到了极限的地步,再不救场可能要火山爆炸,但我依然爱莫能助,莞尔谢绝。嘿嘿,姐妹,这就是婚姻给你上的第一堂课。
等她度完蜜月回来,我们出去喝咖啡,我又听她一直抱怨婆婆,讲她总会打国际电话来提醒,要多做几次才会中彩。她不无讽刺地问我:“是不是她老人家失忆了?我明明说了要丁克啊?”
我附和她:“对啊,做婆婆的,都是这样。有时装聋扮哑,有时耳聪目明。”
她夸我总结得好。我又问她:“不过,你婆婆怎么不去找杨仔讲?”
姚美君没理会我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讲:“你知道吗?我从机场回家,刚踏入门,她就一直打量我,从我额头看到脚趾公,好像在检查一只猪乸一样。”
当场姚美君就下了决定,她告诉我:“龙游浅水遭虾戏,他朝一日,本小姐定要搬出去。”我心想,哪有那么容易?于是提醒她:“这些你跟杨仔说了吗?”
姚美君大惊失色,换作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讲:“那我怎么可能说?我绝对不做挑唆母子关系的坏女人。”
我讽刺道:“哦,这才想起来要做二十四孝媳妇啦?”
当然,姚美君讲得出做得到,她努力做了几年保险和基金,后来又鞭策杨仔卖掉一些坏资产,才购置了这个欧葡式小区的房子,虽然听说还是有公婆很大的资助,但至少她这条龙确实游出来了,做了真正的女主人。我们周边的朋友都以为,好了,她终于过上她想要的好日子了,谁知没多久,她又开始兴风作浪。
讲起来还和我有一点关系。这么多年以来,姚美君和杨仔坚持丁克之家,可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对于孩子,不生就是不生。原本那些阻力,也正如那日我在婚宴化妆间听到的金句,“时间消磨,得过且过”——他们双方父母催促的热情都已经随着时日推移,逐渐冷却下来。我相信,如果不是那天的聚餐酒局,姚美君还会一直坚持当初的决定。
“你在家会无聊吗?”我给她端上洗好的蓝莓,问她。
“看看书啊,或者看电影咯。”她伸出手不客气地抓起一把,塞进嘴里。“反正这么多年,我都没出来做事,习惯了。”
“这位富太太,你找点事情做吧,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我的手机收到讯息,是公司領导发来的请假许可。我看她一脸无所谓,不知怎么,还有点微微生气,我可是请了假来见她,想说此时她或许需要姐妹的膊头靠一靠。
“富太太?呵。”姚美君一边冷笑,一边还看着电视机荧幕。“人生究竟为了什么啊?”
“你不要又问这一题啊姚美君,我答不了的。”我想劝止她,但这句话终究还是没能讲出来,因为两年前她也是这样问我的,一问“世界”,就要发生大事。两年前,就在那场大醉过后不久的一天,她突然约我出去吃重庆火锅,菜刚上来就跟我讲她和杨仔吵架了。我问为何,她讲:“我想要个孩子。”
我极度认真地问她:“你有病啊?”
“我在想,人生究竟为了什么啊?你看我自从搬过来氹仔之后,就没工作了,成日都无所事事。”
“杨太,做人不可以这么故意炫耀的。”我摆低筷子,叉起手望向她。“你无所事事,是因为你事事都得偿所愿。”
“乱讲,我策划的艺术展就没有成功。”姚美君讲的是她乔迁过后,某日突发奇想,计划在海事工房一号布置艺术展,她想邀请一些名星做跨界艺术,但不知道是明星的脾气太大,还是她对于人性的估计太简化,对自己的影响力又过度自信,总之响应者寥寥,甚至就连杨仔也不支持她,他们的家底还算丰实,但没有丰实到可以这样挥霍的程度。姚美君为此事也向我抱怨过杨仔——他一点都不有趣了,极度市侩,已经不再是读书时那个扮抑郁的男仔。我心想,还不是某人逼出来的。
我讲:“那也不能拿生孩子的事开玩笑啊。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傻妹。毕竟你们争取了这么久。”
“人会变的嘛。”她骄傲地讲完,又给调羹上的虾滑吹气。
我讲:“难怪杨仔会和你吵架,换我都会和你吵。”
姚美君沉默了,似乎我不应该帮她男人说话。“他是不是找你劝我?”她往前倾了倾身子,像要审讯我一样。
“没有。你见我十年来和他说过几句话?”其实她估中了,杨仔确实联系过我,但只不过是给我发了一句话:“帮我劝下她,求她不要发癫。”我不明所以,本想今日吃火锅顺便问清楚,但现在我只好按下不谈,因为要是说出去,那就会天崩地裂:一个姐妹,居然敢背地里和自己男人瞒着自己,是可忍孰不可忍。
犹记得杨仔求婚的时候,正是我帮了他,将姚美君骗出来逛街的,这才有他香槟玫瑰蜡烛大阵法,求婚那晚当然人人感动,又泪又笑,但事后姚美君竟然向我追责,还毫无羞耻心地讲:“你被求婚时我可提前告诉你了。”谢谢你呢,让我一点惊喜都没有。求婚这样善意的谎言尚且遭恨多年,更遑论现在去当他的说客,那简直是要被钉上耻辱柱了。
正当我以为这事不了了之的时候,姚美君转个身已经说服了杨仔,还以为自己很犀利。“我跟他讲,女人比男人的寿命长,将来你死了,谁照顾我?”
五
有一次,姚美君发了一张相片给我。我一打开看,原来是她肚子里的胚胎B超彩照。细细粒这么一个,就像一颗蓝莓。我知道她花了大半年积极地备孕,不单自己清淡饮食,还让杨仔戒烟戒酒,就连在我们的酒局上也只喝气泡水,甚至被我翻着白眼揶揄道:“知道那晚我的心情了吗?”她也毫无抵抗之心,笑吟吟地讲:“激将法,本小姐不受的。”
今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我祝贺她,但我又知道,她未来的关卡还将一山放过一山拦。
比如她的公婆,他们很高兴:“你们想清楚了固然是好。”但他们肯定也担心,这两个前酒鬼生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讲:“如果有什么病况,还是不要拖累到他。”也不知道这个“他”指的是孩子,还是杨仔,抑或是他们两公婆自己。
另外就是姚美君的父母,他们风尘仆仆从潮州过来看望她,其中一个差点在过关时中暑,还是我送去医院的。他们也是一边祝贺一边担心,只不过担心的,不是她肚子里的宝宝,而是他们女儿到底能不能撑下去,还数落她:“早让你生你又不生,好了好了,非要熬到现在三十多岁,做高龄产妇你才满意。”
姚美君没有一句反驳:“满意,我很满意。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她跟我讲自己是甘心承受这些的,只是杨仔有时听到了会不忿。他比任何人都要生气。我知道,他们夫妻因为要孩子,已经有原则问题上的拉锯,又在备孕时加深嫌隙。
姚美君讲,她会控制两人性行为的时日,她家里那本台历被她画得花花绿绿,这都基于她所搜集的大量资料,有科学的,也有不那么科学的,更多的是介于科学与不科学之间,比如受孕时的姿势、气温,乃至星盘和潮汐运动。那些因素,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看来,根本不重要,但在她姚美君眼里,都是至高信条。她一一照单全收,活脱脱将他们这对唯物主义的新潮流夫妻,变成另一种“天赐麟儿”的信客。尽管这一切鸡零狗碎的事务都承受了,他们还要遭到父辈们的冷嘲热讽回马枪,依杨仔的性格,他自然是最顶不住的。
我问姚美君如何处置这些矛盾?她却讲:“我和他讲了,生孩子之前我们两夫妻吵架,那吵就吵了,我们一气呵成,全部吵完,不要留首尾,但宝宝生下来之后,我们就得做模范父母,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听她说这番话,我真是啧啧称赞,心想,你也真是奇女子,非杨仔不能娶也。
就在姚美君待产的这几个月里,她的身材更是丰腴起来。有一次我们去看望她,给她带去各种礼物,有尿片、育儿书、宝宝的衫裤和韩国产的吸奶器,当然还有那件哺乳裙。我拆了包装,将裙子抖落给她看,讲:“你别嫌丑,将来一定会用到的。”她很高兴,高兴之余问我们:“我是不是肥了很多?”
我讲:“怕什么?为了它,值得的。”我摸了摸她的孕肚,隆起得不算太大。
姚美君一边舀着鱼胶,一边讲:“我觉得营养都被我吸收了,他都没怎么吃到。”我和其他姐妹们对视了一眼,彼此都心照,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姚美君了,她身上泛着一种淡淡的母意。
这些或许能回答那个问题: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可没等我回答,姚美君就对我讲:“你脸上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脸上?她伸手帮我摘下来,我一看,是阿女今早玩的贴纸,是某个少女卡通图案,粉红色,上面还带着金粉。
我尴尬地笑笑,只好佯装愤怒道:“都不知她什么时候贴上去的,真是衰女包。”
“你看,你有个女,真好!”姚美君深深吸了一口气,又装出客套话的口吻对我讲。
“哎呀,好烦的。日日都要担心她。”
“是喽,这不就是人生的意义吗?”
我顿时哑言。
“有些跑道,我输得见不到前面的人影。”她的眼神落在窗台角落,我也循着去看,原来是朋友们送给她孩子的那些礼物,各类玩具、衣物、尿片,还有一部学步车。之前来做客的时候她讲过,等孩子出生,她要让这个角落作为背景墙,给他拍张照。我们当时只以为是玩笑话,没想到她这样真切地记挂着。
六
姚美君早产了,其实早产的风险我们都已经预备了,只是没想到宫开的日子,比预估得还要早。记得有一次杨仔没空,我去陪她产检回来,她还轻轻笑了一声,讲:“看来我织的帽子,都太大了。”她的笑声听上去很苦,这种苦由无奈垫着,更有一种坚实的残酷,是世上所有做母亲的,都不忍听见的。
我去看她,当我走去厨房,将装过蓝莓的盘子过了一遍清水,放回底下的抽屉式消毒柜,起身抬头时,见到炖汤机已经冒着烟,正想出去问姚美君,但一踏入客厅,就望见她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眼圈发红。我心想,不是吧,看《侏罗纪公园》也能泪目?我一看屏幕,原来是小恐龙在保温箱里破壳的那段戏,几个人类正围着一头小恐龙发出慈母般的哄玩声,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下,仿佛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奇迹。
我过去坐在她旁边,就像当时在电梯里一样,轻轻地抚摸她的背。她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也什么都不敢问。是的,只要她不主动开口,其他人也不必出声。这一点,我还是了解姚美君的。
“你知道吗?孩子出生之后,只是被护士按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就送去NICU了。我甚至都没听到他的哭声。”
“你知道我隔着玻璃看他在保温箱里,他身上插满了各种奇怪的管道,他才多大啊,那么小的一个小生命,刚出生就要被这样对待,我恨不得被插的人是我,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睡在产床上,多难受吗?我连他的房间都已经涂成蓝色了,上面还贴了好多好多星星,关灯就会发亮。你知道的,从前,我还嘲笑你阿女的房间这样设计很丑。”
我以为姚美君会哭着,抱着我讲这些话,但她没有。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她讲出来,这样我才可以告诉她:“我都知道,我明白你的痛苦,可你要好好撑下去呀。”
姚美君坐在沙发上,只是轻轻地哭着,很有节制,在流了几滴泪以后,她就尽量不让眼泪掉下来了。
“怎么了?”我很惊讶,赶忙问她。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好像这样便可以将方才的哭泣抵消,正如半个月前她也是这样沉默的。半个月前,她发给我“死了”两个字的时候,我正哄阿女睡觉,一看到手里的文字,触目惊心,发去问她:“怎么了?”等阿女睡着了,我还没看见她回复的讯信。
我又问她:“怎么不回复我?别吓我。”
“对方拒绝了你的通话要求。”三次。我正担心着,杨仔却发来讯息讲:“她没事,回头讲。”他这样说,我反而隐隐觉得不祥。我见过姚美君发在朋友圈里宝宝的照片,他闭着眼睛,脑袋如同放久了的橘子一样发皱,通红的四肢又瘦又干,他的嘴部插着透明的管道,胸前贴着两张白色的电极片,因为被放在保温箱中,活像个外星文明的动物。姚美君配在照片上的文字写道:“妈妈和你一起加油。”和这张照片一起发出来的另一张照片,是好几张诊断书。我将诊断书发给一些医学界的朋友,他们话糙理不糙,都讲宝宝太脆弱了,夭折是合情合理,不夭折就是奇迹。
“可是宝宝夭折了就再生一个呗。”我心里这样想,但又不忍问她。我看着姚美君,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样子,如今已经是另一种别扭。她沉默着,木然地盯着电视机,里面的小孩们望见了高大的雷龙,正发出赞叹声。那声音将房间里的空气衬托出寂静来,更令人不安。好在厨房里的炖盅机响了一声,可能是什么东西煮好了。我問:“等你想说了你再说,你煮了什么?我给你舀出来喝?”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拿抹布挪开炖盅的盖子,用勺子一撩,木瓜、鲫鱼,我用勺子压开食材,只取汤水,汤水上浮着一层脂肪泡泡,它们一颗颗挤在一起,就好像细胞的群落,似乎只要经过某种序列的组合,就能孕育成一个胚胎。我将汤水舀进碗里,忽然才意识到,木瓜和鲫鱼,都是一些催乳下奶的食材,难道她的宝宝并没有夭折?
我端着汤到客厅,姚美君站起来,接过去喝了一口。她皱着眉,讲:“真的好腻。我前面三十多年喝的汤,都比不上今年的。”没等我接过话,她又笑了笑,讲:“不过还好,我早产,比你少喝一个多月。”“别这样。”我轻轻拉着她的手。
七
“我刚刚还想问你,为什么要喝木瓜鲫鱼汤?”
“这样乳水多点嘛。我量挺少的。”她摸了摸自己的乳房,就像摸到一张只能打出去的麻将牌,难掩脸上的失望。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功效。”
姚美君把汤一口气喝完,抬高手背擦了擦嘴,讲:“现在宝宝已经可以喝母乳了。”
“在保温箱里面?我还以为只能输营养液。”
姚美君没有回答,只是把碗放下,望了望时钟,将手伸到茶几底下,拿出一个物件。我一望,是那个韩国吸奶器。“你帮我拿个乳袋,就摆在冰箱里面。”
我讲:“用这个,很损身体的。”她摆了摆手,明显不想浪费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我只好起身走过去,打开她家的冰箱,却见到有一层满满当当的,都是装了乳水的塑胶袋,有大包有小包,它们整齐地排列着,像影片里面的高科技物资一样,极其冷感,我惊叹得连下巴都跌低。每一包母乳都清楚地标注了日期,但最远久也只是半个月前,奇怪,她为什么能产这么多乳水?
我拿了一个袋子给她,故作无所谓地问她:“宝宝的情况好吗?几时可以出院啊?”我还是不太相信,她的宝宝没事。
姚美君表情明显停滞了一下,很快又坦然地撩开哺乳裙的帘,支起吸奶器。“我不知道,反正我能做的,就是留奶水给他。”
你会不知道?那你说“死了”是指什么意思?我走到落地窗边,越想越气,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我望着远处的海,那无垠的深蓝色令人厌倦。我还是信我的直觉,转过身问她:“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没什么问题,我就想问你,男人为什么只顾着自己满足?”
她的眼神空洞,面部平静,这副神情令我想起她在怀孕初期时,跟我要了很多养胎的秘诀和配方,我讲:“你们潮州人不是最会养胎咩?”她讲:“那也要讲究博采众长的。”过了一段时日,她的烦恼明显有了转向,有一次她问我:“他想那个,可是我怕对宝宝不好,怎么办?”我伸出两只手指,比作剪刀“咔嚓”的样子,讲:“阉掉。”她明知道我是开玩笑,却故作认真地回答:“那可不行,还有用。”
“你堂堂高龄产妇,杨仔也太不为你着想了。”
“他同我讲,是不是有了宝宝,我心里就没有他的位置了?”姚美君叹了一口气,但又讲:“不过,他这样吃醋也挺可爱的。”
我听人讲过,有的孕妇生完仔,会得抑郁症,难道短短数月,姚美君对两性大道理的思考,已经飞跃进步?不过,我宁愿她问我房事,都不要问我人生的意义。
她突然吃痛地发出咬牙切齿的一声,或许是吸奶器频率开太大了。我看了一眼,竟然有一点血丝。
以前我生了阿女,经常向姚美君抱怨喂奶会乳头皲裂,痛不欲生,姚美君每次都是不近人情地嘲笑我,嘲讽我是一部人奶机器,还讲:“怕痛用奶粉不就够了。”殊不知风水轮流转,她也成了母乳的拥护者。只可惜她分娩之后,宝宝被送去新生儿重症病房抢救,后来又交给保温箱,没有她施展的天地。
“你都肿了,”我劝她,“别用了。”
“我全部都要留给宝宝,一滴都不留。”
“又没人同他抢。”我挪开她的手,将吸奶器从她的乳房上卸下来,望见姚美君的眼又红了。这时,我听见她沉沉地讲了一句:“我要离婚。”
“为什么啊?”
“他强奸我。”
“杨仔?”
“嗯。我根本就没心情,他偏要。”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就打趣道:“男人嘛,在自家吃,那也总比去外面偷吃好。”
“他还抢了属于宝宝的奶水。”
“你是说……”我望向她的乳房,她点了点头。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他嘴上还讲是为了安慰我,但多年夫妻,他一碰我,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那一刻,我觉得天旋地转,好像从胸口涌出来的不是乳水,而是血,是泪水。”我望着连接吸奶器的瓶子,乳白色的液体中,我似乎能看见姚美君所讲述的那个夜晚,或许那是世上所有妻子们共有的记忆。
“你帮我找个律师吧,我这里不熟。”我能听到她声音里的慌张。
“傻妹,离婚也未必需要律师的。再讲,你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还有,拜托你想一下宝宝,你想他将来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吗?”没有人比我有资格质问她了,那句“就像我阿女一样”,我已经不需要讲出来。
姚美君清楚的。她欲言又止,仿佛在找话说服我,或者说服自己,她握着我的手,顿了一顿,像挑婚纱那天一样。她着急起来,不断地跺着脚,像疯魔了的钢琴家,我甚至觉得好笑,没想到她会讲出来接下来的话:“但是……宝宝死了,他死了,半个月前就死了……我真的好难过,而且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就因为杨仔怕我伤心。凭什么都是他决定?他在我这么难顶的时候,非要提醒我……提醒我宝宝死了,还讲,没事我们可以再生一个。”
我缓慢地抱住姚美君,我的眼泪却不知何时冒了出来,她潮湿的呼吸声在我耳边一提一放,她讲:“结束的时候,他拿浴巾擦我的身体,我望着我的胸,是那样陌生,荒凉。”
我抹掉眼泪,轻声讲:“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去睡一觉吧,睡一觉就帮你找个律师,就找我以前那个。”
过了一阵,姚美君的呼吸声渐渐平缓,我估计她在我膊头上已经睡着了,我缓缓将她扶进屋子,她半醒半睡地发出两声,恐怕还是没能抵抗睡意。
我给她盖上毯子,想到哄阿女睡觉的时光,觉得姚美君也不过是一个小女孩而已。
我离开了姚美君家,和那个有损痕的电梯间,当然也包括那个袒露乳房的女神像。当我开车经过嘉乐庇总督大桥,由氹仔回到半岛时,大桥两边的海水,被正午的太阳光照得明亮,水波推过去,犹如一道道妊娠纹。我心想,如果浪潮退去,能顺便带走它们,那也是大海的功德一桩。
【作者简介】黄守昙,1994年生12月于广东汕头,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作品见于《上海文學》《香港文学》《诗歌月刊》等刊,曾获澳门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