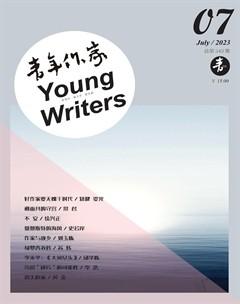过往车厢
一
很高兴白迪能看见我和索米在一起。说来也巧,我和索米从家具城出来刚上地铁就遇见白迪,不过让我略感失望的是,他似乎并没太在意,当时他手拎红酒去关口路阳光小区会见女友,我都不好意思问他是哪一任女友,几年前他放棄结婚要去四处周游时,就有新女友来给他送行。
相比之下,我更为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索米深感骄傲。我还告知白迪,我打算明日陪索米去乌山云顶看日出。但是说完我就想抽自己嘴巴,因为高出我一头的白迪习惯性地越过我把目光投向索米,并表示想和我们同去,他说前段时间出了车祸,捡一条命后忽然明白什么才是他今生最该做的事。我断定他这话是说给索米听的,不过索米始终没看他半眼,回家后告诉我,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白迪。我们当下决定次日改去霍山崇寨游玩,一早就走,并通知了我的弟妹和索米女儿筱青。
让我吃惊的是,天刚亮白迪的车已停在我家门口,而且就他一人,他称已和女友分手。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对我改变路线一点也不惊讶,似乎早知我会来这一手。他笑嘻嘻地帮我拎了行李丢上车,说他和我们走一段,到箐山六里丫口分手,他自己去乌山云顶拍日出。
我将信将疑,又不好拒绝,但我不会让索米和筱青上他的车。我故意对白迪表示她们嫌他的车脏,白迪无所谓,也不在乎我有意不坐副驾驶座,粗糙的大头鞋点着油门上了路。他开得很快,不到中午就甩开七永乡进山了。我坐在后排不停地喝饮料,早上我特别口干,白迪知道我这个特点,车上备了好多饮料。接着我就有了尿意。那时山道弯曲迂回,三转两不转,我憋不住,叫停车。山上风大,吹关了车门,狗日的白迪误认为我已上车,一溜烟开车走了。这可苦了我,当时我的尿撒到弯道下搞野炊的旅人饭锅里,一伙人冲上来发疯般围攻我,我又是个胖子,跑也跑不动,左遮右挡,高喊救命,最后索性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一伙人这才罢手,慌慌张张求我不能死。
我称浑身疼痛,估计大腿骨头断裂。我要赖上他们。一伙人商量后把我抬上车,送到前面箩尔镇石门诊所,然后装着要上厕所,一个个溜出门上了车。车发动一刹那又熄了火,白迪把车横在路中挡住了他们。
我喜出望外。一伙人跳下车蜂拥而上,围住白迪的车,拍打车门要求让道,不然砸窗拖下来打个半死。我为白迪担心,毕竟对方人多,有人拿着钳子,甚至有人捡了路边石块。我不能不佩服白迪,他不慌不忙下了车,一脚踢开咆哮着要撕咬他卡其布衣裤的土狗,又薅开伸向胸前的无数只手,也就是眨眼间,他已放翻两个人,等一伙人安静下来,他开始和他们谈论我的赔偿问题,不赔不准走!
一伙人无奈,丢下赔偿金离开。这时我的家人也赶到,大呼小叫,都怪白迪不该让我喝饮料,真的,连我也怪他不劝阻我,不知道我不能跟他比?不光不撒尿,过去一路吃蛆吃蜘蛛都不会拉肚子。我边说边叫家人拿根棍子来,我实在讨厌那只不停狂叫的破狗,在我看来,它应该朝毫无作用的坐诊医生去叫,从我进来,老东西一直眯着眼打瞌睡。是呵,全家人开始责怪白迪不该带我来诊所。我真的没想到白迪竟然一言不发,几年不见,他脾气变好了?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默默抽完一支烟,吐掉烟蒂后对我说他能帮忙治腿。不要不要,我缩在床上抱紧身子,真的担心他趁索米不在废了我。白迪非但不听,还上来叫我躺好了不要动,一边捏捏我的痛腿。我哎哟乱叫,弟妹们冲上来呵令白迪不要乱来。白迪可不管这些,盯着我说,不想治,他就走。我当然要治,我奇怪经他一捏,疼痛感轻了些,猛然想起他原先跟江湖医生混过。但我警告他轻点,我和他不一样,他经常搞户外运动,脚练得像熊掌。
白迪从门外扯了些花花草草放进桌上大茶缸里,叫四弟买来半瓶苞谷酒,他端起酒瓶灌进嘴,咕噜咕噜在口里涮半天吐进茶缸里,一扬手抓住飞舞的苍蝇,我眼花缭乱中又见他捉了角落几只蟑螂一同甩进茶缸,我强忍恶心看他盖住盖子摇晃茶缸,把酒倒在我腿上来回揉捏,然后一拍我说,可以下床了。我小心翼翼站起身,竟然真的好了。全家欢呼起来。
继续上路。
白迪告诉我,天黑前能赶到康亚镇,那里山高谷深,能听见拉丝河的咆哮,今晚只能住那里。他叮嘱我们晚上不要外出,镇周边亮点闪闪,都是狼的眼睛。我赞同明早分手,我想晚上请他和我家人吃顿饭。白迪不反对,他说这些年在路途上乞讨过,给人卖过葱蒜,也在小城里开过黑车,回想起来,还是和我在一起时愉快。
白迪踩下刹车避让暮归的牛群,重又启动后,他说看得出我这些年过得滋润。这话我爱听,除了告知他我准备和索米结婚外,也谦虚表示不过是有了自己的公司,蓄起三羊胡子和这个有关,总得讲讲威严嘛。同时我也没忘了恭维他,我指一指后座上的尼康相机包,说你总算在干正经事了。他建议我还是按原计划同他一起去乌山云顶看日出。不,不,我叫他不要劝我,我说霍山崇寨那些散落山谷里的黄色木楼是我现在向往的地方,据说寨里会打着手鼓欢迎客人,在长桌宴上收到当地姑娘的香包,会带来好运。白迪笑说那里已经完全商业化,都是做假骗人钱的。我说我喜欢商业化,大家都得找点钱嘛。
二
我没说昨晚劝索米改去霍山崇寨时,她一脸的不舍。我知道她一直向往乌山云顶,第一次听白迪说起日出中乌山云顶的雄奇山势她就神往,连我都跟着摇旗呐喊表示想去。当时我还是知青,我们三人坐在半山上我的住处,我告诉索米白迪是我老朋友,其实我认识他还不到半天。
我是在七桥孟口镇赶集时认识他的,说来也丢脸,那天我走进集市正逢江湖医生小炳在兜售可防刀枪不入的汤药。这的确让我心动不已,因为我在队里常受欺负,当下就买了好几瓶服用,随即便去附近建筑工地寻衅滋事,结果被人家用砖刀拍得皮开肉绽,待我返回缠着小炳索要被骗之钱时,反被其扭了双手叫嚣着扔进旁边的洗马河。
从镇外流来的污浊河水在我脚下吐着黑泡,看着都恶心,我死命挣扎大喊救命,正是我的溪城口音引来了白迪,我不会记错,他是顺着左岸过来的,不时撩开垂在眼前的长春藤。
那时的白迪还是小崽,截一顶“月贡帽”(月贡帽,方言,当年小混混喜戴的帽子。),高挑白净,斯斯文文,可是行为却野蛮得要命,上来就要小炳放过我,对方不听,他便从斜披着的衣服内取出刀抵住小炳,那可是相当于《水浒传》中的朴刀,吓得我汗水一股一股冒。白迪威吓要割下小炳耳朵时,他放了我。我向白迪表示谢意,小炳却带了派出所所长来抓人,我们赶紧逃,临跑时白迪没忘了从摊上钵钵里抓一把钱。我们一直跑到卖碗的王麻子家后门才停下来喘气,附近是打着石碑的作坊,和飞舞着一群苍蝇的肉摊。白迪斜靠着墙问我,遭抓住咋个说?我老实回答: 钱是你拿的!我又气又觉滑稽,忍不住笑,他也笑,还仗义地把抓来的钱分我一半。他说他在附近塘口插队,趁赶集来找点钱。他怕我不懂,特意说明找钱就是“打镚”,进一步说明就是摸包。听得我直咂舌头,这可不像我,我可是老老实实凭劳动挣工分过日子,劳累一天,晚上还亮着电筒下山给队长儿子补习功课。就算有点小毛病,也顶多在旮旯里捉只老母鸡来补身体。
不过我不反感他,反而觉得他有点好玩,一根舌头翻进翻出会说得很,很快让我晕头转向,真舍不得和他分手,买好菜后邀他去我插队的六里坪玩。白迪也是兴冲冲随我到了半山上的家。临上山前,我还特意敲响树下挂钟通知在民小代课的索米来见老乡。我放下菜,先对着镜子把鼻孔里的杂毛剪个一干二净,又忙叫白迪赶紧打消冲凉的念头,山上缺水,要从山脚井里挑上来。
索米来时太阳已快落山,脸红通通的,不停用手扇着汗,说正教学生跳舞。白迪说他想学,原先他一直喜欢看别人跳。索米就示范给我们看,一抬长腿踢开横在前面的扫帚,不料飞起的扫帚却碰爆了悬吊的灯泡。我赶紧让他们去院里跳。索米要白迪跟在她身后,双手搭着她肩。我忽然也想学白迪,可以贴着她,跟着放声高唱。我们六只脚在地上吧嗒吧嗒跳动,尘土飞扬,山摇地动,白迪却薅开矮胖的我,叫我不要混杂其间发憨气,赶紧去做饭。我一缩身子,乖乖照办。
当晚月光很好,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着青椒炒玉米、芹菜豆腐干、韭菜炒鸡蛋,还有一碗小瓜肉片汤。
白迪却说将就吃。我奇怪索米竟然不准我吐舌头,以往她说最欣赏我这类根正苗红的工人子弟,而现在她却无不羡慕地表示,看白迪细皮嫩肉的就知是个讲究的人。白迪承认自己不喜欢在队上劳动,又累又挣不了几个工分,他喜欢四处游走。白迪就是那时说起乌山云顶的。他表示近期想去乌山云顶看日出,真的,他从图片上看到过,雄奇壮丽!索米制止我帮她夹菜,不要挡着她,她闪亮的双眸盯着白迪,不吃不喝吮着筷子,半晌后,她说原先也听说过乌山,一直想去。说得我也心动了,问怎么走?白迪吐掉辣椒皮说,在五里冲爬上凌晨两点从矿山开过来的小火车,到林沙站下,换乘绿皮慢车到雕城,再转坐班车进山。听得我连连惊叫。索米却兴致勃勃问要去几天?三天之内没问题。他俩越说越当真,并不劝我,似乎根本就希望我不去。
这可让我不太安逸,我忍不住告诉白迪,索米无非就是说得热闹,平时见谁都躲,怎么可能和他这个陌生人去乌山?我料想不到索米竟然会掐我一把,而这点可没逃过白迪的眼,他愉快地挪动小板凳凑到她跟前,往她碗里夹菜时,握住她的手说,今晚就走?我闭上眼又睁开,确定没有看错,他真是明目张胆地握住她的手。
我心惊肉跳后又一时焦躁不已,我喜欢索米这么久,平常半点邪念都不敢动。我屏住呼吸,等着她扇他耳光,扎实响亮的那种。不料索米只是害羞地把脸扭向一边,还微微地笑。这让我非常失望,看来我太不了解她了,原来对付她就是要痞里痞气。我忽然醒悟,上去挤开白迪,劝索米留下,我俩好度快乐日子。边说边握住她的手,并且非常嚣张地顺着竿子往上爬,触到她身体……
忽然“啪”地一声,我的胖脸挨了索米一巴掌,没错,是她扇的,干脆利落。我还没完全清醒,索米一下跳起身,怒斥我和白迪拿她当什么人啦?她扭头要走,白迪赶紧上前拉她,被她一脚踩得嗷嗷叫。白迪来不及生气,她转身时碰倒院中木架子,摇晃着砸下来,白迪眼疾手快推开她,自己被砸得呲牙咧嘴。
索米迅速上前问伤到哪里没有?我赶忙分开他俩,没有听见山下狗叫?队长来接我去给他儿子补习功课了。白迪显然巴不得我走,他一再叮嘱我认真育人,反正我这里也没有值得他偷的东西。我知道他还想继续约索米同行,看来他认准了索米会答应。我恨得牙痒,发誓不会让他得逞。
我叫白迪立马走夜路回塘口,我说队长习惯在我这里听半小时收音机,他可见不得知青住地有生人,他才不会和哪个讲道理,先抓起来扇够耳光再踢粪门,然后押到公社仓库地下室一关就是几天。索米也劝白迪走。我叫白迪从屋后走,翻过山就没事了。
我可没料到索米会提议给白迪引路,眼看他牵着略带扭捏的她消失在屋后,我忽然担心两人会一起去五里冲,急忙追上去,不管不顾放开嗓门高喊,索米,队长找你!我喊得格外响,索米当下闪离,白迪一把没拉住,猛跺脚说想掐死我。
狗东西又细又硬邦邦的双手箍住我,我双脚后跟离地喘着气求饶,白迪放开我,他要回去找索米,我说她肯定和队长在一起。白迪不管,要我想办法缠住队长。我保證一定成全他俩,同时心里拨动别的算盘。我一本正经把他带到厨房后面工具房里叫他等着。我快步下山找到队长,如此这般一说。半个小时后,我走进工具房,窸窣一响,白迪激动地扑上来抱住我,唉呀叫了一声僵住了。我拉亮灯,强忍恶心看着赤身裸体的他,故作奇怪地问,索米没有来?刚才明明讲好到工具房的嘛。我说我是特意来给他们送垫子的。白迪沮丧地正要穿衣裤,屋外有响动。来了,我俩眼光一碰,白迪非常麻利地薅开我,另一只手抓住门一使劲,哪里拉得开,门已从外面反锁上。我一跺脚,说遭了,快跑!
白迪慌忙裹了衣裤跟着我扑向窗口,噼里啪啦砸垮封死的窗框,探出头去,不由倒抽一口气。院里站满了人,队长正指挥大家进屋抓人。白迪赶快裹紧衣裤,笑嘻嘻迎着跨进屋的队长说你好,一伸手,衣裤掉地。队长高喊把流氓捆起来。白迪连忙声明只是想在屋内洗个澡,不信问我。民兵们不由分说捆了白迪,他急得直跳,被一棒子打弯腿跪下,还急着要我倒是说话呀。人家嫌他啰嗦,捡起袜子塞进他嘴。
我一下觉得此时站在队长跟前会让白迪怀疑是被我耍了,立马闪身下山去队长家。在得知队长已把白迪带回公社关进仓库后,我又于心不忍,毕竟他帮过我,左思右想,最后溜出队长家去仓库放了白迪。他非常感激,抱着我连说好兄弟。这时身后噼里啪啦飞来密密麻麻的石块,我和白迪赶紧抱头逃窜,他倒是手长脚长跑得快,我却被抓住,队长翻脸不认人,一脚把我踹进地下室仓库顶替白迪。我后来知道,白迪当晚去了民小找到索米,两人连夜出走。我那时真是悲痛欲绝,发誓再不理他俩。
三
车抵达群山环抱的康亚镇已近傍晚,才下过雨,路灯下斜坡街面白晃晃一片。白迪把车停在嘎口巷拐角处的饭店前。我喜欢这里,不光静谧,还可以住宿。店老板拉我避开天花板上掉下的一片灰尘,说他这里相当于准四星,每间屋子都是观景房,月亮升起时可以远眺峡谷,呼吸雨后林木的芳香。
老板表示九个房间是有的,单间在镇东分店,不过放心,有专车接送——当然是马车啰。我觉得正好安排白迪住。我向陆续赶到的弟妹们建议今晚就住这里。一边揽过索米告知请白迪吃饭的打算,索米不置可否。我很高兴,她现在样样事都为我考虑,平时我说需要独自思考公司的事,她便立马出门,无论刮风下雨,十一点以后才轻手轻脚回来。
接下来家人开始点菜时,老板却是一脸尴尬,一问,方知店内厨师刚接电话,儿子被狗咬伤,厨师丢下锅铲走了。老板只好请我们去别家。弟妹们顿时叫起来,跑了一天实在不想动了,再说一路走来,街上黑灯瞎火没有店铺营业。我揽过老板一阵叽哩咕噜,对方同意收一定金额,让我们用店内食材自己做。我转向索米,她说没问题她来做。她一边把削了皮的苹果递给我,并表示刚找到水果刀,慢了些,不要生气。她弯腰帮我换上拖鞋,我啃着苹果,叫她不要忘了擦擦皮鞋上的泥。索米笑着端来一盆温热水放凳子上,她知道我吃完水果后,晚餐前必须要在水盆里练习憋气,雷都打不动,这是我跟原先隔壁丁二哥学的长寿秘诀。索米附在我耳边叮嘱用家里毛巾擦脸,毛巾是从紫色行李箱里拿来的,她带了红色绿色各五块。说完转过身子围上围裙。
我叫弟妹们搭把手帮忙洗洗菜,可她们个个装憨,围着大铁炉子埋头玩手机,包括她女儿筱青和男友。
索米叫我不要张罗,她可以的。我把脸埋进水盆,仍听见弟妹们嚼着香蕉一连声喊,索姐炒香点哦,农家老腊肉切薄些。筱青男友嗓子最尖,说他不吃葱不吃蒜。
厨房里响起洗菜声。
我揩净脸上水时,白迪唱着歌走进屋来,他才洗了车,手上水淋淋的,谢绝我递去的纸巾,说是你连打两个喷嚏,留着自己用!还说在山里要当心,中午热死人,太阳落山后又冷得要命。他边说边伸出手来夺过我手中的毛巾去揩手,我稍愣片刻,感觉他是冲着索米的味道来的,不由觉得好笑,他也跟着笑,歪着头听一听厨房水声,很不满意。半天了还在洗菜?听我说了原委,他说他去帮忙,他炒得一手好菜。
慢着,筱青上来挡住白迪,又扯了一扯我衣袖,悄声说,你憨啊,你怎么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
我笑说赢得你母亲靠的不是外表。同时提醒她不准把我的菊花茶端去给男友,我见不惯。
喂——白迪手掌按着我肩把我转朝他,笑眯眯说,你放心我进去?
他的优越感着实让我不舒服,我拼命摇头,表示没有哪样不放心的。
我心里清楚,现在的索米可不比原先,去年她离婚遇见我,知道我为了她一直未娶感动得落泪,她说她是一只疲倦的鸟,终于找到枝头可以歇息了。当时我站稳脚跟供她依靠,连我都被自己的宽阔胸怀所感动。真的,我倒是担心索米会把白迪轰出来,如果锅碗瓢盆乱飞惹怒店家就不好了。我犹豫片刻,索性和白迪一起朝前走。
四
门里是当年政府归还的白家老宅。
索米住在宅子里,白迪要我当晚把她带出去,他要在家里举办黑灯舞会,女主角伊欢要来,他可不想有索米在身边。那时的白迪可是诸事顺心,他根本没想到我会拒绝他,他也不和我啰嗦,下班后来我上班的街道工厂接我去吃饭,我嘴馋,跟着上了公交车。他把摸来的钱包塞进我口袋,迅速跳下车,我被抓后大喊救命保证去他家,白迪才拦停公交车,我趁乱逃脱。
说真的,我是不想见索米的,可是索米却很高兴见到我。她取下别针,双手向后别上头发,怪白迪不事先告知我要来,这真让我感动,原先对她的怨气顷刻烟消云散。我问她过得怎样?她一脸幸福称很好,父母重返讲台,她现在一家百货公司搞登记,很清闲。
索米放下圆形印染扇子,从平柜上端起那个跟饭盒一样大小的银质火柴盒,划燃后给我点上烟,一伸手扶住桌上被我碰歪的埃菲尔铁塔模型,告诉我,她最近打算和白迪再去乌山看日出。我不无心酸地转看白迪,他却兴致勃勃提议为庆祝重逢去看场电影。当时正热映印度电影《流浪者》。索米拍手赞成。白迪要索米和我先走,他有事晚些来。索米不干,她要白迪一起去。白迪称领导要来家谈很重要的事,关于他的晋升。我扑哧一笑,忙又捂住嘴。白迪保證谈完事就赶来影院。索米说领导来了,你还穿喇叭裤?白迪嬉笑着上前抱住她,朝她白皙脖颈上那块青色胎记亲一口,一边朝我眨眼。我没搞懂,到他跟前踮起脚尖问,哪样意思?白迪咬牙切齿,要我顺着说。哦,我忙说见过他领导,很新潮的。说完给了自己一个嘴巴,说有蚊子。索米笑起来,表扬还是我好,变化不大,干干净净,皮凉鞋里白袜子一尘不染,腰间挂着一串钥匙,一看就顾家。我不由一阵酥软。
有雷声从屋顶滚过。
白迪要我们带上伞,索米却不忙,拿出打湿的手绢在炉子上烤,称烤干手绢就走。又对我说,老宅潮湿,春末还得烧铁炉子。我注意到她不断悄悄弄湿手绢,知道她一步也不想离开白迪。可是白迪又在催,还叮嘱我们在街上吃,吃好点,话没说完,豆大的雨点就泼洒在天井里。
墙上挂钟当当地响。
索米出了一口气,说时间还早,就在家里做饭吃。白迪嫌麻烦,建议煮面吃。我说好。
索米便在铁炉子上架上锅。
我们三人围炉坐下。
白迪心不在焉,说雨小些了。
索米说哪里小,撑伞都不管用。她要白迪安心,领导不会来的。
白迪认为这是阵雨,一会儿就停,站起身要我和他去厨房取碗筷。出来后指着厨房叫我自己去,他要去收拾一下卧室,不能让伊欢看出他这里住着女人。我劝他不要造孽,赶紧和索米结婚。他却说我的任务就是把索米带出去。走两步又转身告诉我,他心在别处,好不容易活出个人样,不满足自己的这点愿望怎么行?我扯住他衣袖说,我实在不想帮他做这种恶心事。白迪笑问我不想和索米单独在一起?我老实回答:想!
白迪坏笑着,轻轻捏一捏我的脸,叮嘱看完电影把索米送回来。我乖乖点头,骂自己贱也没用。
重新围炉坐下时,天井里的雨点仍在噼里啪啦响。
院外巷里人家舂着煳辣椒,呛得我们一阵咳嗽。
炉子上铁锅咝咝地响。
我说这水响声像催眠曲,并说我最喜欢的催眠曲是《银色沙滩》,张口就要唱。白迪要我打住,说他仿佛又听见农村演土戏时敲打的锣声。索米也笑我是脚背上长眼睛自看自高。我忙说我本来就不会唱歌。索米说白迪唱得好,小时候跟他母亲学过声乐。我可不信,果真如此,白迪早吹开了。索米就缠着要白迪唱一首,白迪沉吟片刻就亮开了歌喉,唱的是《银色沙滩》。
白迪以少有的正儿八经对我说,已叮嘱索米,他死后就用这首歌给他陪葬。索米不准白迪乱讲。白迪霎时又恢复痞气,一把揽过索米。我赶紧别过脸去。
白迪朝我眨眼,我懂他的意思,我们可以走了。那时雨的确小了许多,挂钟又在响,已是八点。似乎有人在敲院门。我忙放下碗,催索米快走。白迪要我们走侧门,领导看见他有女朋友影响不好。
索米轻手轻脚带我走,临出门忍不住看一眼院里,哇,领导是女的,也穿着喇叭裤,后面还跟着那么多人,抱着大密纹唱片。索米说领导果然潮,边谈工作边听音乐?我从外关上侧门,不打嗝地告诉她,这说明领导重视这场谈话。
说实话, 我很开心和索米在一起, 我不在乎捡漏,在等待进场的半个小时里,我为高出我半头的她撑着伞,我们有说有笑,在旁人羡慕的眼光中,我无比幸福。可是坐进影院后,她心神不宁,老是看表惦记着白迪,着实让我不舒服。我最终忍不住表示白迪根本不值得她企盼。索米却笑称不想听我挑拨她和白迪关系,她知道我不喜欢白迪。我急了,不加思索和盘供出白迪的全部名堂。我还没有说完,索米已是泪流满面。她已寒心,决定搬回父母家。
她走后我的心简直碎了。
五
不出我所料索米听我说完原由后,气呼呼拧上水龙头,表示交由白迪来做,她不做了。我忍住笑,转朝白迪。他无所谓地耸一耸肩,瞟一眼案板上的肉,笑说他可以做,但必须有个帮手洗菜切菜。他看着我和索米,问:你,还是你?
我忙捂住鼻子表示闻不得油烟,追上索米劝其留下,顾全大局,大家饿坏了。我拽着她衣袖说,反正饭后就与他分道扬镳了。索米这才极不情愿地操刀切肉。我却担心白迪听见会撂下挑子,他却走至灶台,还认认真真用铲子敲一敲锅,问,油在哪里?我忙转问索米,她指一指左边花瓷钵。我赞许地拍一拍她手背,一回脸,眼见白迪往锅里放油,我赶紧闪身,关上厨房门。
此后厨房里一切正常。再后来竟然有了说笑声,我正琢磨白迪凭哪样把她逗笑的?接着就没声音了,一点声音没有,这可不正常。我不敢大意,走到厨房门边,使劲贴着门听,门被猛然拉开,我摔了个扑趴,爬起身故作镇静问往外端菜的索米,还有几个菜?快点嘛,大家饿了。
索米一盘盘往大圆桌上端菜,我背了双手围着桌子踱着方步,眼光扫过宫保肉丁、啤酒魔芋鸭、豆豉茼蒿菜,还有凉拌丝丝红油酸辣粉,心想他们应该没时间搞什么名堂。
弟妹们围上来,纷纷称赞索米。她却摆手称不是她做的,一边在我耳边嘀咕:人家白迪变化很大,竟然学会炒菜。我细细品咂着她的话,心里忽然酸酸地有点不舒服,她再进厨房,索性我也跟进去。
白迪又往锅里放油,这次我可不想离开,一边捂着鼻子叫他少放点辣椒,一边打喷嚏。索米慌忙递给我纸巾。
我看着她笑,她也笑。
我注意到她眼圈有些发红,诧异地问,你哭过?索米说是烟熏的。
我又指一指白迪背影,轻声问,你不恨他了?
索米却转身打开厨房门,太热了,她用手扇着汗,说好想打光胴胴。我赶紧咳嗽提醒她斯文些,这句话不光让我想起原先的她,更会让白迪有非分之想。索米异样地吐一下舌头,上前接过盛满虎皮青椒的盘子,我似乎看见他俩的手指碰了一下,我眨眼再看,她已往外走,慌里慌张的,差点摔了盘子。
我跟进堂屋,顷刻有步入迷宫的感觉。
白迪最后走出厨房,往桌上放下一钵紫菜蛋花汤。
大家围桌坐下。
我的目光落在白迪身上,他也在看我,我可不愿被其知道我在注意他,迅速避开他目光,又忍不住用眼角余光扫着他。白迪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我知道他在找谁。我看见索米在后面走来走去,弟妹们叫她多弄几碟煳辣椒蘸水来,她也只是勉强应着,并没照办,和先前判若两人。莫非两人死灰复燃?我正寻思其可能性,索米称不舒服,要回203号房休息。我还没发言,白迪说要上厕所,也起身离开。我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叫大家先吃,自己则先一步上楼进了203号房,正奇怪索米不在屋里,门突然被推开,白迪急冲冲迈进漆黑屋里,一连声叫索米。
我打开灯。
白迪笑称想问索米好些没有,他有药。
我冷冷告知,索米好得很,已去了楼下。
白迪转身要走,被我拉住,说我们谈一谈。我要他坐下,有话要问。
白迪拒绝了我端给他的茶。我不想再和他绕弯子,干脆直视着他,严肃地问:你是不是又打索米主意?我见不惯他嬉笑的模样,说我是认真的。
窗外屋檐下滴答滴答掉著雨点。
白迪忽然两手一拍,说,这么凉,还有蚊子。他最讨厌蚊子,嗡嗡飞得心烦。我奇怪他竟然也弯弯绕绕,这可太不像他了,过去他可是一向喜欢单刀直入。我心里忽然感到一丝得意,这说明他对我有了畏惧。我习惯性地摆出往日面对下属的姿态,正打算警告他几句。可是白迪却忽然制止我说话,看着我平静地说他打算带索米去乌山看日出。真的,他真是这么说的,说得坦然,还补上一句,其实在车祸后他就一直在找索米。更过分的是,他还轻柔地抚摸一下我手背,好像索米就是属于他的东西,只是暂时寄存在我处,他现在要拿走。我一下有点不知所措。白迪却系好鞋带准备起身结束这次谈话,他并不想听我的意见,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忽然觉得他是处心积虑,包括救我,混进我家,都是精心设计的,我不由悚然一惊,他简直比过去还可怕。我忍不住往前一扑按住他坐下,强忍惊慌问,索米的意思呢?他微微一笑,反问我,你说呢?
我起身又坐下,不能让他看出我乱了方寸,或许他根本就是装诡诈激我,其实已被索米拒绝了呢?索米不憨,知道谁对她重要。我舒畅许多,也想坦坦然然坐好和白迪斗一番智。可是白迪对付我确有一套,不等我架好两条腿,他便用小手指抠着耳朵,自言自语说他和索米不愧是老相好,一拍即合。我一下跳起来,说你再说一遍!白迪奇怪地看着我,重复道:一拍即——我不加思索把半杯茶水泼向他。白迪慢吞吞厚颜无耻地把脸凑到我跟前,冷静地命我拿掉他脸上的茶叶,而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竟然乖乖照办,因为他在笑,微微地笑,又是那种可怕的坏,这种笑藏着深意,让我没了底气。他还没有完,还要求我抹掉其脸上水迹,那是一张历经沧桑的脸,我不仅照办,甚至还哆嗦着想向他求饶,不要破坏我和索米的生活,我简直想给自己一个耳光了。
好在白迪仰望天花板的鬼样子让我打消此念头,我提醒自已,白迪一向心硬似铁,哪管别人死活。又转念一想,凭什么我要央求他?他现在和我已是今非昔比。我觉得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拿出勇气来灭掉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当他嘲笑着要我去擤擤鼻涕时,我毫不犹豫举起茶杯砸向他。白迪闪身躲过,“哗啦”一声杯子落地摔得粉碎。
索米出现在门口的一霎那,我差点要骄傲地挺起胸。可是她对摔物品的行为很不以为然,我气呼呼抬起脚,在空中停了半天也不见她有动静,我不得不沉下脸命她赶紧打扫一地碎瓷片。白迪说索米太累了,他来打扫。我不准,偏要让白迪看看索米如何对我俯首帖耳。我夺过扫帚,转身朝索米迈步,却被白迪绊了一个踉跄,我还没发声,他又迅速扶住我,说好险,不然一个扑趴,被碎片划破挺难看的。我害怕他是旧仇新恨一起朝我宣泄,便扯着嗓子叫起来。弟妹们进屋时,白迪飞快夺回扫帚看似扫地实则作好防范。我立马换上笑脸,称我们在玩游戏。我可不会在弟妹尤其是妹夫们跟前暴露我被白迪戏耍。弟妹们松一口气,叫我们下楼吃饭,他们一直在等我们。
一起下楼时,我决定要拿翻白迪,不然今晚会出大事。
大家围桌坐下。
索米最先给我送来碗筷,她知道医生嘱我要细嚼慢咽。我心里不由一暖,看光景她不像是要跟他走的人呀。心刚落地又提起来,索米催大家赶紧吃,没有听见打雷要下大雨?白迪住得远,早点吃早点回去休息。我放下碗说不忙不忙,既然是老友重逢,又是初识我家人,不喝点酒怎么行?屋内顿时一片叽叽喳喳,我的弟弟及妹夫们包括正拿筷子拨弄盘里香辣鸡爪的筱青男友都赞同,一连声叫老板拿酒和酒杯。我提醒自己稳住,眼见大家都斟满,我对弟弟和妹夫们说,我跑了一天骨头酸软。话刚说完,他们立马代我向白迪敬酒,看着白迪喝下头三杯后,我不断以各种理由鼓动家人轮番和白迪碰杯。他一点不拒绝,并按我要求一一回敬众人。身旁的筱青连说他真能喝。我才注意索米和筱青调换了位置,她坐到白迪身边,还偷偷扯一扯他衣袖,估计是示意他少喝。她果然有变。我上去挤开索米,边和白迪碰杯,边说放心喝,走不了就住一楼过道第一间。我感觉索米从我身后探出头来,正向白迪眨眼,暗示我有鬼?反正我看见白迪点头,似叫她放心。我假装上厕所,偷偷叫来二妹三妹,借她们的项链戒指手镯用用,不准啰嗦,快一点。
大堂响起玻璃破碎声。
弟媳们说客人杯子掉地上了。
白迪承认自己醉了,我说哪里可能,再来两瓶也没事。白迪起身要去卫生间,却是东倒西歪奔了厨房,打鼓一样咚咚捶开了门。店老板跟进去高喊不能朝灶台撒尿。我命弟弟们把白迪架去一楼房间,把行李提进去。
我叫四妹立马把索米送回203号房,转身叫弟弟们不要打麻将,也不准嗑五香瓜子,赶紧报警,家里失窃了!
镇派出所干警到达后,我急冲冲带领其走近白迪房间,一下呆住。想不到白迪竟然不在屋里,莫非假装喝醉,将计就计裹了我的戒指项链跑了?我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慌忙跑到院里,还好,他的车还在。回到屋里时,干警仔细搜了白迪行李包,接着是整个房间,均一无所获。
我急着叫喊搜整个饭店,抓人。
有敲门的声音。
六
半天没有露面的索米进来对干警说,东西全部都在堂屋里,是我酒喝多弄错了。并拿出戒指项链给干警过目。我想不到索米会坏我的事,顾不上考虑她是怎么得到这些物品的。我一再向干警赔礼道歉,干警训我一顿后走了。我希望大家不再提此事。可是所有人像没听见,只顾盯着我,这可让我受不了,威猛一咳嗽,叫他们有屁就放!弟弟们开始责怪我做事不高明,不如镇上买一个关狗的铁笼子直接把白迪送进去。
只有筱青说她能理解我的做法,这倒让我对她另眼相看,她推开缠着她还想要松鼠鱼的男友,上来对我说,错就错在低估了白迪。我有点不高兴筱青略带放肆地拍着我胳膊说,关键是,她想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明摆着白迪不会善罢干休,她可不愿母亲受到伤害,她表示并不恨母亲的善变。
我才注意到索米又不见了,还有白迪,仍然不现身。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扑到窗口看看,阵雨刚停,我的眼光从月下模模糊糊的山谷移至窗边,外墙上有下水管道连结着一楼二楼,我一下毛骨悚然,才醒悟白迪是爬上楼把“赃物”交给索米的,说不定此时他正帮着索米收拾行李哩。不好,我发疯一般直奔楼梯口。
索米独自坐在楼梯顶端等着我,身边放着行李箱。
略显陌生的她迎着我目光,坦承就是想要告诉我一声,她要和白迪一起去乌山。
我心里先是一惊,接着又一喜,她等着我,说明她并不想走。慢着,我挥手叫大家不要上来,然后笑容满面迈上几步到索米身旁坐下,偷偷嗅一嗅她身上,看能否找到白迪的蛛丝马迹,嗯——我闻到一缕香烟味,才发觉鞋底下被她刚熄灭的烟蒂。本来她已戒了烟的。索米迅速起身,使我吞下后面的话,也赶紧站起来,说我帮你提行李。我的意思是把行李送回203室,却被她拦住。我扔掉纸巾,问她白迪在哪里?我去告诉他你改变主意了。索米要我放下行李箱,说白迪去发动车了,他们现在就走。我有点懵,搞半天还是要走?索米说她改变不了自己喜欢白迪的事实,只能听从内心。我有点急了,叫她休想,我决不答应。索米我行我素地提上行李箱绕开我往楼下走,看光景,就算我立马毙命,也不能指望她来照顾我。我大叫弟弟们堵住楼梯口和大门。
灯突然灭了。大堂里传来一片叫唤,我打开手机电筒,看到弟弟和妹夫们躺在一地香蕉皮上,白迪正迈出大门。
我家的男子汉们爬起身要抓住跟出去的索米,并嚷着要圍住白迪车将其掀翻到路边排水沟。我也跟着朝外涌。
院里响起汽车发动声。
我能想象到坐在车里的白迪一如既往无所谓的样子,而索米却是紧挽着他手臂,一副要和他死在一起的表情。我忽然感到精疲力尽,心一横,猛喊家人停住,放他们走,我不想再见到他俩!
我们远远看着索米朝车走去,白迪的车原地一阵打滑,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汽车启动后竟直奔院门,无论索米怎样追赶高喊,白迪就是不停车,我眼睁睁看着他抛下索米独自开车走了。这让我们所有人目瞪口呆,真的,没人能说清楚白迪为何最后时刻突然变卦。
死一般的沉寂,细雨一如既往地纷飞。
山道上孤独的车声渐行渐远。
筱青上前挽住索米,我也走过去,那时天已麻麻亮,索米面色苍白,并不看我。
全家人围拢来,看着我,我顿感茫然,良久,决定行程不变,前往霍山崇寨。我说完转过身子,却被索米拉住,只听到她说:我有话要对你讲!
【作者简介】何文,1957年2月出生于北京,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走过四季》《无限甜咸》,长篇小说《谁为谁停留》;现居贵州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