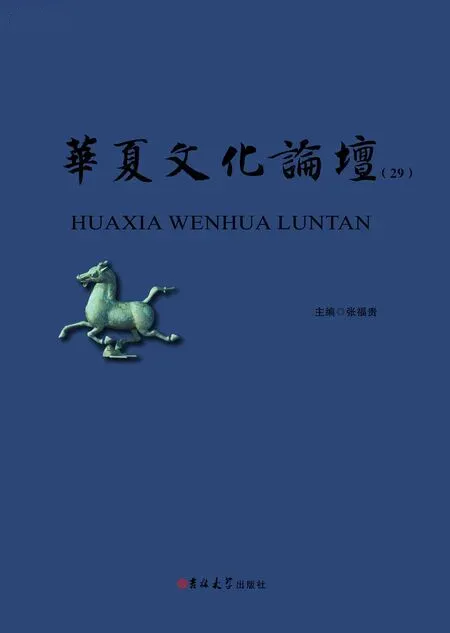苏区法治文化阵地的建构
——论《红色中华》的法制宣传
杨 峰 李 萌
【内容提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先后创办了“政府文告”“苏维埃建设”“问题与答解”“法令的解释”“苏维埃法庭”“审判纪实”“突击队”“铁锤”“警钟”等一系列法制栏目,在立法宣传、司法释疑、执法纪实、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性的法制宣传,努力建构苏区法治文化阵地,积极弘扬革命法治文化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引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和苏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同时,在法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令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体系,极大增强了苏维埃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思想观念。《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至1937年1月25日终刊,共出版324期,其中苏区时期出版240期,发行量最高时约四五万份,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先后创办了“政府文告”“苏维埃建设”“问题与答解”“法令的解释”“苏维埃法庭”“审判纪实”“铁锤”“警钟”等一系列法制栏目,努力建构苏区法治文化阵地,向苏区民众大力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对苏区法治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以苏区时期《红色中华》的法制栏目为对象,探讨苏区法治文化阵地的建构及其启示,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有所借鉴。
二、以成文法规为基础的立法宣传
“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第十二》)良法是善治的基础,知法是守法的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的全国性革命政权,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认可和法律的确认,民主法制建设是依法执政和治国安邦的前提基础。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区的立法宣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始终把立法宣传教育作为重要使命,创刊之初便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组织苏区广大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使其“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①《发刊词》,《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政权的一些重要法规制度常常通过布告、命令、决议、训令等形式发布在《红色中华》上,以便苏区广大民众了解。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向“全中国工农兵士贫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公布了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的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等重要法令。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苏维埃政权合法性,反映了广大工农兵和一切劳苦大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1934年2月14日,《红色中华》全文刊载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一切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红色中华》,1934年2月1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是关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的基本法律。1934年2月22日,《红色中华》以“中字第一号”命令的形式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全文共10章51条,对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工农监察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等苏维埃中央政权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职权做了详细规定。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红色中华》,1934年2月22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武装“围剿”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新生政权面临着紧迫的“肃反”任务。据统计,当时苏区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了70%。⑤瑞金县人民法院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因而,《红色中华》把惩治反革命犯罪的立法宣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先后刊载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1931年12月28日)、《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1933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34年4月17日)、《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1932年9月20日)等。这些惩治反革命犯罪的刑事法规明确规定了反革命罪的适用范围、概念、罪行和刑罚,监狱法规对劳动感化院的性质、目的及其对犯人的监管和劳动感化教育方式进行了规定。①《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红色中华》,1932年9月20日。
马克思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类法规大多通过其机关报《红色中华》对外发布,为广大苏区民众所知悉和遵循。据统计,《红色中华》刊登的各类政府公文共 473 项,其中决议命令类 47则,法律条文类35则③李凤凤:《〈红色中华〉法制专栏设置及影响探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包括了宪法大纲、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刑事法规、监狱法规、红军优待条例、财政条例、暂行税则、工商投资条例、合作社组织条例、借贷条例、保护山林条例、托儿所组织条例、俱乐部纲要等,几乎囊括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各类重要法律法规。这些法令规章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红色政权的合法性、政府部门的组织原则和人民群众的权利义务,规制了各种违法犯罪及其惩治,初步形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体系。尽管这些成文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地区性、临时性和变动性等不同程度的局限,但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意志制定的,是完全不同于过去旧法体系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它们经由《红色中华》的大力宣传成为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实现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三、回应民众关切的司法释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区法制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令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体系,极大增强了苏维埃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思想观念。然而,一方面由于苏区法制在探索创设时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广大劳苦大众长期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法制思想意识淡薄,因而,他们对于红色政权颁布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在理解、接受和运用上存在诸多问题,正如时任中央苏区司法人民委员会委员梁柏台所指出,苏区时期,“在司法上,每种工作都是新的创造和新的建设,所以特别困难”④瑞金县人民法院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第248页。。为此,《红色中华》开设“苏维埃建设”“问题与答解”“法令的解释”等栏目,通过司法机关或权威人士针对一些法律常识问题和民众关心的日常法律问题进行释疑解惑。
尽管苏维埃中央颁布的宪法大纲、组织法及其相关法令明确规定了红色政权的性质、制度及政权机关职责,但由于“司法机关过去在苏区是没有的,是中央政府成立后的创举”⑤瑞金县人民法院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第248页。,苏区民众包括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代表大会、联席会议等一类的概念和职能“弄不清楚,混而为一”①柏台:《代表大会与主席联席会议》,《红色中华》,1932年1月20日。,妨害了苏维埃政权的健全及其相关工作。1932年1月20日,《红色中华》“苏维埃建设”栏目专门刊载了梁柏台关于代表大会与联席会议的普及介绍。文章指出,代表大会是“法权的机关”,“是按照人口为比例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是某一个地方的最高政权机关”,“它可以议决关于该区域内的各种问题”;联席会议是“商议机关”,“对于各种问题不能作最后的决定”,“参加联席会议的人,是某机关的负责人,是按职务指定的”,不需经过选举产生。民主选举是苏区群众当家作主、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体现,苏维埃中央依据宪法大纲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委员会工作细则》《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但各地在选举运动中仍然对相关法规制度理解不够,出现了一些问题。1932年2月17日,《红色中华》“苏维埃建设”栏目刊载了《选举运动与合作社——中央政府指示江西省苏的一封信》,针对江西省苏选举运动问题,提出苏维埃选举运动的任务是“建立强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积极的执行全苏大会一切法令”,“充分的动员群众”,“很积极的选举他们最好的分子到苏维埃来当代表”。②《选举运动与合作社——中央政府指示江西省苏的一封信》,《红色中华》,1932年2月17日。1933年10月6日,《红色中华》刊载了谢觉哉的《怎样开选举会》和梁柏台的《关于选举法上几个疑问的解释》。对于如何开选举会,谢觉哉提出,要按照选举法规,充分尊重选民意愿,“凡属选民,都应该到选举会,凡被选举的人都应经过大多数选民通过”③谢觉哉:《怎样开选举会》,《红色中华》,1933年10月6日。。对于各地因“候选名单与选民名单”“传教者与信教者”区分不清产生的选举问题,梁柏台指出,选举法规定要提前公布候选名单与选民名单,但二者不能“混合为一个东西”,前者是准备选举为代表或委员的名单,后者是全体有选举权者的名单;“选举法上很明白地规定,无论信什么宗教都有选举权”,“剥夺选举权的仅仅是,‘靠传教迷信为职业的人’”,如牧师、僧侣、道士、阴阳先生等,不能把二者混杂了,否则,将会产生“剥夺选举权人将在半数以上”的严重后果。④梁柏台:《关于选举法上几个疑问的解释》,《红色中华》,1933年10月6日。
婚姻问题和土地问题关系到广大苏区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央苏区颁布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规从根本上推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土地制度,使得苏区民众实现了“婚姻自主”“耕者有其田”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愿望,但在日常生活和实际工作中难免产生各种复杂问题。针对苏区民众的关切,《红色中华》专门约请司法部门及其相关权威人士,通过“问题与答解”“法令的解释”等栏目进行释疑解惑。1932年2月24日,《红色中华》“问题与答解”栏目刊载了关于婚姻条例的质疑与答解。署名向荣的读者对婚姻条例中关于离婚的部分条款提出质疑,如第十八条规定“男女同居所负的公共债务,归男子负责清偿”,第二十条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耕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他认为这些规定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不符合男女平等的原则。①《问题与答解——关于婚姻条例质疑》,《红色中华》,1932年2月24日。由于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红色中华》特地约请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来答解上述问题。项英主要从苏区过去男女不平等的历史现实和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层面来答解上述质疑。他说,婚姻法“最重大的意义是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消灭男子对于女子的压迫”,“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婚姻条例,正是站在彻底解放妇女,消灭任何束缚女子的方面来规定的”,如果首先了解了这些问题,上述问题“就容易明白了”。②项英:《问题与答解——关于婚姻条例质疑》,《红色中华》,1932年2月24日。1932年4月13日和6月23日,《红色中华》在“法令的解释”和“问题与答复”栏目分别刊载了署名力梁、嘉宝、温恒贵等关于土地法的疑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的相关答复。力梁等提出,土地法第二、七条关于土地分配有些规定不明确,有些与《红军优待条例》相冲突,土地分配到底是按人口还是按劳动力,豪绅地主子弟参军要不要分配土地,其家属是否享受优待条例等。③力梁:《现在我有几个问题不能了解请即答复》,《红色中华》,1932年4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答复,土地法限定的是有劳动力的富农按劳动力分配一份“坏田”,无劳动力的“按人口来分”,对于贫农中农的土地分配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按大多数“最有利益的来决定”,豪绅地主子弟参军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④《法令的解释》,《红色中华》,1932年4月13日。
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立法主要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所以一些法令规章往往比较概括、抽象,对于一些复杂的生活现象和工作实践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司法机关及其权威人士对相关法令规章及时进行释疑解惑,并通过《红色中华》进行宣传普及,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但提高了民众的法律认识水平,也增强了各级部门依法执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司法解释”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立足执法实践的法庭纪实
法律的功效和权威在于实施,所谓“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王勃《上刘右相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苏维埃政权在中央、地方和军队中设立和完善各类司法机关及其审判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巩固新生政权,打造廉洁政府,维护群众利益。为了彰显革命政权在司法实践中“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精神,《红色中华》专门开设了“苏维埃法庭”“审判纪实”等法治栏目,主要以法律文书和审判纪实的形式,真实再现苏维埃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执法情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审判工作在1934年最高法院成立前,主要由临时最高法庭及地方各级苏维埃裁判部组织实施,审理判决的大多是反革命案件。《红色中华》自第12期始至第41期止,不定期开办“苏维埃法庭”栏目,主要刊载的是各级审判机关的判决书,以及上级司法部门对相关判决工作审核指导的决议、批示、训令和信函等法律文书。据统计,“苏维埃法庭”栏目刊载的法律文书主要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2份;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6份、批示11份、训令1份、信函2份;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判决书6份;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6份;闽西省政府裁判部判决书2份;福建省苏裁判部判决书1份。为了凸显对死刑判决的慎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规定,“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决死刑之权”,“中央区及附近的省司法机关作死刑判决之后,被告人在14天内得向中央司法机关提出上诉”。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红色中华》,1931年12月28日。“苏维埃法庭”通过刊载审判反革命分子及其上诉的判决、批示、训令和决议等法律文书,让苏区民众深入了解苏维埃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譬如,1932年6月2日,《红色中华》“苏维埃法庭”刊载了《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第二十号)和《临时最高法庭批示》(法字第十七号)。据《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1932年5月24日,由主审潘立中,陪审锺桂先、锺文高,书记杨世珠,国家原告人华青彬,组成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法庭,列举了被告人朱多伸“压迫劳苦群众”“吞没公款”等5条罪状,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其死刑,倘若被告不服,可以在一星期内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②《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第二十号)》,《红色中华》,1932年6月2日。在《临时最高法庭批示》中,临时最高法庭“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认为嫌犯不过是“贪污怀私”等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犯罪,且早年有过革命贡献,如今年事已高,因此改判死刑为监禁二年。③《临时最高法庭批示(法字第十七号)》,《红色中华》,1932年6月2日。由于苏维埃革命司法工作尚属起步阶段,一些裁判机关的审判工作难免时有偏差,即便是临时最高法庭也不例外。譬如,1932年9月6日,《红色中华》刊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对临时最高法庭第五号《判决书》关于季振同、黄仲岳、朱冠甫等死刑判决进行“改判”,认为季、黄虽为主犯,但都是宁都暴动的领导者,对革命有“相当功绩”,减免死刑,改判监禁10年;朱冠甫、高达夫等不是此案主谋者,改判监禁8年。④《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红色中华》,1932年9月6日。可见,《红色中华》“苏维埃法庭”栏目刊载的判决书、批示、决议等法律文书实事求是地陈述罪犯的犯罪事实、审判依据和判决结果,使广大民众深入了解苏维埃司法机关对犯罪行为“违法必究”及其自身“有错必纠”的新民主主义法制精神。
《红色中华》的“审判纪实”栏目主要以新闻纪实的方式向读者报道各级苏维埃政府司法机关对一些重要典型案件的审判情况。譬如,1932年2月17日,《红色中华》刊载《闽西苏维埃政府开法庭审判反革命经过》,报道了1932年2月9日至13日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刑事法庭对托派、社党、改组派、AB团军事犯等24名“反革命分子”的审判。1932年8月30日,《红色中华》刊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季黄反革命案件纪实》,报道了1932年8月3日至4日临时最高法庭对季振同、黄仲岳反革命案件的审判。中央苏区时期,司法审判部门十分重视公开审判,通过公审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普法宣传,《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明文规定,“审判案件必须公开”,要“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旁听”。①《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红色中华》,1932年9月20日。因而,《红色中华》的“审判纪实”在详细报道“法庭人选”“法庭布置”“审判罪状”和“判决结果”等审判情形的同时,还突出报道群众的参与情况及其反响。譬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开法庭审判反革命经过》报道,“在审判的时候,每天有四五百人来参加旁听,宣布判决的那一天,并有汀州工农群众的请愿运动,要求政府严厉地惩办这些反革命分子”②《闽西苏维埃政府开法庭审判反革命经过》,《红色中华》,1932年2月17日。;《临时最高法庭审判季黄反革命案件纪实》报道,“当审判季黄反革命案件的时候,瑞金各地的群众四五千人,手执各色小旗,高呼口号”,“推选代表请愿,坚决要求法庭严格的惩办季黄等反革命分子”,“法庭即派代表向示威的群众演说,并愿接受群众的要求,作为该案件的参考”,“群众非常满意,围绕法庭房子一周,高呼‘拥护临时最高法庭’‘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等口号而散”。③《临时最高法庭审判季黄反革命案件纪实》,《红色中华》,1932年8月30日。可见,《红色中华》的“审判纪实”通过对审判现场的纪实还原,让苏区群众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更直接地了解司法机关的执法审判情况,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法律意识。
五、注重廉政建设的舆论监督
作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喉舌”,《红色中华》自创刊起就积极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职责,把“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④《发刊词》,《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先后开设了“突击队”“铁棍”“铁锤”“警钟”“铁帚”等批评监督类法制栏目,检举揭发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一些官僚腐化现象。据统计,《红色中华》刊载的各种批评监督性稿件多达 524篇。⑤李文、韩云:《中共新闻媒体批评性报道的理论和实践源头》,《国际新闻》,2011年第4期。
“突击队”栏目是《红色中华》最早开辟的批评监督性栏目。“突击队”原本为中央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的监督组织,主要采取“公开的突然”的方式“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华人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⑥傅克诚:《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红色中华》借用“突击队”为栏目名称,其用意不言而喻,即同样采取公开“突击”的方式,对一切贪污浪费及官僚腐化现象迅速展开批评和斗争,“并期待尽快取得较大成效”⑦陈信凌:《〈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之间的一段公案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2期。。譬如,1932年3月9日,《红色中华》第一次开设“突击队”栏目,刊载《好安乐的民警局长》,批评了汀州民警局苏局长工作懈怠,贪图享乐,对群众打官腔,“是十足的官僚架子腐化浓厚的腐化现象”⑧方文:《好安乐的民警局长》,《红色中华》,1932年3月9日。。1932年4月21日,《红色中华》“突击队”栏目刊载《好大胆的连副政治委员》,揭露独立第五团一营六连副政治委员赵九苟公然涂改账目贪污,抽大烟,给买鸦片的伙夫开路条等违法行为。①学濬:《好大胆的连副政治委员》,《红色中华》,1932年4月21日。1932年5月25日,《红色中华》“突击队”栏目刊载《好阔气的小岔乡苏》,通过审查账目,批评小岔乡苏吃喝、贪污,两个月用去大洋五百元,呼吁对这样的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严厉打击”。②卓夫:《好阔气的小岔乡苏》,《红色中华》,1932年5月25日。
同样,“铁棍”“铁锤”“警钟”“铁帚”等栏目,也主要通过刊载一些群众通讯员撰写的身边案例,检举揭发各种贪腐、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譬如,1933年3月12日,《红色中华》“铁棍”栏目刊载《剥削群众的妙计》,揭露罗江区前村乡苏主席梁官廷利用做新棺材和砌新灶请客,赚取群众“八毛至一元的贺礼”,“真是顶刮刮的贪污腐化分子”。③谢金修:《剥削群众的妙计》,《红色中华》,1933年3月12日。1933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铁锤”栏目刊载《突击运动的破坏者——青塘尾乡苏主席勒索群众的钱》,揭露青塘尾乡苏主席在突击扩红运动中“用了最无耻的贪污手段”,叫群众给他钱,可以不去当红军,呼吁要让这个革命战争中的罪人“滚蛋”。④王惠民:《突击运动的破坏者——青塘尾乡苏主席勒索群众的钱》,《红色中华》,1933年12月11日。1934年4月12日,《红色中华》“警钟”栏目刊载《把许清庭送到法庭去》,揭露粤赣省筠岭县苏主席许清庭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违抗上级指示,“把国家粮食送给了敌人”,呼吁苏维埃政府“要驱逐他出去,送到法庭去审判”。⑤王叔振:《把许清庭送到法庭去》,《红色中华》,1934年4月12日。1934年9月18日,《红色中华》“铁帚”栏目刊载《把乐观的官僚主义的突击队长清扫出去》,批评长乐区扩红突击队长曾福林,在扩红运动中,“采取了投机商人的取巧办法”来争取模范营报名,导致下面发生了欺骗、捆绑、封斗等极严重的现象,呼吁“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铁帚扫除出去”。⑥乙工:《把乐观的官僚主义的突击队长清扫出去》,《红色中华》,1934年9月18日。
可见,《红色中华》的批评监督类栏目积极响应苏区党和政府的号召,集中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提起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⑦《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中央工农检查部的指示》,《红色中华》,1934年1月4日。,“给予苏区的贪腐、浪费和官僚主义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之无法继续在苏区存在”⑧洛甫:《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1933年12月12日。,从而“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⑨《发刊词》,《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但值得注意是,这些批评监督类栏目由于受当时“左倾”路线影响,也不乏过激倾向,所针对的有些只是工作纪律或作风问题,而并非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总体而言,它们对于苏维埃政权中的违法行为和不良现象的批评监督,为中央苏区政府依法治理,打造“真正的空前的廉洁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结语
法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7、8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红色报刊,在党的领导下,围绕苏区革命建设工作重心,立足苏区民众生活实际,创办各类法制专栏,努力建构苏区法治文化阵地,积极弘扬革命法治文化精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