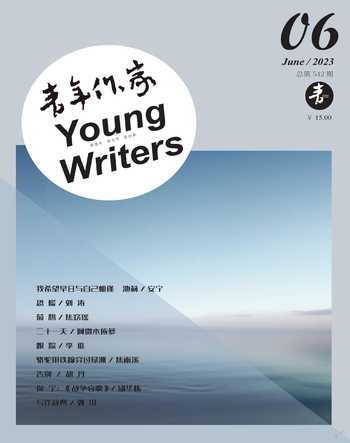斑 鸠

我坐在县车站的花坛边,大理石台面上零星有几块污渍,背靠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底下黝黑的土层散布着烟头和塑料袋,并不时窜出一股尿骚味,我不得不起身来回踱步。地震后,身后的车站已经搬走,大楼如今拆成了空壳,仅余一块空地,停了几排私家车,建筑废料都堆在旁边,乱糟糟的。近处有几个小孩在互相扔甩炮,噼里啪啦,车子的警报声七上八下,耳朵快吵麻了。附近早餐店人这么多,也没见出来管。刚刚走得急,没低头看人行道的瓷砖松落,踩了一脚脏水,裤脚打湿半截。我坐立难安,扶着贴满广告的路灯杆,等陈叔前来。
陈叔叫陈德礼,是个长安车司机,说着重庆口音,半年前在我家后巷租了间房子,做仓库和休息的地方,十天半个月就住一次,同时往周边乡镇上送一趟百货。我第一次见他,下午刚放学,我端着碗辣椒油拌着的豆花往家走,当时他正往仓库里搬货。见我住在旁边,就问,小朋友,向你打听个事。我已经十一岁,不喜欢别人这样叫我,尤其是一个陌生人,于是没好气地说,莫得空。陈叔笑着走上前来,从车里拿出一瓶重庆老汽水,塞给我说,想问下你,你们附近的电工电话是好多?我盯着手里的汽水,又看他一脸殷勤,于是说,你等下,这要问我姑姑。我丢掉塑料碗,抹干净嘴巴,打开铁门。姑姑还在超市上班没回来,我在抽屉里找到了电话本,出来递给他,把名字告诉他,让他自己找。陈叔说,谢谢你,小伙子。
陈叔的仓库里有很多磁带,这是他从奉节带来的,休息的时候,他就用录音机放歌,声音传到我的屋子里,我们不久就熟识了。我经常躺在他烟味很重的铁床上听歌,陈叔则在一旁就着小菜喝酒,两口一杯,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陈叔醉醺醺地问我,今天不上学?我说,叔,周末呢。他说,不出去上网?我说,没钱。他说,大人呢?我说,没大人。陈叔不再言语,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这一次我决定和陈叔进大巴山打斑鸠,再也不回来了。
本来我暂时不想走,这都怪赵成。几天前,他给我透露,有挣零花钱的好路子。隔壁汽配店关门了,老板二楼的仓库还在,门虽锁死,但玻璃破了一个洞,他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很多零件,大扳手、轴承、滑轮,都是铁坨坨,甚至还有铜线,这些都可以卖钱。当天,等天黑透后,我和赵成从家里出来,决定再去打探一番。汽配店离我家一百米,我和赵成从楼后面的臭水沟,悄悄绕到汽配店的隔壁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年久失修,我们径直上到顶楼,再从顶楼翻到汽配店天台。我们蹑手蹑脚来到二楼,隔着阳台,探着身子,一步步来到仓库门口。果然如他所说,玻璃坏了一个洞,用手伸进去,可以打开门锁。此时街上已经冷清,间或有大货车开着远光灯驶过,掀起的灰尘巨大,足以掩盖夜色。我浑身燥热,激动地跟着赵成进了仓库。一进门,机油味浓烈,直堵鼻子。我们不敢开灯,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憋着气摸索。仓库里,装配件的纸箱子垒得很高,一箱箱靠墙码着。我随手拆开一箱,摸出一个大部件,像是扳手,黏糊糊的,奇重无比,单手举不起来。赵成说,这个够重,就它了,说着拿出报纸包着。
第二天下雨,我和赵成同路去上学,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书包很沉,我们换着背。不方便打伞,我们就沿着街边门市走。我们要去滨河路的废品收购站,那里我们很熟,之前去工地上偷钢筋,也是去那里卖的。清晨很冷,风从河里溢上来,我把扳手从书包里拿出来提着,等待着卷帘门打开。老板是个老头,我们在门口踢了半天门,他才慢腾腾地开了门。老头脾气大得很,嘴里嘟囔着脏话。他刚起床,头发很乱,趿拉着一双旧胶鞋,披着件黑不溜秋的衣服,摇摇晃晃地打开卷帘门。我们心照不宣,不多说,扯开报纸,就把扳手往秤上放。老头瞥了一眼,拦着我說,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哦?赵成说,你莫管那么多。老头说,这东西可不好处理,你们赶紧拿走。我说,你先称看看。老头说,不称,赶紧拿走。我们没料到这老头这么倔,好说歹说都不让卖,扔掉实在可惜,没办法,我又装回书包,背着去了教室。
扳手在书包里躺了一天,我担心味道很重被老师发现,就把书包藏在卫生角,用拖把盖着。放学的时候,赵成问我,要不要明天再找个地方问问。我说,这东西没人敢要的。赵成说,北门上废品店很多,去试试。我说,那今天得你背回去,我实在背不动了。当天晚上,赵成妈妈在他书包里发现了扳手,拿着扳手就找来了我家。当时我在陈叔的仓库玩,听见赵成妈妈向我姑姑咆哮,大致的意思是说姑姑没能力教育我,还说我就知道拉着赵成干坏事。姑姑没有和她争吵,只是扯着嗓子叫我回家。见我回来,赵成妈妈冲上前来问我,你们在哪里偷的扳手?我见怪不怪,说,问你儿子。她又说,上次赵成从家里偷钱是不是你指使的?我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盯着她。姑姑这时把我护在身后说,你儿子在你自己家里偷钱,咋怪在我们身上了?赵成妈妈说,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他没那个胆子。至于他,你清楚?姑姑是个好脾气,但也被气得满脸通红,挽起袖子就把赵成妈妈往外推,关上铁门后,她把我往屋里拉,叫我跪下。我勉为其难地跪下,姑姑却先掉眼泪了。她说,你爸爸出去那么久,一个消息也没有,就把你丢给我。好像是我欠他的。你妈妈改嫁了,这么多年也不来看你。你自己要争气啊。听到她说这话,我的心瞬间冰冷下来,不再去争辩。
陈叔告诉我,他有一杆猎枪,他父亲传下来的。小时候,在奉节老家,他常跟父亲在春天上山。我想象在挺拔的山毛榉和青冈树下,他踩在刚出青的杂草上,举着枪瞄准,啵,斑鸠应声落下。我问他那杆枪现在在哪?他说,朋友借去了。我说,想看看。他说,等下次去巴中送货,他就去取,完了之后去大巴山,听说那一带斑鸠很多。我让他带上我,他死活不同意。我告诉陈叔,我想去看我妈。陈叔说,这和带你进山有什么关系?我说,她嫁去了大巴山。他说,你知道在哪吗?我说,知道,我去过一次。我昨天听姑姑给我爸打电话时说,我妈要生小孩了,我想去看看她。陈叔怜悯地看着我说,你还挺孝顺,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去世了。我说,我们差别不大,我其实都快忘了她长什么样子了。
等了快一个小时,陈叔土灰色的长安车终于来了。他按响喇叭,我心领神会地钻进了副驾驶。后座的椅子拆了,箱子堆得满满当当,椅子无法调整,我挺胸抬背,像坐在教室里。车厢内空气很闷,我摇开窗户,看见后视镜的自己,突然兴奋起来,心想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这时陈叔开上主路,点燃一根烟,问我,晕车吗?我说,有点。他玩味地说,要不要来一根?我在烟盒里抽出一根,含在嘴里。打火机快没气了,搓了几下才冒出一缕火。陈叔说,会抽吗?我说,这谁不会的?我吸了一口,猛吞下去,喉咙瞬间就有反应,堵得慌,眼泪都咳出来。陈叔说,你这是浪费。我说,你教教我。陈叔说,深呼吸,把烟当空气。我试了一下,果然不咳了,但这次上头了,晕晕乎乎的,眼睛都睁不开。街上车开始多了起来,路过西门菜市场的时候,有交警在指挥交通。我们开上西门大桥,从这里出去,就算出城区了。我吐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出了窗外。
春天刚到不久,河里的水很浅,一层透明的雾气罩在上面。我们沿着滨河路往前走,车内很安静,陈叔也不开腔,我猜他还是不情愿带上我。这时我突然想起陈叔说他老家有很大的水库,就问,陈叔,三峡到底有多大?陈叔笑了一下,调侃道,听说里面有龙,你说大不大哇?我惊叹道,龙?真有龙啊,跟电视里一样?他说,具体啥样子那晓不得,反正你们这里很快也会有龙了。我说,你又豁我。他说,你别不信,我上次去巴中送货,车子在一个小镇抛锚了,就在附近的老乡家里歇脚。那家人好像有人在省里当官,听他们聊天说,三峡要扩张,你们这里很快也要被淹没了。等水来了,龙自然就搬过来了噻。我想起电视里海啸的场景,隐隐有些害怕,仿佛身后的县城已经被淹没,潮水正在追赶我们。我说,假的吧?陈叔说,千真万确,而且你们这里马上要从四川划出去,跟重庆一样。我说,划到哪里去?他说,成立一个新省,秦巴省。我撇撇嘴,肯定地说,你就是在豁我。陈叔嗔怒道,我饭胀多了。我心里念道,秦巴省?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想反驳陈叔的传言,给出一条我们这里不会被淹没的理由,想到县城正中间的红四方面军指挥所纪念馆,于是说道,我们这里不可能会被淹。陈叔说,为啥?我说,苏维埃的遗址在这,更何况还有一个上万人规模的红军烈士陵园。陈叔说,搬走就行了啊。我说,这么多人怎么搬?陈叔说,我们奉节那么大,还不是该搬就搬,拆迁是一步步来,你家附近不都正在拆迁吗?你看着吧。我想起我家附近废弃的房子和嘈杂的挖土机,开始相信陈叔说的大水即将到来。
开始进山了,树林密布,光线暗了下来,道路也变得颠簸,沿路有好几处路牌贴着:防止坠石。已经离开县城很远了,我心里还是想着大水和秦巴省的事,见我不说话,陈叔说,还想着呢?我说,我想回去了。陈叔说,刚逗你呢。我说,但你说的我都信了。他说,这些事或许会发生,但要有一个过程,就像人死后,要烂在土里,需要很多很多年。我说,那就是说,至少我这辈子都不会被淹没吧。陈叔说,那也不一定。我抬头看了下窗外的天,天气阴晦,仿佛随时都要下雨。
上山的水泥路一撇一捺,像刻在碑上的笔画,写成一个我不认识的字。我们从河谷开到山腰,雾气起来的时候,看不清前面的路。一直到山顶,才逐渐清晰起来。我没去过巴中,奶奶曾经告诉我,她和爷爷走路去过,走了一天一夜。我问陈叔,开车去巴中要多久。陈叔只是说,快了。现在,车子开到了山顶,我从被大水淹没的恐惧中走了出来,想起此行的目的,问陈叔,那杆枪放哪了?陈叔说,去巴中取,放朋友家里了。我又问,斑鸠好打吗?他笑着说,斑鸠懒得很,成天蔫头耷脑的,有人走到了树下它也不会飞走。我说,我们今天就去?陈叔说,对,在巴中吃个午饭,困个午觉,再转到去大巴山。
我告诉陈叔我要去看我妈,只能算说了一半。五岁那年,知道我妈改嫁后,我爸便去了大连。我妈之后回来过一次,要带走我。那天下午,我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隔着铁门叫我的名字,小和,小和。声音很小,像从前给我讲睡前故事的语气。当时奶奶在卫生间洗衣服,我在房间里看《哪吒传奇》,正播到水淹陈塘关这一集。听见有人叫我,看得正起劲,不想搭理,但那声音就不停,我挺纳闷的,于是从窗户望出去。只见我妈烫了个时兴的头发,挎着一个好看的包,正冲着我笑。啊,是妈妈,我浑身颤抖着,嘴巴说不出话。我又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妈妈,她正端端正正出现在铁门的外面。妈妈,我使劲叫道。妈妈,你终于回来看我了。我打开房间门,跳下台阶,哭着冲向她的怀抱。妈妈立马蹲下来,紧紧地抱着我。奶奶在卫生间注意到外面的动静,也探出头来看,看见妈妈回来了,也开心地来迎接她。那天下午,我紧紧抱着妈妈,她去哪我去哪,寸步不离。事情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我妈在饭桌上提出要带走我,给我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奶奶不回应,好像不在乎她说什么。我妈继续说,妈,今天我一定要带走小和。这时我奶奶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带走他,我马上去跳楼,让阎王爷带走我。我问妈妈,带我去哪啊?把奶奶带上好不好?我妈不说话,埋头吃饭。吃完饭,我妈去厨房洗碗,我奶叫我去赵成家玩。我不解,问奶奶怎么回事,奶奶说,你去玩会儿,等下给你买好吃的。结果我刚走进赵成家,没过多久,就听到我妈和我奶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等我从窗户往下看的时候,我妈挎着包气冲冲地准备走,我见状,立马往家跑。我妈见我来了,站在原地不动。我跑上前去,问妈妈,妈妈你要去哪啊。我妈说,回家。我说,这里就是你的家。这时我奶奶说,小和,让你妈妈走。我大声吼道,不行,凭啥子喃?说完紧紧箍着妈妈的手,不让她走。我妈这时却铁了心,非要走,我拉着她,在铁门前来回拉扯,哭声惹得周围邻居都出来看。我哭着说,妈妈不要走。我奶奶却走上前来剥开我的手,我死死攥着妈妈的衣角,手指甲都变得铁青。看见这个阵仗,周围邻居都上来劝。那天,我妈没有走,晚上陪我一起看电视,给我买了一大堆零食。第二天等我醒来,我妈早已不见踪迹。
我妈走了之后,有人说她在上海,也有人说在广州,总之,我再也没见过她。奶奶是在第二年夏天去世的。中午吃过饭,我们都在客厅吃西瓜,她突然翻下床,说想吃雪糕。她得了食道癌,吃不进东西,仅靠流食维持生命,已经饿得看不见血管,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清。这是她生病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吃点什么。我爸当时在隔壁打牌,听见这个消息,从牌桌子上抽出五块钱,打发我去买。距离我家最近的小卖部有两公里,在加油站旁边。天气很热,怕雪糕提前融化,我抱着一个硕大的搪瓷盅,准备买来后装在里面。水泥路热得发光,我穿着泡沫凉鞋走在上面,感觉脚板发烫。我沿着街道两边的建筑阴影走,心里念着雪糕,越走越快,路过巷口的时候,看见赵成在游戏厅门口打游戏,见我来了,赵成说,余和,来打游戏。我想去,但想起奶奶,只好说,我要去買东西。赵成说,我们一起打一把,打完我陪你去。听到他这样说,我也卸下了包袱,于是坐到赵成旁边。一把打完不过瘾,又接着打了两把,等时间耗尽后,我发现我兜里的五块钱不见了。我在游戏厅里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完蛋了,我不敢回家,回去免不了一顿揍,但奶奶又要吃雪糕,我该怎么办。我想,可能等到下午,天气不热了,我奶奶也就不想吃了。我在街上转了很久,还去河边看人钓鱼,直到天光暗淡才往家走。回家后,家门口围了很多人,我听见我姑姑在哭的声音,这时我爸发现了我,恶狠狠地瞪着我,一巴掌打过来,手里的搪瓷盅掉到地上。他责问道,你跑哪里去了?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我爸又说,你奶奶去世了!我感到天旋地转,四周一黑,晕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听到尖锐的喇叭声,四周开始嘈杂起来,好像是到了。我睁开眼睛,看见陈叔正盯着我,说,到巴中了,正准备叫你呢。我揉揉眼睛说,我睡了多久啊?陈叔说,就半个小时不到。我问,陈叔,我们接下来去哪?陈叔说,你饿了不?我说,有点。他说,先去送货,等下就吃。
陈叔先去小学送货,今天是周末,没有学生,我们到的时候,老板正在后屋打麻将。小卖部没开灯,光线很暗,陈叔掀开帘子进去找人,我在小卖部的货架旁等他出来。小卖部门口摆了很多礼品,蜂蜜、补品、饼干,样样都有。我注意到,包装盒上的名字和超市里不太一样,但长得又一样,一时难以分清。不一会儿,陈叔带着老板出来了,老板是个中年妇女,有些不情不愿,眼睛里面布满血丝。陈叔拉着她说,姐,你就看一眼吧。老板无奈地说,现在的人眼睛尖得很。你上次送的货都还没卖完。陈叔说,这次的货不一样,都是饮料,你看你离学校这么近,天气热了,小孩子一定会来买。你看他。陈叔指指我,现在的学生都喜欢喝这种,又便宜,味道又差不多。说完,陈叔从车上搬下一件饮料来,撕开包装,随便拿开一瓶,摇一摇。姐,你看,这气多足,而且三种口味,雪碧味、可乐味、美年达味,选择多得很。老板最终要了十箱。我和陈叔又陆续去了几家小卖部送货,到了一点过,车上还有一大半。我问陈叔,剩下的怎么解决?陈叔说,不急,我们去大巴山,沿途有很多小镇,那里好卖些。我说,那你怎么不直接全部拿镇上去卖了。他说,镇上给不起价格呀。
从早上到现在,我没吃一口饭,肚子早就饿了。能送的货都送了,陈叔把车开到巴中城里,停到一栋楼的地下车库,带我去下馆子。这个点,饭馆过了高峰期。陈叔找了家饭馆,点好菜,叫我先等他。我问他去哪,陈叔说,去拿“那个”东西。说完,比起一个瞄准的姿势。我说要多久,陈叔说,就在附近。你等一下。饭馆的炒锅架在门口,风从门外吹进来,饭菜的香味四溢,胃部微微抽动着,我吞了口水,又找来杯子倒了杯热水。炒第二个菜的时候,陈叔来了。我见他手中空空如也,问道,东西呢?陈叔说,放车上了,等下给你看。吃饭的时候,陈叔要来一瓶白酒。我说,今天就不喝酒了,喝了酒不影响开车么?陈叔说,等下在车上眯一下再走。我说,睡过头怎么办?我想起他喝醉后经常在仓库里睡大觉。他说,不会。我说,等你醒来,就怕天都快黑了。陈叔说,等天快黑的时候,才是打斑鸠的好时机。
后座的箱子卸了一半,车内宽敞了起来。猎枪放在后排,用黑布包裹着,现出枪身的轮廓。我用手摸着枪托,硬邦邦的,像是摸着生锈的铁。我问,这玩意儿能打中斑鸠吗?陈叔喝得醉醺醺的,没理我,把座椅调平,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过了半晌,看陈叔没动静。我试探着叫了一声,陈叔。他没有反应,睡得像头死猪一样,我又叫了一声,还是没醒。我把猎枪从后座顺过来,再慢慢打开车门,轻轻推开,一面盯着陈叔,一面小心翼翼地用脚尖感知地面高度。看来酒的后劲很大,他一时半会儿醒不来,我揣上一盒铁珠,把猎枪背在背上,紧了紧挎带,再看了一眼陈叔,轻轻关上门,这才往车库出口跑去。
街上阳光刺眼,我根据记忆往铁索桥走去。母亲住在铁索桥旁惠康小诊所的二楼,改嫁那年我曾去过一次,不久后,又被那个男人送了回来。我记得他的长相,白白胖胖的,穿一件泛黄的白衬衣,好赌,身上有一股药臭味。听姑姑提过,这个男人经常欺负我妈妈,奶奶去世的那一年,就是他不要我妈妈回来。已经离车库有一段距离,我找到了一处没人的角落,把黑布扯开,猎枪完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猎枪已经很旧,单管,像烧火棍一样。枪身呈暗黄色,上面有很多划痕。我把枪管杵在地上,掰开枪头,掏出兜里的钢珠,塞了进去。我举起来,有点沉,但问题不大,可以瞄准。我用黑布再次包着,然后背在身上。
铁索桥在南门,我走在滨河路上,远远地就看见它立在不远处的河面上,像一杆秤。河面深绿,春天已经到了,近水处无规律地涌出一串泡泡。我轻轻迈着步子,朝铁索桥走去。铁索桥的石板晃晃悠悠,我有些恐高。上一次来,我妈抱着我,用手捂着我的眼睛,这才敢走过去。我盯着脚下的石板,正在恍惚,身后突然一阵喧闹,我回头看,迎面走来一队老年人方阵,起头的举着一面旗帜,庆祝超市开业,后面的老人紧紧跟着,敲锣打鼓,好不热闹。我停下来,等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想起我妈曾告诉我,过桥走路,人多的时候,要停下来,看一看。队伍越走越远,锣鼓的声音被河风卷入水底,铁索桥不再摇晃。我盯着前方,诊所就在对面,那个男人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围着蜂窝炉烤火,还是在接待病人?这不得而知。我踏上铁索桥,太阳暖洋洋的,我耳朵上的冻疮痒痒的。我快步走在铁索桥上,余光看见有人站在桥下的石头上钓鱼,我边走边往下看,这时,浮漂突然下坠,钓鱼人顺势一顿,钩到了。我又停了下来,看到鱼很大,钓鱼人明显是个新手,很快就形成拔河姿势,旁边的人都过来看戏,指导钓鱼人放线,先周旋几圈。我看钓上鱼还要一段时间,继续往桥尾走去。
我走出一身汗,来到惠康诊所门口。大门紧闭,像停业许久。旁边有一家烟酒小卖部,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台式电脑上打扑克。我问,叔叔,这家诊所老板呢?中年男子很沉迷,没看我,说了一句,还在中医院没回来。我又问,中医院在哪里啊?中年男子说,河那边,最高的那栋楼就是,那么几个大字,自己没长眼睛?我多问了几句,明显打扰到了他。我退出来,往中医院去。回到桥上,钓鱼人还在和鱼搏斗,现在他好像略占上风。我来了兴趣,想要看个究竟。鱼的身子隐隐约约,就要出水了。钓鱼人开始握着鱼竿往后退了,想把鱼拉到浅水处。五米。鱼使劲摇晃。四米,鱼往下钻。三米,鱼翻起白肚皮。钓鱼人招呼朋友拿抄网抄鱼。朋友拿着抄网,伸进水里,慢慢靠近鱼。哦,还是条鲤鱼。朋友大叫着。突然,鱼猛地往下钻,鱼线断了。嗨,跑了。你怎么抄鱼的?钓鱼人指责朋友。朋友说,这鱼聪明呢,一直在磨鱼线。我想了一想,下定决心,开始往中医院走去。
我看著导视牌,医院拢共七层,妇产科在五楼,电梯是病人专用,我只好一层一层往上找。医院热络,消毒水味很浓。我想起上幼儿园那会,我身体差,经常大半夜来医院输液,护士都认识我了,那天不赶巧,给我扎针的是个新来的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扎准血管,手直抖。我妈也是护士出身,看不下去,亲自上手才扎准的。不知我妈长变了没有。二楼是医院的办公室,窗明几净的,我往三楼走,三楼是骨科,过道里摆满了床,空气中有一股腐烂味。旁边一个病房有歌声传出来,声音微弱,仿佛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时,一个老爷爷拄着拐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嘴里叼着一根烟,还没点燃,他盯着我,好像注意到了我背上的猎枪,我没再停留,继续往上走。
我背着猎枪走了很久,重倒不是很重,就是很长,尤其是上台阶,走几步就要调整一下挎带,好让猎枪紧紧贴着我的脊背。但越往上走,呼吸变得越沉重。到了五楼,我挨个病房找,玻璃窗很高,我踮着脚往里看,找了一圈没找到我妈,我心想万幸,我妈不在最好,只要那个男人出现。转了一会儿,不见有人,我去问护士,护士说,产房在另外一栋楼,不早不晚,我妈已经进了产房。我只得往另一层楼走去,一路恍惚,不管那么多,时间紧急,我得在此之前办完这件事。产房在对面楼二层,我几个小跨步就上去。刚走到门口,发现门口围了一堆人,那个男人正在其中,把背露了出来,手里夹着一根烟。好多年过去,这男人还是老样子。人太多,我不方便动手,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好时机。我藏在安全通道里,时不时地从门缝里往外看,产房外的人很焦急,大概是在想着我妈到底是正在生男孩还是女孩。不知道我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场景。过了一会儿,产房门打开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跳很快,耳朵闷闷的,像被水泥堵住了一样,听不见医生在说什么,只见围着的人突然就冲进了产房。我妈应该生了。这下麻烦了,我妈在里面,我更不可能动手。不知道安全通道里的声控灯熄灭了多久,我坐在冰冷的阶梯上,隐隐听到外面有哭声,哭得死去活来的,我想出去看个究竟,又始终迈不出去。我于是朝上走,来到天台,心跳还是很快,我把猎枪放下来,躺在地上,闭上眼睛,阳光被云朵遮住,有点冷飕飕,人一冷,就感觉血液在流回胸膛。不知躺了多久,医院楼下响起鞭炮声,持续了很久,世界好像在这一刻土崩瓦解。我仿佛睡了一觉,脑袋里一片空白,心想,我该回去了,这么大的声音,陈叔怕是醒了。
陈叔你听我说,我看你睡得香,呼噜声大,要是有人来地库停车,過来看个究竟,那不全幺台了?往轻里说,人家举报你车里有杆猎枪,而且到处卖歪货,警察来了至少关你十天,你卖的钱统统都要上交。哎,对了,警察不能来,要是真来了,就冲你,啧,你闻闻你呼出的这嘴酒气,估计车里全沾满了酒精,拿点火机一打,整个车里都要燃起来,人家至少给你安个酒驾未遂的罪名。我们进巴中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外地来的大货车都被拦住了。就凭你这辆破破烂烂的渝F的外地长安车,人家蹦起来乱弄你,你没有半点脾气。你问我为什么背着猎枪出去?这你错怪我了,我睡不着,就在滨河路看人钓鱼,我把猎枪拿上是怕你醒来直接走了,不带我。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去大巴山,还怎么去看我妈呢?我老实告诉你,我怕你真不带我,我把子弹都揣上的,你看,兜里揣不下,我都上膛了。好,我不对着你,但我是真的害怕,你要是真走了,十天半个月才来一趟,我总不能走路返回吧。
我一边往地库走,一边想着陈叔醒来后到处找我,我该说什么话。一路晃晃悠悠,凭着本能直觉,我到了地库门口,入口处背阴,黢黑一个口。听说大巴山是喀斯特地貌,山里都是空的,说不定就和地库一样。这个点,车库的车很少,只有几辆沾满灰尘的车停在角落。陈叔的车还在老位置。我走上前去,看见陈叔的脚翘在方向盘上,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了,嘴里还时而念叨着几句,说着梦话,没有半点醒来的迹象。我把猎枪放回老位置,也学着陈叔,把座椅调平,脚翘起来。
闭上眼睛,鞭炮的声音充斥在我的耳边,中间还夹杂着婴儿的哭声,来回循环,我好像又躺到了医院天台。我只好再睁开眼,直直地盯着车顶。地库里很黑,明明窗户严丝合缝,却总有一股阴风往我后背钻。这时我眼睑干涩,很痒,我越用手去挠,它越痒。你在哭啊?旁边突然响起一声,陈叔醒了。我转过一旁,快速擦掉眼泪,直起身来说,咋可能,就是你这车里味道太难闻了,地库又不通风,我眼睛干干的。他说,想家了?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接着又问,陈叔,现在几点了?陈叔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糟了,快五点了,我们得赶紧了。我心想,对,我们要去打斑鸠。
车子驶出巴中的时候,太阳已经变得微弱,像片快要融化的橘子味硬糖。我问陈叔,现在来得及打斑鸠不?陈叔说,来得及,我这货镇上要得多,只要到了,分分钟卖完,对了,你确定今晚不回去,你姑姑就不担心?我说,你放心,我姑姑回乡下了,周末两天都不在。陈叔说,那干脆打完斑鸠,你和我去奉节。我说,去奉节干嘛?陈叔说,你知道你妈住哪里了?我说,知道,到了我会叫你把我放下来。陈叔说,那到时候多打两只斑鸠,你给你妈带过去,补补身子。我说,你先好好开车,别到时候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陈叔说,天黑了,我们就找个小旅馆住,第二天早上早点起来也可以。我说,你不是说晚上最好打吗?陈叔说,忘了给你说,早上也是好时机。我想起医院的事,口中念念有词,怎么好时机这么多,我咋就遇不到。陈叔问,你说什么?我说,尽快吧,我早上赖床,怕起不来。陈叔笑着说,我尽快。
车子穿行在山道上,弯道很多,七拐八拐,陈叔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方向盘。陆陆续续有飞鸟一闪而过,天都快黑了,但距离陈叔说的那个小镇还没到,我有些心烦意乱,于是我问陈叔,斑鸠肉很好吃?陈叔说,你吃过鸽子肉没?我说,吃过,鸽子汤很新鲜呢。陈叔说,味道差不多,但又有点不一样。我问,有什么不一样?陈叔说,野味。我说,野味是什么味道?陈叔懒得解释,你吃了就知道了。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路开始不好走了,坐在车里,就像坐在摇摇椅上。陈叔低头点烟,没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坑,前轮陷了进去。他让我下车看一下。我走上前去,看了一下坑的高度,应该能过,就示意陈叔继续开。我在路边找了几块石头,垫在车子的前轮,几个来回,轮胎还是打滑,上不来了。我们下车蹲在路边,半天也没有车来。手机已经没电了,前面几公里就到镇上,陈叔叫我待在车上不要走动,他记得前面有个汽修店,他去找人来帮忙。
车灯开着,周围便显得暗。我不知道陈叔什么时候回来,等了半天,前面路上没有半点灯光晃动。这时,山里传来斑鸠咕咕的声音,好像就在前面的树林里。这声音无比熟悉,像是在召唤。前面漆黑一片,我走到近处,往树梢扔石头,但扔得不高,晚风冰凉,我一个寒战,我又想起了妈妈,不知道妈妈在医院里怎么样了,她会觉得冷吗?从小到大,我独自度过很多个夜晚,它们虽然逝去,好像在此刻又重新汇聚起来,在我眼前,沥青一般浓稠,我看不见任何东西,喘不过气一样,陈叔怎么还不来?我心里有些焦急,也有些害怕,远处石头的轮廓在此刻都变得阴森。我回到车上,躺在驾驶位,斑鸠还是咕咕在叫,就像在我耳边。我突然想起那个男人的样子,背对着我,一根烟一根烟地抽着,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拿上猎枪,关上车门,朝树林走去。至于陈叔回来了,要怎么找我,或许会叫我的名字,或许原地等我,最严重的无非抛下我一个人走掉。在我这个年纪,别人随意的一个选择,可能就会让我难以承受,但是我无法再等待,明天太过遥远,我现在就要去打斑鸠。
【作者简介】苟海川,生于1996年9月,四川巴中人,2021年开始文学写作,同年获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二等奖,里程文学院第一期湖南作协“新青年”写作营学员。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