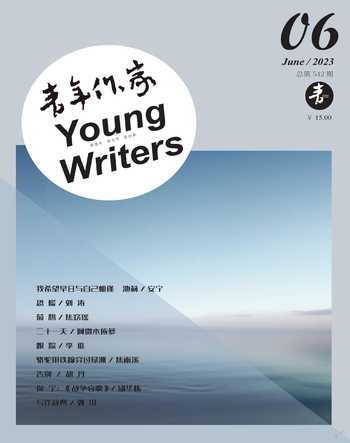胡驼背
胡驼背要开厂。李素芹要招亲。消息很快就在九眼桥33宿舍传开了。
九眼桥是一座石拱桥,坐落于成都府河上,桥如其名,有九孔。府河绕市区蜿蜒而行,河水裹挟着褐色的枯枝、破旧的塑料瓶,吐着白色的泡沫,来到九眼桥,撞上桥墩,激起土黄色的浪花,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滚滚而过。
临河东南处有一老居民区,门牌号是宏济路8号。五十年代修建的院子,隶属于四川大学后勤部管理,在学校建筑清册上编号33,老一辈人习惯称其为33宿舍。这里住着几十户老成都人。
院里是白墙黑瓦的平房。房子有些年头了,雨水顺着屋檐浸下来,经太阳一晒,白墙上留下一搭黑一搭白的渍迹。窗户一律漆成红褐色,框子表面凸起划痕和斑点,像麻脸妇人长了些岁月的皱纹。
有人家在屋檐下用青黄的竹蔑条搭个小棚子,养上两三只兔子。兔子全身白茸茸的毛,小眼睛红红的,透亮得如同玻璃弹珠一般,很是可爱。逢上年节,兔子就进了炖锅。待卤煮熟了,孩子们就站在院坝里,用手掰扯兔头,细细地啃骨缝里的肉,左一下右一下地嘬手指,滋滋有味。从未听说九眼桥哪家孩子为兔子丧命号哭的。一旁的狗却不晓得兔头早已啃干净了,依然昂着头,眼巴巴望着接嘴。
走进院子,经常可以看见两三个老太婆围着老蓝布围腰,坐在丝瓜架下,一边做针线活,一边扯闲篇。几只鸡转着圈一颠一颠地找食。陌生人进来了,黄狗也只是懒懒地吠一两声,嗅一嗅,就走到一边去了。
李素芹住在院子靠左边第一间房,位于上风口。正房两间,带一个小厨房。房门口挂着半截老蓝布帘子。窗台上放了一盆葱,一截白,一截青,根根直立,做菜时掐一把,很顺手。
院子小,一家炒菜,满院子闻到油烟味儿。每逢李素芹炒回锅肉,那香味儿更让人垂涎欲滴。拣肥瘦相间的二刀肉,煮八分熟,切成薄片儿,熬成灯盏窝,浇一勺郫县豆瓣,铲两三下,再撒一把青蒜苗,掂几下炒锅,一盘回锅肉就出锅了。灯盏窝儿堆在白瓷盘里,肥嘟嘟,亮闪闪,滴着红油珠儿,香味扑鼻。
邻居走过窗前,闻到香味儿,忍不住深吸两口气,探头搭讪道:“素芹手艺好哦。今天打牙祭。”
“来吃嘛。”
“哪好意思麻烦。”邻居笑了。
“麻烦啥子哦,添双筷子的事。”
夏天,李素芹常穿一件红底黑格子的衬衫,下摆扎进牛仔裤,干脆利落。她在树下梳头,弯下腰,用一把牛角梳从发根拉刮到发尾,旋即直起身,把一头齐腰的长发一甩,一股海飞丝香波味儿飘了出来。路过的人禁不住站下来多看几眼。
除了这头黑且直的长发,李素芹的长相实在经不起细看。她身材结实,骨骼粗壮,大脸盘,皮肤经成都温嘟嘟的太阳一捂,变成老姜的土黄色。笑起来脸颊的肉便一齐朝鼻梁中间挤,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脸上仿佛缭过一团火焰。
她从成都财贸学校毕业后,在宏济路一家街道企业当会计。父母去世得早,大姐去云南上山下乡,留在当地成了家,剩她一个人在成都单独过活。三十多岁了,没有婚配,难免引起邻居好奇。最近院子里孙大姐介绍她相了两次亲,一个都没有对上眼。不过,李素芹总算开始相亲了。
这天早上,李素芹在厨房里煎荷包蛋。磕开鸡蛋,是个双黄蛋。邻居谭二娃路过,伸头一看,打趣道:“哟,双黄蛋,这盘又黄了两个。”这后半句似乎影射她近来相亲不顺利。李素芹把锅铲往锅沿一敲,骂道:“关你屁事,多嘴多舌,不说话能憋死你。”谭二娃吐吐舌头,躲到一边去。
谭二娃后面还跟了一个人,这时候闪了出来。是胡驼背。他长着一张青白色的脸,眼睛像两粒亮晶晶的黑色玻璃纽扣,嵌在浓眉下。头发自然卷曲,黑油油的,梳得整整齐齐。个子1米6左右,前面鸡胸,后背耸着一个驼峰。他的面容倒是很耐看,有几分清俊。
胡驼背虽然背驼,但走路却一贯昂首挺胸。他背剪着雙手,笑眯眯地说:“双黄蛋,好兆头,素芹今年要出双入对。”李素芹扑哧一声笑了,说:“好你个机灵鬼儿,会说话哄人。”
胡驼背乘机掀开半截门帘子,迈步进了屋。李素芹说道:“有啥子事,赶快说,我还要去上班。”
“我要办工厂,来请神。”胡驼背一本正经。
“请神去庙子,来我这里干啥子?”
“我信你。”
“胡说八道啥子,快说正经事。”
“素芹,我办工厂要请个管财务的。你的本事,我信得过。拿工资还是入伙,由你选。给我几年时间腾挪,一年挣个十来万不是梦。”
“容我想想。”
胡驼背是九眼桥一带远近闻名的人物。老一辈人还记得1963年发生的事情。住在33宿舍有户胡姓人家,男人在工地拉架架车,女人在家糊火柴盒。女人身体不好,只生育一个女儿。有一天,胡家女儿在府河游泳,捞起一个木盆,里面有一个碎花包袱裹着个婴儿。她把婴儿带回了家。胡家男人伸手进襁褓摸了摸,是个带把的。寻思一阵,把婴儿留了下来。请邻居王爷爷起个名,王爷爷捻着胡须,沉吟半晌,说道:“就叫水生吧。起个贱名,好养活。”
胡水生却不好养活。这孩子三四岁时,整日哭闹,小脸涨得通红,全身出大汗。抱去医院,医生说孩子得了佝偻病。慢慢地,胸脯长成了鸡胸,后背也拱出一坨。
胡家两口子垂头丧气。男人打算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找王爷爷商量,说道:“老天爷不给这娃儿赏饭吃啊,我贫家小户咋个养得起残疾人。”王爷爷叹息道:“老天爷哄人,你就得受着。九眼桥头的九树王被雷豁了口子,还照样长成参天大树。日子长着呢,这世道哪里就缺他一口饭吃呢。”
胡家终于留下了这个娃儿。
院子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叫他胡驼背。这孩子虽然身体残疾,脑瓜子却好用得很,书念得尤其好。李素芹大他两岁。他喜欢跟在李素芹后面跑,有李素芹罩着,谁也不敢欺负他。
夏天,九眼桥一带的小孩喜欢在府河游泳。那年头,府河水还是青丝瓦亮的。九眼桥头有一棵黄葛树,当地人称之为“九树王”。这棵树上百年了,站在桥头,伸腰展枝,迎风而立。高五六丈,胸径两三丈,七八个小伙子手拉手方能环抱。树根曝露出地面,黑褐色的,蜿蜒交错,牢牢咬死泥巴地,最长的根横爬出去十几米。这一带孩子喜欢比赛从九树王往河里跳。
那时院子里有两拨孩子。各有一个头儿。一个是李志勇,他年龄不到二十岁,混成了九眼桥的街娃。脸肥唇厚,粗眉大眼,手大脚大,隔三岔五领着一帮孩子翻墙爬树,粘知了、掏鸟窝、打弹弓。有一回捅了马蜂窝,被蜂子追着咬,蜇了满脸的包,得个绰号“毛脚”。
李志勇的对头是丁国庆,白皮细肉,单眼皮,薄嘴唇,能说会道。他妈是九眼桥街道的居委会主任。胡驼背跟他一伙。
这天,两拨孩子在府河边碰上了。毛脚把手向江中心虚晃一砍,说:“大家各游一半,井水不犯河水。”丁国庆一看,九树王划给了对方,便说:“凭啥子九树王在你们那边。”
毛脚翻了个白眼,骄傲地说:“我们人人都敢从九树王往下跳。”他斜瞟了一眼胡驼背。丁国庆便说:“我们也敢,不信比比看。”
毛脚说:“我们各出一个人,来比拼。不光要从树上跳,还要比谁游得远。谁输了,就不准再来府河游泳。”娃娃们齐声喊:“比就比。东风吹,战鼓擂,环球世界,谁怕谁。”
毛脚睃一眼这帮大大小小的娃娃,手指头点来点去,口里念道:“点兵点将,点到你。”正好指着胡驼背。胡驼背那年刚八岁,瘦小干巴,是这帮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毛脚欺他年幼,又是驼背,谅他不敢跳水。谁知胡驼背眼都不眨,跨前一步,小手指着毛脚,说:“我就和你比。”毛脚说:“你挑我比,我可比你大,输了不要说我欺负你。”
丁国庆忙伸手拉住胡驼背。胡驼背甩开他的手,脱掉衣服,往地上一摔,跑上桥头,抱着树干噌噌地上去了。毛脚也选了一处,站在树枝上。下面的人喊:“预备,跳。”只见胡驼背如脱弦的箭直插入水中,竟比毛脚还快了三秒。
两边的娃娃各自助威,加油声喊得惊天动地。桥上的行人听说两个小孩比赛游泳,有一个还是驼背,禁不住好奇,纷纷停下脚步,指指点点地看比赛。九树王边上有家小吃店,吃饭的人听得喊声,把碗一丢,也站起来,涌到桥边,伸着头叫好,急得店小二慌忙拉着客人收饭钱。
毛脚游到府河的三分之二时,想打转身,却见胡驼背还在朝前拱,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往前游。胡驼背光着小身子,驼峰像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水面起伏。他游得飞快,到了对岸,身子一侧,脚一蹬,调头接着往回游。
桥上的人喊起来:“小驼背别游了,快回去。”人们觉得这孩子的体力够不了来回。毛脚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别游了,算你赢了。”
胡驼背把头浮出水面,换了一口气,说:“不叫算我赢,就是我赢了。”在众人的惊呼呐喊声中,他游了个来回。上了岸,娃娃们用手臂搭个马架抬着他,雄赳赳地沿着九眼桥游行一圈。胡驼背一战成名。王爷爷说:“从小看大,这小驼背性子野,赌性大,将来有得看。”
王爷爷真还说中了。胡驼背高中毕业后,摆摊卖过衣服,倒腾过家电,开过水电修理铺,从来没有消停过。现在,院子里的人听说他要开工厂,觉得他又要干一件大事了。
这天傍晚,丁国庆一家在院子里支开了小方桌,围坐吃饭。桌上摆了一簸箕油炸蚕蛹,一盆白面馒头。
谭二娃站在边上,伸出烟熏黄的手指头,从簸箕里拈了个蚕蛹,嚼了几口,白色的肉油顺着嘴边淌。他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说:“丁哥,你晓得胡驼背发财了,要开工厂的事情吗?”
“晓得。说是开个热毯子厂。”丁国庆顺着搪瓷碗边哧溜喝了口白米粥。
“那个叫电热毯。胡驼背财运旺,做生意没有不成的。这盘办厂,你想不想入伙?”
“想入伙,还得人家愿意收你。听说胡驼背对李素芹有意思。”丁国庆的老婆马大嘴插了一句。
“胡驼背已经去请李素芹入伙了。”谭二娃说道。
“看嘛,胡駝背成天在李素芹身边晃,我早就看出他的心思了。”马大嘴撇了撇嘴。
“那还得看李素芹有莫得这意思。他再有钱,也是驼背。”丁国庆捏了一个蚕蛹扔进嘴里,嚼得脆响。
“现如今,有钱就好行事,啥子女人找不到。”谭二娃酸溜溜地说道。
“不要乱说,积点口德。”王爷爷从边上走过,听到了谭二娃的话。
“胡驼背开厂的事情,街道办事处的张科长还没点头,怕出乱子。”丁国庆顿了顿,说道。
几个人说得闹热。隔壁孙大姐伸着耳朵听去了。吃过晚饭,孙大姐就转进了李素芹家,跟她叨咕一阵。孙大姐刚走,李素芹就站在院子里,骂道:“背时砍脑壳的,瞎嚼啥子舌根。个人想钱想疯了,攀扯旁人做啥子。”马大嘴急忙关上窗户。
李素芹在屋里生闷气。胡驼背笑嘻嘻地踱了进来。李素芹恼怒道:“你还来做什么,闲言碎语还不够多吗?”
“你管那些闲话干啥子?痛快给个话,愿不愿意一起干?”
“厂里事情多,一时半会儿怕脱不了身。”
“位子给你留着。啥子时候愿意了,招呼一声。”
“你厂子不是卡壳了吗?”
“丁国庆帮我约了张科长。明晚在九树王火锅店摆一桌。你来嘛,帮我扎个场子。”
李素芹没做声。胡驼背朝屋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嘿嘿一笑,说:“我是丑八怪,可你也不是太漂亮啊。”李素芹站起身,抓起一把蒲扇砸过去,笑骂道:“你欠揍啊。”
九树王火锅店生意好,人气很旺。店里店外摆了十多桌。四个大风扇立在四方哗哗地吹。几十人坐在一起,抡起胳膊烫火锅,热气腾腾。男人们上半身打个光胴胴,露出半个肥白的肚子,吃得大汗淋漓,抹一把脸,一甩手,汗水飞到电线杆上。女人多半很精致,穿个碎花吊带裙,显出紧仄的腰身,涂着红色蔻丹指甲油的手指翘起,筷子上拈着一根鸭肠或一片毛肚,慢慢悠悠地在锅里上下涮。
胡驼背订了张大桌子。张科长坐上位,一行人围坐下来。店伙计端来一个锃亮的黄铜盆子,往炉盘上一架,啪地一声打燃火。一会儿,盆里便翻江倒海起来。红尖椒、麻花椒、白葱节在红汤里翻滚,香气渺渺升起。鸭肠、毛肚、黄喉、毛血旺,还有青绿的藤藤菜、白花花的藕片,摆了一桌。
丁国庆用牙巴咬住啤酒盖,轻轻一用力,呸地一声吐出瓶盖,把玻璃杯逐一斟满,大声说:“今天胡驼背请客,大家吃喝高兴了。”
胡驼背端起酒杯,说:“来捧场的都是九眼桥的街坊邻居。大家这么多年都是靠张科长照应。第一杯先敬张科长,先干为敬。”说完,一仰脖咕噜噜喝了下去。丁国庆说道:“张科长是九眼桥的父母官。我干了。”张科长笑嘻嘻地,说:“诸位客气了。”他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众人齐扑扑伸筷子向盆里捞菜。谭二娃抄起一筷子鸭肠,在盆里上下涮,嘴里念叨:“七上八下,熟咧。”呼噜噜像吃面条一般赶进嘴里。酒过三巡,谭二娃发了言:“李素芹歌唱得好,给我们来一个。”张科长转过头,只见李素芹一张脸被酒精熏得红红的,梳了个油亮蓬松的大辫子,灯光下颇有几分妩媚,便拍手道:“好啊,来一曲。”
李素芹并不推辞,站起身来,说:“好,凑个兴。”便唱了一首《难忘今宵》。她把声线抛得高高的,压住了周围嘈杂的人声。众人的心尖儿随那歌声到了最高处,又缓缓地落下来,仿佛干涸的土地饱吸了一场细雨,五脏六腑无处不受用。
张科长笑道:“这一杯,敬九眼桥的巾帼英雄李素芹。”李素芹笑道:“我哪里是啥子英雄。”丁国庆鼓掌笑道:“对,英雄敬美人。张科长是英雄。”谭二娃兴奋地嚷:“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杯酒喝了,胡驼背的厂子就开张了。”
李素芹不禁面上一沉。张科长的手举着酒杯僵在那里。胡驼背站起身,笑眯眯地说:“谭二娃喝多了,一杯酒而已,张科长啥子阵仗没见过。厂子的事情后说。这杯酒我要买个马,敬素芹是女中豪杰,张科长是人中龙凤。”三个人一起笑了,干了这杯酒。
酒宴过后,满院子的人都以为胡驼背的工厂要开张了。但时间过了三个月,仍然没有动静。人们不禁觉得奇怪。胡驼背请来的三四十个工人,眼巴巴等着。
这天,胡驼背来到街道办事处,见张科长坐在办公桌前,便一头钻了进来。张科长忙让了座,泡了一杯三花茶。胡驼背端起杯子,吹了吹茶叶沫,抿了口茶水,说:“科长忙,顾不上我的事。我厂房空着,一天的租金不是小数目啊。”
张科长蹙着眉,说:“胡驼背,我实话实说。办工厂是好事,但你能不能办个其他啥子厂?这个电热毯,不安全,万一触电了,非死即残,你我要吃牢饭的呀。”
“放心。我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出质量问题。”
“唉,驼背,我心里七上八下。这事搅得我觉都睡不着。你晓得不,有一家国营大厂要上这个项目,你争不过人家的。”张科长苦着脸。
“明白了。你放心。我就要比一比,看谁家的产品过硬。”胡驼背拍拍胸脯。
院子里的人对电热毯议论纷纷。孙大姐对马大嘴说:“万一娃儿在毯子上拉泡尿,见了水,不得触电吗?谁能保证娃儿不拉尿。”马大嘴听了,心里惴惴不安,对丁国庆说:“你别一天跟着胡驼背跑。这毯子插着电,人睡在上面,真没事?万一漏电呢?”丁国庆见了胡驼背也不吭声了。
一连十多天,阴雨绵绵。野猫儿上了李素芹家的屋顶,刨漏了瓦,雨水滴滴答答淋了一夜。天刚亮,她就来拍胡驼背家的门,喊:“驼背,起来没?我家屋顶漏雨了,快去请人来拣瓦。”胡驼背一骨碌翻起身,说:“你等到。”他飞跑着去请学校后勤部的拣瓦工。
拣瓦工是个不苟言笑的汉子,扛着木梯就来了。李素芹站在一堆大大小小接水的塑料盆子中间,愁眉不展。他见了这情景,便把脸故意一板,佯作生气的样子,说:“上个月不是才拣了瓦吗?”谭二娃正在院里漱口,走拢过来瞧热闹,笑扯扯地说:“母猫儿叫春呐,又刨烂瓦了。” 李素芹瞪了谭二娃一眼,说:“就你懂得多,别就是你家母猫造的孽。”胡驼背赶忙打岔,说:“上个月来的是个小年轻,没拣好,还得靠老师傅的功夫过得硬。”
拣瓦工听了这话,就把木梯顺着屋檐一架,噔噔几步,轻轻一跃,上了屋顶。他翻捡一阵,半个时辰就干完了活路。洗了手脸,接过胡驼背递上的白芙蓉,夹在耳朵上。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两口红白茶,说:“驼背,有事尽管招呼。”抬腿走了。
晚上,李素芹端了一碗回锅肉,来胡驼背家。走到门口,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一个男声说道:“这事我去干,贱命一条。万一我没了,只求厂里照顾好我婆娘娃儿。”李素芹张头一望,是一个民工模样的人在说话。
胡驼背沉着脸,说:“我是厂长,谁也别跟我争。”丁国庆说:“我一早就去请张科长,保证把他拉来现场。”胡驼背对谭二娃说:“电从你家拉。怕不怕摊上事?”
“街坊邻居还说这些,怕就不跟你干了。”谭二娃拍拍胸脯。
李素芹走进屋,对胡驼背说:“你忙完了,来找我。我在九眼桥河边等你。”胡驼背点了点头。
夜深了,胡驼背来到九眼桥河边。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地响。路灯发出昏黄的光芒,几只飞蛾绕着灯杆飞舞,电线杆拉出一道斜的长影子。李素芹靠在灯杆上,抱着手臂,问:“驼背,你到底想干啥?”
胡驼背的脸在路灯下显得有些发青,嘴角边起了几粒红疹子。他淡淡地说道:“你放心,工厂能开张。打个赌,厂子开张了,你一准要来。”
“要是没有开张呢?”
“没开张,我手心手背煎鱼给你吃。”胡驼背伸出手掌,上下一翻。
“这么有信心。”李素芹一时起了玩心,拍手过去,正打在他手掌心。
“要没这个自信,你能跟我交朋友?”他握住李素芹的手。
“我就喜欢你心气高。一言为定,厂子开张,我就来。”
第二天清晨,王爷爷把画眉鸟笼往树枝上一挂,拉开膀子,打起了八段锦。谭二娃站在窗前,冲着府河方向,啊——啊地大声号叫。院里人都知道他在练“狮吼功”,学的是某位武林高人。李素芹在树下梳头。孙大姐打开房门,扫门前落叶。
突然,院子里涌进来一群人。有的抬着木盆,有的扛着像铺盖卷的東西,他们簇拥着一个人——是胡驼背。黄狗开始吠叫,一溜烟地跑去张望。大家迈开脚步,交头接耳,互相问要干啥子。
胡驼背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打着酱紫领带,岔开小腿,站在院子中间。人群很快聚拢过来。后面的人被挡住了,便站在自行车架上,伸着脖子观看。胡驼背开口道:“街坊邻居们,这么多年我仰仗各位支持才有今天。现如今我和一帮兄弟开发了电热毯。大家怕漏电,我先试一盘。” 人们互相问驼背打算咋个试。
天空忽然下起了雨,雨点滴滴答答地落下来,砸在人身上。有人喊:“快跑,回去收被子啰。”更多的人却舍不得走,撩起衣服遮住脑壳,探着头,要看个究竟。
这时候,一个民工打来一桶水倒进盆里,把电热毯泡进去,又从谭二娃家拉出插线板,插上电热毯插头。
胡驼背挽起裤腿,开始脱鞋袜。黄狗兴奋地甩着尾巴,围着他打转,蹭他的光腿。李素芹站在人群里,立刻明白了他要干啥子。她紧紧抿着嘴唇,拳头攥紧了,心噗噗直跳。胡驼背冲她点了点头,轻松一笑。
“让让,大家让一下。”丁国庆分开人群,打着雨伞,拉着张科长,挤到了最前面。张科长一看这阵势,脸一下白了,尖着嗓子喊道:“胡水生,你不要乱来,出了事情,责任自负。我可没有逼你。”
“张科长,我这是给街坊邻居们一个放心,与你无关哈。”雨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衣服打湿了。他干脆一把脱掉西装外套,扔给了谭二娃,说声:“接住了。”然后把领带往脖子后一甩,两只脚扑通跨进了木盆。他打了个激灵,趔趄了一下,站立不稳。人群发出惊呼:“倒喽,倒喽。”还有人喊:“触电了,快拿木棒揍他。”
李素芹冲出人群,飞奔过去。他却已经稳稳地站住了,在盆里转了三圈,笑嘻嘻地说:“大家看看,这电热毯见水漏电不?”
众人鼓起了巴掌。胡驼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大家看清楚了吧,尽管放心。”
雨停了,灰蒙蒙的天空撕开了一抹亮色,云朵儿镶上了淡紫色的边。李素芹扶住胡驼背,用一方白毛巾帮他擦了脚。胡驼背穿上鞋袜,原地跳了两下。张科长长出了一口气,捏了捏胡驼背的肩头,说:“驼背,真有你的。”
夜晚,月亮又大又圆,在青云里时隐时现。月光融入府河粼粼细波之中,仿佛无数的银鱼入水,欢喜跳跃,让人忍不住竖起耳朵,去听那鱼跃的声音。两人绕着府河边走。李素芹埋怨胡驼背:“亏你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昨天晚上咋个不跟我透个底,真出事了咋办?”
“说了,你不是要担心一夜吗?我不怕,这辈子命都是赌来的。走吧,去我家,弄点吃的。”
两人摸黑进了家门。胡驼背伸手拉开白炽灯,屋里一下亮堂起来。李素芹进了厨房,伸手摸了摸锅碗瓢盆,没半点油腻。胡驼背拿出一坨牛腩,剁成块,在油锅里爆香,掺入开水,又烫了几个番茄,撕了皮,丢进锅里,收了小火,慢慢熬炖起来。
他拿出一瓶老白干和两个玻璃杯,悄声说:“这牛肉得炖一阵呢。”
两人碰了下酒杯,静夜里叮的一声,又响亮又清脆。胡驼背借着酒劲,一把抱起李素芹,放倒在床上。她黑漆漆的长发散开来,像府河里缠绕的水草。胡驼背只觉得整个人都被水草缠住了,双手汗津津的,拼尽全力想抓牢什么,最后整个人扑进了她的黑发里。
月光洒进来,半个屋子都笼罩在月色之中。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牛肉在炉灶上咕嘟咕嘟沸腾,香味弥漫。两人终于平静下来。胡驼背伸手在床头柜上摸索,抓到一支烟点燃,深吸了一口,红红的烟头一闪。胡驼背说:“素芹,我一出生就挨老天爷一锤子,亲生爹妈都不知道是谁。今天你让我这辈子圆满了。”
“驼背,我打小和你一起混,你向来活得敞亮。老天爷就是把你锤成渣,搅和起来,扔进炉子,你还是块响当当硬邦邦的红砖头。”李素芹把头枕在他的胳膊上。
时间又过去两个月。胡驼背的工厂还是没有开张。那家大厂从国外引进生产技术,先开工了。他前期投入的资金打了水漂,折损了一大半的钱。
街道厂的小姐妹约李素芹去深圳打工。李素芹来找胡驼背商量。胡驼背说:“我晓得你是不甘落下风的人。这盘我虽栽了跟头,可没灰心。你愿意留下来,我们再起炉灶一起干。你要走,我也没道理拦你。”
胡驼背在九树王下开了一家面馆。开张不到一年,他家的杂酱面就远近闻名了。临近饭点,人多得坐不下。有开宝马车的老板,有蹬偏三轮的市民,也有拉三轮车下苦力的人。客人不拘身份,拼个桌,坐在一起吃面。唯一的分别是,胡驼背看见下劳力的人,手上给的面分量多点,三两的面给足三两五。
跑堂伙计喊声:“杂酱三两。”胡驼背站在一方小木头凳上,抓一把面扔进锅里,五六分钟过后,用笊篱捞起面条,倒入青花瓷碗里,浇一勺油汪汪的酱肉臊子,撒一撮翠绿的小葱花,往客人面前一放,冒着热气。客人夹起一撮面条,迎着光一照,红油顺着面条滴下来,肉臊子趴在面条上,活像蚂蚁上树一般。
李素芹站在面店前。九树王的树叶随风飘落,府河上白茫茫一片。叫卖声、车流声、说话声,还有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空气像一锅煮滚的水在沸腾。她不禁有些走神。忽有客人喊:“老板娘,收钱。”她打了个愣怔,定了定神,转身进了店。
【作者簡介】汪仁,曾用笔名含笑;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自由撰稿人;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