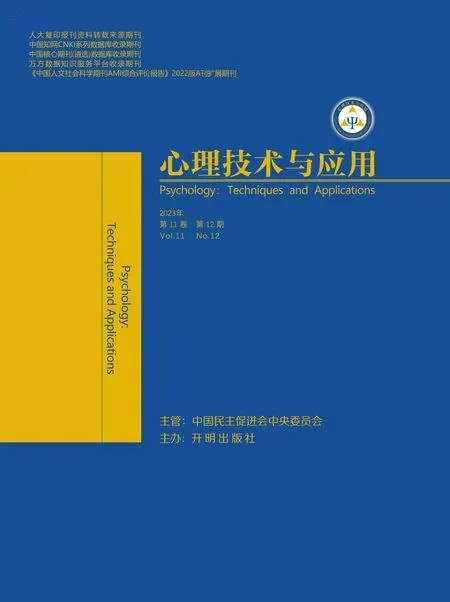幸福忧虑:一种对幸福的“反常”心理状态
徐皓洋 张永红
(1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
(2 成都理工大学,成都 610059)
大笑会唤醒悲伤。(Laughing loudly wakes up sadness.)
——伊朗谚语
1 引言
Seligman &Csikszentmihalyi(2000)开创的积极心理学被认为是一门“有关幸福和人类优势的科学”,在国内外积极心理学领域中,关于“幸福”的研究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孙彩云等,2020)。其原因在于,幸福是个体最常见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积极情绪,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想要追求的东西。然而在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我们不禁会反思关于人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获得幸福都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所有人都乐于追求幸福吗?答案似乎并不是肯定的。
近年来,Joshanloo与其团队考察了世界上多个不同国家、宗教和文化中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态度,他们发现,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对幸福持有消极、回避的看法,认为幸福会带来负面后果(Joshanloo,2013)。为此他们首先通过整理有关“幸福厌恶”现象的相关事实或研究证据(Joshanloo &Weijers,2013),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操作性定义和量表编制建构了“幸福忧虑”(Fear of Happiness)这一心理状态变量(Joshanloo,2013),即指个人因担忧“体验、表达和追求幸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心存对幸福的消极心理状态,并以不同的理由避免与幸福之间产生关系(Joshanloo,2013;Joshanloo &Weijers,2013)。
幸福忧虑受到来自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既具有跨文化性,同时也不乏普遍性。而在当下人们普遍面临社会生活压力和精神愉悦追求难以平衡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并进一步深化有关幸福忧虑这一看似“反常”的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本文围绕幸福忧虑这一主题,系统综述有关幸福忧虑的跨文化证据、操作化(测量)、理论观点、事实性原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研究成果,最后探讨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
2 幸福忧虑的跨文化研究证据
2.1 不同文化对于幸福的重视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认为,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幸福,无法获得幸福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可能会被视为一个人最大的失败经历之一。在西方很多关于幸福的研究都基于“幸福是个人应该追求并负责去实现的东西”这样的假设(Joshanloo,2013)。在美国,人们通常认为,不能表现出幸福的状态会令人感到担忧(Eid &Diener,2001)。
然而,将幸福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之一的想法远非普遍存在(Ahuvia,2001;Lutz,1987)。许多现有的证据表明,幸福在东方文化中并不像在西方文化中那样受到重视。例如,东亚人比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在许多社交场合表达幸福是不合适的(Safdar et al.,2009)。在一项关于对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Lu &Gilmour(2006)发现中美两国民众在不同导向的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美国人具有更高的个人导向主观幸福感,他们认为幸福既是个人的责任也是明确的追求;而中国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导向主观幸福感,秉持关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的辩证平衡态度。在一些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中,人们倾向于认为集体幸福优先于个人幸福(Krys et al.,2019;Krys et al.,2020)。
2.2 不同文化对于幸福的态度不同
在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中,对幸福的消极态度比较明显。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认为“物极必反”(《吕氏春秋·博志》)、“乐极生悲”(《淮南子·道应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极大的幸福往往预示着极大的不幸;而“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传·系辞上》)以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谚训也告诫我们,钱财外露容易诱起他人的盗心,贪图安逸和享乐最终会造成人毁国亡的后果,因此要做到“不露富、不露福”“居安思危”,哪怕身处幸福安乐之中也不忘忧患当下。在日本文化中,一个人处于幸福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是消极和危险的,因为它会带来痛苦(Wagatsuma et al.,1972)。韩国社会也同样存在“现在的幸福预示未来的不幸”的世俗文化(Koo &Suh,2007)。而在伊斯兰文化中,幸福一直与肤浅、愚蠢、粗俗等联系在一起,受到批判和否定;相比之下,一个悲伤的人常被认为是为严肃而深沉的。
Miyamoto &Ma(2011)的研究表明,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倾向于享受积极情感体验,且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中,都表现出抑制积极情感的倾向,比如刻意关注积极情感中的其他消极因素(Quoidbach et al.,2010;Wood et al.,2003);而在一些东亚文化中也表现出对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辩证、混合和无边界的倾向,人们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同时体验积极和消极的情绪(Leu et al.,2010;Miyamoto et al.,2010)。
3 幸福忧虑的操作化与测量
3.1 Gilbert 等人的幸福忧虑量表
在Joshanloo等人提出幸福忧虑概念之前,Gilbert及其团队已经尝试对幸福忧虑进行量化,但他们并未建构概念,只是将其作为横向研究中众多的研究变量之一。在此研究中,该团队根据Gilbert在临床治疗中的相关陈述编制了一个包含九个题项(详见表1)的幸福忧虑量表,用以描述一个人对快乐和幸福等积极情绪的主观感受。该量表是单维结构,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经检验具有较好的测量信效度(Gilbert et al.,2012;Gilbert et al.,2014)。

表1 两种幸福忧虑量表的题项内容(幸福忧虑的操作化)
3.2 Joshanloo 的幸福忧虑量表
Joshanloo(2013)将幸福忧虑的核心主题界定为“认为幸福(或快乐)是不幸(或坏事)即将发生的标志”,并基于这一主题以及相关跨文化证据将幸福忧虑操作化,编制了包含五个题项(详见表1)的幸福忧虑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该量表经独立检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在另一项来自世界多个文化背景的14个国家中的跨文化信效度检验中也表现良好(Joshanloo,2014)。国内学者陈甜等(2022)对该量表进行了汉化,中文版的幸福忧虑量表在国内大学生群体中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Joshanloo的幸福忧虑量表作为目前学界用于测量幸福忧虑最权威的工具,在多个国家都得到了广泛应用(Pacheco et al.,2019;Yildirim &Aziz,2017)。
4 幸福忧虑的相关理论观点
目前学界尚未有关于幸福忧虑专门的理论观点解释,Joshanloo &Weijers(2013)在其对幸福忧虑的阐述中曾借用了两个相近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来间接解释幸福忧虑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相应的跨文化表现,它们分别是情绪评价理论和自我与幸福的文化模型。
4.1 情绪评价理论
Tsai等(2006)在其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情绪评价理论(Affect Valuation Theory,AVT),明确了人们存在的两种情绪类型,即实际情绪和理想情绪。其中,实际情绪是人们在现实中真实感受到的情绪,主要受个人气质因素的影响;而理想情绪主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它存在于人们的期待之中,是人们在理想状态下想要表达的情绪并在特定情境下成为实际情绪的目标指引。
Tsai等将理想情绪分解为效价(积极或消极)和唤醒度(高唤醒或低唤醒)两个维度。通过跨文化数据对比,他们发现,在同样的积极实际情绪条件下,欧美人群相比中国人群更重视体验高唤醒度的积极理想情绪(如幸福、兴奋、热情等),而中国人群更重视体验低唤醒度的积极理想情绪(如轻松、平静、镇定等)。也就是说,在内心设想的理想状态下,欧美人倾向于表现得更加接受幸福感所唤醒的积极情绪,而中国人则倾向于抑制这种情绪唤醒。从另一个角度看,前者的理想情绪与实际情绪的唤醒度水平相一致,而后者则存在差距。因此,幸福忧虑可以解释为,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幸福事件或经历所表现出的在理想情绪与实际情绪唤醒度上的这种“差距”的负面体验。
4.2 自我与幸福的文化模型
Uchida &Kitayama(2009)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向度引入幸福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自我与幸福的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s of Self and Happiness)。欧美文化中的自我与幸福模型偏向个人幸福,表现为每一个个体都被看作是相互独立的,都按照自己的目标行事。在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自我观中,个人内在的幸福感受到极大的重视(Kitayama &Markus,2000;Uchida et al.,2004),原则上每个人只要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
相反,东亚文化中的自我与幸福模型则偏向集体幸福,表现为个体与他人在一定的关系中相互嵌入和联系,个体的行为与他人的目标和愿望协调一致(Uchida &Kitayama,2009)。在这种相互依赖、高度关联的自我模型中,人际和社会层面的幸福就得到更大的重视(Lu &Gilmour,2004)。Hitokoto &Uchida(2015)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互依赖的幸福”的概念,即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与他人和谐相处,与他人处于同样的生活标准,并以集体的视角来评估幸福。他们认为,普通和平凡是衡量相互依赖的幸福的重要标准,因此幸福忧虑可能来源于这种为了保持与他人一致而排斥在同一幸福水平上获得增量的倾向。
5 个体产生幸福忧虑的事实性原因
Joshanloo &Weijers(2013)通过对相关的质化文献素材整理得出了导致个体产生幸福忧虑的四种事实性原因:(1)幸福很可能会带来其他不幸的事;(2)幸福的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道德问题;(3)表达幸福会招致他人的负面对待;(4)追求幸福对于自己和他人都是不利的。本文将这四种事实性原因分别概述为祸福相伴、道德问题、招致恶意以及对人对己不利,并在每种原因的基础上扩充其他相关的论述或研究证据加以说明。
5.1 原因一:祸福相伴
许多人厌恶幸福,因为悲伤、痛苦和死亡等坏事往往会发生在幸福的人身上(Joshanloo&Weijers,2013)。这一观点与道家文化中“祸福相伴”非常相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曾红,2012)。高良等(2010)也指出,中国人的幸福观具有更强烈的未来取向,即对获得幸福以后个人发展的重视大于对此时此刻幸福的体验,这种重视总会包含对幸福过后更好结果的期望和情况变坏的担忧。
Ji等(2001)开展了一项中美跨文化心理研究,两国参与者分别对一系列具体场景、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生历程等进行个人预测。通过跨文化对比发现,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事情(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在未来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方向上的偏离或逆转,也可能是速度上的加减;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偏好非线性的人生历程预测,认为幸福和不幸很可能互相转化,生活不会一直幸福,也不会一直不幸。
但抛开文化对比,这种对待幸福的辩证观点似乎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幸福可能导致不幸的信念,尽管程度较低(Ho,2000)。人们之所以厌恶幸福,可能是因为比起真正地实现幸福,他们更害怕失去刚刚获得的幸福。在一些临床人群中,幸福并不一定是令人愉悦的,反而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们在得到幸福时却总是在等待不幸的发生,认为幸福不会一直持续下去(Gilbert,2012)。
5.2 原因二:道德问题
人们害怕幸福,可能是因为当他们获得了幸福,同时也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在遭受苦难时,会感到内疚并认为自己“像坏人一样”。比如,俄罗斯文化中就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任何幸福或成功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使用了不道德的手段才达成的(Lyubomirsky,2000)。
此外,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一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如妇女、移民、同性恋者等)会表现出对幸福的厌恶和回避,原因是如果他们在所遭受的不公平处境之中仍然选择体验和表达幸福等积极情感,会使他们丧失追求正义和争取权利的动力,从而变成一个道德败坏的人(Ahmed,2007)。
5.3 原因三:招致恶意
在俄罗斯文化中,一个人表达他的幸福或成功通常被认为会招致周围人的嫉妒、怨恨和怀疑(Lyubomirsky,2000)。正如Holden(2009)所观察到的一样,即使在西方,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尽量避免表达幸福(尤其是极度的幸福),原因同样是这种做法会惹恼别人并招致嫉妒甚至是攻击。
在一项美日跨文化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两国参与者自由描述幸福的不同方面、特征或结果,结果日本参与者更多地提到表达幸福可能会造成负面的人际后果,如引起周围人的嫉妒、忽视周围人的感受等,而美国参与者对幸福的描述几乎都是积极的(Uchida et al.,2009)。因此,在一些东方文化中,个人产生的与幸福相关的积极情绪可能会被同时出现的内疚和不一致感等消极情绪所抵消。
5.4 原因四:对人对己不利
Mauss等人的两项研究发现,在积极的诱导条件下,更加重视和追求幸福的被试,其幸福感水平反而更低(Mauss et al.,2011),孤独感水平更高(Mauss et al.,2012),这被称为“重视幸福的矛盾效应”——即越是重视和追求幸福,越可能体验不到幸福甚至损害身心健康。对于追求幸福的人自身来说,积极追求幸福需要不断付出努力,而这让他们无法找到时间或以闲适的态度来欣赏幸福本身(Bruckner,2012)。
关于追求幸福对于他人的影响,Joshanloo&Weijers(2013)指出,对幸福的追求(尤其是以极端的形式)往往会导致“双输”,即追求幸福的人最终会感到不满和疲惫,他们周围的人同样如此。一些追求幸福的人往往以满足自我欲望为中心,这会使他们变得自私,并可能对他人的幸福产生负面影响。
6 幸福忧虑的影响因素
梳理有关幸福忧虑与其他心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我们发现,关于幸福忧虑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信念、心理状态及其他相关因素。
6.1 认知信念
首先,认同并持有集体幸福信念的人由于重视人际和谐,会避免体验和表达个人的幸福或拒绝在与他人同样的生活标准上获得更多的幸福(Joshanloo,2022),这也印证了上述自我与幸福的文化模型中集体幸福取向对个人幸福表达的影响。其次,完美主义者由于具有较低的寻求乐趣的动机水平(Andrews et al.,2014;Randles et al.,2010)和较多的压抑积极情绪的倾向(Smith &Bryant,2013),会认为幸福不利于他们的努力,并贬低幸福的感觉或认为其是不必要的,从而导致对幸福的厌恶(Joshanloo,2022)。最后,对幸福的负面态度也可能与相信某种超自然力量或惩罚者有关(Joshanloo &Weijers,2013),比如相信因果报应和相信“黑魔法”(即以伤害或报复别人为目的的邪恶巫术)的存在(Joshanloo,2022)。
6.2 心理状态
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追求幸福和快乐常常无法让他们中获得愉悦感(Dichter,2010);Gilbert等(2012,2014)对抑郁症患者的研究证明了抑郁与幸福忧虑呈正相关;抑郁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幸福忧虑,那些感到抑郁的人会保持对幸福的排斥和厌恶,并将此作为验证自己当前抑郁状态的一种标志反应(Blasco-Belled et al.,2021)。而孤独感作为一种与抑郁高度相关的心理状态指标,也可以正向影响幸福忧虑水平(Joshanloo,2022)。依恋类型会塑造一个人对幸福的态度,而不安全的依恋通常会使人厌恶对幸福的体验或表达(Mikulincer&Shaver,2016);专注型、回避型和恐惧型依恋对幸福忧虑都具有正向影响,恐惧型依恋还可以作为童年创伤的中介而作用于幸福忧虑(Joshanloo,2018;Lazićl &Petrović,2020)。
6.3 其他因素
一些研究发现,年龄与幸福忧虑存在负相关(Agbo &Ngwu,2017;Joshanloo,2018;Joshanloo,2019),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负向预测幸福忧虑(Joshanloo,2022)。童年心理创伤(包括对儿童的虐待和忽视)以及对童年不幸的感知也是幸福忧虑的重要预测因素(Ahi et al.,2021;Joshanloo,2022;Sar et al.,2019)。具体来说,存在童年心理创伤的人会采用更多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如自我责备、反刍、灾难化)以及更少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如括接纳、聚焦、认知重评),从而强化对幸福抱有的负面态度,这体现了认知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Ahi et al.,2021)。
7 幸福忧虑的后效结果
7.1 对相关心理症状的影响
Gilbert等(2014)对52名中度至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研究发现,对幸福的忧虑是他们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的有力预测因子;而在跨时间条件下,幸福忧虑仍然可以显著预测个体更多的抑郁症状(Bloore et al.,2020;Jordan,2021)。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总是无法从幸福中获得积极的回报,便会增加其抑郁风险。述情障碍是指个体不能适当地理解、处理和口头描述自己情绪的困难症(Sifneos,1973)。Gilbert等(2012)的研究指出,对幸福的忧虑导致了抑郁症患者更多的述情障碍表现,原因在于长期的对积极情绪的抑制倾向或行为使人越来越对幸福和快乐感到麻木,甚至无法辨别它们所带来的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体验。此外,述情障碍也可以通过幸福忧虑的中介作用加剧抑郁症状(Gilbert et al.,2014)。
7.2 对积极心理状态的影响
首先,由于幸福忧虑涉及对积极情绪的抑制,所以它可以预测更多的消极情绪和更少的积极情绪(Agbo &Ngwu,2017;Yildirim,2018),还会降低一个人的情绪平衡(Yildirim,2019)。其次,害怕或贬低幸福的人往往也不会强烈地体验幸福(Diener et al.,2013),对幸福的忧虑会降低生活满意度(Joshanloo,2013;Joshanloo,2014;Yildirim,2019)和主观幸福感(Joshanloo,2018)。Yildirim &Belen(2018)发现,在控制了被试的内在行为系统及相关人口学因素后,幸福忧虑对于心理幸福感的自主性、积极人际关系以及自我接纳维度都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也就是说,个体压抑、否认自己真实的幸福感,会降低其独立性(容易受外界影响),在社交中与他人建立共情、喜爱和亲密关系的能力较弱,并对自己的过往、优势、缺陷等持消极态度。最后,幸福忧虑对心理繁盛(一种完全的、高度的心理健康表现)也起负向作用,它阻碍人们在其各个生活领域内的心理健康整合(Belen et al.,2020;Yildirim,2019)。
8 幸福忧虑的作用过程
8.1 中介变量
心理弹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Yildirim(2019)通过多个横向模型指出,心理弹性部分或完全中介了幸福忧虑对积极心理结果的消极作用,在使个体的幸福感免受幸福忧虑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重要的保护性中介作用。希望也在幸福忧虑与其特定的后效结果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Belen等(2019)的研究表明,能动性希望和路径性希望是幸福忧虑与心理繁盛之间的平行中介;根据“扩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2001),路径性希望可以生成多种方法途径的思维能力,以弥补个体因幸福忧虑导致的思维固化和目标实现途径选择减少的消极后果。而在跨时间条件下,低幸福忧虑的个体可以通过较高的希望感减少抑郁的表现(Bloore et al.,2020)。
8.2 调节变量
Agbo &Ngwu(2017)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不同的人格倾向在幸福忧虑与情绪之间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其中,外向性、开放性和严谨性三种人格倾向有助于在幸福忧虑的影响下保持情绪平衡,而高神经质和高宜人性人格在幸福忧虑的情境下会体验更少的积极情绪。希望同样可以跨时间负向调节幸福忧虑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在低水平希望条件下,幸福忧虑正向预测抑郁,而在中、高水平希望条件下,幸福忧虑对抑郁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Bloore et al.,202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幸福忧虑在定量研究中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以及后效结果的路径图(图1)。

图1 幸福忧虑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及后效结果路径
9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关于幸福忧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较多的拓展空间。本文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有关幸福忧虑的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
9.1 本质揭示与理论机制再探究
Joshanloo作为幸福忧虑概念的提出者和研究的先行者,虽然给出了幸福忧虑的一般定义,但目前关于幸福忧虑的本质仍然有待澄清。纵观上述对幸福忧虑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幸福忧虑是一种以情绪为主导的心理状态,因此从情绪的角度切入并进行本质挖掘是一条关键且可行的路径。在结合已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幸福忧虑情绪本质问题可能的两条阐释路径供今后的研究者参考:
(1)“情绪表达抑制”说。任何一种心理状态总是由相应的心理过程而达成的。情绪表达抑制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通过调动个体的自我控制系统达到抑制情绪表达、削弱主观情绪体验的目的(Gross,2001)。基于此,情绪表达抑制可能是形成幸福忧虑的一种心理过程,即个体在体验到幸福等相关积极情绪之后,自发地采取抑制策略以减少对幸福的情绪表达。此外,情绪表达抑制具有与幸福忧虑相同的跨文化性,即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们不被鼓励也不擅长使用情绪表达抑制(刘影等,2016;Butler et al.,2007),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则相反(刘影等,2016;Soto et al.,2011)。
(2)“混合情绪”说。Cacioppo &Berntson(1994)的评价空间模型和Schimmack等(2001)的情绪注意分配理论都指出,积极(趋近)和消极(回避)是情绪效价的两个独立维度,人们可以同时感受到两种相反情绪,从而产生混合情绪体验。基于此,幸福忧虑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混合情绪,是幸福感和忧虑感两种相反效价的情绪同时存在而产生的情绪体验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幸福忧虑作为一种混合情绪,可能并非是幸福与忧虑的简单叠加,其背后仍然具有复杂的心理过程,幸福感和忧虑感是先后出现并逐渐达到混合共存的状态,且忧虑感的对象始终是幸福感本身及其相关情绪体验或现象事实。在跨文化性方面,集体主义文化对混合情绪的接受高于个人主义文化(Grossmann &Ellsworth,2017;Schimmack et al.,2002),这也与幸福忧虑的跨文化性相一致。
此外,Joshanloo &Weijers(2013)曾指出,幸福忧虑的背后包含了一个对于幸福的多维度评价体系,我们还可以针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不同程度的幸福忧虑(如是否存在从对幸福无感、幸福忧虑、幸福焦虑、幸福厌恶再到幸福恐惧的程度梯次)。(2)对特定水平幸福的忧虑(如是否存在只对高水平幸福感到忧虑的情况)。(3)对特定种类幸福的忧虑(如只对意料之外的幸福感到忧虑)。这些都有助于幸福忧虑理论机制的建构。
9.2 关注幸福忧虑的积极作用
研究发现,混合情绪可以提高个体对他人不同观点的接受能力(Rees et al.,2013)和解决创造性问题的能力(Kung &Chao,2019),有助于个体理解自己当前的情绪体验,并促进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行为(Braniecka et al.,2014)。虽然目前的研究几乎都将幸福忧虑视为一种消极因素,然而无论其是作为一种混合情绪还是情绪表达抑制的策略,幸福忧虑的积极作用都是不能被忽视的。
在更多时候,幸福忧虑的积极作用可能会通过一些特定的中介因素来呈现。例如在中国人群体中,我们可以推测幸福忧虑与中庸思维密切相关,而中庸思维可以促进人们的自信水平(毕重增,2016)、社会适应和情绪调节能力(李启明,陈志霞,2016)。此外,辩证思维、慎独人格、忧患意识、理性决策等都有可能成为幸福忧虑发挥积极作用的相关因素,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9.3 拓展研究领域和方法
在研究领域方面,目前关于幸福忧虑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人际社交、健康行为、个性偏好等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从本文梳理的幸福忧虑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来看,还需进一步考察职业、阶层、收入、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因素以及其他潜在的中介或调节因素对幸福忧虑的影响,这对于完善幸福忧虑的量化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以横断面研究为主,该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次提出,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设计来巩固现有研究中幸福忧虑与其他变量之间所不能确定的因果关系(Joshanloo,2018;Joshanloo,2019;Yildirim,2019),以及运用严格的实验研究来提高研究证据的说服力(Bloore et al.,2020;Joshanloo,2019)。此外,有关预防或降低幸福忧虑的消极影响的干预研究也亟待开发。
9.4 幸福忧虑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是比较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的国家,在数千年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儒家中庸、克己、慎独以及佛家因果循环、道家祸福相依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的幸福忧虑可能早已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了。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一种跨文化心理现象,幸福忧虑在我国本土的研究几乎没有。
首先,从内涵上来说,相比于Joshanloo给出的单维度幸福忧虑,中国人幸福忧虑的内涵也许更加复杂,所包含的维度可能不止一种。目前国内虽然已经引入了Joshanloo的幸福忧虑量表,但仍应继续挖掘幸福忧虑在本土环境中更丰富的内涵,开发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其次,从原因上来说,根据本文前面部分所述内容,中国人可能主要会因为以下三种原因而产生幸福忧虑:(1)认为获得幸福破坏了与他人之间的和谐一致;(2)认为幸福可能会带来不幸;(3)认为表达幸福会招致他人的恶意。除此之外,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最后,从差异上来说,民族文化、城乡地域及职业性质等因素可能会造成国人幸福忧虑水平的差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