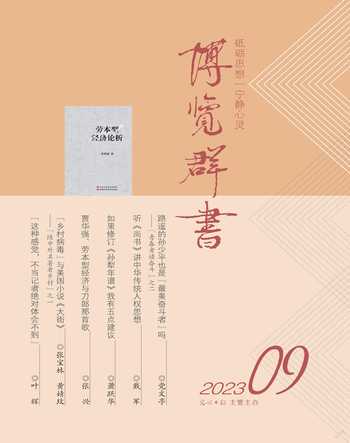萧红在生命最后完成的《呼兰河传》
李小红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故乡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它常常与“家”息息相关,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等情感因素。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就是故乡或家园不断瓦解的过程。中国自近代以来被迫纳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后,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社会结构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批判的一脉创作中,故乡成为他们批判国民痼疾、解剖民族文化心理的切入点;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笔下,充满诗意与隐逸气息的田园牧歌般的故乡,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审美之乡。然而,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民族罹难、现代文明冲击导致的传统裂变的时代氛围中,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让他们笔下的故乡承载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故乡成为他们追忆童年、凭吊少时记忆的载体,表达了他们对于人类初始乐园的想象与构建;另一方面,风雨如磐的中国社会现实,又让他们不得不对乡土中国进行理性审视。《呼兰河传》正是作家对乡土社会在审美层面进行文化探寻又在现实层面进行反思反省的创作成果。
1941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彼时,包括东北在内的大半个中国处于沦陷之际,作家本人也历经人生和情感的磨砺。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萧红在遥远的香港,以追忆的方式,对童年和少年生活过的呼兰河进行了深层次的反观。她在过去与现在、童年与成年、梦幻与现实之间,捕捉少时同祖父在呼兰河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情与景的交融中完成了对乡土生活状态全方位的呈现和对其生活方式的反思。一个带着浓郁北中国气息的小城形象由此跃然纸上,作家不仅展示了东北作为“化外之地”的风情,同时也清楚地映现着自我与故土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在“城与人,孩子与老人,生者与逝者”中传递出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认知。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巧妙地构建了两个叙事空间,大空间是外在的呼兰河城,小空间是“我”家的后花园。后花园的故事以儿童视角展开,呈现出一个鲜活、生动、自由又纯粹的童真世界,这可以看作是女作家在生命的夕阳西下时刻对“永逝韶光”的深情回眸,至真至暖的回忆中充满了温情。它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成为一种隐喻般的存在,是人类生命初始阶段的乐园,也是审美观照下的乡土中国。
柏拉图认为,世界分为本体世界和形成世界,本体世界是世界的恒常状态,表现为普遍、永恒和真理,形成世界是指世界的流动状态,表现为具体、短暂和易逝。生命分领这两个世界,它既稳定永恒也短暂易逝,因此,对生命自在状态的追求受人内心本质力量的驱动所致。在《呼兰河传》小的叙事空间中,萧红用尽笔墨,描写出一种生命的自在状态: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似的。(《呼兰河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P55。以下凡引自该著,仅标明页码。)
小说描写的是自然界中动物、植物生命的自在状态,其实也隐含着对人生命状态的表达。在这样的后花园里,童年的“我”是自在、快乐、物我两忘的。萧红同样用描写自然的方式写出了人类的情感,那些生命的寂寥与欢喜,被她浓缩在肥厚的绿叶子、盛开的玫瑰花、漫天的火烧云和翻滚的麦浪之中,成为她作品中具有隐喻意义的存在。
事实上,写作《呼兰河传》时期的萧红,不但生活上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情感生活也是一波三折。此时,她与萧军已经分道扬镳,与端木蕻良的仓促成婚也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安宁。萧红“在她关闭着的内心,这时候,未尝不是说明对于人间的荒凉的感觉,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的幻灭”(骆宾基著《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86)。正是这种幻灭,让她回溯曾经执意逃离的故乡,回归自然而纯粹的童真世界,所以她对祖父的忆念饱含着非常强烈的情感。然而,这种情感的浓度并没有通过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来体现,而是透过一个5岁女孩童稚的眼睛,将她在后花园中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四时流转表现了出来。萧红以追忆童年的温情来抵御现实的残忍,以祖父的爱来照亮自己灰暗的生活,这未尝不是她书写《呼兰河传》的一种理由。
然而,借写小说来整理自己的人生,回应现实处境,也许只是萧红创作的一种理由。对比一下同时期作家对于乡土中国的书写,我们也许能发现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更深层意义。沈从文、师陀笔下的乡土之城,都保存和雕刻着昨天的记忆,记忆打开,时间凝固,唯有带着体温的故事和人生哲理涌入读者的视野。这些小城与萧红笔下的后花园一样,成为静美乡土中国的一种隐喻,安放灵魂的同时,寄寓作家对国家和民族新生的希望。
当小说从小的叙事空间“后花园”进入到大的叙事空间呼兰河进行叙事时,叙事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一个儿童转变为一个成年的女性知识分子。成年之后的“我”对于呼兰河的审视已经远远超越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而是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呼兰河给予全方位观照。小城中人的生、老、病、死,他们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娘娘庙大会的种种民俗,以及小团圆媳妇、长工有二伯悲剧人生,都被纳入整体的理性审视之中。这种超越儿童视角的启蒙者眼光的介入,使《呼兰河传》在看似冲淡平和的叙事语调之外,增加了悲凉的况味。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呼兰河的荒寒: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P1)
这种荒寒,不仅是气候特征,它更是一个知识者以启蒙视角观察呼兰河小城时的理性认知,这也是弥漫于整个乡土中国的荒寒。小说从第二章开始,以近乎方志的笔法,描绘出了呼兰河城的民情风俗。然而,这些风俗的背后,无一不与残忍和愚昧相联系。比如,“跳大神”表面看似很热闹,本是为了给人治病,然而,到底多少人的病治好了,不得而知。不同于鲁迅对浙东地域陋俗与恶俗的犀利抨击,萧红以绵密细致的笔触记述呼兰河的民俗,每一种民俗中都隐含着她对生与死的辩证思考,与生的热闹相伴的是死的落寞,而这种种的死生,折射出的是社会之残忍与人性之恶。从某种程度上讲,萧红与鲁迅民俗书写的旨归都是相同的——通过民俗解剖国民精神结构,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对社会与人性的批判,在整部小说中作者用笔力度最深的,莫过于对“小团圆媳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小团圆媳妇是个童养媳,她爱笑、不知道害羞、不懂得看人眼色而被她婆婆认为是狐狸精上身,从而遭毒打、“抽贴儿”“跳大神”,以治病之名被活活烫死……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然而,更可怕的是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冷漠和令人齿冷的议论,一群庞大的看客,是鲁迅笔下的“无名杀人团”。这种借叙事人的体察所呈现出的浓重“愚昧”色彩,是萧红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呼兰河人给予的最深刻的批判。
当萧红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看待呼兰河荒寒土地上人生的磨难与恐怖的死亡时,启蒙者视角的运用是复杂的,她没有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而是与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一同受难。因此,她在小说中不断地诉说着关于人生寂寞和荒凉的认知,这无疑是离开故乡、辗转流亡中的萧红的一种彻悟:在国破家亡的中国,处处都是这样充满荒寒的土地和荒寒的人生。此时,我们对作家笔下的“呼兰河”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具体的地域了。她笔下的呼兰河就是现实中的中国。因此,那个充满浪漫与空灵色彩的后花园世界就显示出了它真正的意义,它的存在让整个外部世界显得更加悲凉与无望。
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小说与时代环境、文化思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阐释关系,有时甚至成为特定时代精神的风向标。《呼兰河传》借呼兰河的形塑表达出作家对乡土中国的认知,其形象具有强大而深沉的文化隐喻功能。事实上,当我們以整体性视角梳理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发展态势时,会发现《呼兰河传》独特而深广的意义。
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以解剖保守扭曲的国民集体心像和民族文化心理,呈现原始封闭的乡村生存图景和陈风陋俗,完成对于乡土中国的书写。《呼兰河传》虽然在整体氛围上少了鲁迅的犀利和冷峻,但其创作旨归与主题表达却是一致的。萧红说:“现在或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P2)《呼兰河传》不管是对于风俗人情的书写还是底层民众形象的刻画,都与鲁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追求和他“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精神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版图在鲁迅与绍兴、沈从文与湘西之后又有了新的代表,那就是萧红与呼兰河。然而,萧红的呼兰河又绝不是绍兴或湘西的翻版,它有着萧红独特的温度与气息,有着萧红对人类命运的整体认知。
当萧红以启蒙者的视角进行呼兰河的叙事时,小说的整体氛围是冷清、孤寂和荒寒的。当她以当地人、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呼兰河的故事时,小说却不乏明丽与温馨的片段,尤其是充满诗意和童趣的景物描写,使《呼兰河传》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张力。呼兰河在此时成为作家的审美对象,通过挽歌的怀乡恋旧的书写,寄托对传统文化与童年生活的温情眷恋,表达出对人类初始乐园的追寻与神往,小说因之呈现出了明显的诗性特质。这一诗性乡土中国的书写,上自废名、沈从文,下有孙犁、汪曾祺,萧红可谓承上启下,在文学史上了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迄今的百年文学发展中,乡土成为中国现当代作家重要的表现对象和审美领域,它寄寓了作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希望。萧红在生命最后时刻完成的《呼兰河传》,不仅使呼兰河成为中国文学版图的显性存在,也使文学中乡土中国的形象更显立体丰满。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博士。)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