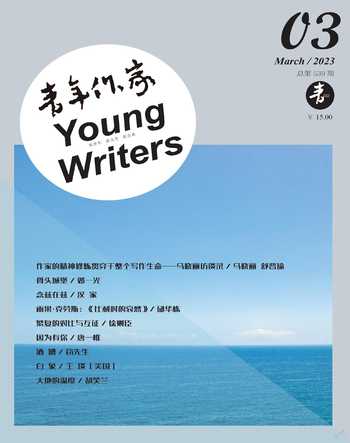岁末去龙泉驿
一
离大理机场还有十来分钟路程时,司机问能不能下去买两个肉包子。我说好啊。她解释,要去喂流浪狗。
机场停车收费,滴滴司机就在机场外背山处的废弃加油站旁开发了一个临时停车场等着接单,加油站老头儿原本养了条狗,加油站倒闭后人去楼空,狗被弃养,一些滴滴司机在接站时就会给狗带点儿吃的,包子、饼干、水果,还有吃剩的米粉。狗饿,什么都吃,辣椒都吃。
看我感兴趣,她又问,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她开的是新能源车,可以免费进两次机场,免费在机场内等候两小时,但她为了喂狗,每次都和油车一起去外面等。“一点都不美丽,但也是条生命呀!”
我们的车还没停稳,狗就来了,一公一母一小,脏兮兮的。公的和小的都被车轧过,瘸着腿,一个劲儿地摇尾巴,叫。司机喂肉包子时,公狗在最前面,小狗在旁边,母狗默默待在后面,我想起包里还有几片面包,就去喂母狗,狼吞虎咽的。司机盯着母狗下垂很长的奶头看了会儿,怀疑她又生小狗了,骂它,你都瘦成这样了你还生!一边喂一边后悔包子买少了,又去找旁边聊天的司机要了瓶矿泉水,倒在路旁的小碗里。
她说好几次都想联系流浪狗救助站,由于种种原因,就作罢了。“就让它们待在那里吧,稍微自由一点,活到哪天算哪天。”
我在候机时把这件小事写在微博上,但无论如何也发不出来,只好做成图片再发,总算发出来了。登机,起飞,从晴空万里的大理到了淅淅沥沥的成都。天气不好,没看到金沙江,也没看到贡嘎山,落地后打开手机,那条微博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
时值疫期,万事休矣,多亏《青年作家》同仁的努力,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才没有二度延期,但八个奖项的获奖者仍有三位被阻在家,无法出席。包括我在内的另外五位获奖者,分别从上海、西昌、泉州、福州和大理飞来。
第二天颁奖典礼开始前,我见到了上海来的作家王占黑。她个子小小的,穿一件oversize的毛呢大衣,衬得人更小了。这是封控两个月后她第一次离开上海,我小心翼翼问起当时的经历,她缓缓地回答着,伴随着间歇的沉默,让我想起六月时见到第一位从上海来的朋友。
颁奖仪式的主持人与朗诵者(我们每个人选了一段自己作品里的文字)的语气盛大而丝滑,我本来在手机里写了一段获奖感言:
“《重走》是历史与现实中两次旅行的双线叙事,历史的比重更大一些,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1938年的春天,和那些故人成了朋友。交初稿的时候,正是2020年早春疫情最严重之际,我目睹了这两三年周遭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不仅现在与未来是无常的,历史也是流动的、变化的,是不同记忆版本之间的竞争,所以一代一代的人总要重走历史、重写历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写作可以对抗那种在我们周围弥漫开来的无力感。我们也许可以安慰自己说,不管怎么样,先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总归是有意义的,因为未来的人看我们此刻,无非也是看历史,也会看到彼此竞争的不同版本的记忆。我们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版本,供未来带着善意的读者去参考。”
上台太匆匆了,还没等我从主持人的话语流里找到气口,发现自己已经捧着奖杯坐在台下了。
我们住在龙泉驿区的东安湖边。我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座引都江堰水而来的人工湖。湖畔草木扶疏,湖水浅而清澈,沉水的丝绒状水草很多——APP告诉我,它们叫微齿眼子菜,光影在其间游走,水变得更清亮了,还有少量圆叶子的水金英举起三瓣黄色小花。总之,看起来颇抚慰人心。我发现自己在疫期写文章总不由自主用到“抚慰人心”这个字眼,我怀疑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最高审美。
东安湖公园公众号的一篇文章解释了湖水为何如此清澈:水生态修复最主要的工程就是沉水植物的构建。在浮叶、漂浮、沉水、挺水植物4种生态型水生植物中,沉水植物对富营养化水体的综合净化效果最佳,是沉浊水态到清水态转变的关键物种。同时,食藻虫的投放,可使水体中藻类、悬浮物颗粒等大幅度下降,迅速提高水体透明度。食藻虫消化蓝藻后,可产生弱酸性排泄物,降低水体PH值,反过来又可抑制蓝藻生长。如此一来,水下光照条件也会得到显著改善,为沉水植物群落的生长提供条件,形成良性循环。
2021年9月,东安湖发现了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桃花水母,专家撰文解释说,这些水母显然是随着湖泊注水,从都江堰以水螅体状态随水而来的。水螅体对环境要求并不严格,如果水质不佳,便长期吸附于水下或岩石缝中生存下去,只有水体无污染,PH值在6.4-8之间,水温在25-32摄氏度之间,水螅体才有可能以出芽的方式,发育出硬币大小、通体透明、如倒扣的碗般在水中开合游动的水母体。东安湖湖水是如此清澈,以至于成都大运会龙泉驿赛区的公众号要专门写篇文章提醒游客——就像对待一则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湖水虽好,还是不能直接饮用哦。
三
下午是采风时间。吃过午饭,活动主办方请我们到一处地势较高的休息厅喝咖啡,俯瞰碧绿的东安湖,并越过唐风盎然的东安阁远眺灰色的龙泉山脉。听地方专家讲述龙泉驿历史,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里的水系与古道,用在场的作家凸凹的话说,一些文明沿着河流走,一些文明沿着驿道走。
龙泉驿区没有大的河流,几条小河分属岷江与沱江流域,在我们东南方向绵延的龙泉山脉即是分水岭。明清时期的古道“东大路”,从成都东门的锦官驿出发,过龙泉驿,翻龙泉山,到阳安驿(简阳),一路向东经资阳、内江,到达重庆,再沿长江出川。我一边听一边想写《重走》时所熟悉的普安道,从云南出发,横穿贵州,抵达湖南常德,沿沅水下洞庭,入长江,与东大路上的商贾、旅人、学子汇于九省通衢的武汉。
无论是沿着河流走,还是沿着驿道走,目的都是流通,人与物的流通,财富与观念的流通。流通与开放带来活力、带来文明,禁足和封闭则带来守旧、带来僵化。经过2022年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對那位好心喂狗的女司机的两句话更加念念不忘了:“一点都不美丽,但也是条生命呀!”“就让它们待在那里吧,稍微自由一点,活到哪天算哪天。”狗尤如此,人何以堪。
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地点从这一届开始永久落户东安湖,据主办方说,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写作营,邀请全国的作家来此小住、创作。这里确实环境不错,负氧离子高,入夜又静谧,在东安阁酒店住宿的两天,我睡得极好,料想如果在此续写新书,效率一定不低。次日天放晴了,气温回升,参会人员陆续离开,只剩我和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培浩、《青年作家》编辑王棘和封面新闻首席记者张杰四人,我们绕着东安湖散步,走了几乎一整个上午,聊时局,聊人心,放松而愉悦,这是裂变年代来自同温层的温暖,过去我们做媒体的总是喜欢把“破圈”挂在嘴边,如今我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三五同仁,守住内心的火苗,在小世界里亦可有所作为。
四
东大路有一条北支路,经洛带镇越龙泉山到达沱江边的金堂县五凤溪,比起中路和南路,北路可以借用更多水道,省钱省力,因而作为商道开始发达起来,这也带来了五凤溪与洛带镇的繁荣,民间谚语有云:“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甄子场(洛带),装不满的成都府”,来自川东乃至下江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通过此路运往成都,滋养着这座享乐的消费型城市——恰与《重走》中细细描摹的长沙有异曲同工之妙。
喝完咖啡,我们乘车前往洛带古镇。导游是本地客家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把大量客家人从闽粤带到了这里,并落地生根。她在普通话、四川话与客家话中不断切换解说,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她的客家话远远谈不上流畅,许多句子说不出来,但许多词汇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譬如,“落水”(下雨),“着衫”(穿衣),“栖等”(站立),“食朝”(早饭),听来古意绵绵。在博客楼内的客家文化展示厅,我盯着一幅“客家五次迁徙路线图”看了半天,前往洛带的一支,走的正是沟通成渝的东大路。
流亡的历史有时也是新生的历史。现居纽约的文学大家王鼎钧先生曾经被问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计划,他回答:“今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洛带古镇另一吸引我的地方,在洛带公园。我们在古镇漫游参观时,不止一位本地文史专家自豪地提起这座1928年模仿成都第一座公园(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兴建的现代公园。公园由出任洛带镇保卫团团长(他的另一身份是袍哥)的广东客家人刘惠安首倡,入园处有一副楹联,“公产本无私,到此游观,俱是主人俱是客;园亭非易建,须知爱惜,一堆花草一堆钱”,有人评论,“虽未表达出对于共和政体的认可,但一种关于‘公共的社会生活理念却已然切实形成并被付诸实践了。”更有趣的是,公园内还设有“女宾休息所”,专供女子饮茶,男宾不得入内。洛带客家人占绝大多数,据说,谁家的女人若因吵架而负气去了女茶社,丈夫就只能在茶社门口的石榴树下“坐冷板凳”,等着女人出来了。我们一行数人,边走边聊这一百年前的掌故,感叹“现代”触角的无远弗届,亦感叹我们曾经到达过何处,此刻又身处何处。
【作者简介】杨潇,1982年生,湖南人;曾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为哈佛尼曼學者;著有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现居云南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