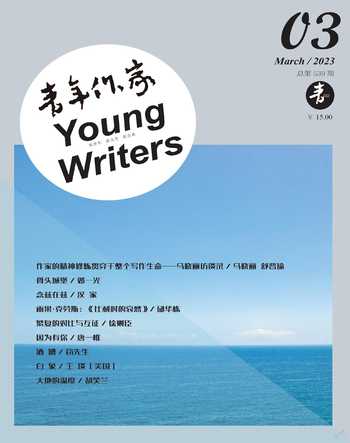刀影微寒
一
村里有个牛四郎,乃一介屠夫,鸡鸭牛羊见啥宰啥,手里见不得活物。提及牛四郎,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买卖也准称,心眼也实在,就是死得着实可惜。人们路过他家小院,看着门锁着,个个唉声叹气,无非在想他,想他宰杀后卖的肉。以前那个门是敞开的,每逢二、四、六,四郎下午准时出摊,生肉鲜红,熟肉喷香,天黑之前,保准卖得干净。日子本来细水长流,直到那天陈哑巴溜达过来。
那个午后平淡无奇他收摊格外早,阳光斑驳在他懒洋洋的脸上,瞌睡沉甸甸地袭来。就在他发出第一声呼噜的时候,陈哑巴来了,拍拍肉板,把他吓一跳。
陈哑巴不是真哑巴,从小说话慢,大了不学好,和焦双喜搭着伙偷鸡摸狗,有人暗地里骂他,这诨号便传开了。牛四郎被他搅了好梦,没好气地说:“收摊啦,想吃肉早来!”
陈哑巴说:“俺可不是来买肉!后天俺老娘生日,想把那头黑猪宰了,麻烦你呗?黑猪一半留着,一半便宜卖你,咋样?”
牛四郎一听来了精神。那头黑猪名气比他都大,膘肥体壮,肉质上乘,他垂涎已久。他把尖刀亮出来,“啪”一下插在案板上。陈哑巴明白,歪着头说:“亏不了你,现在就去!”四郎二话不说,攥起尖刀就往外窜。是呵,冥冥之中安排好似的,今天肉卖得早,他闲置了一身气力,就等着这么一场硬仗!闻风而动的人们,蚁群一样尾随上去。那黑猪通人性一般,见到牛四郎仿佛知道末日将近,暴躁不安、上蹿下跳。这果然是个大家伙,猪鼻又长又尖,像粗硬的肉锥。牛四郎宰了数不清的牲口,哪将黑猪放在眼里?他兴致大发,和陈哑巴说:“我不要帮手,自己就能制服!”说罢直接跳进圈里。众人一听拍手叫好。见他跳进猪圈后,明显一个趔趄,明眼人看出来,这完全不是那个结婚前的壮汉了。
牛四郎是个粗人,却隔着好几个村娶了个精致女人,皮肤白皙,嘴唇透红,一头钻进牛四郎家小院,人们说这简直羊入虎穴。人们担心女人经不起四郎的折腾,怕这个新媳妇被牛四郎生吞活剥了。但事实是,婚后女人越来越光鲜,而原本粗犷的四郎渐渐佝偻了腰身、收敛了戾气,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脸上猛张飞似的胡须,竟也软软地打起弯来。见他这副模样,一些买肉的深知其意,还与其打诨:“这猪腰子你别卖了,得留下补补啦!”与之形成对比的,他卖肉的生意却越来越好。婚前他出摊,天黑前总零零散散地剩下些,还得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有时要到邻村去叫卖;如今,西山的日头还高高的,他有的是工夫晒太阳喝闲茶。人们知道,是新来的媳妇能干。这个女人,烧的肉色泽亮红、肥而不腻,煮的血清亮滑嫩、状若豆花,里里外外又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的女人,谁都高看一眼、多看两眼。渐渐地,买肉的过去不喊牛四郎,都喊这女人,又不知道她娘家大号,某天不知谁喊一声“牛娘”,她的名字便在村里传开了。这名字已响过了牛四郎。
村长胡小手担心,对哑巴说:“得多下几个人,我怕四郎架不住。”四郎听见说:“村长,你信不信我把猪鼻子塞你腚里!”说完还哈哈一笑,但这笑,有些发虚发飘,中气不足。黑猪仿佛也从中听出猫腻,从一开始的惊恐躲闪,到听到笑声后逐渐气定神闲,甚至敢撅着长鼻与四郎沉默对峙。这样的四郎少见,这头不畏屠宰的猪更是少有。
三两下追逐后,猪尾巴还没摸着,牛四郎就开始大口喘气。有人问:“四郎,你那一身铆劲呢?”有人说:“让媳妇折腾没了!”牛四郎满脸通红,想骂又喘得不行,喉咙里像有人摁着压着;黑猪成了精似的,在窄小的猪圈里闪转腾挪,反倒戏耍起了牛四郎。他干脆停下,缓缓再战。陈哑巴有些不耐烦,说:“先把猪捆起来吧,省得你瞎折腾!”牛四郎一听双目瞪圆,冲他“呸”一口,攥紧尖刀,转身准备再攻,孰料那黑猪竟从背后偷袭上来,一鼻子顶进他宽大的裤裆里,只听一声惨叫,人仰躺下去;黑猪又顺势补一鼻子,像一颗长钉将四郎钉在了圈坑里,人直挺挺的,毫无反应了。
人群慌了,陈哑巴带头跳进去,把人拖上来就往医院送;半路上,人就没了。当夜,村里忽然刮来一阵旋风,吹得门帘子“呜呜”响,像有人在哭;吹得树枝子“嘎吱”脆,像有人在闹。多少人还在梦里,就觉出风的不寻常,不约而同醒来,支起耳朵,偷偷听着门外窗外的哭声闹声。
这哪是风?这不是四郎的魂魄么?不少人便久久不愿睡去,或者说,睡意全无了。
二
四郎辈小,旋即草草埋了;牛娘也匆匆走了,像被那阵夜风刮丢了似的。牛家院门紧闭,几只家雀落在院门上,望去显得那么突兀。这里曾经有多么热闹,如今便有多么荒凉;荒凉在村里,荒凉在人们心里。谁不心疼四郎?连那些眼馋他、嫉妒他的,也都开始念他的好,他的老实本分,他的粗厚坦诚。牛娘嫁来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给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好像她就該嫁到这个村,就该嫁给牛四郎,就该卤肉卖肉。这么多“就该”组合在一起,让她成了村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一旦走了,像扯筋割肉般疼。但心疼归心疼、念想归念想,在胡小手心里,考虑的远不止这些。他隐约觉得,牛娘终究要回来,考验他的时候在后头。他曾闲逛到陈哑巴家喝茶,看见他大肚子老婆笨拙地烧水做饭,不疼不痒地关心几句;又见他一院子的鸡鸭羊牛,日子过得也不差,心里的话如饱饭后的嗝儿,逆着劲往上蹿,三言两语就提到牛娘。陈哑巴装傻充愣,刻意回避,胡小手不和他周旋,直接问:“如果牛娘回来,怎么赔偿人家?”
陈哑巴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我赔偿?”
胡小手说:“被你家猪拱死的,跑得了干系?”
陈哑巴说:“你情我愿的事,要怪就怪猪吧,黑猪要杀要剐随你们!”
胡小手的小手在桌上使劲拍一下,把哑巴老婆大肚子惊得一颤。哑巴说出这话,不出他所料。这种事其实难啊,没有具体赔偿标准,好孬多少全凭良心。回到家里,看到满地被夜风吹落的枣花骨朵,有些还没开苞哩,就要落地成泥,叫人心疼;触景生情,想到了牛娘,心里便空落落的。谁让他是村长呢。
四郎头七那天,村里热闹了一阵,像有贵客降临。人们老老小小的都出来,眼睛亮亮的,高兴地喊:“牛娘!牛娘!”果然是牛娘,袖上、鞋上还绣着白布,笑着和人们打招呼;但眼皮肿着、鼻头红着、嗓子哑着,那略显生硬的笑里,便多出了几分惆怅。
胡小手不敢怠慢,请了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者,喊了陈哑巴,太阳还未暖透呢,就急匆匆赶过去。一进院,看见那几日不见的天井里,角落已经生出些杂草;暗沉的枣树下,牛娘正坐在凳子上磨刀。那把刀正是牛四郎的尖刀。这把鲜血浸透的钢片,正在牛娘专注的摩擦中散出寒光。
人齐了,围着枣树坐下,心照不宣,直奔主题。陈哑巴和胡小手接触后,就打了预防针,一上来就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任凭大家明情辩理,语重心长,他不为所动;也不是不赔,就一头黑猪,别的半分钱也不出。眼瞅到了中午,热乎乎的天气加重着人们心内的浮躁,有的老者已经不愿和这无赖多费口舌,干脆提出报警,其他人也应和着,开始东扯西扯起来。胡小手偷瞄一眼牛娘,她面色苍白,郁結愤懑,便不忍再看第二眼。一条人命让一头猪打发了,换作谁,都是无法接受的。他心焦无助,又盼着这个女人,若能撒泼骂街就好了,死咬着陈哑巴不撒手就好了。但这可能吗?就在一头乱麻之际,抬眼瞧见,那西院墙上,皮球一样的东西正一沉一浮。那是焦双喜的黑脑袋。
他刚想骂一声,陈哑巴说话了:“焦双喜,你下来,别成天偷鸡摸狗似的!”
焦双喜不客气地跳下来,指着陈哑巴说:“你只赔一头黑猪,太没良心了,这不缺德吗?”
陈哑巴站起来就要和焦双喜动手,让一圈人拉住。有个老者说:“你俩挺有意思,从小捣蛋玩到大,一根绳的蚂蚱,怎么还掐起来了?”
焦双喜怒气冲冲地说:“我就是看不惯他!”
陈哑巴说:“我也看不惯你,装什么好人!”
枣树上惊起一片捕食的飞鸟,洒下一阵凉凉滑滑的东西。飞鸟过后,几个老者站起来就要走,胡小手不再勉强,把两人训斥一顿后,试探着问:“牛娘,你啥意见?”
他的话音颤颤的,带出藏也藏不住的心虚,生怕牛娘做出出格的反应,让他、让陈哑巴下不了台。出乎所有人预料,牛娘没多提任何要求,这令其感动而内疚,他赶紧叫来老婆,再三叮嘱:“今晚在这里陪着吧,别回家了,这是个好人、好人!”
焦双喜说:“好人就该吃屈?”
胡小手见牛娘进屋了,赶紧说:“你就消停下吧!”
一个老者问:“双喜,听说出去学本事了?”
焦双喜说:“不瞒您说,我这几天跟着县城那个刘一刀学了手艺,以后就干屠宰了!”他拍拍腰间,别着一把长长的砍刀。
陈哑巴说:“这是要和她抢饭碗!”
焦双喜说:“哑巴,我在帮她!可不像你!”
焦双喜说完,几个长者对他点点头,以示肯定。几天不见,这个和陈哑巴齐名的、亦臭名远扬的光棍汉,忽然大变性情;又或许因了对牛娘的同情,反而对他充满了些许期待。
瞅着焦双喜和他腰里的砍刀,人们准备彻底忘了牛四郎。
三
焦双喜果真变了,这不奇怪。牛娘既然能让四郎变得病恹恹的,为何不能让双喜重新做人?
他有的是力气,别着砍刀大街小巷揽活,又把营生做到了十里八乡,屠宰的生意比牛四郎的只大不小。那源源不断的新鲜肉源,隔三岔五运到院里,牛娘只管煮、卤,肉色肉香没减半点,还是两天一出摊,还是早早地就被抢空。在这阵痛快里,牛娘又活了回来,她又成了人们眼里那个干练麻利的女人。焦双喜这么卖力的意图不言自明,他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在牛娘家出入,直到胡小手找上门来。
胡小手新增的烦恼源自陈哑巴的举报。哑巴家最近接二连三丢东西,且都是活物,鸡、鸭、羊,丢了一个遍。起初没在意,把棚子笼子扎紧了,还丢;以为来了黄鼠狼,撒了药布上陷阱,还丢。有天夜里,他蹲在院子里半宿,终于等到一个黑影跳进来,往鸭圈里溜,抓贼心切,反把贼惊跑了,但被盗一事落了实锤。
胡小手说:“谁和你有仇?”
陈哑巴说:“除了焦双喜,想不出第二个。”
着实,论动机,两人刚吵一架,焦双喜有报复嫌疑;论身手,焦双喜攀岩走壁有一套;论名声,焦双喜小偷小摸惯了。胡小手说:“捉贼见赃,你没证据别胡说。”
他心里也犯嘀咕,打发走了陈哑巴,便径直去了双喜家。双喜刚从邻村转来半扇牛肉,正起劲地一块一块解肉。胡小手看出来,这家伙对牛娘铁了心,进院就说:“这么能干,以前咋没看出来。”
焦双喜说:“以前也能干,你是瞧不起人。”他正一条一条砍着牛肋骨,用的是巧劲,但柔中见刚,粗细相接,看出了力道和功夫。焦双喜这种人,只要聪明用在正处,日子没有过得差的。牛娘若跟了他,不是什么坏事。
胡小手拐着弯说:“我正准备让你嫂子去跟牛娘说叨说叨,你这老大不小了,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焦双喜一听赶紧放刀,两手在裤子上抹几下,进屋就要倒水。胡小手说:“得,小兔崽子。”
见他老实了,胡小手才说:“咱开门见山,最近陈哑巴家里丢东西,是不是你干的?”
焦双喜瞪圆眼珠子说:“绝对没有。这屎盆子不能往我脑袋上扣!”
“我不怀疑你,是哑巴怀疑你。”胡小手说,“你没有就好。这肉哪里搞的?”
焦双喜说:“十里八乡的,谁还不给双喜点面子。别说,还都是以前打过架的,不打不相识啊。”胡小手听完点点头,开始喝起茶来。他不相信焦双喜敢出去偷牲口来卖。焦双喜眼珠转半天,说:“这算不算报应?”
是不是报应,已非胡小手说了算。这件事开始在村里迅速发酵。怪哉,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报应说”,这哪里是贼?分明是牛四郎啊!这家伙死得冤啊,死得屈啊,一个粗枝大叶的爷们,怎么死不行,非要被一头猪拱死,去了阎王殿都被小鬼耻笑,这陈哑巴又偏偏欺负小寡妇,他焉能灵魂安放?焉能不报复仇家?哑巴坐不住了,不光流言蜚语直冲他来,大肚子老婆在流言里也发烧继而胡言乱语,令其不得不屈服于某种神秘力量。他放弃报警,转而托人四处打问那些“神婆子”“神算子”,家中也开始焚香吃素,一时间整个村里人心惶惶。
人们吃肉的热情跟着跌减下来,牛娘家的生意也随之降下温来。如此,焦双喜反而有了更多与牛娘独处的时间,不仅帮着煮肉卖肉,还勤快地打扫院子,拾掇家务,里里外外弄得像模像样。牛娘终究是女人,她一开始与焦双喜保持着距离,但天长日久,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牙齿哪有不咬舌头的,焦双喜那黑黝黝的手,牛娘那白皙皙的手,像打了花儿似的,总会在肉板上不经意间地触碰。牛娘从针刺似的缩回来,到碰着黑手像摸着猪肉牛肉般稀松平常,两人真似过起了日子般。抬头看那枣树,分明已挂满了花生粒大小的青果子。
待牛娘将四郎遗物一一打包,放进了偏房的一个衣柜里时,焦双喜听见衣柜的大锁头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在他眼里,这间小屋乃至院落乃至整个村落,才真正换了天地。他去了趟镇上,选了一块好肉,打了一壶好酒,包了两条好烟,去了趟胡小手家。傍晚,胡小手老婆来到牛娘家,笑嘻嘻地攥起牛娘的手:“树上喜鹊喳喳叫,咱妹子好事要来到!”
牛娘的脸红扑扑的,赶紧去烧火做饭炒菜,拦也拦不住。晚饭桌上,有酒有菜,有说有笑,有旧情又有新愿,焦双喜便多喝了几杯,又努力控制着,怕醉倒了,像那西游记里醉酒丢丑的猪八戒,惹得物极必反;但还是喝多了,守着牛娘不能不喝多,胡小手两口子何时走的,他全不记得,恍惚间,出现洞房花烛的错觉,迷迷糊糊走进里屋,一头栽进了被窝里,那里面香喷喷、暖烘烘的,像牛娘软软的身子。
当他于深夜口干而醒时,窗外一轮银盘似的月,正向他射出神秘而幽静的光。他起来准备喝口凉水,却发现屋门半掩着,顺着月光走出去,一个幽灵般的身影正从院墙跳出去。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洗一把脸,明月、枣树、肉板,都清晰地沉默在眼前。他才想起来,此刻是在牛娘家。他惊慌失措地走进屋里,寻了一遍又一遍,哪有牛娘的影子?一簇极短而逝的白亮,于暗夜中引起他的警觉。他鼓起勇气寻过去,恰是那把尖刀,于月光的反衬中不甘寂寞。焦双喜霎时酒醒,浑身起了无数鸡皮疙瘩。他大叫一声,像个丧家犬一样窜了出去。
翌日,陈哑巴发现家里又丢了一只大白鹅。他终于请来了“神算子”,遵照他的意思,将一块灵符用砖头压在了四郎坟头上。他不再大呼小叫,也不再找胡小手诉冤了。
那焦双喜却浑身发热、头重脚轻,下不来床了。
四
陈哑巴够意思,请“神算子”去给双喜瞧了瞧。“神算子”说:“杀气太重了,你忘了牛四郎咋死的?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杀生多了必然折寿,放下屠刀吧。”
焦双喜听不进去。他难受,病了好几天,牛娘没来看他一次。他困惑,他苦闷。他怀疑那个晚上吃饭喝酒是假的,他之前为牛娘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特别那个夜晚、那个黑影,再就是那把尖刀。牛四郎死了,这把尖刀应该随之永远地消失。他又记起,那个协商赔偿的下午,陈哑巴把黑猪绑了,放在板车上给牛娘推来。板车刚放下,惊心动魄的一幕出现了。那个上午还在胡小手老婆怀里黯然神伤的弱女子,竟然疯也似的冲上来,手里攥着明晃晃的尖刀,直奔猪脖而去,随着黑猪尖声哀号,血如喷泉四射;尖刀在女人手里像缝衣服的针线,一下、两下、三下……在黑猪的头、肚、腿、腚上来回穿梭,直到被捅成了马蜂窝。在焦双喜眼里,牛娘杀的根本不是猪,而是人。此后,在与牛娘朦胧而局促的接触里,他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又觉察不清楚。他现在明白了,就是这尖刀,薄薄的钢片,成了立在他与牛娘之间的一道墙。
他起身出门,一绺风儿围着他转,像牵在他身上似的。这风儿完全没了之前的干燥,带着熟黄的味道,比春风厚沉,又比秋风暖韧。大概到了夏季最好的时候了。
远远地,他就看见牛娘在门前忙活。他攥紧腰间的砍刀,上去就和牛娘忙活起来。
抽着闲空了,他随意说:“牛娘,我这把砍刀,不比你那把尖刀好使?”
牛娘忙活的手戛然而止。她抬起头来,望着他,他亦静静望着她。她长了一个并不明显的瓜子脸,但那双凄凄的眼神,与那天痛杀黑猪的女人的眼神,是那么的相似,好像这眼神一直没变过。她的沉默令他心不在焉,开始变得笨手笨脚,仿佛那堵墙,已经将他与牛娘隔了个严实。一个人在他背后轻拍两下,只见陈哑巴笑嘻嘻地说:“晚上没事喝两盅去!”焦双喜想起他请“神算子”给自己看病,便不好拒绝,也无暇顾及牛娘的感受了。
两人在村曾形影不离,一起捣蛋,一起偷摸,一起酒肉,臭味相投。但来了个牛娘,两人关系莫名紧张起来。陈哑巴主动请酒,倒不是大度大气。因为偷盗一事,他一度怀疑焦双喜所为,某天夜里还偷偷打碎过双喜家窗玻璃,后发觉和双喜无干后便一直心怀内疚。焦双喜和牛娘订婚的事情传出来,他一直想重归于好,焦双喜也正有此意,一根绳上的蚂蚱,早晚得凑到一块。
晚上,弟兄两人推杯换盏,东拉西扯,说起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唏嘘不已。焦双喜比陈哑巴大几个月,端起酒杯颤颤地说:“弟啊,你这都快是三个孩子他爹了,不能再和以前那样了!”
陈哑巴也举起酒杯,歪着嘴说:“哥啊,你也是马上结婚的人了,也不能和以前那样了!”
“干!”
“干!”
两人痛快地一饮而尽,肩头沉,心里重。借着酒劲细看对方,那鬓角的杂毛已窜出灰白,黑脸的角落已生出沟壑,岁月正毫不留情地蹉跎着两人。酒杯,不知不觉又满上了。
陈哑巴老婆肚子已滚如皮球,走路蹒跚如肥鹅。“你兄弟俩少喝点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话音未落,忽听得鸡棚里一阵窸窸窣窣。陈哑巴红着眼叫一声:“不好,又要丢鸡!”陈哑巴老婆叫唤一声:“王八蛋,我管你是人是鬼,老娘跟你拼了!”说罢,肥鹅似的往外扭。陈哑巴歪着嘴说:“都请神了,沉住气吧!”那夹菜的筷子还未放下哩,就听见院里传来一声惨叫。两人大惊,飞也似的窜了出去。
五
胡小手从镇医院回来时,已接近中午,老婆问:“哑巴媳妇咋样了?”
胡小手气喘吁吁地说:“大人保住了,孩子没了,都快足月了,真可惜!”
“昨晚上究竟咋回事?”
“哑巴和双喜喝酒呢,听着院子里有动静,哑巴老婆先出去了,大着肚子呢,你说她急啥?刚出门就摔了,她说像被谁推了一下……嗨,你先给我整口水喝……”
跟胡小手一同回来的还有焦双喜。双喜够意思,从昨晚一直陪到现在。他正急匆匆地往牛娘家赶。远远地,却看见牛家院门紧锁。他一头雾水,前前后后寻了个干净,始终没有找到牛娘。
他窜进胡小手家里,哭丧着脸说:“牛娘没了!”
胡小手正在喝水,从鼻子里呛出来,好一阵咳嗽,才说:“说清楚,啥!”
焦双喜说:“大门上挂着锁呢!”
两人又出去找,还发动群众找,找了半晌,终于找到了一个知情人,是个放羊的,说上午放羊时,看见牛娘去村北坟地了。又说,她来到一个坟头上,把坟头上的砖头扔了,然后在坟堆里挖了一个窝,埋了一个白布包裹。
胡小手问:“埋的啥?”
放羊的说:“太远,没看清。”
焦双喜怔愣着说:“我知道埋的啥了。”
牛娘此去再无消息。又生出各种传言,大都飘浮在空中,虚虚实实。牛四郎在村里只有零星的远亲,已没了至亲之人,牛娘远走或是远嫁,不再和村落有任何干系。胡小手慨叹:“双喜可惜了!双喜可惜了!”
他所叹息的那个男人日渐沉默,还悄悄白了头,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有个老者说:“这闺女来了,村里就没消停过。走了,未尝不是好事。”这话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如果牛娘不在,那午后的光阴里,院前不再有肉摊,风中不再飘肉香,这村还是原来的村吗?又有些许人,期盼着、憧憬着,某一日那个女人又重新回来,毕竟,小院子还在呢。
这天,胡小手在村里走访,来到牛家小院。那院门的大铁锁在风吹雨淋里,已变得锈迹斑斑。他忽然想起西院墙,以前常被焦双喜爬着偷看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他也爬了上去。
大半个天井露在眼前,里面已杂草丛生,一派萧瑟,各种杂物堆积,仿佛在告诉他,离去的人断然是无意再来了。那枣树就在眼前茂密生长,红彤彤的枣子像被猪血染泡过似的。它是村里树相最隽秀、果子最爽甜的一棵。以前这个季节,四郎家院里总会拥满摘枣子的孩童,他们欢乐地、无虑地在这个小院出入,四郎则潇洒地在门口卖肉。这里曾是一块无忧乐土。
他从墙头下来,忽地想起了颓废的双喜,就要过去看。路上,这棵枣树还在他脑海中舞动,树下曾经被风刮落的枣花,有些仍残存于树根。这些夭折的花骨朵,相比枝頭的红枣,确实不值一提,但它们确实来过,又仿佛没来过,又仿佛虽来过但终究还得离去。
就在这思索回忆里,他一步一步朝双喜家走去。
【作者简介】小咩,本名杨连峰,80后,山东利津人;在《山花》《时代文学》《当代小说》《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若干;著有小说集《落花兮有槐》、散文集《洋江寓言》等;现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