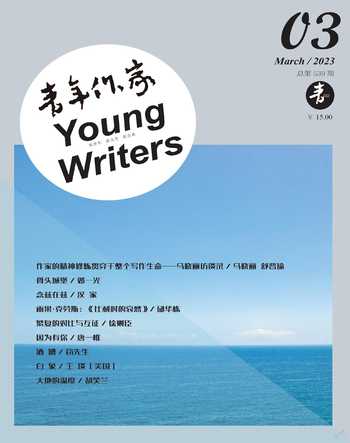等 候
她们科室里多是漂亮的姑娘,進出都热闹,像是开着遍地的花。凭她的年纪和资历,算是元老了,姑娘们都叫她主任。她呢,只好摆出慈祥的笑,笑着笑着就老了。
其实她也才四十出头,论年富力强,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光景,她自己给自己催眠,不愿出风头,老老实实地做她的整形外科主任,玻尿酸肉毒素什么的从不往自己脸上打,线雕拉皮激光美白更是避讳。她说老了就得正正经经地去老,就像一朵花到了凋谢的时候,你不能指望再抽蕊含苞地开一次。开,就是为了等谢的这一天。
这话没人肯信,进出她们科室的,哪有不爱美的?都疑心她是为了躲清闲——手术排得太满,有时候一整天下不了手术台,她口口声声自然规律,那些光是为了贪图漂亮的就不大好意思找她主刀,这样就给植皮或是割血管瘤的让出位置来。其实这想法多余了,人们为了美是不遗余力的,割双眼皮的照样觉得自己的一双美目比较重要,而乳房填充或是抽脂的也没打算往后排期。她在手术台上站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就这,她每天也来得最早,等着上手术台似的。
她办公室的后窗正对着医院大门口,从窗户里能见到街上流过来流过去的人和车。背景从来没有变过,变的是人,早些年一头黑发,渐渐斑白了双鬓,现在连头顶也覆霜盖雪了。她看着他走进来,瘦瘦高高的个子,一步迈出去,抵寻常人两步。但到底是五十多岁的人,腰身有些佝偻,不像多年前那么挺拔了。她看着他,像是看着自己,从二十岁的小姑娘,到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要是他和她换个位置,他在楼上看她,而她从大门外不紧不慢地走进来,他也能清楚地看到她头上有了白发吧。
这幅颠倒的画面,她是想象过的,只是从来没有机会得到实践。
这是她每天早早地就来到办公室的原因,早早的,这样就不会错过了。她可以看着他,从医院大门口走进综合大楼这么一段不长的距离,不会超过一分钟,然后各自忙碌地度过一天。
一分钟,一天。换算起来似乎很不好理解。但是把这一分钟放到一生的背景里,那就大不一样了。有了某种神圣的意味,她想,她的爱情就是这样神圣。
为此,她的网盘里专门有一块地方是安放这份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的,除了她的日记、她和他的往来邮件,还有一部不知道从哪个网站下载的旧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1979年的《北京文学》,第11期,她记住了小说面世的时间。那年她还没出生呢,但他已念初中了。她总是喜欢玩这种加减年份的游戏,像个贪玩的孩子,对脑海中不着边际的虚构暗里着迷。遇到什么事情,例如她参加高考,或是第一次独自去旅行,必定要把那个时候的他换算出来,想着他们如果在那个时候相遇,会有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样的想象往往让她感到满足,正好填充了现实中她和他之间的不足。
她和他,只是同事关系,或者说上下级关系,再远一点儿,她还是个实习生的时候,跟在他后面做过几天助手,喊过他“老师”,除此之外,不能再亲密了。
说起来,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并且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止步于这种平淡的关系,但在她的记忆里,过了二十年仍旧鲜活——记忆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那时候她刚刚从医学院踏入医院,一字之差,变化可太大了,不仅是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且她整个身心也经历着剧变——她实习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妇产科,虽然在医学院里的知识储备已经够扎实了,但到底还是个小姑娘,看到妇人生孩子,忍不住感到惊悸,对于子宫和产道的想象都变得扭曲了。
不可能。她痛苦地想。妇人哀号起来,下体撕裂的感受在她这个助产士的身体里非常明显。这样想的时候还会伴随呕吐,她吐得苦胆都出来了。一道来实习的几个同学,有男有女,反应都没有她明显。这种事情,因人而异吧,他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她,只是淡淡地说,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这真是一句朴素的真理。
后来她终于习惯了从角落里毫不引人注目地默默看他,竟然觉得无与伦比的快慰和宁静。他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有那么一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她一点儿也不在乎,爱一个人是那么美好,她爱他,这就够了。
当她还喊他“老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个小姑娘与其他实习生的不同。她的功课名列前茅,而且专心、细心、耐心,这些都预示着她将来会是一名优秀的医生。他告诉她,慢慢来,这是一道生门,尽管血淋淋的,可是没有哪一个科室像妇产科这样值得。
他用的词儿可真有趣,“值得”,她咀嚼着他的话,觉得哪怕用一生去爱,而一无所得,也是值得的。
他,一个男医生,居然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好多妇女都是他的粉丝。她想想未免好笑,眉眼弯弯地笑起来,压着岁月的沧桑。
最好笑的是,她也是他的粉丝呢。
在妇产科实习结束,他请他们几个实习同学吃了一顿海鲜。因为太贵,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内陆城市还没有吃海鲜的习惯。他说请他们吃顿好的,好让他们记住妇产科是个多么值得的好地方。大家都起哄,喝了不少酒,几乎个个东倒西歪。只有她是清醒的,因为她对海鲜过敏,这顿饭吃得简直像受难。他抱歉地说下回专门请她,川菜、粤菜、杭帮菜、本帮菜,随她挑。她笑着摇头,他却大手一挥,不容她表示异议似的,端起杯来说,今天大家都高兴,你吃点儿亏,包涵我这个东家考虑不周。给她说得不好意思起来,不由自主地举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
在海鲜酒店喝完,还不尽兴,大家又东倒西歪地结伴去了KTV,开了个大包厢,侍应生送上来一箱啤酒,于是接着喝。
在这里喝和在饭店里喝又不一样。一是氛围不同,二是程度有异。在东倒西歪的基础上,又加上乱七八糟,每个人和平时都不大一样。没有老师和同学了,没有医生和实习医生了,男同学攀着他的肩头叫老大,女同学呢,脸红扑扑的,一口一个欧巴。她坐在他边上,也改了口。第一声叫得还有些羞涩,第二声就很自然了,欧巴、欧巴,这样叫着,何止是顺口,简直是甜蜜了。她偷眼看他,正好遇到他的目光也热烈地投过来,她刹那就沦陷在自己的战栗里。
她不是没有恋爱过,刚上大一就有男生追求她。不過她是个目的论者,觉得校园恋情多半不会有结果,所以一直没有理会。直到上了大三,她才在众多追求者中接受了那个最长情的男生——不接受好像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两年来,他每个周末都站在她的宿舍楼下,送花、送巧克力、弹吉他、用蜡烛摆出心形和她的名字,各种花招,多么招同宿舍的女同学羡慕嫉妒恨。可是,和他比起来,她顿时觉得所有的男生都只是过客。他们全部加起来也比不上他的一根手指——他的手干净修长,灵活而稳定,能把绕脐三周的胎儿从母亲的产道里温柔地接到这个世界,如果对着阳光看,他的每一根手指都是透明的,像玉雕,堪比完美的艺术品。她就不只一次地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他的手托举着艰难的生命,奋力啼哭的婴儿以及虚弱而欣慰的母亲,都成为这双手的背景,构成世间最蕴藉深沉的图画。
这样的图画让她眩晕,不顾一切地情不自禁。
那么是因为这双手而爱上他吗?
她问了自己一千遍,然后第一千零一遍地否定了这种爱屋及乌。
不,不是的,他的头发、他的呼吸、他的衣袂,都让她感到眩晕和情不自禁,像遥远的月亮神秘地牵引着地球上的潮汐。就这样不知所以地深陷进去,明知道他是她的老师,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的粤语歌唱得好,几乎和他的那双手一样,在全院是出了名的,都说他可以上红馆开演唱会。他倒不知道她的粤语歌也让人惊艳,一开口,大家就嗷嗷地起哄,说要点一首男女对唱,两人PK一下。这就把他俩推到一起去了。
《片片枫叶情》,凄婉得不像话的一首老歌,他唱张智霖,她唱许秋怡,百转千回地一曲下来,全场都沸腾了,巴掌声和口哨声掀翻了屋顶,都说比原唱还像原唱。她唱得太投入,眸子里泪光点点,唱到“片片叶儿携着我此生所爱,一飘再飘梦更远”的时候,几乎不能自已。她心里翻腾得厉害,明明是表达恋人分手后不舍之情的一首歌,在她演绎起来,似乎是把时光倒着流了一遍,还没有开始,就哀叹他们的结束了,不得不“低叹再会了这段缘”。他怔怔地看着她,几分惊讶,几分心疼,大约还有几分莫名其妙。
说起来他是她的老大哥,相差十几岁,论年纪、资历、专业知识和人生的经验,他都是可以给她上课的。可是他听了她的歌之后,忽然觉得心底某个小角落里,被微妙地拨动了一丝琴弦,不大肯承认他是她的老师,而宁愿做她口中的“欧巴”了。啊,是因为这是一首情歌吗?他摇着头想,而且这里的灯光气氛都太暧昧了,酒精把荷尔蒙蒸腾得到处乱窜,简直像是扑面的蚊蝇,打都打不掉。他和她又碰了碰手中的啤酒瓶子,表示庆祝,一首歌合作得这么完美,他们肯定是有默契的。这种默契如果延伸到工作和生活中,想想都让人觉得愉快。那么,就为了这种愉快干杯吧。
她后来读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当读到“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心里就会痛得发麻,因为“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她完全把自己读进去了,并且进去就出不来,相信“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
他和她不也是这样吗?在无数个不眠的夤夜里,她听着歌流泪,想念他的味道、他的眼神、他的一颦一笑,明明在白天看到他了,却不能走上前去给他一个拥抱、倾诉她的相思,只能客气地打个招呼,或者远远地望一眼,彼此没有任何僭越世俗眼光的交流。
不能有任何引起别人怀疑的交流,她知道的,他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她怎么能做第三者呢?这样不名誉的事情也太羞耻了,她承受不起,并且因为她爱他而让他去承受那样的羞耻,她也不愿意。所以,不能做那样的事,连想一想也是对那桩既成婚姻的犯罪。那么就默默地爱吧。他知道也好,不知道更好,她爱他,可以用一生来做计量单位。
她多么希望早一点儿遇见他。
她上幼儿园的时候,或者小学一年级,最迟不能超过小学二年级。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给他介绍对象的表姨还没有把他后来的妻子介绍给他,也就是说,他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去爱她。他们遇见了,在公园的滑梯旁,他笑微微地对她说,等她长大了,就娶她做他的妻。她一下子就信了,并且笃定地答应他,她一定会做他的妻。这下轮到他感到吃惊了,他只是路过这里,偶然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心里觉得喜欢,所以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怎么?她看他愣在那里,就得意地笑起来,她才不会告诉他,她一直在这里等他呢。
这样的故事被她虚构了好多遍,她都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一个作家了。像写《爱是不能忘记的》那位女作家一样,她也可以写出那样虐心的爱情故事。
真是虐呀,男主和女主只相互看了对方一眼,就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可是,不能,他没能等她长大,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了。
要是她现在贸然向他表白,那么就会把他推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她不忍心,只有守住那道线,爱他,却心口难开。
他不知道吧,或者装作不知道。
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说过的话都算数,后来果然专门请她吃饭。地点是她挑的,一家本地土菜馆。是不是应该有所期待呢?哦,不,她一听说上次作陪的那些人一个都不少,就知道自作多情了。他是知道分寸的,请一个女孩子吃饭,和请一桌人吃饭,大不一样,虽然这次他只是想请她吃顿饭。
自然又喝了酒,没有酒是不成的,没酒的话,就连去KTV唱歌都好像没有足够的理由。
这回他们唱的是张学友和邝美云的《只有情永在》。
更老的一首歌,简直老得刚刚好。邝美云唱这首歌的时候,正好是她小学一年级升二年级那年的暑假。他选的这首歌,正合她的心意,她觉得他们一定是心意相通的。不相通怎么唱得了这样的老歌?
她唱: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他唱:懒得问恩怨怎分开。
她唱:当一切若浮云。
他唱:只有情永在。
他们合唱:心中记一份爱。
啊,她唱着唱着泪流满面,比上次更加不能自已。他反倒笑起来,抽了纸巾,给她擦眼泪,还怜惜地在她鼻尖上刮了一下,说,傻丫头。这动作真是恰到好处的亲昵,那样的灯光、啤酒、氛围里,谁也不觉得突兀。有个男同学已经和身边的女同学抱在一起哭起来,他们是一对恋人,但是等到实习结束,就要面临不得不分手的局面——一个回南方,一个去北方,总之是南辕北辙。他们的眼泪给她打了掩护,只有他知道她为什么哭。
他问她轮转到哪个科室了,她说呼吸内科。他点点头,说呼吸内科的主任是他大学同学,两人睡过上下铺。当时他们考研准备的都是一个方向,没想到后来他干了妇产科,真是鬼使神差,也可以说命运是多么神奇。他这样说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望了她一眼,那一眼看得她心怦怦地跳,好像真是他说的那样,迎头撞上了命运。
再以后他们就没有什么机会聚在一起了,他对她做出的唯一亲昵举动,就是那次轻轻地刮了下她的鼻子,怜惜地说了一声“傻丫头”。
他到现在还记得她小小的鼻尖那冰凉的手感,真是奇怪,喝了那么多酒,包厢里又密不透风,大家都热得冒汗,怎么她的鼻尖是凉的?或许这就是她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的理由吧,她总是在那么多人当中让他觉得不同寻常。
虽然后来见面的机会不多,却无处不是她的影子。他也觉得奇怪,这不是他这个年龄人的正常念头。
那么,他这个年龄的人,正常的念头应该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的专业搞好,还要平衡好家庭,尽量往上走,不辜负把他培养出来的农民父亲。他的老父亲,不容易呀,砸锅卖铁地供他考学,好不容易儿子出息了,可父亲进城看儿子,还要看人脸色哩。因为媳妇是标准的城里人,在媳妇眼里,农民父亲多少有点儿磕碜。媳妇也是知识分子,所以大面儿上还过得去,不过父亲来过几次,就不大愿意进城了。父亲说你们有自己的小家庭,我也有自己的几亩地,等将来,我侍弄不了这地了,就和这地埋在一起,也不碍着谁。这话说得儿子有愧,可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把城里的家散了,陪父亲回老家种地去。
他的女儿也一点儿不像他,长得太漂亮了,和他的妻子一样漂亮,加上在姥姥家待的時间多过在他夫妻俩身边的时间,所以和爷爷没有感情也是正常的。他有时候都怀疑女儿和他的感情也很稀薄,因为他太忙了,忙得忽略了她的成长。有一次他去外地参加会议,想忙里偷闲给女儿买双鞋,不知道码数,只好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淡淡地说,你还是别买了,买了她也不喜欢。他愕然,随后觉得一阵悲哀。
这些婚姻里的琐事,她是不能理解的。她还那么年轻,眼睛里清澈得只有爱情。所以他苦笑着摇摇头,在回复她的邮件里写道:考研的方向并不是人生的方向,况且就算是人生的方向,也不是不可更改的。你怎样决定都好,关键是自己喜欢。
她和他的交流,多半是这样中规中矩的邮件。朋友、老师、同事、前辈,无论哪一种身份都好,都是干净的。干干净净,这是他面对她时,他对自己的要求。就算有一种感情是不可遏制的,他也必须扼住感情的喉咙,不然怎么对得起她呢?连自己也对不起。
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医院,果然如他所言,由于时间的训练,业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过任时间这个教练再怎样敬业,她的婚姻也并没有顺利地提上日程。大学时谈的男朋友自然是分手了,她觉得和男朋友结婚的话,实在是不负责任。男朋友苦苦哀求不得,终于改掉了在她这棵树上吊死的打算。再往后,她一直单身,他隐约知道一点儿她的情况,但绝不打听,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
他呢,在一个中年人正常的轨道上忙碌着,评正高,做博导,然后成为全院最年轻的副院长,在世俗的评价体系中,确实春风得意。偶尔他也会想到她清澈的眼神,希望她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可她为什么一直单身呢?他摇摇头,但难免又会想,她还是单身的好。可是,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终究不与他相干。他没有想到医学美容中心三楼那间靠东的办公室的窗口里,每天都有一个人在等他,用炽烈的目光迎接他踏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走进来,又目送他的背影走进综合大楼西侧入口的阴影里。
时光流起来就像水一样,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还有些波澜,三十岁以后,她婉言谢绝了最后一个相亲对象,一下子就波澜不兴了。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也觉得无趣,渐渐不再操心她的婚事,毕竟医院里永远都有年轻的姑娘,一茬一茬地生长着,把老去的姑娘从浪花里淘出来,甩在滩涂上。她脸上的天真,逐渐被一种慈祥所替代,看什么都顺眼,花花草草,莺莺燕燕,都好,都因为她的一双手,变得更好。
真是好呀,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双手,现在和他的手一样,被很多粉丝追捧呢。
医院成立医学美容中心的时候,她当仁不让地被推到副主任位置上,主任由分管副院长兼任,不怎么到中心来,实际上是她担纲挑大梁。她当时还想,如果他来分管美容中心,那该多好,凭空多出好多请示汇报的机会,不过终究也是空想罢了。
他自然替她感到高兴,她还是个实习生的时候,他就说过,她和其他实习同学都不同。实际上,到底是她和别人不同,还是她在他心中与众不同,他从来没有深入想过这个问题。或许是不敢想,或许是因为想了也没用,所以不让自己想她是最好的办法。
彼此这样想念着,又拼命压下那种念想,真是痛苦,可是能怎么办呢?他做不下抛妻弃女的事,尽管女儿已经大了,已在国外读书,一年也难得见一面;妻子呢,供职的那所大学正好有个在那边交流访问的机会,就跟过去了,实际上是母女俩把他给抛在了国内。但到底他们才是一家人,二十多年来,都是一家人呀。他在医院领导班子里的位置也很微妙,原先提拔他的院长退下去以后,又空降了一个少壮派,班子里那些元老看他的时候,都是看笑话的眼神。他在业务上是一把好手,做官这方面却是个庸才,于是一年两年的,就原地踏步了。不过这也没什么,父亲早就去世了,他不用再那么努力,怕辜负了父亲,顶多是辜负自己。
自己有什么可在乎的呢?辜负就辜负了吧。
只是不要再辜负别人。
所以,不能爱,不能表白,不能往前走哪怕一小步。
她理解他,就是因为理解他的难处,所以才更爱他——现在没有人相信爱情了,难道不是因为责任感弱化吗?既然没有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两个人拴在一起,爱可是比婚姻脆弱得多。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你和他谈什么爱呢?这是个悖论,没办法解决,她的爱情就只能是苦恋,像一杯苦咖啡,不能一饮而尽,要慢慢品,品一生还不够。
一年又一年,快得很哩,转眼又到年根儿了。今年他是一个人,女儿因为毕业实习,抽不出时间回来,妻子也就顺理成章不回来了。这早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默契,什么都以女儿为重,一个家嘛,孩子比什么都重要。他一點儿年货也没准备,用不上,反倒是累赘,一个人挺好。
她在家里和母亲包了饺子,又帮父亲贴了春联,这一年就算正式过完了。接下来,是新的一年。新年是什么模样呢?多半和旧年一模一样吧。她心如止水地想,爱是不变的,所以一切都不会改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亲不再关心她的婚事了。他们的关心只换来她的不耐烦和年复一年单身的决定,还惹得全家都不高兴,那就算了吧。这几年,算是彻底安静了,年过得一派祥和。母亲在厨房炸圆子,油烟机抽得轰隆隆响,还是有逃逸的油烟从门缝里弥散出来,搞得客厅乌烟瘴气。她坐在沙发上,陪着父亲看电视,深深吸一口这浓郁的烟火气,觉得很满足。她歪着脑袋想,他在干什么呢?也和她们家一样,一家三口享受着人间的烟火吗?那么,他应该也是满足的。
不过这种满足在随后暴发的疫情面前就显得单薄而琐碎了,尤其是医疗战线,他们面对的要比普通人更多、更残酷。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他们自己也是普通人。
母亲抱着侥幸说,幸亏她不是感染科的。她现在的工作倒是轻松许多,那些可做可不做的美容美体手术,都用不着排了,在生命面前,再完美的脸和身材都得让位。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去病房看看春节前收治入院的病人,抑或站在办公室的窗口凝望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哪个方向呢?她感到心乱了,和以前站在窗口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她知道他每天都会从一个确定的方向走过来,然后她再目送他去另一个确定的方向,可是现在,她一点儿也没有把握。
放假回来,她才知道他跟着援鄂医疗队走了,原本想不到的,论专业,他可不是医疗队需要的医生。可又想想,也不难理解,他分管危重症医学科,呼吸专业也曾经是他的研究方向,说他是全科也不为过,况且她不知道这个春节他是一个人过的,决定名单的时候,医院领导一致通过由他来做小组领队。
这没什么可研究的,她倒不怀疑,即使没有医院的决议,如果需要一个人冲在前面,他也会迎难而上。这就是他的个性,她爱他,不也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她收回模糊的视线,在窗前转了个身,背靠着铝合金窗框,发出深深的叹息。
已经立春了,这个春天和以往的每个春天都不一样。她胸前剧烈地起伏着,想到这个春天他化身为和死神战斗的武士,心中有说不出的骄傲和悲壮。
她带着强烈的情绪,握紧了拳头,像是要和虚空中的敌人一决高下似的。
【作者简介】刘鹏艳,作家;著有小说集《雪落西门》,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并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现居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