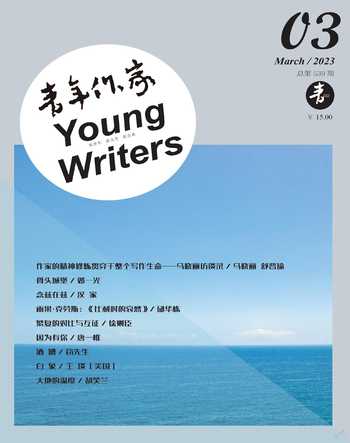关于故事或者故事的作者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很多年前成立了一个创意写作班,叫做“牡丹江师范学院乃寅写作班”。“乃寅”是黑龙江作家韩乃寅的名字。韩先生也是牡丹江师范学院的校友,生前一直致力于母校大学生创意写作实践,因此有了一份动人的赤子之情。看这个写作班的名字就知道,这差不多就是个写作工坊的设置。这是牡丹江师范学院很厉害的地方,它是较早开创意写作课程的大学,至少是黑龙江省的第一所,没有之一。而且,它有自己的法子。首先是工坊形式,每个班级十几名或二十几名同学,来自每一年秋天开学季的一次全校范围征召。所以,学生来源理论上涵盖这所大学所有的专业,只要你真心热爱文学,哪个专业都是可以报名的,在这一点上真的足够创意,给不同学科的孩子提供了文学造梦的机会,结果就是班级里理科生文科生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在文学的天空下展开讨论和写作实操。这个课程是一门公选课,有学分,但我觉得这个学分对学生们的“约束”可能极小,主要是一种助动,或许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福利都指不定。课程设置简单说有两大块,一方面是文学院专业教授给弟子们讲授文学与写作理论,而我们——几位作家主要带领学生操练。写作班有专门的工坊——创作室,空间不大,圆桌式,平等研讨,自由抒发,舒适熨帖,在里面讨论和操练文学都不痛苦,大概美滋滋的感觉更多一些。我看到学生们很放得开,经常遨游在想象之中,畅所欲言——再怎么说,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考量标准。
我是2019年3月加入这个团队的,笔名窃先生的高云天同学2019年秋季入学。这是一位天津男孩,一位瘦弱的少年,是一位活跃人士,喜欢表达自己;有时候很时尚,扎辫子、大风衣、长围脖那种;有时候又不修边幅,头发纷披,衣着随便一穿的样子。他主持写作班的读书会、跨年晚会,如果有些活动他换了角色做一个参与者,那他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因此他是我最早将名册上的名字与实体人对上号的几位学生中的一位。
我记得窃先生加入写作班不久,就一次发给我三篇小说,篇幅都很短,就是率性而为,兴致所至,操作自由,想写啥就写啥,想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再看故事,都是对成人世界的觀察,跟自己的少年生活没有关系。他这就跳出了自我的小圈套,有些细节还挺精彩的。依我看,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一个在十年间一直做着材料作文训练的孩子,单说转换一下叙述视角都是很难的,这么快就松绑了自己,还主动给自己一条想象力的缰绳,用第三人称视角讲一个虚构的故事,这还真是挺让人惊喜的。聊了聊,知道他之前从来没写过小说,用他的话说,他只写过几篇小随笔——我猜过几年,他回头思虑说过的这句话,称为随笔的文章,可能会觉得还是草率了。当然,我这边并没有丝毫哂笑的意思,因为总是这样:当我们对文学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回头看自己的来路,就会会心一笑,而这一笑又不大有辛苦劳累的烦扰,而是因了日复一日思索、顿悟、积累、实践以及探索所获得的长进,甚或某些通透端正的成熟下获得的文学真相,都在那一回头中,给我们安慰与奖赏。我没有别的行业感受,单说文学中的你,十年前和十年后,就似乎不太是一个人了。十年前你好像还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瞎写”,而十年后谁也“忽悠”不了你了,你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逻辑,而且自洽。目测窃先生在小说的写作上,大概率不需要那么久,依据他接下来三年时间里的创作,他已经有了很赞的佳绩了。
窃先生的《酒糟》最早拿给我时,还不是完成稿,三千字左右的样子,我先看了,也听他讲了预设的故事,建议他拿到课堂上来大家讨论。写作这件事,的确必须构建自己的大格局,虽然它是个人作品,但是讨论的好处是双赢,一方面作者自己混沌不清的东西,或许在自我表白、剖析或者听取他人说法中突然显现灵光,而变得清晰、变得丰饶。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在讨论别人作品的时候,何尝不是一种实践?因为你要切入,你要使你的观察合情合理,你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视角——作者的、读者的、评论者的,你要抽身故事之外,又要深入故事内里。但是,小说毕竟是作者的,他要运作自己的逻辑,讨论是一回事,结果又是一回事,这难道不是文本讨论的目的吗?窃先生在讨论课上谦逊随和,但实际上不是轻易“让步”的人,这一点之后会重提,还是回到他的文本上来。
《酒糟》写了一个幻灭的故事。一个叫于鹏的男子,从一个天真洁净的小男孩(和天下所有小孩子一样),沦落为酒鬼,并最终死于酒精中毒(或者死于悲观沮丧)的故事。这个小说里面有广阔的社会背景,显而易见的是原生家庭的罪与罚,这似乎是故事的近景。窃先生下手实在狠,追踪三代,如同应对法庭一样,给出夯实的证据:这户人家对家暴的热衷,不是偶尔的人性偏差,而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宿命。还有远景,远景更加纵深,从于鹏的知青母亲身上看到,个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附着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而被裹挟之后产生的后果,并不终止在本人本代际身上,却由毫无准备的、并不相干的下一代承担——这是多么的不公平!这又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发现!它实在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
《非典型相爱》同样是幻灭的故事。如果说《酒糟》关注了三代人,付出漫长的时间才缓慢交出人生真谛,那么《非典型相爱》聚焦的时间线索非常短促,仅仅一两年,但是对男主人公来说,他的爱情幻灭,已经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了,总之非常惨烈。但是细细观察,男主人公的幻灭,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如外在的因素,至少似是而非,难以确定。女友屈服现实的距离吗?像是又不是,小说因此就不同了。幻灭来自自我的不能耐受——生命承受之轻还是重呢?不管读者是否愿意承认,都可以在他的内在上看出端倪,坦白讲是他内在的缺欠。这缺欠又不是可以审判的,谁那么刻薄,要去审判年轻人的爱情呢?至少,我愿意给他的爱情幻灭以同情和怜悯。
我不知道窃先生是不是有意为之,这两个故事在主题上有着惊人的和谐之处,都观照了幻灭,“冷酷”地致主人公以绝境。它们全都有悲剧气质,作者毫不在意揭开故事真相。窃先生对小说结构的安排,亦显示出一种天然的能力。《酒糟》中规中矩,以故事人自述的形态叙事,线索绵密,步步相随。而《非典型相爱》简直就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势,它依靠时间线索吗?它信赖故事情节吗?它探索意识流动吗?窃先生的文字跳跃、腾挪得相当自由,也非常奔放,那种裕如、自信,那种丝滑般流畅的收和放,真不像是一个“00”后刚刚拿起笔的小男生写出来的。要不怎么说,写作的天赋才是最硬核的个人装备呢?
在文本之外,窃先生不太和我聊天——学生总是像花儿一样各有不同。这是很有趣的,有的孩子喜欢和我闲聊,有的孩子就不。有的孩子需要你具体到在字词上与他切磋,而窃先生,他没有错别字,标点用得也行,文本格式总是十分恰当。如果我告诉他,某些细节有些薄弱,他会回复说:好嘞,我再看看。如果他同意你的意见,再交上来的确不一样了。如果他不同意,他会跟我解释他的想法,绝不会委屈听从,而这时候我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一方面我真心不认为我就是对的,文学哪里有标准答案?一方面我早就告诉每一个同学,小说是你自己的,你说了算。我觉得保持一种自由独立的心态也是写作者的素质,或许它也是同学们对写作付出全情努力的自我动力。所以,我并不担心学生们的作品不完美,因为不完美那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啊。一个作家真正成熟起来,大抵不是写作老师教他的结果,他是不是完全无意识,是不是有文学的自觉,那又能怎样呢?他早晚会发现这些,并把握它们。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每一个写作者,大概率是在自己写作当中不断犯错的教训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和人的成长何其相似。所以,我最常告诉窃先生和他同学的话,就是:你别着急,慢慢来。
【作者简介】安石榴,本名邵玫英;在《北京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有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刊转载,著有《大鱼》等小说集五部;现居黑龙江牡丹江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