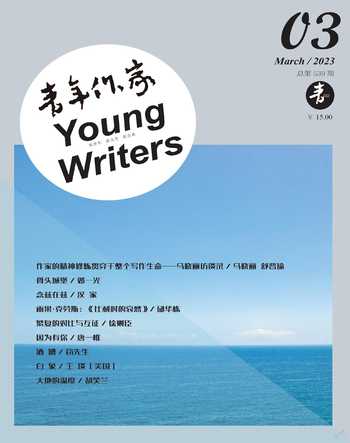拟态与真实
所谓拟态,就是以人的视角,去揣测、模拟,继而描绘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的存在状态。就我们要谈的小说——《因为有你》而言,对象是一条名叫元宝的小狗。始终没弄清楚它是否名贵,甚或是何品种。明确的是,它是条公狗——虽然这也并不重要。所谓真实,就是说,立足想象的“拟态”写作,边界在哪里?分寸怎么掌握?目的是什么?
掉一句老书袋: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这里“唯一”的限定,琢磨起来很有意思: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遗世独立,站在生活潮涌的岸边,隔岸观火。那么就意味着,是人,就不缺乏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的生活;同时,把非人类的“生活”纳入文学,就一定会被我们的生活笼罩。很难想象,用上帝的视角审视,人类是否被赋予了“主角光环”,但可以肯定,我们的主角心态由来久矣!
在我们诞生之前,众多生物(仅就生物而言!)登上地球的舞台,已经有数十亿年之久,但我们相信,亘古如斯的几十亿年的等待,只是为了迎接人类作为主角迅速而隆重地登场。虽然远古人类的心理活动很难捉摸,但不难想象,“人为万物之灵”的意识,并非秉自天赋。只是我们直奔舞台中心,别的生物就被排挤、驱逐,直至被孤立在世界的边缘,人类也慢慢把自己当成唯一、当然的主角。
有少数的物种,被拣选出来——不论幸运或者不幸,参与到人类生活的历史中来:有的从古至今都至关重要,比如作为庄稼的“黍麦稻菽桑麻”等,作为家畜家禽的猪牛羊、鸡鸭鹅等,都是人类富足的底色;有的,曾因某种功能被广泛利用,还曾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关键因素,比如作为耕种、运输工具的牛马,尤其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马,但后来随着功能的消失或减弱,跟生活的关系从紧密慢慢变得疏远。与生活的疏密程度——这就是一种“生活”关系,很自然地会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比如苋菜,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叫做“葵”。《古诗十九首·十五从军征》中,就说到了这种菜:“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做饭,采葵持做羹。”《诗经》也屡屡提及。但是在三国以后的诗歌中,它几乎消失了。背后的事实就是:“葵”在历史的选择中逐渐被淘汰,以致忘记了它原来的名字;后来有部分地区重新吃起来,却只能叫“苋菜”。
古今小说名篇,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来看,家养动物,有关马和狗的最多。但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分水岭就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它们在生活中也进而在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双向逆转:马不再在战争中占据核心位置,自然地也逐步退出普通人的生活;而狗,却越来越深刻地涉及生活的日常。狗,刚开始只是一个掠夺残羹冷炙的追踪者,因为狩猎时的配合、警戒,也是一个狗肉“移动的冰箱”,而被驯化。跟马正好相反,伴随实用的功能属性失去价值,它们没有被抛弃,反而勇敢地向现代城市突进。真是令人非常惊讶:它们几乎没有疑虑地接受、适应了新的规则和秩序——只给人类提供理解和陪伴,甚至乐不思蜀,忘了是狗。
可以用几个有关狗的名篇,和《因为有你》做简单的文本对比。
莫泊桑的皮埃罗,到底是否一只温顺或暴躁的小狗,甚至是否漂亮,我们似乎并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两个老姑娘,在经济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中,需要应对被偷盗的可能。所以,皮埃罗只要能够看家护院就好——最低限度,它得活着。但是,两位老姑娘因为实用(防贼)而来的慈悲心,终究抵不过四个法郎。这就是《皮埃罗》的核心——金钱的胜利。这是个纯粹典型的19世纪“狗故事”。
屠格涅夫的《木木》,可能是我读过的有关狗的小说中最震撼、最有艺术感染力的——这跟巴金完美的译笔有重要关系。小说语言和叙事节奏掌握得十分完美,与故事氛围非常融洽:聋哑巨人格拉西姆是最能干的仆人,也带有与世界隔阂的单纯和善良。他的情感梦想被女地主的专权随手打碎——更让人屈辱的是,最纯洁的爱情被女方辜负。但这些,他都准备默默承受。直到他被迫把他唯一的慰藉——爱犬木木淹死,才真正突破他的底线,进而反抗。这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俄国的“狗故事”——既有深沉的疼爱,也有农奴彻底的反抗;因为疼爱,所以反抗。
《因为有你》刚开始,以紧贴的第一人称,叙述一条走丢的狗,在垃圾场里挣扎求生的苦熬。流浪狗群中也有等级,充满怨恨、刻毒的嘲讽,也有拉帮结派,为了每一次进食勾心斗角。我觉得,它会是一部反向的《野性的呼唤》。杰克·伦敦的巴克,在人类的摧残中觉醒,挣脱人类,逃归荒野,最终变回了狼——也许,元宝会在被人遗弃的角落,带领一群流浪狗,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狗社会。我很快就落空了。其实,我并不喜欢《野性的呼唤》。一群雪橇犬,确实可能逃跑而野化——是否能变成狼,则是个生物学问题。但一群狗,竟然能设计复杂的逃跑计划,而且还有统一的“理想”:这种异想天开,只能是小说家对小说文体的一次越界——也就是我开头提出的“边界”问题。唐一惟明智地选择了回避,但也并没有彻底地摆脱问题。
元宝有关乡下生活的回忆,抒情而动人。乡下的生活宁静有趣,并且安定,对元宝来说,也富足。元宝在乡下的生活确信而自知。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奶奶的疼爱。爱,是元宝整段回忆的核心,也是作家的。对乡村生活环境,尤其熟悉的乡村人物,我们有确定的感受和把握方式,处理起来水到渠成。换句话说,这是现代乡村文学的积淀。现当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有代际差异。也可以说,这是19世纪西方乡村文学的积淀。勤劳的奶奶,生活拮据,无奈告别乡村——既是奶奶,也是元宝,情节竟然与《木木》隐然相似!
做个小结:写到这里,小说可能并没有提供新的思考——不管是有关当下生活,还是狗在当下生活中的角色,语言、叙事分寸的掌握,说得上惊艳。说到底,无论用什么视角,写小说的必然是人,感受和思考的内容,也只能是人的生活,并且是以人的方式。法郎士有一个短篇《里凯》,也是狗的视角,但是第三人称,情节很是简单。主人一家三口在搬家,而里凯(小狗)理解不了:以往不容被打扰的主人,被打扰了;以往不能翻动的地方,被搬家的人翻动了;平时的低等人在家里进进出出,而神圣的狗窝也被他们拿走,它只能躲进篮子里——家里到处是恐惧。里凯最后被主人带去散步,街上摆着家具,有句极为精彩的描述:“他(主人)也把佐埃的独脚小圆桌放到不受侵犯的地方,它落到街上好像感到很害臊似的。”是里凯在看、想,但肯定更是法郎士本人!年轻的唐一惟,多数地方语言分寸的拿捏,也都很惊艳——除了结尾。
逃归城市,回到人群——作为一只已经彻底被豢养的宠物狗,这是元宝最渴望的选择,也是小说最贴近现代小说的地方,然而也是最远的。当然可以分析,结尾和《野性的呼唤》有多么相反的对称性——但这不是关键之处。致命的是元宝的结局:治疗费是个难题,女主人把儿子的温情晾在一边,而彭娇(一个接近赤贫的爱狗者),也因为治疗费而极可能导致家庭破裂。虽然有一点儿现代生活的影子,但是我们应该更清楚地想起莫泊桑的《皮埃罗》——一个有关金钱的故事。小说结尾,元宝对主人儿子成长的参与和影响,是一个可能的方向——这个方面,张炜老师的中篇小说《爱的川流不息》提供了极致的描写。
其实,它们已经完全接受人类制定的新秩序,也竭力揣测人们的意图,并按照他们的意图活着,但是很多时候,无论它们如何祈求,人类也不给它们这个完全奴役它们的机会。这,是比被奴役更痛彻心扉的悲剧!
【作者简介】宗永平,作家、文學编辑;江西新余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责编过若干优秀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时光的隐寓》、长篇小说《炫耀》等;现任《十月》杂志副主编,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