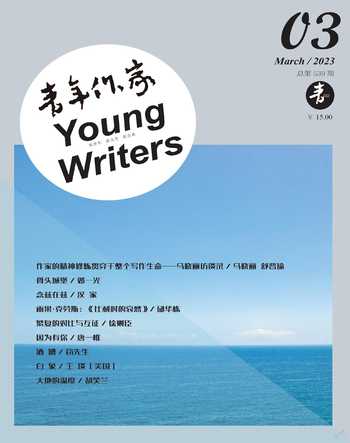繁复的对比与互证
徐则臣
众生平等,万物一也。如果人类能够进入一草一木、一鸟一虫的内心,应该会发现,它们也有一个自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离愁别绪和期待与纠结。所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才会如此震撼和深入人心。那只名叫格里高尔的甲虫和农庄里的动物,固然有拟人的成分,但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你必须承认,它们也在它们自身的逻辑里。价值与信念,生存和毁灭,如何直面现实和自我,怎样才可以更有尊严和有意义地活下去,这些问题它们一定也要面对。在这个意义上来阅读唐一惟的《因为有你》,它的优点和问题就同时凸显出来了。
小说中的这条先叫狗、再叫元宝、最后被命名为稳稳的狗,差不多可以为人世间的狗做代言。活在人群中的狗无非这几类:在平常人家,不管多尊贵的品种,也只能过上简陋的“狗”的生活;碰巧生在富贵之家,于是集宠爱于一身,名字都可以珠光宝气如“元宝”;倘若成了丧家的野狗,什么背景都白搭,脖子上拴着金项圈也只能去垃圾场里刨食;但劫波渡尽,沧海桑田的大世面都见过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唯求“稳稳”地活着便好。但它们毕竟是活在人间的狗,它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纠扯在与人的关系里。狗眼中有人,人眼中有狗。“因为有你”,既是狗生中因为有你这个人,也是人生中因为有你这条狗。庄周与蝴蝶,这是一个互看的过程,互为镜像。
不能说小说中的这条狗命途不济,好日子它没少过。尽管乡村生活贫寒朴素,但奶奶可是把它当孙子养的,情感上是何等的富足。到了城里,陌生是陌生了点,还被去了势,小男孩也是真心实意把它当弟弟待,华服美食伺候,以至于竟可以耀武扬威了。即便折了后腿,饱尝主人的冷眼,还是有一个叫彭娇的女人甘愿舍弃婚姻来施以救治。这人间终没有放弃它。
但它的确也有着过山车般跌宕的狗生,在垃圾场饥寒交迫地受辱寻食,幸运地到了家门口,就差临门一脚回归过去的安乐窝了,一辆车从它后腿碾过,又成了一个需要破费救治的累赘。一条散发香水味的富贵狗受了伤,还可以被目为不幸的残狗;一条瘦弱肮脏的狗残了,那只能是一个恶心讨厌的废物,弃之唯恐不及。此等落差,不仅让狗看清了自己的狗生,也必是弄明白了人生。鲁迅先生沉痛地写过:“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世态炎凉之于“元宝”,大约也如此吧。
唐一惟之本意,大约也在“狗眼看人”。这世上,有好心的奶奶,就有功利的儿子和媳妇;有天真无邪、爱心过剩的小朋友,也就有冷漠绝情的年轻母亲;当然,有薄情寡义的主人,幸而也有义薄云天的“路人甲”彭娇。此番繁复的对比与互证,完全成立,唐一惟写得饱满丰沛,世故人情曲折幽微。这条狗之复杂,简直成了人。写实的功力确实没得说。“因为有你”如一声长叹,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间!
但小说似乎并不该就此结束。狗眼中有人,人眼中亦有狗,这当然好;倘要更好,还要狗眼中有狗、人眼中有人。人狗互鉴当然必要,唐一惟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人和狗分别照一照镜子,可能是更高意义上的必要。其实小说已有所涉及。狗当初离开野营烧烤的一家人,完全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为了自由和远方。决定救治它的新主人彭娇,不循常人路,是为了“自由人生”。也就是说,人与狗,内心里都存着一份“为什么活着”的隐秘。只是作为人的彭娇更清醒也更清晰,并决意为此不惜一切,作为狗的“我”,却浅尝辄止,依然摆脱不了对人、对“他人”的依附。
这个依附,既是前度刘郎渴望重依旧主,也是结尾处的“不想拖累她,一旦身可由己,我就会逃离开去,继续去流浪”。最后的结果或许殊途同归,都是继续去流浪,获得自由与远方,但这个自由却是被动的,“依附”即取消自我的被动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主动的、发现自我意义上的自由。这个自由内化于心,也必会源于生命自然且必要的冲动,外化于行。彭娇意识到了,而元宝距它尚有一步之遥,一步之遥往往咫尺天涯。这也是我武断地以为《因为有你》的一个遗憾。不过我也相信,既有彭娇做了先导,唐一惟很快就能跨过这一步,下一篇小说当更好。
徐則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