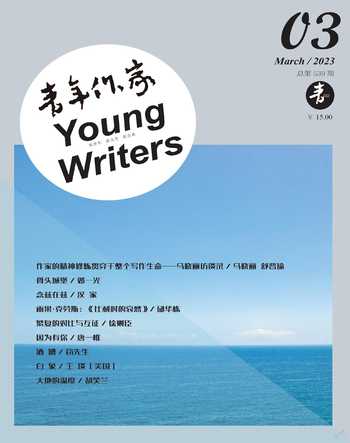非典型相爱
窃先生
直到刚才,他鼻子里都还充斥着她头发的淡香。
十二月的华北总要吹一些说不上暖也说不上寒的风。风是雨头,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总是这样说,吹一些风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于是老人说:“要下雨了。”他很不以为然,十二月的华北是不会下雨的,他要按计划出门。“要下雨了。”老人再一次说,可是他听不到了,他已经带好东西走出门去了。
已然擦黑的天伴着有些刮脸的风和窸窣的雨,显得十分阴冷。只披了一件风衣的他浑然不觉,只知道在上腹与胸口之间的位置有一团火在灼他的胃、烘他的心。他最初是背着包走的,随后被火烤得热起来,也跑了起来。背上的包在颠簸中滑下,双肩变了单肩,最后索性拎着它奔跑。他越跑越快,越快越跑,仿佛火不在他胸中,而是在身后灼烧。突然间,他不跑了,脸上挂着不受控制的表情,在原地大口地呼出哈气,模糊了打着伞的她的脸。
“冻得你都透了!”她这样说,然后拎着他如同拎自己右手里的行李箱一样上了楼,走进半个月前就订好的酒店房间。心中烧着火的不仅是他,她也一样。上午的考试中她就被火烤得喘不上气,灼得胃里痉挛,在教室里就吐了出来,吓得监考老师脸色发白。当监考老师走下来时,只看到她扭曲地笑着朝自己摆手,嘴角还挂着没擦干的液体,让监考老师险些比她先晕倒在教室。关好房间门,两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宽衣,让两团火隔着肉体紧贴在一起。
十二月华北不常见的雨渐渐停了,他和她胃尖的烈火已平息。他枕进她的头发,她贴近他的胡须,互相吮吸着对方身上的气味。
“你的头发,很香。”
“洗发水的味道罢了。”
“同样的洗发水也不会让我变香。”
“你累得说胡话了,睡吧。”
他的头埋在她的头发里,睡着了。梦里他想起了他们的初识。他初上高中时对隔壁班的她一见钟情,而暑假在旅行团中的偶遇才是两个人情感的开始。再开学的分班延续了两人的缘分,自此日渐亲密,约定考进本地的同一所高校同一个专业。之后他有些模糊了,是否还没毕业就被家长发现了呢?但总之他们被默许了,就这样走进了高考考场,带着对未来的美好幻想把试卷乱答一气,随后手牵着手、臂挽着臂地逍遥自在了。最终的结果是如他们所愿:二人成绩悬殊不过一分,却与约定差之千里。出人意料的是,他再三调剂留在了约定的学校,而她离开家乡选择了约定的专业。
他梦到了现在,梦到短暂的分别不能动摇二人的感情,紧接着是这四年八次重逢中的第一次:他枕着她的头发,她贴近他的胡须。然后她在他的睡梦中把头发悄悄抽走,只留下一封信就无影无踪。
他惊醒了,直到刚才,他鼻子里都还充斥着她头发的淡香。然而此时,他眼前只有一封带着她头发香气的信。
他拆开信,洁白的信纸上仅有一行漂亮的字迹——
我要走了,不要寻我。
他回家后就一蹶不振,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昏迷一样。没几天他就开始发烧,呼吸也越发急促,每喘一口气都紧锁眉头,痛不欲生。几天下来水米未进,却从胃里源源不断呕出物来。
十二月末的华北,年份是2019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言已经传遍网络,他家的老人忧虑地说:“是不是染上非典了?”医生对此不以为然:“您家孩子健康得很,去做心理咨询可能比来内科管用。”
“可是他症状像非典。”
“老爷子,非典早过去了。”
在床上像病人一样躺了一周之后,他忽地起来了。像平常一样,仿佛没有病过,只是相比之前,反应显得慢那么一拍。如果有人来问他身体是否好转,要等上一阵,才能看到他的脖子牵着脑袋僵硬地点头。
实际上他很清醒。这一周的高烧没有打断他的思绪,他努力地思考“我要走了”是何种意味。但他失败了,他想不出除了分手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读,或者就算她可能真的到某个地方去了,自己又怎么找到她呢?大病初愈一般坐起来之后他还在思考,专心得乃至外界刺激对他毫无作用:听得见人说话,却不知在说些什么,只是迟缓地点点头敷衍过去,随即继续探索找到她的办法。他想到去寻她,去她家寻她。半个月后他确实去了,在敲开门看到陌生的面孔才明白“我要走了”兼具两重含义。
转眼间一月已快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她的小小习惯——每个月写一封信的习惯。他期望她的信能像之前一样按时送达。很遗憾,除了十二月在枕头上发现的那一封之外,他家的信箱再也没收到过任何东西。他决定主动出击,临时买来信纸与信封,以及封信封的贴纸——她用的都是火漆,他没这个本事。在经过一天的苦思冥想后,他第一封生涩的信终于出炉。这之前他从来只收信,没有写过,对他而言,读字已然艰辛,何况书写。他不知道她在哪,于是只好寄到她的学校,期望能有一丝转机。
这是他寄出去的第六封信了。天气已经热起来,他写信时要经常擦汗,不然汗珠就把墨水晕开,让读者以为笔者动了何种真情。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读者,他按月寄出的六封信全部石沉大海。
在要去寄第七封信的时候,他家的老人终于发现了异样,逼着他老实交代了。
“怎么不用微信呢?”
“红叹号。”
“什么是红叹号?”
“就是她把我拉黑了的意思。”
“就是你不能给她发消息了?”
“是她不让我发了。”
“意思是她不理你了?”
“意思是我们拉倒了。”
“啧,你这孩子。”
“什么?”
“从来都不随和。”
他沉默了几秒,用气音说:“胳膊肘往外拐,架炮往里轰。”
小区里的快递站就在他住的樓门旁边,除了常寄快递外,每日进出的眼缘也让他和快递站老板熟识。他像往常一样麻利地填了单子付了款,老板却让他多等一会儿——正有一辆快递车朝这里驶来,上边有无数个快递等着老板入库。他被数个铁架子以及上面的快递包围着坐在仅有十平方米的昏暗小屋里。铁架已经把墙壁占满,绝无空调的席位,只有头上悬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旧式铁风扇,仿佛头上悬着一柄铡刀。老板一边扫描着包裹,一边与快递员大笑着交谈,他的鼓膜透过充满汗滴的耳道隐约听到他们聊天的内容:
“今天的快递真多啊。”
“可不是么,还有几个外国字的。”
“外国字的?这小区人真能折腾啊。”
“你看,这不就是吗?”
老板突然不笑了,因为快递员递过来的信封上面除了一堆像是地址一样的外国字,还写着他的名字。老板把这封信入库,又很快出库,然后递给了他。就算上面的字是甲骨文也没关系,她的火漆印他永远也不会认错。老板说:“我给你把快递单子打了。”他问了老板寄到信封上的这个外国地址需要多少钱。
他不在乎价格,他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如果可以,他愿意每个月都花上一些,来换她的来信。他像过去拆她的信一样,先用拆信刀轻轻地把信封的上封口整个划开,然后拿自己那把又细又长的手术剪把火漆印小心翼翼地剪下,修整多余的信纸,让纸的轮廓与火漆印的轮廓完全重合,最后拿出放在屋子最阴凉角落的铁盒,把套了塑封袋的火漆印码进去。
他把信纸抽了出来,上面带着和她头发一样淡淡的香。他开始一句一句地、一字一字地读。信的开头写:吾爱。这两个字让他放下了一半的心,如果她心意已决,一定不会这样称呼他。他又继续往下看。她先为自己的不辞而别道歉,如此真挚而诚恳,乃至光是道歉就占据了一整页的篇幅。他看了看手里已然需要用“沓”来形容的信纸,总算安心了,这是一封除了道歉还有其他内容的亲笔信。她在信里说,她考了雅思,去澳大利亚读书了,为了陪她上学,父母也卖掉了在本地的房子。他现在知道,为什么寄出去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了。她说,她知道他们要相隔甚远了,她不愿这样痛苦,也不愿他受这样的痛苦。她说,是她没有选择留在本地陪他,这样的愧疚感日夜折磨着她。她也担心着未来,她看到了诸多无法心意相通的境况,看到了太平洋两岸各自的痛苦……于是她想逃了,她想悄悄地逃,但没能忍住,还是给他留下了最后一封信:她虽然不忍,但又不由地期待着——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人仍坚持寻找着她。
信的字迹常有被晕染开的,需要他仔细辨认。他相信笔者一定动了何种真情,因为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是寒冬,那样冷的天气是不必擦汗的。后几页信纸比前几页更加皱巴巴,他更加坚信了笔者动情的说法,但紧接着又发现自己手心潮湿粘腻,污了正攥着散发着淡香的信。他在更加模糊的字迹中继续阅读着。她说,这半年时常心中不安,愧疚折磨着她。她假装一切已经过去,但胃尖总有扭曲的感觉使她干呕,这被当地人当成新冠的症状。但她知道这种感觉和十二月在华北时的感觉一样,和每个见不到他或是即将见到他的时刻一样。只不过它不来自胸口的那团火,而是内心最底处的阴冷,这种让人冷战的感觉像浪头一样轮番打在她的胃上。最终在六月澳洲一个吹着说不上暖也说不上寒的风的夜晚,她心中纠葛的感情忽地清晰了一些,于是她写了这样一封信,每落一字都使情感更加清晰。在最后一字写完之后,她想通了——她知道她爱他。
华北的白天越发短了,暑气早已散去,时常吹起的风从凉爽渐渐变成微冷。街上人的穿着由短袖变成了长袖,气温低下来了,他却仍然穿着T恤,背后洇着他用汗液画出的地图。他像夏天一样发汗、发热,惹得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看他,在诸多目光的注视下,他又走到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宾馆前。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到这里。他原本是漫无目的地走,因为他想躲开家里老人没意思的玩笑。老人说他火力壮得能睡凉炕,他说早八百年没人睡炕了,老人骂他不到二十的小毛孩子提什么八百年。他家老人和他一直是这样的,或许老人以此为乐,但他只觉得这种不甚幽默的话语让人厌烦。过去他总是在这种时候跑出门去,去她家——或者任何什么有她在的地方——待上一天,哪怕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他也觉得有意思极了。但她此时已远在南澳,有时与他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有时与他差了两个半小时。他最多只能撞大运一样地在社交网络中呼唤她,希望正赶上她不那么忙的时刻。
当他毫无目的地走到了这家宾馆前,这种机缘巧合令他觉得有趣,他把这家宾馆的招牌拍了下来,想发给她看。这实际是在没话找话,用报告一样的方式创造聊天的机会,以求和她的交流能再多哪怕几秒。在澳洲上预科的她每天焦头烂额,交不完的pre和赶不完的ddl,她再也无法像在国内时那样用与他的交流填满课余时间——她现在根本没有课余时间可言了。两个人原本稀松平常的问候变成了打卡一般的任务,并且大部分时间都由他优先完成。重获爱情的她应该正被愧疚纠缠着,和之前的愧疚并不是同一种,如果说上一次愧疚来自她对他的爱,那么这次的愧疚就应当因为他对她的爱。他所表现出的对她的关心与爱护时时让她觉得对他有所亏待。他说,这只是作为爱人应当做的。这“应当”让她更加惭愧,自己竟连最基本的都没能做到。于是隔着太平洋她给他打了一通电话,里面充满了眼泪。她说,你实在不应该养我这样一只电子宠物,每天中午十二点上线喂食,下午三点上线浇水,像每日任务一样打卡培养亲密度。他说,我不在乎。但是他的意见起不到决定作用。
这一次轮到她卧床不起了。连续的高烧让她的室友无比紧张,但超市的卷纸已被抢空,室友断定自己要和她一起死于新冠,几乎绝望。一周之后她又奇迹般地康复,精神状态仿佛前一整周都躺在床上呻吟,且水米不进,只向外呕吐的是另一个人一样。室友喜极而泣,当即回屋把遗嘱撕得粉碎。当然这些他都没有见到,是在她的电话里听说的。那通充满眼泪的电话之后,她一直拒接他的回电。这一次他倒是冷静,因为他掌握了她澳洲的电话号码,虽然见面更能解决问题,但退而求其次,只要有联系的途径就总有挽回的机会。连续一周坚持不懈地拨打,终于再一次听到了她的声音。他和她都不太能想起那天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据她的室友回忆,那天她的屋子里和卧床那几日一样沉默,偶尔传出几声抽泣,发出一声沉闷的鼻音“嗯”之后,她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走了出来。
这件事几周之后,他对着那张刚拍的宾馆照片发呆。站在街边良久后,他把照片删掉了,以免又勾起她的何种不安。于是这张照片就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消散在手机的内存卡中。
重归旧好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仍保持着通信习惯,每月一封。他们总是在信里承诺着再度相见。他们所期待的事情可以列出一张一人多高的清单,然而现实总是把他们的期望击碎,将他们从幻想的山崖上推下。
十二月的华北总要吹一些说不上暖也说不上寒的风。“要下雨了。”他家的老人这样说。他无心理会,他刚刚挂掉与她的视频电话,这是她在澳洲过的第二个生日了,而这通视频,是他们这忙碌一年里第一次重新看到对方的容貌。她已经顺利升入了大一,上着一周七天的早八课。她告别了那时的室友,收拾好东西摔门就走,转手租了单人的公寓。屋子不大,设施齐全,她本来也没有过多的要求。数不清的作业让她没什么做饭或是打扫的心情,当然也没什么打电话通视频暧昧的心情。来到澳洲已经两年,每个假期都不能回国,她因此持续地低落。她很少向他吐露这些,一如他也不会让她知道自己的那些事一样,她不希望为数不多的几通电话被她的抱怨填满。可是不提这些,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对国内的情况已然一无所知,在澳洲的生活又无法提起他的兴致。下半年的电话常常是静默,两个人都各忙各的。他总想挑起些话头,但多是她不了解的,对未来的期许也已经厌烦,谁也不愿再提。倘若在一间屋子里,他们沉默地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何不适,但在通话中沉默实在有违初衷。两个人都藏着汹涌的情感忍受着电话里静默的电流声。
那一天并没有下雨,十二月华北的天阴了一个礼拜,然后才飘一些窸窣的小雨。他终于选择拨通她的电话。他说:“我们可能就到这里了。”
她说:“你不要太难过。”
他说:“我尽量不难过。”
她说:“等我回去有机会再一起玩。”
他说:“还是先算了吧。”
这一次,他被家里的老人拖着去了医院。他又一次發烧,呼吸困难。他感到胃被人揉作一团,总是想呕吐。心口灼热又阴冷,好像之前的那团火还在烧,又好像折磨过她的心底的浪头现在打在了他的身上。他选择写信,把几年来的情感——真挚的、虚伪的、炽热的、冷漠的、坦诚的、隐瞒的、爱的、恨的……全部寄托于这一封信上。他写道:你待我很好。他写道:我并非不想与你再见。他写道:过去的感情太复杂。他写道:有朝一日我会重新面对你,但那大概很遥远。他写道:在放下之前,我们不要再联系了。他写道:再见!
他寄出了这封信,觉得浑身轻松。窸窣的雨过后,夕阳把大地映得通红。恍惚间他觉得,就算她现在站在自己面前,他也能如同普通朋友一样陪她寒暄一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