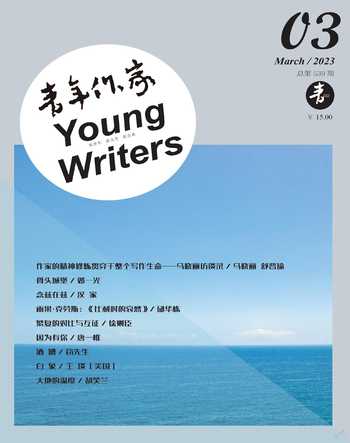酒 糟

引子
夏日的暑气稍稍散去了一些,门前的梧桐随着微风窸窸窣窣地响,摇晃的树叶挡住了九月的夕阳,斑驳的树影映在店门前写着“讲故事换花”的小黑板上。
我是个做咖啡馆生意的,店面不大,摆了吧台和两个柜子之后,刚好能摆下三张桌子。吧台后面是我的储藏柜,上面摆了各色豆子与虹吸壶之类的玩意儿,还有一两瓶拿来烤甜点的朗姆酒。甜品是不卖的,但点了咖啡的顾客可以随意地拿走一两份。另一个展柜上没什么东西,只有放在最中间的鱼缸还算是个展品。我没什么养动物的天赋,只能定期更换水里的鱼来保证这玻璃缸免于空无一物的尴尬。
虽然不会饲养动物,但养植物我是有一套的,出于爱好,店里空余的地方基本都摆上了我精心培育的花卉。某日,一位有雅兴的顾客说想买走几盆,我是不大愿意的:一来是自己辛苦栽培的东西,二来实在不好定价:便宜进的,高价卖了?我不想做那样的生意。但我是十分好奇且八卦的——要是街上有人吵架,我一定得打听清楚前因后果才走——于是我便让他讲故事,故事动听,便可以挑走一盆。其他顾客见了也纷纷效仿,时间久了,成了门店的特色。只有一位顾客,讲故事换的不是花,而是酒——那位叫于鹏的客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我种满花草的咖啡店里。
于鹏是个虎背熊腰的中年人,大约五十来岁,脸色极黑,据他所说,他曾当过十年的兵,也许是因为这样,他身上鼓起来的肌肉多少带了些疤痕。他每次来店里都会坐在展柜旁边的位子上,常看着缸里的鱼发呆。他从来不喝咖啡,一直来店里找我讨酒喝。我原本是大不情愿的——哪有来咖啡馆喝酒的道理?但他却说愿意讲故事来换,这叫我一下子就妥协了。最初我只用做甜点的朗姆酒对付他,他来得越发勤,故事也越来越有趣,于是我便依他的要求,买不同的酒给他。但讲来讲去,总是他在兵营里的那些事,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一概不与我提。有几次我趁他酒醉,试图套几句话出来,他却机敏得很,总是绕开我的话题,醉酒的那种糊涂劲,他全然没有,我也只能叹他有个好酒量。
那日我正给花草浇水,父亲踩着风铃的声音走进了店里。几天之前,父亲打开了家里存了三十年的XO想要尝尝,但可惜,他已经过了喝烈酒的年纪了,于是便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拿去小酌。我向来是不饮酒的,但在咖啡里加一些白兰地,估计能招徕不少顾客,便要了过来。父亲这次,就是来给我送酒的。
趁着店里清静,与父亲闲聊了几句,他并未久坐,正赶在吃饭的时候,再不回去的话,母亲要怪罪的。
父亲走后,于鹏开口问道:“你父亲?”
“嗯,对。”我一边回答,一边把XO放进身后的玻璃柜。
“真好,我爹从来不会和我聊天。”
“你父亲现在……”
“死了。”他说。
“喔……”
“今天的酒,还没给吧?”他提醒我。
“那你今天的故事呢?”我要根据故事决定给他什么酒。
他嘿嘿一笑:“那瓶XO,什么故事能换。”
“不换。”这一大瓶XO,是我父母结婚时别人给的赠礼。它见证了我家三十年的悲欢,我实在不想这样轻易地交出去。
“什么故事都不行?”于鹏不愿意放弃。
“唔,也不是不行。”我说。
“想听什么,我都讲!”于鹏有些急躁了。
“讲一讲你的童年吧,还有你家里的故事。”我不带一丝罪恶感地打探他家里的消息。毕竟是交易,故事换酒,合情合理。再说,见证了我家美满生活的酒,也应当用别人家真实的故事来换。
“呃……行!”他分明咬着后槽牙说的,“倒酒吧。”
见他同意了,我便给他倒了一杯朗姆酒。他疑惑地看着我,以为我要反悔。
“先讲,讲完再说,我说话算数。”我一笑。于鹏第一次来店里讲故事换的,就是这一瓶朗姆酒。既然他要讲一个全新的故事,我想,也应当用这瓶朗姆酒开头。
“好,你听着。”他说。
一
我爹一直想当红卫兵。
我并非想要强调红卫兵,那时候很多人都是红卫兵;我也不是对红卫兵有什么想法,仅仅是提那么一句。
他想当红卫兵,但是他不认字,也没上过学,人家不让他当。当然不是在这个城市,是在他老家,他老家在河北的一个村子里。你问我具体在哪里,大概是河北和山东交界的位置。这都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我妈是本地的,天津人,不是你知道的那种城市人。直辖市还有郊县呢,她就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你要是觉得我妈还是比老家那种穷村里的人要强得多的话,那我再给你打个比方,我妈就是那种,能因为地里的一根萝卜和邻居二婶吵架吵一个月的人。
要说我爹妈是怎么认识的,那真是天大的巧合。你知道老三届吧,我妈就是最早的那一批。按理說城市郊县的人应该留在本地种田就可以,偏偏他们县前一年盖了新学校,修了厂子,占了不少耕地,当地生产队收不下那么多学生了。这一下子,我妈就得到更穷更破的地方搞建设了。管分配的人让她挑,回祖籍还是去兵团,我妈要回祖籍,于是就来我爹的那个村子了。那村子,我记得是叫“于家村”。她到了之后就被分进了我爹的那个生产队。我爹那老色胚子,一眼就看上了,整天照顾着她。再怎么说我妈也是县城出来的,起码在学校里待过几天,她没事了就教我爹看看书写写字。我爹没上过学,但他是真的喜欢看书。过去他看小人书只能看个画,现在连字都能看明白了。于是他就越来越喜欢我妈,我妈又整天受着我爹照顾,两人就这么好上了。
他们俩好上谁最高兴呢?我爷爷。自己两儿子有一个搞上了“知青”,那在全村神气得很,屁股大的城市姑娘可是不多见的!其实那也不算是城市,但是那么封闭的一个村子,哪分得清市区和郊县呢。于是我爷爷就张罗着给两人操持婚礼,我三叔当时羡慕得呀,老往我妈身上瞟,为此还被我爷爷打了一顿。二十多的人,当着大伙的面让亲爹揍。这其实也是常事,村里人都习惯了,那年头都这样。
在婚礼上闹这么一出,我爹不觉得有啥,我妈不行,她可挂不住面子。那个晚上她跟我爹吵了半宿。我爷爷一看小两口头一个晚上啥也没干,又急又气,又把我三叔打了一顿。
后来“东方红一号”发射那年我出生了。本来他们俩结婚快两年没怀孩子,我爷爷还挺生气,因为这个没少骂我爹——那会儿他就不打我爹了,打不过了。我爹挨训了就跟我妈打架,一巴掌能把我妈从大门口扇到里屋去,我妈也不含糊,跳起来朝我爹肚子就踹,我爹躺下了还伸手抓她腿,站起来拽着满屋地走,我妈就捡地上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板凳也好马扎也好,抓起来就砸我爹,我爹就抓她头发,拿膝盖顶她脑门,还往墙上撞。周围的几家人听见了都过来看,但是谁都不敢管,管不了。其实我也没见过他们当时打架什么样子,但是我小时候他们就是这么打的,我估计那时候也一样。
我爷爷不是生气他们结婚快两年还没孩子吗?就他们那么打,就算有也得掉了。但是七零年我出生了,一生下来就带把,我爷爷可乐坏了,不能说乐坏了,得说乐疯了。我爺爷不骂我爹了,我爹也就不打我妈了。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又是鸡汤又是鱼汤的,我爹不吃鱼,嫌腥气,但那时候他就忍着干呕给我妈熬汤。
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妈家里发电报过来问,怎么还不回来?我妈回信儿说结婚有孩子了,就不回去了。这一下子给我妈家里急得够呛,带着人来村里要人。我爷爷领着半个村姓于的,给人家堵在村口不让进,还差点打起来。我妈当时带着我在地里干活呢,不知道,我爷爷也没告诉她。都是后来到城里投奔娘家人,家人不认她了才知道的。
所以我也是在老家出生的,小村子的孩子也没别的事,整天就是野。没事上地里偷人家棒子、萝卜,上小河沟钓鱼,往井水里尿尿。每回我偷棒子让人家看见了,抓着带回家里,我爹都得当着人家的面揍我一顿,一边揍一边骂街:“你他妈个小兔崽子,老子他娘的养你就为了让你偷棒子给我?我他妈的打不死你。”他是真的很生气很用力地在打。但是他骂街声音太大,每次都得把我爷爷招来,我爷爷就喝住他,不让他打我,然后还要骂那被我偷棒子的人:“我孙子偷你个棒子是看得起你,少他妈给脸不要脸。”我爷爷在村里辈分高,大伙也都不敢说什么。
托我爷爷的福,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没怎么挨打,但是我妈就不行了。我爹打不了我,就打我妈出气,两人就在家里打架。我小孩啊,看见打架就哭,我爷爷听见了就把我领走,领到他屋里去,给我吃糖,当时糖多贵啊,我爷爷每次都给我吃。现在想想,那糖真甜,和你给我这酒味道有点像,但你这酒比那糖差远了。
于鹏拿起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我还想再给他倒上一杯,但是瓶子已经空了。
“明天再说吧,每天这个时候你都该轰我走了。”于鹏脸微红,咧着嘴冲我说。我看看表,已经十点多了,确实该打烊了。
“你这洋甜酒,没劲。”他拿过我手里的瓶子,“38度,甜水一瓶。”他放下了瓶子,稳稳地站了起来,就像没事一样,“趁着天还有点热,明天给我整几箱啤的吧。”我答应着,目送着他出门了。
二
于鹏照例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了。他背着光进来,显得脸更加黑了。我收拾好了手头的东西,把预先买好的一整箱啤酒搬了出来。
“这个牌子的?”于鹏说。
“怎么的,他们家的啤酒招你惹你了?咖啡馆给你供酒就不错了。”我笑着用胳膊肘怼了怼他。
“没事,就是我爷爷一直说想喝这个牌子的啤酒。”他说。
老家的酒,都是自己村子用粮食酿的,外面买不着,是实实在在的高粱酒。我爷爷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告诉我外国人都是喝啤酒,比高粱酒好喝。我爷爷是个酒鬼,整天喝酒,喝得很多,他打的嗝都永远带着一股子酒味。
可能是血缘关系吧,我爹也喝酒,说得好听点那叫“豪饮”,说俗了就是喝大酒,喝酒也不就菜,就拿一个小酒盅倒着喝,干喝。一般来说喝高了人就糊涂了,或者倒哪儿睡着了。我爹不一样,他喝完酒还是很清醒,但是一喝醉了就生气,无名火。喝急了就找我妈的茬,菜太咸、汤太淡、碗摆得不正、筷子摆得太斜。总之,没有他挑不出来的毛病,我妈听烦了,就骂他:“死鬼,喝完酒就他妈撒疯。”
我觉得他就在等我妈骂他,他好有理由发泄自己的怒气。往往这个时候他就抄起空酒瓶子朝我妈头上砸。你可千万别说这是喝多了随便抄起来的,十个酒瓶子,有酒的没酒的混在一起放着,他一准拿起的是没酒的那瓶。酒就是他的命,哪怕这瓶子里有一滴酒没有倒净,他都不会拿起来。
他打我妈会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我妈不再出声音为止。我妈还手,当然还手,她这个脾气的人不会不还手,她是不会愿意吃一点亏的。但她终究是女的,打不过。打着打着她就没力气还手了,只能哭,一开始是撒泼式地哭,我爹嫌烦,就接着打她;然后是呜呜地小心翼翼地哭,我爹就继续打。一直打到我妈瘫在地上,用手捂住嘴抽搐着流眼泪,他才心满意足地继续喝酒。
过一会儿我妈就会站起来了,因为还有碗筷没有收拾,她不收拾就没人收拾了,下一顿饭就没有碗可以用,没碗用就没法开饭,开不了饭我爹就会打人。
但她站起来以后第一件事不是洗碗刷筷子,而是看向我这边。“你他妈的看什么看?”我妈往往会这么骂我,因为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常常看着,也不是我想看,老家的房子就那么大,站在房门口就能把里屋的东西看个遍。她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只好把脸扭过去。“我跟你说话你他妈看都不看我一眼?”骂完之后她就会去拿着擀面杖进来打我了。你问我爷爷怎么不来管了?老爷子整天喝大酒,把肝喝坏了,耳朵也喝坏了,整个一小瘦黑老头,谁说话也听不见,就自己一个人闷屋里喝酒。医嘱?他就没听过。
我妈打我也不总是那一套说辞,还会有别的理由,比如“叫你他妈的不好好上学”,或者“叫你他妈的不听老师话”。其实这些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就我老家那个小村子,本来就没几个人上学的。我爹当初把我送去学校,还叫周围几家邻居笑话了好几天,他们说我爹是傻子,放着能种田干活传宗接代的小子去念书。我爹很生气,他破口大骂,他说我们家的小子将来要考状元上大学的,你们懂他妈个屁,然后他还要借着这个气头用力地拍拍我,“你他妈必须给老子上大学,听见没有!”
但实际上村里的学校都不能叫学校,只是来一两个村里辈分大的人往前面一站,给我们讲他见过的事,就跟你店里的客人每天给你讲故事一样,但比不了你店里的样,那全都是荤事,你懂吧,给一群五六岁的孩子讲荤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去了不到一个礼拜,觉得他们不是好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了。每天说是出门上学,其实还是去各种地方野。
纸包不住火呀,有一天我去地里偷棒子又让人抓到了,被揪着耳朵找我爹去了。他们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女人先敲开我家的门,找我爹告状。我爹不信呀,他说:“我家那小子上学去了,以后要考状元的。”女人说:“他考个屁,你们家的小杂种上我家田里偷棒子去了。”一边骂一边叫她家男人把我拽进门。
我爹那个气呀,一把就把我抓过来,从门口拿了个酒瓶子往我身上砸。他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打我呀,一下一下地打在我的胳膊、背、腿上,他边打边问我:“你他妈不是上学去了吗?”我说:“学校上课的都不是什么好人。”他说:“你放屁!在学校教书的能不是好人?”我委屈啊,我说:“他们每天什么都不教,尽讲些荤东西!”结果你猜我爹说什么?他说:“放你妈的屁,我他妈能不知道学校教什么?你知道的比老子还多!”他一天学都没上过,最后还落个他什么都知道。我哭啊,他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信。
那两口子还在帮腔,“你跟着你儿子一起上学看看不就知道了,看看你是不是也能考个状元。”我爹气得脸通红,打得比刚才还狠。我觉得他打我不为了惩罚我,只是为了泄愤,泄早几年我爷爷护着打不到我的愤、泄自己没上过学的愤、泄被别人羞辱的愤。
那两口子起先还笑呵呵地看着我爹揍我,过了好一会儿了,看我爹还没有停的意思,他俩害怕了,“差不多得了,就一个棒子你还打死他啊?”但我爹仍然没有停下。最后你猜是怎么结束的?看到我腿上这三条疤了么?他用酒瓶子打我,有几下打空了,打在了门框上,把瓶子打碎了。瓶子碎了他都没停手,最后带齿儿的碎酒瓶子直接划在了我的腿上,划出了这三道口子,血哗哗地流。那两口子看到见血了,赶紧拉住了我爹,把我往医院送。我当时被打得都没什么意识了,都是后来拆线时候听大夫说,口子再往上偏几毫米,就是我的大动脉了。你以为我身上的疤都是在军营里落的?不是那么回事!从那时候我就发毒誓了,我一定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
于鹏的脸红红的,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醉了。一整箱啤酒,就只剩下半瓶了。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你醒醒酒再走。”我有些担心他。
“嗯。”他拿起了最后半瓶啤酒,“我刚跟你说了,我爷爷想喝这个牌子的啤酒对吧?”
“嗯。”刚刚说过的事,我怎么会忘呢。应该说,凡是客人给我讲过的故事,我都不会忘记。
那年天还冷的时候,我爷爷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说村口的小卖铺开始卖这个牌子的啤酒了。老爷子说他想喝。那时候他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眼球整个陷了下去,耳朵也听不见了,脸黑魆魆的,比黑煤球浅不了多少,人瘦得跟“芦柴棒”一样。我和他说,等他好点了就给他买,估计他也没有听见。
树刚开始冒芽,老爷子就走了,最后他也没喝着这个牌子的啤酒。我爹和我三叔給他操办后事,我爹干活干得更多,因为我三叔腿有毛病,我当时以为他是因为喝酒喝坏的。
老爷子下葬之后,我爹就和我妈商量到她娘家那边去。我爹早就想从这小村子里飞出去了,他觉得种田一辈子没有出息。但碍着我爷爷还在,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爹知道老爷子不可能同意的。在我爹看来,爷爷的话就是圣旨,哪怕他已经老得打不动人了。
“于是你们一家子就到这个城市来了?”我问道。
于鹏把最后一点啤酒一饮而尽,“对,我爷爷也走了,房子和地,都留给了我三叔,他自己种不了就租给别人,多少是点财产。我爹和我妈就直接投奔我妈娘家去了。”
“我记得你母亲娘家人不是和你家闹掰了么?”我说。
“对,给人家打走了。”于鹏把空酒瓶放到了桌上,小小的咖啡桌几乎被酒瓶占满了,“从那以后我妈再给娘家发电报都没有回信了,这次说要进城也一样。那时候郊县都被划进市区了,街道早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我妈原先住的地方。结果人家早搬走了,这闺女他们不认了。我爹一看吃住都没着落了,就骂我妈,我妈也不含糊,两人在大马路上就打起来了,就跟过去在老家打架一样。但是这回他们把警察给招来了,警察把我们带去了派出所,人家是真好心啊,了解情况以后给我们找了便宜的旅馆住着,告诉我们哪里能租房。但是打架这事,一听说是两口子,人家就没管。”他还想伸手去拿酒,却发现已经没了。
“一箱12瓶,你酒量真是了得。”滴酒不沾的我实在无法想象一整箱下肚是什么感觉。
“啤酒而已,还行。”于鹏摆摆手,“明天给我弄点白的吧,就要——我想想——二锅头吧。”说罢他站起来,缓缓地、稳稳地,好像只是小酌了几杯的样子。
“好,你也路上小心。”我仍然目送着他离开,隔着玻璃门,他冲我抬了一下手,示意我放心,随即就消失在不远的路口处。
三
天渐渐黑得早起来了,顾客也都走得越来越早了,于是到了于鹏快来的时候,店里只剩下我了。我坐在窗边的吧台发呆,瞥见于鹏走进店里的身影,我总觉得,他的脸庞比擦黑的天空颜色还要深。
见他来了,我便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瓶二锅头。于鹏在我这喝了快两个月的酒了,他的酒量我大概是知道的。一瓶不够,但我又不敢买太多,他要是喝个烂醉,在我店里撒疯,我还真没法处理。好在这种情况一次都没发生过。
“嗨。”于鹏朝我打了个招呼,然后点点头。我觉得他这头是冲着酒点的,但我并不在意。
“给你点两个酒菜?”我笑着说,一边拿出了手机准备点外卖。
“不用!我干喝就行。”于鹏笑了一下,随后露出一个神秘兮兮的表情,“你知道,我们在城里安家之后,我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答。
“喝二锅头。”他呷了一口酒。
进了城后,我们晚上在旅社住着,白天就四处去找房子。我们从老家折腾到城里,一路上路费花去了不少,租房只能租最便宜的。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套合适的,赶紧结了旅社的钱来付房租——晚结一会儿就得多收一会儿的钱。就这样算计着,最后交完第一个月的房租,余下的钱只够我们吃三天。
搬进新房的头一个晚上,我妈兴奋得满屋转,“我们终于也是城市人了。”她一直这样念叨着。我爹呢,蔫溜溜地出去了,再进门时手里多了一瓶二锅头。我妈这个气啊,刚才她有多兴奋,现在她就有多生气,她破口大骂:“你个死鬼!三天的饭钱就让你换了酒了!”我爹不搭理她,径直坐在桌旁的凳子上,开了酒瓶子,准备尝一尝城里的酒是什么味的。我妈看他完全不搭茬儿,更生气了,过去就给我爹来了一巴掌。这一巴掌给我爹打急了,他把那瓶开了盖的二锅头往桌子上一放,站起来就抓着我妈的头发往门口走,他得护好这瓶酒,打着打着把酒碰洒了可不行。他们两个就这么在屋里打起来了。那时候我都十岁了,他们打架我也不哭,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桌上的那瓶二锅头。过去在老家,我爷爷只用筷子蘸着高粱酒给我舔过,很辣,辣得我烧心,但是我没舔过城里的酒,城里的酒是不是也这样辣、也这样烧心?我好奇呀,我把头凑过去,准备舔一舔酒瓶口。这时候我爹已经把我妈打得在地上抽搐了,他停了手,准备回来尝尝城里酒的味道。他一扭头,正瞅见我伸舌头舔酒瓶口。
“好呀,你小子他妈的还想偷喝老子的酒?”他脸涨得通红,比喝醉了酒都红,他俯下身子在地上抓了抓——他想找空酒瓶子,但这是新家,酒瓶子还没有囤起来。他的目光落在了墙角的鸡毛掸子上。他一把抓起鸡毛掸子,直直地朝我冲过来,“你他妈的喝老子的酒?”鸡毛掸子重重地落在我的后背上,“好,老子让你喝,给老子喝,把这瓶酒都喝完!”我害怕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反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喝呀!”他一边吼着一边用鸡毛掸子打我,像是在打一个仇人。他打得我疼啊,我就按他说的,拿起酒瓶子往嘴里灌。酒辣啊,辣得我烧心,我喝了一口就开始咳嗽。他看我不喝了,就又打我,“老子让你喝啊!”我就只能忍着咳嗽继续往嘴里灌,咕咚咕咚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就这么让五十多度的白酒滑到嗓子里去。正喝着,他又狠狠地打我,“老子让你都喝了?”这一下重重地打在我的肚子上,我一口没咽下去,直接喷了出来,然后不住地咳嗽。“妈的,浪费老子的酒。”他从桌上拿了杯子开始倒酒,倒完一杯看了看趴在地上咳嗽的我,“去!去他妈那边咳嗽去!”他一脚把我踹开,我整个人差不多躺在了地上。这时候我妈已经站起来了,她拿了擀面棍朝我走过来,“妈的,小兔崽子学会喝酒了是吧?”她用擀面棍打着不断咳嗽的我,我爹就在旁边一口一口地喝着酒,看都不看一眼。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
钱花完了就回不来了,只能再想办法挣。第二天一大早我妈就出门找活干了,被吵醒的我爹懒散地躺在床上,嘴里还骂道:“他妈的,娘们也要出门找活儿,谁知道是不是什么正事。”虽然骂着,但他完全不起来,就在床上慵懒地躺着。到了下午我妈回来了,手里还拿着几张毛票。她在老家那么些年,只会种地,但是城里没有地给她种,她也不知道能去哪里找工作,只能漫無目的地满街晃悠。快中午的时候她走到一个胡同口,听见门口两个老太太谈论胡同里有人家要找看孩子的阿姨。她们说:“现在这样的人不好找,得满大街打听去。”我妈听了就上去问:“你们看我行吗?”两老太太一看就给领过去了。那家是两口子,女的刚生完孩子,男的是精神科的大夫,工作脱不开身。我妈把情况跟人家一说,人家将信将疑,说你先干一天试试吧。我妈就在人家家里干了一天。到了那家男人回来,她才算是下班。人家一看还不错,就商量着让我妈长久地干了,按天结钱。虽然不多,但是够我们三口吃几顿的了。
我爹就这样在屋里闲了一天,过去在老家的时候他还看看自己珍藏的小人书,但是这次行李太多,来的时候没有带着,他就这么在床上干躺着。他也不做饭,在老家的时候中午我饿了只能去找我爷爷,我爷爷就把他那发苦的炸咸鱼分给我吃。现在搬到城里了,我连那口炸咸鱼都吃不上了。我爹看见我妈高兴地攥着毛票回来,气就不打一处来,“妈的,死娘们儿去哪赚的脏钱?”我妈本来挺高兴,听了这话火气腾地就上来了,说:“死鬼,吃饭的钱叫你拿去喝酒了。现在我去人家家里给看孩子,累死累活赚回来的毛票你说是脏钱。好,有本事我买菜做的饭你别吃!”不知道我爹是不是觉得理亏,还是因为让女人赚钱养活一家子太丢人,这次他没和我妈打架,只是骂骂咧咧地回床上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妈就去人家家里上班了。我爹觉得面子上挂不住,装作睡得很熟,等我妈走了,他才坐起来,“妈的,娘们儿出去赚钱。”他这样骂着,但还是不出门找工作。到了下午我妈回来了,她比昨天还要高兴,她一进门就冲我爹喊:“死鬼!我问了人家大夫了,人家医院现在招看护,你这一身力气也往正道使一使,他们医院也不远,就在这条马路尽头……”我妈话还没说完,我爹就吼道:“那他妈是个精神病医院!你他妈的叫我去看精神病?你他妈安的什么心?”他吼着,从床那边冲过来,和我妈厮打在一起。
我妈转天是鼻青脸肿出门的。我爹还是等我妈走了才起,但那天他没骂骂咧咧,他穿好了衣服就出门了,临走扔给我几分钱,要我中午自己去外面买东西吃。到下午我妈回来了他都没有回来,我们两个吃完了饭,他才慢悠悠地进门,手里还拿着一瓶酒。“死鬼,你又拿钱去买酒了!”我妈骂道。我爹一点也不生气,“我今天买酒是庆祝的,人家医院痛痛快快地就请我去上班了。”我妈也笑起来了,“死鬼,昨天还和我打架,等着,我去给你加两个下酒菜。”我妈笑着就奔进厨房了。
我爹上了半个月的班,他们医院下来了文件,除了精神病人,也收治毒瘾患者。我爹能拿的工资更多了,工作还变成了铁饭碗,他一个人就能养活一家子了。那天我妈破天荒地炒了四个菜,还做了一锅汤,专门在我爹的那碗汤里多卧了一个市场门口便宜买的鸡蛋。我妈边做饭边念叨,等那家女人出了月子,自己就不干了,好好持家,好好伺候我爹。
我爹还是没有放弃让我考状元那个梦想。在城里的日子也基本稳定了,他开始给我找学校。他和人家小学的老师说,说我在老家的时候上过几年村里人办的学校。人家老师说你那学校我们不认,想上就得从一年级开始,和那帮六七岁的孩子一起上。我爹没有办法,他在家里本事大,到了外面都客客气气的,尤其是见了老师,他连个“不”字都不好意思说。于是我就开始和六七岁的孩子一起上一年级了。
城里的学校比老家的好得太多,不,我老家的根本就不能叫做学校。这里有课本、有真正的老师,我在这里上的才是真真正正的学校。
我比同班的人都大,理解起东西来也快,基本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我爹很高兴,但从来没有夸过我,他说这都是应该的。他常嘱咐我:“你得好好学。”我点点头。“将来考状元上大学。”我点点头。“以后有出息了孝敬我。”我没有点头。
他有一点小事就这样打我、骂我,他打我是真的往死里打,是打仇人那么打。我那时候就决定,将来我一定不打孩子,一定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从那时就开始想办法要报复他了,但那时候我小啊,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我就想,小学毕了业赶快出去工作,离开这个家。结果呢,八六年实行义务教育了,我小学毕业跑不了,还得接着上初中。我比同届的人都大啊!等到初中毕业我都已经成年了。我就又想,毕业之后不考高中,直接去当兵。只要我不上高中就考不了状元,就上不了大学,他的愿望就实现不了。
初中毕业之后我马上就去我们那里的征兵处填好了表,没等中考分出来,我的体检合格报告已经到家了。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们想拦也拦不住了。我爹看到了报告,脸涨得通红,他抓起酒瓶子想打我,但是又放下了。他坐在桌旁,一杯一杯地喝着酒。半晌,他问我:“你真想去吗?”我点点头。他又不说话了,闷闷地喝酒,又半晌,他说:“你去吧。”
等我妈知道这事之后,她差不多疯了,她骂我,“你个小兔崽子!你怎么想的你?就这么去当兵走了?”她说着跑进厨房拿起了擀面杖,“我把你腿打断你就去不了了!”她朝我扑过来,我没有躲,她现在已经打不疼我了。“你个疯娘们儿懂什么?”我爹突然抄起了空酒瓶,朝我妈打过来。我就坐在那里,看他们扭打在一起。
“然后你就去当了十年的兵?”我看着他喝光了第一瓶酒,问道。
“嗯。我以前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基本都是當兵时候听来的。”他的脸已经泛红了,“我本来想继续在兵营里待下去的。”
“那你为什么回来了?”我问。
我的班长对我很好,我是独生子,连个表兄弟都没有。但我感觉班长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他比我大一岁,家里穷,上不起学,母亲也很早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都很小,就他父亲一个人种地。他出来当兵,家里少一张嘴,每个月还能寄钱回去。
我当兵第十年,我班长的妹妹来消息,说父亲去世了,他马上收拾行李准备走了。我问他,我说你走了还回来吗?他说他不回来了,父亲走了,只有两个妹妹,家里没有个男人是不行的。我班长对我太好了,我舍不得他走,我就哭了。但是我哭有什么用呢?他的家庭需要他,我怎么可能拦得住他呢?班长临走的时候,劝我也回家去。十年了,我一次家都没回过,连信都不写,最开始的几年,我还能偶尔收到我妈的来信,我每一封都看了,但我从没回过。后来就没有再来信了,也许是我妈收不到回信,不再写了。我不愿意通信,也不愿意回去。
上车之前,我的班长跟我说:“血还是浓于水,不是吗?”说完他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原地。回去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他说得对,于是我办了退役,拿了钱回来了。
等我一到家就后悔了。进门之后,我只看到我爹像十年前一样,坐在桌子边上喝酒,他更黑更瘦了,就像当年我爷爷一样,但我连我妈的影子都没见到。我问他:“我妈呢?”他只是喝酒不说话。我以为他和我爷爷一样把耳朵喝聋了,就更大声地问了一遍:“我妈呢?”结果他还是不说话。我急了,我一把把他手里的酒杯抢过来,他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看见他头上的青筋鼓起来了,他想打我,但是他已经打不过我了。当时的我比现在还要壮得多,当时的我就是一头熊。我瞪着眼睛又问他:“我妈呢?”他低头用小蚊子一样的声音说:“不知道。”我说:“每天和你住一起的人你不知道?”我明白问他没有用,就去敲邻居家的门,邻居跟我说:“几年前来了救护车,把你妈抬走了,然后你妈就再也没回来,看救护车的图标,应该送去离这儿两条街的医院了,就是挨着养老院的那家。”
我赶紧往医院跑,到了那里我跟人家大夫说了我妈的名字,我求人家给我查查。人家说:“你妈当时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我听完就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人家医院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后来没有来信了,死人怎么写信啊?
我缓了会儿,问人家大夫死因是什么?大夫说:“突发性心梗,但她浑身都是淤青,跟着来的人——大概是她丈夫吧,说是让车撞的。抢救了两个小时没救回来,让那人去交钱的时候他就直接跑了。尸体在停尸房躺了一个礼拜都没人来领,已经处理掉了。”我一下就明白过来了,我妈是让他打死的,让他打到抽搐,躺在地上,一口气没喘上来死的。他没有告诉我,连葬礼都没有办,甚至遗体都没有领、没有火化!我妈在信里就和我说过了,他的退休金和我在兵营拿的工资差不多,但是让他买酒花得月月亏空,这个时候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他有钱买酒没钱给我妈下葬!我妈的尸体连他的一瓶酒都比不了!
到家之后我就把他的衣服全都打包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就只是看着。打包好了我把门打开,把包袱扔到外面,然后抓着他的领子——他也不反抗,就这样随着我的劲——把他拽到门外,大吼着:“滚!”然后重重地甩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倚在沙发上,开着电视喝酒。我把他没喝完的几瓶酒全都喝了,现在想想,得有四五瓶,他存不住酒,都是当天买当天喝。我那天还开着电视就睡着了,我梦见了我妈,她还是拿着那根擀面杖。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让敲门的声音吵醒。那时候电视机正播着早间新闻。我打开门,是邻居领着我爹找来了。邻居心眼好,让我爹住了一晚上。邻居劝我,说:“再怎么着这也是你爹,你不能这样啊。”我说:“我他妈管他是谁,他爱去哪去哪,死在外面才好!”说完我就把门甩上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这回是警察来了,他们说,我如果不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就要拘留我。我问他们,送去养老院算尽义务吗?他们俩互相看了看,迟疑地说算吧。我说好,然后我就给医院旁边的那家养老院打电话,让他们来把人接走。
邻居想要劝我,但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
不多一会儿,养老院的车就来了,警察跟管事的人交代了几句就走了。我和管事的说:“交的钱,全从他的养老金里扣,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推着我爹上了车,走了。
钱不从我的口袋里出,养老院也就不常联系我。
这之后我给我妈补了一场葬礼,在市郊买了块墓地。尸体没了,我就翻出几件她的旧衣服,还有那根擀面棍,一起埋了。
“那之后呢?”我问。
“料理完我妈的事之后,我去附近的小学找了个门卫的活计,还处了个对象,是他们小学里新来的老师,大学刚毕业。就因为我拦了几个要打孩子的家长,人家觉得我不错,聊了几次之后就跟我好上了。她是个正直的好女孩、好老师,我想要真诚地对待她,但我还是骗了她,我说我父母都过世了,没有其他的亲戚。”于鹏说。
之后大概过了有五年吧,养老院给我来电话了。
当时我和爱人已经商量订婚,婚礼也在准备了。养老院那边给我来了电话,说我父亲得了痴呆,我对着电话大骂,我说人没死就不要给我打电话。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的肝衰竭也很严重,现在已经送到养老院旁边的医院了,你抓紧过来照顾吧。你要是不来,我们就只能让警察介入了。”
我没有办法,只能请了假去医院全天看护。我爱人听说了,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我以为善恶有报,让他哪天在养老院里被人掐死、打死,谁能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不是有心想要骗她,她有个美满的家庭,是个孝顺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我的做法,我怕她因为这个和我决裂!我只能和她保证,事情办完一定一五一十地和她交代。
等我再见到我爹的时候,他已经黑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以为他见了我要骂我、打我,但他没有,他笑呵呵地看着我。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发自内心的笑容,于是我恶狠狠地问他:“你笑什么?”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笑呵呵的,笑呵呵地朝我叫道:“小腾子……”
这么久了,他还想和我装疯卖傻!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骂他:“我说你他妈的叫我什么?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结果你猜怎么的?他坐在那床上闷闷地哭起来了,他一边哭一边说:“小腾子……你怎么骂我……”
他没和我装疯卖傻,他是真的把我当成了那个“小腾子”!我原本想骂他,想让他在病床上体会我童年的感受,我要把他对我做过的事再对他做一遍。但是,现在我是“小腾子”了,即使我打他、骂他,他也不会知道他对他的亲儿子伤害有多深了。
“那……小腾子到底是谁呢?”我又问。
“当时的我上哪知道去。”于鹏又干了一盅酒。
他的病情恶化得很快,都是因为他常年喝大酒。才一个多礼拜,就从普通病房转到ICU了。他的痴呆也时好时坏,有时能想起来自己结过婚有个儿子,更多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农村,但他始终都管我叫“小腾子”。
在ICU里躺了两天他就开始昏迷了,我倒是不担心,早点完事也好。我全都算计好了,到时候钱交完了就让他也留在这儿,是做标本还是解剖都看医生的喜好了,我和他不一样,我不给医院留债务。
大概是昏迷的第四天吧,他一下子就醒了。我本来不知道,忽然间听见他喊我:“鹏……我们这是在哪呀……”
我实在没有想到他在这种时候认出了我,我有太多的话想说了,我想骂他、啐他,想让他知道他伤我多么的深、他自己的尸体将面临怎样的处理……我的耳边嗡嗡地响,我的脸都憋得通红。我开口对他说道:
“我们在ICU呢,爹。”
他“哦”了一声,就咽气了。
“那你最后,把你父亲的遗体接走了吗?”我看着他喝完了最后一盅酒。
“我把他扔医院了。”于鹏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
“你肯定没那么干。”我说。
“我小时候听三叔说,有一种酒是低度的清酒。”于鹏说,“我长那么大还没尝过。”
“好,明天一定给你预备上。”我目送着于鹏融进了夜色中。
四
今天下了大雨,这个时间天上本该是一片橙红,现在却是黑压压一片,太阳还没落山,于是乌云之中又渗出些血色来。我缸里的鱼死了一条,但这一天来店里躲雨的客人实在太多,还没来得及把它捞出来。
于鹏很准时地撑着伞出现了。隔着玻璃门,他的脸黑得几乎融进了天空里。他朝我点点头,收了伞坐在他的老位子上,一扭头便瞥见那条死了的鱼。
“今天刚死,还没来得及换新的。”我拿着抄網,预备去捞。
“不忙。”于鹏摆摆手,“你先给我拿酒吧。”
“你父亲的遗体,你究竟怎么办了?”我给他斟了一杯清酒。
于鹏拿着酒盅看了片刻,又放下了,说道:“带回老家了。”
我们刚在这个城市落脚的时候,我爹就和我妈说了,说他死了还是想埋回老家去。我妈就骂他,活还没活明白呢,先把死之后的事琢磨好了。我知道,我爹虽然想往城市跑,但是他放不下老家。
整个尸体的来回运输实在是麻烦,我就把他火化了。虽然老家都是土葬,但是不碍事,大棺材里放一盒骨灰,倒也挺合适。
我回村之后是我三叔来迎的我,我已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不怎么高、瘦瘦的、瘸着个腿,就是脸比原先更黑了。
我带来的只有那一盒骨灰,不怕尸体烂掉,也就不用着急操办下葬的事。三叔拿了几瓶村里酿的高粱酒,跟我在一个没有菜的方桌上用小酒杯喝了起来。
我一上来就问他“小腾子”是谁?三叔惊讶我知道这个名字,他说我爹原来在家里排行第二,小腾子是我爹和他的大哥,也是我爷爷最疼的孩子。
三叔说:“过去还不是耕田记工分的时候,咱家种出来的粮食要拉到县城去卖的。别说咱家,咱们村那时候都没有一头牛。要运粮食,就靠人力,一个小车,前面的人拉着,后面的人推,一走好几里,都这样。你爷爷每次拉粮食,都要你大爷——也就是小腾子在后面推着。虽然是喊他去干力气活,但是有个好处,回来的时候总有一块你爷爷给买的水果糖。后来,我和你爹大一点了,也闹着要去,但你爷爷从来不让,只让你大爷去。你大爷得了糖,他不吃,揣兜里带回来,等你爷爷看不着的时候,他才掏出来,放嘴里咬成两半,吐出来给我和你爹吃。
“吃饭的时候,都是你爷爷盯着你奶奶盛饭,谁吃多少,都得看你爷爷的意思。你大爷的那碗饭,总是比我们的多出一小团米饭来,除了你爷爷,就是他的饭最多。我们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谁也不敢说,说了就要挨打。咱们家自己种地的时候是这样,后来一个村合种一片地了,还是这样,多少年都没变过。
“后来到了一九六零年,村长说咱们村附近的山里有美国间谍,组织村民在山周围埋了地雷。我跟着你爹和你大爷兴冲冲地同其他小年轻一起上山抓间谍去了,去的时候还好,还都能认出在哪埋了地雷,都躲着走。下山时候有的地方陡,视野不好,你大爷一脚就踩地雷上了。那都是土制地雷啊,劲大,连全尸都没留下。倒是多亏他大我们两岁,是领队,离大部队远,没别人受伤。但是你爷爷疯了,他当着全村人的面,跪在村口地上哭,哭得撕心裂肺。
“回去之后你爷爷闷头喝了两天酒,转过天来的晚上,他把我和你爹都叫过去,手里拿了根木头棍子。他问我俩,为什么让小腾子踩上了地雷?你爹低着头不说话,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一边哭一边说,我们哪知道,我们也没想到。你爷爷脑门上的青筋一下子就起来了,他跳起来,把我按在板凳上。‘我他妈的叫你不知道!我他妈的叫你没想到!他一边骂一边打,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腿上,他在打一个谋杀了他大儿子的仇人。打到最后,他没有力气了,就把棍子一扔,盘腿坐回炕上喝酒了,‘滚吧!他这样骂我俩。那时候我已经没什么意识了,腿也没知觉了,是你爹拖着我回的里屋炕上。第二天起来我腿疼得不行,走不了路。你爷爷骂我装着玩,又打了我一顿。从那之后我的腿就瘸了,走不动路了。”
“你爷爷打人狠,跟打牲口似的。他拿的是大木棍子,都是拿做锄头用的那种。尤其喝完酒之后,脾气更大,一个眼神不对了都要打。不仅打我们,还打你奶奶,你奶奶也不敢还手,只在大半夜里偷偷哭。你奶奶叫你爷爷打得浑身都是毛病,一刮风下雨就疼得不行。刚开始吃大食堂没两年,你奶奶就走了,那是我第二次看见你爷爷哭,没第一次哭得那么凶,但那眼泪也一直往下流。
“你爹对你,真是比你爷爷对我们好多啦。你最起码还上过学、读过书,我们别说上学,连字也不认识一个啊!一出生就是在地里,将来也埋在地里。你爹还带着你和你妈进城去,真好,我做梦都没梦见过你爷爷带我进城,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城里是啥样的。我腿脚有毛病,只能靠土地流转那点钱过日子,更别提找老婆了。我有时候真羡慕你爹,有妻有儿的,死了还能有个人送终。
“当初你妈走了之后,你爹回村了一趟。他和我说,你妈得了急病,走了,医院那边钱交不上,人家不给人。你爹带回来几件你妈常戴的首饰,叫我喊人打了棺材,把首饰放进去埋了。我说埋进媳妇们的那片地里吧,你爹不让,非要和咱家人埋一块儿。也不知道你爹和你说了没有。”
喝完酒,三叔带我去看了坟。
三叔说:“现在这个坑,就是埋你爹的。他上边,是你爷爷,你奶奶不在这边,你奶奶埋进媳妇们的那片地里了。你爹旁边这个,就是你妈,你爹非要把她埋在这边,和他埋一块儿。你爹告诉我,不给你在老家留坟地。他总和我说你读过书,又去当了兵,有出息,别往老家跑,死了也留在城里,当个彻底的城市人。
“你爹另一边是你大爷,就是小腾子。将来我死了,我就埋你大爷另一边去。我和村长都说好了,我每天早上去他家坐一会儿,要是哪天我没去,就是死了,他就来帮我收尸。枕头底下有我的土地流转证明,我死了,那个证明就算他的了。”
“埋完你爹,你就回来了?”我问。
“嗯。”于鹏说,“我也没和爱人说,就直接回家了。我没想到,也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他当年经历过那样的事,但他仍然对我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我有些不知道怎样看他了,我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该记恨他,他当过可怜的儿子,但也是混蛋的爹。我就这样在家里喝了几天闷酒。我爱人不知道从谁那里知道我回来了,也可能她每天晚上都来我家看一看,看看我屋子里的灯是不是亮的。她有我家的钥匙,她进来之后看到我在桌子旁边烂醉的样子,这是我最不愿意让她看见的。她问我:“鹏,怎么了?”我不知该怎么说,只是低头攥着酒杯。她就又问我:‘鹏,怎么回事?我还是没说话。她急了,把我手里的酒杯抢了过来,问我:‘鹏!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我也急了,从地上抓起一个空酒瓶子就想朝她身上砸。瓶子快碰到她的时候我停住了,我看到她含着眼泪,一臉惊恐,看着我像看陌生人一样。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做的事情——曾经一个混蛋爹做过的事情。我把酒瓶子扔到了地上,我说我们结束吧,我悔婚了。她大哭着,走了。”
于鹏看着那个死了一条鱼的鱼缸,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爷仨就像酒缸里的三条鱼。在酒缸里出生、长大,在酒缸里娶妻、生子,最后老了、死了,就沉下去,沉到缸底,变成一块一块酒糟。就算从这个酒缸出去了,也会进到下一个酒缸,永远在里面当一条鱼,谁也逃不掉。”
于鹏说:“明天,你给我预备酒吧。故事差不多结束了。”
我答应着,送他出了门。回来之后我才看到,今天的酒,他一口都没喝。他没借着酒劲,就讲完了今天的故事。
五
今天的天气很好,店里人也不多,十分悠哉。我掐着表,等着于鹏来品尝这一瓶XO。他花了五天,用一个好故事换来了喝这瓶酒的资格。我本以为他会提前几分钟到店里来,享受他的“报酬”,但结果到天大黑了,我才看见那张熟悉的、几乎和夜色融在一起的脸。
我倒好了酒,放在了他常坐的桌子上。
“今天有些头晕,来得有些迟了。”于鹏说。
“无妨,好酒不怕等的。”我说,“昨天你没有说完,那之后呢?你爱人又来找过你吗?”
“我搬家了。”于鹏喝下了第一杯,“我把原先租的房子退了,重新找了地方住。那之后我给她发了条短信,告诉她我是骗子、混蛋。她还年轻,爱上我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我让她去找更合适的人了。学校门卫的工作我也辞了,但没再找,我平时除了买酒不怎么花钱,退伍之后每个月给的钱也够花了。仔细算算,现在的日子也过了十多年。”
“那你怎么突然找到我这里来了呢?”我又给他斟了一杯。
“最开始,我是真的想来喝咖啡的。”于鹏说,“总是喝酒,身体受不了。本来想着找点替代的东西,但是一进你的店里,就看见你柜子里的那瓶酒了。我实在忍不住,才会找你来要。”
我看他喝完了第二杯,笑道:“这酒劲大,你慢点喝。”我又给他倒上了第三杯。
于鹏把第三杯一饮而尽,示意我不要再倒了。他说:“真是好酒,有年头,够劲!真给我喝得有点上头了。”
“那你就趴在这睡上一会儿,打烊了我便喊你。”我说,“哦,对了,这瓶酒,你走的时候带上,你给我讲了那么精彩的故事,它理应是你的。”
于鹏摇摇头,说:“算了,不能再喝了,我们这辈子,都是被酒给害了。”随即他把头埋进臂弯里,睡着了。
我明白,他说的“我们”是谁。
……
店里已经收拾好,我轻拍了于鹏两下,但他却没有回应。
我稍稍用力地拍了拍他,他仍然没有动静。
我轻推了一下他的头,头径直地歪了过去。
我用手探探他的鼻息,发现他已经没气了。
结局
警车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救护车拉走了于鹏,而我则被带到了警察局。
“你和死者,什么关系?”警察问我。
“我是老板,他是顾客,就这样。”我答。
“什么时候认识的?”警察又问。
“大约两个月前吧,他第一次来我的店里,那个时候认识的。”我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矛盾?”
“他又不喝霸王酒,我们能有什么矛盾?”
“那你跟我们来吧。”警察把我带到了医院。
“你有没有主动喊他喝酒?”医生问我,警察坐在旁边听着。
“没有。”我说,“都是他提出要喝,我去给他买,就是这样。”
“你真的一次都没有劝他喝过酒?”医生又问。
“没有。”我说,“我不喝酒,只是看他喝。我的店里也有监控,都可以证明。”
医生叹了口气说:“这个人,两个月以前刚从我们医院跑出去。
“大约两个半月之前,我们醫院的救护车拉来一个病人,就是这个于鹏。来的时候已经口吐白沫、神志不清了,叫救护车的是一个安装空调的工人。据他说,他当时正在给客户装外机,从户外平台往下降的时候,他经常透过窗玻璃往别人家里看几眼。他说他也没有恶意,就是好奇。平台降到于鹏他们家的时候,这工人看见他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抽搐,身边还有一堆酒瓶子。他吓得叫工友赶紧给医院打电话,倒也多亏了这个工人,不然于鹏的命早就没了。
“这个于鹏,常年酗酒,据他说,他这样每天喝到烂醉如泥的日子已经有十多年了。你看他的脸,黑成这样,就因为他的肝功能严重受损。上次口吐白沫就是因为酒精中毒,好在是抢救回来了。本来应该住院观察两个月的,结果他住了不到半个月就跑了,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我算了算时间,刚好和他第一次来我店里的日子对上。
医生说:“本来他不应该再碰酒的,但是他跑了,跑去你那里又喝了两个月的酒。这次是因为大量摄入酒精,诱发了脑溢血。好好的一条命,就因为喝酒。你说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的?喝酒之后情绪也很不稳定,经常会做出暴力的行为。唉!一个个泡在酒缸里的人啊!早晚都要像这样,变成缸里的一块酒糟!不过你既然并不知情,也没有劝过他喝酒,那他的死和你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走了。”
夜已经深了,我从医院里走出来,看到头顶掠过一只鸟。
有条鱼跳出了酒缸,变成小鸟,飞走了。我想。
【作者简介】窃先生,原名高云天,2000年生于天津市,现就读于牡丹江师范学院2019级汉语言专业,“乃寅写作班”2019级学生,热爱文学;《酒糟》《非典型相爱》为作者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