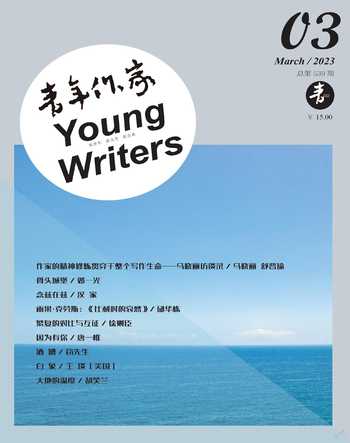龙泉驿纪行
一、去成都
9月27日,得知华语青年作家奖将于10月9日颁奖。我为获奖感言写了如下一段话:
这是一次一再推迟的聚首,也是一次执着到倔强的颁奖;这是一次特别而难忘的经历,因此也是一次特别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有幸加入华语青年作家奖这个久负盛名、朝气蓬勃的奖项行列;更因为,它促使我们更强烈感受到我们时代某种内在的气流,也让我们思考在不确定性空前加剧的时代,该如何寻找确定性;在一个一面内卷、一面躺平的时代,该如何葆有“青年性”;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该如何寻找总体性。波兰诗人札加耶夫斯基说:尝试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生命无往而不在残缺中,我们孤独、寒冷、悲伤、茫然甚至可能绝望。可是尝试赞美,不是遗忘苦难;尝试建立我们对世界的肯定性,不是忘记世界的残缺,而是尝试在种种“不能”之中,倔强地坚持“可能”,就像这次可能搁置的聚首。这也是我所理解的青年和文学的精神。
10月9日颁奖,我大概说了几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话。那天晚上,罗伟章老师穿过大半个成都来到龙泉驿跟我们相聚。老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我们并非要寻找确定性,或许不确定性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有勇气拥抱不确定性。
座上人声嘈杂,可这句话我却琢磨上了。可不就是这样?何来绝对的确定性呢?百分之百、万无一失、应X尽X……有时候把我们推入绝境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对绝对确定性的无尽追求。
二、认领
10月10日早餐时,和杨潇、张杰、王棘聊了一会儿非虚构。我想起王安忆一篇文章《为何虚构与如何虚构》,关于非虚构,王安忆说:
非虚构的东西,它有一种现成性,它已经发生了,人们基本是顺从它的安排,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它、承认它,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于是,它便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也无法产生后天的意义。
王安忆对虚构认识很深,对非虚构却似有误解。她以为非虚构有种现成性,人们拿它没办法,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恐怕不是这样的。现成与创造不是非虚构与虚构的区别,而是坏作品与好作品的区别。虚构作品中,岂不是也有大量因袭旧制,直接认领而了无创造的作品;好的非虚构,又岂有那么便宜的认领?不管虚构与非虚构,在作家与好作品之间,永远都隔着千山万水、沟壑纵横。没有勇气、耐性和创造力,很多东西“现成”地待在历史中,可是它不属于你。这是我理解的杨潇的工作。
没有任何艺术是现成的,可以像上班打卡、饭堂打饭那样“认领”,生命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然都有某种现成性。它具有一种蛮力,要求我们服从,按照其逻辑行事。这种生命的现成性,也可以称为生命的规定性。但生命自由的达成,恰恰是来自对规定性的超越而非认领。它给你一条阳光道,可是你坚持走向你的独木桥。这就是生命的自觉。这是对现成性、规定性的抵抗。所以,艺术生命的真谛就是“不认领”现实交给我们的方程式。可是,难道就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认领”的吗?当然有,我们唯一应该认领的就是存在交给我们的天命。可是,天命何在?我们只能一直凝神去倾听啊!
三、“永生的喜悦”
10月10日上午,和杨潇、张杰、王棘绕着东安湖公园走了一圈,湖光塔影,花自开放,游人不多。想起张杰昨天说到的“时间的飞地”,心有戚戚焉。又想起了杜甫草堂。这里像新造的湿地公园,跟杜甫草堂自然是大异其趣。这次时间是太赶了,不然我还想去杜甫草堂。2018年7月23日下午,我在杜甫草堂逛了一下午。杜甫草堂里各种花木令人印象深刻,银杏、香樟、桢楠、刺楸、柏树等古树随处可见,兰花、桂花、茶花,果然花重锦官城。我最流连的却是藏经楼内那一对千年银杏。这对银杏入选成都十大古树,这十大之中,有八株都是银杏。惜乎我来得太早,银杏翠绿,7月不是银杏的黄金时刻。
很多人爱成都,各有各理由。成都有多个侧面供人爱,我爱成都有个特殊的侧面,是银杏。成都有杜甫草堂,也有几千棵古银杏树。诗圣远去,留下杜诗和杜甫草堂。很多年长或与杜甫同龄的银杏树也一直在。1983年,成都人将银杏选为市树。我不知道是何因由,是爱银杏的绚烂,还是爱其药用,抑或是引银杏的高古和在蜀地的大量留存?“2001年成都市园林局摸底调查发现,锦江、青阳、武侯、成华、龙泉驿、新津、崇州等区(市)县现存银杏古树2042株。”(蒋蓝《蜀地银杏轶事》)
银杏与成都与杜甫,有一种内在一致性。
我常觉得,木棉是上天送给南方的礼物,上天作为礼物送给中原和北方的植物则是银杏。作为一个南方人,我曾在北京生活过三年,深秋时节,突然发觉上天可能是偏爱北方的。北方的秋天,天空藏着一个五彩的锦盒,而银杏是其中最炫目的锦缎。那些在春夏平平无奇的行道树,到了深秋突然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将金黄的泼墨染满天空。又像是一个平凡的歌手,在秋天突然唱出音色辉煌的咏叹调。你很难不被秋天的银杏迷住。那无数的小鸭掌、小团扇在空中摇曳。正如臧棣的诗句“金黄的树叶酝酿着/永生的喜悦”,是的,当我们望向秋天的银杏时,我们被一种“永生的喜悦”所俘获。因为秋天的银杏,天空变成一个晃动的幸福陷阱,让人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銀杏树挺拔,银杏叶飘逸,银杏的喜悦是灵魂而非肉身的喜悦:
一株金黄的大树里已有天堂——
它的影子像日记。银杏的绿玻璃球
滚动在灵魂的棋盘上。
——《银杏丛书》
我是在感受到银杏的绚烂和清逸之后,才知道银杏的坚韧和隐忍的。
作为树,银杏早在恐龙时代便已存在。在过去两亿年里,银杏一直倔强地保持着原有的面貌。也就是说,恐龙们看见的银杏和我们看到的银杏是同一种银杏。美国植物学家彼特·克兰《银杏:被时间遗忘的树种》就是一部银杏史。银杏的生存策略是不争:
化石证据表明,在近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这一类植物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在接下来的几千万年时间里,银杏遍布整个劳亚古陆(包括今天的亚洲大部、欧洲和北美洲,当时它们还没有分离,而是拼合在一起形成一块巨大的大陆)。然而,这却是一段艰辛的移民史。银杏偏好生长于溪边,在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就生长不好。可是溪边却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许多蕨类和苏铁也喜欢生长在这里。为了避免和它们竞争,银杏采取了一套忍气吞声的策略:一是生长缓慢,每年只获取少量的养分就够了,决不贪多,其他的养分就任由别的植物吸收好了;二是在长到超过别的植物的高度之前绝不分枝,就只有一根精瘦的主茎;直到树梢见到了充足的阳光,才从容长出侧枝,逐渐变成一棵丰满的大树。当然啰,也只有在熬出头之后,才能考虑谈婚论嫁——也就是开花结果。
可是这一套对付蕨类和苏铁还比较管用,对付白垩纪新兴的被子植物就不管用了——因为被子植物争夺资源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当被子植物兴起之后,银杏就不可避免走上了衰败之路。到500万年前的上新世,银杏已经在北半球大部分地方绝迹,只在中国还有分布。上新世之后,紧接着就是著名的“第四纪冰期”,很多不耐寒的古老植物都在这场大灾难中绝种,银杏的分布地也进一步萎缩。再后来,银杏的天然分布更只局限于浙江省的天目山,可能还有西南地区的几个狭小地方。这真是一场悲剧。(刘夙《银杏悲喜剧》)
两千多年前,当银杏已经濒于消亡的時候,中国人发现了银杏的价值,将这一树种保护下来。通常,人们认为这里的“价值”是指医用价值,但我相信两千多年前那个“发现”银杏者,一定在某个秋天下午长时间与银杏对视过,并被一种不可救药的“永生的喜悦”所击中。
银杏就是如此完美化合了沧桑与绚烂的两面。银杏生长极缓,一般二十年才结果,四十年才大量结果,所谓“公种而孙得食”。可是这种如此隐忍的树,却并非一味蜷缩的,它身上那种华丽而幽微的生命感性,是枫叶这类秋冬大鸣大放的植物所无法比拟的。秋冬季节的枫叶层林尽染,固然可观,但远观胜于细看。
四、老杜
如果要在中国诗人中找一个最具银杏气质的,我想到的只能是老杜,沧桑而绚烂,遒劲而天真。银杏与老杜,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相通。我爱老杜,因为他的诗里有风和日丽,有山河破碎,有生命辗转,有思念绵绵,有欣喜若狂,有家国历史,也有从寸心到天地的自然转变。杜甫的诗里有那么明媚的色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太好看的春天了,可是这明媚里有愁肠——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这是因历史断裂、山河破碎而长久流浪者特殊的看春之眼。跟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便不一样。白居易纯是忆江南之美景如画,老杜却是带着百转千回的心与春相遇。故而,叶嘉莹由老杜此诗而想到的是李商隐的《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只是李商隐哀婉的流浪苦完全压过了风和日丽的春景。在杜甫,却完全是乐景写愁情。他并不完全被这流浪打倒,在埋怨人生。他还挺着瘦弱的腰,也看着这美丽的景。
老杜的愁肠,也有铺天盖地的时候,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实在是太悲苦了,但更多时候,儒者老杜是要把这些苦藏起来的。他对世事沧桑、历史变幻、人生辗转的感慨常常是引而不发的。小时候读“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以为不过是他乡遇故知,现在才突然嗅到了那种悲苦的气息。你想想,安史之乱前,长安城里,在不同的场合里邂逅琴师李龟年,谈不上是好朋友,那时的琴声好,全是快乐诗酒的氛围。现在呢?江南好风景啊,又遇见李龟年,或许还是那琴声,可是时空都变了,这曲声依旧,世界和人都面目全非。好个杜甫,他才不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曲声依旧笑春风”呢,那不是杜甫,他的愁苦常常就安放在好风景之中。
我常用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来说明诗歌显见的光影声色和沉潜的时空延伸。杜甫的了得在于他在一个窗框中,通过雪和船将时间和空间并置起来,使得诗歌显见的画面背后深藏了千年万里的巨大张力。
杜甫真是一个好诗人!诗里有情感、有想象、有风和日丽,更有藏不住的愁肠百结和江山历史的沧桑面影。以诗称史,杜甫命途多舛却胸怀苍生!有意思的是,杜甫虽是古典诗圣,却也备受现代诗人推崇。因为他不但人格伟大,诗也伟大!他能够在“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的诗句中把无限绵延的时空隐于人间的光影声色之后。可浅读,可深思。浅读则观风景秀丽,心地朗润,深思则见冥思悠远,沉郁顿挫。杜诗通往普通人生的艰辛和坚持,也通向山河岁月的沟壑纵横、破碎千里。千年之下再读,每每只觉,你依然在面对一个如此真实朴素而又灿烂天真的沧桑老人。
诗人西川说,因为有杜甫草堂,成都这座城市便有了灵魂。或许,杜甫草堂使成都的城市灵魂有了更浓重的诗意;同样,因为有了银杏,成都的城市灵魂更添了韧性和绚烂。1983年,成都便将银杏选为市树是有眼光的。如果再迟了,恐要被其他城市抢去。可是,论匹配度,还是有杜甫草堂的成都与银杏最配。
现在想来,我后悔了!我该在成都多待两天的,或者去龙泉驿石经寺看看那两棵古银杏树也好呀。
【作者简介】陈培浩,青年批评家、文学博士,1980年生,广东潮州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著有《歌谣与中国新诗》《互文与魔镜》《正典的窄门》等;现居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