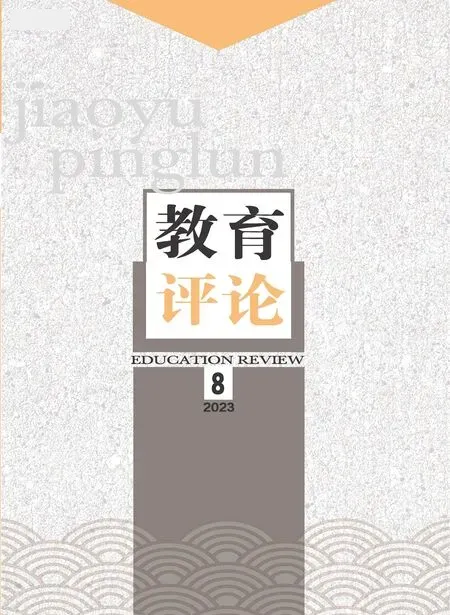以乡村书院为载体的“4+1”泥土课程理论框架及实践探索
蒋福超
乡村振兴最终要依靠乡村人才的振兴。乡村教育的振兴最终会为人的现代化注入时代力量。这样,乡村孩子就能享受到国际先进教育,让学习从脚下的泥土出发,让万物启蒙,让文明复兴。本文从当下乡土课程的困境出发,认为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以下简称PBL)在乡村学校更具有开展的便利性和必要性,它吻合乡村教育哲学的理念,连接了乡村与社区的关系、学科与经验的关系。它从课程入手,发展实验性认知思维,能真正实现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进而通过教育振兴,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一、缘起:乡土课程的困境
可以说,当下乡村学校已经具备乡土课程开发意识,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下,课程开发也初见成效,建成了各具特色的乡土课程资源库,甚至开发出相应的校本教材,以课程的方式进入学校课程设置。
这些行动在保存村庄记忆、传承乡土精神等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乡土课程开发仍有巨大欠缺的现实情况下,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学校,在乡土课程开发与使用中走入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课程内容组织学科化。在乡村课程开发水平较高的学校,乡土课程的内容组织往往以学科的方式呈现,或有详尽的教材,或进入课程方案予以呈现。学科化的乡土课程往往成为“面子工程”,让乡土课程丧失应有的教育功能。乡土课程成为静止、客观的“被观察者”,学生与乡土的联系限于课堂和教材,陷入了传统应试教育的泥沼。
二是教学方式表层化。囿于以上现实,教学中,教师把乡土文化作为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了解”“知道”了一些零碎的乡土知识,但这种教学可能不仅达不到预想效果,还可能因为额外增加了许多记忆负担而让孩子远离乡土课程。
三是没有透彻理解乡土课程开发的教育理念。乡土课程开发的目的指向哪里?价值到底如何?这是乡土课程开发的出发点。但是,乡村学校往往认为乡土课程开发是以保存乡村文化,让学生了解村庄、爱上农村为旨归,其价值也因此指向发展学生品德、振兴乡村文化。其目的和价值观是理想化、表面化的。如果教师不能让学生将身边的乡村生活经验转化为成长的素材和资源,乡土课程就可能仅仅是愿景而已。
那么,该如何组织乡土资源,让学生的学习建基于生活经验,真正将学校和乡村社会链接起来?我们尝试从PBL与乡村、乡村教育的契合性入手,探索、发展出一套能实现乡村学生、乡土资源、学校课程三者之间协同发展的课程框架。
二、PBL与乡村教育的契合性
(一)链接村庄与学校的无边界学习
真实性是PBL的核心灵魂之一,即要面向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在PBL中,“项目的立意要真实。所谓真实,指能有助于学生从学科学习和社群生活两个层面,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对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有意义的”[1]这种主体在场的教育经验,才是教育经验的核心。正如派纳所说:与屏幕上模拟的经验不同,现实世界的具象性经验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正是这样来自实际生活的教育性经验,才能使我们一直保持清醒的意识,即“全面觉醒”。[2]
在真实世界中,概念性理解才成为可能,其衍生的复杂交往、面对不确定性的人格养成也有了实现的场景。项目的真实性也有益于提升学生社会参与中的公民意识,特别是当项目的“产品”面向真实的受众发布时。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即学生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真实情景中学习时,学习效果最好。[3]
PBL的真实性要求学习走向无边界,即打破学校学习的场域,走向社区,走向服务学习的新模式。这种“学习在社区”的做法还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正如美国生态主义乡土教育哲学家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所认为的,这也是实现一个人完整人性的关键所在。人只能在其周围的土地和社区中实现他们的人性。
当个体进行人格建构时,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生态性的,这种人格建构并不是在孤立的情况下发生,而是为社区生活所调节。源于此,才出现“自我”的概念。贝瑞认为,人不是被社会建构的,而是和个人生存的地理空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一个人的完整人性取决于他与他居住的土地的深度联系。贝瑞说,“正如我们和我们的土地是彼此的一部分,所有在这里作为邻居生活的人、植物和动物都是彼此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单独繁荣”[4]。
PBL在农村具有更便利的实施条件。乡村学校与社区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关系,乡村学校的教师许多来自于学校所在地村庄或者周边村庄,这为乡村学校与村庄中的人与事发生关联提供了各种便利性。PBL真正解决了农村学校和农村社区的关系,有专长的村庄成员或家长可以参与项目,学生也能在项目中置身于成人的生活环境,发展社会情感能力和专家思维。
这样的学习,就是“无边界”学习。课程与生活、学校和社会、教师和学生等二元结构被解构,乡村孩子的学习在PBL的催化下变得更加“在地化”且“国际化”,乡村发展也变劣势为后发优势,在乡村PBL这一课程与教学国际趋势下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二)链接学习与乡村生活经验的协同思维学习
教育3.0时代,他人即教师、学习在窗外、世界是教材。乡村PBL契合这一精神,将学校学习与农村生活紧密结合。下文,笔者将阐述两者结合的机制问题,即在这结合过程中,学习是如何通过协同思维而发生的。
传统学习是线性、累积式的,先小步子,逐渐积累,认为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理解性智慧,这是对学习的一种误解,认为我们的学习都是一种归纳的方式。在认知哲学史上,这属于唯理论的思维,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能力加工、合成经验,将其变为理性认识。布鲁姆的学习目标论就是这一哲学范式的表现,认为学习是通过低阶(识记、理解、应用)到高阶(分析、综合、评价)、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与人的理性能力由简单的记忆向高级的创造发展的阶梯式路径一一吻合。
项目化学习翻转了布鲁姆的目标分类学,用高阶的学习包裹低阶的学习,不是自低到高逐步学习具体的内容,而是翻转这个过程。[5]它从创造性认知要求的顶端开始,让学生在驱动性问题产生的强大内动力中创造一个真实的产品,进而产生理解。
这种以理解为指向的高阶学习,打破了旧有以知识累计为指向的低层次学习模式,这是通过PBL中“产品”的不断迭代来实现的,这当然为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理解教学的集大成者格兰特·威金斯(Grant Wiggins)说:获得理解的最好方式是揭示式学习,即需要教师设置情景,引发困境,引发儿童的认知冲突,并在尝试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初步形成对这个问题“朦朦胧胧”“似懂非懂”“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默会知识”,并在恰当时机抛出“概念”,引发学生学会用语言、文字、概念表达出来。[6]
因此,设计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得出推论。理解,要求学生模仿实践者产生新理解时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模仿他们的思考、提问、检验、质疑、批评和验证。不能仅凭信任就去接受“理解”,而是要求“探究和实证”。PBL与乡村生活经验的协同,就是在学科化的“假设”与生活化的“验证”之间来回进行“杜威式的穿梭”,理论(知识)具有了存在主义意蕴,理论不再是“镜式”地关照现实而是去创造。学习即存在,项目即创造,知识即观念。这样,在经历整个人类文明历程的过程中,学习让每个生物个体获得了存在于世的自我解释。
这一理念,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当下课程改革奉行的学习理论即是如此:学习应该基于自己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赋予经验以意义。如何建构自己的知识,如何赋予经验以意义,我们曾经误入歧途,将建构主义学习误以为简单的“放手”“小组学习”“动手操作”等。
活动成为学习的“佐料”“餐前甜食”,或者高级一点,将活动变为“学科拼盘”。学生对零碎知识的浅层次学习,不只让学生感觉到得不偿失,也让教育者丧失了对变革的信心,我们如此“折腾”学生,最终还是要回归读写背的应试教育,这种对教育变革的习得性无力感,也深深伤害了教师的教育热情。要进行乡村PBL的变革,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一点。
(三)认知学徒式、利他的合作关系
从根本上说,乡村教育的目的应该指向创建民主、文明的现代农村社区,在这里,年轻一代和上一代、老一代相遇,人们在社群中负责地生活,塑造了个性,也影响了集体。这种生态主义乡村教育哲学将社区视为人自我形成的根基,视为彻底改变学习方式的核心支柱,视为民主社会形成的底层逻辑。PBL与这种乡村教育哲学的根本契合之处正在于此,即人的关系的现代化。
1.现代学徒式的学习关系
高质量的项目化学习不是一种点缀,也不仅是学科拼盘或者学科实践活动,而是让学生通过真实而有意义的问题探讨,用类似于真实的成年专家(如科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像认知学徒一样,参与到学习过程中。
这种认知学徒不只体现在作为非专家的学生与专家之间,也体现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所有关系的发生都指向具体事务(“产品”),学习不是为了听从教诲或应用知识。听从教诲让人学会服从,应用知识让人被知识奴化。传统教学是学科知识本位,而PBL则是面向真实世界、创造本位,两者结合,才可以实现知识学习的理性化和问题解决的创造性的双重效果。或者说,在知识学习上进行深度学习,在认识世界上解决真实问题、参与社会。
某种程度上,杜威只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理性化的问题,而在第二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不彻底。这是杜威对学校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决定的:杜威认为学校即微型的社会,是社会的“裁剪版”,这是学校中心的教育观。杜威在批判教育与社会脱节时,又将社会扭曲成一个变形、剪切过的社会,学生学习效率提高了,却回避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回避了一个韦伯提出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困境。
在价值多元、诸神纷争的人世间,人类不可能仅仅通过理性的增强就可以达成和谐共生。面对复杂、真实、甚至不可解决的社会问题时,以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为第三种理性发展的教育目标,就显得更加可信、可行。在这种交往理性下,学习即交往、学习即为了交往,PBL的学习观恰恰契合这一精神。从这个角度讲,乡村PBL就是塑造现代化的人际关系,塑造现代乡村社会。
2.利他的个人发展与人际关系
PBL让我们从改造世界转为创造世界。我们改造世界就是改造他人,是控制甚至极权倾向;而创造世界,则是创造一个共享、利他、服务型的社会。利他、利万物,这才是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中国的义利观,应该重新得到重视和解读。
综上,PBL触发了学习的真正内驱力。内驱力是兴趣、成就、利他三者的交叉处。PBL就是产生内驱力的学习。产品来自兴趣、带来成就感,并有利于他人、社会和世界。
假如中国的教育变革具有世界影响,很大可能是在农村,原因是农村更加宽松的教育环境、与自然的天然关系、课程变革的国际趋势与农村现实的契合等,各种因素得天独厚。特别是相较于城市来说,保留更加完整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更是为PBL在乡村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三、泥土课程:乡村学校PBL课程实验及“4+1”课程框架
(一)乡村PBL实践经验
项目式学习的开端可以上溯到百年前克伯屈提出的“设计教学法”。他系统阐述这个方法,是通过1918年9月发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设计教学法》一文。他说,在批评班级授课制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时,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把教育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更彻底地统一起来,开始构想某个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概念。这个概念必须强调行动因素,特别是全心全意、充满活力、有目的的活动。[7]
设计教学法在“五四”运动时期进入中国,杜威这一时期的访华也为设计教学法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俞子夷、沈百英、顾西林等教育家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江苏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浙江省立杭州师范附属小学等学校开展了学校实验。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定号召全国小学推广实行项目设计法,从此,设计教学法的发展达到了兴盛阶段。
幼教界推广设计教学法始于陈鹤琴1923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展的设计教学法实验,随后幼教界也陆续开始推行设计教学法,并在1927年克伯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下访华时达到了顶峰。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设计教学法自身带有的理论问题,设计教学法走向式微,并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逐渐消失在理论和实践界。
我们以彼时开展PBL的两大模式分析PBL在彼时的问题、缺陷。第一种模式是主题式的综合课程模式,将多学科围绕同一主题进行教学。有学校反对学科中心的课程,认为那割裂了本来“整个”的儿童生活。他们设置乡土课程为中心,唱歌、游戏、手工等其他学科都以乡土课程中的中心问题展开探索。如,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秋末的农人生活”单元,围绕“乡土”这个主题,语文课做农舍的研究报告,美术课进行农舍、收获的写生,手工课进行农具、农舍的仿制,音乐课学习割稻歌、表演割稻歌、耕田游戏等,书法课书写“农人真辛苦”等,并进行调查、欣赏、参观、研究(稻)等活动。[8]再如,研究“猪的生活”,阅读课上学生读“三只小猪的故事”,作文课学生就写“小猪的快乐”,算术课就计算“猪肉的卖价”,美术课上学生就画“老猪和小猪”,手工课就做泥猪和用篾做猪圈,唱歌就唱“小猪挣食”。[9]
第二种模式是将课程按照模块进行划分,如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在初次实验失败后,把课程分为故事、观察、手工、游戏、体育等“系”,并把算术的学习寓于游戏之中。也有学校把语言、文字、故事合成一系,地理、历史、公民、社会常识合为一系,算术、卫生、自然、园艺合为一系,体育、音乐合为一系,劳动、美术合为一系,等等;在后来由设计教学法延伸出来的“协动教学法”中,又将课程分为“处世、愤悱、康乐、藏修”四类活动。[10]
综合以上百年前PBL兴起后的中国实践,不难发现,当时的课程变革其本质是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之争。第一种模式可以说是综合课程中的关联课程模式,保留原来的学科独立性,寻找学科之间的共同主题;第二种模式可以说是综合课程中的广域课程,它由合并多门相邻的学科内容而成。这种忽视学科课程,侧重综合课程的做法,受到不少批判。“非有其他方法的补充,则学习太散漫,太凌乱;它的效能太限于目前应用,从小商店、小银行的活动所得的数目知识,决不能供给儿童所需的算学;从戏剧表演所得的历史事实,决不能代替系统的历史研究。直接应用或工具的学习,只能得到知识的一麟一爪,没有整个圆满的眼光,根本原则的把住。”[11]
其实,这一批评还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症结。百年前,设计教学法的本质问题在于陷入活动的陷阱,缺少学科的维度,将学科知识和学生生活经验对立起来。这种学习观早就受到杜威的批评,因为杜威强调的“做”绝非简单的活动,而是强调反省思维在“做”中的培养,通过“假设”在“做”中的不断升级,实现协同思维。
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它缺少真实任务的思维挑战,不能围绕核心知识与能力展开严谨的学习设计,并以产生一“产品”(即思维的物化)为最终的结果,最终难以发生基于专家式思考的深度学习。
(二)以乡村书院为载体的“4+1”泥土课程框架
如上所述,当下的PBL必须摆脱百年前囿于课程组织形式的变革模式,特别是要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以及对学习本质的要求。
当下时代是“雾卡时代”,学习的本质由“解释、应用”过渡为“学习即创造”“在创造中学习”。在21世纪核心素养导向下,国际所倡导的主流PBL强调做事中发展专家思维,阐述跨情景地、可迁移的深度理解。
PBL研究学者夏雪梅教授在反思设计教学法的百年变迁后,提出让PBL“涅槃重生”的方法——进行严谨的学习设计,通过驱动性问题,将课程标准中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作为探究问题的工具使用,并将课程标准作为学习结果评价的重要依据。[12]
在这一背景下,乡村PBL的开展尤其要具有现代精神和国际精神。反之,将乡村学习框定在前现代社会和乡土视野的做法,是对乡村教育极大的误解甚至坑害。我们要通过乡村PBL,培养具有本土精神、国际视野的现代人。
本着以上精神,力图避免百年前乡村PBL实施的误区,笔者带领的学术团队在实施乡村PBL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务必使学习基于真实世界的真实任务展开,并以“产品”为最终的学习成果。产品可以是研究报告、书信、海报、戏剧表演、相册、模型、流程图等各种形式,以思维的物化产品激发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当然,产品形成的思维过程也是评价的指标,而非单单是产品最终的结果才是PBL评价的核心。
二是避免基于核心知识与核心能力展开的探究学习陷入浅层次、娱乐化的浅学习、假学习。这就要求PBL的学习要产生概念性理解,提升元认知水平,在学习中注重复杂性交往能力的培养,大单元备课、逆向设计、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思维的可视化工具等教育理念、模型和工具都需要充分加入到PBL中来。
三是在课程设置上,避免陷入对立的二元思维,坚持学科课程的PBL化和PBL式的综合课程两种课程形式相结合的原则。以一周课程设置为例,学科课程为4天的课时量,综合课程为1天课时量,实施“4+1”的课程结构,但必须强调的是,不论是“4”还是“1”,都要具有PBL精神,在学科课程上,要从孩子的乡村生活经验出发,将生活经验与学科概念相勾连,进行协同思维,并在能开展PBL学习的学科和课时中,充分发挥PBL的作用。当然,决不能陷入僵化、死板、教条的执行,让所有学科、课时都使用PBL,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另一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
在综合课程中,避免学科拼盘式的PBL,真正挖掘乡村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如未来乡村设计、我的家乡模样项目墙、解决乡村污染的宣传品、家乡农产品的营销方案等),形成“超学科乡村主题”的探究循环,要注意PBL探究的长期性、完整性。
一个驱动问题的解决,一个PBL产品,一般持续至少4周时间,一个学期能有2-5个产品为宜,一个完整的探究过程需要经历“疑难情境——定义问题——提出设想——产品雏形——实验迭代”的网络化思考与实践过程,需要保证充分的学习时间。
同时,为了解决成人支持问题(PBL强调无边界学习,倡导专家进校作为产品导师,以打通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我们的学术团队还对学校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变革,引入了“乡村书院模式”,作为教育资源的聚合地。
乡村书院是自唐肇始的传统书院的现代性转化,是以乡村学校及教师为责任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组织。它可以建立在乡村学校,可以建立在村庄文化中心,甚至建立在一些撤点并校闲置下来的学校里。它主要通过发挥文化中心的作用,通过举办讲学、地方文化传承、传统与现代祭祀仪式等活动,吸引一些大学教师、学者专家、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各类公益组织机构人员甚至村庄能人参与到村庄文化教育中来,让乡村书院成为一个资源聚集地,以解决PBL教学中的人、财、物匮乏的现实问题。
当然,除资源聚集的功用,乡村书院的“根本要旨在于恢复社会文化共同体,进而重塑社会,重塑乡民、乡村孩子、乡村教师”[13]。这也是乡村PBL课程的最终旨归,即培养现代乡村孩子、培育现代乡村社会。基于以上课程精神与组织变革探索,我们设计了如下课程框架。
在课程目标上,乡村学校PBL课程体系指向培养具有本土精神、国际视野的现代人,所以可称之为“泥土课程”,即基于本土的课程,但课程精神是现代的、国际的。
在课程主题上,分为“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表达”“社会如何组织?”“世界如何运作?”“我们的地球村”等六大主题,分别从人文、社科、自然科学、语言与艺术等维度,对自我、社会、自然及其相互关系展开探究。
在课程内容上,如上所述,设置“4+1”课程模式,基于PBL精神,将学科教学与超学科教学相融合。
在课程实施上,概念性理解、复杂交往、元认知、健全人格等成为未来学校及乡村孩子的认知发展目标,并通过SEL、大单元备课、思维的可视化工具、逆向设计和真实表现性任务等,学习核心知识,发展关键技能。
(三)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愿景
需要注意的是,乡村PBL课程框架并不仅仅适合农村,只不过因为课题原因,我们选择了乡村学校作为实验学校。PBL的重要核心精神在于学习的在地化、在地资源的课程化,在于社区与学校的无边界,这点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相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思考、研究、实践乡村教育,不要将乡村教育“特殊化”,不要将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刻意区别开来。至少在课程与教学的本质精神上,这种差别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乡村PBL课程的探索中也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开展高质量的PBL设计,使其不至于再次沦为活动化或者拼盘化的伪PBL。教师的教学观、课程观、学生观等文化层面的变革如何与PBL精神相契合,如何培植其生长的文化土壤,如何将核心知识与能力与PBL产品结合起来,如何处理PBL的效率与公平、自由问题,等等,都是摆在每个热心于乡村PBL课程变革的学者、教师面前的问题。相信随着《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实施,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有更加完善的答案,但在这一过程前经历的煎熬和焦虑,是一场蜕变必然带来的痛苦。
四、结语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靠歌声迷惑水手的女妖塞壬(Siren),她有迷人的美女面孔,但颈部以下是鹰一般的身体。当海上水手们听到她唱出的凄美歌曲,都陷入了极度疯狂,甚至跳入海中追寻塞壬的身影,直到葬身海底。知识如同这个女妖,我们追寻她的召唤,但往往被愚弄、驯化甚至打击得体无完肤。是什么让知识变成了迷人的女妖?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细致分科造成知识整体性的碎裂。专业化知识将人打扮成专家,专业区隔成就了个人的权威,却造成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享乐人没有心肝”。
二是知识与自然的割裂。人类的智慧首先来源于跟大自然交往过程中的好奇、惊异,知识与自然的天然关系在现代知识的死记硬背、应试评价中被摧毁。这些做法扼杀了好奇心赖以生成的那些身体感觉。
三是知识与社区的割裂。人、知识、社群三者的互动,是人获得生长力量的重要来源,知识与社群互动产生的地方性知识,是一个人发现自我、形成自我的来源。知识的责任感也是知识对人的最大意义,人在社群中了解、分享知识,知识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他人,从而产生了意义。
四是知识与自我的疏离,这主要表现为知识与个人经历、个人生活、个人经验的疏离,知识不能由己而生、为己而存,就成为异化自己的外在力量。
PBL正是疗治以上疾病的良药。乡村PBL尽管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只要它能真实地符合信息时代的学习本质要求,只要它能实现乡村孩子、乡村社会的精神现代化,我们都应该给予它更多的关注、更大的信心,因为它能帮助乡村孩子从知识女妖的歌声里逃脱,扎进泥土,汲取智慧,成为一个更有灵性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