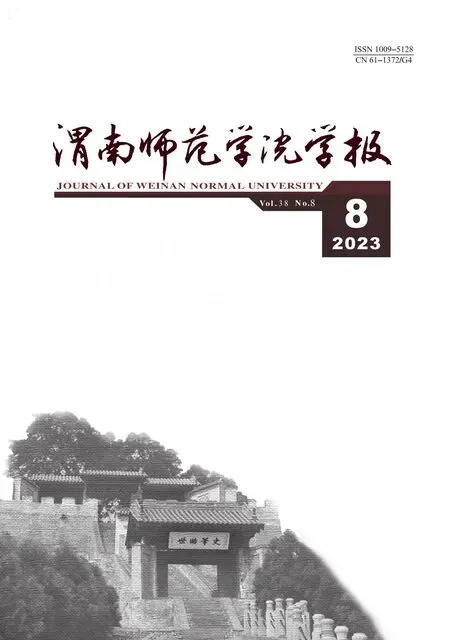论屈复与清代秦声
张世民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西安 710000)
一、清代史家对屈复其人其诗的早期评价
屈复(1668—1745)者,何许人也?简要地说,屈复是清初诗人,清代秦声的奠基人。对于屈复的生平及其诗论诗作,《清史列传·文苑传》卷二如此介绍和评价:
屈复,字见心,陕西蒲城人。年十九,试童子第一。忽弃去,走齐楚吴越间,转徙至京师,以诗学教授弟子。居僧庐,坐卧土床中,与客约,不迎不送,不作寒暄语。诸贵人以问奇至,趾相错也。初则高杖,四童扶持,与客讲论诗文源流、诸史兴亡陈迹,以及关河扼塞、兵马槽盐、天文律历诸事,剀切详明,言之凿凿。尝注《楚辞》,自以新意疏解之,颇得骚人言外之旨。说《李义山诗》,一洗穿凿附会常谈。论诗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谓陶(潜)之饮酒,郭(璞)之游仙,谢(朓)之登山,左(思)之咏史,皆自有所以伤心之故,而借题发之,未可刻舟而求剑。其诗浑劲朴质,独开生面,讬意不凡。郑方坤、王永业甚称之。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不赴试,举主杨超曾未见复,复亦不谢。沈德潜谓复以布衣遨游公侯间,不屈志节,固是有守之士。无子,妻死不再娶,时比之林和靖。著有《楚辞新注》八卷,《李义山诗笺》《弱水集》《江东瑞草集》(按:括号内人名均为引者所加)。[1]
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判断:首先,屈复是一介布衣诗人、漂泊诗人。为了谋生,他以诗学教授弟子,与三教九流皆有来往,其中不乏清朝公侯贵胄。但他“不迎不送”,谢绝私交。他放弃了家族责任,早年就行吟江湖,寄情远方;因未有子嗣,尝收养族子,却又疏于扶养。其次,屈复精通诗学源流,对于诸史兴亡陈迹以及关河扼塞、兵马槽盐、天文律历等事,也都“剀切详明,言之凿凿”,这与他广游历、多知见、善观察密切相关。他年轻时放弃科第、出关东、下江南、上京师,游踪遍及大半个中国,与明清之际昆山顾炎武壮游北方大抵相似。再次,屈复有独立的诗学主张。“论诗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通过对屈原《楚辞》的注释,对李商隐诗的笺注,对《乐府解题》和《唐诗成法》的揣摩,尤其是对老杜诗的点评,均获得了独家的见解。对于陶潜的饮酒诗、郭璞的游仙诗、谢朓的登山诗、左思的咏史诗,也都坦白了作者内在的伤感,认为这些诗歌皆有借题发挥之处。这也是他对诗学“寄托说”的一种艺术举隅。屈复个人诗作“浑劲朴质”,也践行了这一诗学主张。最后,屈复为人有操守,有节概。在政治上,他对于清政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但在诗学坛场,他却“以布衣遨游公侯间”,甚至获得过满族勋贵重臣的举荐。
以上是《清史列传》编撰者对屈复其人其诗的一种早期评价。
二、清中叶以降学术界对屈复及其《弱水集》的褒贬评价
屈复,字见心,号悔翁,他的一生,堪称是诗学的一生。他的著述宏富,似皆与诗学探究有关。《楚辞新注》[2],“是他一生研究楚辞的心血凝结,‘实乃清世研习楚辞名作’(黄灵庚《楚辞新注》提要)”[3]85,其中《天问校正》[4]“首开其错简之全面整理,直接影响了后世许多治骚大家,如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汤炳正、林庚,以及台湾的苏雪林等”[3]87,堪称是其深入《楚辞》研读的必然结果;《玉溪生诗意》(一作《李义山诗笺》),对前人引经据典、繁芜驳杂之处予以删节,仅留切合己意者;对原注未涉及者,自为补注于后。注后有对每一部作品的分段注解,以说明诗意。屈著《唐诗成法·凡例》中,尝谈及选诗标准:“初唐风气始开,其法尚疏。至摩诘、少陵,神龙变化,不可端倪。中晚以来,间有奇格,然奇即是法,奇亦不能离法也。”“初、盛、中、晚,皆有佳作。或专选初、盛,或专选中、晚,此一人之偏好,非古今之通论。兹集有法者,虽中、晚必登;无法者,虽初、盛不录。然诗佳而无法者,未之有也。”[5]其所说“诗法”,偏重在起结、呼应、承转、跌宕等方面,兼及遣词造句,言情写景。有时也点评诗家,大都态度和平、审慎。对于好的诗句或诗眼,皆以圈点标出。另有《乐府新解》《评定〈全唐诗〉》《杜工部诗评》《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选》等,皆以诗论为根柢。晚年著作《百砚铭》,为古今各类砚台制作韵体箴铭,以石喻人,警策句子颇多,亦与其诗学研究密切关联。
对于屈复及其代表作《弱水集》的学术评价,清中叶以降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6]佛经中有“弱水三千,惟取一瓢饮”的说法,屈复取此以为诗集名,恐怕正有着在诗歌的海洋中,汲取一点一滴的用意吧。概而言之,历来涉及屈复其人其诗的评价,大抵有三种基本类型:
(一)以沈德潜、袁枚为代表的“贬抑论者”
清代诗坛繁荣发展,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就诗学派别而言,譬如王士禛(1634—1711)代表的“神韵说”、沈德潜(1673—1769)代表的“格调说”、袁枚(1716—1798)代表的“性灵说”、翁方纲(1733—1818)代表的“肌理说”等,大都各具特点。其中屈复所代表的“寄托说”,距离王士禛所在的时代较为接近。其所作《王渔洋诗选》,对其诗学主张有所研习、有所点评;作《明四家诗选》,也彰明了明代诗家的诗学源流、治学特点。嗣后,“格调派”诗人沈德潜强调温柔敦厚,他在《国朝诗别裁》中写道:“悔翁以布衣遨游公侯间,不屈志节,固有守士也。诗虽未纯,亦时露奇气,惟过自矜许,好为大言,而一二标榜之人,至欲以一悔翁抹倒古今诗家,于是学者毛举疵瘢而苛责之,悔翁无完肤矣。余所选数章,皆铓刃不顿,人宜厌心者。”[7]1157-1159沈氏用貌似公允的笔法,嘲讽了屈复其人及其诗作,表达了明显的贬抑之意。而“性灵派”诗人袁枚,专意与明代前后七子作对,其所倡导的闲情逸趣,也与关陇学人相去甚远。袁氏所著《随园诗话》卷四对屈复的随意指摘,源自山左颜懋伦贡生的无礼之举。据悉该贡生探访屈复,当面指摘其《书中干蝴蝶》二十首为“委巷小家子题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对此无礼冒犯,屈复缄默不语,竟被认为无言以对,由此可知其人处世态度之轻薄。而袁枚引以为据,除自证轻薄而外,并无何等诗学价值。信然,由于社会风气的交互濡染,袁氏观点风靡一时,对屈复的诗学评骘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8]40-45至于“肌理说”代表翁方纲,则因时代较晚,与屈复缺乏互动。屈复撰《论诗绝句》云“三代而还尽好名,文人自古善相轻”,对此表达了相当通兑而不屑一顾的态度。
(二)以樊增祥等人为代表的“褒赞论者”
除同时代的诗人郑方坤、王永业盛称外,历来称道者也代不乏人。针对沈德潜、袁枚等人的轻薄态度,清末陕西藩司、诗人樊增祥在时人徐璋所绘《屈悔翁秋风罢钓图》卷尾题跋,感慨“袁、沈同时轻薄甚,岂知万古有江河”,可谓一针见血。当代诗学巨擘钱钟书援引《韫山堂文集》卷八云:“近日北方诗人多学悔翁(屈复),南方诗人多学确士(沈德潜)。屈豪而俚,沈谨而庸。”将屈复与沈德潜的诗风作了对照分析。《国朝诗钞小传》则认为屈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知先生之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穷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足为外人道也。”《西青散记》指称:“(屈复)所著《弱水集》甚富,江南许元基品其诗为国朝第一。”《国初十家诗钞》亦云:“屈弱水之寄托遥深,清奇浓淡,异曲同工,堪为后学楷模。”[9]前揭《清史列传·文苑传》卷二,亦称“其诗浑劲朴质,独开生面,讬意不凡”[1]。上述评论,堪称清代学者对屈复其人其诗的褒扬论者。
(三)以钱钟书为代表的“褒贬互见论者”
钱钟书起初堪称是贬抑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其晚年观点与早年说法相去甚远。早年在《容安馆札记》中,他通过清初陕籍诗人李天生(因笃)、孙髯翁(豹人)等人的诗学对比,对屈复其人其诗颇有微词。他写道:
屈复悔翁《弱水集》二十二卷。粗浮冗率,腹笥又陋。杂凑杜撰,于是空套之中参以俚俗,既逊李天生(因笃)之入格,复输孙豹人(髯翁)之入情,秦声之最下者。咏古赋物,动辄数十首,烟瘴榛芜,而高自位置,宜随园之讥也。《国朝诗别裁》卷十二《孙枝蔚》条有云:“近有秦人,胸无典籍,好为大言,至云作诗先洗去李、杜俗调。庸妄如此,而人群然信之,云远胜豹人,不可解也。”即指悔翁,三十五卷录悔翁诗。[9]
显然,这完全是站在沈德潜、袁枚的固有立场上所发表的意见。到了晚年,钱钟书对屈复诗作的评价有了新的变化。1982 年,他在陕籍诗人王典章(字幼农)《安隐庐诗存》跋尾写道:
因贯之学人获睹幼农先生遗诗,雄豪绮丽,兼而有之。秦声本自李天生、屈悔翁,以迄近日于髯翁,皆铁板铜琵之意多,玉琴锦瑟之致少,先生于其乡献,可谓经纶超群者矣(按:贯之,王典章之子)。[10]
在这里,他将雄豪绮丽、铜琵锦瑟两种不同的艺境诗风加以对举论列,突出强调了清初李天生(因笃)、屈悔翁(复)至民国时期于髯翁(右任)、王幼农(典章)等人一脉相承的秦声传统。尽管就重评起因而言,居间不无人情因素,但也正是这种人情因素,促使他有了新的鉴别,作出了新的判断。在艺评基准上,钱钟书也从原先严苛的、不无依傍的贬抑论者转而成为宽容的、不乏新识的褒扬论者,这也标志着钱氏诗学鉴赏心态和学术评价立场有了重要的变化。钱钟书曾将李因笃、屈复作为清初秦声的导源人物,肯定了清末至民国时期于右任、王典章等人的诗风,显然是超越早年定见的一种新的诗学观点。
三、当今之世应对屈复及其诗学著述作出新的评价
站在诗学后辈的角度,我们大可不必陷入先辈们的流派纷争,而要葆有清醒的认知态度和不倚的学术立场。众所皆知,秦陇、吴越两地之间的学风、诗风差异由来已久,而不同地域、不同文风之间的相轻相砥也夤缘成习,所以这种不同地域、风格和时代之间动辄出现的褒贬评价虽则易于出口,却也有碍知见。当今之世,我们完全有必要作出新的理解、感悟和判断。重读屈复及其《弱水集》,至少有六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就诗学源流而言,屈复的“寄托说”,实属清代早期诗人一种重要的诗学观点,同时也构成了清代秦声的特色内涵
何谓秦声?通常疏解是:“秦地的音乐,又名秦腔。”秦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11]3086-3090即指秦地民间音乐。然而这一诠释未免以偏概全。相较秦地民间音乐而言,那些带节奏的诗歌作品恐怕更是秦声的基本内涵。如果说秦陇梆子腔诞生于明末清初,那么诗学意义上的秦声,恐怕还要远溯到《诗经》时代。尽管历史在演进,声调在变化,但是基于特定的民风、民俗基础上的秦声,历来具有慷慨悲怆和委曲欣悦相兼顾的音声特点,这早已蔚成了一种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周秦时期的秦声,固然以《诗经》为典型代表,而汉魏以降,蕴含于乐府之中的秦声、秦韵,恐怕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一种秦地民间音乐。隋唐时期,关中属于帝都所在地,其时代音声有博综中外的兼容性,而宋元以降,随着关中地区逐渐转向地缘化,属于秦人的地方音声也日益泛起。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文章之士,其学问必有根据。”“时代变迁,文字遂异。”“自唐以下,文始有派。”[12]5-6正如昆山顾炎武与江南学风、余姚黄宗羲与浙东学风、衡阳王船山与湖湘学风之间的学风互动一样,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等清代学人与关中学风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清代秦声最早的导源人物,作为长辈的李因笃与青年诗人屈复之间,也有过诗学上的密切互动。李因笃称赞屈复“三秦之秀,全在于此”,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呼效应。从明代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到后七子重视民歌民谣的传统,秦声中的慷慨激昂与委婉曲折、庙堂悲歌与民间声调相辉映,也滋育了秦声内在的兼容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声纷敷中的屈复其人,确有开拓清代诗学新域的历史创举。其寄托说,既有那个变乱时代的家国悲情,更有作为人物个体的身世怀感。由于明清之际动乱频仍,朝代转换,蒲城屈氏元气大伤,屈复父辈因乱罹难,他个人婚姻遭遇挫折,对于他放弃科举,负命出关,尤其是考察故国情实,寄寓一己胸怀,有着必欲以诗代答的诗性情结。“诗与远方”,就屈复的生平来说其实是一个历史写真。屈复的诗学研究,将源自《诗经》以下的诗学传统一一勾勒,《诗经》的赋比兴,《楚辞·离骚》的故国情怀,《乐府题解》的民间韵致,《唐诗成法》的独到剪裁,《李义山诗笺》的内涵蕴蓄,《杜工部诗评》的寄托遥深,乃至明四家、王渔洋之诗,都贯穿着他一以贯之的诗学思考。其《王渔洋〈秋柳诗〉四首解》认为:“四章寄托高远,蕴藉风流,字句典雅,玩之有余味,诚妙作也。……至于寄托用意,稍有参杂重复,则不可不知。……要之渔洋如天生美人,即风鬟雾鬓,敝衣倒屣,其一种遗世独立之致,终不可掩也。”[13]
(二)就诗歌题材而言,屈复坚持独立的不合作立场,撰写大量有所寄怀的诗歌,其寄托方式精微而多样
历来诗歌叙事,大抵有两大类:一类是咏史纪事,蕴含了人生况味和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向外用力,而人生况味是向内用力。置身官场,感怀酬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人在江湖,优游世间,又不免抒发其一己情怀。以上两者,都是有“我”的写作。屈复以布衣行世,写人事往来的诗歌相对较少,一些有限的内容也以天地自然、个人寄怀为主。屈复一生特别敬慕其远祖屈原,以及鲁仲连、岳飞、文天祥、郑所南等人的人格志节,且矢志力行,不慕名利、不畏强暴。尤其是三辞怡贤亲王允祥千金之聘,更为人们所称道。其时刑部侍郎杨超曾,虽不认识屈复,却仰慕其学问人品,特地上疏举荐屈复应博学鸿词。屈复借口老病,坚不应征,也不面谢,特作《感遇诗》三十首表达感怀,其诗句含蓄深厚,慷慨感人。而与此同时,有关节烈女性的长调吟咏,也带有强烈的、寄寓性的人生叩问。他所写的《枞阳姚烈妇》,虽有师法《孔雀东南飞》之处,但钱钟书贬其“鄙俚尚不堪为胡稚威《李三》之什作奴仆也”,恐怕言之过当。通过屈、胡两人作品对照阅读,恐怕很难得出如此判断。钱钟书称其开头“‘雄鸡雌鸳鸯,单情安可双。鸳鸯会独死,乃在古枞阳。’不知鸳鸯为同命鸟,已令人笑齿冷矣”[9]。更是对作者诗意表达的一种片面揶揄。在我看来,屈作虽然够不上思想启蒙,性别认识也有限,但其对于社会暴虐的谴责与批判,对于节烈行为的同情与反思,仍然有其悲天悯人的基本思想立场。另一类是写自然万象,包含了静态物象或动态物象两种。它是一种超越自我感受,超越主观认知的物象书写。《弱水集》中用功最深、用力最勤的,恐怕要算是咏物诗。格物致知、寄寓情态,是这类咏物诗篇的最大特点。吟咏物像胜于吟咏史事,书写事实胜于心理描绘,这是屈复迥异于时人的诗歌语境。一朵书中干蝴蝶,被他用20 首诗歌来吟咏,当时造访他的轻薄贡生不解诗意,认为李杜诗集中从未见到,钱钟书初读时也厌其咏之惮烦,但这种不理解、不感知和不体悟,尤其是李杜词库中的有所阙如,恐怕正是屈复诗作的卓荦之处。钱钟书说:“卷十七《书中干蝴蝶》七律二十首,即随园所讥切者也。序云‘窃香惰性,顿改风流;争絮生涯,忽潜骚雅’云云,颇有心思,而诗不称。他有《雁字》四十首、《水中雁字》二十首、《黄牡丹》二十首,何不惮烦?了不足采。”[9]在这里,钱氏仍然站在随园立场上加以否定,却也不得不肯定其“颇有心思”。而震泽杨复吉称:“悔翁先生为关中骚坛巨手,著有《弱水集》,其咏物诗极吹影镂尘之巧。近时谈艺者竟诋其卑琐,真拘墟之见,不足与辩也。《楚辞新注》,条分缕析,妙契精微;《天问校正》,更为创获。观书眼如月,此之谓夫?”同时还有人肯定《书中干蝴蝶》有独特诗眼,指其“悔过之词,无意不备”,并强调《雁字》:“咏物诗,精切难,超脱难,寄托更难。斯题又最忌呆用一画、天书、玉篆、笔阵、熟滑等类死贴字面。四十首中不犯忌,而易所难,此其所以独绝也。”[4]1-7这些鉴赏意见,其实都是冷静的、客观的评价。
(三)就诗家情怀而言,屈复放弃科举,拒不仕清,虽不能拔擢于当代,却也饶具节操意识,不失为非遗民的“遗民”诗人
清初,大抵有两类文人:一类是入仕文人。除了出身清初的仕人外,那些出身故明,既仕明又仕清的贰臣也不乏其人。这些贰臣对清朝的统治尽管不无腹诽,但却又背叛家国,予以呼应。乾隆初年,弘历皇帝站在封建道德话语立场上,曾经将钱谦益等降臣纳入《清史列传》中的“贰臣传”,本身就是对此类变节人物的一种否定。其时绰有文名而被列入贰臣传的人物,还有周亮工(栎园)、吴伟业(梅村)等,其诗文虽传之于世,但不及钱谦益“受厄之酷”。清初博学鸿词科的设置,名义上是倡导实学,补救空疏学风,实质上却是清政府罗致人才、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当时不少文人通过科试而进入仕途,成为清政权的拥趸者。
另一类是遗民文人。遗老遗少,皆以政治上的不合作为标志。然则“明代之遗民,实清代文学开国之元勋也”[12]7。除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等人,因出身故明而拒绝仕清,故被称为“遗民”外,也有像屈复这样的“遗二代”,他虽然生在清初,却也拒绝仕清,堪称是思想上的“遗民”。所以有人称屈复为非遗民的“遗民”诗人。[14]69-75受制于清代酷烈的文字狱,屈复既未用诗歌来抗争,亦未投身反清复明,但他在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也是其遗民立场的重要标志。年轻时,屈复参与过童子考试,一旦确定独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放弃了科举考试。他的放弃行为,不独针对科举考试,同时包括家族生活,他出关后在山东郯城找到了新的天地。有人认为:“屈复在外奔波五十年,游历半中国,三上北京,三下江南,所到之处,惟游访名胜古迹、先贤遗事,结交同志,作诗授徒。屈复之诗以寄托为主,熟练地运用形象思维的手法,写出了大量动人的诗篇。特别是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他不避杀身之祸,以诗歌作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不愧为有人民性的伟大诗人。”[15]86-90就诗作本体而言,屈复年轻时到富平县游历那年,路过吴三桂与农民起义军王永强作战的流曲川,特作《过流曲川》诗,对这位民族败类予以无情鞭挞,对农民起义军予以高度颂扬。此时吴三桂早已被清朝抛弃,所以这一声讨谈不上针对清王朝的统治,却足以反映作者的遗民立场。所以也有人认为“屈复是清初陕西蒲城的一位具有民族气节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16]85-87,认为他与乃祖屈原同思共虑。然而屈原生于战国时期,楚国被秦国所灭,其移民情结自然难于化解;屈复则生于清初,虽也耳闻故明掌故,却无从亲炙感受,他能辞却功名拒绝政治上的合作,却无法擢发于时代,不食人间烟火。尤其是清代前期,依然是封建家国天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尚在孕育之中,而两种不同的国体、政体,决定屈复无法在独擅胜场的文化领域也隔绝人寰,永不合作。康、雍、乾时期,清政府在与沙俄政权的对抗中廓清国家疆域,逐渐蔚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作为家国天下,清王朝在封邦建国基础上所确立的新政体,通过满汉互动,民族合作,也确立新的封建道德话语立场,所以当时学人在文化领域有所合作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屈复在政治上的不合作和在文化上的合作立场,也包括以布衣之身遨游于公侯之间的文化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固然要肯定其具有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具有独立不倚的个人情操,但要因此强调其民族气节,则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认识误区。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基于同一道德话语体系,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则是与异质文化传统的历史对抗,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四)就诗学话语而言,屈复的诗作风格被界定为“豪而俚”,亦即雄豪而通俗,自有其扎实的语言根底和独特的话语风格
所谓“豪”即雄豪、豪放,它是我国北方民俗风气的一种典型写照,同时更是关陇诗人的个性特征。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著《诗集传》指出:“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周南、召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17]546这个结论性概括,指出老秦人“厚重质直”的传统个性,而这一传统个性的浑然放大,构成关陇地区的人民性格。有基于此,整个清代构成秦声的秦地诗歌、秦腔,也都具有雄浑豪放、慷慨激烈的天然秉性。屈复诗作不空灵、不矫韵,一贯以质实朴厚的诗风,寄托着一己的思想情怀,堪称是这一民俗风气的历史写真。而所谓“俚”,即鄙俚、俚俗,实际上也是对民间通俗文风的一种挹取。从明代前后七子开始,一方面追求汉唐文风、诗风,另一方面又超脱古文运动,关注民间声频,所以民间声频日渐响亮。这种民间声频,纵然用语粗鄙、略显俚俗,却也有独到境界。屈复的诗作风格,大抵上质直朴实,并无华言丽藻。他的作品寄托遥深,不乏韵外之致。屈复所在时代的公共知识和私人认知,决定他所独具的私人话语空间。前者是正在发生的情态、事态和物态,后者则带有诡秘性的话语特征。屈复的诗性语言,更多的是借助公共语言,表达了一己的国民情怀。在屈复谢绝提携的诗作中,用语也都不直截了当,而是用诗性话语、诗性方式来表达一己态度。这一点,也是源自屈原《楚辞》的一种对话方式。在《离骚》中,屈原自譬香草美人,而诗人屈复也有类似的取譬心理。这种语言上的寄寓特点,确实显而易见。屈复对于明清之际王士禛等人的诗选,亦足以见出他的诗学用语重寄托的特点。以“虎”字为例,《弱水集》中对“虎”的取譬便非常丰富。诸如虎雀、一虎万夫、栽松柏刻虎羊、虎狼、虎丘、雕虫画虎、沙虎狼吼、虎啸龙吟、虎颠熊倒、虎豹、虎踞龙蟠、龙跳虎卧、威虎健鱼、射虎飞鹰、龙战虎牢、虎穴蛟宫、鸡偪剥虎咆哮、狐裘虎迹、虎时啸猿夜啼、艾虎蒲人、龙争虎战、潜龙飞虎、龙骧虎踞、虎啸龙屠、虎啸螀啼、龙虎卫鬼神司、愁虎畏途、虎迹鲸奔、虎脊鸡肠、鳌饵虎符、虎羊列驼马镌、射虎惊鸾、画虎雕虫、虎穴龙湫、鸾凰侣虎豹群、金虎暮鸦、城乌石虎、牛羊下虎豹尊等等,皆历历可见。
(五)就诗学批评而言,屈复在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等历代诗集的专题研究中,提炼一己的诗法、诗意和诗学观念,同时又从《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选》中,寻觅出一种近世的诗性参照
清初北方学子师从屈复,他亦用以授课,因而他的诗学批评影响一时。屈复的文集不曾流传后世,而其现存著述,大抵上都与诗学教育有关。在注解楚辞、乐府、唐诗、杜诗、李商隐诗的过程中,屈复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结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对于《楚辞》《乐府》及李商隐诗作的研究,大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予以增删,然后表达自己的诗学立场。《庄子》虽非诗,但后人通过《庄子》(又称《南华经》)却发现一种诗旨诗意,所以研究诗学源流而谈及《南华通》,将其作为当代诗学的研究对象,恐怕也不足为奇。近年学术界谈及屈复与庄子《南华通》的关系问题,值得注意。清代陕籍学人李元春辑刊《青照堂丛书》时收入《南华通》七卷本,署名作者屈复,对晚清至民国社会影响很大。但清代乾隆年间有孙嘉淦《南华通》七卷本传世,因流传不广,为人忽略。经过今人学理考证,初步认定孙嘉淦的著作权。但按照屈复注释前人著作用于教学的特点,很可能也是他当年所选诗学教材。至于孙氏原注与屈复补注的异同关系,尚需认真甄别,才能有所厘定。[18]17-21至于屈复对《全唐诗》的评说,基于《全唐诗》开编不久,屈复就在入京之际有幸获读,并予以点评,其实这也是其丰润辞藻、觅取蕴藉的一个重要渠道。其所著《唐诗成法》,正是这次集中阅读的学术正果之一。要探索《弱水集》的诗学观念,尤其是屈复的诗学批评观念,务必研究其所关注的诗眼、诗旨和诗法,舍此别无他途。
(六)就诗风传承而言,由屈复等人开创的“寄托派”,在清代至民国陕西诗坛的影响也非常深远,通过陈涛、王典章到于右任等人的诗歌创作皆能看出这一点
明末清初,陕北农民起义的声势空前浩大,山陕豪杰匡扶故国的豪气亦如日在天。乾嘉之际,陕南各地为安置白莲教起义民众而不遗余力;咸同时期,一方面平息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另一方面抵御列强入侵,反对鸦片肆虐,陕西人民的牺牲抗争精神此起彼伏,从未歇息。在此环境背景下,屈复等人倡导寄托诗风,强调诗歌务必表达真情实感,勇于批判社会现实,由此也就抟成了新的气象。当时陕甘文坛,不少诗人群落都受此影响。譬如赵时春被称为“秦人而为秦声”(胡松《赵浚谷诗集序》),钟惺《文天瑞诗义序》:“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沉之思,其所为诗义,盖犹有秦声焉。”《四库提要》馆臣点评孙枝蔚诗:“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19]又李念慈“有《谷口山房集》,施闰章称其雄爽之气,勃勃眉宇,盖秦风而兼吴、楚者”[20]13355。由此可见,陕甘作家的创作深深地植根于关中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清末至民国时期,刘古愚嫡传弟子陈涛(伯澜)所撰《审安斋诗草》、王典章(幼农)所撰《安隐庐诗存》、于右任(伯循)所撰《半哭半笑楼诗集》等等,其诗风兼具雄豪与绮丽、慷慨与柔婉两种风格,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具有北国民俗气节的慷慨节奏。于右任等人擅长《山坡羊》等北曲词牌,更寄托强烈的家国情怀、深远的历史感怀和入世的命世襟怀。于右任留有大胡须,人称于髯翁,其绝笔诗《望我大陆》,固然有骚体的诗风特点,却也与清代初年的慷慨学风遥相传承。至于屈复的慷慨劲节,有所寄托,甚至以静物描绘表达审视态度,以节烈凭吊表现志士立场,以历史吟咏表白千古况味,也都显示独特的文脉传承。所有这些,大抵都可诠释为屈复寄托诗派的具体传承。
四、结语
清赵翼《论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代初期,以李因笃、屈复等为代表的陕西诗人,其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大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堪称是清代秦声的奠基人和首倡者。尽管早在明清之际陕西各地早已地缘化,不再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然其独特的国防战略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文化积淀,仍然披靡广大、影响深远,构成最具民俗性的地方音声。屈复的一生,既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是诗学不辍的一生,其所开创的寄托遥深的诗作风格,在艺术上重视节奏铿锵,在情绪上强调真情实感,勇于暴露和抨击社会黑暗和官场腐败,这种诗风对于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陕西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尽管清中叶以降学术界对于屈复及其诗风褒贬不一,甚至《清史稿》删掉屈复传记,但只要肯于摒弃历史的偏见,我们也就能够发现其中包孕的合理内核。屈复诞生于清代初期的陕西腹地,但却有牢不可破的遗民立场;屈复拒绝科举应试,但却不拘一格,广交朋友;屈复具有豪侠任性,但却植根民间,善接地气;屈复重视诗学批评,但却创作率意,信马由缰;屈复生前备受争议,身后却影响深远。对于屈复其人其诗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是揄扬过度而是研究不深。要想深入研究屈复及其《弱水集》,就不能不熟悉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理清当时的主要社会命题;要想精研深识屈复其人的基本诗学观念,也就必须重视其所关注的诗眼、诗旨和诗法,舍此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