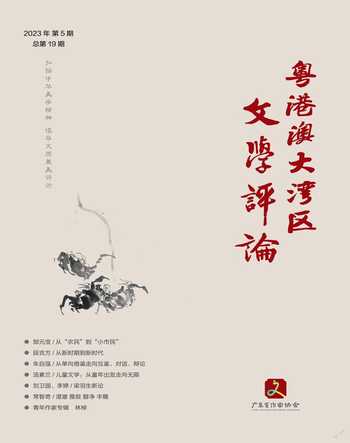黄礼孩:找寻精神世界里的无限性
黄礼孩 廖琪
一、故乡原风景:自然的观察者
廖琪:对于家乡徐闻,您已过于熟识,但于我们这些异乡人,第一次见到,那种触动是战栗的。头顶瓦蓝的天幕,大块的白云浮动,数不清的白色巨大风车在天地之间转动,风吹衣袂,我第一次站在大陆最南端广袤的菠萝的海高地,大片的苍绿、青翠、褚红、土黄的斑斓色块毫无遮拦地映入眼帘,渐次交替,线条优美,一眼望不到边的起起伏伏,就像上帝亲笔渲染的一幅巨大无比的油画。你可能很难想象,我是有多么喜悦,哀伤又幸福。突然涌动着一种躺在红土地裸露的胸膛上哭一场的冲动。看着波光粼粼的玛珥湖,湖边一丛丛身姿绰约的青树,无比怀想逝去的青春岁月,想穿越回时光隧道,牵着翩翩少年的手,谈一场无禁忌的爱情……徐闻真是一个产生诗意、诞生诗人的美丽地方。我似乎是在一刹那,捕捉到了你诗中的许多我不曾触摸到的意象。
家乡是一个人剪不掉的精神脐带,您至今怀着怎样深沉的情感?骄傲、深爱,抑或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
礼孩:我十分理解你的喜悦、哀伤及幸福。有时候,通过他者的感受并回望自己的故乡,就像我作为你的朋友回到你的出生地,有着莫名的渴望。你说的故乡是理想化后面的场景,生命在审美一致的前提下,同理心会更为强烈。你作为异乡人来到徐闻,会带着某种想象,现实未必与你心中的吻合,但陌生感还是带给你深深的体会。徐闻作为一个农业县,那天空、云朵、土地,还没有太多的变化,比如土地上的贫穷与愚昧。作为生命出发的旅程,从童年到青少年时代的痕迹,已经很遥远,它们留在记忆里,镶进生命里,那是精神永远存留的地方。就像鲍勃·迪伦说的:“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才能安然的睡在沙滩上?/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作男子汉?”岁月流逝,更多的感慨来到生命中,当年那个最普通的孩子,今天活出了别的样子,在别人看来应该骄傲,但之于我却是复杂的,生命有丰盈的时刻,也有空缺,就像故乡,它有时是明亮,有时是灰暗。
廖琪:白鹤林有首诗《孤独》,“‘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照顾着/历代的星辰”,读到的时候,会觉得这也是你的童年写照。家乡丰富的自然资源,辛苦劳作的日常,困守岛上的封闭寂寞,无边大海的阻隔,对海洋外世界的向往,带给您最多的是什么?孤独、想象、心灵的驰骋?
礼孩:白鹤林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同代人,我懂得他的深情。有無数的童年,不是所有的童年都值得书写。人生在后面赢得个体的“精神王国”后,回头观照你的童年,那个童年才有深意。就像我童年的伙伴,他们与我一样经历了童年,但他们其中更多的人淹没在不为人所知的时间深渊里。其实,我自己也一样,被岁月的常理所把控。童年是每个走向未来的诗人的本钱。我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得为少年时代的伙伴保存童年的记忆。面对贫穷、困顿的少年生活,美丽的故乡只会给你增添忧伤。因为离开,时空发生了变化,事物在你与故乡之间,留出足够多的图景,文学正是不同图景里的描绘。如我诗中所言,童年是“又穷又冷”光阴里的一块糖。
廖琪:西川说你“非常敏锐”,这应该是一个诗人最基本也必须具备的天赋特质,只不过于你更为鲜明。故乡原风景对一位诗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最终走向诗歌这条路,应该是经过阅读和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吧?
礼孩:诗歌确实是关于天赋的事业。原乡是不少诗人作家的心灵之地,我也不例外。极少有无师自通的诗人,每个诗人都是在别人的精神里活出新的形象,然后自己独自成长起来。我童年时代没有接触过现代诗歌,读初中后接触的是街上流行的诗歌,但这已经是很好的状态。直到到了广州,才知道什么叫经典的诗歌。诗歌的写作,很多时候来自阅读的影响,作为写作者,你得主动去阅读,去寻找精神的导师,你需要一个巨大的自我教育过程,你得在自我的教育里成长起来。
廖琪:汤显祖与苏东坡,虽在徐闻短暂停留,他们于你的文化影响呢,是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存在吗?
礼孩:小时候除了看连环画之外,并没有所谓的历史教育,除了课本里的人物,哪里知道汤显祖与苏东坡。对汤显祖与苏东坡的认识,那是我有了一点文化自觉之后的事情。徐闻是一个偏远之地,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尽管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但本土出生在历史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找不出一个,所以对于短暂停留在徐闻的汤显祖,乃至苏东坡,都觉得不同寻常。宇文所安说过,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之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这是文化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追求文化的人,去读他们的诗,了解他们的人生,仿佛你离他们很近,很近,觉得很亲切,就像你的同代人或者同乡。
廖琪:您大概在什么年龄离开的故乡?离开后开始大量诗歌写作,还是在故乡时候写诗已有名气?
礼孩:我大约18岁左右离开徐闻。在老家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写诗歌,并有发表。在湛江读高中的时候已经在湛江的报刊发表了一些诗歌,在当地有点小名声吧,还被湛江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在那个时代语境里,一个读书一般的小镇少年,文学突然作为梦想出现,也是拜文学所赐。
廖琪:“登云塔”“白茅海”“菠萝”“阳光”“海洋”……故乡的原风景,不断出现在你的诗歌中。“菠萝叶边上长着细密的锉齿/像是柔软的刀片,它要锯出成长的印痕/我少年薄薄的衣裳/也渗出血迹/生活的栅栏是层层叠加的菠萝叶/大陆之南的阳光在空中挥舞/对折着炙热的梦/那么火辣,又如此空荡/有时,我停歇手中的活/手搭凉棚望向远处,这世界不理解/贫穷角落困倦的少年/呵,请原谅我心碎得不一样/生活带来的是长刺的菠萝叶/而不是别的花朵”(《它不是别的花朵》),“这郁葱的丘陵像蓝鸟起飞/对应着少女起伏的秀发/游弋的线条如时光的窃贼/盗来大海深处水草的梦境/又缓慢地沉入菠萝地里去”(《我爱它的沉默无名》)……
应该是你看过世界之后,对故乡的自然景观和少年生存境遇的反观吧?富有亚热带、热带特色的自然景观虽然常出现在你的笔端,这些美好的异域的意象,并非所有人都能真实触摸或者感受到,但这些诗歌绝对不是单纯的自然书写,它已沾满情感,故而也才真的打动人。
礼孩:诗歌是空间的艺术,离开出生地后,你有了适合的距离观看,会看得清晰,就像绘画有时候往后站,更能看到画面的结构。诗人蒙塔莱说过,真正的文化是当一个人忘记他所学的一切时依然保留的东西。你提到的诗歌,我希望是情感的渗透,是语言的唤醒。我写故乡土地上的事物,它来自生命的体悟,是生命里复杂的状态。自从我去了世界不同的地方后,我会不自觉把故乡与世界不同的地点链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希望在熟悉的写作里寻找到陌生的声音。人与精神世界结为一体,情感的深切表达才有在场感,也是记忆的回声,同时,时间的回声梦想着文本的自由。
廖琪:作为广州、徐闻的文化名片,这些年您不遗余力地推介徐闻,这种超乎寻常的热度,源自什么?
礼孩:为自己的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天经地义的。很惭愧,我能力非常有限,做得还远远不够。对于徐闻这个远离发达经济与文明的地方,其欠缺的地方实在是太多。最缺的应该是先进的观念、意识、思想吧。因为愚昧、无知与落后什么时候都是我们的敌人,当智慧、勇气、激情、梦想及创造的心灵在徐闻人心里生出来,用不了多久,家乡会得到改变。当然,说到具体的欠缺,应该是政策的宽松给予及持续的投入。
二、情感源头:母亲与“海棠”意象
廖琪:除了故乡,母爱也是一個人情感的源头。
“海棠花像火烬/呼吸在我漆黑的内心/天堂的一朵朵火焰/划破我记忆的皮肤/伤痛仍在原处/母亲手上的银器/像海棠花一样掉下/碎了”(《掉下》)
“那是一个我用斧头/修改木头的日子/它是白昼也是黑夜/它是母亲在深夜/坐一次慢船去天国看病/她越来越远离她的身体(她爱着我们,却不再拥有)”(《远行》)
“十六年了/房子后的海棠树已枯败/这关闭了的屋子/就像海棠花的眼睛/合上了就再也没有睁开”(《永别》)
“一朵熄灭的火焰奔向星星/我不知道它能到哪里去/它跟我一样呼吸、颤栗着/它的暗
像闪电一样跪下来/我不知道那一年母亲是否带走了我的乳名”(《睡眠》)
这些诗歌读来,令人心碎,朦胧中似乎在看到孤独无助的小男孩守在母亲床榻前的情景。一个人对母亲的眷恋爱护思念又无力的情感都呈现了出来。
这些诗成于何时,母亲跟海棠的意象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呢?
礼孩:母亲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母亲去世时我刚初中毕业,一直很迷茫,也很无助。后来写作,母亲这个最直接的形象就不断出现在诗歌中,这里面是寄托,也是爱的铭记,是永恒的记忆。诗歌里的“海棠”其实是另一种花,叫“黄槿”,是我弄错了。母亲跟“海棠”或者“黄槿”的意象,都是童年的记忆。小时候在黄槿树下长大,南方茂盛的植物或者阳光般绽放的花朵,仿佛都隐匿着母亲的身影,写作让我在词语的沉默里安身立命,找到了慰藉,那是爱的依恋。每一个写作者,内心都有各种念头,关于母亲的一切,她从来没有消失,母亲作为一种生命就存在诗篇里。
廖琪:作为较小的儿子,母亲有限的陪伴时间,获得的爱深沉又永恒,“母亲的行走是花朵上熄灭了的火焰”,“黑夜的尽头涌动着恐惧与陌生”,这些会不会成为你人生和诗歌哀伤的基调和情感的缺口?(很抱歉,我这样问)
礼孩:哀婉与感伤确实是我诗歌情感的一面镜子。少年时代,我就是一个忧伤的牧牛、牧鹅、喂猪少年。这与生存的状态,与生活的困顿,与无助的人生都有关。母亲作为你生命最重要的庇护者,当她生病了,你也觉得自己生病了,这样的伤痛一直留在记忆里,成为生命的痛苦。多年后,当我慢慢找到自己的小理想,随着写作题材和思考的东西多了后,这样的情绪才得到拓展与转移,但却从来没有消失。
廖琪:人生而孤独,渴望爱和被爱,是一辈子的课题。你对爱怎么解读?
礼孩:爱,始于渴望。有什么样的爱,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关于爱,我觉得保罗的《爱的颂歌》说得最经典了。爱是一种发现和践行,人生必须在爱中完成,人生才有意义。应该说爱是生命的支柱,爱是无尽的喜悦,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份喜悦的沐浴。
廖琪:我读过的您的纯粹的爱情诗并不多(许是我孤陋)。“爱情没有预兆,它像雾中之船/来到跟前才察觉,而它远去/似是水中之月,只留下暗转的远影”(《花布衫》),含蓄朦胧,短暂又无疾让人伤怀的爱情。
《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远在他乡的水银姑娘,我沿途收集你的碎片/却又在风中丢失,此地终是陌生的旅程/想起上次的告别,忧伤像海水从未停息/一个人携带的地中海,越来越辽阔,我推开迷途,试着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内含的情愫是给人无限遐想的,“水银姑娘”是不是有什么隐喻(水银是有毒的哦,难道寓意爱情也有毒?或者说诗人中了爱情的毒?即使“忧伤”“迷途”,但我仍试着“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是像信鸽一样捎去爱恋者内心深处最美妙的思念、祝福和情愫吗?
礼孩:《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这首诗歌很多人喜欢,但很少人知道“水银姑娘”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我写得过于隐秘,给读者带来困扰。“水银”在诗歌里,可以理解为“像水银一样的姑娘。诗歌看起来抽象,没有具体的情节,但诗歌很多时候也是诗人的一种自传。“水银”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孩,聪颖,美好,喜欢过她。有一年有机会与一些艺术家去欧洲,她答应与我一起去,后来她没有赴约。诗歌写了一种离别,但又不想写她的名字,就用她喜欢的“水银”代替。诗歌是一种言外之意,诗歌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它藏有一些隐秘的东西。对于读者来说,不知道也不会影响到阅读。
三、宗教情怀:慈爱、博爱、大爱
廖琪:你身上萦绕着一种不俗的宁静,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说的 “散发出一种善良,脸上洋溢着气息生动的微笑,这种友好的微笑又如此具有说服力”,诗歌中也是透着宗教般的沉静、神圣。这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神圣感。叫我总认为是跟宗教信仰有关。即使没有受洗,但基督教宗教的情怀和道义,原罪思想,慈悲,博爱,是否已渗入血脉?思想烙印?
礼孩:人生应该是一种燃烧的热情。一些时候,我也有孤寂、不安的时刻,但与真诚的朋友们在一起做事情或者探讨一些人生话题,环境会改变人的情绪。我希望自己是生动的,而不是一件废物。我自认为自己是善良的。善良是一种品质,它必须在你的血液中。以前与诗人东荡子、世宾等几个人一起提出的“完整性写作”是在美国“9-11”发生的那段背景里,我们看到世界的破碎与人的残酷,就想用诗歌中的明亮精神来消除内心的黑暗。诗歌必须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之光,它是灵魂的救赎。人是有限的,但基督教宗教的情怀和道义是无限的,作为诗人应该看到这点。当神性作为一种尺度,写作才可以被丈量。
廖琪:从你的很多诗篇中,看到的不是宏大,更不是盛赞。你的眼光关注很多人根本看不到或者不屑于看到的小事物上,卑微的生命,隐秘的情感,弱者的尊严。
比如那朵在山道拐弯处的沙土上盛开的花儿,“没有多少人注目它,它也不为多数人盛开/它没有野心,不多情,有一些荒凉/它把小小的坚韧藏好,挽着泥土的手/数着自然的日历,心底一亮,就翻过岁月的山坡/隐秘让一朵花保持着它的纯真/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我保留了拐弯处被遗忘的花朵”(《我保留了拐弯处被遗忘的花朵》)。
像沙子一样微小的苔藓,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身世,阳光偶尔对它露出笑容也很快消失, 如此卑微的生命,“习惯用潮湿的眼睛看一切/呼吸腐敗的空气/它坐在暗处/似乎在等待”(《苔藓》)。
“我知道再小的昆虫/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犹如飞翔的翅膀/要停栖在树枝上”《飞鸟与昆虫》
“我珍藏细小的事物……它们生活在一个被遗忘的小世界/我想赞美它们,我准备着/在这里向它们靠近/删去了一些高大的词”(《细小的事物》)
我们从小被灌输或者耳濡目染受到的教育:追逐卓越、更高、更强、更远、伟大、崇高、炫目,但诗人的敏感、同理心,眼光放的位置,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悲天悯物的伤怀,从很小的事物上获得“一花一世界”的顿悟和馈赠,从渺小、苦难、贫困、不公、残缺、遗憾、灾难、多舛、吊诡、无力,追逐善、美、光明,与命运的恩典——从“残缺的世界里辨认出善和光明。”这其实传达了你的人生观、生命态度和诗歌观。
诗意匮乏,俗世庸常,消弭人的灵气,一个人与自我、与他人、与人生、与世界,充斥着矛盾,怎样达成和解?
作为诗人,你认为,你的使命是什么?
作为个体,你认为,你的功课是什么?
礼孩:你读我的诗歌很仔细,读出来其中蕴藏的大意,或者有些其他读者没有感受到的。我写那些小的事物,是因为自己也是一粒尘埃,与自然中那些不显眼的事物也是同等的,并不比它们高贵。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历史写的都是大人物,小人物几乎不可能被记录被书写。为普通人书写是困难的,但你得为那些平凡的人生发声。有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小的事物来替代某种感情。诗人,在国外曾经被赋予很多不同的社会意义,但现在诗歌很难成为一种力量,很难再去影响社会生活。每一个诗人对自身都有不同层面的定位。我作为写诗的,希望在写作上能够灵活运用汉语,写出有辨别度的诗歌,写出能够触动心灵的诗歌,能够与当下发生关系的诗歌。当然,我因为做不同的诗歌推广,比如我们的国际诗歌奖、广州新年诗会、《中西诗歌》杂志等都在不同的层面被诗歌界之外的人看见。艺术家渠岩老师说,“当下的诗歌因为黄礼孩而变得有魅力”,当然这是鼓励的话,但同时告知我们,诗在功夫外,诗歌需要一种美学上的转换,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使命是“诗歌如何被看见被听见被触摸”,这也是一个诗歌的生命旅程。个人丰富的情感、敏锐的思想、有效的表达就是我的小功课。大的功课,当然是我的生命境界是否可以更高一些,能否把边界拓展得更远。
廖琪:您诗歌的一个关键词:命运。“命运信仰了黑暗”(《缅甸的月色》),“就像芬芳散尽,才是花朵的命运”(《来年的花朵》),“我对命运所知甚少”(《飞扬》),“命运早晨给予的,傍晚又收回去了”(《远行》),“她丰盈的乳房/已被命运温柔地看见”(《被命运温柔看见》)。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自己和他者的命运。
礼孩:诗歌是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世界,命运正好有这样的特质,命是一种生老病死的定律,运却是变化的、流动的,为前面几乎是既定的事物带来变化。我也没想到诗歌里出现“命运”这么多,可能是一种内心暗示,对未知的世界一方面是好奇、渴望,另一方面是不安、恐惧,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有时候会在诗歌里流露出来。世间万物相连,命运这东西是与他者有联系的。当你用爱去支持这个世界,他人的命运也会往好的地方发展。比如诗歌,如果带来好的心境,带来新的认知,诗歌自然就是大地上的光。诗歌就像命运,有着难以把握的一面,但我们却渴望控制语言的流向,让词语的力量把你带往你内心的乌托邦之地。
廖琪:你在书里写道:“长着一颗背叛俗世生活的心,身体在物质主义之内,精神在边界之外,这双重的折磨,它们具有真实的幽灵般的命运,仿佛正面已经走向了死亡,它的反面未曾诞生。挣扎出诗人,诗歌是诗人展示出来的荒诞世界,一如在阴影中,我们看到光反抗着诞生。我确信,明暗之间,有一条界线,仿佛词的闪电”。赌徒的心也是诗歌的心。写作是对边界超越性的寻找。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
礼孩:因为写作与人生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有限性的人,所以渴望去寻找精神世界里的无限性。至于边界在哪里?这不是科学问题,而是艺术问题。比如地平线出现彩虹的地方,它就有了一个新的界限,彩虹消失,界限也随之消失。每个人的界限都是靠想象力来决定的,想象力强大,其边界也在无穷变大。有些诗人的内心狭窄,其边界也就变小了。边界什么时候都与变化的心灵相呼应。我们说明与暗之间有界限,就像爱与痛之间有痕迹一样,有时候是可以感受的,很多时候无法抵达,所以界限里有自由与飞扬的召唤。
四、个体的真实到群像的现实:
介入现实的质感与升华
廖琪: “今天早上,我去赶地铁,不断地/接近生活,在生存的深处”(《独自一个人》),“时代的丛林就要绿了”“我的心在疲倦中晃动/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 ” (《谁跑的比闪电还快》),“生活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那些被抵押的日子充满了敌意”(《被抵押的日子》)……
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哀伤、失意、贫穷、苦难、困境、囚徒,对速度的反抗,对抗被异化,这些诗歌呈现了个体的真实和现实。我有一处疑问是,即使你已扣响了扳机射出了批判的子弹,为何诗歌呈现出来的情状,并不是低处的沉重肉身的呻吟,无论作品内质如何,起码作品的表象始终给人“轻快”的感觉,无论多么现实残酷,你呈现出来的都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从黑暗转化为澄明的轻快与灵动,“将生命、良心、自由、希望、欢乐和悬而未决的激情置于真理和理想的庇护下”,给人高蹈、理想和浪漫的精神指引。这并不容易,除了思想的升华,精神境界的超脱,这样的诗歌美学品质,跟心性有关?是怎么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呢?
礼孩:写作是可见的,但又像暗房的工作,期待冲洗出满意的照片。写作显然是一门手艺,你得不断锤炼,才能熟能生巧。巧的发生是一种渴望与热爱。“巧”,是之前的能看见,到后面的无可见,这既是经验,也是思想发生的偏移。我们得承认天赋这件事情,我天赋不足,但多少还是有一点,当你启动后期的努力,之前残缺的天赋也会得到一些修补。我相信自我教育这回事情。我得去教育自己,才有一个生命的转变。对于诗歌的写作,你必须渴望,渴望一个乌托邦,也许你企及不了那个世界,但你内心有了那样的图景,内心的激情会一步一步帮助你去完成。
廖琪:语言的高妙,精美,又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呢?这也是我非常惊讶,觉得不可思议之处。
礼孩: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当你着迷于语言带给你的世界,你就想办法去做到。写作就是让语言发生之前所没有的折射,你就想办法去擦亮语言。一是训练自己的语感与内心想象力的契合度,二是把心力放到你的笔下,尽量去描述你以前没有描述过的事物,不去重复自己的意象与语言,不要被惯性的思维所统治。
廖琪:《条纹衬衫》是我并未过多留意的一首诗歌,经世宾的解读,一下打开了文字背后辽阔的情感和世界。这首诗是创作在何种情景,其实作为诗人您自己表达的初衷是什么,那么呈现出来后,与读者的解读是否出现偏差。(承载着较多的现实指向、信息体量,隐喻密布、意象集中、意境辽阔)
“风尝着命运的灰烬。就此别过/一个囚徒被押往徘徊之地/凭什么去解开生活的纽扣/疑问是条形花纹衬衫/穿在身上,像一个从污水之河里/上岸的人,淌着水。这包裹的水纹/渴望阳光猛烈地折射生活/阴晴不定的游戏/为躲开谜底而涂黑这个世界/一只病虎,轻盈如蝴蝶/没有蔷薇可嗅,它提着镜子与灯/寻找一件边缘潮湿的条纹布衬衫/世界需要新的编织/却从不脱下那件破烂的条纹衬衫/猫头鹰躲在口袋里,幽灵一般的视像/随时把命运带入不祥的黑色梦境”(条纹衬衫、猫头鹰、黑色梦境)
礼孩:诗歌有时可说,有时不可言。有些东西说透了,反而没有个中的那么一点小障碍,一览无余肯定不是好诗歌。诗歌存在误读也没问题。所以,对于这首诗歌,看读者内在的闪光照在哪里就看到哪里吧。
廖琪:直接书写政治的不多,《去年在朝鲜》是一首引人关注的诗:“猫头鹰在夜色里闪烁警惕的眼”“这里没有通往教堂的道,也没有去酒吧的路”“这个不为人知道的国度,一味披着神秘的面纱”“树林犹豫着,在风中展示一个假冒的真理”“大海在朝鲜是一头困兽。”“一个再自闭的地方,大海也要唱出它的歌,时间有足够的耐心等到海水蓝得心碎/封闭在贝壳里的歌声也要唱出人性的嗓音,充满群山和海洋”
即使面对政治这么敏感的话题,你也没有过激的言语,露骨的抨击或情感宣泄,隐喻暗含其中,从文字中给人读到那个国度人民的生存境遇,作为人的不自由,政治的一手遮天。结尾导向一种精神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和高歌。
你認为面对政治和负面,诗人该做些什么,诗歌要怎么不违心地表达?
礼孩:《去年在朝鲜》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首诗歌,奇怪的是这类诗歌,我后来写得少了。诗人处理的是语言与价值的问题,不存在只写光明不叙述黑暗,或者只爱成功,不看失败。不是这样的。一个好的诗人,他/她得有内化的能力,面对一个现实的题材,你得思考,如何写出其新意,写出你思考得到的部分。诗人不能太过于沉迷于现实的外部时间,必须从被支配的精神里去发现什么。
廖琪:传统文化、古典诗歌对您是否有深刻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哪里?精神层面吗?
礼孩:当然,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就像空气一般存在,你不可能脱离现实独自生活。古典诗歌是我们精神的背景,是我们的食粮,是生活的底蕴。古典诗歌与节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断把过去的时间拉到眼前,古典也成为当代的一部分。
廖琪:你会喜欢哪些中国诗人?比如苏轼?
礼孩:喜爱的古典诗人还是蛮多的,他们的生命、诗歌都充满了诱惑。至于苏轼,他的有限,他的不朽都与时间有关。在思想、文学、艺术上,苏东坡都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天才,也是大师。
廖琪: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是否有精神传承的脉络?
礼孩:当然有。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尽管形式上已经不一样,但精神是相通的。比如有时读杜甫的诗歌,你会觉得他是当代诗人,是因为他诗歌里是个人的表达,也是对人类世界的陈述,他诗歌里的愤怒、愁苦和殷切的期望都带着流动性,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廖琪:外国诗歌是不是对你影响更大一些?
礼孩:一个诗人,他/她需要更多的文化滋养,这个文化不仅仅是本土本国的,也有外来的。诗歌一直在追求民族性声望和国际性伟大,诗人应该拥有人类伟大的心灵,这样的心灵让他/她成为独特命运的诗人。早年的写作受中国现代诗歌影响,后来视野打开,国外诗歌的光也就照了过来。显然,当代外国诗歌一直影响着我。
廖琪:从五四运动的白话文,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到今天,百年了。诗歌的汉语之美,它的现代化和经典化,你怎么看?
礼孩:经典化,一直都在进行,但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一切都得时间和人类心灵来选择。有些诗歌在诗人活着的时代可能被发表被阅读,不过未来并不当表现在受欢迎就是经典化的。能够经典化的诗歌,有一部分是现代化的,有一部分需要在漫长岁月里,不同时代的读者都有共鸣。所以诗歌的普遍性是需要的,但诗歌处理语言与经验也是美学精神。经典是诗人与一代代的读者一起完成的。
廖琪: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您影响很大,我看到您写了很多他的文字。他对您的评价也是极高,他说“当看到黄礼孩诗歌的译文后,我惊叹不已。这才是真正的诗歌。”那么,你认为的好诗是什么?怎样才算有“诗”味。
礼孩: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先生对我有影响,他认清了偏见与不公正,他诗歌在处理现实题材时没有纠缠于现实,而是写出他自身切实感受到的世界,在个人经验里呈现了世界经验。我很高兴,他读了我的翻译诗歌之后,给予我的鼓励。所谓的好诗,虽然因人而异,但还是有一个共识,首先不是语言上的陈词滥调,诗歌要有想象力和语言上的更新力,能够为读者创造一个世界,你在阅读之时,能体味到其中的微妙。
廖琪:我在你身上发现了你所做事的共通处,诗歌、建筑、舞蹈、音乐、影视、装帧设计、文化活动、美丽的女孩……爱所有美的事物,痴于人间一切美好,一个心灵上名副其实的美学家。
礼孩:过奖啦,艺术家生活多少带着想象吧。我们几乎总是生活在物质的前面,我只不过想在平庸的人生里活得有点乐趣而已。
廖琪:你说:物化时代,大众远离当代诗歌,却又热衷于诗歌的种种秀场。那么,这么多年你策划了各种诗歌活动、文化品牌活动。(冒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活动是作秀)新年诗会、文学散步………吸引了怎样一群人,于一座城和普通市民是怎样的一种在场?
礼孩:你说的,也许就是生活的矛盾之处。不过,所指不同。普通市民有他们的生活仪轨,他们不关心诗歌等审美事物,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喜欢诗歌,但他们又有随大流的特点,所以得有更好的东西给到他们。新年诗会作为一种创意文化,它适合引领普罗大众。
廖琪:勘探一个人的过往和现在,探究他之为他的缘由,是非常令我着迷的一件事。我一直还有个疑问,你怎么可以做到那么谦和、谦卑、微笑、不温,又如海一样深邃深沉,谜一样叫人着迷。
礼孩:谁的人生不千疮百孔?你这是逗我吧,我有吗?如果有,我将视为一种荣耀;如果没有,这是一生的努力。
廖琪:如果给你选择,你想做自然界中的什么?植物动物还是一刷光?
礼孩:做诗人安德拉德的“一只鸟”吧。他在《等待》中写道:“时间,无尽的时间/沉重,深邃,/我将等待你/直至万籁俱寂/直至一块石头碎裂/开放成花朵/直至一只鸟飞出我的喉咙/消失于寥廓”。我希望自己是这么一只時间之鸟。
廖琪:是否还有梦与困惑,甚至恐惧……
礼孩:梦与困惑,恐惧,什么时候都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