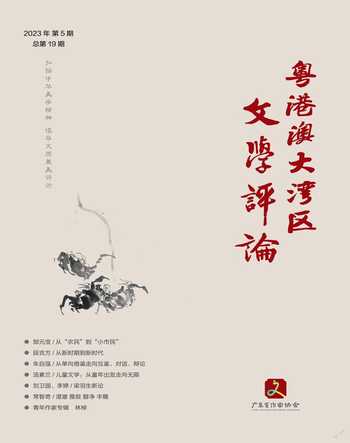复兴论、现实主义与涅槃之光
张智谦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百年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怎样采用新的历史视野以获取新的历史启示,是当前学界亟须讨论的一个命题。《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抓住“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文学史的叙述范式,超越“启蒙”与“革命”等习见的话语体系,从复兴论的角度重新梳理新文学史,又以敏锐的目光与独特的视角审视了近年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实践。该书从百年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第三种范式—复兴论、极具时代意识的现实主义新辩、近年创作中所闪耀的传统涅槃之光等三个层面,以宏观审视与微观透视两个维度,将中国文艺复兴的话题引向了更加深入和阔大的境界。
关键词: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复兴论;现实主义
一 、复兴论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五四是无法绕过的存在。百年前的那场文学革命,将中国文学截为泾渭分明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段。“古代”与“现代”之间的“断裂”乃至“对立”关系,已广为人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大量成果皆表明,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盘反传统。以现在的视野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是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些著述在反抗傳统的显象下,潜藏着五四主将们接续并复兴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愿望。
然而,学界在确定中国文学传统并非因五四而断接后,又出现了文学研究的思维定式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生发展的历程本就与西方文化思想、文学作品的流入息息相关,加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理论热潮,致使中西维度的研究占了主流,成果虽然丰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来源于中国文学传统,如今应无人否认,但中国文学传统在何种层面上介入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即中国文学传统如何在中国新文学中涅槃?它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若以学界“中西维度”与“古今维度”的研究范式、“启蒙史”与“革命史”的研究视角来进行探究,很难在已有成果之上有所突破。
在百年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启蒙论”与“革命论”早已作为根本的方法论或一种根本的历史观,然而它们却各自存在着难以自我解决的理论问题。“启蒙论”以西方视界审视中国,中国成为客体,主体性与他者性的问题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个性与差异性被消融。“革命论”拆解了现代启蒙话语逻辑与思维定式,却缺乏中西平等对话,容易陷入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为何是“复兴论”?事实上,自晚清民国以降,现代中国的复兴便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目标,因而中国的复兴形象也就成为众多作家着力书写的目标。无论是以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的,坚守中华民族国家本位的近代知识分子们构建的中国形象,还是新时期以阿诚、莫言、陈忠实为代表的,力图在中西文化平等对话中,重镀民族自我的作家们所构建的中国形象,都有力证明了“复兴论”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文学历程,无疑是切中肯綮。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复兴论”取代“启蒙论”与“革命论”,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研究线索过于错综复杂,仅以单维度进行审视,终归是盲人摸象,难脱窠臼。李遇春教授充分意识到了现有研究范式在这一话题中存在的局限,因此他秉持“兼容并包主义”“多元共生主义”的态度,以第三种范式——“复兴论”对五四以来的中国百年文学历程进行了回望与审视。
“复兴论”早在《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的姊妹篇《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得以体现。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李遇春教授纵横捭阖,尝试重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相当完整地梳理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现代中国的发生发展历程。此后的四年间,李遇春教授又继续梳理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文艺复兴思潮及其复杂因子,《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得以问世。该书的文章皆聚焦于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目标和归宿,指向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
在首篇《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三题》中,李遇春教授从复兴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历程,梳理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三次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新文学主将开始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致力于中国文学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复兴。第二次是“五十年至七十年代文学”时期,中国古代的话本、章回体小说、古典诗歌传统全面复苏。第三次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以寻根文学运动作为显著标志,寻根文学及其思想,作为一种文学精神,贯穿于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李遇春教授在对这三个阶段的描摹中,生动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文化碰撞所实现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激活与重构,并从文本和文化两个层面,精要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创造性转化文化传统方面所取得的瞩目实绩。
接下来,李遇春教授从“启蒙”“革命”“复兴”三个关键词继续深入,从“文艺复兴”的源头说起,重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与基本轮廓。或许是忧心读者误解他忽略或贬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他明确阐明:“与启蒙或革命话语体系相比,中国的文艺复兴话语体系更加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它不是简单地将中西和古今二元对立起来处理中国问题,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借助西方现代文化和文艺的外力来激活或复活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资源,最终达成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这三者是可以共存互补的,它们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史和文学史。”1“复兴论”的优势显而易见,它不仅恪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位立场,还具有罕见的包容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在李遇春教授看来,“无论启蒙还是革命,最终的历史目标都不可能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不论是启蒙性质还是革命性质的文学形态,大抵都可以纳入中国的文艺复兴话语体系中予以重述”1。
为了证实此观点,李遇春教授开始以“文艺复兴”的角度重述中国当代文学后四十年。若以习见的文学史观念来看,“寻根文学”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段历史潮流,然而李遇春教授却提出,“寻根文学”不仅仅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学思潮,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潮”。他认为,无论是在所谓“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中还是“新世纪文学”里,“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显在或潜在的整体性创作潮流可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2。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带领我们返回了“寻根文学”运动的现场:从韩少功的理论解析到具体文学脉络的进程绘演,再到 “新时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兴盛、“海外新儒家”思想的回潮与流行以及长篇力作的剖析。这一段历史的展开,有力印证了李遇春教授的观点,其中的精彩论述,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寻根”思潮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文学史中的勃勃生机,也展示了当代中国作家在不同程度为推进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所做出的努力。
二、现实主义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主流,“现实主义”已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并继续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創作指南”。与此同时,“现实主义”随着历史语境的转变与众多学人的延展,获得了许多面目与名号,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等。此外,因为每个作家、研究者心中都有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口袋,吸收各种异质术语,扩大自身的定义范围。如今,“现实主义”已然成了一个理论与话语纠缠的高度复杂体系,以至于难以给它下一个清晰的、有共识的定义,这种被理论话语体系层层包裹的“现实主义”,无可避免地遭到了模糊化与污名化。因此,李遇春教授在“复兴论”之后,将论述的焦点放到了“现实主义”之上,力图解剖百年来高度纠缠的理论话语体系,将之“还原”为本真的样态。
为了真正理解“现实主义”,系统地梳理“现实主义”自百年前译介到如今的流变史,也许是最为稳健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层层剥茧,厘清缠绕不清的理论话语体系,同时也以史为鉴,为中国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贡献。然而,此类研究在学界并不乏见,已有不少成果。更重要的是,若将论述聚焦于历史流变之中,百年来层层叠叠的话语体系,不仅会极大程度地干扰论者的最初目的,枝蔓纵横的理论延伸也很可能会使读者在叙述中迷失方向。或许正是因此,李遇春教授并没有选择文学史论,剥开纠缠复杂的“现实主义”,而是直接将其拆分为“现实”与“主义”来重新理解,也即是胡适所说的“多研究些现实,少谈些主义”。如此便直接抓住了“现实主义”之核心“现实”,把握到了研究对象的意义内核与价值本体。李遇春教授写道:“对‘现实的发现永远高于对‘主义的崇拜,因为‘主义是灰色的,而‘现实之树常青。”3
李遇春教授进一步分析,“现实”并非平面概念而是立体范畴,它由看得见的“现象”与感受得到的“精神”组成。“现实主义”着力于实境书写,“现代主义”执着于虚境书写。但无论是现象还是精神,实境还是虚境,都是“现实”的一种。“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往往执着于实境书写,而现代主义则对虚境情有独钟”1。在对“现实主义”的意义内核进行探寻后,李遇春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问题。他认为,“现实主义”并非包治作家创作困境的灵丹妙药,当下中国作家们并不缺乏各种“主义”,缺乏的是对转型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体会与探究。只是躲在书斋中向壁虚构,停在生活表面浮光掠影,用理论肢解真实生活,最终是无法抵达文学创作的化境。文学创作必须像鲁迅先生那样,不仅要勇敢地透视与解剖中国的现实与现实的中国,而且还要发现日常生活中所掩盖的心理现实与精神真相。
对“现实主义”进行深刻阐释后,李遇春教授开始对“新写实主义”沉寂后的发展一探究竟。从五四启蒙语境的“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语境的“革命现实主义”,再到改革语境的“新写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和文学旗号的“现实主义”已有百年历史。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不仅在“圈外”失去了轰动效应,“圈内”学界也不再热情于为新的文学潮流命名。“新写实主义”口号渐渐冷却,其旗号也渐次沉寂,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主义”的终结?答案是否定的,毋庸置疑。但问题是,“现实主义”这股文学创作潮流去向何方了,它新的艺术面目是什么?学界虽然有着一些零散的文学新旗号,例如“新历史主义小说”“新都市小说”等,但都无法容纳“现实主义”的新变。李遇春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微写实主义”。
“微写实主义”是该书的创新性的成果之一,也最能体现李遇春教授的学术原创性。百年前,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甫一登场,便被冠以了“写实主义”的名号,“写实”是一切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共性。“微写实主义”则是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艺术变体。李遇春教授给出了清晰的定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潮流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文学新方向与艺术新形态” 2“微写实主义”就是“新写实主义”的艺术延伸物,是“新写实主义”在艺术延伸和神话的轨道上走向成熟乃至极致的产物。3李遇春教授追根溯源,进而分析“微写实主义”的发生与形成。自《诗经》以降,“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潮,“微写实主义”得以在中国本土文学土壤中生根发芽。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文学传统,直接催生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微写实主义”文学潮流。如果说“新写实主义”主要还是外国文学思潮“中国化”的产物,那么“微写实主义”就主要是中国文学传统自身“蜕化”的结果。无疑,“微写实主义”也是中国文学传统涅槃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宏观阐释之后,李遇春教授开始分析“微写实主义”在具体作品中的不同表现。在李遇春教授看来,“微写实主义”有着两条艺术路向。一是以贾平凹《废都》为代表的描述型“微写实主义”,以客观地描述与精细地呈现为艺术取向;二是以陈忠实《白鹿原》为代表的分析型“微写实主义”,以冷静的理性思维和笔触为特点。两种艺术路向都以呈现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象为核心。自“陕军东征”后,中国长篇小说热潮中恰好涌现出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取向:偏重于描述型的“微写实主义”有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刘震云等等;偏重于分析型的“微写实主义”则有莫言、刘醒龙、余华、格非等作家。这些作家在“写实主义”创作上虽有所偏重,但都在“写实主义”的道路上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三、涅槃之光
“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代表着它的新生,其根在过去,花在当代,果实仍在未来。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今,无数作家致力于此,这场意义深远的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运动远未终结。不过,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1。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们来说,如果仅墨守中国文学传统,而无创造性转化,那么“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于批评家而言同理,如果仅只墨守过去的范围与范式,那么文学研究也如一潭死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一样会成为镜花水月。这项伟大的事业必然需要两者齐头并进才可达成。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们创作了不少作品。李遇春教授聚焦于此,发现了贾平凹、刘醒龙、欧阳黔森、姜天民、迟子建、乔叶、张好好七位作家在继承并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的努力,他以历史理性与价值构建为着眼点,采用微观透视的方法,分析了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涅槃之光。
李遇春教授对贾平凹三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回溯式的小说美学考察,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小说艺术形态变化与“微写实主义”的成型。李遇春教授指出,贾平凹的“微写实主义”不仅反叛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的创造性转化。李遇春教授以《极花》为例,集中论述了贾平凹“微写实主义”的特点:一是客观冷静、含蓄深沉的超越性精神姿态的“不二之法”,二是将以简驭繁、化实为虚的新“闲聊体”,三是细节与场面结合的“时空型”、四是多元人物群像的“块茎结构”。可以说,李遇春教授对贾平凹创作阶段性变化研究,既是以新的视野与谱系深化过去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发现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涅槃的重要成果。
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而言,小说艺术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并非其内涵的全部。古人云“文以载道”,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涅槃”,同样承载着作家们对于当代人格的一种理想塑型的愿望。对于这一点,李遇春教授选择了湖北作家刘醒龙作为范例进行论述。在本书中,李遇春教授着重分析了《蟠虺》与《黄冈秘卷》中的文化人格。《蟠虺》中的主人公曾本一因两种文化人格,即理想主义的圣贤人格与功利主义的俊杰人格的激烈冲突,而产生了内心的坚守与沉沦、挣扎与救赎。《黄冈秘卷》中的三种黄冈人格,即接受政治文化改造所形成的复杂人格、由儒家现实功利人格传统转化的人格、本土化的黄冈地方文化人格。李遇春教授指出,“在这两部长篇近作中,刘醒龙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重塑中国传统的创作倾向。一方面,刘醒龙在长篇写作中着力挖掘中国文化传统资源在当代中国民族性格重塑中所扮演的反思现代性功能;另一方面,他还在倾力尝试中国文体传统资源之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文体重塑的可能性,两者均指向了中国传统的重塑与再生。”1这个评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刘醒龙两部长篇小说的核心价值所在。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极为重视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古人不仅托物言志、寄情遣怀,同时也发展出对于自然天地的叙事传统,即博物传统。博物传统源远流长,《博物志》《山海经》是古代博物叙事的经典之作,在当代作家之中,来自贵州的欧阳黔森便有意识地承袭了这一传统,在其小说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李遇春教授指出,欧阳黔森走的是一条现代博物体知识性叙事之路,他把专业的地质学知识融入到小说的叙事与故事中,运用诗意的笔触去摹写贵州的地理风物。“他尝试着从不同的艺术路徑将自身的专业地质学知识、地质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融入小说叙事中,给传统的博物体小说灌注了现代科学精神与人性内涵。”1除此之外,李遇春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欧阳黔森的小说抓住了贵州历史上各类奇人异事,此为中国古代传奇传统。欧阳黔森的博物传统与传奇传统都统一在其对贵州边地文化的艺术书写中,“从这个意义上,欧阳黔森的小说世界无异于一部文学性的贵州地方志,它悄然续接着中国古代地方叙事传统”2。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最能够体现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觉吸取与改造的,也许是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李遇春教授指出,这本小说所取得的实绩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于叙事上。《伪满洲国》有机结合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两种叙事模式,采用“纯编年体”作为外部结构,依靠“准纪传体”为内部结构,以编年纪事结构贯穿人物空间组合结构,实现了编年体与纪传体两种叙事模式在当代中国历史演绎小说中的立体复活,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时空观念的改造与重构。其次是在人物群像上,为了使众多人物自由地发声,迟子建汲取了《红楼梦》《金瓶梅》中的中国化日常生活叙事手法,彰显了以战乱中的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性深度为艺术重心的现代小说叙事传统。最后是在反讽寓意艺术上,《伪满洲国》的现代荒诞意识和反讽艺术,蕴含着作者对中国明清长篇小说奇书文体传统的继承,同时小说以现代人性人道主义思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情感,使之与古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儒道释思想话语体系区别了开来。综上,李遇春教授完整地展现了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如何汲取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资源,以现代灵魂重构了中国古老的长篇历史小说叙事传统。
结语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只是学界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业已成为主流意识所明确提出并倡导的文化发展趋势。但正如於可训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一旦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一种流行观念,就很容易沦为谈资,失去它原本包含的问题意识。因此,要论述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不仅需要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较深的功底,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密切关注。较于前作《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进行了写作倾向上的调整,即从形式上出发,进而更深层进抵到了文学的思想和文化内容层面,将中国文艺复兴的话题展得更开、更广、更深。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是一个长远的使命,中国当代有无数作家正在朝着这一方向持续迈进,李遇春教授也会如於可训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新著问世,以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之助”4。
1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4页。
1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4页。
2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4页。
3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8页。
1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7页。
2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9页。
3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74页。
1 [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0页。
1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81页。
2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98页。
4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I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