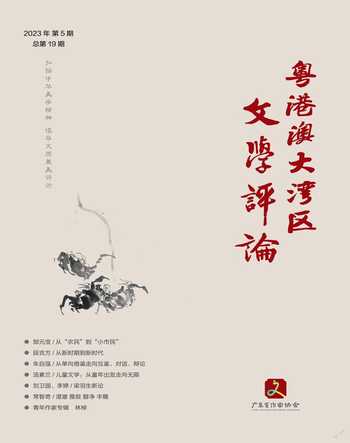整体视野·典范建构·多元共生
王艳芳
摘要:黄万华先生以一种“逐日”之学术精神,数十年来孜孜矻矻、不事喧嚣地从事着“百年汉语文学史”的“补天”“填地”和“融通”研究。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海外华文文学进程的关系考辨中获得的整体观视野为观照,通过史料的挖掘和打捞,对既往文学史论述中的缺漏和断裂进行卓有成效的填补和缝合;并在互为参照的辩证思维中,以跨界对话的方式思考并推进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典律建构及其实践;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段、区域、个体华文文学作品的差异性进行综合分析和艺术审美,提炼并升华出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中多元共生的华文文学史观。
关键词: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文学史观
2022年6月,黄万华先生著《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下)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皇皇80万言的巨著,不仅是他多年来潜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术成果的集其大成,而且标志着由其个人撰写的“华文文学三史”(以下简称“三史”)全面告竣。所谓“三史”,是指2014年出版的《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1、2017年出版的《百年香港文学史》2以及《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上编“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三史”的研究、写作和教学贯穿了黄万华先生的学术生活,也覆盖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更重要的是,“三史”的文学进程都按照三个历史时段展开:即二战前、二战后和近30年,由于所处的世界性背景相同,民族性命运相连,地域性文学课题则在发散、相遇中产生对话、汇聚,是故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得以浮现。3著者于《百年香港文学史·代前言》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后记》中反复强调的这一共性,构成其文学整体观的重要前提。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宏观层面,通过整体性、跨越性、流动性、多元性、共时性和历时性及其互为参照的动态阐述进行文学史的整合,有效连缀并弥补既往华文文学史的断裂或缺失之处。其次,在微观层面,打捞区域文学的各种历史遗存,发掘、辨析被遗漏甚至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整理、研究不同区域和时段的重要文学期刊,填补并细化华文文学的空间全貌,同时呈现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互渗互动。再者,这不仅是个人撰写的完整而系统的华文文学史,体现出上述个人治史的创新与特色,而且与其四十余年的华文文学教学相辅相成,并代入其社会生活、文学阅读、理论思考以及经典建构的个人经验。其华文文学史观的重要关涉在于,梳理并辨析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既指向各区域华文文学和包括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内的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涉及各区域华族华人文化影响下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1最终指向在海外华文文学百年进程的现代性语境和跨文化场景中,中华文化所直面的生存现实、所经历的传统延续及其所实现的创造性转换。总之,其所体现的华文文学史观既表现为一种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又表现为一种空间视域上的整体性,同时具备特定“时空体”意义上的文化贯通性以及“多元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
一、互为参照的文学整体观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下编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论”。上编共七章,对整个百年不同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进行纵向梳理和分段论述;下编共三章,主要对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内在肌理进行横向扫描和深入剖析,涉及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中国性、在地性、世界性与身份认同的关联,百年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建构以及语言追求等专题。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千头万绪、庞杂纷繁,起点不一、进程各异,为使文学史的论述一方面符合文学发生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凸显清晰科学的历史线索,论者采取了时间脉络上的三分法,即早期海外华文文学、战后海外华文文学以及近三十年海外华文文学。其中“早期”是指“海外华文文学诞生后至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这个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在于“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伸”2;“战后”则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近三十年”则主要指1980年代以后的三十余年。这种时间上的分段显然不同于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也不同于其他版本的华文文学史体例安排,其文学史观的超拔之处不仅在于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內华文文学创作本身呈现出来的历史性差异,而且特别关注不同时段之间的历史性连续,从而将不同时间段落中的华文文学以分段的方式进行了无缝对接式的勾连,从而实现了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真正视为一个时间整体的文学史书写实践。
与此同时,在科学的时间分期之外,还有着极其有效的区域划分。在历时性这一主体线索之下,对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文文学进行了共时性的分区论述。遵循着文学史体例的时间线索,聚焦东南亚、北美、欧洲这三大华文文学板块的同时,兼顾作为后起之秀的大洋洲和东北亚华文文学,并在“近三十余年”这一文学史时段中给予充分论述,体现出空间视域层面“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视野及其文学史论述。由于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发生和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华文文学的传统板块,因此在具体的论述中史论结合、以点带面,不仅梳理了早期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美国、加拿大等作为国别的华文文学的历史,而且对这时期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论述和审美分析,如邱士珍、林参天、铁抗、林语堂、陈季同、盛成、蒋彝等的海外创作,并充分结合早期欧美的留学生文学和旅居文学现象展开相关分析,同时根据扎实的文学史料尽可能还原当地华文文学发生的现场。战后东南亚华文文学不仅分头论述了马来亚、新加坡由联邦到独立过程中华文文学的分合与崛起,同时增加了对越南华文文学发展的介绍;除了重点展开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格局、现代主义发轫,新加坡华文文学“六八世代”的崛起等重要文学潮流和现象的论述之外,对韦晕、商晚筠、李永平、潘雨桐、陈瑞献、郭宝崑、王润华、淡莹等重量级作家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主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和论析。
战后北美、欧洲地区的华文文学部分除了关注旅美台湾作家群现象和欧洲华文文学的气候渐成之外,重点论述了活跃在北美的鹿桥、黎锦扬、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杨牧、王鼎钧等的创作,以及欧洲的程抱一、熊式一和韩素音等人的作品及其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近三十余年的海外华文文学则在重点关注东南亚华文板块之外,给予欧洲华文文学相当的重视,主要论述了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瑞典等国的华文文学以及赵淑侠、杨练、林湄、鄭宝娟、虹影等代表作家的创作,以详尽扎实的作品分析客观论断作家的文学史价值;北美等地区的华文文学主要分析美国、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崛起与成熟,所涉作家众多,且都是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界最为活跃、最大程度参与世界文学建构的一群;同时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的华文文学状况巧妙融入本章的论述,既关注到近年来大洋洲华文文学发展的最新态势,同时亦补足了与中华文化联系较为密切的东北亚华文文学创作。以上对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论述不仅一以贯之地采取了整体观照的方法,而且注意到其历史脉络中的重要节点和时段,并始终强调波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各地区华文创作的影响,同时充分注意到战后不同区域华文文学思潮、现象及其文学史脉络的转换和嬗变。
众所周知,黄万华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沦陷区文学研究,初始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1,随后扩展至华北、华东沦陷区文学2,姑且不论沦陷区文学研究在彼时所面临的风险,也不说其史料搜集的艰难,仅是将沦陷区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整体的必要构成部分的文学史整体观,就显示出极为超前的学术探索精神,其对文学史论述空间的开辟、掇拾和连缀,对文学史论述时空构成的思考就此开启。将沦陷区文学置放于整个抗战时期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并以此为基础和契机,展开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内的二战以及战前战后文学研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开阔的整体观文学视野中,之前被遗漏、被忽略或被遮蔽的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新马文学,包括美华、欧华、澳华文学等悉数以独特的形态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于是,黄万华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一方面打通了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时间,从晚清到二战,从二战到冷战,再到近30年,实现了纵向勾连;另一方面缝合了百年文学史叙述的空间,从东北沦陷区、上海沦陷区,到新马、台湾、香港,又到欧洲、北美,直到澳洲、东北亚,实现了大陆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横向联结。在纵向打通和横向跨界之后,还实现了不同时空、种族、文化的差异性跨越,融通了不同时空体内的文学内涵,在实现某种程度跨文化对话的基础上,构建了广博而浩瀚的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共同体。“互为参照”的文学整体观不仅体现在对于不同历史时段及其之间连续性的强调,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及其之间影响关系的重视,还特别注意到文学媒介在不同时空体中所起到的沟通和引领作用,尤其是纯文学期刊在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群形成中的无可替代作用,如马来西亚的《蕉风》、美国的《华侨文阵》、台湾的《现代文学》《文学杂志》,香港的《文潮》《文艺新潮》等不下几十种。
事实上,黄万华先生的文学整体观由来已久。他曾借用约翰·多恩的“没有谁是个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土,整体的一部分”来强调人类对生命整体意识的诉求,认为“生命整体意识正是我们力图将祖国大陆、台港澳、世界各国华人的创作整合成开阔而又有典律倾向的文学史的立足点”。正因为其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摹画并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面貌”,所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意义仍在于沟通祖国大陆、台港澳、海外各国这多个空间存在的汉语文学的血脉联系,去除单一立足于某一地区可能造成的对文学的遮蔽,让各种文学得以相遇,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1当然,这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在操作层面,亦有其辩证和包容的方法论:“如果说,历史的整体性是以包含丰富的差异性为前提,呈现开放性的话,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恰恰在尊重差异、不连续性、相对自律和不平衡发展性中将各地区、各国别华文文学联系起来考察,既坚持隐含在总体性中的方法论,又关注对于种种‘裂缝‘异质等分析,而当这两者并无很大的不一致时,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就会得以深入了。”2此即“互为参照”的文学整体观。
早在《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的《前言》中,黄万华先生就开宗明义提出了其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认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统性”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内容是其“分合性”。所谓“分合性”是指“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同时发生于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社群某些历史空间的进程,并逐步衍生成‘中国与海外格局中的汉语现代文学。在这样一种文学格局中,考查其中任何一种文学,都需要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以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突破对现当代文学的人为分割。”3而近百余年的世界文学史表明,确实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中华民族文学一样,在百多年政治、经济、历史和战争风云的裹挟下,流散到社会体制、人文生态、语言习惯、外来文化等迥然不同的各种空间,形成了长期分割,甚至各行其是的文学传统。因此,“倡导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就是希望治文学史者人在本土,却能观照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而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充分接纳其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4并进而提出了典律建构这一学理性和操作性兼具的文学史整合思路和方法。
二、文学整体观视野下的经典化建构
如前所述,文学史研究的“越界”指向的是“整合”,“整体观”视野指向的则是“经典化”建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学界论述颇多。在黄万华先生看来,“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还是建构主义的经典观,经典化都始终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任何文学展开自身,并进入自身传统的过程都是经典化的过程,即便是当下人们对同时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也是在参与文学的经典化。”1在充分论述了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性或潜经典性之后,认为经典化必须要经历一个沉淀的过程,尽管作家们的创作已经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其经典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因此经典化问题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发生阶段和五四新文学存在着的呼应关系,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中国现代文学;那么,经历百年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其经典化的衡量标准、思想内涵和精神维度已经远远溢出了中国新文学的传统。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准则已经不适用于充满异质性的、纷繁驳杂的海外华文文学。然而,尽管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内容和表现形式却并未溢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和接受范畴,只不过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冲撞及其融合中经历了创造性的轉换。无论是马华文学、还是美华和欧华文学,无论是早期、还是战后,抑或近三十余年的海外华文文学,都具有浓重的中国情怀:“无论着眼于当前还是传统,也不管立足于东方还是西方,它们都同样‘根在中华,甚至交汇合流,共同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并使我们在二者的互为参照中看到了中国文学发展在创作范式、文学格局等方面产生的种种新质。”2黄万华先生构筑的宏大整一的汉语新文学史观,其间充满着发生在不同层面创作个体身上的曲折、变动,彼此之间互渗互动,举凡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出走”与“走出”,以及内化与缝隙、打通与分界,中国经验与善性西化等观点都是对其复杂性、多元性所进行的极具逻辑性的智慧思辨。但是,在瞩目所有这些适时性变化或者创造性转化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或遗忘其对母国传统文化的反向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华人华文文学中的散播、继承与弘扬,最终还必须回馈到其自身。
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讨论的现有准则,《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经典化的衡量标准:“‘第三元是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性所在,也是考察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视角,因为它产生于海外华人与多种文化对话的生命体验中,包含了其移民生涯的丰富经验,也体现出中华文化海外播传中的智慧。”3产生于对话关系中的“第三元”,既被视为华文文学追求的精神自由所在,也成为以跨文化对话为根本境遇与特质的海外华文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其所具备的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文化的多元指向也成为衡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的重要维度。当然,此处的“三”并非实指,而是“多”的代名词,“三元”亦即“多元”。该著中类似的观念表述,还有“第三只眼”的说法,是指超越了简单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一种更为复杂辩证的视角:“对母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都能自觉反省,认真评估,让两种文化,尤其是中西方文化展开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的对话,也让不同文化从未有过地接近。”4这无疑是立足于中西方文化对话立场上的华文文论建构,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典律建构同样具有启示作用:“这种中外文化交流的慧眼,事实上也推进了‘第三元视野中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1
据不完全统计,“三史”述及的作家超过300位,仅重点论述的作家就有127位之多。其中台湾文学62位,香港文学29位,海外文学34位。为什么是这些作家而不是其他?其筛选重点论述的作家所依据的,则是“文学的经典筛选性和文学史的历史传承性”这一价值尺度,故而进入“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既有“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如林语堂、程抱一、陈舜臣、高行健等;也有反映中华民族新文学经典性高度的重要作家,如白先勇、王鼎钧、杨牧、郑愁予、北岛等;还有对特定区域或时代的典律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如叶维廉、陈瑞献、黄锦树等;此外还有在各个文学领域中独具个性并对所在国文学极具开拓性的不胜枚举的作家们,仅马华作家就有几十位之多。此作家作品个案的选择标准,一方面验证了上述互渗互动互为参照的文学整体观,另一方面借此也可窥探不同时空体或场域的具体文化生态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多重影响和建构关系。
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台湾文学研究的论文,黄万华先生的华文研究已经走过了42年的历程,但他始终自谦“是个难务正业者。当初作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连带关注了抗战时期的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后来做战后30年文学研究,尝试将这30年中隔绝的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文学沟通,一直未能专心致志研究华文文学。”2未能“专心致志”研究华文文学的黄万华先生,反而为华文文学的研究建构了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寻绎到了最为恰适的研究方法,并积累了丰厚的基础研究成果。站在历史的总体性和文化的整合性立场对之进行统观研究,在阅读海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关注并深入论证其差异性和多元性,并有效地融合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流脉迁延与转化。更为重要的,还在教学过程中“力图揭示近、现、当代文学原本就贯通的历史血脉,探讨完成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文学历史整合的具体途径,强调在人生的感受和文学的感觉结合中的作品阅读”3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正因为如此经典化建构的丰硕成果,台湾文学才有更值得致敬和珍惜之处。
三、多元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
带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海外华文文学进程的关系考辨中获得的整体观的文学史视野,一边挖掘和打捞史料,对既往文学史论述中的缺漏和断裂进行卓有成效的填补和缝合;一边在互为参照的辩证思维中,以跨界对话的方式思考并推进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典律建构及其实践;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段、区域、个体华文文学作品的差异性进行综合分析和艺术审美,提炼并升华出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中多元共生的华文文学史观。无论早期的沦陷区文学研究,还是后来的马华文学、台湾文学研究,甚至近年的美华、欧华以及香港文学研究,都贯穿着整体性研究视野,这里的整体性既意味着汉语新文学史的历史整体性,也意味着包含不同区域和国别在内的全球华文文学的地理整体性。
从华文文学的整体性出发,在整体与局部关系构成、边缘和中心转换的动态视角中,分析中华文学在不同时间和地域中的开枝散叶及其流变过程,并于流变中探索典律的生成与建构,其中必然包含着对于不同个体之间差异性的关注与强调,这正如张福贵先生所指出的:“在差异性梳理和阐释中,黄万华实质上是从两个层面来完成自己的论述的。第一,各地区华文文学发展本身存在的差异性;第二,与中国文学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前一种差异是显而易见和毋庸赘言的,而相比之下,后一种差异性更值得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实质上应该是一种描写内容和艺术审美的个性化。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不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差异,也不只是写作者身份的差异,而是一种书写对象和文化视域的差异。”1正是这种“多元共生”的差异性存在,才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和书写,“差异中的同一”也才可以代表和诠释其人类性及其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内涵和价值追求。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风潮的影响下,黄万华先生深入到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最前沿,沿着整体观的文学史观念,不断突进和越界到台港文学,由《百年新马华文小说史》国别和文体的华文文学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最大限度地铺展研究领域并结出累累硕果,堪称完美的研究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华文文学的早期历史的梳理追溯,还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联的分析;无论美华、欧华文学与中国早期留学生文学以及旅外作家的关联探究,还是关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述,都是为了凸显这些地域的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包括中国新文学传统在内的)之间的关联,也是为了夯实其间的关联,进一步弥合裂隙,接续遗存,彰显那些在祖国大陆文学传统中被压抑,甚至被中断了的部分在海外的赓续,特别是中华传统的异地复活与全新转化。因此,其学术理想并不仅仅在于撰写上述“三史”,而是包括“三史”在内的整个汉语新文学史,如此方可将其十数年来念兹在兹的、整体的、互为参照的、跨媒介的研究囊括在内,也才可以真正和彻底地实践其文学史观。
然而,越过山丘,依然有山丘。整合所有的区域和历史时段及其文化传承之后,那被整合后的存在,在更广阔的时空里仍然只是局部和个案。没有面面俱到和完整如一的整体,任何整体都是相对于更高更大的整体的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存在。作为局部的整体,其内部生生不息的瞬息变幻和多元共生也决定了经典的非唯一性,甚至经典的非固定性,换言之,整体视野和多元共生最终所指向的典律建构本身即是动态的、时刻处在调整中的、非唯一性非固定化的行为过程。此外,不管承认与否,所有的研究者都有其个人立场和出发点,研究者的站位或发声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归属与认同。毫无疑问,黄万华先生华文文学史观的站位是中国大陆,但他在研究中已尽其所能、最大程度地采取了“换位思考”下的“互为参照”视角。因此,尽管其文学史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八九十年代社会启蒙思潮和文学史论争思想成果,但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执着更体现着一种文学研究的赤子初心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特别是近年来,世界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话语迅疾转向,伴随着弥漫全球的新冠疫情,一种似曾相识的新的文化语境已经悄然成形。于是,之前某些相对保守的观念甚至都不再能够满足意识形态话语一体化的要求,缝合的速度终究还是抵不上分崩离析的速度,整合的情怀也拯救不了各自为营的顽固。孜孜矻矻四十年,启蒙的抱负、传承的情怀,连同众声喧哗的发声语境似乎一去不返。毕竟有些东西注定会消失,那在另外一个时空场域里流传或复活下来的也许并非原来的传统,甚至越是急于缝合,所发现和面对的裂缝也会越多和越大——有时候不得不裁除那些无法弥合的撕裂,整合反而遮蔽了更多的真实。当其时,也许拆解才是解决纠结的出路,解脱束缚方能缤纷自现,或许这样呈现出来的才是本真的多元共生的原生态。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学者佛克马、蚁布思夫妇在北京大学的学术演讲,给中国文学研究界带来关于“文学经典化”1的思考,之后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的演讲则给中国学界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整体性和经验主义”2的方法。而随后这两种演讲的翻译和出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深远影响直至今天。毋庸讳言,黄万华先生的文学史观也受到其总体性的研究视野、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念的很大影响。黄万华先生由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以一己之力,在贯通整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牢不可破的、确凿而鲜明的关系存在,特别是治史之严谨扎实、周详厚重、思辨与逻辑都令人叹服,其于华文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建树独树一帜且国内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巧合的是,就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出版的同时,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3简体字版出版,这部“敞开着,由一百六十一,或一百八十四,或一百六十九个星门通向一个文学宇宙的文学史文本”所讨论的也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但它“不是完整成体系的文学史,但却是有着流动性的、始终在生成中而拒绝完成的文学史”4,“整体观”“线条型”的文学史观恰恰是其要解构的,认为只有此书的“星空图”书写体例可在一定意义上成就某种“自由的阐释”。由于站位、所置身的时代潮流和文化场域、个体所累积的知识谱系等的不同,文学史观的大相径庭很容易理解。对于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来说,即便面临沉默如金抑或千篇一律的现状,依然不乏以复杂思想和创造性思维重新开启众声喧哗局面的未来可能,何况研究者们还正在进行着不同形态和观念的书写与研究呢——这不仅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多元化案例,或许还正是人们所期望的“多元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和书写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编号19BZW1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编号19ZDA27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编号22&ZD280)的阶段性成果。
1 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2 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3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后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1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66页。
2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1 申殿和、黄万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 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 黄万华:《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 黄万华:《前言:面对台湾文学,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现当代文学史观》,《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4 黄万华:《前言:面对台湾文学,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现当代文学史观》,《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31页。
2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81页。
3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31页。
4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87页。
1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07页。
2 黄万华:《后记》,《越界与整合:黄万华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3 黄万华:《后记》,《越界与整合:黄万华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1 张福贵:《〈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相关话题》,《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1 [荷蘭]D.佛克马、E.蚁布斯:《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加]斯蒂文·托托西演讲:《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美]王德威主编;张治等译:《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4 宋明炜:《“流动性”与“此时此刻”——关于〈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读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