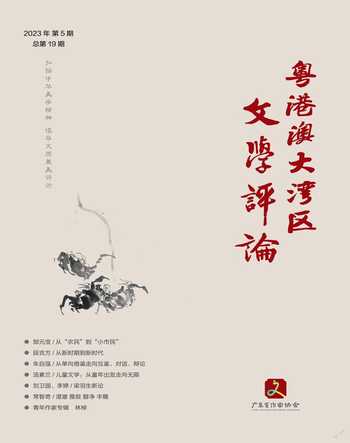托物起兴·节奏抒情·文人品格
翟传秀
摘要:作为一位地域性的散文家,黄国钦创作有風格独特的地域文化散文。黄国钦地域文化散文的风格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物”的书写。它不是单纯地描写地域文化风物、人物,而是采用托物起兴的方法,书写了具体而独特的“物”,使之携带着丰富的情感元素及文化基因。其次是“情”的抒发。它不仅仅进行了诗意化的倾诉与审美情感的表达,更为内在的,是它不断进行着由“物”及“情”的连接与转化,创造出一种虚实交替的情绪节奏。最后是文人品格。在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中,一座城市的独特风物、人物,汇聚、转化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风情与精神,反映出黄国钦对历史与当下、自然与人文、乡村与城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关系的思考,体现了他直面当下的当代文人精神气质与思想立场。
关键词:黄国钦;地域文化散文;托物起兴;情绪节奏;文人品格
在黄国钦的散文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与风格性的作品,是书写潮州这座城市地域文化的散文。除此之外,黄国钦还创作有书写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散文,同样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之所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不只是因为其描写了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的风物、人物,阐发了诗意情感与文化精神,而更是因为其以“物”起“情”,发掘出“物”的代表性、生动性,并在书写“物”与“情”的连接、转化过程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内在情绪节奏及艺术品格。作为当代文人精神气质和思想立场的体现,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创作在当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思想魅力,它使得地域文化变得有机而生动,既是历史的、显性的、实在的,也是当下的、隐性的、精神的,有了更为清晰、丰富和深入的呈现。
一、托物起兴:独特风物与人物的
选取与书写
“一个有自己独特和独一想象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作家。”1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总是以一地区或一城市特有的风物和人物起笔。这些风物与人物不仅仅是被作家描绘和书写的客体对象,同时更是激发作家情感和想象、拨动作家心弦的精神性存在。可以说,独特风物和人物的选取及想象书写,在黄国钦地域文化散文中发挥着类似于“兴”的重要功能。“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1,“兴”即诗人将感情寄托、倾注于所见之物,创造出生动、具体的诗歌艺术形象,以此为发端,触动并激发人的情感与精神,为后面所咏内容作铺垫。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便是创造性地书写了一些特殊的风物、人物,以托物起兴的方法,来引事、起情;用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或物象吸引读者,调动读者的审美情趣,引导读者带着兴致和好奇展开阅读。
在书写潮州地域文化的散文中,黄国钦精心选取了潮州独有的山川风物及历史人物,作为散文的开篇以及叙述线索。由此说开去,其散文就构造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生动,并且独一无二的文化背景和情感基调,令读者随读随感、身临其境。例如,在《烟雨潮州》中,黄国钦就从潮州的“水灵地气”起笔,以诗化的语言,具体地描绘了潮州的雨、水、池、井。读者也就一步步跟随着作家有关“物”的文字描写去感受潮州,漫游在潮州的街、巷、民居之中,观赏了潮州独特的木雕、石刻,领略了潮州独特的人文景观,如韩公祠、湘子桥、石牌坊、莲花井、晴雨亭等。通过散文这般对潮州山光水色、风俗民情的开掘与书写,读者得以具体地感知这一方水土孕育出来的独特潮州文化,更好地品读潮州这本“1600年的大书”的意味,真切体味到这一方钟灵秀气的土地上女子和男子的聪敏好学,以及诗书传家的传统。
还如《向南的河流》这篇散文,黄国钦以一条河流的历史为开篇及叙述线索,围绕着河流的历史,讲述、想象了潮州这座城市里发生的历史故事。这条河流便是韩江。也许,很多人都会将韩江视为潮州的标志性风物、景观,注意到韩江对于潮州的重要意义,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如此详细地记述并想象这条河流所承载的,甚至是参与建构的城市历史与地域文化。在这篇散文中,有关韩江的书写,亦串连起诸多潮州独有的风物与人物,如韩愈、吴均、方耀等几任州官,如南北大堤、广济门城楼、“水板”、祠堂等。这些风物与人物看似平平无奇,在现实生活中也较少被人关注,有些甚至已经被人忽略、遗忘,然而,在黄国钦的笔端,它们却成了潮州地域文化的具体象征,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承载着一座城市、一个地域令人缅怀的岁月与神奇。正如黄国钦所言,“一条向南的河流,牵动着我和我的心灵。南方是一种宿命,就像这条河流,就像我。河流走了几千几万年,还在这里,我长了10年又10年,还在潮州。潮州历史的音容笑貌,潮州往昔的好事歹事,就烙印在我的基因里”2。于是,跟随着黄国钦对于韩江等独特风物、人物的书写,读者也得以跨越朝代、穿越古今,在纵深处真切地感受潮州历史与文化,看到韩愈们“以天下为己任”,亲力亲为地祭鳄、治水,也看到历代人民因为感念他们而举办的祭祀活动;看到一条长堤“记载了无数故事”,也看到韩江正在继续“向我们讲述她浩浩淼淼的故事”。类似地,《韩江流过潮州古城》《千古风流潮州城》等散文同样是托物起兴,选取了韩江、韩愈、韩公祠等特殊风物、人物作为重点书写对象,营造出具体而生动的诗意氛围,凝聚审美情感,引领着读者于不自觉中贴近、深入和体味潮州的地域文化。
带着由自身成长的地域环境所培养的文化敏感性,黄国钦还创作一些描述其他城市地域文化的散文。其中,他更是敏锐观察、感知到不同城市的不同地域文化,选取了一些独特的“物”作为代表意象来展开创作。比如《在北京下馆子》中,黄国钦就通过写自己在北京下馆子的经历,描绘出北京这座城市的素描图。这一书写起点,与其他作家单着眼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古城楼等历史建筑相比,的确是一个更为新颖、同时也更具烟火气的观察视角。由北京的馆子入手,黄国钦带领着读者一起,领略了其中蕴藏的文化基因与城市精神:“除了能品味北京人幽默风趣的脾性儿,还能感受到北京人那一种纯朴醇厚的人情味,领教领教他们的热心肠。”1除此之外,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中还书写过上海的车站广场与洋楼,广州的街头与寺院,闽西和赣南的革命历史文物等特殊之“物”。在《上海,一个不逝的记忆》中,黄国钦书写了上海车站广场的嘈杂、人的精明,以及上海洋楼的陈旧与威严,通过呈现这些“物”的繁华表面,作家试图同读者一起讨论和思索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在书写广州这座城市的印象记《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广州大印象》时,黄国钦又将眼光投射到街头和寺院,读者亦跟随着作家的视角,既看到广州街头的车水马龙,也看到广州寺院的僻静、清雅;既看到广州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一面,也看到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面。总之,通过着重书写街头与寺院此两“物”在广州的并存,黄国钦意图呈现这座城市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并试图由此引导读者去感知广州的地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五月的旅行》里,黄国钦同样依据地域文化特色,选取了散文有关“物”的书写视角。一处处独特的历史遗迹和革命文物(如汀州试院等)的描绘书写,配合着作家对历史材料的诗意化想象、发挥,使得散文整体情感充盈、笔墨饱满,有效激发着读者的共情,帮助读者具体地感受闽西和赣南片片红土地上的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
二、情绪节奏:由“物”及“情”的交替
正如前文所述,黃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创作采用了托物起兴的方法,通过代表性风物和人物的起笔、书写,营造出独特、具体而稳定的抒情氛围,从而从容地推进散文的叙述,更自然地表达审美情感,引出所要歌咏或评价的一个地域、城市的文化精神。此外,这些特殊风物和人物不仅仅在开篇出现,有时它们还间隔着分布于整篇散文之中,彼此串连。于是,这些不间断、散点式的“物”的描写,与作家试图要传达、抒发的“情”之间,就形成了或隐或显的、或深或浅的有机关联,整篇散文内部也就形成了一种起伏舒缓、独具生命力的情绪节奏。
这种因“物”“情”之间的有机关联而形成的独特抒情节奏,在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中有具体的表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由“物”及“情”的交替。换句话说,在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中,首先“物”的书写发挥着“起兴”之用,它是独立的,作为一道独特工序,引渡、连通着作家想要抒发的“情”。其次,在“物”与“情”散点式的连通中,“物”也消融着自身的界限,转化为一种“情”。于是,具有实体性的、多样的“物”,向着具有抽象性的、多元的“情”,不断地发起程度不一的迭变与移位,散文的抒情就达到了一种起落有致、虚实相生的节奏效果。
《春诗——潮州元宵民俗侧记》中,黄国钦书写了潮州地区独特的元宵民俗文化。作家先是通过祭祖、赛大鹅、花灯等风俗,描绘了古往今来潮州人闹元宵的固有程式和仪式,呈现出这一传统佳节在潮州的独特形式、意味,以及它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对潮州人的独特意义。这是一次由“物”及“情”的连接与转化。然而黄国钦并未止步于这一诗意情绪的营造,他又续笔书写了当前潮州元宵节庆祝活动中新的发展、变化,“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潮州的元宵民俗,又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昔年的元宵掷佛,已经被现在的现代游乐取代了”“四海的潮州人,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谱写这一年一度的元宵花灯谊”“元宵,是传统的;元宵,是大家的”1。在这一续写下,潮州的元宵民俗又经历了一次由“物”及“情”的连接、转化,它超越了自身的物质性,有了新的、超越地域而团结四方的政治与文化凝聚力,成了“联结四海潮州人乡思、乡谊、乡情、乡魂的红红的纽带”。正如黄国钦所言,这篇散文“它的立意,就是政治的立意”2,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整篇散文抒情节奏的循序渐进,明晰两次由“物”及“情”交替的意味。在这里,作为“物”的元宵民俗,亦实亦虚,既显示了自身的历史性与实在性,也不断冲击、回应着作家的“情”,逐步携带上更多抽象的抒情信息。而这一过程中,散文本身就像是有了自主呼吸,带着独特的情绪节奏,一步步深入读者的心。
这一由“物”及“情”的交替中生成的独特抒情节奏感,在黄国钦的《向南的河流》中更为鲜明。《向南的河流》里,黄国钦以韩江为起点,将想象漫开去,带领着读者一步步接近潮州,发掘不同的“物”中承载与映射的潮州文化精神。首先,散文从韩江起笔,依次写到韩愈、韩公祠与北堤,由“物”及“情”,呈现了潮州这一方土地上生存的艰辛,探讨了潮州人民民心向背的历史成因,称颂了一位好官的品格;接着,散文又笔锋一转,重新从“物”起笔,从广济门城楼写到吴均以身祭水、几任州官前仆后继治水,并再次由“物”及“情”,愈加强调了潮州这一方土地上的奋斗与承担,赞扬了历史上潮州官民造就的传奇,表达了对潮州地域文化的深厚感情。最终,在这篇散文中,“物”不只是物,而附着上了精神价值,“情”也不只是情,而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两者自然连接、转化,层层交融、结合,虚实交替间,织就散文的内部张力与情绪节奏,散文亦由此显得韵味悠长。类似的还有散文《韩江流过潮州古城》。作家同样从韩江运笔,笔墨蘸取了潮州独特的饮食、民居建筑,于不同侧面描绘着潮州这一方地域上“锲而不舍的不屈精神”与“雅致的清纯的文化”,抒发了自己对潮州地域文化的诗意认识与热爱。在此过程中,不同的“物”的书写,都向着“情”发生程度不一的迭变与移位,错落有致地呈现着潮州地域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性。
秦牧和韩愈作为潮州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以其行动与品格,影响着潮州的民风民性,铸就出潮州的文化底蕴,塑造着潮州的城市精神。在《秦牧与家乡》《吾乡人民为何纪念韩愈》等散文中,黄国钦亦通过一个个与人物相关的故事,不断地由“物”及“情”,抒发心绪,以虚实交替的情绪节奏,将历史文化人物(秦牧和韩愈)与一个城市(潮州)的关系缓缓道来。
三、文人品格:当代文人的精神气质
与思想立场
在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中,经由独特“物”的连接,地域文化得以具象呈现,经由独特“情”的抒发,地域文化得以层次丰富、韵味无穷。其间,历史与当下、自然与人文、乡村与城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根共生的关系,被频繁揭示,然而它们是否已然熔为一炉?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亦给出了自己的观察、评价与反思,由此显示出其第三个艺术特征——文人品格。
黄国钦地域文化散文的文人品格是具备当代属性的。曾有学者归纳出中国文人传承的三个传统,即“悲怀伤感,好作苦语”“匡时济世”“眷恋自然,希企隐逸”1。在阅读中国文人如陶渊明、苏轼、郁达夫等的创作时,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其中存有类似的传统文人品格。而黄国钦作为中国当代文人,他所面对的现实与苏轼等传统文人,以及郁达夫等现代文人所处的现实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故其创作也就有所区别,呈示出中国当代文人独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立场。正如黄国钦所言,“文化文化,以文化人。文学就是化人的一个步骤”2,可以说,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所呈现的颇具当代性的文人品格,既继承了中国文人写作传统中“任性自然”的心性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同时又直面现实、不囿于感性局限,增添了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思想内容,包括对新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关注,对地域文化发展新趋向的观察、反思,等等。
《在凤凰山做客》一文中,黄国钦描写了神秘的凤凰山区,既写到关于这个山区独特的传说和故事,也具体书写到凤凰山区高峰上的天池、杜鹃花,以及凤凰茶,带领着读者走近这一方土地和文化。但作家笔下的凤凰山区不仅仅是远古的、神秘的,它还是当下的、现代的。作家从凤凰茶中发现了历史与当下的联结,发掘出“茶为什么做得越来越香的道理”,那便是因为公路修到了凤凰山区。“以前乌岽没有公路,茶做好了,茶农就要走来回10个小时的山路,挑到凤凰去卖,于是茶价就被‘杀了。这两年呢,因为有一条公路修到了乌岽的村口,现在每年茶季刚刚开始,就有很多汽车、摩托车等在了乌岽村里,一种空前的积极性就被‘等出来了”3。在这篇描写凤凰山区的地域文化散文里,作家就是以当代文人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立场,发现并揭示了公路对于乡村的深刻意义,体察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在这一地域的成功结合,他既以欣赏的目光描绘了凤凰山区传统文明的神秘风采与诗意,又不避讳现代文明对于古老的凤凰山区的影响,真率、诚实地面对了当代现实,以散文记录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同样写凤凰山区的地域文化,《那天我在畲寨逛荡》也呈现出一种当代文人品格。这篇散文着重书写了凤凰山区里的畲寨风光与畲族文化,并由畲楼、畲话、畲寨的宝物《龙犬图》展开了想象与抒情。其间,作家仍旧不仅从畲寨古老而独有的风物中发掘历史、想象历史,饱含深情地书写畲寨的文化积淀与神秘诱惑,同时,他还发现并书写了畲寨中的新事物、新变化,“寨子里在起新寨楼。地基已经平好了。向阳坡地上金光万道。……我看着夯地基垒墙壁的壮健的男人,看着扛木头挑担子的矫健的女人,心里由衷油然感到一种振奋,有新畲楼住毕竟比什么都美好!”4可以看到,对于畲寨的风光与地域文化,作家并没有过分夸饰、猎奇,没有仅仅满足于呈示其历史的、古老的、异质的诱惑性,而是真诚地书写着这方土地和文化新的发展,展现了当代文人应有的现实立场与人文关怀。
除了书写古老的乡村/山区地域文化,真实地记录其中现代文明的有效渗入,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还书写现代的城市地域文化,关注到其中遗存的历史文化印记与传统经验,呈现了一些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关系处境——和谐共处或错位抗衡,表达了自己作为当代文人的态度与思考。例如,《旭日东升》中,黄国钦书写了一个城镇——东升镇的地域文化发展史。东升镇紧邻珠江,在过去的历史中它经常受到珠江水质的侵扰,然而,近些年受益于“碧水工程”的治理,这个不起眼的城镇逐步“孕育出一个日升东方的现代版神话”,并开始致力于文化名镇的建设。在黄国钦笔下,这座平凡小城的地域文化显示出非凡的丰富性,它善于继承历史经验、发挥地域优势,既注重具体的经济建设,也尊重抽象的文化建设,表现出既面向未来,又继承过去的开放姿态,把握住了历史与当下、自然与人文、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等的关系平衡。类似的,还有黄国钦《高原纪行》中对于东胜这座新兴城市地域文化的书写。这座城市曾经是破舊、荒敝的,但伴随着国家的基础工程建设与开发,它也呈现出新的形象。黄国钦观察到这座城市的新城区里与地域人文历史相关的崭新文化建设,如“蒙古包和马鞍造型的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飘逸的哈达和绿色的草原结合的鄂尔多斯文化艺术中心”等,提炼出这座城市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关注并赞赏了其中自然和人文的相互辉映,以及其中传统与现代、历史和当下的和谐共存。
在上述城市的地域文化里,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是和谐共处的。此外,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还关注、书写了一些现代化大都市的地域文化,发现其中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等的关系错位,提出对这些城市地域文化发展倾向的反思。如《上海,一个不逝的记忆》一文。这篇散文中,黄国钦通过观察、书写上海的车站广场与洋楼,发现“历史留给上海的那一份丰厚馈赠,到了今天,反过来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难以超越的局限和莫大的束缚”1,可见,对于上海的地域文化,黄国钦持审慎的反思态度,他认为历史在其中没能得到有效转化,而与当下上海地域文化中现代性的趋势产生了对抗。虽然黄国钦地域文化散文中常伴随有忧郁、批评等格调,但却恰好共同彰显出其文人品格。其核心,仍是黄国钦所反复表达的,对于历史与当下、自然与人文、乡村与城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关系的思考,以及对于这些两两关系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期待。“远古的原始,和现代的时髦,相交相接,既匪夷所思,又理所当然。当人们了解了这段掌故,反而觉得最正常不过,感知过去,品味当下,憧憬未来,有何不可?”2
概而言之,上述创作实践从整体上反映并证实着黄国钦地域文化散文的独特文人品格,同时,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为什么黄国钦的地域文化散文会那么重视书写“物”与“情”的交融(包括采用托物起兴的手段、创造由“物”及“情”的交替),以及黄国钦后来为什么能够融合实在的史料与想象之虚构,写出《潮州传》这样一部专注于潮州地域文化发展、变迁的大书。
1 黄国钦:《拉祜的歌声》,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64页。
1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2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5页。
1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1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2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1 罗成琰:《郁达夫与中国文人传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 黄国钦:《拉祜的歌声》,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42—343页。
3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2页。
4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1 黄国钦:《花草含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2 黄国钦:《潮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