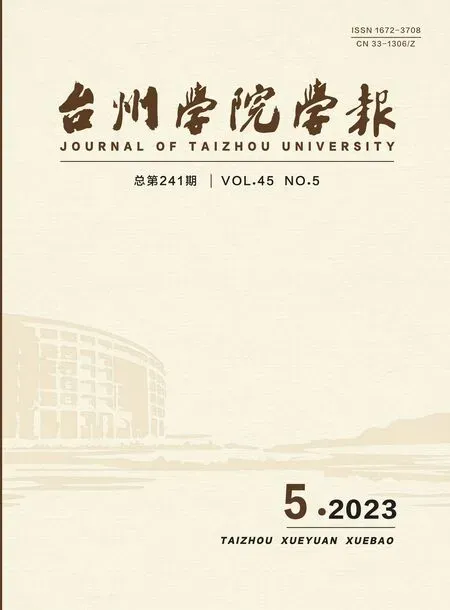西力东渐与明代火器技术的重塑
冯震宇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16 世纪开始的西力东渐与中西会通,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西方火器技术的传播成为中西碰撞和交流的一项重要历史内容。西方火器技术来华在明代主要有两波:一波是中葡战争与佛郎机铳的传入;一波是明清战争、耶稣会士与红夷大炮的传入。与清朝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传入不同,明代的这两次西方火器技术传播均是明朝政府主动为之,终而使得佛郎机铳和红夷大炮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火器。除器物之外,明代军事技术家和前线军事将领还掌握了大量西方火器技术知识,如弹道知识、操作技术、弹药比例关系等,这些新的器物和知识与中国传统火器技术相融合,使得明代火器技术发展进入新阶段。
一、中西相遇与西方火器技术来华
16 世纪,伴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展开,西方国家开始向外扩展势力,中西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频繁而有力。中西相遇的最初阶段,在根本上是军事力量的碰撞,16 世纪的中西相遇(中葡战争)是这样,19世纪的中西冲突(鸦片战争)也是这样。其中,决定军事冲突力量对比的最重要因素便是火器技术的发展水平。
(一)西方火器技术来华第一波:中葡战争与佛郎机铳的传入
葡萄牙是西方世界扩张以来第一个与明朝发生冲突和联系的国家,在16 世纪相继攻占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后,开始将触角伸向中国。正在崛起的西方殖民国家葡萄牙和东亚朝贡体系稳定结构中的明朝在经济、工业、军事方面处于大体均衡的水平,彼此均未占有绝对性优势。在此背景下,葡萄牙虽然拥有较为先进、便利的火器——佛郎机铳,但在战争中互有胜负。在战争的冲突中,以佛郎机铳为代表的火器技术得到了交流和传播。明朝开始关注这种西方火器,并进行大量仿造,使其最终成为明军的主力火器之一。
中葡之间的正面冲突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屯门和嘉靖元年(1522年)的西草湾①西草湾之战发生在嘉靖元年(1522 年),但是《明史》和地方志中记为嘉靖二年(1523 年)。戴裔煊在《明史·佛郎机笺正》中指出,嘉靖二年是指明世宗下令就地诛戮俘虏之年,而不是战争开始和进行的时间。《明实录》在嘉靖二年条下先交代了之前的西草湾之战,然后提到了明世宗处理俘虏的决定。《明史》略去了后一段文字,变成战事发生在嘉靖二年,编史者不知,致发生错误。。在这两次战争中,葡萄牙人的舰载佛郎机铳杀伤力强、精准度高,给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明军不得不以纵火船只冲击、潜水凿沉舰船等方式来损毁对方的战斗力。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明朝官员和前线军事将领认识到佛郎机铳这一西方先进火器的威力,依托在战争中俘获的佛郎机铳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了仿制佛郎机铳的技术传播过程,并很快开始推广。
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对佛郎机铳的威力及其流传经过作了如下记述:
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嘉靖二年,鋐后为冢宰,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唯恃此铳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上从之,至今边上颇赖其用。[1]
中葡海战之前,对于佛郎机铳威力的直观认识,顾应祥在《静虚斋惜阴录》中也有所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 年),葡萄牙使者费尔南·佩雷斯率领的舰队在广州停靠,等待明廷对其朝贡请求的答复时,鸣礼炮致意。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这种行为引起了明朝士人的恐慌和不满,认为其具有攻击性[2]。顾应祥还提到了彼时备倭卢都司赠送的佛郎机铳的形制,其外用木裹,以铁箍三四道束之,以防止发射弹丸时铳管炸裂;在校场试验得出其最大射程为二百步,有效射程为一百步。顾应祥还抄录了与此搭配的火药方,与中国不同。顾应祥认为佛郎机铳最适宜用于船上进行水战,用于城守也可,但用于野战则效果不佳。
其后,经过东莞县白沙巡检司巡检何儒、广东按察司副使汪鋐等前线军事将领对葡船上的技术人员的策反和对佛郎机铳的缴获,明军逐渐掌握了佛郎机铳的制造和操作技术。佛郎机铳传入中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仿造,逐渐成为一种使用频率极高的本土化主流火器。《明会典》载:
大样、中样、小样佛郎机铜铳。大样,嘉靖二年造三十二副,发各边试用。管用铜铸,长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余斤。每把另用短提铳四把,轮流实桑腹内,更迭发之。中样,嘉靖二十二年将手把铳、碗口铜铳改造,每年一百五十副。小样,嘉靖七年造四千副,发各营、城、堡备敌,重减大铳三分之一。八年,又造三百副。二十三年,造马上使用小佛郎机一千副。四十三年,又造一百副。嘉靖四十年,造佛郎机铁铳。[3]
佛郎机铳最初进入明朝视线的是其在海船上的应用,在舱内暗放,使得敌船不敢靠近,成为一种制敌利器。因此,明朝最初对佛郎机铳和其载体蜈蚣船同时进行了仿造,认为只有装备在蜈蚣船上才能发挥出佛郎机铳的威力。后经过明朝兵仗局的大量仿造和发边使用后,佛郎机铳技术深入到了中国的边防重镇。
(二)西方火器技术来华第二波:明清战争、耶稣会士与红夷大炮的传入
与佛郎机铳单纯通过对外战争传入的路径不同,红夷大炮是在明清鼎革战争与耶稣会士东来的双重背景下传入的,是明廷在面临东北边患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这一过程由耶稣会士和明末中西会通的重要人物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共同促成。历经三次赴澳购募西炮西兵,终而在火器技术、知识和器物上均实现了深度“西化”。红夷大炮在体型和威力方面远超之前的各种火器,它的传入,使得明末火器技术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与佛郎机铳相比,红夷大炮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威力巨大。红夷大炮的炮身较长,通常有丈余,这使得弹丸在铳身内获得较大的加速度。因此,无论是射程,还是击中目标所产生的威力,都是佛郎机铳和中国传统火器无法匹敌的。第二,采用前装式,封闭性好。采用后装式的佛郎机铳一直受困扰的一个问题便是在装放弹药时的封闭性问题,由于母铳和子铳规格的偏差,它们之间总会有缝隙,从而导致漏气,最终影响到铳身内部对于弹丸的推动力。前装式的红夷大炮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三,采用更精确的瞄准装置。佛郎机铳和中国传统火器仅有准星、照门等瞄准装置,红夷大炮则配置了铳规、铳矩,甚至是望远镜来进行测准,其精确度大大提升。
《天工开物》载:“红夷炮,铸铁为之,身长丈许,用以守城。中藏铁弹并火药数斗,飞激二里,膺其锋者为齑粉。凡炮爇引内灼时,先往后坐千钧力,其位须墙抵住,墙崩者其常。”[4]红夷大炮传入之后,便迅即成为明末火器技术发展的主流和标志,并最终成为明清(后金)之间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明末清初火器技术史的主要内容便是围绕红夷大炮的传播、仿制、实战为中心展开的。
二、西方火器技术传华的主要内容
历经两波西方火器技术传华的浪潮,尤其是受第二波的影响,中国传统火器技术的理论知识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充分吸纳了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理念。在火器铸造技术、倍径技术、铳台技术、弹道学知识、操作技术、弹药比例关系等方面,均形成了很多新的认识,并通过《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等火器技术典籍将其固化下来。明代军事技术家和前线军事将领在此基础上,掌握了过去未曾有的火器知识,革新了火器技术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火器技术发展的趋同。
(一)火器弹道学知识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家对物体运动进行了新的思考,近代动力学诞生。对于抛物体(包括炮弹)的运动,中世纪的理论认为是首先以直线向前运动,然后突然垂直地落在地面上[5]。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科学家塔尔塔利亚在军事方面最先对这种现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其1537 年出版的《新科学》中,涉及了弹道学和炮学的抛物线原理。但是,真正对抛物线原理做出科学解释的是同为意大利科学家的伽利略,他在1638 年出版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总结了自己先前对于物体抛物线运动的认识:“物体在竖轴方向下落作匀加速运动,在水平轴方向以恒定速度作匀速惯性运动。当这两种运动合成在一起时,该物体的运动轨迹就是一条抛物线。”[6]伽利略意识到抛物线原理在弹道学和炮学方面的实用性,在其后还推出了一些详细的数学表,上面列出根据大炮的仰角所对应的理想射程。可见,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已经开始解释火器技术的发展,并为之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
耶稣会士的东来,也将火器弹道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国。焦勖所著《火攻挈要》代表了明末军事技术家对火器弹道学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认识水平,保存了中国最早的对于弹道学认识的史料。
焦勖在《火攻挈要》中提出,应该将各种火器分定等次,挨次编立字号,并事先测出其用弹用药量、平放射程、仰放(从一度到六度)射程,统一记在一本册子之上。再依照小册子上的内容,将相关参数刻在相关火器上之后,将小册子分造三册,一本存铸铳官留底,一本存帅府备查,一本存本将教练。要求司铳军士详记所司火器的各种参数,以备演习和实战,无论战守攻铳皆所必用[7]1306。可见,这种对于火器弹道学的理解是应用于明军的火器实战的,军士开始按照炮表来操作火器。焦勖还在《火攻挈要》中介绍了不同战法所适合的不同放法,如竖放之法只用于飞彪铳,可以设为十一度(82.5°)、十二度(90°)进行攻城战;倒放之法只适合守铳,倒放一度(7.5°)至四度(30°),攻击城下之敌;平放之法最宜用于战阵,百发百中,万无一失。
但是,并不能刻板地认为平仰发弹所到之处是定则,焦勖更深层次地认识到:
盖火力迅急,多有弹已落地,仍复激起而去数里。若是,乃余气之所飘至,实非正力之所推击。此等苗头,不但难于定准,且强弩之末,虽中亦无用也。其法只以弹着靶者为准。[7]1306
在这些分析中,体现出了焦勖对于火器射击的惯性运动和有效射程这两点弹道学知识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够像西方学者那样用科学用语表述,但是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其所体现的知识原理是一样的。文中的“余气之所飘至”,即是惯性。焦勖认为,铳弹落地由于惯性所致的射程不能算作实际射程,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射中目标也无济于事,因为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有效射程必须是按照铳弹命中靶子的那一个距离计算。
(二)射击辅助工具——铳尺
西方传华火器技术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命中率高,而且瞄准技术更加趋向计量化,这一切都是由于使用了射击辅助工具,主要有铳规、铳矩、铳尺。在火器点放时,除了测铳口高低仰倒角度和射程距离外,还要对各种铳炮对应的装弹量进行测量,以使火器的点放效果达到最佳。铳尺就是这一需求的产物,最初由伽利略发明,并意图用于军事用途。《火攻挈要》将铳尺与铳规放在一起进行了解说,并配有图(见图1):

图1 铳尺形制
权弹用药之法,则以铳规柄画铅铁石三样不等分度数,以量口铳若干大,则知弹有若干重,应用火药若干分两。但铁轻于铅,石又轻于铁。三者虽殊,柄上俱有定法。无论各样大铳,一经此器量算,虽忙迫之际,不惟不致误事,且百发百中,实由此器之妙也。[7]1291
按照焦勖的解说,在两柄上刻画适应于铅弹、铁弹、石弹三种不同的铳弹的刻度,在量出铳口大小时,便可以看到三种铳弹所对应的三种刻度。此刻度值读出了所需铳弹的重量以及对应的火药使用量。因此,无论何种铳炮,经过铳尺测量后,便可以有一个数量化的弹药量需求数,司铳者照此填放即可,效率得到提高。
(三)火药与铳弹的比例关系
随着西方火器技术的传入,明朝军事技术家开始认识到弹药之比的数量关系,尤其是对于中、大型火器的弹丸与火药根据火器的不同、用途的不同进行匹配,讲求弹药相称的原则,以适应于各种战争。
明末军事将领、军事技术家孙元化结合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知识和自己的实战经验,发现各种火器所需装填的弹药重量比,常随着炮弹的不同而变化甚大。将孙元化在《西法神机》里对各种类型火器的弹药比例关系进行归纳,可以列出表1。

表1 战、攻、守铳弹药比例关系表① 可参见孙元化:《西法神机》,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技术卷:第5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0-1263页。
焦勖在《火攻挈要》中强调“量弹用药”的原则,认为小弹的弹药比为5∶6,中弹的弹药比为1∶1,大弹的弹药比为6∶5[7]1316。与孙元化论述的一般铳炮弹药比略有不同,同等条件下焦勖提出的火药量要多一点。焦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药多力猛而能远到”的效果。而且,焦勖还指出不同的铳炮适应于不同材质的铳弹,如鸟铳等使用小弹的铳炮适合用铅弹,因为其体重透甲而能伤命;大小狼机、战铳、攻铳适合用铁弹,因为其体重便于击远、攻坚、破铳之用;近距离发射的短铳适合用石弹,因为其体脆,见火碎裂,散布范围宽而击众广泛。
两广总督王尊德在其火器著作《大铳事宜》(已佚)中也提出铸铳时对于弹药比例关系的讲求标准:铸铳一千斤重,用弹二斤半,药二斤十两;一千三百斤重,用弹三斤,药三斤;二千斤重,用弹四斤,药四斤;二千七百斤重,用弹七斤,药七斤,方相配合[8]302-303。王尊德认为药少会导致送弹不远,药多会有炸膛的危险,尤其是打造制成的铳炮,不可药多。
三、明代火器技术的转型与重塑
(一)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的贡献
作为来华耶稣会士的先驱,利玛窦与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一起促成了中西会通这一历史大事件。在接触西方科学的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利玛窦那里了解到了西方火器技术的发展状况,其与中国火器技术的差距给他们内心以强烈的落差之感。通过学习,徐光启不仅成为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军事技术家,而且结交了一批精通火器之学的传教士,如毕方济、龙华民、汤若望等,联络了一批对西学感兴趣的奉教官员,如李之藻、孙元化、张焘、王徵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习和传播西方火器技术的群体,为明末引进和发展西方火器技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的那个时代,西方的军事学已经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就有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
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故智勇之将,必先几何之学,不然者,虽智勇无所用之。吾西国千六百年前,天主教未大行,列国多相并兼。其间,英士有能以赢少之卒,当十倍之师,守孤危之城,御水陆之攻,时时有之。彼操何术以然?熟于几何之学而已。可见,此道所关世用至广至急也。[9]
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西学群体奉旨编纂的《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书,其中的几何和代数学知识在军事上的应用也较为直接,为军事上设计堡垒、量度弹重和测量高远时所必需(对于铳规、矩度、铳尺等的认识即依赖这些书中提供的理论知识做支撑)。精习西方火器技术的孙元化和焦勖,在其所著的火器技术专著《西法神机》《火攻挈要》中,即包含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如火器倍径技术、铳车技术、弹道技术、铳台技术等)。明末西学群体的数学知识都来自利玛窦等传教士,由徐光启、李之藻做中介,而流布到更广的范围。
利玛窦在与李之藻的交往中,曾讨论过欧洲的军事,这些对李之藻的知识结构和对西方火器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李之藻在《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中叙述如下:
昔在万历年间,西洋陪臣利玛窦归化献琛,神宗皇帝留馆京邸,缙绅多与之游。臣尝询以彼国武备,通无养兵之费,名城大都最要害处,只列大铳数门,放铳数人、守铳数百人而止。其铳大者长一丈,围三四尺,口径三寸,中容火药数升,杂用碎铁碎铅,外加精铁大弹,亦径三寸、重三四斤。弹制奇巧绝伦,圆形中剖,联以百炼钢条,其长尺余,火发弹飞,钢条挺直,横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其余铅铁之力,可及五六十里。其制铳或钢或铁,锻炼有法。每铳约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车,有地平盘,有小轮,有照轮;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定里数,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兼诸技巧。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10]
利玛窦虽然早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便已去世,却深深影响了一直到明末时期(天启、崇祯)徐光启等中国西学群体在火器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行动。如徐光启在天启年间谈到铳台技术时,说“其法传自西国,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今略参以己意,恐未必尽合其法”[8]175-176。进而,徐光启向朝廷提出,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地,可以一面遣人取铳(第一次购募西铳),一面差人访求,并将利玛窦的门人丘良厚一并访来,以传授利玛窦在世时提到的铳台技术。这样,便借由寻求利玛窦传承下来的技术,实现了传教士入华的愿望。
汤若望则是继利玛窦之后最有名望的传教士,耶稣会最有功于中国的伟大人物之一,与利玛窦并称为耶稣会之二雄。天启二年(1622 年),汤若望与金尼阁一起来到中国。崇祯三年(1630年),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明廷召汤若望和罗雅谷一起赴京接替邓玉函的修历任务。费赖之对汤若望的评价为:“吾人得视若望为中华传教会之第二创建人。盖公教在前朝受恩宠,并得南明王朝诸王之爱护,得畏新朝之加罪也。若望虽不忘明帝恩,然视教务尤重,所以不惜迎合新主之心,遂获得顺治帝之爱敬。外省诸传教师赖此得不受内讧外侵之害。能维持教务于不坠,盖若望之功也。”[11]
在崇祯四年(1631 年)吴桥兵变之后,以孙元化、王徵、张焘等为代表的西学群体主导的西式火器部队损失殆尽,面对后金的强大攻势,朝中大臣认为精通西方数理之学的汤若望应该也懂得铸炮之术,要求其指导铸炮工事。虽然汤若望推说自己所知仅得之于书本,并没有经过实践的磨炼,但也只得勉为其难地答应明廷的请求。崇祯十五年(1642 年),汤若望铸成弹重20 磅的大炮20 尊,在城外40 里的广场上进行实弹射击试验并取得成功。明廷进而要求汤若望铸造炮身重量不超过60 磅的小炮500 尊,以便兵士出征时携带,并且在撤退时肩负而回,汤若望也应允[12]163-165。由于汤若望治历铸炮有功,崇祯皇帝“奖若望勤劳,赐金匾额二方,上勒文字,一族其功,一颂其教”。汤若望还进而对京都城墙的外部防御工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制作木制模型呈送给皇帝。
德国人魏特的《汤若望传》描述了汤若望在挽救明朝政权所做的工作:
汤若望从事枪炮的制造已经到了第二年。这时皇帝心内忽起兴趣,也令宦官们表现他们的技术,这是因为他们常在御前屡次以此夸口的原因。汤若望在这件事情上很和蔼地帮助他们……铸造大炮的工作尚未完成,皇帝即表示愿一闻汤若望对于城墙外部建筑最优形势的见解如何。汤若望拟具了一个计划,并且制造木模一副进呈皇帝。[12]117
在为明廷造炮的过程中,汤若望还口述并由焦勖整理了《火攻挈要》。该书刊印于崇祯十六年(1643 年),系统论述了西方火器的冶铸、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技术之法。该书记述的诸多西方火器技术均有独特之处,如:大型火器的模铸法、倍径技术、炮弹重量与炮膛内装火药的比例关系、铳规铳尺的使用。与中国传统火器的打制技术相比,模铸技术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它大大地便利了大型火器的制造,而且加强了其抗膛压性。这一项技术随着《火攻挈要》的介绍传入中国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到清朝时由军事技术家龚振麟创制了铁模铸炮法,与泥模铸炮法互补。该书还为不同用途的铳炮设计了不同的仰俯角度数,以图达到更好的射击效果,显示其已经认识到了射角与射程之间的弹道学关系。这些先进的火器技术理论和知识是明代的传统火器技术中所没有的,将其归结为理论知识必然会有利于西方火器技术在华的传播与融合。
(二)西方火器技术与徐光启的军事改革构想
在与利玛窦等西方耶稣会士接触的过程中,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较为深入地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火器技术是救亡图存、挽救大明王朝的利器,是反败为胜的关键。明末三次购募西炮、西兵,使得西方火器技术深入明朝内部,徐光启、孙元化等借此时机,进行了军事改革,使得明末火器技术实现了质的改变。在军事改革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传教士汤若望、陆若汉、毕方济、龙华民和同教中人张焘、王徵等人的襄助,从而形成一股以宗教关系为纽带的引进和传播西方火器技术的力量。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的萨尔浒之战以来,后金在辽东攻城略地,步步紧逼,对明军的战争从被动变为主动。面对明军节节败退的颓势,集科学家和军事学家于一身的徐光启提出一系列军事改革计划,以重振明军军威。其主要内容有三点,即多造铳器、建造铳台、构建车营。
第一,多造铳器。徐光启认为,战守利器,莫如大铳。在引进西方火器的过程中,徐光启开始着力促使来华传教士和铳师教习中国士兵造器之法,刻意访求,进行仿制。对于造铳的数量,须得小铳三百位,以实诸台;再造大鸟铳万门,以备城堵,则万全无患。而且,所造铳器要达到西方火器技术的标准——弹必合口、药必等分、发必命中,不惟易于歼敌,兼用药不多,易于防火。徐光启还提出“视远则用远镜,量度则用度板”,要求士兵用西式测准工具来使用西方火器。
第二,建造铳台。徐光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六月上《辽左阽危已甚疏》,提出各种御敌之法,其中一点便是亟造都城万年台以为永用无虞之计:
臣再四思惟,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造台之法,于都城墙四面,用大石垒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分为三层,下层安置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大铳大,周城只须十二座,形裁或小,量应加添。再将旧制敌台改为三角三层空心样式,暗通内城,如法置放。[8]111-112
徐光启建议在既有敌台之外,接建西式空心三层锐角台,此功若就,即可渐置大小炮位,以达到强有力的火力配置。这是天启六年(1626 年)凭城使用大炮取得宁远大捷后的一个总体战略。徐光启认识到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出引进的西方火器的威力,给后金军队以重创。再加之随着西炮、西兵而来的西方铳台技术(三角形制的锐角台),可以使得“闻敌仓皇,茫然定策”的窘境得到改观。徐光启从未忘却造台计划,己巳之变方歇,崇祯三年(1630 年)正月,徐光启即上疏请求建造铳台,借鉴西法铳台,意在消除射击死角,充分发挥火铳效力。然此事亦不了了之。终明之世,北京未能以西法构筑敌台[13]。
第三,构建车营。这一点是军事改革计划最核心的内容。徐光启于崇祯四年(1631 年)十月上《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提出构建车营,以增强御敌能力的主张:
臣自东事以来,累次建言,皆以实选实练、精卒利兵、车营火器为本,不意荏苒至今,未犹施用。而贼反用之,以至师徒挠败……夫车营者,束伍治力之法也。臣今所拟:每一营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然后定其部伍,习其形名,闲之节制。行则为阵,止则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用大器,则为法以围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至,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8]310-311
徐光启认为依托车营作战,才可以发挥明军火器的多、精、习熟等优势,而且以车营为壁垒拒之,才可避免利器沦为他有。徐光启的宏伟目标是办成十五营,六万人,即每营四千人。而且他指出成就四五营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成就十五营则不忧进取。如奏疏中所述,成就车营,需要实选实练的精良士兵充任,比一般的士兵要求要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徐光启将希望寄托在其门下弟子孙元化身上,建议速招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再辅之以别处可选募之将领与兵员,配以广东等地向京城输来的西式火器,则可大幅度提升明军战力。
(三)明代火器技术知识体系的充实与革新
明代最主要的火器著作大部分诞生在明朝中后期,这一时间节点与火器技术在明朝中后期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的高峰相对应。这些火器著作形成了一个融合中国和西方火器技术知识的学术谱系,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可以系统地反映中国火器技术在明代中后期的发展水平(见表2)。

表2 明朝中后期主要火器著作一览
这些著作对中国传统火器的种类和形制做了详尽的介绍,并涉及了西式火器的来历、优势(倍径技术、测准技术、强大的威力)、结构(前后准星等具体形制)等,包含了明朝中期的所有火器技术成果。分而言之,《筹海图编》记述了明军使用的海战武器装备,以及葡萄牙人制造的佛郎机。《兵录》介绍了当时对西方国家的野战炮、攻守城炮进行研究的成果,以及对各种火药配方和配制理论、技术进行分析解剖的研究成果[14]。《神器谱》是继《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筹海图编》等书之后,关于火绳枪制造与使用的理论水平更高、系统性更强的著作,在实践上创制了许多形制构造更新颖、用途更广泛的火绳枪。这些都反映了明代已把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放在御敌保国的战略地位,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把明代中期单兵火器的研制和使用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耶稣会士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西方火器技术知识传入了中国,明末西学群体便成为这些知识的承接者。受传教士带来知识的影响,孙元化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写出了《西法神机》,韩霖根据自己所学的炮学和筑城术写出了《守圉全书》,焦勖则是按照汤若望的口述写出了《火攻挈要》。这三本著作是明末新式火器技术著作的代表,与之前的传统火器技术著作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于火器的界定有了数理标准,全面反映了同时期西方火器技术的发展内容。
《西法神机》写成于崇祯五年(1632 年),是一部介绍西方16世纪有关火器制造和使用方法的重要专著,全书约3 万字,分上、下两卷。《守圉全书》写成于崇祯十年(1637 年),是新式火器著作中对西方铳台技术的介绍和分析最为详尽、有力者,内含大量中外火器技术交流史料,非常珍贵。由于此书刊印后,明朝便趋于灭亡,在清朝被列为禁书,因此流传非常狭窄,其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识和研究,目前有黄一农、汤开建、郑诚对之有过较为详尽的研究。《火攻挈要》译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 年),由传教士汤若望口述而成,论述了战、攻、守各铳的制造和尺量比例,铳台、铳车及铳弹、火药的制造等,价值与《西法神机》相当[15],二者得到的关注和研究都较为充分。《火攻挈要》分上、中、下三卷,附图40 幅。
此外,还有《兵录》一书,内含一部分西方火器技术的内容,其作者不是西学群体的成员,写作过程也与传教士联系较少,为辑录性质。《兵录》共14卷,25万字,附图484幅。其资料来源,一半辑自《武经总要》,一半采自明代新材料。其中的“西洋火攻图说”集中介绍了西方火器技术,含有大量西方火器图,文字内容与《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相同,辑自二书。
四、结论
在15—16世纪特殊的国际形势(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西方大扩张)下,葡萄牙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发生冲突和联系的国家,通过战争的方式传播了佛郎机铳这一先进火器及其附带的火器技术知识内容。与葡萄牙特殊的宗教背景和权力关系相关。耶稣会士东来,为明朝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西方火器技术,使明朝在器物和知识方面均有突破性进步,大大地促进了明代火器水平的提升。
明末西方火器技术传华的历程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初期,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为代表的西学群体引领了一大批军事技术家对西方火器技术进行引进、传播、著录。明末火器技术确实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火器弹道知识、操作技术、弹药比例关系等核心技术均已为明末士人掌握,体现在《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著作中,并有一定的修订。但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清初的统一和走向稳定,到了清朝中后期,火器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火器著述稀少,火器技术发展的良好势头中断,直到清末变法图强,才又重新得到发展,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