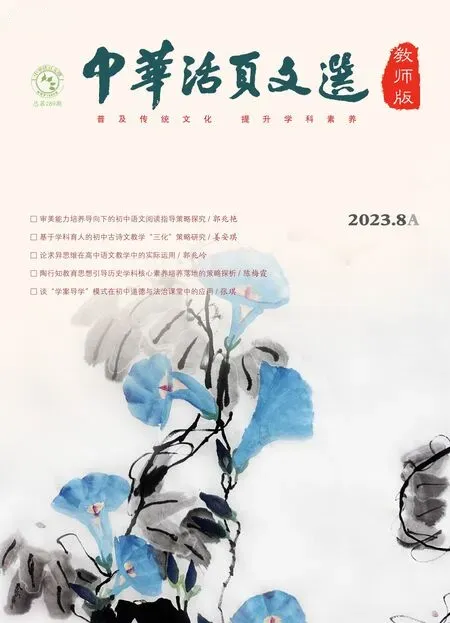语文素养的概念探析
■ 杨博翔(太原市第三实验中学校/山西省太原市)
一、“语文素养”的词源分析
语,形声,从言吾声。从字形结构上看,“言”为“说”意,而“吾”为“我”意,其字面意义就是“我说话”的动作。《说文解字》中释义:“语,论也。”即其意义为:谈论、议论、辩论;在《尔雅》中释义为:“语,言也。”即是说话、交谈的意义。由此可见,“语”的本义就是指人们口头表达、交流的这一动作。文,从玄,从爻。《说文解字》中言:“文,错画也,象交文。”即其意义为交错画的花纹。而在《说文解字序》中言:“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也就是说书写的字形为文,加上读音即为字。由此可见,“文”的本义就是人们书写之后的产物。当“语”与“文”组合在一起时,“语”和“文”就具有双重词性,一方面指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产生的行为,另一方面指口头语言与书面语。故而,“语文”是人们遵循语言规律所进行言语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即产生口头语和书面语言的行为与结果的合称。
素,从生从糸,从金文的字形结构来看,其造字本义为以麦秆为原料的草编工艺品。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素,白致缯也。”即指未染色的丝绸。也就是说“素”本是名词,但“素”所传递出的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本色的特质与姿态,进而衍生出“质朴天然、原来的、本质的”等形容词意义。养,从食,羊声。从甲骨文的形体上来说,“养”的本义是放牧羊群。在发展过程中,慢慢由作物养殖、牲畜养殖扩展到了养育后代。由此,《说文解字》中将“养”释义为:“养,供养也。”
仅从词源本义的角度,还是不足以揭示“素养”的本质含义,仍需要挖掘“素”与“养”背后的文化意义,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素养”。就“素”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麦秆何以能够被编织成工艺品?蚕丝何以能够成为绸?麦秆之所以能够编制,是因为它生来就具有的柔韧特质;蚕丝之所以能够织布,是因为它具有柔软、保暖、聚合的可塑性。所以,“素”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是生命所拥有可被塑造的、天生潜能的本色本质。而“养”字的背后是一段持久关照的生命历程,是一个需要付出与呵护的生命过程,和它有着紧密联系的因素包括了情感、意愿以及时间投入。它是一个不断付出、内化、外显的生命历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素养”的本质就是人在先天所具有的可塑造的生命特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与实践从而达到的为社会群体所认可的某种高度。
二、课程标准发展中的“语文素养”
2000年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中第一次出现“语文素养”这个词,《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中的“教学中应注意几个问题”这部门内容特别指出:小学语文实践教学要将重点聚焦在探索并保持知识、能力和情感的联系上,重视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之间的联系,突出教学重点,强化综合锻炼,注重学生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感悟、积累与运用,着重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从整体上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也对语文教学实践提出了要求:语文教学要基于教学目标的明确来简化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工作综合性,突出能力、知识、情感之间相互交错的联系,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感,提升语文积累量,全面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的“教学中应重视的几个问题”中同样指出:要从整体能力考虑,全方位培养学生语文素养,注重积累、感悟和熏陶,强化语感和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在以上几部教学大纲中,“语文素养”的侧重方向都是语文知识的积累、语言能力及语感培养,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语文素养的具体内容,而且其出现位置均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提醒部分中,并非核心位置。
2001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的语文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要让全体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素养。语文学科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指导,帮助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发展语文思维,培养语感能力,使其具备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阅读文本、文字表达以及沟通交流能力。此外,语文课程教学还要将品德修养与审美情趣的培育作为重要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实现学生德、智、体、美的和谐全面发展。2003年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语文课程在高中阶段的设置要以全方位培养学生语文素养为重点,充分体现语文素养在学生继续发展与不断提高中的作用,以便让学生拥有从容应对今后学习、生活甚至工作方面难题的能力。高中阶段的语文课程要最大化凸显其优势与特色,基于民族精神的培育传承和弘扬,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让学生建立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要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需求的关联,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去感受和积累,理清自然、社会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让语文课程全方位促进学生发展,体现语文课程的教学价值。从以上两个课程标准的表述中,我们能够看到“语文素养”已经跃升到课程目标的核心位置,其内涵也不仅仅是“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语感培养”等概念的排列组合,而是将其融合在一起,并加入“审美情趣”“文化熏陶”等新内容形成一个整体。
2018年1月,相关部门正式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其中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解释为: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各种语言实践活动,实现知识积累与建构,最终在具体情境中表现为语言运用的能力形成过程,其中每个环节都综合体现了语言学科的语言知识能力、思维品质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仅仅被表述为“语言能力”和“语言品质”的简单相加,这显然不能被人信服,静态的叠加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揭示出语文素养的含义。
按照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方式,笔者将“语文素养”具体分为六个层次:
一是必要的语文知识。如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内容必然要包括汉字的音形义知识,基本的语法知识,常见的篇章段落结构知识等内容。
二是丰富的语言积累。开展语文教学需具体的课文,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必然要参与到阅读之中,并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简单而言,学生形成语文素养的基础就是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以及常用的汉语词汇,背诵一定数量的优秀诗文,阅读一定数量的课外书籍。
三是熟练的语言技能。当一项技能达到熟练以后,就成为一种能力。语文教学必须让学生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培养其朗读、说话、写字、作文等基本语文技能,让学生学会如何运用多种形式的阅读方法以及常用的语言表达形式,掌握常用的思维方式,用规范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维结果,具备初步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能够在不同的场合恰当使用语言文字技能,并形成良好的语感。
四是良好的学习习惯。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教是为了不教”,这也是当前语文教学需要遵循的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形成学习语文知识的兴趣,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学好语文的自信心。其中包括认真听讲的习惯、勤查字典的习惯、书写整洁的习惯等。
五是深厚的文化素养。教师要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促进学生审美情趣及文化品位的提升,尊重多元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营养。
六是高雅的言谈举止。通过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培养出儒雅的气质和文明的举止。学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也要耐心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的观点,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欣赏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学会与他人沟通和交际。
综上所述,课程标准中的语文素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并不仅仅指的是一种技能或能力,而是一个个体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修养。通过语文素养的提出,使语文教学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人文精神的熏陶、完美人格的塑造,这是对历次语文教学大纲的历史性超越。
三、相关辨析中的“语文素养”
通过对相关词语的辨析,我们能够揭示出词语的核心意义。所以,我们把“语文素养”与“语文能力”“语文素质”进行对比分析。
1.语文能力与语文素养
“能力”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心理学大辞典》的释义为注意使人成功完成某种活动的心理特征;《教育大辞典》中的释义为顺利完成某种活动需要的个性心理特征。“素养”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平日的修养;在《辞海》中的释义为经常休息培养。根据以上工具书中对“能力”和“素养”的释义可以看出,“能力”指的是一个人能胜任或完成某项任务所具备的自身条件(包括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其重点在“功能型”;“素养”指的是一个人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在某个方面达到的高度。由此可见,“语文素养”这个词的重点在于语文学科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语文能力”的认识都是指听、说、读、写能力的静止排列,而“语文素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内在气质,强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融合。“语文能力”在某种成那个度上说带有很强的实用性,不能涵盖审美情趣、思维品质、人文情怀等内容,但“语文素养”就可以很好地涵盖这些内容。
2.语文素质与语文素养
“素质”在《新华字典》中释义为“人的生理上的原来的特点;事物本来的性质;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指出“素质,是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其缺陷会造成能力发展的障碍”;《心理学大辞典》中解释为“个体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可见,“素质”是指人的先天禀赋,与生俱来的生理认知。根据词典的解释,“语文素质”就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时所具备的先天条件。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素养”强调后天的习染、培养,而“素质”强调的是先天所具有的基因基础。而且“素质”可以进行一定的量化来进行测度,但“素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可量化。细化分析“语文素质”中的“质”在词性上属于名词,表达的学习状态是静止的。“语文素养”中的“养”在词性上属于动词,表达的学习状态是一种持续性的、自主性的动态化过程。所以语文素养的培养和形成不单单是教学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状态的终结,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言语实践的过程。
四、语文素养的限定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语文素养应当基于两个角度予以限定。一方面是对象的限定。本文所研究的教育集中在基础教育,对象为学生,尤其是初高中学生,由于它和其他普通素养存在较大差异,它属于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语文素养。例如,一名作家,其语文素养包含了很多不同内涵,较强的写作能力、丰富的阅读积累、深刻的社会体验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容量会逐步增多。此处所说的语文素养对学生而言仅仅是一个最低标准。所以,教师必须要结合学生不同时期的身心发育规律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培养目标。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涉及较大的层次空间范围,在培养过程中需要进行“量化”。此处的量化指的是依靠客观、具体的数字来明确规定学生在不同成长和发展时期需要培养形成何种语文素养,唯有提出明确的最低标准才可以确保语文素养培育与提升目标的最终实现。
过去的课程标准中也提过“语文素养”,但并未涉及“核心”二字。语文素养包含丰富的内容,一般来说包括听、说、读、写能力,或是文学修养等,但界定依旧相对模糊。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及的“语文核心素养”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与审美创造。如此,语文课程自身定位更加明确,一直以来关于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学什么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语文核心素养”的概念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引申出了很多理论生长点。
语文核心素养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应当重点关注对思维能力的理解。直觉与形象思维在过去的实践教学中容易受到忽视,教师一般重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如在学习一首诗的过程中让学生一边诵读一边想象所描写的画面,其中有联想,同时也有感悟,即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特别提及了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这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小学以及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要尤其重视想象力的发展,培养其探究欲,关键在于提升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另外,新课程标准中提出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主要涉及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批判性等,这些特性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很容易显现出来,语文教师也应当予以关注。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阐释,笔者认为“语文素养”的内涵就是学生在先天母语基因的基础上,通过后天自主的言语实践,在不断内化和外显的反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言语运用能力,并且通过言语实践积淀语言知识,建构思维方式与品质,培育情感态度,形成具有个性特征的综合性、生成性的母语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