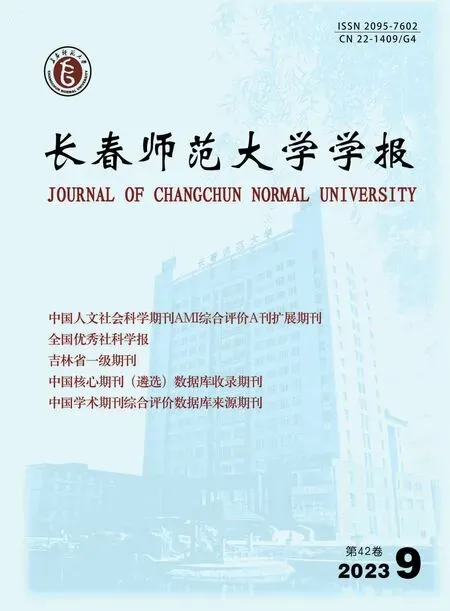《蝴蝶梦》的女性形象解读
——兼论与《简·爱》的互文性叙事解读
陈 琪
(黎明职业大学 通识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于1938年创作的浪漫哥特式小说《蝴蝶梦》是一部女性作品。小说中,贫困的孤身女“我”在陪伴贵妇人范·霍珀夫人时,意外认识了刚失去妻子不到一年的迈克西姆,在短期内与之结婚并回到曼德里庄园,其后发现庄园原女主人生前的行为和影响力,经历种种困难,最后与迈克西姆过上平静的生活。小说出自女作家之手,笔触细腻,是典型的描写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叙事作品。这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刻画了中产阶级女性典型代表吕蓓卡和来自社会底层的无名女性“我”晋升到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两个人物对小说情节的发展是举重轻重的,二者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小说对这两个人物采取了并置的叙述方法,并且两个人物与小说《简·爱》中的两个人物形成主体间性,二者有着不同的互文对象。
一、两个女性形象对比
小说故事时间以“我”在陪伴范·霍珀夫人的过程中结识迈克西姆开始,叙事时间却以“我”和迈克西姆在异乡的小客栈生活开始。贯穿小说的一条线索是“我”与迈克西姆的浪漫爱情。通过这条线索,读者可以解读出“我”的故事、性格。贯穿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吕蓓卡与迈克西姆的关系。这条线索以追述的方式呈现出来,即在正常顺序叙述中插入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些过去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故事时间开始之前,即在小说的故事时间之外。顺着这隐约出现、融合于第一条故事线索的第二条故事线,吕蓓卡生前的经历、与她相关的事件慢慢浮现出来,使读者从关于吕蓓卡的假象中慢慢了解到真实的她。
“我”和吕蓓卡在小说中成为一对对立体,构成并置关系。并置的意义在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原本零散的、孤立的事件和人物组合在一起,借以凸显其内在联系,使事件、人物之间产生呼应、对照、比喻、暗示等效果,达到特定的艺术目的。”[1]这两个女性的并置产生了强烈的对照效果:在对爱情和男性的态度上,“我”唯爱情至上,对迈克西姆基本言听计从,是迈克西姆理想的妻子,而吕蓓卡不需要爱情,对男性持嘲弄的态度,是迈克西姆的梦魇;在与他人的相处上,“我”敏感、胆小、脆弱、自卑,有社交恐惧症,而吕蓓卡优雅、得体、大方、能干,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在生活能力上,“我”住的房间是丈夫按照他的意愿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的情况下装修的,而吕蓓卡将曼德里庄园成功改造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文明去处;在性格上,“我”单纯、善良、真诚、温顺,缺乏独立性,而吕蓓卡虚伪、叛逆、独立、华丽、自私,有独特的价值判断体系。
作者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两个极端的人物,“我”柔弱平凡的形象映衬出吕蓓卡刚强艳丽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代表了女性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两种性格,体现了女性作为矛盾体可能同时拥有的某些对立的特质。
二、两个女性形象的互文性叙事策略对比
《蝴蝶梦》与《简·爱》同为哥特式小说,有很强的互文性。互文性也叫文本间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指每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许多不同元素拼成的,这些元素在宏观或微观上与其他文本遥相呼应,或相似,或相同,或对照。互文性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在写作该文本之前的知识储备是长期积累的,包括驾驭的文字、写作的意象、文章体裁等,这些知识储备与作者的文本内容形成互文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有的作者有意采用互文手段以达到某种写作目的,如引用典故、仿拟等。
《蝴蝶梦》中的“我”和吕蓓卡在小说《简·爱》可以找到各自不同的互文对象。
“我”与简·爱形成互文关系。二者同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种叙述者的好处是将叙述者想让读者了解的人物的某些方面展示给读者,包括心理活动,使读者对叙述者的经历感同身受,对叙述者产生好感。“我”和简·爱都是平凡的年轻女性,都嫁给婚姻失败的比自己大20多岁的英国男性贵族,而这两个贵族都生活在一个与其前妻秘密有关的庄园,最后都在庄园被烧之后与男主角过上平凡的幸福生活。
吕蓓卡与《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形成互文关系。两人同为叛逆、放纵、无所畏惧的女性,都以悲剧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两部小说刻画这两个人物时,都采用旁观者作为叙事者。由于旁观者不是被叙述者本人,所以旁观者眼里的被叙述者形象与真实的形象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有失偏颇,导致读者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误解被叙述者。此外,旁观者无法深入到被叙述者的内心,所以无法了解被叙述者真实的感受,使读者很难对被叙述者产生共情。“如今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为吕蓓卡‘翻案’——这位‘蛇蝎美人’和《简·爱》中的伯莎一样,都是没有话语权的、被妖魔化了的人物,因此,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也算是女作家们对于男权话语与写作常规的一种反抗。”[2]
以下分析这部小说如何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描写“我”的形象,又如何通过第三人称叙事的有限性剥夺吕蓓卡的话语权。
《简·爱》以简·爱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倾听周围的声音,大胆讲出自己的思想,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使这部小说力透纸背,为不幸又勇敢的女性发声。《蝴蝶梦》也采用了这样的叙述手法:“我”到庄园后所发生的一切是在法国小旅店通过梦境和回忆来追述的,是内在追述。“我”作为叙述者,与主人公重合,描述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的影响,通过“我”的视角聚焦周围的人、事、物,通过大量“我”的心理描写刻画“我”的形象。首先,直接叙事“我”对自己的评价。比如,回忆自己初到庄园时,直接刻画内心,评价自己的行为:“那时候,我满怀急切的希望,一心只想取悦于人,但却处处显得极度的笨拙。”[3]15这样的自我评价比比皆是。其次,通过“我”的动作、言语和环境描写,间接刻画“我”的形象。动作方面,主要体现出“我”的胆怯性格。如“我”到庄园后第一次会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位置,一看到迈克西姆示意的眼神,“我马上站起身来,拖开椅子。可是由于身体撞了餐桌,打翻了贾尔斯的一杯红酒。”[3]127这几个动作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我”笨拙的社交经验和紧张的心理。“运用语言和文体的不同形式来刻画人物是常常采用的,它不仅可以将人物的语言与叙述者的语言区别开来,而且人物语言的独特形式可以体现出其社会状况与个性特征等。”[4]作为小说主要线索的参与者,“我”的话语较多。如迈克西姆说要和“我”结婚时,感到“我”对他的话不相信,便说“看来我的建议你并不太感兴趣……我还以为你爱我呢。”我赶紧说,“我的确是爱你的,非常非常爱。我一整夜都在为你而哭泣,一想到从此后再也见不到你,我就受不了。”[3]71这些表白的话,让读者看到“我”单纯、可爱、较真、直率的个性。除了有声的口头表达外,语言还包括无声的心理活动。小说里有大量“我”的心理描写,也因此,这部小说可以看成“我”成长的心路历程。环境描写方面,“我”对自然的热爱体现在对一草一木的回忆,开篇就是以“昨晚梦里我又回到了蔓德里庄园”描写了庄园的景色,而后则通过回忆体现出“我”对夏日午后清凉舒适自然环境的热爱,展现了“我”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使一个健康、单纯的女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简·爱》中的第二女主角伯莎没有发言权。人们看到的是她给简造成的巨大的恐惧,是她疯狂的嚎叫和破坏行为。她的疯狂与简的理智形成鲜明对比。她的所思所想没有人知道,因为她只有外在的破坏行为被“我”看到,只有疯狂的吼叫被“我”听到,她内心的痛苦却没有人关注。伯莎被塑造成疯子,所以她不会理智地跟人讲述她的痛苦。这些都使读者只能看到她疯狂的一面,却看不到她被利用与人结婚而后又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同样,《蝴蝶梦》中的吕蓓卡在小说没有直接出现,而是间接表现。她的形象饱满起来,靠的是与之有接触的人物回忆她过去生活的零星片段,包括其外貌、思想、言行。另外,通过对庄园内外布置的环境描写体现出吕蓓卡的审美个性。吕贝卡的形象是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者刻画的,即通过丹弗斯太太、迈克西姆的奶奶、吕蓓卡的情人费弗尔、忠实的总管弗兰克、主教夫人等人之口追述。由于“我”是在吕蓓卡死后一年左右才遇到迈克西姆,所以对她生前事情的追述是在本文故事时间之前,属于外在式追述。如主教夫人如此形容吕蓓卡:“她是那么聪明”“她真是个尤物,充满奕奕活力”“她确实有才华……她确实是个出众的美人”。[3]155弗兰克用一句话概括了她的外貌:“她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3]167她贴身女仆,也是把她奉为偶像的丹弗斯太太,对她了解得最多。小说通过弗斯太太之口讲出吕蓓卡对男女之情的看法:“男女之间的情爱对她来说是场游戏,仅仅是场游戏。她曾亲口对我这么说。她去找男人,那是因为她觉得好玩……她笑你,就像她笑话所有其他男人一样。好多次,我等她尽兴归来,看着她坐在二楼房间里的床上,笑话你们这些男人,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3]387“没人制服得了她,是的,谁也别想制服得了她。她一向我行我素,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她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怕。她有着男子的胆略和精力。是的,我那位德温特夫人就是这种奇女子。当年,我常对她说,她应该在娘肚子里投个男胎才是。”[3]287另外一个对她的真实性格了解较多的是迈克西姆,“我”就是通过他才知道他们婚姻的不幸:“她生活腐化,放浪形骸,水性杨花,势利伪善,穷奢极侈,能言善辩,精明过度,心硬如石,享乐至上”[5]。对被剥夺话语权的吕蓓卡内心所思所想,读者无从了解。可以说,叙述“我”时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是全面的、可靠的,特别是对心理的剖析能够让读者想“我”之所想,让读者在感情上同情、接受“我”。而吕蓓卡在叙事中处于劣势,因为对她间接的刻画使她失去为自己辨解、展现真实想法的机会,使读者失去深入了解她思想的机会,也就无从在感情上同情、理解、接纳她。
吕蓓卡的性格特点通过庄园装饰的特点和她的房间布置也可见一斑。据统计,石南花在小说出现33次。许绮认为:“曼陀丽的一切都是由吕蓓卡……按照她个人的喜好布置的,因而石南花也是她的杰作。石南花的浓艳和美丽就是吕蓓卡形象的真实写照,这种看似美丽的东西实际上却充满了诱惑和邪恶。”[6]此外,晨室的布置也体现出吕蓓卡是一个有着高品位又妩媚、充满诱惑的女人。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晨室是这样的:“晨室栩栩如生,鲜明而光彩夺目,有几分像窗下成团成蔟的石南花。我还注意到,石南花并不是单单充斥在窗外的草地上,而且已经侵入房间内部,那娇艳的脸孔正从壁炉架上俯视着我。”[3]109庄园里和房间里对石南花的大幅使用,使吕蓓卡华丽、高调、夺目的美得以在环境中间接体现。
三、结语
通过对《简·爱》中两个人物与《蝴蝶梦》中两个人物的横向互文解读,可以加深和拓宽对两部小说的理解,激活这两部小说文本的内在意义,发现这两部小说之间的互融共通、相互交织、相互借鉴,更便于理解《蝴蝶梦》对不同人物采用的不同叙述手段,更加清晰地了解两部小说对不同人物的处理方式对人物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