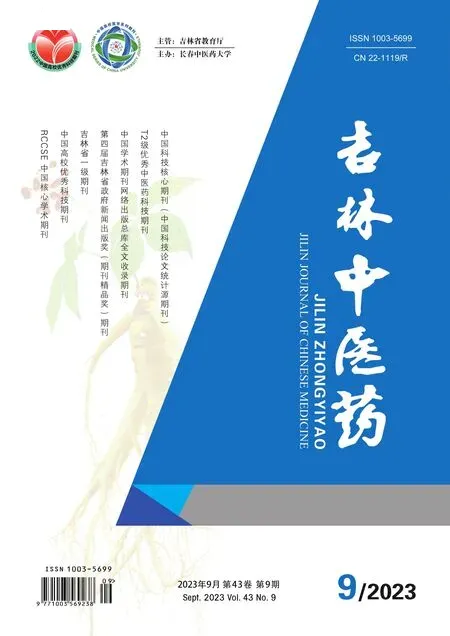陈锐运用温阳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经验
温晓娟,张 鑫,陈 锐
(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长春 130117)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以持续性白蛋白尿排泄增加,和(或)肾小球滤过率进行性下降为临床特征,与终末期肾脏病关系密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健康。西医治疗本病主要采用改变生活方式、控制血糖、稳定血压、调节血脂等方法[1]。根据糖尿病肾病临床表现,可将其纳入传统医学“消肾”“水肿”“尿浊”“关格”等范畴[2]。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在治疗糖尿病肾病方面,疗效明显。陈锐从医20 余载,在糖尿病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陈锐认为临床上糖尿病肾病患者大部分存在阳虚的症状和体征,故多采用温阳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现将陈锐临证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1.1 气损为病发之因 糖尿病肾病初始,患者因禀赋不足、嗜食肥甘、久坐少动、情志不节等致脾土壅滞,形胖体肥,运化失常,内热丛生。《素问·奇病论篇》曰:“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脾胃论》曰:“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脾胃为气血之本,后天生化之源,若脾气受损,运化失常,散精障碍,精微蓄积,日久则血中之精不能布散全身,致血糖升高;《傅青主女科》载:“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脾肾先后天相互滋生,脾损肾亦受累,肾气虚则封藏失职,关门失禁,精微下漏,溺中泡沫。
1.2 阳虚为病成之本 随着糖尿病肾病病程的推移,脾肾阳虚之态日渐显露。首因内热耗气伤津,导致气阴两伤。“气虚乃阳虚之渐,阳虚乃气虚之甚”,加之阴损及阳,间接伤及阳气;再者着衣单薄,贪凉饮冷,失治误治,寒凉之药肆用,直伤人体之阳。《圣济总录·消渴统论》载:“消渴病久,肾气受伤,肾主水,肾气虚衰,气化失常,开阖不利,能为水肿。”肾中虚冷,温煦无力,气化失常,津液代谢障碍,临床常见畏寒,腰膝酸冷,下肢水肿,大便溏薄,小便频数,舌淡紫苔白腻,脉沉等阴寒之象。
1.3 毒蕴为病进之标 糖尿病肾病后期,肾阳衰惫。肾主水,司二便,无力推动津液运行,水湿浊毒难以排出,蕴积体内,随血入肾,上犯肺、胃、心、脑,《景岳全书·癃闭》 载:“水道不通则上侵脾胃而为胀,外侵肌肉而为肿,泛及中焦则为呕,再及上焦则为喘,数日不通,则夺迫难堪,必致危殆。”中医将对机体有不利影响的物质统称为“毒”[3],《金匮要略心典》曰:“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运用现代诊疗手段发现糖尿病肾病患者肌酐、尿素氮、尿酸等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此与“毒”相呼应。反之,病理产物又可作为新的病理因素阻碍气血运行,形成恶性循环,加重糖尿病肾病发展。
1.4 络损为病极之果 糖尿病肾病晚期,久病入络。现代医家将糖尿病分为郁、热、虚、损四期,糖尿病肾病可归于损期[4],此阶段多表现为肾络的损伤。肾络是气血津液交换的场所,肾络空虚,气血津液运行障碍,津聚为痰,血停成瘀,肾络瘀滞使肾脏由功能性病变逐渐向器质性病变过渡。痰瘀胶着不解,引起脉络瘀阻和损伤,这与现代研究证实的由血流动力学改变和血液流变学异常引起微循环障碍及血管内皮损伤、血管痉挛具有相似性,亦是肾脏发生器质性损害的严重病理阶段[5]。
2 治疗思路
2.1 温阳运脾化痰湿 《灵枢·本藏》言:“脾脆,善病消瘅易伤。”首次提出脾脏虚弱为消瘅发生的内因。《景岳全书》载:“消渴病……皆膏粱肥甘之变,酒色劳伤之过,皆富贵人病之而贫贱者少有之”,揭示消渴病的发生与嗜食肥甘厚味,痰湿浊瘀内生,脾胃受损紧密相关。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以运为主,以化为生,运在前,化在后。“运”即是水谷、水液经胃和小肠的受纳腐熟与分清泌浊变成精微物质上达至脾的过程;“化”紧随其后,将精微化生的精、气、血、津液输布全身,营养五脏六腑、四肢九窍、筋骨经络。气化失司,温煦减弱,则脾化不力,散精障碍,导致精微蓄积过多,因“血糖者,饮食所化之精微也,若脾失健运,血中之精则不能布散全身”[6],血糖必然升高;精微滞留日久,聚而生湿、成痰、化热、留瘀,病理产物变成了致病因素。《临证指南医案》指出“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脾宜升则健”“脾喜刚燥”,《三消论》认为“今消渴病,脾胃极虚,益宜温补药”,故而甘温升脾阳、助脾运、化痰湿在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中尤为关键。
临床上糖尿病肾病患者多有形体肥胖,肢重酸沉,大便黏腻或溏薄等表现,其以痰湿蕴结为标,脾肾阳虚为本。若以大剂量温阳健脾药补本虚,因湿浊、痰瘀闭阻气机、瘀堵血脉,导致药力发挥受碍,故在治疗上应先消后补,清温互辅,药用清半夏、茯苓、大腹皮,少佐理中汤治疗。陈锐称清半夏、茯苓、大腹皮为“开路先锋”,比例常为1:2:2、1:3:2、1:4:2、1:6:2、1:8:2。其中清半夏为半夏经8%的白帆溶液浸制而成,毒性和辛燥之性大减,化痰之功倍增,用量15 ~30 g;茯苓甘淡渗湿,健脾止泻,偏于利水,可治生痰之源,用量较为灵活,随患者舌苔色、质而增减,最多可用至240 g。若患者腹胖异常,常添薏苡仁相须为用以增效,剂量多在为90 ~120 g;大腹皮行气宽中,利水消肿,《本草汇言》誉其“为宽中利气之捷药也”,现代研究表明大腹皮能够治疗胃肠气滞所致的胃肠功能障碍[7],用量15 ~45 g。若大便秘结者,大腹皮易瓜蒌仁,以增润下之功。《伤寒论方汇言》载:“脾土虚弱,灌溉失职,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上升于口,理中汤温补脾土,津液得升,口渴乃解。”理中汤药用人参、甘草、白术、干姜,剂量稍轻,意在温脾阳而不助火, 化痰湿而不伤阴。脾阳充,气机畅,血脉通,脾之运化自然归于正常。
2.2 温阳调肝理气机 肝郁是糖尿病的始动因素[8]。其一,肝与脾五行属性相克,肝郁则乘脾,继而波及水谷精微在体内的正常运化,终致消渴,《血证论》言:“木之性在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则水谷乃化”。其二,情志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肝主疏泄,调畅情志,疏泄太过则见烦躁易怒、头部胀痛、面红目赤;疏泄不及会有郁郁寡欢、善太息、易悲悯。明代赵献可曾云:“凡郁皆肝病”。多数糖尿病患者在发病前都有情志失调史,且有部分患者因精神因素而导致病情加重及复发,同时证实了治肝的合理性[9]。古人对此也有记载,刘完素言:“消渴者……耗乱精神过违其度,而燥热郁盛之所成也。”张子和道:“消渴症,如若不减嗜卧或不节喜怒,病虽一时治愈,终必复作。”可见二人皆认为情志不调,喜怒不节可诱导消渴病的发生。
现代研究[10]发现,如果光照时间及光照的量低于正常,人体出现抑郁状态的概率及程度也会随之增加。除了自然界的阳光,机体自身的“阳光”也可驱散阴霾,改善抑郁状态。仝小林院士据此提出“阳光散霾法”理论,指出“扶阳则阴霾自散,壮火则忧郁自除”[11]。陈锐认为,凡以阳虚证为主要表现且伴有情志不遂、血糖经饮食运动药物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都可采用温阳解郁法治疗。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本,故温肾尤重。在治疗当中取类比象,病轻者“播撒阳光”,药用淫羊藿、仙茅温补肾阳,剂量15 ~30 g;重者“悬挂太阳”,药用肉桂,附子大补命门之火,15 ~30 g 效佳。肝体阴而用阳,阳气为推动肝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故太阳当空,阳光温煦,机体阴霾自除。再者性味辛入肝经之药的使用,柴胡理气助肝用,郁金行血补肝体,该药对量简效宏,剂量一般15 ~20 g。此外,对症辅药,失眠者,酸枣仁、首乌藤各30 g 起用;紧张显著者佐合欢花15 g 安神缓焦等。在临床运用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具体治法,温阳可君可臣可佐,但必不可少。
2.3 温阳补肾固精微 《外台秘要》曰:“消渴者,原其发动,此责肾虚所致……腰肾即虚冷,则不能蒸于上,谷气则尽下为小便者也,故味甘不变。”指出消渴的病机关键在于肾中虚冷,气化无力。《金匮要略》首载运用温阳法治疗消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陈锐以为,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因脾损而受累,渐至脾肾阳虚,演变日久,肾阳衰惫。肾阳虚行水之功减弱,津液蓄积四肢则水肿,上凌心肺则见喘咳、呼吸难续;肾阳虚不能温煦膀胱,封藏失职,关门失禁,精微输布不循正道,滞于血中则血糖升高,流于小便则次频质黏,肌肤失濡则瘙痒难耐;肾阳虚奉养肾阴失职,肾阴亏则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少寐多梦;肾阳虚化生肾气受阻,肾气不充,肾精失固,在上耳鸣耳聋,在中腰膝酸软,在下阳痿、精冷、溺中泡沫。故在糖尿病肾病后期能见到肾气虚证、肾阴虚证、肾精亏证、肾气阴两虚证、肾阴阳两虚证,但肾阳虚统归所有。因此在糖尿病肾病后期多提倡温肾阳以滋肾阴固肾精,达到水火相济,阴平阳秘。
根据此期特点,陈锐用水陆二仙丹加减治疗。水陆二仙丹出自《洪氏集验方》,由芡实、金樱子组成,药虽两味,却有健脾益肾,固肾止遗之功,原书称其“久服固真元,悦泽颜色。括苍吴寅仲,久服有奇功”[12]。已有学者通过动物实验证明水陆二仙丹能有效降低阿霉素肾病大鼠蛋白尿,且在改善阿霉素肾病大鼠营养状况、调节蛋白质代谢及脂质代谢方面有良好作用[13];临床运用发现其能明显降低糖尿病肾病患者尿微量蛋白指标。陈锐尊崇“重剂起沉疴”思想,金樱子芡实通常1:1 使用,微量蛋白尿30 ~60 g,中量蛋白尿60 ~120 g,大量蛋白尿120 ~240 g,未见异常。再者是温补肾阳药物的选取,凭脉断虚,根据尺脉沉寒程度,由轻到重分别选取桂枝、淫羊藿、菟丝子、肉桂、附子;因变改量,根据患者服药之后的病情变化,增减剂量。寒微者选桂枝,寒少者首推淫羊藿,且初服剂量都在30 g 左右;寒多者则肉桂9 g起用;寒甚者附子服15 g 为度,不济者30 g 也可,先煎久煎减其毒性。
2.4 温阳降糖击靶心 陈锐认为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皆与阳气的盛衰密切相关,因气损而病生,阳虚而病进,阳衰而病重。《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指出阳气是人体之本,物质化生之源;又言“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说明了只有阳气正常运转,顾护肌表、抵御外邪的作用才能正常发挥;李中梓亦在注解中将人体生理之火比作阳气 ,以此突出其温煦诸脏,奉养周身之功[14]。故温阳在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中举足轻重,而血糖高居不下又是糖尿病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具有降糖作用的中药又多呈寒凉之性,因此如何寒温配伍成为降糖的症结。
陈锐基于中医“苦酸制甜”理论,将降糖类中药分为苦寒和酸甘两类,前者有大黄、黄连、黄芩、黄柏、知母、天花粉,后者为黄芪、党参、葛根、赤芍。苦寒之药一则清泄胃肠,使积热泄于前后二阴;二则压制偏亢之胃气,抑止食欲。在临床运用中多以6:1、5:1 或4:1 佐制干姜、大枣去性存用,固护胃气。酸甘之药敛气敛阴,化生阴津,既可补益气阴以固本,又能滋阴清热以除标。其次,根据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又可将这些药分为强中弱三个梯度,黄连为首,其有效成分小檗碱可从多条途径调节血糖、血脂水平,且其降糖作用对胰岛素分泌无影响[15];知母、赤芍、天花粉次之,其中知母多糖可减轻胰岛素抵抗和修复受损胰岛细胞组织[16],赤芍可增强人体清理活性氧的清理力,清除自由基,进而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17],通过天花粉制备的酸性蛋白抗氧化治疗可改善糖尿病相关症状,防止血糖波动过大[18];桑叶、桑枝、桑白皮、黄柏、葛根效果较前稍弱,起辅助降糖作用。
2.5 温阳通络治未病 《黄帝内经》首提络的概念:“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脉是经脉的分支,肾络是肾经在肾脏的分支,结合中医络脉的结构特点与现代解剖学知识,肾络与肾小球毛细血管网具有极高的相似度。由此可认为,肾脏微血管可归属于肾络[19]。糖尿病肾病寻根追底归属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范畴,故治络即为治肾。
陈锐以为糖尿病肾病为消渴病日久,痰湿瘀血蓄积肾络所致,故通络为第一要义。“ 络以辛为泄”“非辛香无以入络”。辛味药首推藤类,其次为虫类,此二类药都可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肾脏微循环 ,延缓肾功能的衰退。陈锐在临证中善用酒大黄、烫水蛭合黄芪益气活血,化瘀通络解瘀毒,瘀轻者则三七易水蛭。黄芪的用量一般根据患者的乏力程度而决定,酒大黄3 g 足以活血并引经,烫水蛭剂量6 ~9 g;桂枝、鸡血藤 、大血藤温阳通络,补血行血,可减轻四肢麻木肿胀之异感,三者用量15 ~30 g;蝉蜕、僵蚕、全蝎、蜈蚣搜风通络,攻逐走窜,无所不至,使“血无凝着,气可宣通”。蝉蜕、僵蚕用量15 ~30 g,全蝎3 ~9 g,蜈蚣1 ~2 条,常打粉冲服。此外,因血瘀证是糖尿病中常见的病理变化,且与多种并发症有直接关系[20],故温阳活血,化瘀通络的治疗应贯穿疾病始终,体现中医未病先防及已病防变的思想。
3 病案举例
宋某,男,55 岁,2021 年10 月31 日初诊。主诉:血糖升高2 年。现症:神疲乏力,腰膝酸软,皮肤瘙痒,心烦,急躁易怒,肩关节痛,纳可,眠差,夜尿1 次,有泡沫,大便每日1 行,质黏。舌淡紫,苔白腻,脉沉涩。BP 135/80 mm Hg(1 mm Hg ≈0.133 kPa),身高165 cm,体质量69 kg,BMI 25.34 kg/m2。既往糖尿病病史2 年,现自服盐酸氨基葡萄糖酸片0.24 g,每日3 次,每次2 粒。实验室检查:尿微量白蛋白(UMA)44.25 mg/L, 糖化血红蛋白(GHB)9.3%,糖化血清蛋白(GSP)490 μmol/L,空腹血糖(GLU)13.55 mmol/L,低密度脂蛋白(LDL-C) 3.26 mmol/L。尿常规:尿蛋白(+ -),尿糖(3+) ,比重 1.033。西医诊断:糖尿病肾病Ⅲ期。中医诊断:下消(脾肾阳虚,肾络瘀滞)。治法:益气温阳健脾,解毒通络保肾。方药组成:清半夏15 g,茯苓60 g,大腹皮30 g,黄连60 g,知母30 g,赤芍45 g,天花粉30 g,酒大黄3 g,烫水蛭(冲服)6 g,黄芪60 g,丹参30 g,金樱子90 g,麸炒芡实90 g,桂枝30 g,鸡血藤30 g,大血藤30 g,白芍20 g,甘草15 g。每日1 剂,水煎服,早晚分服。并嘱患者停服盐酸氨基葡萄糖酸片。
2021 年11 月28 日二诊,患者自诉上症减轻,现畏寒肢冷,腰膝酸冷,服药至今体质量减轻7 kg,眠差,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沉涩,BP 128/94 mm Hg。自测空腹血糖:6.8 ~8.8 mmol/L,早餐后2 h 血糖5.6 ~11.2 mmol/L,睡前血糖8.2 ~12.7 mmol/L。查UMA 7.86 mg/L, ACR 8.73 mg/g,GHB 8.4%,GLU 7.15 mmol/L,LDL-C 1.32 mmol/L。尿常规未见明显异常。调整上方,赤芍减至30 g,金樱子减至30 g,麸炒芡实减至30 g,加炒酸枣仁30 g,首乌藤30 g,黑顺片15 g。每日1 剂,水煎服,早晚分服。
2021 年12 月26 日三诊,上症减轻,肢冷缓解,体质量较上次减轻3 kg,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微黄,脉弦细。BP 120/78 mm Hg。自测空腹血糖:5.3 ~7.3 mmol/L,早餐后2 h 血糖6.5 ~8.2 mmol/L,睡前血糖7.1 ~11 mmol/L。查尿微量白蛋白(UMA)11.19 mg/L,糖化血红蛋白(GHB)6.8%,糖化血清蛋白(GSP)357 umol/L,空腹血糖(GLU)6.44 mmol/L,低密度脂蛋白(LDL-C) 1.61 mmol/L 。尿常规未见明显异常。调整上方,去金樱子、麸炒芡实、酒大黄、烫水蛭、白芍、甘草、炒酸枣仁、首乌藤,茯苓减至30 g,黄连减至45 g,加肉桂15 g,三七6 g。继续守方加减治疗,患者现血糖平稳,尿微量、血压等指标控制良好,病情趋向好转。
按:患者糖尿病病史虽仅有2 年,但因血糖控制不佳,现已进展到糖尿病肾病阶段。其平素嗜食肥甘,贪凉饮冷,加之失治误治,过用寒药,致脾胃虚寒。迁延日久,脾肾阳衰,温煦、气化功能减退,气血津液运行受阻,致痰湿、瘀浊内生,蓄积日久,蕴而成毒,损伤肾络。方中水蛭破血逐瘀,活通肾络,佐少量酒大黄通腑泄浊并引药入肾;黄芪为补气圣药,且可升阳举陷,固摄蛋白,丹参行血补血,此二药相伍,既补气扶正又活血化瘀,补而不滞,紧跟糖尿病肾病正气亏肾络瘀的特点;金樱子酸收、芡实甘缓,酸甘化阴,滋而不腻,专固下漏之精微;清半夏、茯苓、大腹皮温阳化痰,利湿行水,使痰浊从二便而解;黄连、知母、赤芍、天花粉分梯度降糖,精准打靶,配伍肉桂、附子去性存用,同时又温补肾阳壮命门之火,使先天不寒;桂枝、鸡血藤、大血藤通达四末,已病防变。诸药合用,实现脾肾双补,浊去毒清,肾络通利的目的。
4 小结
糖尿病肾病由糖尿病失治误治迁延日久而来,病情缠绵难愈,病机虚实夹杂。糖尿病肾病以阳虚为本,兼挟痰瘀浊毒。陈锐对糖尿病肾病以温阳为基本原则,通过化痰湿、畅气机、固精微、调血糖和通络脉,使正虚得补,痰瘀得清,浊毒得消,临床疗效明显,证明了中药独立降糖的可行性与优势性,为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拓展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