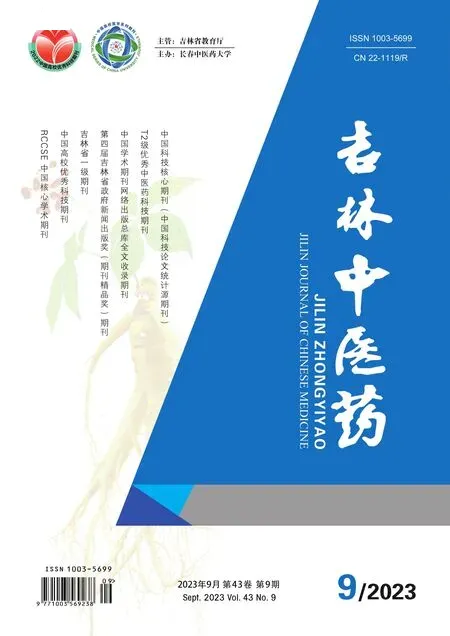王檀从脾肾虚冷论治慢性咳嗽经验
李直辰,王 檀,王科举,王子元,陈梦竹,李安冬,龙庆海
(1.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2.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长春 130021)
咳嗽是机体的一种防御性神经反射,能够清除呼吸道内有害因子及分泌物[1-2]。慢性咳嗽指是以咳嗽为主症,病程>8周,且X线片影像学诊断无明显异常者。慢性咳嗽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可造成神经、泌尿、心血管、消化等多个系统的并发症,如抑郁、尿失禁、血管破裂等[1]。
王檀从事中医肺病学科临床及研究近40 年,擅长诊治呼吸系统疾病及多种内科杂病。王檀对《医贯》及《脾胃论》均具有独到见解,将二者融会贯通,重视肾为先天之本与后天脾胃对人体的影响,临证以理论探讨作为先导,临床疗效甚佳。《景岳全书》中首次将咳嗽分为外感及内伤两大类[3]。王檀认为,不管是外感邪气致咳,还是脏腑内伤致咳,咳嗽的病机均为肺气不清。慢性咳嗽多与脏腑内伤相关,致病特点为本虚标实,脾肾虚冷为本,邪气干肺为标。咳嗽迁延不愈,最终会累及脾肾,二者互为因果,导致慢性咳嗽的发生及迁延。笔者将王檀对肺脏生理特征的见解及从脾肾阳虚论治慢性咳嗽的学术思想总结如下,以飨同仁。
1 肺脏的生理特征
1.1 肺本无气血阴阳 王檀认为,肺脏中不能生成气血,并非肺中无气无血;亦非肺脏无阴阳之属性,而是指肺中不化生阴阳。肺为相傅之官,《黄帝内经》曰:“上焦开发,……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说明肺脏主一身之气的运动,《类经》中对气的生成加以阐述为“人之生受于气,气者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此气出于中焦,传化于脾,上归于肺,积于胸中之气海。”宗气为“聚于胸中”之气,可见肺中宗气的生成依靠天之气与中焦脾胃化生之谷气[4],肺脏本身不能生成气。《黄帝内经》云:“中焦受气取汁……是谓血。”说明血的化生在于中焦与心,《医碥》中对肺中之血加以阐释:“化生于脾……宣布于肺。”血液化生后,贮存于肝脏,而后血随气上宣于肺[5],说明肺自身不能生血。“阴阳者,虚名也;水火者,实体也,人之真元也。”赵献可的肾水命火之理论[6]对人体之阴阳加以阐释,肾水为阴,命火为阳,肺脏之阴阳亦来源于肾脏与命门。故肺本无气血阴阳,为清虚之体。
1.2 肺为人身之橐龠 肺主一身之气,司呼吸。胸中宗气可“贯心脉而行呼吸”,在宗气的支持下,肺脏能够顺利吸入清气,呼出浊气,故肺为人与自然之气清浊交换的场所,气机升降之枢纽。肺朝百脉,主治节,可“通调水道”“输精于皮毛”,可在其宣发的作用下将水谷精微物质布散周身,营养身体各个脏腑,身体中的代谢产物也会通过肃降的作用下排出体外,保持呼吸道及消化道清洁。可见肺脏对于身体的清浊之气交换、水液的运行、营养、精微物质的代谢均发挥着关键作用[7]。
2 慢性咳嗽的基本病机
王檀认为,慢性咳嗽的病机关键为肺气不清,咳嗽是人体自我保护机制,是肺祛邪外出的过程,即肺“使之清”引发的结果。《素问·咳论》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虽然其他脏腑均可引起咳嗽,但咳嗽最终均由肺脏完成。肺为清虚之体,为一身之橐龠,参与着人体代谢工作,若气血水津不能够正常布散周身,就会化为邪气困阻于肺,影响肺脏正常的宣发肃降功能。《医贯》云:“肺为清虚之府,不容一物,毫毛必咳。”如若气道内存在少量的浊气或痰饮,会通过咳嗽将其排出体外,但若宗气虚衰或病理产物堆积过多,无力排出,导致痰浊、瘀血、水饮等病理产物长期留滞于内,咳嗽便会反复出现,消耗肺气。脾为肺之母,宗气的产生又与中焦脾胃密切相关,久病便会累及脾土;肾为肺之子,肺的肃降功能受到影响,以致肾水不能得到充养,肾脏亦虚。故“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8]。
2.1 脾肾虚冷为本 命火位于两肾之间,是人体生命活动及气化的原动力,人体各个器官的正常功能均需要命火的温煦与蒸腾[9]。王檀认为,命火以少阳的形式寄存于肝胆,通过肝的疏泄功能横泄于脾胃,助脾胃将水谷运化成精微物质,上输于心肺,布散周身[10]。患者在贪凉饮冷或房事劳伤等因素影响下,形成脾肾虚冷状态,命火温煦不及,导致肺脏气化不利,无法将精微物质布散周身,留滞于肺,生饮生痰,脾胃不及以致宗气虚衰,无法将痰饮及时排出,肺气不清,日久形成慢性咳嗽。
2.2 痰瘀结聚为标 在脾肾虚冷的状态下,阳气无以充养上焦心肺,肺脏虚弱,宣发功能受到影响,无法将精微物质布散周身,造成堆积,也可因心无所养以致心神不用,信息传递不畅,气血水津不归于正化,留滞于肺。肺脏肃降功能受到影响,机体外感时邪,无力祛邪外出,以致邪恋于肺。王檀认为,不管是内停之气血水津还是长期滞留之邪气,有余便会化火,导致局部积热,热毒蕴结[11]。或在是虚冷状态下,肺脏虚弱,但命火仍需升腾,因“虚者受之”,造成“火走一经”现象,火与气血水津煎灼成为痰瘀,结聚于肺。长时间的精微物质不归于正化亦会导致脾肾愈发不足,二者互为因果,气机枢纽受到阻碍,地气不能上而为云,天气也不能下而为雨,金水无法相生[12]。咳嗽迁延不愈,损耗正气。
2.3 心胃火盛为标 脾肾的虚冷,会导致肾精不能上呈,水火不能相济,心火偏旺;再者命火升腾不足,心神失于温煦,心脏便会通过君火的释放充养心神,维护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君火长期不守其位[13],易形成心火偏旺之证候。《脾胃论》云:“言心火旺能令母实……故脾胃先受之。”火为木之子,心火偏旺,肝木挟火势而妄行,乘于脾胃;或“肾者,胃之关也。”肾阳不足,导致胃中食物腐熟迟滞,中焦斡旋不利,日久瘀积化热,胃为阳木,故形成胃火亢盛。心胃火盛,火性炎上,冲逆于上焦,肺为娇脏,不耐寒热,火热之邪气炙灼肺脏,肺脏又需通过肃降功能将邪气排出,形成慢性咳嗽。
3 临证经验
在临床诊治慢性咳嗽过程中,若患者咳嗽迁延不愈2 个月以上,出现畏寒肢冷,乏力,劳累或感寒后加重,纳呆,便溏,小便清长,面色晄白,舌淡苔白滑,脉沉细[14]中3 种及以上症状,即可诊断为脾肾虚冷证之慢性咳嗽。王檀认为,温补脾肾以改善全身虚冷状态为治疗之本,肃清因脾肾虚冷留滞于肺中的病理产物为治其标,组方上通常标本同治,疗效颇佳。
3.1 温补脾肾治其本 针对脾肾虚冷病机,王檀选用附子理中丸[15]为基础方剂。附子理中丸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理中丸加附子组成。理中丸有温中补虚,梳理中焦之阳气,恢复脾胃气机升降之功。其中干姜辛热以温健脾胃,人参味甘,大补后天之脾气;炒白术性甘温,燥湿以健脾;炙甘草甘温益气补中。辅以附子补火助阳,使下焦之元阳得以上升,上焦阳气得以布散,改善全身虚冷状态。若患者畏寒肢冷较重,可加肉桂、淫羊藿、巴戟天等补肾助阳;若出现阳虚泄泻者,可加补骨脂、肉豆蔻等温中止泻;若阳虚湿盛者,可加姜半夏、陈皮燥湿健脾。
3.2 化痰散瘀治其标 身体虚冷产生的痰瘀之有形邪气留滞于肺,会出现咳痰量多,色白或黄,或难于咯出,喉中痰鸣,过食肥甘厚味后咳嗽加重症状,王檀常以附子理中丸为基础,配合苇茎汤合薏苡附子败酱散以清肺化痰散瘀。其中苇茎甘寒,擅清肺热,能退热而清上,薏苡仁可除湿而下行;桃仁活血祛瘀、冬瓜子清肺排痰,二者合用,清上肃下,使痰瘀得散,从大肠而解;败酱草味苦,祛瘀清热。若患者痰瘀日久伤气,可加生黄芪补气助邪气外透;若瘀滞重者可加乳香、没药等活血行瘀。
3.3 清心胃火治其标 若机体脾肾虚冷,脏腑相互影响,心胃无形之火冲逆于肺脏,患者易于出现干咳少痰,心悸,烦躁,反酸,失眠,遇刺激性气味或食用辛辣食物后咳嗽加重的症状,治以温补脾肾为主,兼清少阴之心火,泄阳明之胃热。仍以附子理中丸为基础方剂,重用黄连,取其苦寒之性味,清降心火,又降胃气,气降则火消;配合麻黄与苦杏仁宣发肺气,射干泄热下气,使邪有出路;紫菀与紫石英同用,紫菀味苦而入心,能泄上炎之火,紫石英重镇,固摄心阳;辅以厚朴宽中下气,调畅肺与大肠上下之气机。若饮食瘀积于胃过多,可加焦三仙健脾消食;若胃气不降以致胆气不利,可加枳壳、竹茹等清胆和胃;若出现心烦、失眠较重者,可加酸枣仁、柏子仁等养心安神。
4 预后及转归
若脾肾虚冷之状态得以纠正,肺中之邪气及时清除,咳嗽便会逐渐痊愈。若痰瘀长期结聚于肺,侵蚀肺体,化腐成痈,形成慢性肺痈[16];若脾肾虚冷状态持续加重,肺络痹阻,形成肺痹[17];若火邪伤及肺中气道,肿生挛起,痰饮停滞以致肺管狭窄,肺气遇火邪奔迫而出,发为哮病[18]。
5 病案举例
患者,女,42 岁,2021 年10 月12 日初诊。主诉:咳嗽、咳痰5 个月,加重10 d。患者于5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痰,就诊于当地医院,行肺部CT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咳嗽,予盐酸卡丙特罗片50 μg 每日1 次口服2 周,症状稍有好转。10 d 前,患者因感寒后上述症状加重,于当地诊所静滴阿奇霉素注射液(具体用量不详)治疗1 周,症状未见明显好转。现症:咳嗽、咳痰,量少,色微黄,质黏,胸闷、气短,咽痒,乏力,畏寒,纳差,眠可,大便溏,每日2 ~3 次,小便正常。舌暗苔黄腻,脉沉弦细。西医诊断:慢性咳嗽;中医诊断:慢性咳嗽,证属脾肾虚冷,痰瘀结聚。治以温补脾肾,化痰散瘀。方药组成:干姜15 g,人参15 g,炒白术20 g,炙甘草10 g,蜜麻黄7 g,生薏苡仁50 g,冬瓜仁15 g,败酱草15 g,桃仁10 g,芦根50 g,赤芍20 g,生黄芪50 g,肉桂5 g,茯苓15 g,熟附子7 g,乳香7 g,没药7 g。10 剂,每日半1 剂,水煎,每日分2 次服用。
2021 年10 月28 日二诊:咳嗽现已减轻,服药后5 ~7 d 咳痰量明显增多,1 周后痰量逐渐减少,现咯少量白色清稀痰,偶有气短,乏力较前改善,纳眠可,二便正常。舌红苔白,脉弦滑。在原方基础上去蜜麻黄、附子,加桔梗7 g,白前、前胡各15 g。嘱患者少食辛辣、寒凉食物,多行户外运动。1 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已无咳嗽、咳痰,乏力明显减轻,余无明显不适。
按:此例患者咳嗽症状迁延日久,乏力,畏寒,脉沉弦细,为脾肾虚冷之证;虽痰色微黄,舌苔黄腻,但此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因其肺中痰瘀结聚日久化火所致;10 d 前外感后,外寒使身体更加虚冷,所以咳嗽加重。王檀以温补脾肾,化痰散瘀之法治疗。方中理中丸为基础方剂,干姜辛热,火热温补脾胃之阳气,辛能入肺,宣散肺中之水饮;人参味甘,补益脾胃元气,升提脾气补上焦阳气;炒白术味苦甘性温,运脾补脾;炙甘草甘温,最合脾气,补中气健运。辅以苇茎汤合薏苡附子败酱散,清泄肺中瘀热,散瘀排痰。芦根退热清上,生薏苡仁除湿下行,桃仁、冬瓜子、赤芍合用行瘀化浊,败酱草消痰排痈、祛瘀生新,附子与肉桂合用能助命火蒸腾,通行十二经,振奋阳气。重用生黄芪助人参升提脾气入肺,透散因阳虚内陷之瘀毒;茯苓补脾利水,使肺中外溢之水谷精微重归于正化;蜜麻黄引药入于肺经;乳香、没药同用活血行瘀。二诊中去除附子,以防附子久用化火,消耗肾精;桔梗取代蜜麻黄载药上行,亦能宣肺化痰;患者仍有气短,加白前与前胡降气消痰。王檀洞悉慢性咳嗽之中医病机本质,通过温补脾肾之法,改善患者“虚冷状态”,调动患者身体机能,辅以清肺散瘀之品助患者排出肺中痰瘀,肺气得清,故病愈。
6 小结
慢性咳嗽中医发病机理较为复杂。王檀从其中医病因病机出发,着手于肺脏本身生理特性,认为咳嗽发病机制为肺气不清,脾肾虚冷为慢性咳嗽之本,病理产物扰于肺脏为标。整体审查,标本兼治,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中医理念,为中医临床治疗慢性咳嗽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