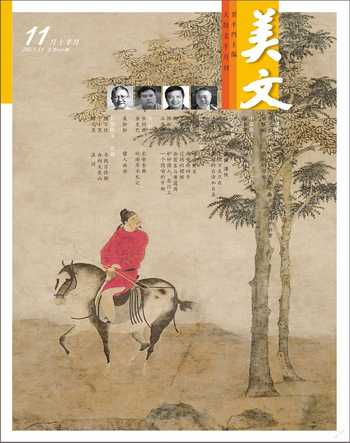一个隐喻的开始
丘脊梁
八字门是岳州郊野的一个地名。这里根本就没有一张特别的门,但对于我来说,三十年里,始终有一道隱形的门,在控制和激励着我的人生。我大半辈子的经历,细想起来就是与时间和命运不断搏斗,然后通过一道道无形的关卡,慢慢接近和抵达自己的理想。
三十年前,我还只有十九岁,从两百里外的大山深处丢下教鞭,跑到岳州城里来寻找内心向往的东西——依靠文字养活自己的肉身也养就自己的精神。说得通俗点,就是想到城里找一份与文字相关的体面工作,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我,已教了一年的小学,在省市报发表了几十篇副刊作品。从厚厚一本的样报剪辑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辽阔的未来。我觉得逼仄的大山已容不下我日益膨胀的野心,而岳州城里的报社,才是我安放灵魂的最佳处所。我信心百倍地来了,哪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的朋友就是报社领导,看都不看我的作品,只反复强调复旦新闻系的应届生他都没有接收。从他鄙夷与不屑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单薄和寒酸。我只得退而求其次,央亲戚帮我找一家单位做文秘。费尽周折之后,城郊八字门的一家工厂接纳了我。从此,我的人生就与八字门有了不解之缘。三十年里,我换了多家单位,辗转几个城市,但最终还是落脚在八字门。我感觉八字门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隐喻,我的一生似乎都逃脱不了“八字”的控制。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到八字门报到时的场景。那时节,岳州城刚刚被中央列为沿江开放城市,城郊新成立的国家级开发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我那在市计委工作的亲戚,同时兼任开发区某部门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开发区今后会不得了,而我要去的那家工厂,则是这里首家冒烟的企业、首家年产值过亿的实体。总之,这里遍地黄金,通江达海,前程似锦,远比到报社做聘用记者写几条狗屁消息强。我将信将疑,先坐公交,再转短途,又换三轮,迎着深秋微寒的晚风,充满向往地来了。三轮车夫将我丢到暮色中的一处荒野,说八字门到了。我问工厂呢?他说鬼才知道。我抬头张望,只见推平的土地上长满一人高的茅草,铺天盖地,无边无际,一阵秋风吹来,瞬间就将我淹埋。我突然难过极了,感到自己有如一粒尘芥,刚刚好不容易从深山中飘出,一不小心又被人扔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卑微的我们,连被人发现的可能性都极小,哪里还敢去奢望自己的理想?正在我急得想哭时,亲戚打电话喊厂方来接我的帆布吉普找到了我。我这才知道,我的目的地还在几里之外的蓬蒿深处;而我的理想,可能已距我万里之遥。
收留我的工厂是一家挂靠在政府的集体企业,实际控制者是一个私人老板。他以过人的眼光和灵通的信息,早在十几年前,就以极低的价格在八字门的荒山野岭上征得几百亩地。如今,他旗下已拥有多家实体,据说成了全市的首富,单是在八字门这片土地上,就建有一家年产万吨的饲料厂和一家专供出口的保健品厂。我来时,饲料厂正与一家国有大厂、一家金融机构,三方发起组建注册资金380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3800万元,现在看来是个小数目,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可大得吓人,一个穷点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这么多。怪不得我亲戚认为这里堆满了金山银山,执意要把我安排进来。然而,在我的眼里,却只看到了一片枯黄与荒芜。
那时的开发区,白天机器轰鸣,尘土飞扬,晚上就变得黑灯瞎火,死寂冷清。在我们厂区周边几里的地方,除了没来得及推平的山包上残存几栋人去楼空的建筑,根本就看不到人间烟火。听老员工讲,离我们最近的单位,是好几里外的火葬场,在巴陵东路没有修通之前,进出都得经过这个让人胆颤心惊的地方。现在巴陵东路是拉通了,但进出厂区的道路,只是拖货汽车从茅草丛中碾压出来的一条临时土路,坑坑洼洼,高高低低,歪歪扭扭。平时要想进趟岳州城,如果没有便车,得先沿土路行走一里多到巴陵东路,站在路边等上半天,运气好时能挤上临近县区进城的长途班车,运气不好时,就只能吃一肚子灰尘又黯然打道回府。进城后如果下午五点前没有搭到车,那就只能步行十几里摸黑返回。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区的陌生之地,我年轻的心一下变得苍老。刚来的那段日子,下班后我常常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厂区周边的旷野里行走,走着走着就陷入到焦枯的茅草深处,分不清方向,也看不到出路,而天色又渐渐昏黑下来,我突然感到无比孤单和忧伤。我不想在这里荒废自己的青春,暗暗开始谋划如何逃离。
谁知我在这一干就是四年。之所以待了这么久,并不是我爱上了这个地方,而是我没有能力脱离它——我被工作和现实绑架,动弹不得。进厂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老板的随身秘书,提包、买单、挨骂、写材料,从早忙到晚,连撒尿都要跑步前进,哪里还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前程与理想?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似乎把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灵魂都卖给了他,除了炮制出大量天花乱坠的材料,就是跟着他天南海北地飞,声情并茂地吹,地动山摇地喝。他有一次骂我时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会写文章的人多得很,你离开了我,就狗屁都不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刚给他做秘书,他就给我开了四百五十元一月的工资,差不多是我教书时的三倍,甚至比我那副处级的亲戚都高。除了工资,还有大量的补贴和奖金。这年年底回家过年,只短短几个月我就给了父亲三千元钱,相当于他在信用站做会计两年的工资,他惊得不敢接。我知道,我和我患癌的父亲都需要这些钱来维持生存与生计,有时甚至还需要维护一下心底的体面和虚荣,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是在岳州城里,不可能还有谁会给我更高的待遇。在金钱与现实面前,我只能妥协,只能让精神和理想暂时退场。跟他做随身秘书的这一年半里,我没有写过一句属于自己的文字,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曾经把写作视为生命。只有从报刊上读到熟悉的文友的作品心里酸酸时,我才知道灵魂深处,还是需要某些与物质无关的东西来抚慰。
我后来不再跟随老板跑,主要原因是除了能写点材料,太不会来事了,喝酒也毫无长进,他安排我担任了工厂的办公室负责人,直至离开。这两年半的日子,相对于此前来说轻松不少,也有了一些自由。我除了依然要炮制大量的材料外,还增加了很多事务性工作,但业余有了自己掌握的时间可用来读书。我一方面在参加文秘专业自考,一方面每个周末到市区的书店买回一大堆自己感兴趣的书,文学、历史、哲学、社科、学术,都有。我搞不清岳州城里有多少家大型商场,但知道深藏在大街小巷的每一家书店。这些书和书店,充实了我的时间和精神,后来也指引和左右了我的人生。书读得多了,曾经淡忘的理想又慢慢浮升上来,我又重新有了写作的冲动。可惜的是繁杂的事务和随时要写的各种材料,让我无法尽情书写,只能利用周末写上一两篇短散文或小小说,然后用公家的信封和邮票铺天盖地地寄往全国各地,虽说广种薄收,但一年下来也能发表好几十篇。照理说这种状态也接近我追求的生活了,但我与工厂一大批分配来的年轻学生们一样,始终快乐不起来。原因除了工厂摊子越铺越大(扩建年产四万吨工程,各省设分支机构)、效益越来越差、工资越来越少、老板脾气越来越臭外,最主要的是我们全都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看不到工厂的希望。那时下岗潮席卷全国,人人都忧心忡忡。加上地处八字门这个美其名曰开发区实为荒郊野岭的鬼地方,大家都有一种被城市和现代文明抛弃的感觉,似乎是被囚禁在一个荒岛上进行劳动改造,心中充满了压抑和苦闷。那几年八字门虽说陆续有了一些新建的企业,但总体仍是十分萧条,连吃饭的餐馆都没一个,只有几个棚子搭建的临时小吃店,招牌菜居然是酸豆角炒肉泥和蚂蚁上树。我常常和我近年接收来的大学生们一起,到这些棚子里吃饭,喝啤酒,发牢骚。这里面不乏武汉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之类的名校学生,只因政策性原因,他们被命运扔进了这个不公不私、不城不乡、不上不下的单位。他们喝着喝着,骂着骂着,有人就哭了起来,说明天就走,一天都不愿呆了,什么档案、户口、身份,通通都不要了。我看着这些我代表工厂亲手签字盖章从市计委社会发展科接收过来的同龄人,感到无比痛心,也无比愧疚,似乎是我害惨了他们。好在他们从来都不怪我,也从来不避我,并不因我是老板的大秘书,就将我划为另一个阵营。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过工厂的主人,因为我与他们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内心完全相通,也随时在准备着离开。
来工厂的第四年,我正式向老板提出了辞呈。他大吃一惊,一方面极力挽留,一方面给了我很多承诺。看到我去意已决,只好同意,并用他曾经引以为荣的奔驰600送我。其实对于老板,我并无恨意,相反还心存感激。尽管这四年里,我在工厂挨他的骂最多,几乎成了他无可替代的出气筒,但他对我的收留之情、知遇之恩,值得我终生铭记。我之所以执意要离开他,离开八字门这片土地,除了现实的原因,更多的是我对理想的追求和精神的需要。这四年里,我曾拿过高薪,也曾穷困潦倒;曾掌握权力,也曾贱如蝼蚁;曾获得荣誉,也曾出现失误。但这些都不是我内心所需要和在意的。我更看重与推崇的是文学艺术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可这些在八字门这片文化荒漠中,看起来更像一个笑话,不但不可能自由生长,反而会随时遭到摧残与毁灭。四年来,我总是在工作与爱好、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通过一条秘密的暗道躲躲闪闪、摇摇晃晃、别别扭扭地反复偷渡,心情因此长期紧张、抑郁,痛苦至极。现在,我终于战胜了自己,毫不犹豫地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大大方方重新去追寻心底的诗和远方。尽管前途未卜,但我依然感到如釋重负,俨然是穿越了一道命运之门。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终于从八字门走进了岳州城。如果用时间来计算里程,平均每天大约前进了五米,速度比一只蜗牛都慢。这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至于我的理想是不是在岳州城里等着我,我完全没有把握。我只是觉得,离开了荒芜的八字门,也就是接近了心中的目标。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又重新回到八字门并在此过上曾经向往的生活,我才知道理想有时并不在远方,它就在我们身边,与距离和时间都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一个奋斗的过程。
我离开八字门后,先是用自己在工厂的积蓄和父亲的支持共三万六千元钱(差不多可以买一套房),在岳阳楼边开办了一家纯文学书店。我梦想在这块最有文化底蕴和思想高度的风水宝地上,实现自己的追求。我设想以书养文,最终达到读书、卖书、写书、出书的和谐统一。但一年半后,当我不分白天黑夜读完店里的大部分书籍时,本也亏得差不多了,最后只好关门大吉。唯一的收获,是我对文学与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不再满足于写点副刊小稿,不时有作品出现在了纯文学刊物上。这点小小的进步,对别人来说简直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是阅读在我笔端的反射,让我有了更多的理由和信心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书店关张后,我凭着一大堆的样报样刊和倚马可待的写作能力,顺利通过一家国有金融机构的招聘,成为他们内部报的执行主编。在这个“钱多人傻”的地方,我真是把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原来半年出不了一期的报纸,我来后变为半月出一期,每期四个版,从一版到四版,从写稿到编稿,从摄影到画版,全由我一人包了,而质量在全省系统的评比中,次次名列前茅。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我居然把这份内部报纸,做到了在系统和客户中,期发十万份,广受读者欢迎。每到出报日期,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就纷纷等在我办公室,以便领去后迅速分发给客户。甚至还有本地的正规媒体,几次三番跑来找我谈广告合作。这次办报经历,基本圆了我走出大山时的梦想,可谓是理想的基础版或微缩版。因为除了没有公开出版物号,其他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状态。在这里办报的两年多,是我工作最单纯、收入最有保障、作品发表最多、生活最有规律、人生最快乐的时期。期间我完成了买房、结婚、生子这三件大事。要不是省城的一家报社力邀我去办周末版,我很可能就在这个单位一直干下去了。促使我放弃优越条件告别娇妻幼子远赴他乡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高薪诱惑,而是内心深处那份挥之不去的理想和情怀。当一个正规的编辑做一个正直的报人,这个念头就像一粒种子,始终深埋在我的心田,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不顾一切地破土而出。这种精神的力量,现实、时间甚至是爱都无法阻挡。
我去的报社是省报的一家生活类子报,那几年办得风生水起,在省城影响很大,我曾是他们的一名作者。当我走进三十多层的新闻大厦,与先前编发过我多次稿子的责编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办报时,突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也油然而生。从大山深处,到城郊八字门,再到岳阳楼下,又到企业报,直至如今进入省城大报,我通过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跌跌撞撞一步步接近了追求的目标,焉能不用心学习努力工作?所以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我把自己的全部才情,差不多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了这张报纸的字里行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高手如云的报社,没有新闻专业科班背景的我,业务能力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不但负责头版,每次改版时,领导还总是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我先做出样版,再给其他同事依葫芦画瓢接着编。这份认同与信任,让我确信自己的选择完全正确。有时我编稿累了,站到大厦的窗前,望着满城的车水马龙和灯火辉煌,偶尔也会想起荒无人烟郁闷苦逼的八字门,感觉眼前的一切有如做梦一般。生活就是这样,当理想的光芒突然照进现实时,由于它的久求而不得,我们往往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总认为那只是一种幻象,或是一种虚构。其实,这都是自身长年累月与现实搏斗的结果,只因成为了内在的习惯和品质,我们看不到悄无声息的成长与前进,才忽略了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活有时还会出现另一种形态,那就是修炼到一定程度时,事情往往会陡然发生逆转——当你的视线低于现实想求得它的恩赐时,它理都不理你;但当你的眼光高过现实对它视而不见时,它又四处寻找你。正当我旁若无人沉浸在省城报社的理想世界时,岳州城里的两家报纸、省城的另一家报纸、武汉城里一家发行量大得吓人的杂志,几乎同时委托不同的人辗转找到我,力邀我去共襄大业,开出的条件均十分诱人。我平静如水的内心开始波浪翻涌了,考虑到妻儿一直没在身边,我决定抓住机会回岳州城去。我选择了最初求职的那家报社,他们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在我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帮我解决编制调了进去,并任命为子报分管编务的副总编辑。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十一年前,当我低声下气想进去做个临时工时,当时的领导正眼都不瞧我一下;如今,他们却把我抬举为难得的人才,客客气气地请了回来,想想都滑稽。当然,我并没有怨恨那位领导的意思,他有他的难处,而且也完全符合情理和原则。之所以多年后事情发生逆转,变化的其实不是报社,而是我自己。十余年的历练和拼搏,我早已不是当年的我。我是另一个穿越过无数道命运之门的人。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另一件事,居然是在离开八字门若干年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我离开八字门后,很少再到这边来,特别是当年的工厂,已成为了记忆中的一个背影。但我知道,这些年来,随着城市的东扩和持续多年的建设,地处开发区核心地段的八字门村早已脱胎换骨,市里的行政事业单位扎堆往这里搬,高档小区集中往这里建。我们报社也顺应潮流,很早就在这边买了地,谋划把办公大楼和职工宿舍全部搬迁过来。经过多年的建设,终于全部完成。作为报社的一名职工,我也有幸在新办公大楼后面的职工宿舍购得一套划算的集资房。搬迁过来后,我才知道八字门已成为新城区和闹市区,功能齐全,设施完美,相比起来,我们原来在市中心办公的地方反而显得破败和寒酸。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八字門的命运,在自身不断蝶变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怪不得如今岳州城里的人,都以居住在这边为荣。
特别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原先的工厂,竟然与我现在的家只相隔不到一千二百米。搬家后不久,我特意在一个晚上散步时,沿着小区附近的通海路去寻找当年的工厂。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地点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尽管都属于八字门村的地盘,但相隔遥远。哪知才走了一千米,就到了巴陵东路与通海路交汇处。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是当年唯一有点城市气象的路口(铺了水泥,其余的均是黄泥巴断头路),我们常常站在这里等进城去的班车。我们的工厂,就在直线距离二百米远的营盘岭路边。我沿路走过去,果然在昏暗的路灯下看到了熟悉的围墙和门头。站到工厂的大门口,我抬手看表,发现整个过程只有十五分钟。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完全没想到两地相距这么近,更没有想到,历经二十多年,我又回到了原点和起点!我这大半生,原来竟然是一直在围绕着八字门转圈圈!我不知道这是生活的滑稽,还是命运的荒谬。我突然又想起八字门这个名字,我觉得自己转一大圈又回到这里,说不定还真是“八字”注定。
我很想进去看看我的工厂,但陌生的门卫不让。我告诉他自己曾是这里的职工,他不耐烦地说,哪里还有工厂,早搬到屈原农场去了,现在围起来准备搞房产开发,有什么好看的!我这才发现,我曾参与过建设的办公大楼、四万吨厂房、圆筒仓等标志性建筑全都推倒了,围墙里面堆满了建筑材料。而周边原先长满茅草的旷野,密密麻麻地竖满了16层、32层甚至是48层的住宅,抬头仰望,只见半空一片灯火辉煌,如同是天上的街市。这地方,真的已找不到半丝旧时荒芜的景象,空中倾泻而下的,似乎全是烟火与繁花,怪不得房地产商会看中工厂的这片宝地。我拨通了一个与我一样很早就离职了的同事的电话,然后又通过他联系上了好几个当年分来一两年就逃离到深圳、厦门等地去了的大学生,大家对工厂的现状无不唏嘘。但各人的状态都非常不错,有的成了资产过亿的企业家,有的成了某个领域的技术权威,有的成了公务员,有的成了像我这样的报人,大家都在自己的赛道上跑出了满意的成绩。我突然想,如果我们当年没有离开,没有朝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不顾一切地奋进,现在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很大的可能,是与留下来的同事一样,如今跟随工厂整体搬迁到了乡下,连继续留在八字门的资格都不具备。如此想来,我历经二十多年重新回到八字门,其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与回归,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上进和升华。
那个晚上,我一边与他们通话,一边穿行在八字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感到在八字门这块土地上,还真的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门。现实的,有单位的门、小区的门、住宅的门;隐形的,有事业之门、财富之门、地位之门。这众多的门,哪一扇都不会轻易向人打开,我们只有经过大量的付出和长期的努力,才能够通行和进入。也就是说,所有门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都应当叫作“奋斗之门”——是漫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奋斗,才成就了今天的八字门和八字门上的我们。
我现在在报社主编着一份文化周刊,同时兼任一家纯文学内刊的执行主编。工作之余,写点小说和散文,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抵达了当年的理想。可我的内心,始终充满了悲悯和忧伤。我觉得报人只是一种职业,我们应当有更高的追求。在现实生活和精神深处,依然有一道道各种各样的门等待着我去穿越与通过。也许,永远不停顿,永远在路上,这才是人生的“八字”和宿命。八字门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隐喻的开始。
(责任编辑: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