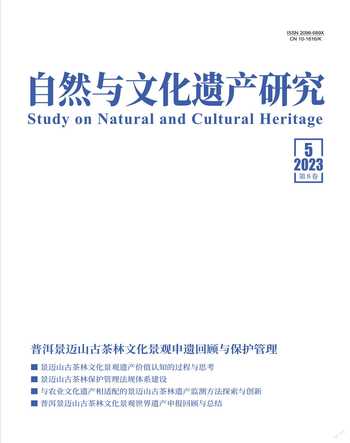关于陕西省秦始皇陵立法保护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文章通过总结和回顾陕西省关于秦始皇陵的立法实践活动,重点阐述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和主要变化,分析了立法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指出地方人大在制定文化遗产领域专项法规时,应当把握“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立法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遗产特性和地方工作实际,贯彻全过程民主,制定出务实管用、人民拥护、高质量的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
关键词: 秦始皇陵;世界文化遗产;立法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23.05.033-041
Abstract: By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Emperor Qin Shihuangs Mausoleum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vision background, revision process and main changes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Emperor Qin Shihuangs Mausoleum in Shaanxi Province,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legisl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when formulating spe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should grasp 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 of “non-conflict, distinctive and implementable”, focus on problem orientation, heri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work practice, ensure democratic process, so as to formulate practical, popular and high-quality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Emperor Qin Shihuangs Mausoleum;world cultural heritage;legislation
1 問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共有56项,世界遗产总数居世界第二,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含文化景观5项)。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类型丰富、文化风格多样、时间跨度长、地域分布广、后备资源充裕。从1985年批准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迅速,项目申报热情持续高涨、保护状况稳步改善、基础工作日益加强、管理监测能力不断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断显现、国际合作逐步走向深入[1]15-18。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气候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外环境局势的演变,文化遗产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断涌现,文化遗产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完善管理体制、健全责任机制,加强管理机构人员配置,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推动遗产保护利用成果共享,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顶层规划和探索实践。法律保护是完整地实现技术保护、行政保护、社会保护等其他保护的根本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加强世界文化遗产法治建设具有战略性、长期性的重大意义,是解决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突出问题的关键。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法治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化,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也不断丰硕。
1.1 理论研究综述
有关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方面。
一是对《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相关国际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的研究。如,汤晔峥[2]就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纲领性文件从《威尼斯宪章》到《公约》的转变入手,分析阐释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转型与重构过程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史晨暄[3]对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修订过程进行研究,梳理了突出的普遍价值概念、评价标准、真实性和完整性条件、特殊类型遗产列入导则的主要变化,分析了标准修订的原因以及进步局限。刘红婴[4]则立足《公约》,分析了世界遗产的法定标准、法定程序和法律价值,并指出了世界遗产国内立法要义。
二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研究。一方面,从应然层面提出完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建议。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主张是要制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法规,以明确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律地位,提升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效力。如,单霁翔[5]立足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出要加快制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彭跃辉[1]350-353指出:完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体系要从国家层面制定中国文化遗产龙头法和地方层面提升立法精细化程度两方面入手。姜敬红[6]则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之必要性及立法构想。另一方面,从实践操作层面对现有世界文化遗产专项法规进行分析,探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如,彭蕾[7]分析了当前世界文化遗产地方性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世界遗产地方立法应具备的基本要素。王云霞[8]通过分析了故宫法律保护的现状和趋势,探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穆永强、张水菊[9]回顾了敦煌莫高窟的立法保护历程,总结了敦煌莫高窟法律体系建立的经验。
三是外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研究。当前学界对文化遗产外国法律制度的研究范围较广,尤其对文化遗产保护成效卓著的意大利、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制度研究最为深入。如,龙运荣[10]分析了意大利和英国的文化遗产管理模式,指出我国可借鉴的制度经验。周超[11]对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修订进行研究,指出:日本更加均衡地处理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之关系,形成了区域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利用的理念。薛里莹、张松[12]梳理了澳大利亚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遗产保护法律在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相结合,遗产法规与环境法律体系相结合,世界遗产和国家、地方遗产保护立法相协同等方面的特色和做法。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对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推进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理论的构建和拓展,增进了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和规律的认识。但从文献数量来看,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单项立法研究和来自立法实践一线实证分析还较为缺乏,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专项立法的样本库还有待充实。
1.2 立法实践综述
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实践,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各省市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专项立法活动。据笔者从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国家规章库以及司法部备案法规规章数据库查询,截至2022年年底,中央和地方被赋予立法权的机关针对38项世界文化遗产共制定了78部世界文化遗产专门保护法规。其中:中央立法中行政法规1部,为《长城保护条例》;部门规章1部,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地方立法中,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53部,其中8部为“长城”立法,5部为“明清皇家陵寝”立法,2部为“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立法,7部为“大运河遗产”立法,7部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立法。政府规章23部,其中5部为“长城”立法,4部为“大运河遗产”立法,7部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立法。
从立法保护的覆盖范围来看,32项世界文化遗产均已配备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覆盖率达84%。暂未立法的6项世界文化遗产或准备立法或涵盖于该地其他法规的保护范围之中。如,四川省虽然未对“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单独立法,但是2015年12月,该省人大制定颁布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对省内的世界遗产进行了统一的调整规范。再如,北京市2021年1月颁布施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2年5月颁布施行《北京市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护对象涵盖了暂未专门立法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天坛和颐和园”。
从立法的时间上来看,2000年以前,世界文化遗产立法进程相对缓慢。2000年以前制定的遗产法规、规章仅有10部,与同期世界遗产对应的仅有4部,立法数占同期世界遗产数的比重仅为1/4。2000年以后,立法进程明显加快。2000—2010年的10年间制定了遗产法规、规章23部;2011年至今制定遗产法规、规章45部,其中近5年就制定了26部。世界文化遗产立法进程的加快与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以及2015年《立法法》修改,赋予设区的市在“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权限分不开。
从立法质量上来看,地方立法还存在一定提升空间:一是存在部分法律条款用语不规范不严谨、制度措施笼统、含义模糊等问题,立法的针对性及精细化程度仍然不够;二是部分立法陈旧,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立法超过15年且还未修订(不含修正)①的法规规章多达20项,其中7部还是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有关保护理念、保护原则、保护制度亟须更新;三是部分立法为满足申遗条件,为制定而制定,存在重复照搬上位法和其他遗产地法规,制度大而化之、设定行为和责任较粗,不易解决实际困难,缺乏地方特色等问题。
因此,为了提升世界文化遗产的治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破解当前制约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世界文化遗产立法的质量是首要解决的问题。陕西省早在2005年便颁布了专项法规《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2021年,根据新形势发展需要对《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2021年5月执行。新《条例》施行2年来,运行平稳,有效遏制了秦始皇陵保护区域的违法建设等影响文物本体和环境风貌的行为,保护、管理、利用工作得到了规范和加强,取得了预期效果。本文拟通过全面回顾总结陕西省关于秦始皇陵的立法实践经验,以期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帮助。
2 秦始皇陵概况
2.1 基本情况
秦始皇陵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皇帝陵墓,是我国5 000年文明史中秦统一天下历史节点的重要承载地,是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重要历史见证地,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秦始皇陵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南倚骊山,北临渭河,行政区划属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占地面积约45 km2。1961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2 遗产构成
根据真实性、完整性原则,秦始皇陵由历史环境、整体格局、遗存本体及馆藏文物4部分組成。秦始皇陵的历史环境是由骊山山系、渭河水系、台塬地貌共同构建。整体格局是依据秦始皇陵的山水环境选址、帝陵丧葬礼仪制度、工程修建等因素,形成骊山片区、帝陵片区、丽邑片区和五砂厂片区组成的遗存分布,呈现“三层级环绕、中心四象、山水呼应”的宏大帝陵整体格局②。迄今为止,考古工作发现并确认的与“秦始皇陵”紧密相关的各类遗存本体117处,包括:封土和地宫2处;内城、外城及相关遗址41处;陪葬坑38处;陪葬墓、修陵人墓地9处;陵园附属设施7处;其他文物20处。馆藏文物包括陶器、铜器、玉器、金银器、铁器、石器、骨器等共计6 284件组,62 970件。
2.3 立法概况
为加强秦始皇陵文物保护,提升法治化水平,2005年7月30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2010年、2012年分别根据《行政处罚法》的修正和《行政強制法》的颁布,对《条例》个别法律责任条款做了修正③。2021年3月31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
3 首版《条例》及实施成效评估
2005年首次颁布的《条例》为加强秦始皇陵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该《条例》的制定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针对秦始皇陵遗址区内私搭乱建、炸山取石、商业开发等严重影响遗址安全和环境风貌的行为,进行了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规范相关主体行为,明确法律责任,以加强对秦始皇陵的保护管理。实施10余年来,秦始皇陵的保护状况、管理模式、利用水平不断提升,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保持,为秦始皇陵的持续保护、研究和利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条例》的颁布意义重大、实施效果显著。
3.1 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显著改善
拆除了秦始皇陵封土的登陵道路,制止了游客登陵行为对封土的破坏;对秦始皇陵外城垣以内的村庄、企事业单位整体搬迁;对外城垣设置了保护围墙、配备监控设施并在周边进行了绿化;依法拆除了违建的部分工业厂房,清除了穿越秦始皇陵的“临马”公路;依法实施保护区划内的工程建设审批制度。目前,威胁遗址和环境风貌的人为破坏因素已大幅减少,有效保护了秦始皇陵的本体安全和整体格局。
3.2 初步建立了监测体系
成立了遗产监测队伍,对文物保存环境、遗址本体和遗址外部环境进行长期监测。实施了对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测、游客的监测、建筑物沉降的监测、大气质量检测以及陵区的监测巡查等。
3.3 初步理顺了管理体制
对秦俑博物馆、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文管所、临潼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分属不同部门的机构职能进行了整合改革,成立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实现了统一管理,大幅提升了管理效率。此外,根据“秦始皇陵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④的规定,撤销了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成立的秦始皇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13],将秦始皇帝陵交由陕西省文物局管理,确保了国家对文物的所有权[14]。
3.4 加强了对秦始皇陵的展示利用
依法推进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实施内外城垣、封土、东西门阙等多项文物保护展示工程,陵园整体格局初步显现。K9901陪葬坑(百戏俑坑)、K0006陪葬坑保护展厅及铜车马博物馆的建成开放,进一步展现了秦始皇陵的丰富内涵。目前已形成以兵马俑博物馆和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核心的展示体系。
4 现行 《条例》及修订的具体情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不断进步,我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改革在不断深化,使秦始皇陵的保护利用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 《条例》部分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求。因此,陕西省于2020年3月启动了《条例》的修订工作,经过多轮研讨修改,新版《条例》最终于2021年3月31日颁布,5月1日起施行。
新版《条例》共37条,由于篇幅较短没有分章,但是总体是从总则、保护管理、展示利用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逻辑编排,每个部分的顺序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和内在逻辑进行排列,体系完整、逻辑清晰。其中第一至第十一条为总则部分,依次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保护原则、文化价值、政府职责、部门职责、机构职责、经费管理、鼓励捐赠、保护义务、表彰奖励。第十二至第二十三条为保护管理部分,依次规定了保护规划、依法征收、保护区域、保护标志、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禁止行为、保护范围工程报批、建筑控制地带禁止行为、建设控制与审批程序、调查处理、可移动文物管理、文物监测。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七条为展示利用部分,依次规定了展示原则、展示方式、科研交流、游客管理。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群众参与、发现报告、安全巡查与涉案文物移交。第三十二至第三十五条为法律责任部分。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七条为附则,规定了援引条款和施行日期。
4.1 修订背景
第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的讲话精神。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时强调:“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陕视察,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守护好黄帝陵、兵马俑等文化遗存,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推动秦始皇陵保护立法的重要动因。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的讲话精神,保护利用好秦始皇陵这一中华文明标识,有必要对秦始皇陵的价值和保护利用状况进行再梳理,强化价值认知,深化保护利用水平。
第二,主动适应改革,解决工作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应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随着中央关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放管服”改革以及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深化,原《条例》的规定与改革举措存在一些冲突,因而造成实际工作诸多困扰,故有必要进行及时修改。
第三,强化保护措施,与《公约》相衔接。秦始皇陵是世界文化遗产,理应满足《公约》要求,履行国家责任。因此,有必要从保护全人类共同遗产的认识高度、从确保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着手,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对遗存本体和环境风貌的保护。
第四,提升利用水平,充分发挥秦始皇陵价值。依托秦始皇帝陵和兵马俑而建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全球瞩目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是闻名世界的旅游目的地。博物馆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超过1亿
人次,日渐成为展现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重要国际文化窗口。这给博物院对文物的内涵挖掘阐释、展示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从明确展示原则、规范游客管理、发展文化产业、提升科技水平等方面进行规范和保障。
4.2 修订过程
《条例》的修訂流程与新立法基本一致,修订工作历时1年,主要经过了以下程序。
(1)公布立法计划。2020年年初,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各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组织提出的立法申请,经审查立项,公布了立法计划。陕西省秦始皇陵条例(修订)确定为一类审议项目。
(2)起草并送审修订草案。根据省人大和省政府的相关要求,草案的初次起草工作主要由陕西省文物局负责。省文物局制订了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修订工作方案,通过收集立法资料、走访调研、研究讨论,形成了《条例》修订的初步草案并报省司法厅审查。
(3)省司法厅审查修改草案。省司法厅承办处室经过立法座谈、公开征求意见、省内外调研、集中改稿等程序后,提交省司法厅党组会议讨论,讨论通过后报省政府常务会审议。
(4)省政府常务会审议。2020年11月16日,省政府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5)省人大常委会审议。2020年11月23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议案进行了初审,第二十五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条例》。期间,省人大法制委、法工委和科教文卫委进行了多次的征求意见、实地调研、专家论证和集中修改。
(6)颁布《条例》并宣传。新修订的《条例》于202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27日,省人大组织了新闻发布会。此外,省市官微、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新 《条例》进行了宣传解读。省文物局,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有关单位也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宣传。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宣传,营造了较好的社会氛围。
4.3 修订变化
修订后的《条例》共37条,较修订前的28条,共新增10条,删除1条,实质性改动14条,条文规范性表述5条。可以说本次修订幅度大、变动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厘定各方保护职责。新修订的《条例》第五条至第七条分别对政府职责、部门职责以及秦始皇陵保护机构职责进行了细化明晰。政府对秦始皇陵的保护负主体责任,新《条例》明确了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三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将原 《条例》中的“有关工作”表述进行了细化:规定秦始皇陵所在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保护;规定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秦始皇陵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对秦始皇陵保护的相关工作;细化了秦始皇陵专门保护机构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职责,并进行了分项罗列。修订后的职责表述更加清晰、更具可操作性。
(2)明确行政执法权限。按照原《条例》⑤、《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15]第五条规定,在原有的执法体制下,秦始皇陵的执法主体资格在陕西省文物局。实际操作中,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的行政执法工作由陕西省文物局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实施,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行政执法工作由陕西省文物局委托西安市临潼区文物部门实施。随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⑥,执法力量下沉,由市县组建综合执法队伍进行执法,省级主管部门原则上不设执法队伍,现有事业性质执法队伍要逐步清理消化。因此,由陕西省文物局直接进行行政执法不再合适,且委托执法的规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在工作实践中,临潼区文物部门多个针对秦始皇陵保护区划内违法建设所做出的行政处罚,也因适用原《条例》第八条“被临潼区人民法院判定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而裁定不予执行该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极大地影响了秦始皇陵保护区域的违建清理工作。针对这一问题,新修订的《条例》第八条第一款对执法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西安市、临潼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划分,依法承担秦始皇陵文物保护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同时,新《条例》就临潼区文物部门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事权进行了划分,第三十条规定:“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安全巡查由秦始皇陵保护机构负责,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文物安全巡查由临潼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从而解决了保护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管理责任不清晰的问题。
(3)优化保护对象表述。新修订的《条例》对保护对象范围更加周延,增加了秦始皇陵的定义,在保护对象范围中规定除了对秦始皇陵文物本体外,还包括历史风貌和周边自然环境。此外,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对保护对象的列举表述也更加严谨。
(4)强化保护区域的管理。新修订的《条例》对保护范围的禁止行为表述进行了优化并增加了兜底条款,增加“其他可能危害秦始皇陵安全、破坏历史风貌和周边自然环境的行为”项。特别针对秦始皇陵周边违法建设行为较多的问题,增加了第十九条建设控制地带的禁止行为。其中第三项“禁止修建、仿造歪曲历史、损害秦始皇陵真实性的人造景观、景点”更是直接对粗制滥造山寨文物说不,以遏制滥建之风。
(5)强化对文物的展示利用。为更好地发挥秦始皇陵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新修订的《条例》新增了展示原则、展示方式和科研交流等内容。同时,新《条例》还对立法目的进行了补充完善,增加要“发掘传播其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内容,在第四条强调支持对秦始皇陵文物考古和文化研究,以发挥其文化价值。
(6)对接《公约》保护要求。新修订的《条例》在立法目的、保护原则、保护义务、保护对象、保护区域禁止行为、工程建设报批、展示原则等条款中,对真实性、完整性的保护理念均有体现。新 《条例》注重与 《公约》 的衔接,规定秦始皇陵保护规划编制应当符合《公约》要求,持续提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
(7)完善了法律责任。受限于当时“中央立法对处罚手段的高度垄断”的立法背景,原 《条例》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几乎毫无空间。特别是2012年因《行政强制法》颁布而对《条例》进行清理修正时,又将针对“保护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修建人造景点”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物高度超过10米”2项违法行为设定的拆除强制措施和罚款删掉,使得《条例》中最重的法律责任仅为1 000元以下罚款,法律责任部分形同虚设。随着近年来对地方立法权的适当释放,特别是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扩大了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⑦,《条例》顺势而为,在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等上位法不抵触原则的基础上,对新增加的建设控制地带违法行为设定了适度的行政处罚,并对《条例》中其他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对照上位法进行了梳理,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责任规制,大大提高了《条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效。
5 秦始皇陵立法经验与反思
5.1 立法经验
第一,充足的立法前期准备工作。成立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立法专班,做好立法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扎实开展立法调研,找准研判秦始皇陵保护、管理、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分层次召开立法座谈会,收集政府部门、博物馆、专家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为 《条例》 修订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
第二,满足秦始皇陵双重身份要求。秦始皇陵具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双重身份,新《条例》在遵循《文物保护法》基本制度的同时,积极对接《公约》要求。以《文物保护法》为根本依据,执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的基本制度。同时,要求划定秦始皇陵保护区划时应当与作为世界遗产的遗产区、缓冲区相衔接,注重周边环境的保护与协调,加强遗产监测,确保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三,将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法律条款。针对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结合陕西大遗址保护经验,将“坚持文物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并重,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写入《条例》的保护原则。
第四,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针对保护职责划分不清、执法权限不明、巡查责任落实不到位、各规划不衔接、违法建设多、让“文物活起来”措施不够等问题,《条例》逐一进行了规范。
5.2 存在不足
第一,未明确保护区划具体范围。对秦始皇陵的管理基本制度就是划分保护区域,通过限制保护区域内工程建设、生产生活等活动来达到秦始皇陵本体安全和环境风貌的协调。所以,尽管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保护范围由省政府进行公布,但是《条例》作为向公众广泛宣传并需知晓的保护秦始皇陵专项地方性法规,且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内的违建现象较多,能在《条例》里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四至范围效果最好。当然,本次《条例》制定过程中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是由于《秦始皇陵保护规划》正在修编,基于一些实际原因,将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区划做出较大调整,规划修编完成报由省政府公布周期较长,而《条例》修订涉及的执法问题、事权划分问题又亟待解决,为了保障法规的基本稳定性和严肃性,因此《条例》未明确秦始皇陵保护区划的具体范围。
第二,制度创新还不够。《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而 《条例》 总体上看还是存在重复上位法规定,制度创新较少、固定常规较多的现象。比如立法方针照搬《文物保护法》,未能根据遗产特性提炼出更具针对性的原则方针、保护规划、经费管理、个别保护和利用措施等一些条款,对上位法的宏观规定也未能做到实施层面的进一步细化。
第三,社会参与度仍然不足。从整个立法程序上来看,政府部门参与较为深入,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参与还不够。虽然 《条例》 修订时,广泛征求了意见建议,如通过组织座谈会、发公函等方式征求了国家文物局、陕西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级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意见建议,并在网络上向社会各界进行了多轮公开征求意见,但从反馈的情况和实际操作来看,立法在部门之间博弈较多、在不同群体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较少。
第四,对公民权利关注还不够。总体来看《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是一部部门行政管理法,行政管理色彩浓厚,凸显了行政权优位和公民的义务本位,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的保障关注还不够,这与秉持人民主权、自由平等、协调发展等观点的现代行政法治理念还有一定差距。比如:虽然在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时进行了移民搬迁工作,但保护区域内仍然存在部分村庄,大部分还在文物保护措施更为严格的保护范围之内,村民的发展权受损但还没有规定相应的行政补偿措施。
5.3 对地方性立法的借鉴意义
第一,把握“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立法原则,立管用的法。不抵触原则的初衷是为了反对越权立法、坚持法制统一,而非句句要找上位法依据,不敢创新,要从法理价值去判断,只要与大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则不矛盾、与大法的禁止性规范不冲突即可。要敢于制度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制定细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切忌照搬照抄上位法,避免“上下一般粗”不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要注重对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突出不同文化遗产类型的特点和地方特色。如大遺址的立法重点应统筹协调遗址本体的保护与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线性文化遗产的立法重点应在跨域协同、遗产一体和整体价值维护上;农业文化遗产的立法重点在活态保护及解决权属、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关键问题上。世界文化遗产的立法还特别要注意与《公约》及《操作指南》等要求的衔接,善于将国际上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当地的保护利用工作实际相结合,寻找特点,探求规律,制定出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国际视野的法律规范。
第二,深化公众参与度,探求真正民意,立民主的法。2023年3月《立法法》修正,突出体现了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立法要由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立法向扩大公众参与,推动民主立法转变。除了召开立法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以外,要适时开展立法听证会。立法听证会公开透明,实施效果更好。其参与主体更加广泛,能够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缓和冲突、消除误会的平台,听证会达成的结论更能为各方接受,进而有助于立法的实施。
第三,找准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立群众拥护的法。古罗马塞尔苏斯说过:“法律是公平与正义的艺术,是利益衡平的艺术,像音乐一样,正义之美是恰好的比例与有序的排列。”要树立行政法治思维,“破除公权至上、社会本位、公益本位、义务本位的束缚,体制机制的弊端,既得利益的羁绊,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转变”[16]。为了保护文物的公益需求而适当要求公众作出适当牺牲本无可厚非,但是立法者需要考虑平衡和比例问题,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需要考虑补偿。可以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补偿方式可以是直接的经济补偿,也可以是税收激励、政策扶持、发展权置换、社会保障、荣誉表彰等多种形式,补偿的资金可以从门票收入划拨,也可以建立基金、发展文化产业合作社等形式,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此外,要合理配置权利(力)、义务和责任,加大行政管理方式手段的创新,加强事前的管理,推动服务、指导、柔性的管理制度,不能简单地一罚了之。
(4)提升立法技术,加强立法实施监督,立高质量的法。首先要提升立法技术,法律概念要确保同一性、不矛盾性和明确性。比如对世界文化遗产定义、真实性完整性要求、遗产分区管理等关键概念,要准确进行界定,把握定义内涵和外延,并正确使用逻辑联接词,确保逻辑严密,语言精当。其次要注重法律法规之间的统一协调。文化遗产地立法时要把相关的如该省的《文物保护条例》《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城乡规划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全部找出对照,特别是法律责任的设定要合理平衡,避免相互冲突造成执法依据相矛盾。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行为文件上升为规章的或者规章已经上升为法规的,要对原文件、规章同时废止,避免适用上的冲突混乱。最后要加强立法效果评估,强化实施监督,评判法律制度在实践运作中产出的质量和水平是否能够达到立法预期效益。各省人大、司法厅等立法部门,文物、旅游等具体实施部门以及人大、政协等监督机构,包括利益相关群体应当作为评估主体和重要参与者,采取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推动文化遗产法规得到正确有效的实施。
此外,要加强立法部门人员的文化遗产等专业知识培训、加强专业部门人员的现代行政法治思维培训,不断提升立法工作者的能力素质,使之既有感性的道义情怀,也有理性的逻辑思维;既有完善的知识储备,也有深入的调研实践,这样才能立出科学的法。
作者简介:李莹(1987—),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管理。E-mail:490187297@qq.com.
① 我国立法实践中,法律(广义)修改有2种形式:修订、修正(包括修正案和修改决定)。由于“修正”的修改幅度较小,一般是对现行法律 的个别条款进行部分性的修改,不改变原法律的施行时间;而“修订”的修改幅度大,涉及原则、范围或重要制度的调整变化,是整体性 的修改,施行时间也重新规定。
② 资料来源为《秦始皇陵保护规划》。“三层级环绕”是指环绕封土地宫,由陵园内城垣—陵园外城垣—陵区构建的3层级陵区布局;“中心 四象”是指由陵园规划布局构建起以封土地宫为中心,东西门阙与南北外城门址形成的“中心四象”格局,并再次延伸出以陵园为中 心,以南北山水环境序列空间和东西帝陵丧葬礼仪空间为主的陵区“中心四象”格局空间。
③ 2010年5月27日,《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第十二条中“征收”改为“征收、征用”,并将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罚款金额由“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改为“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第二十四条“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改为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2012年1月6日,根据《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有关行政强制规定的决 定》,将涉及上述处罚条款的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删除。
④ 参见2005年版《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第四条。
⑤ 参见2005年版《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第八条。
⑥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8〕59号)。
⑦ 2021年1月22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三款:“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可以补充设定 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彭跃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5-18,350-353.
汤晔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转型与重构的启示:从ICOMOS的《威尼斯宪章》到UNESCO的《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J].现代城市研究,2015(11):47-56.
史晨暄.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J].风景园林,2012(1):58-62.
刘红婴.公法视域的世界遗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258-268.
单霁翔.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思考(下)[J].北京规划建设,2005(2):104-109.
姜敬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之必要性及立法构想[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學院学报),2005(1):117-119,123.
彭蕾.世界文化遗产地方立法路径谈[J].中国文化遗产,2019(2):59-68.
王云霞.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以北京故宫为样本[J].中国文化遗产,2013(5):8-9,56-63.
穆永强,张水菊.敦煌莫高窟法律保护体系的确立与完善[J].前沿,2014(Z7):80-84.
龙运荣.从意大利和英国管理模式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J].湖北社会科学,2010(7):108-110.
周超.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之间:关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2018年修订的评析[J].文化遗产,2020(1):16-23.
薛里莹,张松.从“国家财产”到“澳大利亚遗产”:澳大利亚遗产保护立法历程及特色[J].国际城市规划,2023,38(2):90-98.
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部分文物旅游景点管理体制的通知[EB/OL].(2007-08-08)[2023-08-29].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zcwj/nszfwj/szf/202208/t20220808_2237564.html.
张颖岚.文化遗产地管理对策研究:以秦始皇帝陵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03-104.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正)[EB/OL].(2017-07-28)[2023-08-29].http://wwj.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flfg/fg/201707/t20170728_2131175.html.
陈公雨.地方立法十三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