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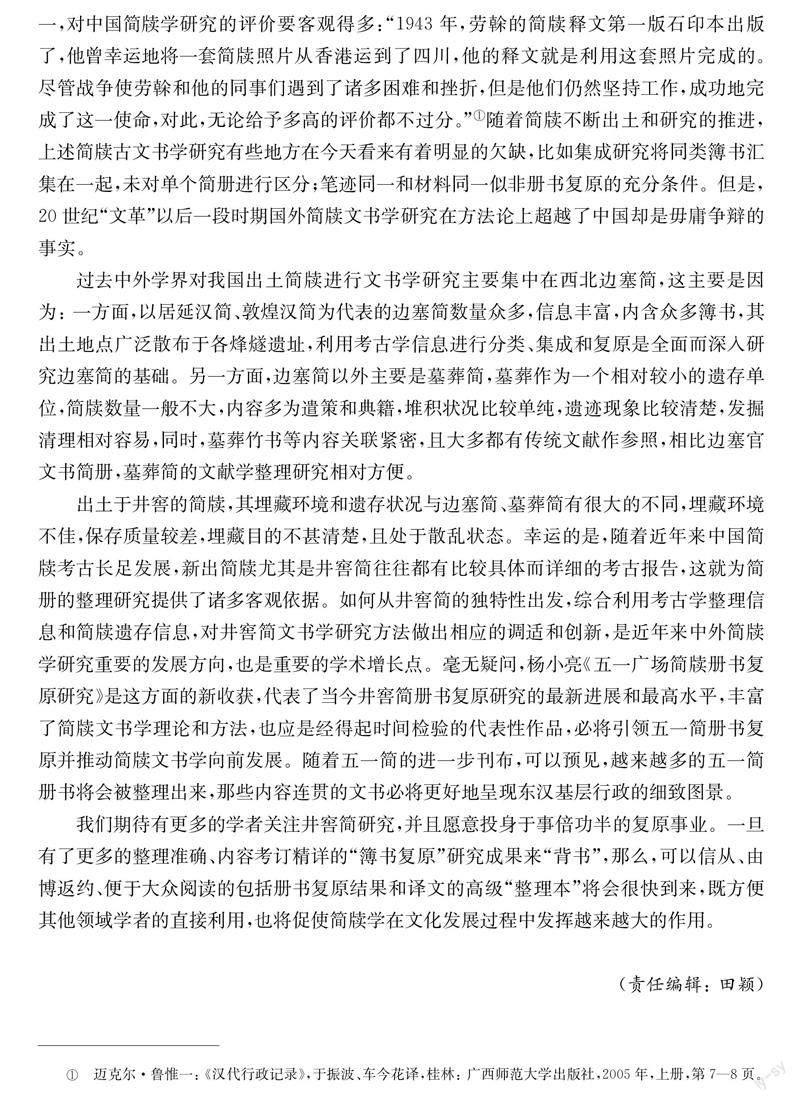

摘 要: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册书复原 简牍学理论 简牘文书学 简牍学史
2010年6—8月,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以下简称“五一简”)在湖南长沙五一广场1号窖出土,总数近七千枚,是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东汉简。很长时期以来,相比数量众多的秦、西汉以及三国简,东汉简的数量明显偏少,有的夹杂在居延、敦煌简中难以区分,有的是零星的墓葬简,整体上看来比较散碎。不仅如此,相比简牍与秦、西汉、孙吴史日趋活跃的研究,东汉简与东汉史研究也显得比较冷清。不过,当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长沙九如斋、东牌楼、五一广场、尚德街和益阳兔子山东汉简牍等陆续出土和刊布,东汉简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并且对东汉简推动东汉史研究寄予厚望,其中尤以五一简备受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五一简不仅数量众多,不少保存较好,而且很多可以编连为内容大致完整的简册文书,为探讨东汉内地郡县乡里(丘)的文书行政,特别是刑事诉讼提供了绝佳的第一手材料。
五一简出土至今,先后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第壹至陆卷,(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上海: 中西书局,2015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陆)》,上海: 中西书局,2018—2020年。)刊布简牍2600多枚,接近总数的2/5,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讨,迄今发表专题论文两百余篇。古语云:“蓄力一纪,可以远矣。”(《国语》卷一〇《晋语四·重耳自狄适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作为五一简整理组的核心骨干,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杨小亮研究员长年投身于这批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博士学位论文《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经修订,于2022年4月在中西书局出版。作为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简的专著,该书不仅具体论述了五一简的整理过程和简册文书的基本类型、大概样貌,为学界要言不烦地介绍了五一简的整体概况;而且细致复原了11份具有代表性的简册文书,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以信赖的文本;还从理论层面对册书复原的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为学界进一步开展五一简文书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示范。
一、 五一广场简复原的里程碑
五一简是湖南长沙首批出土于窖坑的简牍,其埋藏环境与走马楼、东牌楼、尚德街等古井简相近,内容皆为县政文书,因而被合称为“井窖简”。(关于“井窖简”的埋藏原因及其性质,近年来学界多有探讨,相关研究成果如郭伟涛: 《论古井简的弃置与性质》,《文史》2021年第2辑,第27—44、78页;凌文超: 《简牍何以“井”喷》,《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6日第5版;张忠炜: 《浅议井窖出土简牍的二重属性》,《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200—204页。)但是,五一简的埋藏地点是“窖”而不是“井”,窖坑简与古井简存在一些差异。例如,与废弃后的水井短期内被用于堆积垃圾进行填充(防止坠落事故)不同,这类窖坑应当一直被用来堆放日常废弃物,那些被长期利用的窖坑,遗存简牍的时限往往比古井简要长一些。据迄今所见五一简记录的年号,这批文书的时间大抵从永元二年(90)延续到永初七年(113),涉及东汉和帝、殇帝、安帝统治时期,时间跨度长达23年以上,是目前井窖简中涉及皇帝最多、时段最长的一批简(东牌楼东汉简、走马楼吴简仅涉及灵帝时期和吴大帝前期约十多年)。这对于考察皇权更迭背景下的国家、社会治理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
作为窖坑简,五一简为日常废弃物,但是,其遗存形态显得比较特殊。既有焚毁之余(如2010CWJ1②∶31),又有集中堆积(如第①层西侧临坑壁处),(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6期,第9页。)应当是前后多批次将废弃文书焚毁或直接扔弃到垃圾坑。这种遗存状态既与集中填埋的走马楼吴简不同,也与日常遗弃的且多为残损零碎的东牌楼东汉简相异。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将五一简聚集出现且保存较好的,但又因各种原因呈现散乱状态的残篇落简整理为可资利用的“册书”(简册文书),并无直接经验可资借鉴,这也是摆在诸多五一简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杨小亮先生长年从事简牍整理研究,重视“册书复原”工作。他曾综合利用简牍文书学方法对肩水金关汉简、走马楼吴简等材料中的簿籍、文书进行复原,(例如杨小亮: 《西汉〈居摄元年历日〉缀合复原研究》,《文物》2015年第3期,第70—77页;杨小亮: 《“表坐割匿用米行军法”案勾稽考校》,长沙简牍博物馆编: 《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中西书局,2017年,第173—189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年来,他根据五一简的特点,通过扬弃先行简牍文书学研究方法,在五一简册书复原研究方面夙夜勤励,成绩斐然,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具有推广意义的复原操作方式。
一批简牍是否能够又是否有必要进行复原,首先需要进行系统的调查,得出一些整体性认识。作为整理者,杨小亮先生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在开展复原工作之前,对五一简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其包含的册书结构进行系统分类,(关于簿书内容的排列,侯旭东先生利用西北汉简有过系统分析,参见其作《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58—73页。)如图1所示:
这为五一简册书的复原提供了指引和参照。当我们将若干文书简编连起来,其复原结果究竟是呈文,还是作为附件的呈文,抑或是簿籍,编连的结果又是否完整,这都可以与上述册书结构进行对照,从而提示下一步的复原、整理工作如何进行。
册书结构的分类与其首简、尾简、标题简的特征密切相关。作者认为,文书的首简(开头)、尾简(结尾)和标题简是册书构成的标志要素,无论在书写格式上还是语言风格上都极具特色,是册书结构分类和册书复原的重要依据。书中对五一简中所见的首简、尾简、标题简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统计。
关于首简的不同特征,作者指出,“不带附件的呈文的首简”A面常出现“文书中套用文书”的现象,如引用“府书”“廷书”等,B面则一定会对文书的主要责任人的用印情况加以说明,并预留出收文时间及收件人等待补充信息的位置;而“带附件的呈文部分的首简”,如“写移书”类呈文,一般都记有“谨写移”“谨移”“右……如牒”,其篇幅相对短小;至于“附件部分的首简”,单面书写,缺少背面的责任人以及待填补的文书到达日期等信息。以此为据,书中逐一列举出“只有呈文的册书首简”68枚、“带附件的呈文部分的首简”40枚、“附件部分的首简”(区分出1枚)。
尾简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不带附件的呈文尾简”,一般以“文书主要责任人+(职事无状)+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结尾。另外,“唯”+平出也是确定文书尾简的标志。另一类是“带附件的呈文部分的尾简”,还可细分为两种: 一种是“写移书”类呈文的尾简,一般比较短小,有时首简即尾简,其下行、平行文书以“如府书律令”“如诏书律令”等套语结尾,其上行文书以“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结尾,或仅以“敢言之”结尾,结尾处经常也会署有启封日期或相关责任人等信息;另一种虽然也以“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结尾,但简文中有“谨右别人名如牒”“傅(附)议解左”一类的词句提示该呈文带有附件。按册书种类,书中具体列举出“不带附件的呈文尾简”106枚、“带附件的呈文部分的尾简”32枚。
标题简的鲜明特征是往往以“某书”结尾,如各种“解书”“傅前解书”“除前解书”“匿衣物书”“服书”等;也常标注文书的发送方向,如“诣左贼”“诣狱”“属曹”“诣尉曹”;而且大多标注启封记录,如“某月某日开”等。有的简面上还有对所呈报内容的“批注”。据作者调查,五一简中所见的“标题简”共计101枚,其中带附件的册书的标题简7枚。
此外,签牌(木楬)虽然与册书密切相关,但是,作者认为,它产生于册书的存档环节,应是档案卷宗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标识,以方便检索,并不属于运行中册书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也不能等同于册书的标题。作者统计五一简签牌(木楬)共计166枚。结合调查统计的册书首简(108枚)、尾简(138枚)、标题简(101)枚,五一简中存在复原可能性的册书应当在百件以上。然而,五一简是日常废弃的文书档案,并非集中填埋简,在1号窖中的分布比较散乱,而且不少是残损简,因此,大多数册书都是残缺的,能够完整或大致复原的只有少数。
通过对册书首简、尾简、标题简的详尽调查和对册书结构进行分类,建立起五一简册书复原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一方面对学界已复原的4件册书加以检讨和反思,或指出其册书命名上存在的问题,或修订其排序及内容考证方面的疏误;另一方面依靠简文内在逻辑及书体、形制等成功编连复原了3件册书和2份案卷,分别是: 1. 广亭长晖言傅任将杀人贼由并、盗由肉等妻归部考实解书
2. 从掾位悝言考实仓曹史朱宏、刘宫臧罪竟解书
3. 连道写移奇乡受占临湘南乡民逢定书
4. 守史勤言调署伍长人名数书
5. 右部劝农贼捕掾悝言盗陈任GF9A3者不知何人未能得假期书
6. 直符右仓曹史豫言考实女子雷旦自言书佐张董取旦夫良钱假期书
7. 北部贼捕掾绥言考实伤由追者由仓解书
8. 女子王绥不当复还王刘衣案卷(两件册书)
9. 楮溪例亭长黄详杀不知何一男子案卷(两件册书)
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细致解析与考订册书内容,例如,对残断简牍进行系统缀合和统计,方便学界利用;对不少存在问题的释文进行订补,基本可以信从;对一些疑难字词进行详细考证,提出很多具有启发性意见;对晦涩艰深的文本进行系统通解,深入浅出地呈现简文含义,从而为学界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比较完整的东汉诉讼文书,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以凭信的依据。可以说,《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既是当今五一简册书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系统复原五一简册书的开创者,无论对于五一简研究,还是册书复原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 简牍学理论探讨的新进展
簡牍学理论探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简牍学目前仍是一门形成中的学科,相关理论体系、学科术语存在不少争议,且有很大的探讨空间。(近年来关于简帛学理论探讨的新进展,可参看蔡万进、邬文玲主编: 《简帛学理论与实践》第1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作者娴熟运用简牍学理论、术语、方法并提出诸多独到见解,颇具启发性,对于推动简牍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兹选取若干创见或疑点加以评介。
首先,关于“册书”术语的使用。作者根据长期以来学界的使用情况对“册书”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简牍文献中广义的‘册书应当包括‘典籍册书和‘文书册书,前者如先后发现的可分别归入《汉书·艺文志》‘六略的数十种可称之为‘书的典籍文献,后者如数量更多的各种可编联成册的官文书等。从学界对‘册书一词的使用情况来看,一般则多指‘官文书类册书。”(杨小亮: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上海: 中西书局,2022年,第4页。)“册书”是当今简牍学研究中习用的术语,诚如作者所言,一般指成册的官文书。然而,当我们细究“册书”的含义,《汉语大词典》给出了四个义项: (1) 史册,史籍。(2) 册命之书,古代帝王用于册立、封赠等事的诏书。(3) 亦指一般诏书。(4) 明清时向官府承包若干户钱粮的税吏。(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 《汉语大词典》,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030页。)可见自古以来“册书”并未用来指普通的官文书册籍。大庭脩较早开展的“册书复原”研究也以诏书为主,不过,他同时又将骑士简册、迁补牒、功劳墨将名籍等簿籍纳入进来,拓展了“册书”的外延。(大庭脩: 《汉简研究》,徐世虹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大庭脩“册书复原”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册书”指代官文书简册的用法随之推广开来。
笔者虽然并不反对“册书”的这类用法,特别是在典籍、诏令复原过程中使用“册书”应当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官文书簿籍,笔者历来主张以“簿书”称之。(凌文超: 《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簿书”不仅指簿籍,也指行文连贯的官文书简册,如《汉书·王吉传》云:“(公卿)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汉书》卷七二《王吉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3页。)王充《论衡》曰:“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黄晖: 《论衡校释》卷一二《量知》《谢短》,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548、554页。)公卿、文吏办公时的往来“簿书”,当然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官文书。五一简、走马楼吴简等材料中的文书、簿籍应当可以统称为“簿书”(广义),具体的官文书简册则可以用反映其性质的自题名如“爰书”、“解书”、“檄书”、“簿书”(狭义,特指簿籍)称之。原来惯用的“册书复原”似乎也可以用“簿书复原”来替代。
其次,关于官文书的分类。以往简牍学界按文书内容将官文书分为“簿籍”与“文书”两类。但是,据五一简簿书复原等的结果,常见“簿籍”与“文书”一起编连的简册。有鉴于此,作者从文书构成的角度将册书分为“不带附件的册书”和“带附件的册书”两类。前者是纯粹的“叙事性文书”(呈文),后者有三种形式: 簿籍+呈文、呈文+呈文、簿籍。其中,“呈文+呈文”形式的簿书,以往学界关注较少;对于缺乏“呈文”无需运行的“簿籍”,作者称之为“死文书”。这些都是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意见。
当然,对于“死文书”一类提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解释,以免引起误解。因为文书的功能在于信息的传递,信息不仅有空间的传递,也有时间的传递,前者是流转中的文书,后者是存档的文书。只要是使用中的文书(没有废弃)就是“活文书”,即使静置存档长期无人问津,似乎也只是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需要查找相关信息,信息传递的功能马上就被激活了,甚至也可以进行空间的传递。
再次,本书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且可以复制、推广的册书复原方法。作者提出的册书结构分类,以及对册书构成要素(首简、尾简、标题简、签牌)进行的全面调查,为五一简册书复原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具体的册书复原工作中能起到纲举目张之效。
至于册书复原的基本步骤,作者提出一开始就要重视图版处理、释文、缀合工作,有些是以往册书复原过程中很少注意的地方。例如,“异形”简牍的多个角度扫描和拍照;释文借鉴吐鲁番文书释读过程中使用的符号表示缺失文字的长短;文字隶定上使用统一的标准,新造字后用“固定”的文字方式加以说明,以方便检索;依据材质、形制、正反面茬口与纹理、字体、出土号、文字内容和格式对残简进行缀合,这些都是册书编连的前期工作,处置得当对于册书复原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册书编连是册书复原的关键。作者认为册书的编连主要依据文书的结构进行。特定的文书有特定的结构,在格式上也有固定的套语。具体而言,即依据首简、尾简、标题简为册书搭建起基本的框架。作者特别指出,目前五一简册书复原对标题简不够重视,没有充分利用标题简提供的信息。五一简册书标题简一般编排在册书之后,常有启封记录、签署和批文等内容,对册书复原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册书中间部分内容,主要通过行文逻辑,以及一些关键字、词的检索来逐步补充和完善。人名、地名、套语、习惯用语、简牍形制、书写风格、文字内容、编绳痕迹都是确定散简是否属于同一册书的依据,相互结合,共同促进册书的编连、复原。
然而,对于以往簿书复原尤为重视的“揭剥号”(简号),作者认为只是册书复原之后作为补充和验证成果的旁证,简号相连或相近,只是结果的反映,而不能进行反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不过,考古发掘者曾提示:“第①层西侧临坑壁处,为数十枚较集中的木牍。”(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6期,第9页。)我们不知道这部分聚集出现的木牍是否单独进行处理,又是否制作了专门的揭剥位置示意图。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我怀疑或许也可用来作为册书复原比较客观的前提依据。
此外,根据系列册书复原的结果,作者有不少新发现和总结性评论,提出了一些高明的见解。如五一简“写移”类册书有竹简与木两行一起编连的例子,可见材质、形制不同的简牍也存在编连的可能性。又如,一个签牌可能对应同一事项的多份册书,多个签牌也可能同时对应一个册书(后一点期待更多的明确证据)。再如,册书的收卷可能存在“卷轴型”和“折页型”两种方式。作者还主张将册书复原的目标分为文书流转、档案留存两种状态,反对将不同流转阶段的所有相关材料都“集成”在一起,在册书复原过程中应根据材料的多寡和复原目的的不同,选择性地将册书复原到某一个层级,这当然是非常可取的意见。
本书在简牍学理论方面的总结与探讨,尤其是从文书构成的角度对册书结构进行新分类、五一简册书复原框架和方法步骤的总结以及册书复原目标的判定,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与方法,提供了经验示范,对于促进五一简乃至井窖简簿书复原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 简牍文书学研究的新收获
自20世纪早期汉晋简牍出土以来,我国的简牍搜集、发掘、整理、刊布、研究已走过百余年历程。一百多年来,学界在简牍辑佚考证、分类整理、文书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刊布了许多简牍整理本,也發表了大量简牍学研究论著,一门以简牍为研究对象,具有专门理论体系和鲜明特征的简牍学学科日趋成熟。简牍学研究经过百年积淀,因机缘与机遇的不同,中外学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和范式,特别是在文书类简牍方面。审视中外简牍文书学的研究历程,庶几可以更好地凸显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在学术史上所处的位置。
我国简牍学研究素来注重“二重证据法”,文辞考释精审,史实考证扎实,是为其长。但长期以来对简牍材料的考古学信息利用不够,将简册视作独立的材料,结合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开展复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相关的整理一般是根据内容和格式进行分类,相比简文涉及的历史问题研究,简册复原整理的研究相对滞后。倘若以“理解之同情”回顾我国先行研究,这种研究传统的形成,有着诸多的客观原因。
我国学者开展简牍学研究之初就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并深刻地影响了简牍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初新发现的简牍是伴随斯坦因、斯文·赫定、橘瑞超等人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所谓的“探险”而出土的,这些汉晋简牍并不在国人手中。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揭开了我国简牍文书整理研究的序幕。(罗振玉、王国维: 《流沙坠简》,京都: 东山书社,1914年。)他们根据沙畹的手校本对简牍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运用传统金石学和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对其中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内容结合相关传世文献进行考释。不仅如此,王国维还重视结合斯坦因考古报告进行研究,并深入解析简牍文书制度。虽然无法利用原简以及对近代考古实践参与不够,限制了罗王的研究,但是,他们在简牍分类、引入近代考古学和发展“二重证据法”方面的功绩,影响深远。因此,可以说,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奠定了我国近代简牍学研究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地区发掘汉简约1.1万枚。居延汉简的出土,再次推动了我国简牍学研究的发展。然而,整理工作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此时,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发掘报告尚未完成,(居延汉简考古报告迟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正式出版。Bo Sommarstrm,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39, 41. VII. Archaeology 8—9),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56, 1958.)劳榦仅利用手中的反体照片,克服重重困难,对居延汉简进行了释文和考证。(劳榦: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石印手写本,四川南溪,1943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石印手写本,四川南溪,1944年。)他在简牍分类和利用居延汉简考察汉代史实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王国维运用的简牍学研究方法。同时,他也感叹“现在居延汉简的原发现人贝格曼的报告尚未出来,我们无法知道详细出土的情形,以及随着出土的器物,对现在的考释有很大的不便”,(劳榦: 《居延汉简考释自序》,《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2页。)劳榦显然认识到考古学对简牍学研究的重要性。以王国维和劳榦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简牍学研究者较少结合考古学信息开展研究,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所致,不应苛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逐渐安定下来,随着学科和研究范式的近代化以及学术成果的积累,简牍学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如陈梦家《汉简缀述》在利用居延汉简发掘报告和西北科学考察团旧档的基础上,将近代考古学引入居延汉简研究,重视文字学、年代学、简册制度等在简牍研究中的作用,不仅继承了简史互证的传统,也强调居延汉简简册作为史料的独立性。(陈梦家先生在整理武威汉简之后,从1962年到1966年短短三四年间,对居延汉简、敦煌和酒泉汉简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共完成14篇论文,当时发表的只有5篇,后来皆收入《汉简缀述》(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60年代,我国学界已开始以出土地点为依据,根据简牍形制、简文格式(书写款式)、字迹、内容、性质对居延汉简簿籍进行集成或复原研究,尽可能地恢复简册的原来面貌,如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沈元: 《居延汉简牛籍校释》,《考古》1962年第8期,第426—428页;陈公柔、徐苹芳: 《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年第3期,第156—161页。)这类简牍文书学研究与同一时期国外学者森鹿三、永田英正、大庭脩、鲁惟一等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并无多少差异。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简牍学界自觉运用考古学信息,结合简牍遗存信息对简册进行整理与研究,简牍材料逐步摆脱传统文献的附庸地位,简牍文书学研究在我国开始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简牍文书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册书复原日益受到重视,如谢桂华对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的系列研究,相关论文后收入其著《汉晋简牍论丛》。(谢桂华: 《汉晋简牍论丛》,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其二,简牍分类的研究不断改进,如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在永田英正集成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居延新简,对居延汉简所见簿籍作分类研究。(李天虹: 《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3年。)该书虽以“分类”为名,但实质上就是简牍文书学研究;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根据简牍文书自身存在的规律,并尽可能应用其原有的称谓,对秦汉简牍文书进行分类辑解。(李均明: 《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9年。)其三,在简牍学研究的基础上,日渐重视简牍文书学理论的归纳、总结和专门研究,如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和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李均明、刘军: 《简牍文书学》,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汪桂海: 《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以上對国内简牍学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外的相关研究。“二战”后,日本学界开始关注居延汉简研究,受西方学界的影响,强调用“古文书学”方法来进行系统研究。日本学者研究居延汉简“古文书学方法”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以森鹿三、永田英正为代表的简牍集成研究,即按一定的标准,如以出土地点、年代、样式、人名等为依据,将零散的简牍集成起来加以研究利用。永田英正后来将简牍的记载样式和出土地点确定为简牍集成最重要的基准。(永田英正: 《居延汉简研究》,张学锋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39页。)另一类是以大庭脩为代表的册书复原,即按出土地点和原简编号顺序,以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为原则对册书进行复原。(大庭脩: 《汉简研究》,第10—13页。)
值得指出的是,“集成”与“复原”并无截然两分的界限,正如大庭脩所云:“最先对汉简展开册书复原研究的,是麦克·鲁惟一博士。他的大作《汉代行政记录》,集成了基本属于同一笔迹、同一出土地的同类简牍,而且探究了它们的含义。这种操作实际就是在复原册书。”(大庭脩: 《汉简研究》,第10页。)在大庭脩看来,严格意义上的简牍集成实际上就是册书复原,因此,他将骑士简册、功劳墨将名籍等簿籍集成纳入了“册书研究”篇。虽然“册书复原”可以整理出诸多语意连贯的文书文本,但因简牍残缺或文句晦涩,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簿书集成”虽然很多不能连读,但是,随着集成框架的准确判定,很多时候各类简牍先后顺序并不妨碍簿籍的理解,无论是簿书编制之初,还是我们今天的整理,簿籍之内数量众多的同类简的前后次序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一般也不会因此造成误解。因此,可以说,“集成”与“复原”殊途同归,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方法运用上的差异,追求的目标则是一致的,都是整理出可以准确通读的简册文书。
日本学界在居延汉简集成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简牍学研究方法提出严厉批评。他们认为王国维、劳榦对居延汉简按简牍内容进行分类,“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欠缺”,“没有意识到如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这么多新出土的资料加以研究这一问题”,没有考虑到简牍的形状,未充分注意到各简牍的出土地。桥川时雄甚至称“中国虽有古文书,然无古文书学”。藤枝晃也认为“事实却正如桥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这句话稍作演绎的话,大概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作比喻,这就是: 挥着剑乱舞乱砍,即使真的能把敌人杀死,也很难称得上是正规的剑法,只有从基础开始按剑谱进行训练,才能掌握真正的剑法”。(大庭脩: 《汉简研究》,第8—9页。藤枝晃: 《居延汉简研究·序文》,永田英正: 《居延汉简研究》,第1—2页。)
相比之下,受日本居延汉简研究影响,同样对居延汉简开展集成研究的英国学者鲁惟一,对中国简牍学研究的评价要客观得多:“1943年,劳榦的简牍释文第一版石印本出版了,他曾幸运地将一套简牍照片从香港运到了四川,他的释文就是利用这套照片完成的。尽管战争使劳榦和他的同事们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挫折,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工作,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对此,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迈克尔·鲁惟一: 《汉代行政记录》,于振波、车今花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上册,第7—8页。)随着簡牍不断出土和研究的推进,上述简牍古文书学研究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有着明显的欠缺,比如集成研究将同类簿书汇集在一起,未对单个简册进行区分;笔迹同一和材料同一似非册书复原的充分条件。但是,20世纪“文革”以后一段时期国外简牍文书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中国却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过去中外学界对我国出土简牍进行文书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边塞简,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以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为代表的边塞简数量众多,信息丰富,内含众多簿书,其出土地点广泛散布于各烽燧遗址,利用考古学信息进行分类、集成和复原是全面而深入研究边塞简的基础。另一方面,边塞简以外主要是墓葬简,墓葬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遗存单位,简牍数量一般不大,内容多为遣策和典籍,堆积状况比较单纯,遗迹现象比较清楚,发掘清理相对容易,同时,墓葬竹书等内容关联紧密,且大多都有传统文献作参照,相比边塞官文书简册,墓葬简的文献学整理研究相对方便。
出土于井窖的简牍,其埋藏环境和遗存状况与边塞简、墓葬简有很大的不同,埋藏环境不佳,保存质量较差,埋藏目的不甚清楚,且处于散乱状态。幸运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简牍考古长足发展,新出简牍尤其是井窖简往往都有比较具体而详细的考古报告,这就为简册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诸多客观依据。如何从井窖简的独特性出发,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对井窖简文书学研究方法做出相应的调适和创新,是近年来中外简牍学研究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毫无疑问,杨小亮《五一广场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收获,代表了当今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也应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代表性作品,必将引领五一简册书复原并推动简牍文书学向前发展。随着五一简的进一步刊布,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五一简册书将会被整理出来,那些内容连贯的文书必将更好地呈现东汉基层行政的细致图景。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井窖简研究,并且愿意投身于事倍功半的复原事业。一旦有了更多的整理准确、内容考订精详的“簿书复原”研究成果来“背书”,那么,可以信从、由博返约、便于大众阅读的包括册书复原结果和译文的高级“整理本”将会很快到来,既方便其他领域学者的直接利用,也将促使简牍学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