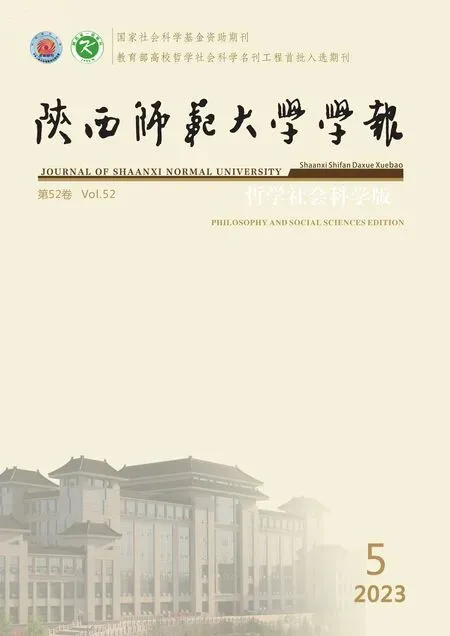论杜甫的朝班记忆与谏官形象重塑
傅 绍 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宫廷为官的经历,给杜甫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拾遗”的谏官身份,是杜甫一生最骄傲的符号,他对自我身份的描述几乎都是借用拾遗的官职特征,如“近侍”“近臣”“诤臣”“廷争”等。然而,杜甫在朝期间并不是个有政绩的谏官,甚至在他谏官经历中几乎没有一次成功的谏诤,正如他在《题省中壁》云:“衮职曾无一字补”[1]卷6。然而,在流寓西南和荆楚的漫长岁月,朝官经历的回忆却成了杜甫重要的精神滋养,在此,我们借用杜甫的诗句,把这种记忆称为“朝班记忆”。文艺心理学认为,记忆虽然是一种基于过去的心理活动,但过去往往因现在的某些因素唤起,构成与现在相对应的情绪或心理,刺激作者以选择和改造的方式去进行记忆书写。杜甫的朝班记忆书写就是通过对过去经历的选择和改造,建构了几次符合谏官要求的谏诤过程,对自己的谏官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而后人对杜甫谏官品质的认识和认可,也是基于他重塑的形象。
一、 告别罪臣心理
杜甫官八品拾遗,官职虽低,但职掌重要,“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奉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2]卷43。杜甫为官期间最悲壮的谏诤是疏救房琯,这次以失败告终的谏诤,改变了他的仕宦节奏,先是“移官”,再是“罢官”。经历这一系列挫折后,杜甫的政治心理怎么样呢?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杜甫的朝班记忆书写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杜甫在秦州时,作有《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三十韵》,直接由朝中友人的升迁而引发了对自己为官时回忆:
帝力收三统,天威总四溟。旧都俄望幸,清庙肃惟馨。杂种虽高垒,长驱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涨水望云亭。法驾初还日,群公若会星。宫臣仍点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趋栖凤,朝回叹聚萤。唤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掘剑知埋狱,提刀见发硎。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旅泊穷清渭,长吟望浊泾。羽书还似急,烽火未全停。师老资残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辞愤激,烈士涕飘零。[1]卷8
自宋代以来,这首诗理解一直存在分歧,分歧的焦点在“宫臣”以下8句中的“唤人”诸喻之所指。一种认为是自指。宋代师某云:“凡此皆甫自喻,不见用于世也。”[3]卷6宋赵次公曰:“(唤人二句)以言二公初不自眩鬻,以骏马佳人为喻。”[4]340清仇兆鳌曰“此自述索居之况”,又曰“(唤人二句)一开一阖,虽望人顾盼,而自惜廉隅,此借良马佳人为喻也。埋狱伤沉沦已久,发硎,幸见用方新”。[1]卷8今人陈贻焮曰:“自述离群索居的苦闷和感慨。”[5]503另一种认为他指。宋赵次公曰:“(掘剑二句)以言二公稍因迁用而后见其才也。”[4]341明代王嗣奭曰:“(宫官二句)谓侍御未得其人,先言此以为二子擢官得人地也。”又曰:“(唤人二句)此谓二子不轻进。”[6]卷3浦起龙曰:“(此八句)以已陪衬而转惜其发迹之迟。”[7]卷5杨伦曰:“此记其抱屈明时,及方喜迁官之事。”[8]卷6萧涤非注此诗曰:“‘官忝’二句,上句自述,以反衬下句二子之困,以带起‘唤人’二句守身自爱而不见知于人之意。”[3]卷6
本文无意讨论“自指”和“他指”正确与否。虽杜甫用典可能造成理解的多义性,但诗歌的解读总得依循一定的规则,我们且依循角色和文气连贯的规则,从上下文看,“官忝”是作者自指,“侏儒”是作者对朝中庸碌辈的蔑视,这几句叙写自己为谏官时的体验。如果“唤人”4句是他指,则在从“官忝”到“侏儒”中插入他者角色,中断了人物叙事的角色链,造成文气中断,不符合诗歌解读的规则。所以,我们在此选择“唤人”4句是自指的说法。
那么,从字义上看,“唤人”4句所喻乃入仕前的情形,而杜甫此时已在朝为官,如果是自指,的确又与他的身份不符。如何解答这个疑惑呢?如果我们从杜甫入秦州后自我角色的再认知入手,庶几可以找出答案。
杜甫入秦州之前,经历了“移官”和“罢官”两次官场变化。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离开长安时,他挑选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点,写了一首长题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亁元初从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出此门有悲往事》。这是杜甫第一次用30字以上长题,他有太多的忧愤无法在诗中直吐,只得借助诗题说明背景,以同一空间的今昔对比,表达自己内心之悲苦。题中的“悲往事”,与他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所述基本一样:“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独谒龙颜。”[1]25这段“麻鞋见天子”的艰难经历,深深地印刻杜甫的心中,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既增加他的伤感,又会强化他的“忠诚”意识。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写道: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1]卷6
此4句的蕴含,前人多释以忠厚、敦厚,如《杜诗镜铨》引顾宸云:“移官岂至尊,不敢归怨于君也;当时谗毁,不言自见。又以无才自解,更见深厚”[8]卷5。然而,这可能是用传统的逐臣心理对杜甫的超前解读,其实杜甫在对皇帝的谢表中,罪臣心理还是挺强烈的:
所以冒死称述,何思虑未竟,阙于再三。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罗网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1]卷25
应该说这才是“移官岂至尊”的真实解释。他虽自称“直臣”,但还是承认自己思虑不足、言语有阙。他自称“无才”,是自嘲,但更是对自己朝官生涯的总结。应该说,“移官”时的杜甫,有着较强的罪己心态。他所悲的“往事”,有昔日赴行的艰辛,也有自己言官不称的遗憾。
杜甫的这种心理,在他“罢官”之后有了质的改变。《立秋后题》有“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辞官入秦州,杜甫既摆脱官场束缚,也从心理和情感上拉开了与朝廷的距离,进而以另一种心态来审视自己的过去和人品。《佳人》就是杜甫对自己政治品格的重新定位。历代杜甫的注本对这首诗讨论的焦点是诗所写是否有所本。仇兆鳌说:“天宝乱后,当是真有是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恺至如此。”[1]卷7其实是否有其事并不重要,关键是杜甫为何要写这位佳人?杜甫对女性外在美并不感兴趣,他生平中不是没有遇见漂亮女性,也偶尔写过,如《壮游》“越女天下白”、《月夜》“清辉玉臂寒”之类,都只是概要地写一下,没有花过多笔墨。而在《佳人》诗中,他投入了深情,颇费笔墨。他融合了从司马相如到李延年再到曹植关于女性的描写艺术,遗貌写神,曲尽弃妇的内心世界。作品结构很简洁,“(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以上述佳人之遭遇,以下写佳人之志节”[8]卷5。这简洁的上下文结构,具有极强的隐喻色彩,与杜甫的人生遭遇高度相似。
可见,杜甫写《佳人》的动机十分明显,有无本事并不影响对作品的解读。通过《佳人》中的“佳人”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的自我认知发生了两大转变: 其一,从自责到自傲。他以“绝代佳人”自许,不再认为自己是“无才衰老”的无用之辈; 其二,从乞怜到自矜。他不再以入仕在朝为荣,而是以幽居深谷求自适。他为乞求一官,失去了太多的自尊,经历罢官转折之后,他释怀了,“日暮倚修竹”,寂寞中的优雅,失落中的清高。
以《佳人》为标志的自我认知调整深深地影响了杜甫的朝班记忆叙事,他要通过记忆叙事,重新塑造自我形象。这种重塑,首先从入仕形态开始。前引之“唤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掘剑知埋狱,提刀见发硎”4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美满的入仕情节。一者如良马美人,恃才自衿,衍期待时;一者乘时而出,大展才华。这是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却是杜甫前半生的遗憾。10年困守,求仕长安,一事无成。《乐游园歌》:“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哪有恃才待贾的尊严?入朝为官后,忠诚履职,却遭驱逐。《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去岁兹晨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满眼香。”哪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曾经的求仕和官场,给杜甫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当他调整自我认识之后,便力图在自己政治记忆中还原一个理想的自我。于是,他用“唤人”诸句的意象,替换了当年让自己难堪的经历,让记忆叙事展现一个符合自己理想追求的自我。明白此,我们就能解释“唤人”4句虽然与杜甫的生平经历不符,但他依然以此自喻的动机了。
正是有形象重塑的心理,杜甫终于敢正面当年“移官”时的遭遇了。“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旅泊穷清渭,长吟望浊泾。”杜甫在这里描绘了朝中的两类人:一类是谋图个人私利的“侏儒”,一类是心系天下的“独醒者”。杜甫明言自己被逐出朝廷、漂泊江湖的根本原因是皇帝清浊不分。忠而遭谤,信而见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屈原的影子,他以屈原式的悲忧表达自己逐臣的愤懑,一改其再出金光门时的自责与自抑,把自己与包括皇帝在内的混暗官场的格格不入真率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杜诗镜铨》所引顾宸所评“移官”诸句是对杜甫逐臣心理的超前解读,只有当他与官场拉开了距离并对自我进行重塑时,那种怨和怒才有释放的心理空间。
“忠臣辞愤激,烈士涕飘零。”秦州时期的杜甫,在向“故人”陈其“索居”之情时,再次把自己的形象鲜明地标示出来。从给皇帝写谢状到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一直都有一种罪臣心理,《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敢怒而不敢言。秦州时期,杜甫朝班记忆的自我重塑改变了他的政治心理空间,他给自己定位为“忠臣”“烈士”,向世人表达自己的忧愤,也向自己的罪臣心理告别。
二、 谏诤经历的建构性叙事
记忆是与个人性情和兴趣密切相关的心理活动,作者对往事的回忆与书写,对他此刻的情感和心理有很大的安抚或宣泄作用,而这种作用来自记忆书写对现在自我的建构性意义,建构的方式就是缺失补偿,即用回忆书写对自己过去的不足进行弥补或完善。这在杜甫谏官的朝班记忆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甫很在意“拾遗”之职,成都时期,邻居田父还直称他为“拾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今年大作社,拾遗能往否?”晚年流寓湖南与韦迢唱和时,仍以拾遗官职相称,如韦迢诗题《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等(1)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官称别名”条:“(唐)宰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拾遗是谏官,杜甫任谏官期间很敬业,即使夜晚寓直时都想着上朝之事,《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但在杜甫诗中我们很难直接找到他在朝期间的“封事”和言事活动,他对谏诤活动的记述出现在他弃官西行后。
杜甫对自己谏诤活动的回忆,是由朝班记忆触发的。他直接描述的谏诤经历有两次。一次关于吴侍御,一次关于房琯。这两次的结果都不完美,对吴侍御,是“不所为”;对房琯,是“误作为”。这两次不完美的过去是他政治人生的遗憾,对他的心理影响极大。但是,杜甫成功的谏官形象,恰恰是通过对这两次谏诤的建构性回忆书写实现的。
杜甫与吴侍御的事,在《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中有叙述。吴侍御履历不详,是杜甫在凤翔时的朝班:“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一个侍御,一个拾遗,二人同供职于那段非凡的岁月:“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在这期间,吴侍御卷入了一场冤案,遭受贬谪:
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1]卷8
这是一个审查“间谍”与良民的案件。吴侍御为少杀无辜,十分慎重细心。但还是因为没有遵照上官的意图(“失意”)把良民当间谍杀掉,而触怒了朝廷。《杜诗详注》引赵次公注曰:“详味诗意,吴之贬迁,当辩论良民,以此取忤朝贵耳。”[1]卷8面对吴侍御的处境,作为谏官的杜甫没有为他辩说,尽管与皇帝近在咫尺,也未能秉职直言:
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1]卷8
这就是杜甫在吴侍御事件中的“不作为”。但是,这段文字似未损他的谏官形象,其中的自责和伤感,刚好完成了杜甫谏官角色的建构。杜甫从他人和自我两个维度,把自己在朝时期的情怀和品质彰显了出来。从他人的维度上来说,他在叙述事件过程中,点出吴“狼狈”的原因,确立了吴侍御直臣的形象。杜甫此时的辨冤,虽然于事无补,但成就了他人的美名。所以前人评此曰:“吴之盛德,托之彩笔,千载犹生。”[6]卷3从自我的维度来说,杜甫承认自己身为谏臣,与“丹陛”近在咫尺,未能挺身直言,有负于吴侍御。但杜甫在赞赏吴侍御直节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人格认同,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自己直臣品质。而他事后的极度自责和痛苦,又隐含了“不能作为”的无奈,强化了直臣的悲苦。如明申涵光曰:“‘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真情实语,声泪俱下。王摩诘云:‘知尔不能荐,羞为纳献臣。’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他人便多回护矣。”[1]卷8
杜甫对这次“不作为”的回忆,用悔恨式的表白,表现了谏臣的良知,友人的情义。在朝班记忆书写中,他重现当年自己面对同僚蒙冤而“不作为”的过程,并用建构性的叙事,安抚了当年的谏职缺位给自己造成的心理痛苦。一次行旅中的偶遇,唤起了他的朝班记忆,对朝班记忆的建构性书写,让杜甫的谏官品质更加突出。
杜甫在房琯事情上的“误作为”,文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本文在此无意探讨其过程或结果的正确性,只是想借助杜甫朝班记忆叙事,突出其从“误作为”到“敢作为”的转变,显示朝班记忆在杜甫谏官形象重塑中的作用。
杜甫与房琯的关系,虽是杜诗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关于杜甫对此事的认知转变,人们关注得不多。如果沿着时间顺序把杜甫对房琯事件的表述进行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杜甫对此事的认识,经历了从“误作为”到“敢作为”的叙事转换,这种转变体现了杜甫本人在朝班记忆叙事中对自我形象建构的节奏。这种节奏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壮游》《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诸篇中逐步展开,向着完美谏臣的目标高度接近。这是杜甫在朝班记忆中对自己谏臣形象最成功的建构。
杜甫在房琯事件上的“误作为”,源自他自己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
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汙。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衂,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何思虑未竟,阙于再三。[1]卷25
杜甫谢表中承认有罪,自己疏救房琯是“误作为”。他的逻辑有三: 其一,董庭兰有错。他“贫病之老,依倚为非”; 其二,房琯有错。他交友不慎,“一至于玷汙”; 其三,杜甫自己有错。他“思虑未竟,阙于再三”。当时面对朝中的种种压力,杜甫认错服罪,迫于生死考量,不得不如此,我们无权苛责。但如果杜甫对房琯事件的叙述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或者这种认知,那他的谏官形象是不完美的。好在,在杜甫离开朝廷的日子里,朝班回忆的书写给了他新的政治心理空间,他建构性地再述了自己在房琯事件中的作为,在重演那段悲痛历史的同时,重塑了自己的谏官形象。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房琯病逝于阆州,时杜甫流寓于此,撰写了《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文中写道:
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1]卷25
在这个叙事语境中,杜甫最大变化是改变了罪臣心态。忠君罪己,是古代贬臣的政治话语传统,杜甫在此前写的《建都》一诗中说“牵裾恨不死,漏网辱君恩”,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但在这篇祭文中,杜甫改变了往日怨而不怒的敦厚,向君主表达出了强烈的怨怒,表现了诤臣的风骨。首先,他敢言“君”之过(阙)了。在《北征》中,他只是含蓄地说:“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那是委婉,也是胆怯。而在此时,他胆气壮了,能直面君王之遗阙,尽显谏臣之刚直。其次,他不再把过错归到自己和房琯身上,认为房琯和自己都没有过错,而是小人谗害忠良,及君王不闻良言。“何不闻”!语气多么怨怒。再次,他坦言自己曾舍身去疏救房琯,遗憾苦谏无效,并为此“终身愧耻”。唐司空图说杜甫的这篇祭文“宏拨清厉”(2)《杜诗详注》引《唐诗纪事》。按今本《唐诗纪事》无此语。,恐怕正是从文中这强烈的正直感和酣畅的叙述语气而言的。
在这篇祭文里,杜甫把当年的“误作为”改写为“敢作为”。谏诤回忆的建构性书写,成功塑造了一位正直无畏、忠诚重义的谏官形象。杜甫内心固有的政治正义感,在当年险恶的朝廷环境里被压抑,他屈从于生命的本能,以罪臣的心态去谢恩。如今,随着时空的改变,对房琯的崇敬和悲悼激发了他内在的刚正与胆气。所以,在他追忆当年时,记忆中书写建构功能让他对当时的情形进行取舍,使自己的谏诤活动与房琯的不平遭遇形成了双向联动,既突出了房琯被贬的悲剧感,又让自己失败的谏诤充满了正义和崇高感。可见杜甫在这段朝班记忆的书写中,倾注了多深的感情,难怪古人说:“(杜甫)以救房琯左迁,乃平生最大之事,故此篇亦生平最著意之文。”[1]卷之25其“著意”之处,不仅是为房琯鸣冤,更是在为自己正名。
此后,在杜甫对房琯的题写中,房琯都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悲剧良相。如《别房太尉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1]卷13《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一德兴王后,孤魂久客间。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1]卷14他把房琯与诸葛亮和谢安并提,一赞其事君之忠诚,二赞其理乱之才能。刘克庄说:“子美与房琯善,其为哀挽,方之孔明谢安。投赠哥舒翰诗,盛有称许,比之廉颇、魏绛。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或疑与素论相反。愚谓翰未败,非事前所知。琯虽败,犹不失为名相。及二人各败,又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何相反之有?”[1]卷14刘氏所言,符合杜甫的诗史笔法,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否认其对房琯评价的前后矛盾,因为在杜甫的朝班记忆书写中,房琯的形象也进行了重塑,杜甫以记忆中的建构性叙事,把房琯塑造成了一个乱世忠臣的良相形象。
同样,在此后对自己谏诤经历的书写方面,杜甫也多用传统谏臣常用的经典动作——“廷争”来描述自己当年的壮举。他在《壮游》中写道:
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1]卷16
诗名《壮游》,初读让人难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前人评曰:“上章,‘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故拈‘昔游’为题。此章,‘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当拈‘往游’为题。若作壮年之游,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壮’字疑误。”[1]卷16然细读全篇可知,“壮”字无误,乃作者有意为之。杜甫所说的“壮”,不指年龄,而是他平生几段值得回味的经历,即他所谓之“壮心”。叙少年多才,是豪迈之游;叙吴越齐赵放荡,是豪侠之游,“一幅游侠少年图”[8]卷14。叙天宝年间长安之困,是悲士忧世之游;凤翔京城之宦,是谏臣悲壮之游;叙久客巴蜀,是贬臣伤心之游。这是杜甫回忆自己豪而壮的一生,诚如王嗣奭曰:“此乃公自为传,其行径大都似李太白。然李一味豪放,公却豪中有细”[1]卷16。这里与其说“细”,不如说“变”,是杜甫由豪情万丈到豪游天下再到悲情官场终而“壮心消尽”[8]卷14的心路历程。杜甫忆写自己的廷争经历,更充满了一种侠士的无畏之气、志士的刚正气。在这一段描写中,杜甫建构性地再现了自己当年廷争的壮举,把一个心忧天下、不惧生死、执着进谏的谏臣形象塑造得更加感天动地,一扫当年“误作为”时的谨小慎微,凭借他内心的豪气,尽展一个谏臣不畏君王、敢作敢为、恪尽职守的神采。正因为如此,杜甫才把这次廷争视为他政治生命中的壮事,写到他自传式的“壮游”中,成为他人生最精彩的一笔。
也许,我们再去追问杜甫任谏官期到底有什么作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杜甫本人的感觉才是他为官的真实体验。在他朝班记忆的叙事里,谏官的良知是他记忆选择的重要心理基础,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建构性叙事,“不作为”和“误作为”在杜甫的朝班记忆中都褪去了当年的阴影,“悔无为”和“敢作为”的叙事弥补了他为谏职时的缺席感和羞辱感。于是,以称职谏官的动作描述自己的谏诤作为,几乎成了杜甫夔州时期朝班记忆的主调,如《秋兴八首》其三“匡衡抗疏功名薄”,《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迟暮宫臣忝,艰危衮职陪。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廷争、抗疏、折槛,这就是杜甫朝班记忆所定格的抗辩色彩极强的谏臣动作,恪尽谏职,刚勇逼人!
三、 谏官精神的回归
为官上朝经历给杜甫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朝官上朝有班序,是为朝班。据《通典》“文武百官朝谒班序”载:“中书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各以官为序。供奉官:左右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通事舍人,在横班。若入阁,即各随左右省主。”[9]卷75朝官上朝整齐的班序如鸳鹭之有序,故又喻为鸳鹭行,或鸳行,这也是杜甫朝班书写用得最多语汇,如《秋野五首》其五“身许麒麟阁,年衰鸳鹭群。”《社日二篇》其二“鸳鹭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等等。
杜甫客寓江湖的岁月里,时时伴随着朝班回忆。《秋兴八首》其五言晚上的梦中有:“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四言白天的望中有:“寒空见鸳鹭,回首忆朝班。”杜甫的忆朝班,既是回忆他当年在朝廷中的为官经历,又是在唤起自己作为朝官的责任与担当。所以,杜甫晚年被某种特定场景唤醒他的朝班记忆时,他往往将昔日的朝班角色移置到当今的现实朝政中,自己虽然不在场,但角色不缺席,昔日的朝班经历拉近了他与现实的距离;谏官精神的回归,调整了他审视现实的姿态。朝班记忆与现实背景相混,江湖悲士与堂庙谏臣合一,这便是杜甫晚年朝班记忆书写的突出特征。
受这种唤醒和书写机制的影响,杜甫的朝班记忆书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应酬,而是针对朝廷重大事件的角色置入,将自我与当朝朝臣形成对比,表达自己缺席的遗憾和对在朝官员尸位的不满,《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五所谓“不息豺狼斗,空惭鸳鹭行。”“惭”,兼指自己的过去和当今的朝臣。这种思维在他的《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也有体现:
群盗至今日,先朝忝从臣。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黄阁长司谏,丹墀有故人。向来论社稷,为话涕霑巾。[1]卷13
这是有感于代宗避吐蕃而离京奔陕之事而发的。杜甫一直关注此事,为此写了很多诗,有《收京》《伤春五首》《释闷》等。在这首诗中,他点出“丹墀故人”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道出了自己的谏臣心曲。《杜诗详注》引黄生曰:“七八,嘱其传语故人,见在野尚切倾葵,在朝当勤补衮,乃使至尊独忧社稷,岂不深流涕。”[1]卷13这种感情杜甫在《释闷》中也有直接表达:“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可见,作者点出自己当年“忝从臣”,是为了让朝中的故人看到他当年的作为,像他一样尽谏臣之职。正如他在《伤春》其五中所云:“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萝。”[1]卷13这种对比,正是作者忆朝班的现实寄托。
同样,对蜀中的战事,杜甫也十分关注,虽无力上书,但在送友之时,也适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其《赠李十八秘书别三十韵》即如此。诗中,杜甫也是以朝班记忆入题,忆写当年同朝事君的往事:“往时中补右,扈跸上元初。”“通籍蟠螭印,差肩列凤舆。”接着便借送友人入朝,委婉表达了对西蜀战事的见解:“对扬抏士卒,乾没费仓储。势藉兵须用,功无礼忽诸。”这几句大有深意。仇兆鳌注此曰:“其奏对君前,当以师老财匮为言。盖全蜀之势,今方藉兵,不得不用,而诸将冒功无礼,如所谓抏士卒、费仓储者,其可忽之而不问乎?”[1]卷17可见其思虑之深。他以忆朝班为媒介,意在唤起李秘书的谏诤意识,希望他进京之后能将蜀中战事的得失如实报告朝廷。这首诗的结构也体现了作者角色置入的意识,全诗30韵,第一部分言昔日扈从,第二部分言蜀中战事,第三部分叙送别。前两部分中,作者忽略了自己今昔身份的变化,用谏官角色与入朝友人对话,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济时精神。只有结尾4句才明言两人角色的不同,充满了无尽的感伤:“杜陵斜晚照,潏水带寒淤。莫话清溪发,萧萧白映梳。”但其主旨却并不在此,而是希望友人此次入朝能发挥济时的作用:“此行非不济,良友昔相於。”杜甫寄情之深,于此可见。
杜甫在巴蜀时期,以“闷”为题的作品较多,如《释闷》《遣闷》《拨闷》《解闷》等。多数诗的写作意图较为明晰,如《释闷》,讽代宗奔陕,《拨闷》戏言以酒去闷之法,《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戏言以诗酒遣闷。唯《解闷十二首》,内容较杂,难一语明言。诚如郭曾炘云:“数篇之中,忽而寄讽,忽而寓感,忽而自喻,旋褒旋贬,议论错出,令读者为之昏眩。”[10]355但在这组诗中,我们的确能读出杜甫心中之闷,“一辞故国十经秋”的经历,让杜甫目睹异乡之风物,生发了无尽的思绪和难解的郁闷。王嗣奭云:“非诗能解闷,谓当闷时,随意所至,吟为短章以自消遣耳。”[6]卷8细品这组诗可以发现,触动杜甫愁闷的,有他昔日的友人,更有国家兴衰的回忆。后者源自其朝班记忆所唤起的谏诤意识,这就是他最后4首集中写荔枝诗的动机: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翠瓜碧李沈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
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骀背死,劳生重马翠眉须。[1]卷17
据《唐国史补》“杨妃好荔枝”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11]19这是关系唐王朝兴衰的大事,杜甫自然深有感触。杨伦曰:“四首皆借荔枝遣兴,蜀岁贡荔枝,志所触也。”[8]卷17杜甫虽然不是玄宗朝的谏官,但亲历唐玄宗晚年宠幸外戚、荒淫享乐而致天下大乱的昏聩政治,当时就作《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进行讽刺。当年玄宗劳民伤财为杨贵妃千里贡鲜荔枝,是京城士人讽议之焦点。而当杜甫来到荔枝的产地,回想安史之乱给天下百姓带成的灾难,他更是感慨万分。荔枝引发了杜甫无尽的郁闷,唯有将它与国运联系起来讽吟,才能让自己内心的郁闷得以消解,于是他集中笔墨,连写了4首。王嗣奭曰:“公因解闷而及荔枝,不过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还复入长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讽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盖伤明皇以贵妃召祸,则子孙于其所酿祸者。宜扫而更之,以亟苏民困。公于《病橘》亦尝及之,此复娓娓不厌其烦,可以见其忧国之苦心矣。”[1]卷17“玉座”“丹宫”明指皇宫,杜甫以缺席叙事的方式,描述了为敬贡鲜荔枝所造成的众生劳苦相,感慨深沉。“云壑布衣骀背死,劳生重马翠眉须”,直启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甫不是玄宗朝的朝班,但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故国之思唤起了他对故人和往事的记忆,记忆中的谏臣意识让他对荔枝生发了国家兴亡之沉思。
晚年的杜甫漂泊异乡,但心在济时,有一种报国无门的焦虑。他《岁暮》中自述道:“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1]卷12此时,如果杜甫的朝班记忆被唤起,其内心深处的谏臣意识也会激发为一种济时热情。他把自己最推崇的“敢爱死” 的谏诤精神赋予他人,他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他人身上,借以显示一个称职谏臣的品质和境界,这在他送别严武的诗中表现得最直接。杜甫与严武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府主与幕僚的关系,他们有着深厚的朝班之谊。杜甫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是他在秦州时期写的一首长诗,诗中充满了对往日朝班生活的回忆,虽然他们都因房琯事件而被贬,但杜甫对严武还是寄予了厚望。所以当代宗即位,严武再召入京时,杜甫激动万分,写下了《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这不是杜甫的私情,而是无数乱世离乡者的心愿,是朝纲重振、天下安宁的标志。这种心愿构成了杜甫晚年恋世情感的重要成分,朝班记忆作为他的潜意识思维,让他经常打破时空,今昔并写。这类思维中虽然谏臣意识不明显,但忆朝班、归朝班的情感交织,依然能让人感受他的政治期待。如《太岁日》:
楚岸行将老,巫山坐复春。病多犹是客,谋拙竟何人。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荣光悬日月,赐与出金银。愁寂鸳行断,参差虎穴邻。西江元下蜀,北斗故临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脱要津。天边梅柳树,相见几回新。[1]卷21
诗歌的标题是写太岁日,当为正月初三,而诗中实写元日之事。注家们对此的解释也不一样。赵次公曰:“正月一日谓之太岁日,盖当年太岁之始日也。”[4]1 244王嗣奭认为有误,“注以初三日戊申为太岁日,然‘衣冠拜紫宸’乃元日诗也。须再订”[6]卷9。潘鸿曰:“太岁日,疑当时以是为庆,故诗有阊阖、衣冠等句。”[1]卷21其实联系杜甫当时的处境,又可以忽略时间的具体性,他是以太岁日的庆贺联想到了元日,由此触发了他的朝班记忆。在朝班记忆的书写中,他忆写当年元日“衣冠拜紫宸”的荣光,感叹而今“愁寂鸳行断”,心情极为感伤。“谋拙”之慨耐人回味。当年被逐出朝廷,是他“拙”还是君“昏”,杜甫内心十分清楚,所以才无悔自己“生涯脱要津”。在此,杜甫虽然没有明写谏诤,但在忆朝班的感伤中,还是有对自己当年秉直谏诤经历的肯定,隐含着自己引以为傲的诤谏意识。这种感觉在他的《人日》(人日为正月初七)也有同样的表露:
佩剑冲星聊暂拨,匣琴流水自须弹。早春重引江湖兴,直道无忧行路难。[1]卷21
世少知音,怀才不遇,皆源自“直道”。“直道”是谏臣的基本素质,亦是最高境界。仇兆鳌说:“直道处世,固属正理,但用之此诗,却非本意。当时一救房琯,十载流离,尝云‘薄俗防人面’,又云‘便笺狎楚童’,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岂敢自矜其直,与世无患哉。”[1]卷21此语恐误解了杜甫。杜甫自入秦州之后,凡言房琯之事,再无忧恐,更无悔意。在此诗中,剑“暂拨”,言对世间失望;琴“自弹”,言无求知音。他以“直道”言己,自傲于世,无悔当初,“有浩然一往意”。[8]卷18可知,杜甫故作狂诞的孤傲中,也透露着对自己谏诤经历的自赏。也许,节俗的欢乐是他人的,杜甫只是借节俗的媒质,唤起自己的朝班记忆,以今昔角色的反差,激发自己对往日角色的向往。
四、 结 语
拾遗,作为杜甫政治生涯中的短暂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政治符号。杜甫的朝班记忆书写,大都围绕着他的拾遗经历展开,那段失败的谏诤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因记忆书写中的重塑功能而得到了安抚。从忠臣身份自认到谏职践行建构再到谏臣意识回归,让杜甫的谏官形象更加鲜亮突出,是朝班记忆书写,完成一段文学和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