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不能忘情吟》中“不能忘情”的一些内涵
陈嘉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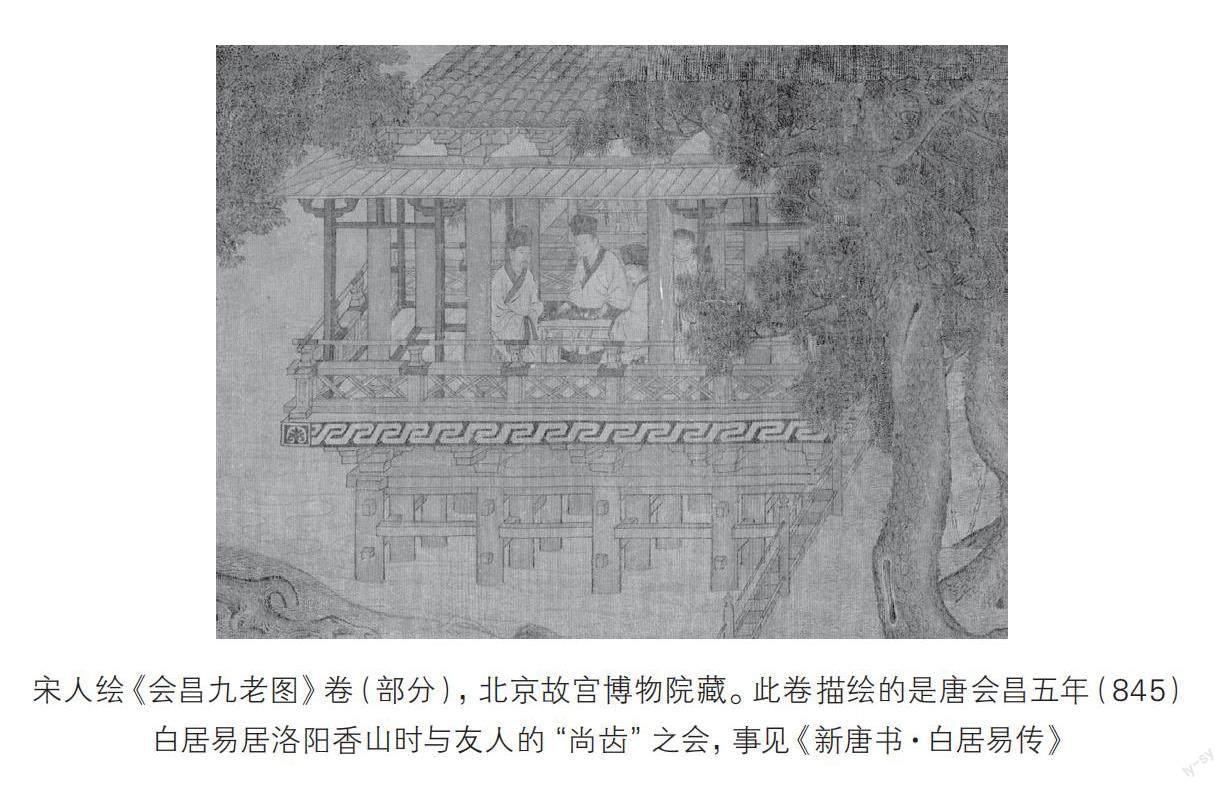
《不能忘情吟》是白居易写于开成四年(839)的作品。在“序”中,白居易讲述了自己取消放妓卖马计划的事:
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馀,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外,将放之。马有骆者,驵壮骏稳,乘之亦有年。籍在长物中,将鬻之。圉人牵马出门,马骧首反顾一鸣,声音间似知去而旋恋者。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娈有辞,辞具下。辞毕涕下。予闻素言,亦愍默不能对。且命回勒反袂,饮素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句随吟之短长也,凡二百三十五言。噫!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
尽管此文简短,但研究者们对“不能忘情”的内涵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多数论者对“不能忘情”持肯定态度。学者们主要认为这体现了白居易“中人”的自我认知(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不能忘情”是“支撑白诗抒情性的品质”(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对“不能忘情”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较少。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谴责白居易把人和马等同的“虚伪”(裴斐《看不透的人生》)。
虽有诸多文献珠玉在前,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应如何解释白居易曾取消放妓卖马的计划,一年后又实施的行为?作为妓的樊素在诗人眼中是人还是物?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来发现《不能忘情吟》中“不能忘情”的一些内涵所在。
一 作为物的妓与马
在《不能忘情吟》的开头,白居易对妓与马的介绍一如商品简介。据过往经验,若无“长物”,诗人会感到心静与自得。作于大和四年(830)的《销暑》中有“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诗人对个人境遇的认知影响着他对“长物”的态度。在作于大和七年的《把酒》中,白居易自觉已“拖金紫”“及暮齿”,受到命运优待,故不必占有“长物”,吃饱睡好即可:“朝餐不过饱,五鼎徒为尔。夕寝止求安,一衾而已矣。此外皆长物,于我云相似。”
在唐朝,妓、妾地位低下,“以妾换马”在白诗中也能见到。例如,在《酬裴令公赠马相戏》中,白居易委婉地拒绝了裴度“妾换马”的提议:“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诗人对以妓换马大致持一种不贬斥也不实践的态度。
尽管如此,白居易仍视妓女为物品。在诗人看来,妓是一个薄情的群体。《有感三首·其二》中,因妓女频繁易主,白居易直言“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妓与马被诗人以同样的角度进行评价。而对于老去的妓女,诗人也不满意。《追欢偶作》中,有“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若说不能长久地陪伴主人是妓女无情的表现,那么嫌弃妓女的衰老、频繁更换妓女也可以说是白居易无情的表现。
然而,当写到某位具体的乐妓时,诗人的感情色彩会发生变化。《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中有“四海故交唯许汝,十年贫健是樊蛮。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诗中,樊素、小蛮与白居易的“四海故交”并列。尽管她们是妓女,但相伴的时光使白居易对她们产生了更深的感情。
综上,作为群体的妓女在白居易眼里并不是“深情”的代表,他覺得培养妓女并不值得,并频繁换掉老去的妓女。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视妓女为物品。但另一方面,少数得以陪伴他多年的妓女成为诗人一段时光的见证者,有着超出普通物品的意义。因此,妓女虽然被白居易视为物品,却并非普通的物品。
二 《不能忘情吟》—对物的深厚感情
认识到白居易将妓与马视为非一般的物品后,回到《不能忘情吟》中,既能理解白居易放妓卖马的计划,又能注意到,诗人并非“无情”。何以见得?“马骧首反顾一鸣,声音间似知去而旋恋者”,白居易能感知骆马的情感,而这是无情之人做不到的。
白居易对马有着深厚的感情。大和元年,白居易作有《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诗中历数和小白马有关的记忆,并直言对死去的小白马“不能忘情”。此后,他仍未忘记小白马。作于大和九年的《往年稠桑驿曾丧白马题诗厅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中,有“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
对亲人、挚友“不能忘情”,从魏晋到中唐,已被明白地道出。但对物的“不能忘情”,若无适当的理由,很容易招致像陆机对魏武帝那样的指责(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于是遂愤懑而献吊云尔”)。白居易面临着这样似有若无的压力,于是有了“自知无乃太多情”的反思。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多情”超出了限度,但同时以此为借口,道出了自己对马儿的思念。
四年后,《不能忘情吟》中的白居易显得已经“忘情”了。然而,“事来搅情”,他本秉持着绝对的理性,但樊素的陈词强调她与骆马都有“情”,并反问白居易是否“无情”,令诗人深受触动:
辞曰:主乘此骆五年,凡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隤。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咍,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曰: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在《不能忘情吟》的“序”中,白居易引用了王戎的话。而白居易被打动的过程,则令人想起《世说新语·伤逝》中山简被打动的场面: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较之王戎,山简的情感表达是经人点拨的结果。他的“更为之恸”既是为早亡的孩子,又是为失子的、有情的父亲。王戎的回答体现了魏晋士人开始在“情”这一方面不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他强调的是“我辈不能忘情”,而非反驳将孩子视为“物”的说法。对王戎来说,无论孩子是“人”还是“物”,在永远的离别面前,一个有“情”之人不可能不为之悲。
在《世说新语·言语》中,还有一则关于“不能忘情”的故事: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顾敷能从忘情与否的角度看寺中弟子的行为,更胜一筹。不过,结合王戎丧子的故事,可以发现,人的“不能忘情”为“泣”提供了可能性,但人必须得意识到“不能忘情”的合理性,“泣”才会成为人的行为。否则,即便心中有“情”,也可能会去劝一个哭泣的人“何至于此”。
如果读者曾经被王戎的言语打动,并形成了前面所提的关于“不能忘情”的认识,那么,他们读到《不能忘情吟》时,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观念是否需要有新的提升。于是,通过使用“不能忘情”这个字眼,以及设置启发与被启发这对关系,白居易使“不能忘情”的对象扩大到物,并启示读者进一步发现“情”更丰富的内涵和价值,让自己的“情”得到世人的接纳。放妓卖马的行为本身在当时是合理且对双方有益的,一年后樊素也离开了白居易。但在写下《不能忘情吟》的这一天,由于妓与马对主人有情,白居易对妓与马这意义非凡的物亦怀有不能忘的深情,他们推迟了最终必有的离别,暂时沉浸在动听的《杨柳枝》和醉人的美酒中。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