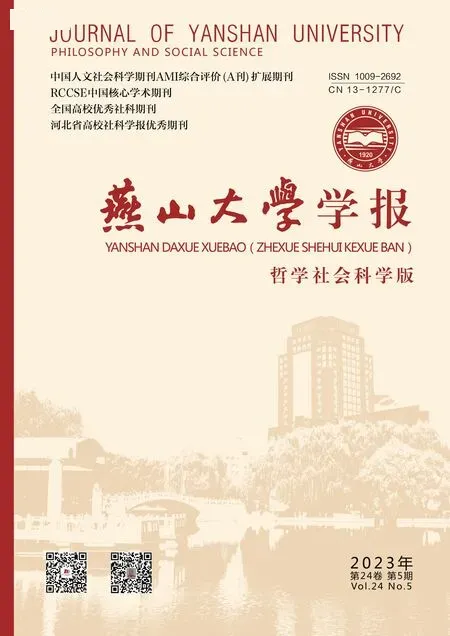《文心雕龙》与李奎报的“九不宜体”观
朴性日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 引言
李奎报(1168—1241),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著名文人,《东国李相国集》与《白云小说》的作者。与李奎报同时期的《破闲集》作者李仁老(1152—1220)、《补闲集》作者崔滋 (1188—1260)都是高丽汉文诗话的奠基者,后来活跃在朝鲜王朝第九代国王成宗在位期间(1470—1494)的代表文人徐居正(1420—1488)所著《东人诗话》《东文选》更能突出古代韩民族汉文诗话的独创性。刘强教授认为,从诗学风格来看,中国诗学的两大主流,唐诗与宋诗在高丽都已经被输入和接受,唐宋诗歌对高丽诗坛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诗学理论来看,自《诗经》、萧统《文选》所包含的文学理论,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乃至宋代诗话著作都在高丽诗坛留下了痕迹。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高丽汉诗的自身创作实践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因而到高丽末期,兼容并蓄的文学整合便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趋向①。至今中国探讨李奎报对中国诗学接受研究论文有:邹志远《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东疆学刊》,第15卷第4期,1998年10月)、马也《朝鲜作家李奎报对曹丕“文气”论的阐发与变异》(《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6卷第6期,2017年6月)等。韩国国内探讨李奎报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方面的文章有:金昌庆《李奎报对魏晋文人的认识》(《东北亚文化研究》第16辑,2008)、文承勇《李奎报文学论对六朝文论的接受状況》(《外国文学研究》第12号,2002年11月)等。毋庸置疑,李奎报在《论诗中微旨略言》《答全履之论文书》文章中提出的诗歌创作论有这样的特征。笔者认为李奎报提出的“九不宜体”最具文学批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足以成为本理论的参照对象。
二、从《文心雕龙》看“九不宜体”之用事
李奎报在《论诗中微旨略言》一文中提出,在诗歌创作中不应该犯“九个错误”:
诗有九不宜体,是余之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一篇内多用古人之名,是“载鬼盈车体”也。攘取古人之意,善盗犹不可,盗亦不善,是“拙盗易擒体”也。押强韵無根据处,是“挽弩不胜体”也。不揆其才,押韵过羌,是“饮酒过量体”也。好用险字,使人易惑,是“设坑导盲体”也。语未顺而勉引用之,是“强人从己体”。多用常语,是“村父会谈体”。好犯丘、轲,是“凌犯尊贵体”也。词荒不刪,是“莨莠满田体”也。能免此不宜体格,而后可与言诗矣。②
值得一提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将“位体”定在“六观” 之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列“八体” 而论述作品的风格,并在《文心雕龙·封禅篇》中指出明确大体仍是构思的第一步,还在《文心雕龙·镕裁篇》中谈及创作过程时称首先要做的是设定感情后定题。③《说文解字》将“体”字解释道:“总十二属也。”④在这点上,李奎报和刘勰在文学创作批评方法上有相同之处。倘若站在《文心雕龙》的立场解释“九不宜体”,乃成为“在创作过程中的九种禁忌”的意思。通过考察原文中列出的“九不宜体”可知,李奎报并不是彻底的排斥用事,而主要批判过度重视修辞。全莹大教授把“九不宜体”分为四个特征而总结说:第一是别过于滥用用事;第二是避免换骨夺胎;第三是不要过于依赖押韵法,但也不该过于脱离标准方法;第四是在修辞上避免险字和下流话。⑤显然,刘勰和李奎报都讲究创作的“体”。古今中外,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构思上,“体”始终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再说“体”是一个深奥而多样的概念。《文心雕龙·通变篇》云:“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⑥,这视为李奎报的创作批评论,虽然仅限于“作诗”方面,但在文章中的主旨仍然保持“体”的重要性。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云:“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又云:“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表示文章本来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很难擅长所有体裁。魏文帝曹丕在原文中列建安七子而评论道: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⑦
众所周知,这是支撑《典论·论文》下半句中出现的“文气”概念,高丽时代的 “文气”概念也受其影响很大。⑧原文中“学无所遗,词无所假”界定了成功文人的特性,都是善养浩然之气。在这点上,《文心雕龙》同样主张作家需要精通“经典(宗经)”和“训诂(练字)”。将该文意放在李奎报“九不宜体”里面,“九不宜体”是包含文章体制的内外因素:“载鬼盈车体”“拙盗易擒体”和“凌犯尊贵体”是古人之意与作者之意的关系,“挽弩不胜体”和“饮酒过量体”是押韵规则与作者在文章表达上对押韵的掌握间的关系,“设坑导盲体”和“强人从己体”是文字规范与作者对文字处理间的关系,“村父会谈体”和“莨莠满田体”是意境与作者的严肃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九不宜体”内外因素分类可知,《文心雕龙·宗经篇》“体有六义”⑨足以可作为“九不宜体”的参照点。在这里,“设意”的前提是要把握“体”。李奎报在《上赵太尉书》一文中谈及自己的学习经历道:
余自九龄始知读书,至今手不释卷。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至于幽经僻典、梵书道家之说,虽不得穷源探奧、钩索深隐,亦莫不涉猎游泳、采菁摭华,以为骋藻之具。又自伏羲以来,三代两汉秦晋隋唐五代之间,君臣之得失,邦国之理乱,忠臣义士奸雄大盗成败善恶之迹,虽不得并包并括,举无遗漏,亦莫不截烦措要,览观记诵,以为适时应用之备。其或操觚引纸题咏风月,则虽长篇巨题多至百韵,莫不驰骋奔放笔下停缀,虽不得排比锦绣编列珠玉,亦不失诗人之体裁。
通过原文可知,对李奎报亲身经历的论述可放在《文心雕龙·神思篇》“陶鈞文思” 进行探讨。《文心雕龙》举例说明“用事”,如司马相如、杨雄等著名作家是通典范的。⑩与李奎报同时代的李仁老《破闲集》主张“錬琢之工”。后来的高丽文人崔滋在《补闲集》中提及高丽中期文人俞升旦(1168—1232)对当时高丽文人用事的梳理,高丽文人写作时想要用事,作文上引用《六经》与《三史》,在作诗上引用《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文人的文章,可是不该从此用事。《文心雕龙·事类篇》云:“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这是警惕作者用事上的错误。《文心雕龙》举了引用上的错误,其中陆机(261—303)的例子综合地包含用事上的问题。陆机将“日葵”比喻成“葛藤”是谬误,他认为“庇”字比“卫”字用得恰当,是陆机在文章措辞上的问题。实际上,陆机《园葵》诗中的“ 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的前一句取自《左传·成公十七年》“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下一句取自《左传·文公七年》:“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則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此,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事类》篇的陆机《园葵》可视为“九不宜体”的第八个“凌犯尊贵体”的例子。刘勰总结说 “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沈密,而不免于谬”,刘勰的总结想要表明他们的谬误导致作品之“体”的消失。《补闲集》有提及高丽诗僧元湛读李奎报《南游诗》“秋霜染尽吴中树,暮雨昏来楚外山”,觉得本诗句在用事手法上存在问题,则说:“今之士大夫作诗,远拖异域人物地名,以为本朝事实,可笑。”崔滋给“用事”下定义道:“凡诗人用事不必泥其本,但寓意而已。”诗僧元湛对李奎报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可是元湛的视角不过是仅限于诗境的风土人情而已。正如崔滋总结那样,如果李奎报的本诗没有失去“体”,那么他就不会犯陆机在《园葵》中“用事”的错误。回到作诗中的用事问题上,《文心雕龙》和“九不宜体”始终围绕“体”而进行批评。
三、“九不宜体”对“为文而造情”之批判
《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作诗的原理。后来生成的陋习“为文而造情”是对其原理的叛逆。不只刘勰一人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强烈批判该陋习,高丽时代的文人也对此进行了批判。李奎报“九不宜体”中的“设坑导盲体”和“强人从己体”是恰到好处的例子,而且这两个文体不只是文字与作者间的关系。若从“村父会谈体”的特征考虑,也包含对过度重视修辞的批评。崔滋在《补闲集·序》中提及当时文人崇尚过度修辞问题道:
若剽窃刻画,夸耀青红,儒者固不为也。虽诗家有琢练四格,所取者,琢句练意而已。今之后进,尚声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语生。练对必以类,故其意拙,雄杰老成之风,由是丧矣。
实际上,“九不宜体”的第六个体“村父会谈体”接近于南宋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广义上说,是过度重视修辞引起的一种弊端。有趣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篇》不完全反对过度修辞,是因为《诗经》《书经》为了教化以及训诫也采取夸张手法。固然,后来文章也需要夸张手法。用事手法也可以支撑夸张手法,《文心雕龙·丽词篇》云“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词,则昏睡耳目”,一方面蕴含用事手法也是一种过度修辞,若用得普普通通,反而使读者感到疲倦。因此,前章节《文心雕龙·情采篇》之“赞”云“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彩寡情,味之必厌”,表明过度修辞是缺少情感。虽然《文心雕龙》没有讲到“村父会谈体”,可是从批判修辞上的意义来看,“村父会谈体” 有可能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作者在作品中过于使用平常语言,另一个是指作者不通晓经典可是想展现自己的文采,但文章的文采颇为平庸。《文心雕龙·指瑕篇》也提及当时文人在“用事”修辞上的陋习道: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
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排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显然,刘勰和李奎报都严厉批评他们所在时代的文风弊端。李奎报《论诗》中在涉及到相似问题时道:
迩来作者辈,不思风雅意。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间嗜。意本德于天,难可率尓致。自揣得之难,因之事琦靡。以此眩诸人,欲掩意所匮。此俗已成,斯文垂坠地。
这诗句与当时高丽王朝的社会风潮有一定关系。据《高丽史》记载,第四代国王光宗在位年间(949—975)至第三十四代国王恭让王在位年间(1389—1392),“诗、赋、颂”是高丽王朝时代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可是后来有些学者上奏批判当时考生过度重视修辞的问题。李岩读解《论诗》的本诗句说主要揭露和批判充斥当时高丽文坛的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作者严肃批评当时所谓的诗人辈不顾文学自身的规律,不思古代《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的“风雅意”,“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而得意的行为。朝鲜汉文学原来就是全盘吸收中国文学文化的各种机制和形式,存在着模仿的可能性,所以朝鲜历代进步文人都为防止这种模仿之风而百倍警惕。《文心雕龙·附会篇》对过度重视修辞美有言:“依赖于技巧一定会忽略整体架构”,按照《附会篇》的解释,李奎报在《论诗中微旨略言》中的“诗以意为主”里的“意”是指 “体”,因而李奎报在下一句说“缀辞次之”,这不光意味着“缀辞”是作诗的第二个难关,也是提醒明确“体”之后,开始使用修辞技巧。《文心雕龙·定势篇》也同样批判当时文人重视过度修辞美,但本篇探讨的是过度修辞美上的用事:
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
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
通过考察原文,能联想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的“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而这两个现象点明了《文心雕龙·总术篇》中的“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西晋时期的挚虞在《文章留别论》一文中也批判过度修辞美,说孙卿、屈原的文章有古诗的本意,但到了宋玉的时代,文章修辞就开始华丽以及浮华。李奎报《论诗中微旨略言》中提出了两个诗格:“山人之格”“宫掖之格”,前者是纯粹意义上的诗格,而后者是奢侈夸张的诗格。我们之所以能看出他批判的是“宫掖之格”,是因为李奎报在《论诗》中云:“以此眩诸人,欲掩意所匮。”本诗句可视为专门批判“挽弩不胜体”和“饮酒过量体”,原因在于这两个“不宜体” 的问题在于作者虽然重视修辞,但反而忽略了修辞上的规范。《文心雕龙·声律篇》云“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脣糺纷”,表示作者过于追求造出新词,从而引起文章语言上的不通顺问题。得了“设坑导盲体”和“强人从己体”的病,那么“镕裁”可以做处方药。《文心雕龙·镕裁篇》给“镕裁”下定义说:“规范本体谓之镕,翦韯浮辞谓之裁”,也就是说,“镕裁”能解决在押韵和修辞上有问题的 “体”。从原理的角度分析“镕裁”,“镕裁”既肯定“用事”,又肯定“修辞”。
四、为“新意”而“通变”,为“通变”而“新意”
前文分析了“九不宜体”对“用事”与“修辞”的批判。实际上,“九不宜体”始终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对该问题的特征,李奎报在《答全履之论文书》一文中说:“虽《六经》、《子史》之文,涉猎而已,不至穷源,况诸家章句之文哉?既不熟其文,其可效其体盗其语乎?是新语所不得已而作也。”原文中的“新语”不该理解为“创造新的词汇”,更不该理解为“一种逃避经典范式”,在此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疑问:为“新意”而“通变”还是为“通变”而“新意”?李奎报又说道:“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诗,然后效而能至也。否则剽掠犹难。譬之盗者,先窥谍富人之家,习熟其门户墙篱,然后善入其室,夺人所有,为己之有,而使人?知也。”这并不是李奎报想要辩护“新语”,也许对李奎报而言,“新语” 是在作品中体会到的温故而知新,而不是彻底叛逆经典体制。那么,“九不宜体”是以实现拥有“新语”和“新意”为目标的吗?
在朝鲜王朝初期文人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指出李奎报可视为用事论者。虽然李奎报曾说过“要脱出陈腐而做出自己独创的表达,绝对避免借用过去的诗歌语言”,可是李奎报的诗文里面仍然存在用事的痕迹。徐居正举了三个例子道:其一,李奎报的诗句“黃稻日肥鸡鹜喜,碧梧秋露凤凰愁”是袭用杜甫的诗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其二,李奎报的诗句“洞府徵歌鼓玉案,教坊选妓醉仙桃”模仿的是李白的诗句 “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其三,李奎报的诗句“春暖鸟声软,日斜人影长”是借用杜荀鹤的诗句“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三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作品的气氛与原诗几乎相同,只是字面上有所变化。徐居正在原文中将李奎报作诗上的例子称之为“用事”,而笔者认为以上三个例子都有“换骨夺胎”的痕迹。在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当时两国文人对用事的概念理解有差异,中国说的“用事”一般指的是“典故援用”,例子中的李奎报诗句主要是效仿唐代大诗人的创诗句,重点不在于以他们的故事作为作诗题材,那么古代韩国说的“用事”是指“作为典范”。根据该特征重新看“九不宜体”,李奎报的文学主张是“纯属于作者”。通过考察徐居正在文章中举过的李奎报诗句,可知在李奎报那里的“用事”概念可从《文心雕龙》“通变”概念而考虑。《文心雕龙·通变篇》批判当时才子道:“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这是主张“通变”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李奎报凭“九不宜体”想要表述的是作者都需要“通”与“变”,这两个因素都不能缺,而刘勰在《通变篇》之“赞”中云“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倘若将“新意论”和“用事论”分开讲,乃同等于“变”与“通”之争。那么“九不宜体”是李奎报的“新意”还是他的“新语”?笔者认为,“九不宜体”是两个问题:即“为新意而通变”与“为通变而新意”。
五、 结语
综上所述,从刘勰《文心雕龙》尝试确定“九不宜体”,使我们重新考察李奎报到底是属于新意论者还是用事论者这个问题。“论诗”这标题本身已表明,李奎报的批评论仅限于作诗方面。如果从《文心雕龙·明诗篇》“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而考虑,“九不宜体”则包含很多意义范畴。笔者认为,被后来学界称之为“新意论”与“用事论”概念尝试强制界定李奎报的理论趋向,而其尝试看似将李奎报的理论不仅与陆机《文赋》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可绑在一起谈,而且与挚虞《文章流别论》的“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捉”也可放在一起谈。就算其尝试的逻辑是成立的,但这不仅仅是只考虑了很少一方面,而且貌似是过于站在朱光潜《诗论》对“诗话”特征的解释。有另一个解释说所谓 “东方诗话学的诗学文化体系”,就其内容而言:既包括诗话的诗学批评,把诗话作为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独特样式来研究;又涵盖了诗话所体现的诗文化特质,把诗话作为一种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诗文化现象来研究。回到主题,虽然刘勰与李奎报跨越了几个世纪,《文心雕龙》足以作为“九不宜体”的尺度。《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指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整体来看,李奎报“九不宜体”可视为《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心思想“洞晓情变,曲照文体”的扩展版。关于“体”的重要性,曹顺庆教授在著作《中西比较诗学》“艺术风格论”一章中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风格论中,“体”与“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气”是“因内而符外” 的东西,它是作家本身对风格所起的决定作用,着眼点主要在作家本人。而“体”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当然“体”离不开“气”,有了“气”,才可能有“体”。从《文心雕龙》的角度分析“九不宜体”,实际上是借刘勰的文学理论来看李奎报的诗学,“九不宜体”只不过是分析的切入点而已。
最后,我们要回答“九不宜体”到底是属于李奎报的“亲身经历”还是属于“当时文风的弊端”这一问题。此问题可以从《文心雕龙》的写作主旨来考虑。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及当下论文意的文章时,他认为《文心雕龙》尝试从整体来探讨文意。若只看标题,“文心”与“雕龙”都包含文意的内外因素,而“九不宜体”只包含“内”;如果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体”,那么“九不宜体”也具备文意的内外因素。
注释:
① 刘强著:《高丽汉诗文学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第153页。
② 【李朝鲜】洪万宗撰;赵季,赵成植笺注:《诗话丛林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33页。收录了【高丽】李奎报的《白云小说》。
③ “位体”出自《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九篇》: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工商。“八体”出自《文心雕龙·体性第二十七篇》:若综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奧,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直强调“体”的重要性,譬如在《文心雕龙·封禅第二十一篇》云:“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还在 《文心雕龙·镕裁第三十二篇》云:是以草创鸣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⑤ 【韩】全莹大、郑尧一、崔雄、郑大林著:《韩国古典诗学史》,首尔:弘圣社,第85页。
⑥ “通变”篇名的“通”指的是“体”。因此,《通变篇》的首句“夫设文之体有常”表明“通” 是原理。《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篇》: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
⑦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十二·魏文帝典论论文》。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主编:《昭明文选译注》(第六卷),长春:吉林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71-72页。

⑨ 出自《文心雕龙·宗经第三篇》: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
⑩ 刘勰在《文心雕龙》列举过可作为模范的作家。例如,《文心雕龙·事类第三十八篇》举了杨雄的例子道: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篇》举了司马相如和东汉经学家马融的例子道: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马融鸿儒,思洽登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