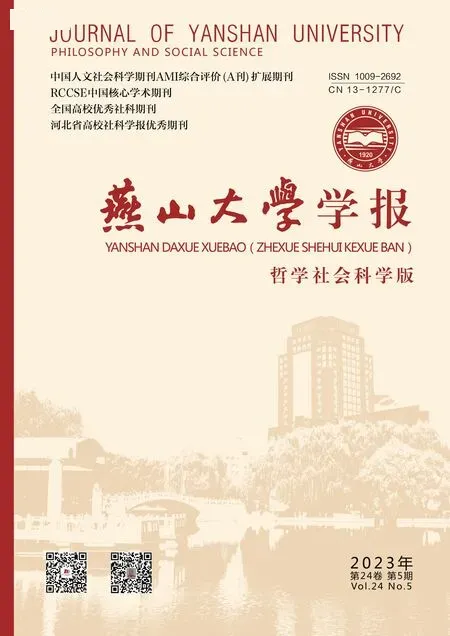易安词英译误读的哲学阐释学观照
于锦涛,杨彩霞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一、 引言
李清照的“易安词”兼有婉约、悲郁之特点,其英译活动肇始于1926年冰心在韦尔斯利大学完成题为“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的硕士论文之际。据粗略统计,选译、全译易安词的作品已有51本[1]。20世纪70年代之后易安词英译活动日渐兴盛,相继出现的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徐忠杰以及许渊冲的英译本都受到了译学界的广泛关注。揆诸当下,李词研究大抵可分为两类:其一为译者研究,研究范畴主要围绕善用“以诗译诗、音韵美、膨胀性和解释性、跨文化”[2]48四大翻译原则和以“重视原文主旨传译、哪怕牺牲原文的音韵美”为翻译风格的徐忠杰、兼有“基督佛教徒(Christian Buddhist)、诗人(Poet)、政治激进者(Political Radical)”[3]229三重身份的王红公、主张“再现原词的‘音美’,并不是机械地字字对译”[4]75的许渊冲三位译者;其二是翻译本体研究,其主要包括易安词中文化负载词、叠字的翻译策略研究,词中女性形象的嬗变研究以及易安词译介综述等。
传统观念里,作者往往被视作文本意义的唯一来源,是解读文本的绝对权威。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作者权威被消解,人们对所谓的“正读”“精准阅读”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出于对文本多解性的考虑,解构主义理论批评家布鲁姆(Bloom)提出了误读这一概念[5]。误读是指理解者基于自身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和文化视角等对文本进行的解读。由上述定义可知,误读必然会导致读者对同一文本的差异化理解。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易安词的众多英译本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存在差异,而每一种解读都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随着哲学阐释学思想兴起,人们从理论层面上对误读有了新认知。在哲学阐释学思想的观照下,重点以伽达默尔(Gadamer)的“前见”和“视域融合”哲学理念为理论指导,通过对比易安词许渊冲、徐忠杰和王红公英译本,试为易安词英译中的误读寻求哲学解释,为诗词英译实践带来启迪。
二、 译者的前见与易安词英译
翻译,作为中外文学关系发生的第一现场,本身就涵涉了阐释。[6]5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伽达默尔声称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之中无可避免地掺杂着解释者自己的思想[7]496,并且他援引“前见”一词来表示理解文本或认识事物之前,由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地位等因素而构成的人类先存的心灵状态[8]38。文化背景、人生经历各不相同的几位译者的前见自然也相去甚远,静默的文本借助于他们的前见变得鲜活生动、多样化起来。
李清照一生历经两宋,其词前期写闺阁之愁闷,后期悲家国之离乱,个人情愫与历史内涵都寓居于词作之中。“诗译英法第一人”的许渊冲家学渊源,从事文学翻译六十余年,译著等身。文化层面上,他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深谙易安词背后的文化脉络,熟悉词间典故与喻指;语言层面上,对文言和诗词格律的驾轻就熟降低了理解原词上的难度。由此可见,许渊冲的前见使得他在易安词的英译实践中占据了一定优势。
徐忠杰早年留学时专习英国文学,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译诗词。英国文学的学习经历和自身中华文化背景使其能从英汉文学对比角度理解阐释易安词,善取两种语言之长处、充分表达词意。
美国诗人王红公的前见决定了他择取翻译作品的方向性和他在翻译实践中所发挥的创造性。王红公早年辍学,自习多语,诗歌成就斐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王红公。20世纪初他投身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40年代发起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60年代的女权运动也对他影响颇深。在择取翻译作品时,受东方情结和女权思想影响,他将目光投在了“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照身上,几部汉诗译著中无不收录其词作。在翻译观念上,腾脱于狭隘的“忠实”概念,他“将诗歌翻译从形形色色的等值理论中解放出来,既尊重原作的制约性,也尊重译者的创造性”[9]90。由此可见,其历史经历、文化视角和身份特征使他成为易安词的独特译者。
三、 易安词英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
视域是一个处境概念,它包括了从身处之处出发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而且视域会随前见的变化而变化。理解过程并非要将自身视域悬置起来,相反,正是在调和各方视域、达到视域融合的过程之中主体得以理解文本。值得注意的是,不独是理解者有自身的视域,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也会有一定的视域,且包含着作者原始的视域。[10]45解读、翻译易安词的过程不仅包含译者与原文本的历史视域融合,还有译者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目标读者与译作的视域融合。不同译者对易安词产生误读的根源可以从这三度视域融合中寻到解释。
(一) 第一次视域融合
在布鲁姆的定义中,误读是每一位读者都会经历的过程,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合理性。译者是易安词的特殊读者,其解读原作的过程即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了解原作、拓展自己当前视域的过程。文本深嵌于历史之中,其视域必然包含着历朝历代的注释与解读,因而,唯有尽可能多地参阅相关注解、使自身当前视域与原文本的历史视域尽可能重合,对文本的理解才可越为深刻全面。鉴于译者误读原作时自身视域与原文本历史视域的重合程度不同,其解读与阐释必然也会呈现差异化特征。
在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中,李清照化虚为实,用形似舴艋的小舟难以承载以凸显出哀愁之重。为中华传统文化所熏染,许渊冲力图接近原作的历史视域,努力在译文之中呈现出原词的文化意味。他以“意”为先,主张“求真是低标准(必要条件)”[11]100。“舴艋舟”一词被他具体化地译作“The grief-laden boat(载着忧愁的小舟)”[12]93,既增加了译本的可读性,又同样择用“化虚为实”的手法寄忧愁于小舟之中,传递出词意之美。误读所致的差异化阐释可以从王红公的译文中得窥一斑,王红公自身视域与原作视域融合的结果是他最终选用了“vessel(a large boat or ship)”[13]49一词来阐释“舴艋舟”。可以理解的是,基于不同的前见两位译者的不同阐释都有其合理性。但从普通读者的视角审视两种译文,笔者认为后者的处理似乎与原词竭力营造的“船之小难载愁之重”效果略有背离,译者仍需扩展自身视域,以加深对原词的理解。
译者对“碧云笼碾玉成尘”的误读也使得此句在译入语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宋时茶为团状,用时则在器皿之中碾碎。此处“碧云”指青色的茶团,“笼”为茶笼,“玉成尘”则是碾碎如尘[14]。对比许渊冲的阐释“Green cloudlike tea leaves ground into powder of jade”,王红公采用直译的方法将其译为“Blue green clouds carve jade dragons. The jade powder becomes fine dust(青云雕玉龙,玉粉化微尘)”[15]37。笔者认为,如此译法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译者试图用直译的手法令译本陌生化以凸显其独特性,从而达到延长审美时间、增强审美效果的目的;二来概因译者在自身视域与易安词的历史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没有参阅相关注疏解释来完善自身的前见、消弭自身视域中的盲点,在尚未探明文字背后所指的情况下就仅根据字面意思进行翻译。
各位译者对《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尾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解读也不尽相同。误读带来的多元化阐释主要体现在“争渡”一词的主语上。据陈祖美[16]的考证,此词记述的是作者15岁时泛舟出游的经历,“争渡”意思为“(误入荷花丛的我们)奋力划水”,但词中“争渡”的主语是“我”抑或是“我们”学界仍存争议。许渊冲把“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翻译为“Drunk, we returned by boat and lost our way, and strayed off in the thicket of lotuses blooming, get through! get through!”据此可以推测,他认为本阙词记叙的是主人公携侣同游的经历,故将主语译作“we”。翻译“争渡”时,许渊冲也用了同样的重复手法,既简洁又极具音美。徐忠杰运用“最得手的是膨胀性和解释性原则”[2]48,他的译文“I struggled and struggled out of the tangle”[17]81解释性地将“争渡”这一动作的主语(I)和原因(out of the tangle)都阐释出来。反观王红公,基于自身前见,他在理解本阙词时脑海中构思出的是“鸥鹭争渡到对岸”画面,故而将“争渡”一词处理为“鸥鹭”,其译文“They crowded into the air/And hastily flapped away/To the opposite shore”[15]38体现出很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与原作之间难以消弭的时空之隔令我们无法确凿地说哪一种阐释最为准确可信。了解原作、力求自身视域与原作视域尽可能融合的过程中,不同译者对原文的解读都有其合理性。若以易安词的相关注疏为依归来评判,笔者认为王红公对“争渡”这一动作的主语的理解较为独特,他重新组合了原词中的意象,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使原作在译入语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除了以上语义层面上的偏差,易安词中的女性形象也在译者的阐释中发生了嬗变。李清照在《点绛唇·蹴罢秋千》中塑造了一位打罢秋千、见客含羞的少女形象,许渊冲等人的译本基本都还原了这一形象。然而,王红公用“Lasciviously, I get up and rouge my palms”来诠释“起来慵整纤纤手”,又将“和羞走,倚门回首”处理为“Embarrassed, I run away/And lean flirtatiously against the door”[15]43。译文中借“lasciviously(淫荡地)”与“flirtatiously(卖弄风情地)”描绘出的是一位女性迎接新客人到来的画面,带有很强的情色意味,如此阐释与其他译本差距甚大。王红公大半生生活在艺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旧金山地区,极力提倡“个性”“性自由”等自由观念。[18]基于这样的前见,他竭力在译本中令女性意识得以高扬,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于我国宋代受“三从四德”等观念束缚的保守女性,而是如本阙词中一样大胆、开放的女子形象。
第一次视域融合之中,译者要完成深入了解原文、扩大自身当前视域、尽可能与原文的历史视域融合交织的过程。由第一次视域融合所形成的新视域会进一步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进行融合,继而生产出译本。然而,由上述译例可见,译者自身视域与原文本历史视域融合度不同,译者的解读也不尽相同。
(二) 第二次视域融合
图里(Toury)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中也强调要让译文“更贴近目标读者的期待”[19]。不符合目标读者期待的译本很有可能会无人问津。因此,诗词英译也必然要将目标读者的视域纳入考虑。也即是说,经过第一次视域融合所形成的大视域还要继续与目标读者的视域相融合。这一过程中,译者对原词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为了契合目标读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译者在尊重原作内涵的基础上,对原词语义进行不同程度的变形或对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重构。
1. 语义变形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互换,同时肩负着对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负责的使命”[20]93,因此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呈现在译文之中也应尽可能地让读者理解,为读者所接受。增加文本可读性的惯用之法便是通过话语解释,让原作的深层语义显化出来。
例1. 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膨胀性解释
许渊冲译文:
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12]95
徐忠杰译文:
I’ve a sense of something missing I must seek.Everything about me looks dismal and bleak.Nothing that gives me pleasure I can find.[17]85
王红公译文:
Search.Search.Seek.Seek.Cold.Cold.Clear.Clear.Sorrow.Sorrow.Pain.Pain.[13]31
《声声慢》写成于李清照南渡之后,是国破夫亡的凄怨之作。开篇的十四字叠词,悲情婉绝。当乡土、丈夫、往昔的快乐都不知所踪,“寻觅”二字已非简单的动作描摹,但一时间寻觅什么,李清照也并未在语言层面上呈现出来。如此一来,文本的开放性给予了三位译者进行多元化阐释的空间。王红公用与原文类似的重复手法,实现了类似的音韵之美。但若从目标读者的角度来看,若是他们的前见之中缺失相关的历史背景,动词的重复不仅略显生硬而且会造成理解障碍。对比之下,许渊冲和徐忠杰秉持着以意为先的前见,在诠释时都不约而同地在译出核心语义的基础上有所增添:前者将所寻之物、冷清凄惨的所指都在译文中明示出来;后者则选用了散文性的话语对原词进行细致入微的诠释。两位译者均选择形式上的一致性让位于内在含义的对应性,笔者大致可以推测:两位译者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接受视域,愿与读者的视域融合,生产出满足读者期待的译本。
例2. 对“佳节又重阳”的文化过滤
徐忠杰译文:
To climb high somewhere marks the day,
Which itself marks the season’s turn?
Porcelain pillows;gauze nets?
Aside must all such things be thrown?
When,at midnight or thereabouts?
One feels one is chilled to the bone.[17]83
《周易》中讲“九”为阳数,故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日。李清照借此句点明时令,只为了突出秋后的清冷氛围。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是目标读者前见中的盲点,把握这一点对增加译本可读性、促进译本传播至关重要。徐忠杰舍弃文化色彩浓厚的重阳一词,只借“登高(climb high)”这一重阳节习俗引出季节之变化。不同于“Double Ninth Festival”等译法,徐忠杰的过度阐释过滤掉了原词的文化色彩,使原意稍稍变形,目标读者更容易读懂译本。
2. 文化信息重构
译者与原作者之间永远隔着时空的藩篱,不论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内容的再创造”[7]498。既然如此,译者便从追求绝对忠实、对等的传统翻译观念中解放出来,并基于自身前见,在译入语中创造性地阐释原作。在易安词的英译中,为了兼顾目标读者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译者对原作中的文化信息进行了重构。
在翻译《一剪梅》的首句“红藕香残玉簟秋”中“玉簟”时,王红公选用了其他意象对原词中意象进行了重构。“玉簟”意为表面清凉光滑如玉、供坐卧铺垫用的竹席。香残的荷花,生凉的竹席,这两件事物本无关联,词人将其连缀起来只为暗指天已入秋。王红公将玉簟替换为“玉质的帘子(Jeweled curtain)”,并化静为动将两事物连结起来,勾勒出一副花香在玉帘上渐渐散去的画面。语义上失去的对等性在审美效果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被“误读”式重构后意象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词句背后的画面同样传递出一种意境美,也进一步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
“黄昏”指日落天晚之时,在中国古诗词中多被词人借以烘托忧愁的氛围。因其在汉语语义之中仅表述时间概念与“黄色”关联不大,所以许渊冲等人在翻译“黄昏”一词时常用“dusk”或“twilight”交代时间便足矣。正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把黄叶称为死叶(dead leaf),麦克白在落幕之时也用“yellow leaf ”暗示生命已近凋逝之时,“yellow(黄色)”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的象征含义之一就是萧瑟、衰败、忧伤与死亡。[21]王红公译文的独特性在于,他在翻译“东篱把酒黄昏后”一句时,在惯用的“twilight”一词前加上了与目标读者审美习惯相契合的“yellow”一词,将“黄昏”译为“the yellow twilight”[13]14。这样的能动处理既将彼时悲伤凄凉之感带到了文本表层,也把黄昏的内涵延展到了时间概念之外。
参阅相关文献可知,词牌名“好事近”中“‘近’指舞曲前奏,是大曲中某一遍曲调名称”[22],调名最初指以“近拍”的曲调形式,用以讽刺好(hào)事之辈。或许译者考虑到词牌仅是规定全词字数、格律和曲调之用,而且原初的“好(hào)事”之意与易安词的内容并无关联,如若直译会令读者不明所以。故而王红公与许渊冲两译本中均摒弃了词牌这一最初含义,对其进行了重构。王红公将其直译为“Happiness Approaches(好事将近)”。不同的是,许渊冲并未将“近”字直接阐释为“将近”,而是删繁就简仅仅保留了核心的“好事”二字,将其译为“Song of Good Things(好事曲)”。对读者视域的细心考量才令两位译者用“好(hǎo)事”这样较为正面的含义覆盖掉词牌的负面语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消除理解障碍之用。
经过第二次的视域融合,目标读者的接受视域参与到译本的生成中来。从语义阐释到文化信息的创造性重构,译者对于原文本的误读使译本更趋多样化,译本的最终形成是译者从第一次视域融合所形成的新视域出发,“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对目的语系统所固有的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和审美习俗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作出准确的判断”[10]94的结果。
(三) 第三次视域融合
与译者理解原作的过程类似,译本走向读者之后,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前见来阅读译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当前视域以期与译本的视域尽可能相融合,达到理解译本的目的。由于读者各自“前见”不同,他们对译本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和评论。责任心强的译者会参阅读者的评论来完善自己的前见,增加自身视域与文本历史视域的融合度,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对易安词进行重译,使译本在历时世界中得到更新和丰富。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的当属王红公。
他在1956出版的《中国诗百首》(OneHundredPoemsFromtheChinese)(下称《百首》)一书中收录了7首易安词。方志彤(Achilles Fang)在阅读了王红公的译文后,曾评论称,总的来说王红公是成功的,甚至(经过一些修改)一些短小且直接的作品译得很准确。但因为他所求助的中国朋友并非专家,也许他们沟通上的失败造成了译本中的一些错误[23]。无独有偶,Bishop也发现,有时王红公译本差强人意,或许可将其归因于译者为使中国诗人的态度和理想与19世纪或20世纪的西方抒情诗人相一致,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条件。[24]书评中均点出了王红公在理解原作上存在的问题,由此也可以倒推出,1956年翻译易安词时译者视域与原作视域的融合程度还有待提高。1972年出版的《兰舟:中国女诗人》(TheOrchidBoat:WomenPoetsofChina)(下称《兰舟》)中,9首易安词名列其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肯定了本书的价值,它介绍了许多非汉学家读者永远不会看到的诗歌,但书中确实包含了许多错误。[25]
虽然以上评论中对译本的对错评判仍具有很强的作者权威论和文本意义一元论的意味,但各方评论很有可能会拓展译者的视域,为其带来新的启示,更新对某一文本的认识。而且理解活动本身具有动态性的特征,随着阐释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动,其视域的边界也会不断地得以延展,与他者视域融合度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对文本产生新认知。1979年,王红公在钟玲的帮助下重新整理翻译了《李清照诗词全集》(LiChingchao:CompletePoems)(下称《全集》)。从Mcleod[26]、郝晓静[27]以及葛文峰[28]等人的评价中可以考证:经过数年深析原作、考评读者反馈,其自身视域与文本视域已达到了较高程度的融合。不妨通过以下几个译例细致体察译者是如何不断完善自己的前见,更新理解的内容。
例1. 原词: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鹧鸪天·寒日萧萧上琐窗》
《百首》译文:
To encourage my frivolity,
And get drunk with the aroma
Of my wine cup.
I refuse to be burdened
By the yellowing heart
Of the chrysanthemum.[23]122
《全集》译文:
It is better to accept my fate.
Drunk in front of my wine cup
I should not be ungrateful
For the yellow chrysanthemums
Along the Eastern Wall.[13]40
汉字“负”的多义性导致了王红公译本的多样性。“负”字一有“负累、负担”之意,二来表示“辜负”。《百首》中收录的译文“I refuse to be burdened by the yellowing heart of the chrysanthemum(我不愿为日渐发黄的菊花花心所负累)”所呈现出的是女子酒醉之后孤傲娇嗔的心态。1979年王红公对这首词的理解已不同于往日。他将此句重译为:I should not be ungrateful for the yellow chrysanthemums along the Eastern Wall(我不该辜负东篱边的黄菊)。全句意为“倒不如随便饮酒在杯前醉去,莫辜负东篱菊花一片黄”。原本醉赏秋景、乡愁难解的词人在写到尾句时宕开一笔,弃忧愁而写豁达,一片悠然洒脱都寓居在东篱菊花的景致之中。以笔者之见,王红公更新了自身前见、拓展了自身视域并对这首词获得了全新认知,新的阐释在情感层面上与原作的历史视域更为融洽。
例2. 原词: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永遇乐·落日熔金》
《兰舟》译文:
A friend sends her perfumed carriage
And high bred horses to fetch me.
I thank my old poetry and wine companion.[15]42
《全集》译文:
A friend sends her perfumed carriage
And high-bred horses to fetch me.
I decline the invitation of
My old poetry and wine companion.[13]82
《永遇乐·落日熔金》写于词人流寓临安又恰逢元宵节之时。由《兰舟》中的译文可知王红公将“谢”字理解为“感谢”,主人公被塑造为在元宵佳节与友人饮酒作诗的女子形象。结合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彼时由于几经离乱,李清照早已没有酒酣歌畅的心情,因此“谢绝”了酒朋诗侣的邀约。“谢”字的多重语义给了王红公阐释空间,但他的解读与原作的历史视域似乎难以相融。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如此阐释也很有可能会令读者疑惑:在全词落寞的基调下主人公为何欣然应约赴宴?
然而,理解者的前见具有自我覆盖、自我消解的特性。在《全集》的译文中,任他香车宝马,主人公还是婉拒了友人之请(I decline the invitation of my old poetry and wine companion)。王红公将“谢”字理解为“谢绝”,这样一来,译文与原作的历史视域迭合度更高,全词前后因果关系更加合理,不至于让读者有如堕五里雾中之感,故而译本视域更容易与读者视域融合在一起。
译者通过考察读者的评论,发觉了前度误读原作、翻译原作时前见中的盲点或者视域的有限性,继而发起完善前见、扩展视域的过程。译者从新视域出发,重译译本,将其带向读者,再度发生三次视域融合的过程。重译过程也诚然是译者误读易安词、生产出多元化译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译者的视域得以更新扩展,原作也一步步得到了更加深刻的现代诠释,其历史视域得以跨越历史的藩篱较为完整呈现在当今读者面前,与读者视域实现融合交织。
四、 结语
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思想的观照下,易安词英译误读背后的原因显现出来。译者所持有的前见各不相同,因而便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和价值立场上对易安词进行了误读并在译入语中进行了多元化诠释。
易安词的翻译过程发生了三度视域融合。最初,译者自身视域与易安词历史视域融合程度的不同令译者对原文产生了差异化的解读。再者,译者将目标读者的视域纳入考虑之后,从语义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原词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以增加译本的可理解性。读者解读译本的过程中,两者视域发生融合;通过考评读者的评论,译者可以完善自身的前见,不断深析原作,对易安词进行更加深刻的诠释。
伽达默尔的思想为易安词的英译误读提供了哲学解释和理论渊源,也启迪诗词英译者,唯有不断更新完善自身的前见、扩大自己的当前视域,既尊重原词的历史视域,又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视域,才能忠实地将中国古典诗词带入异域,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以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异域语境中得以较好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