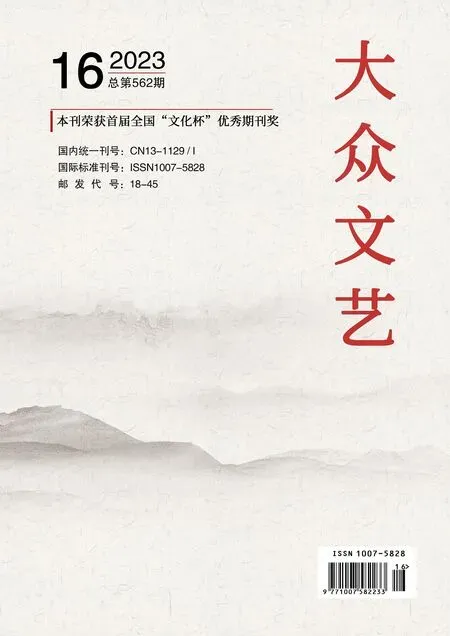伊恩·麦克尤恩前期儿童作品中非常态伦理环境中的伦理身份异化*
许媛媛
(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六安 237000)
1978年,《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短篇小说集发表,其中包含《家庭制造》《蝴蝶》等八部短篇小说,后于1978年出版了《水泥花园》和《床笫之间》,因其主题阴暗这三部小说并称为“惊恐文学三部曲”。笔者认为,主题阴暗仅是麦克尤恩作品假借的表象,表象之下隐喻当代人类生存危机,以及对道德伦理的探讨,正如翟世境所言:“他描绘阴沉恐怖的场面,表现心灵与性爱的危机,实在是具有揭示社会痼疾、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严肃意义。”[1]
麦克尤恩前期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对家庭伦理、儿童成长等主题的深入挖掘和剖析,其中儿童角色的不幸和灾难这一创作特征迭出不穷。作品中儿童的成长轨迹虽有不同,但最终的命运却大致相同。作品中麦克尤恩构建了一个非常态的伦理环境,家庭和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儿童成长充斥着压抑、恐惧,导致其逐步走向伦理悲剧。本文以伊恩·麦克尤恩前期儿童作品《蝴蝶》《家庭制造》《水泥花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当代英国社会伦理环境、家庭伦理环境等非常态伦理环境的深层挖掘,理清其对儿童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异化的作用,由此领悟麦克尤恩对当代家庭伦理的忧虑和审视对待孩子成长的方式,以及健康家庭伦理环境对儿童伦理身份的确定、伦理意识形成的至关重要作用。
一、荒原型社会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2]唯有回归当时的英国社会和小说世界的伦理环境,方能探寻文中主人公伦理选择错位和伦理身份异化的根源。
20世纪70~80年代,英国进入动荡转型的后工业时代,生态环境被破坏,文化失去规范,贫困与纵欲并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际关系扭曲,整个社会大众失去信仰。个体成长离不开客观伦理环境,在这样信仰缺失、道德衰败的社会环境中,少年不期望通过诚实劳动来达到奋斗目标。麦克尤恩在《家庭制造》中虽未展现主人公成长的客观伦理环境,但部分细节可见端倪。“我”和雷德蒙辍学成了无业游民,四处闲逛。“我”的父亲在面粉厂工作,每天超负荷工作,回到家身心俱疲却收入微薄,因为“我”小偷小摸挣得远比他多,面对父亲,“我”是报以嘲笑的态度,“我和雷德蒙喝茶时经常笑话这种对生活的消极背叛……笑话他们为了肯定自己,把一生的低眉折腰看成是美德;”[3]他嘲笑父辈安于天命,只是因为父辈们一星期的艰苦谋生不及他在书店一下午的活挣得多,对于父亲和叔叔的礼物也嗤之以鼻。60~70年代的英国信仰缺失,此时“性解放”运动推动了“性自由”等伦理观念的形成,并通过公共媒介被广泛而过度地传播,颠覆了英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在成人污秽言语的熏陶下,“我”的性意识得到启蒙,“我意识到自己的童贞,这令我憎恶”[3],社会对性的开放态度加剧了小说中所谓的“处男羞辱”意识。对性禁忌的无知让“我”陷入了伦理混乱,从而促发乱伦悲剧。“我”诱骗妹妹玩过家家游戏,完成进入成人世界的仪式性的“自我升华”,从文中“瞻仰我的光辉形象”“感觉到的是自豪”“加入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3]等描述,我们逐渐体会到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盛行的性解放观念的嘲讽。
依据聂珍钊先生的“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解释、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2],如若溯源小说主人公的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异化根本,有必要从小说世界的伦理环境入手。《蝴蝶》中呈现的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工业废区,工厂间穿梭着褐色的河水,没有公园,且大部分工厂已然废弃,窗户都没有,纤道上半天都碰不上人,没有生机俨然一个精神荒原,目光所及,尽是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污染、破败与萧条。
重返《水泥花园》的伦理现场,通过体验小说世界的压抑和窒息的环境,不难洞悉小说主人公伦理选择的动因。小说中,“我们的房子又老又大,建得有点像个城堡,厚墙、矮窗。”[4]房子的设定远离闹市区,这无疑是一个相对孤立的位置:从外部环境来看,原本他们家的房子立在满是房子的街上,如今它却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空地上;步入屋内,陈旧、破败感窜入眼帘:地窖光线阴暗,房门几乎要从铰链上脱落,花园里野草乱窜,一旁的假山部分倒塌,小池塘也荒废见底。父母在家庭之外都没什么真正的朋友,也不允许孩子把朋友带进家门。在某种层面上废弃的房子和街道、与朋友绝缘暗示着杰克一家所处的社会伦理结构的损坏。花园、房屋、街道等象征着社会文明和秩序,其废弃、倒塌隐喻杰克家庭的社会伦理结构的腐化。四处乱窜的野草,意味着杰克等人的兽性因子如野草肆意疯长而脱离社会秩序的控制。
二、缺失型家庭伦理环境
从文学伦理学关于斯芬克斯因子的相关阐述可见,人的身上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成人进行理性的伦理抉择,往往是后天教化和培养的过程中形成的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因子的结果,这种后天教化即伦理规训,或社会文明秩序,造就伦理身份的确定,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子女消退兽性因子(自然天性),塑造其精神天性成为伦理人。“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伦理混乱无法归于秩序重构,则形成悲剧文本。”[4]伦理规训作为儿童成长轨迹中决定性因素,有着重要的伦理身份确定和伦理抉择引导作用,其主要表现为父母或一方实质上的缺失导致教育与规训的缺失。家庭伦理规训的缺失使得青少年不懂基本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易造成他们在步向成人过程中伦理身份混乱而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
在三部作品中,家庭模式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共性:父亲强权或以缺位的方式出现在家庭中,从不教管,而母亲似乎久病不起,肉体上羸弱,缺乏权威,孩童被剥夺了正常成长的机会,从而异化成边缘人。父母或一方实质上的缺失导致伦理规训与教导的缺失,失去榜样和引导作用,青少年极易触碰伦理禁忌不自知,甚至破坏社会的伦理秩序。回顾《蝴蝶》,“我”出生于单亲家庭,由于母亲与我的面部畸形,没有朋友,尤其缺乏异形朋友,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保持高度警惕,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在警察局里甚至还没等我作陈述他们就开始怀疑我了”[3],“她们不自然地扫了我一眼。她们怀疑我什么,和其他人一样”[3],文中的这些主观臆测使其与社会正常生活渐行渐远,成为置身事外的边缘人。同时,在他成长过程中母亲未能提供家庭的温暖和恰当的规训,造成母亲与“我”的疏离,甚至对于母亲的离世也无动于衷,躲得远远的,且厌恶那些亲戚们。母亲的离世、父亲的缺失使得“我”毫无道德约束,从而造成“我”在空虚发闷的生活中假借“捉蝴蝶”欺骗邻家女孩企图猥亵并最终将其溺死。起初,对于女孩的接近“我”只是想找一个可以一起散步的朋友,哪怕只是一个九岁大的孩子,女孩对自己的这种好奇感使“我”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她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为我的朋友”[3],但他的这一想法却在后继行为中逐渐扭曲。“说服她和我一起走运河已经变成当务之需,这念头让我着魔”[3],原始的兽性因子与良知不断斗争,而后逐渐被本能所控制,以运河边有蝴蝶有船只诱骗简,导致男孩一次次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最终迷失人性偏离社会伦理原则,触犯“恋童”和“弑童”两重伦理禁忌。作为最后一位见到简的人,男孩被警察要求去见简的父母。他精心准备,烫了西服,挑选领带,喷了香水,却在临出门时忽然改变主意,为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而精心装扮自己感到厌恶,这一系列行为表明“我”知晓文明,但后续行为也显示“我”并不愿遵循社会普适规范和礼仪。文中他试图阻止简逃回家,避免简将发生的事告知他人,说明潜意识中他是有鉴定道德行为的能力,但从诱骗到性侵再到弑童的过程中,其伦理身份异化,从游离于社会主流文明的边缘人,变为触犯伦理禁忌的问题少年。
在成人道路上,父母是子女效仿的道德榜样,如若父母或一方缺失造成伦理规训的缺失,无疑效仿和引导,在伦理选择中理性因子逐渐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控制,斯芬克斯因子失去应有的平衡,最终打破伦理禁忌造成伦理悲剧。《水泥花园》中兄弟姐妹由于父母的缺位,使得他们在身份确认过程中缺乏引导,出现姐弟关系畸变为母子关系、姐弟乱伦的伦理混乱现象。并且亲子伦理关系关系冷漠,以致孩子对他的死都无所触动。父亲因为心脏病不能干重活,但杰克在搬运水泥时使用伎俩促使“他承担的重量跟我一模一样”[5],嘲弄着父亲的羸弱,间接地触发他的病情和死亡,甚至是在父亲倒下,他尽管明白此时必须跑过去却也迟疑许久,没有立马呼救,导致错过抢救时机,间接促成父亲的死亡。在成长敏感期遭遇父亲身份的突然缺席,紧接着母亲身份的空缺,家中无人作为他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朱莉在家庭中的身份是母亲,妻子,还是姐姐?母亲在世时,她有着明晰的伦理身份:女儿和姐姐,却从她掌管家中事务开始,伦理身份变得模糊,时而表现为家庭的母亲,时而是姐姐,三种身份在朱莉身上交织,无力辨别。杰克和朱莉伦理身份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混乱。父母双亡,原本完整的社会伦理架构倒塌,在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中失去伦理参照,导致他们在伦理选择时即道德成熟过程中遇到难题而无人给予引导,其伦理意识无法产生,导致很难完成对自我身份确认的伦理选择。
亲伦关系决定伦理规训能否实现,亲伦关系出现裂痕,则意味着父母之间、亲子之间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处于错乱的状态。错乱或异化的亲伦关系,使得青少年游离于道德禁区。《家庭制造》中父亲做着十二小时轮班的工作,晚上到家时筋疲力尽,脾气暴躁,无力管束子女;日常生活中,“我”承担了一部分照看妹妹的任务,基于此,读者可以感知这个家庭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故事中兄妹关系冷漠,被迫照看康妮,宁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也不愿参与她的游戏,害怕被朋友看见而耻笑。生活中雷德蒙充当父亲的角色“给我启蒙了成人生活的秘密”[3],我迫切期望自证以摆脱“处男羞辱”,从而做出触犯伦理禁忌的行为,根本上是其对伦理秩序和规范的无知,这源于亲子伦理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伦理规训的缺位。作为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两性关系和谐平衡至关重要。在麦克尤恩前期作品所描述的家庭环境中,夫妻之间缺乏真挚的情感交流,充斥着冷漠与伤害,丈夫对妻子的身体与语言伤害破坏夫妻感情的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的和谐,而故事中呈现的家庭悲剧无不源于这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使得少年成为家庭的受害者,而夫妻缺乏沟通和理解也是当代社会夫妻伦理关系解体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子女是夫妻之间爱的关系的客观体现……父母把子女作为他们的爱,即他们的实体性的定在加以爱护。这就是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或者说子女被抚养和受教育的权利。”[6]早期作品中的青少年自我的社会融入困难,带有厌世情绪,异化为“边缘人”,从中我们也可窥探出当代社会被异化的亲子关系。亲伦关系是家庭伦理环境的产物,奠定儿童伦理身份的确定和正向伦理抉择,如若家庭伦理规训缺失,儿童伦理规则无以建立,则引发伦理悲剧。
结语
前期作品中麦克尤恩运用隐晦的叙事刻画非常态的社会和家庭伦理环境及其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非常态伦理环境反映了伦理误导、伦理规训,通过对上述作品中非常态伦理环境进行分析,还原伦理事件发生的社会、家庭伦理现场,是我们解读作品中非道德伦理选择的关键。同时作品警示家庭伦理规训的缺失造就成青少年伦理意识薄弱,无法建构自身伦理规则,导致伦理悲剧,隐喻不断提高家庭伦理规训意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