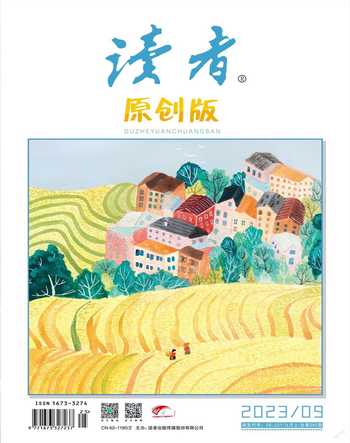浆水
南在南方
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里有个小故事,说宋太宗问状元苏易简:“食品称珍,何物为最?”他说:“臣闻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臣止知齑汁为美。”太宗笑着问他为啥。他说,有一回天气很冷,他一边烤火,一边喝酒,喝着喝着喝多了,抱着被子就睡。睡到半夜觉得渴,起来找水喝,走到院子里,天上挂着月亮,他发现雪地里有个大瓮,没喊书童,自个儿用雪搓几下手,揭开瓮盖就喝齑汁,喝了个美。他想,天上神仙喝的瓊浆也没这个好喝!太宗应和几声,大约也不晓得齑汁是个啥东西。
这事传出去了,有人问苏易简齑汁是咋做的,他说:“用些清面菜汤,再切些菜放里头。”可他没说,等着汤酸了才算行。
我看过几个对“齑汁”的注释,有说菜汤的,有说腌菜水的,没道理。苏状元后来说了“用清面菜汤浸以菜”,如果是菜汤,再“浸以菜”就多余了。至于腌菜水,也许是关于“齑”这个字,范仲淹有“划粥断齑”的典故—一锅粥等冷了,用刀划成四块儿,再从坛子里挑几根腌菜配之。朝齑暮盐,清苦之极。他写《齑赋》:“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如果苏状元喝的是腌菜水,那么咸,并不能解渴啊。
而苏易简所说的,是至今在西北地区依然盛食的浆水。浆水的制作离不开面汤,只是加了青菜—以芹菜为佳,切得短短的,放在坛子里。家里人多,差不多得有个瓮。烧开水,搅些面糊倒入拌匀,再倒进瓮里,盖好,等它凉,等它发酵变酸。为啥以芹菜为佳?浆水里有芹菜香不说,咬在嘴里还脆生生的。
浆水酸了,菜也酸了,隔上几日还得用热面汤来“投”,不然要生白沫,不中吃了。
也有不搅面汁的,擀了面条,净锅来煮,剩下的面汤,也能做浆水。浆水是个妙物,不说浆水面条,平日里,搅团、面鱼儿,虽说也用别的汁水来调味,但缺了浆水,总是个缺憾。有浆水的吃食,撒点儿葱花,挑点儿辣椒,披红穿绿,乡野的情趣都有了。秋来,捣点儿韭菜花,那就更惊艳了,就像早春飞来一只燕子,忍不住想要问它点儿事情,它只是呢喃,有点儿莫名其妙。
《本草纲目》里说:“浆,酢也。炊粟米热,投冷水重浸五六日,味酸,生白花,色类浆,故名浆水。”李时珍说的是纯浆水,类似的还有用绿豆来做的。将绿豆磨成浆,煮开,放着让它变酸。要吃时,加水煮开,下面条、汤圆、麻花都行,加些青菜,调盐。吃的有了,喝的也有,还稍稍有点儿嚼劲儿。
说起嚼劲儿,想到东坡的一则笔记:“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

东坡直接用大麦蒸饭,嚼起来啧啧响,他用浆水淘着吃,觉得好吃。他不知在我老家,大麦淘洗浸泡之后控水,用石磨来磨—不是磨面,只是磨碎,大麦成了条索状,加细盐,上蒸笼。另一边烧浆水,捣些蒜泥等着。蒸好,盛在碗里,浇上浆水,那才叫“西北村落味”!
我喜欢喝浆水,每次回老家,下了车,必叫一碗浆水面,连汤带水,呼噜而尽,长吁一声,甚觉安慰。只是最近一次,吃了却感觉味道异样,问店家,为啥用醋?店家说浆水用完了,都是个酸味,用醋也一样。我放下碗筷,付钱走了。浆水有点儿浑浊,它酸得平和,而醋常常有些“尖酸”。
浆水还有一个典故,《搜神记》里说后汉有个叫谅辅的人当官,廉洁奉公,老百姓的一口浆水他都不肯喝。有一年属地大旱,他祈雨,一祈,二祈,三祈,就是不下雨。他继续虔诚祈祷,结果,普降甘霖,几成神迹。
前两天看到一句“如渴思浆”,突然想起老友德强。他说当年高考结束,为省几元车票钱,从县城步行回家,近百里路。清早开始走,翻山越岭,走到中午,又饿又渴,怯怯地走向一户人家要点儿水喝,大娘给他舀了一瓢浆水,咕咚下肚,他就好像又活过来了,直到天黑才走回家。这一瓢浆水,他怎么也忘不了,工作后,凭记忆找到了那户人家,去道谢。大娘哈哈大笑说:“这点小事儿,害你跑这么远的路!”说着,又给他舀了一瓢浆水。
——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