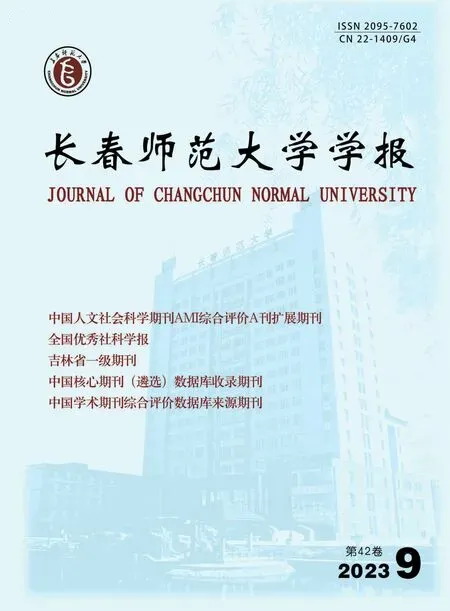《文选》编撰始末与刘勰参修考
马朝阳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文选》的成书,不仅有赖于萧统的“主选政”,亦有赖于东宫众学士的协助作用。其中,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具有较高的文评造诣,同时具备编撰图书的经验与能力。他因“深得文理”而被萧统“爱接”,辅助萧统编撰《文选》、从事“文学”之事成为他的分内工作。根据刘勰的仕官时间、《文选》的编撰时间等,刘勰在职责、能力与时间上都具备参与编修《文选》的客观条件。
一、萧统以“文学”之由“爱接”刘勰
萧统有文化上的抱负,汇集了如刘勰一样的大批学士。所以,东宫多有“文学”研讨盛会,这为《文选》的编撰埋下了伏笔。《梁书·刘勰传》载,萧统因“文学”而对刘勰“深爱接之”[1]710,从而使刘勰进入东宫,任“通事舍人”。以此为据,学界有观点认为二人关系匪浅,也有因史书记载过少而怀疑萧统“爱接”真实性的声音。
杨明照先生指出,舍人亦“文学”之士,被萧氏父子所重视,“舍人之兼东宫通事舍人,甚为梁武所重视”[2]16;“舍人深得文理者,与昭明相处既久,奇文共赏,疑义与析,必甚得君臣鱼水之遇,其深被爱接也固宜。”[2]21萧统因好“文学”而“引纳才学之士”,使东宫出现“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况。刘勰“深得文理”,所以与刘勰等学士“商榷古今”,应是“率以为常”。周唯一先生指出,萧统与学士的学术交流、讲说论辩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经纪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对义理与章句的讨论;二是有关篇藉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对书的种类、性质、作用的辨析,以及对篇目等问题的辨析;三是有关古今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古今之争、《文选》所选古今作家作品比例、选篇标准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文选》的编撰,非常重要且复杂,所以东宫才常常出现讨论“文学”之事的盛会。根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大梁之二十一载(普通三年)……讨论经纪”的记载,东宫学士云集之盛况大概出现在普通三年(522)至六年(525)之间,萧统与学士的多次商讨大多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刘勰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3]。首先,普通三年至六年期间,刘勰任东宫通事舍人,具备参与商讨的客观条件。其次,作为优秀的文评家,刘勰崇尚孔儒之道,博学广识,对文评中的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从本质上说,刘勰与萧统的文评观念是一致的,都属于“文质彬彬”的折衷派。萧统与刘勰有过“文理之辩”,才会对刘勰“深爱接之”。刘勰深得文理、胸怀大志,正是萧统所看重之人。可见,《梁书》中萧统对刘勰“深爱接之”的记载可信度很高。
二、《文选》编修始末
辅助萧统编撰《文选》是刘勰这样的“文学”之士的职责。判断刘勰是否参与《文选》的编撰,涉及刘勰的卒年、受敕编经的时间以及《文选》开始编撰、成书的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后,刘勰是否参与《文选》的编撰以及参与的程度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一)关于《文选》成书时间的两种说法
宋代晁公武引用的窦常“不录生者”说成为《文选》成书时间的主要依据。窦常是唐人,距离梁代较近。钟嵘在《诗品》中举出了“不录存者”的体例,所以,此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具体以陆倕去世之年(526)为《文选》成书时间的上限或下限。随着文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此说也受到了质疑。反对“不录生者”一派提出应以诗文创作时间为限。根据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文选》成书时间的上限是天监十二年(513),下限是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相差18年之久。
1.遵循“不录生者”说
此说以陆倕去世的普通七年(526)为限。但是,各家认定的具体时间不同。20世纪40年代,缪钺先生提出,以窦常之论,《文选》编撰应始于大通元年(527)至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何融先生支持朱彝尊的“闻有千卷”说法,认为《文选》在东宫学士鼎盛时才能完成。鉴于普通七年(526)后东宫文士逐渐衰落,何先生提出普通七年(526)应该是《文选》成书时间的下限,梁代作者刘孝标所作《辩命论》的天监十五年(516)应该是《文选》成书时间的下限[4]。穆克宏先生认为,萧统在普通三年(522)编撰了《诗苑英华》,但并不满意,还要编撰一部文集,所以《文选》的成书时间应在普通三年(522)至普通七年(526)[5]。清水凯夫先生针对“刘孝绰主编说”,考证了刘孝绰的为官、被弹劾、服丧等重要事件,认为《文选》成书时间的上限为普通七年(526),下限为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6]。
此派观点以“不录生者”为核心,具体论述涉及《文选》中梁代作者的诗文,兼顾东宫学士的重要作用、萧统的心情等诸多因素,却并未论述窦常所论“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的问题。
2.反对“不录生者”说
支持此说的有王运熙、曹道衡、许逸民、王立群先生等学者。此派观点认为,不能将窦常所言作为不录何逊的依据;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研究不应以窦常“不录生者”为依据,而应以《文选》所收录诗文的创作时间为根据。
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指出,在普通七年(526)之前,也有去世的梁代名家,如王僧孺、吴均等人,而萧统未选,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符合其选录标准。与“不录生者”说相比,更可信的是对《文选》中梁代作家所作诗文时间的考证。《文选》所收诗文的创作时间下限在天监十八年(519),所以应以此为参照来考察《文选》的成书时间[7]。曹道衡先生指出,《文选》并非以作者卒年为限,而是以作品的创作时间为限。曹道衡先生细致考证了梁代刘孝标、徐悱、陆倕的6篇文章,认为其写成于天监十二年(513)或天监末年(516-519),在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研究上应以此为断限[8]。许逸民先生指出,“不录生者”说仅是窦常通过《诗品》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猜测,并不可信。萧统在天监十五年(516)开始撰集《类文》,在编撰过程中有了再编一部选本的意图,所以《文选》成书时间的上限应是天监十八年(519)之前,而下限应在普通三年(522)。[9]王立群先生结合《文选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选为再选本、萧统的心情等因素,提出《文选》的成书时间是天监末(516-519)至普通三年(522)或七年(526)[10]。
此说指出了窦常“不录生者”说的矛盾之处,并以作品创作的时间取代了作者去世的时间,更被研究者信服。
(二)《文选》成书区间为天监末年至萧统去世
学者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研究,以梁代作家所作诗文的时间为限的观点更可信。将“不录生者”的说法作为不录何逊其文的原因,难以成立,因为何逊约卒于天监十八年(519),萧统完全可以选录他的作品。骆鸿凯评价《文选》的选文:“纤靡之音百不得一……齐梁有名文士若吴均、柳恽之流,概从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见。”[11-29]何逊与吴均是齐名的永明体后期代表文人,其作品风格纤弱,过度重视形式美,所以不能被选录。“何逊不逊,吴均不均”,两人德行有亏。萧统知道他们的为人,所以没有选录其作品。根据曹道衡先生的考证,《文选》中的梁代诗文最晚作于天监末年,这为《文选》成书的上限提供了可信的材料。正如诸多学者所论,《文选》成书和诸多问题息息相关,如东宫学士、丁贵嫔去世、太子心情等。
根据《梁书》《南史》等史书记载,结合俞绍初先生所编《昭明太子集》、曹道衡和傅刚先生所著《萧统评传》等对相关问题的考证,对有关《文选》成书的事件进行梳理(表1)。

表1 《文选》成书相关事件
从上述与萧统相关的事件中,可见如下七个问题。
其一,天监十五年(516),武帝下敕修《华林遍略》。萧统受此启发,召集学士编撰《类文》。宋人吴棫在《韵补》的《类文》条下注曰:“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萧统在收集文献的过程中,面对“千卷”的诗文,有了进一步编选总集的想法。所以,在编选《类文》的同时,萧统以及东宫学士也为编选《诗苑英华》《文选》作了准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萧统对编集有极高的热情,东宫学士的规模也不断壮大。
其二,天监十七年(518)至十八年(519),萧统完成《类文》。至此,萧统查找文献、收集资料的基本工作已经结束。普通初年(520—521),萧统开始带领东宫学士集中从事选集的编撰工作。
其三,普通三年(522),根据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指出:“结合信中自称编集《诗苑英华》是往年之事,而且说‘其书已传’,原可证此信写作年代当不会太早而可能已至普通末。此时,《诗苑英华》业已流传,而《文选》则尚未成书。以此又可以作为《文选》的成书在萧统死前不久、即大通到中大通初年的旁证。”[4-348]此年萧统已编成《诗苑英华》,《昭明太子集》十卷也由刘孝绰编成。但《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未提《文选》,说明《文选》在此年并未完成。
其四,普通七年(526)是萧统人生的转折点。首先,此年十一月萧统母亲丁贵嫔去世,至孝的萧统为此伤心不已。《梁书》记载,萧统“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梁武帝遣人宣旨:“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食。”可见,梁武帝对萧统既有心疼又有责怪。随后武帝屡次下旨,萧统依然“日止一溢,不尝菜果”,最后“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1-167]在梁武帝看来,太子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以国家大业为重。萧统在此时显然没有做到梁武帝对他的期望,甚至还要梁武帝屡屡劝他进食、为他担忧。陈延嘉先生指出,这是梁武帝对萧统不满的开始。随之发生的蜡鹅厌伏事件,让梁武帝对萧统彻底失望,甚至产生废太子的想法。此时萧统已失去梁武帝的信任,东宫学士云集的盛况也逐渐衰落。
其五,普通七年(526)到大通元年(527),萧统为母亲服丧,因其父梁武帝尚在,所以只服丧一年。此时的萧统心情无比低落,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这一时间段萧统应该未能从事编撰《文选》的工作。
其六,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下诏,任南平王萧伟为太子太傅,意在监视萧统的一举一动。此时,梁武帝与萧统的父子关系已经非常紧张。
其七,中大通二年(530),也就是萧统去世的前一年,梁武帝召晋安王纲还京,任其为扬州刺史。此时,梁武帝已经为太子接班人定好了人选,萧统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萧统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其内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逐渐放下了功名利禄,不再努力讨梁武帝欢心,而是在生命的最后做那些遵从本心的事情。他在此年上书《请停吴兴等三郡丁役疏》,反对梁武帝的《发上东三郡民丁开渠诏》。此事可说明三点:萧统已经与普通的臣子没有两样,只能通过“上疏”让父亲看到自己的政见。其次,萧统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地位与处境,他更在意百姓的生活。最后,萧统还没有病入膏肓,依然可以编集著述,而《文选》成为他表达自己情志的重要工具。此时的《文选》已经基本成书,萧统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辩命论》《广绝交论》等文章。《辩命论》本是刘孝标“自伤不遇”的自喻,萧统选录此文在于表达自己“荣惭一命”的感慨。陈延嘉先生指出,萧统敢于把梁武帝不喜欢但十分优秀的作品选入《文选》,正是他能够成为“选圣”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解释了梁武帝不喜欢刘孝标而《文选》却予以选录的问题。曹道衡指出的梁代三人(刘孝标、徐悱、陆倕)的六篇作品,不同于梁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去世之前的绝大多数作家所作。所以,此六篇作品或为萧统在此时期修订《文选》时所选录。
普通七年(526)蜡鹅厌伏事件后,萧统的心态有了极大的变化。“文学”之事正是萧统宣泄情绪、表达情志的途径。所以,萧统服丧结束的大通元年(527)到萧统过世的中大通三年(531)这一阶段,应是《文选》最后修订并完成的阶段。
(三)《文选》成书的三个阶段
曹道衡、俞绍初先生指出,《文选》的成书是有一个过程的。《文选》体大精深,内容庞杂,体现了萧统高超的文评标准。笔者认为,《文选》成书分为三个阶段。
酝酿阶段,即天监末年(约516—519)。萧统组织东宫学士为编集做查找资料、筛选文献方面的准备工作,并为编集制定选录标准。筛选文本的数量不似朱彝尊所说“闻有千卷”,但选本的编撰仍然需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一时期,萧统的编撰热情较高,东宫学士逐渐壮大。值得注意的是,萧统在《文选》之前还编撰了《类文》《诗苑英华》等书。所以,此时期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只为《文选》一书而作。在萧统编撰的总集中,《文选》成书最晚、价值更高。
集中编撰阶段,即普通初年(520)至普通七年(526)。萧统对已经成书的《诗苑英华》并不满意,遂总结《诗苑英华》的优劣,把更好的选录标准用于《文选》一书的编撰。萧统在此时期带领众多学士集中编撰《文选》。其一,经过第一阶段的筛选,佳作名篇已经初见端倪;在《文选》传世之前,已经有《文章流别集》这样的选集出现,为萧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萧统在编撰《文选》之前,已经有编集的经验,所以也有《文选》为“再选本”的说法。这些例证都说明,在集中编选《文选》时,其工作量并不像朱彝尊所说的“闻有千卷”。其二,萧统是一位优秀的选家,不仅在价值体系、选录标准方面把握航向,也常常亲自校勘,行编辑之事。所以,东宫学士只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修订阶段,即大通元年(527)至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此间,《文选》已经基本成书。萧统在经历蜡鹅厌伏事件之后,通过对《文选》的修订抒发情志。他把自己的心境变化融入对《文选》的编选工作,升华了《文选》的思想。学士不断出走,但并不影响萧统对《文选》作最后的修订与完善。
笔者以为,《文选序》未提及蜡鹅厌伏事件以及萧统表现出的闲适心情,与《文选》成书的时间在他去世前不久并不矛盾。其一,《南史·昭明太子传》记载,蜡鹅厌伏事件以后,萧统十分“惭慨”。“惭”是对梁武帝的惭愧之情;“慨”是被奸臣诬陷、遭梁武帝打压后的愤慨、委屈、抑郁之情。梁武帝晚年多疑,对萧统并没有穷尽其事已经是“网开一面”。萧统为免惹怒梁武帝而不能再提及蜡鹅厌伏一事,也因心中积郁而不愿再提及此事。《文选序》以简短之文叙述众事,主要在于论“文”,而非论“史”,无需事事兼顾。其二,萧统自小作为储君被委以重任,常常身不由己。此时,他深知继大统已然无望,把陶渊明当成自己的知音,此时的他正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2]所以,《文选序》未必表达出萧统郁郁的心情。其三,普通初年至普通七年是《文选》编撰的集中阶段。普通七年时,《文选》已经基本成书。所以,《文选序》很有可能已经在成书的第二阶段写好,符合“监抚余闲”“心游目想”的情况。蜡鹅厌伏事件之后的几年时间,只是《文选》成书的完善阶段。
《文选》作为选本中的菁华,其成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思考与磨砺的过程。随着萧统思想的变化,《文选》的质量也在升华,萧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选录标准。
三、刘勰参修《文选》始末
《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了萧统的众多学士,可考者有40人之多。辅助太子编集著述,正是他们的分内之事。陈延嘉先生指出,学士的协助工作有:其一,筛选文献材料;其二,对选文定篇等具体问题提供自己的意见;其三,校勘具体的诗文入《文选》。刘勰不仅“深得文理”,还具有编撰图书的经验,正是众多辅助之臣中的一分子。
根据刘勰入职东宫、受敕编经、卒年的时间①与《文选》编撰时间三个阶段的比对,可知刘勰参与《文选》编撰工作的情况(表2)。

表2 刘勰参修《文选》时间线
根据刘勰在东宫仕官与《文选》编撰时间的比对,可知刘勰具备参与《文选》编撰工作的客观条件。
刘勰于天监十六年(517)任东宫通事舍人,此时正值萧统编集的准备阶段。刘勰因“深得文理”并作成《文心雕龙》而被赏识,进入东宫后自然投入查找古籍、筛选版本等编集的基本准备工作中。天监末年(约516—519)正值编撰《文选》的酝酿阶段。刘勰在“文学”上与萧统有一定的往来,在选文定篇的标准上影响着萧统。
普通初年(520)至普通七年(526)萧统服丧以前,是《文选》编撰的集中阶段。此时期,刘勰一直任东宫通事舍人一职。所以,刘勰完全参与了《文选》编撰的重要阶段,与东宫众学士一起履行校勘、辑佚、删改文献等职责,辅助萧统编撰《文选》。经过此阶段的工作,《文选》已经初步成书。
大通元年(527)萧统服丧期满开始至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是《文选》编撰的修订阶段。因东宫学士没落,萧统主要根据自己的思想变化对个别文章进行增补。刘勰约在中大通二年(530)受敕编经,所以,刘勰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能够参与《文选》最后的修订阶段,辅助萧统完善以及升华《文选》。
综上,刘勰参与了《文选》的酝酿编撰阶段、集中编撰阶段的工作,并极有可能参与了《文选》编撰的修订与完善工作。刘勰在东宫所从事的助编工作时间跨度长,涵盖了《文选》编撰的全部阶段。刘勰东宫仕官与《文选》编修过程时间线的重合是刘勰参修《文选》的必要条件。刘勰“深得文理”且具备编辑能力等客观情况,成为探究《文心雕龙》对《文选》诸多影响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萧统与刘勰的文评观念是非常相似的。《文选》选篇尽显儒家教化的深义,绝不同于刘勰所斥责的讹滥文风。萧统与刘勰在“文学”思想上的碰撞,对萧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渗透于萧统的泛文学观、文体观等方面,体现在萧统的创作与《文选》编撰过程中。骆鸿凯有言:“昭明选文,或相商榷,而《刘勰传》载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被昭明爱接;《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11-12]周贞亮有言:“昭明选文,必与彦和共相讨论,即彦和亦必代为搜讨,此可推想而知者也。”[13]两书在选文定篇以及诸多文理观念上多有印证,而刘勰又作为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二人在“文学”活动上联系密切。所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他的文评观念对萧统以及《文选》的成书构成一定的影响,是可信的。
萧统因刘勰“深得文理”而召其入东宫任职。刘勰在东宫任职十余年,有较长的时间与萧统进行“文学”往来,不仅参与了《文选》编撰全部阶段的工作,而且不断表达自己的文评观念与理想。不论从《梁书》中二人交接的记载,还是从萧统与刘勰志同道合的“鱼水之遇”来看,萧统对刘勰的“深爱接之”是合于情理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容易考查的“选文以定篇”,更上升到了“敷理以举统”的境界。对于二人的关系,正如刘勰《知音》所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14]
[注 释]
①笔者在《刘勰及东宫职事考论》一文中已有详述,本文从刘勰参修《文选》的角度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