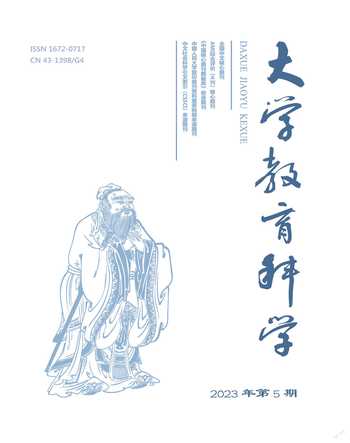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类型美学
孟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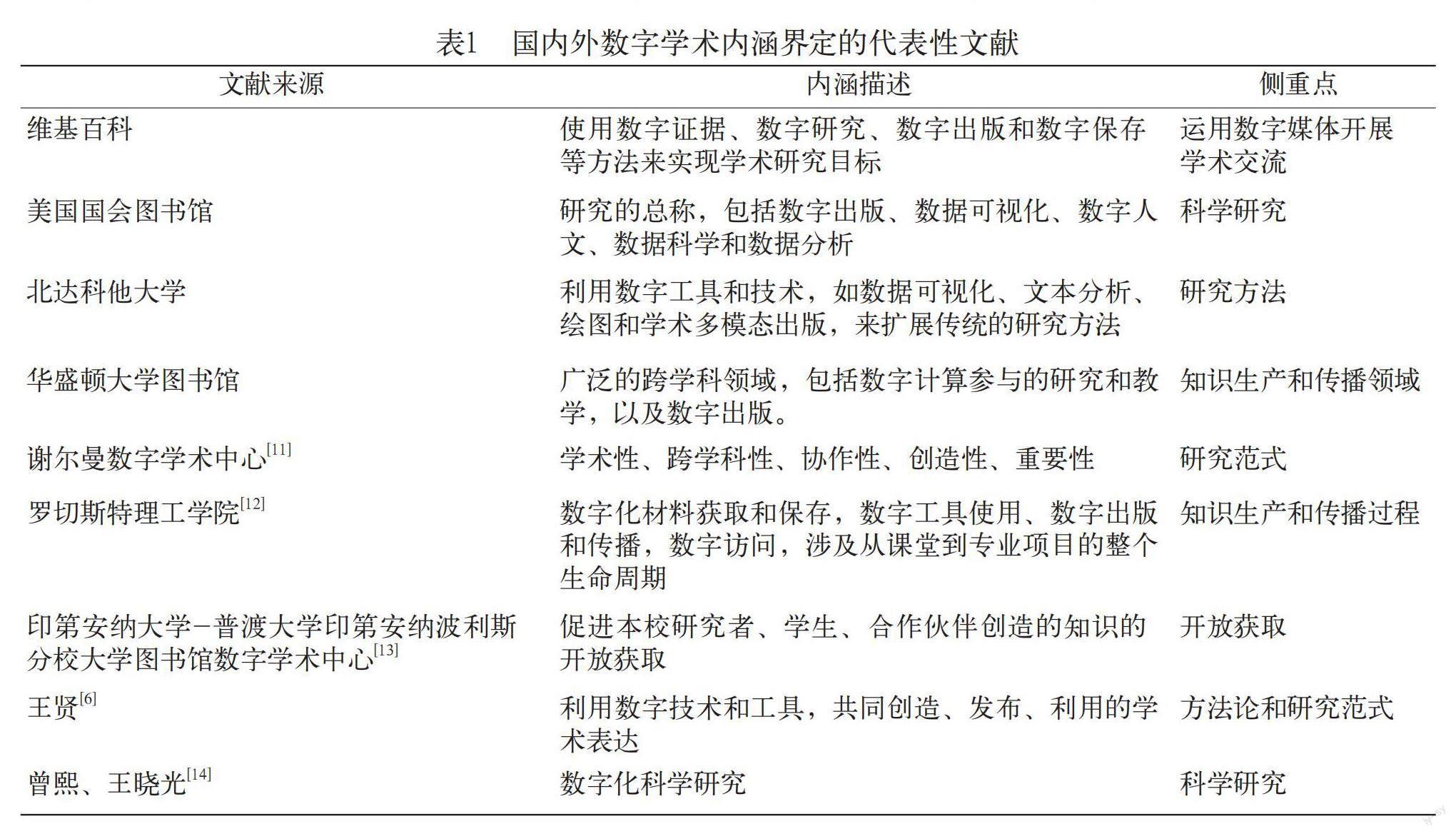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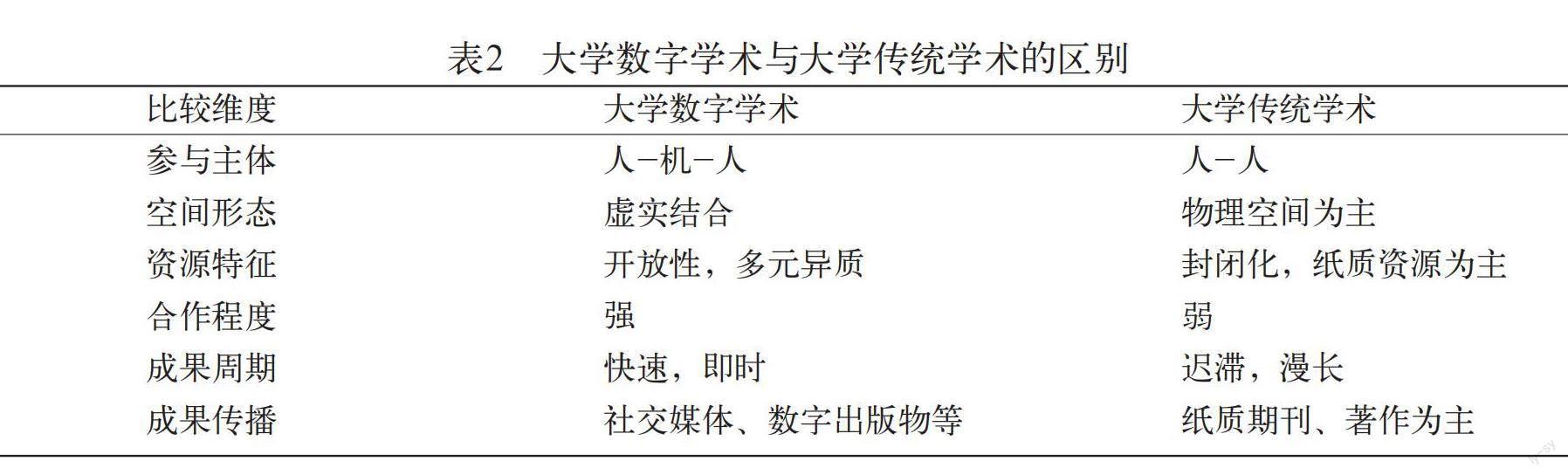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孟 畅,女,山西太原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价值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l8)阶段性研究成果。
明清之际,小说文体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结构的中心。19世纪末,随着西方小说技法与理念传入中国。之后,在二者的双重合力下,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模式开启了漫长的现代转型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小说从1902年起开始呈现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大幅度背离,辛亥革命后略有停滞倒退趋向,但也没有完全回到传统模式;‘五四前后突飞猛进,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基础,此后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了。”[1]在与之大致相近的时间段,法国人将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带入中国。自此,早期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小说宛若并蒂双生花,同根共荣,相生相成。
一、传统类型范式的沿袭: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小说+电影”模式实践
上海这一城市因西方列强殖民而开启发展之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稳固的士绅阶级文化传统的影响力相对降低,反而勃兴了独特的市民群体[2],并相应地形成大众对通俗文化的审美趣味,最为典型的就是对通俗小说、电影等文化产业的生产与消费。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化环境催生了大批清末民国的通俗小说作家与早期电影人,其中的主力便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作家的成长与创作激情都受到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影响,在结合西方创作技法、融入新文化的进步观念后,他们沿袭传统类型范式创作出大批广受市场青睐与民众好评的武侠、言情、侦探等通俗小说。之后,他们又成为电影核心内容资源的提供者,以编剧、小说改编电影、创作影戏小说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搭建起小说和电影之间互动的桥梁,打破艺术媒介的间隙,为初生的中国民族电影找到“中国故事”的落脚点,在传统类型美学的基础上实现电影产业发展的本土化。
(一)“哀情”成潮:本土类型电影观念的生成
从1896年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至今,中国电影史曾长期处于讳谈商业的状态,也正因此,从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导的早期商业电影的消费娱乐属性便被特定话语一再批驳,其所昭示的民族叙事类型美学也被一并遮蔽。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内,以新文学为“正统”的研究话语也令不够“先锋”、过于“通俗”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长期背负骂名。[3]然而,无论是将之粗暴地视为言情小说群,还是简单地概括其为擅长创作柔媚软靡情调“通俗小说群”的小说流派,都是对人员庞大、样态丰富的鸳鸯蝴蝶派创作的不公。单论小说,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可包括言情、科幻、侦探……武侠、党会等等,绝不是‘历史、‘言情或者‘武侠等几个单字所能涵盖。其中趣味、风格与工资承袭的传统十分复杂。”[4]更难能可贵地是,通过“小说+电影”模式,鸳鸯蝴蝶派文人将其广泛而又典型的类型叙事美学带入到电影创作当中,助力了早期爱情片、古装片、侦探片等类型电影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开发了武侠片、家庭情节剧等本土类型,甚至基于传统文化及文人心态开创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亚类型片种,最为典型的便是爱情电影中的哀情片。[5]
据历史记载,1921年前后,鸳鸯蝴蝶派文人开始大批进入电影创作的相关部门。“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6]1923年但杜宇和朱瘦菊、周国骥等人一同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拍摄了朱瘦菊编剧的《古井重波记》。与第一部影片《海誓》的中西风格混杂的状态不同,《古井重波记》以年轻寡妇陆娇娜为核心,从女性视角出发,编织了一出贤惠美麗女子孤身育儿,寻觅真情而不得的人生悲剧。影片从陆娇娜和年轻律师李克希相识开始,最终定格于森森墓碑前,陆娇娜“终其身为不幸之人”[7]。影片一经上映便引发观影狂潮,被称为“中国影戏界空前之作品”[8],甚至有人赞誉“中国影片自古井重波记出,新生命方开始,此剧有文有武,有喜有悲,表演逼真,布景华美”[9]。在叙事上,整部影片颇有明清时期才子佳人书的模式遗风,刻意设置第三人来制造情感波折,又用巧合和错过令情节曲折离奇,达到动人情绪的目的。更关键的是,影片同时注重电影的视听艺术特性,借物喻人情,将抽象的命运与具体的画面相结合,以静物鲜花的开谢作为留白,给观众留下回味无尽的空间,隽永而唯美。也正因此,影片将抽象的哀婉与愁绪具象化,不仅成功地将《玉梨魂》开创的哀情小说类型电影化,更将之内化为一种中国电影类型,并对家庭情节剧、社会伦理片等造成较大的影响。
1924年,以鸳鸯蝴蝶派小说为剧本,中国出产了大量具有类型意识雏形的影片。因为当时哀情小说占据市场主流,于是相应的哀情电影也层出不穷。首先是徐枕亚的哀情小说《玉梨魂》,经由郑正秋改编、张石川执导后搬上银幕。《玉梨魂》的原著是当时哀情小说之中的扛鼎之作。同时,小说以骈散相间的文言文描写现代人的情感生活,这令其不仅成为传统的才子佳人书和现代通俗小说之间的过渡,且天然地赋予电影更丰富的文学性。郑正秋和张石川在制作时便充分考虑到原著的语言风格特色,在电影字幕上下了一番功夫,不仅大量摘录原文诗词,还在电影改编情节与原著不同时,尽量在字幕上做到工整对应,风格统一,还原原著风采。虽然字数过长与诗化的字幕并不符合电影艺术特性,但在当时环境下却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不仅解决了早期电影粗鄙流俗的问题,还强调了影片的民族性,从文化表达上与欧美影片做到实质性的分野。
《玉梨魂》后,《奇女子》《还金记》《啼笑因缘》《广陵潮》等哀情电影大量涌现,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通俗小说和类型电影更多的新结合与新实践。20世纪20年代初,鸳鸯蝴蝶派文人开创的“小说+电影”模式不仅令“哀情”叙事从书本走向银幕,也令中国早期电影得以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奋力前行,萌生出民族电影的自我文化品格与类型美学。
(二)作者印记:早期中国电影类型的分化
1924年启,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纷纷投身电影实践。《玉梨魂》在市场上的成功也令郑正秋下定决心和鸳鸯蝴蝶派文人合作开发具有类型美学特色的中国电影;老将包天笑就此出山就任明星电影公司的编剧主任,先后改编创作了《空谷兰》《可怜的闺女》《多情的女伶》《好男儿》等多部电影,这些影片多为包天笑本人较为擅长的社会言情类型题材,是其小说和电影互文的结晶。1925年,朱瘦菊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编导了《风雨之夜》等多部作品,并在天一公司推行出古装片热潮后,邀请周瘦鹃“故事新编”创作剧本《马介甫》。同一年,徐卓呆与汪仲贤合办开心影片公司,专注于滑稽影片的生产制作。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大量鸳鸯蝴蝶派文人先后进入电影界,如徐碧波、程小青、严独鹤、江红蕉等,此后20余年时间里,《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银汉双星》《金粉世家》《奈何天》等耳熟能详的名作被陆续搬上银幕,由通俗小说改编类型电影的创作热潮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因市场语境变更而平息。
在花样繁多的早期中国电影中,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久的类型莫过于社会伦理片。鸳鸯蝴蝶派电影人受现代都市文化滋养,创作主题往往流露出鲜明的个体生命体验与人格意识,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诉求,但同时他们始终为民国都市生活中某种程度上的“礼崩乐坏”而深深忧虑。针对相关社会问题,鸳鸯蝴蝶派电影人寄希望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导向和归化作用,意图通过社会伦理影片中的道德感召情节来劝人良善。周瘦鹃便曾指出好友朱瘦菊摄制《马介甫》和新编伦理剧作《儿孙福》的目的都在于“借银幕感化人心”[10],也曾诠释自己编剧的《马介甫》:“使大家知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像这样劝善惩恶的绝好剧本,可不是大有功于世道人心么!”[11]在《风雨之夜》中,男主人公余家驹和道士之女卞玉洁之间暗自滋生的暧昧因家庭的责任束缚而硬生生斩断,家驹妻子更是因为想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而生出反抗姨夫的勇气,拼命化解了强暴危机。片尾处家驹和妻子在互相坦白自己曾经差点出现的过界行为,侧面烘托出中国传统的克己美德。整部影片以颇具哲理的浅淡手法,细细勾勒出一张“人生难免于情网”的众生百态,通过“唤醒情网中苦恼众生之迷梦”[12]来寓示世人应加强自身修养,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来武装自己、对抗“社会”。这些社会伦理类型影片对中国电影创作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其所推崇的伦理教化观念仍旧影响着中国影片的叙事立意选择,是类型片价值体系构建的核心之一。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纷争之中,民众迫切地渴望安全与稳定,“就在民间形成了一个呼唤匡扶正义的体制外江湖侠士的内在诉求”[13]。又因中国历来有志怪说侠的文化传统,于是在强烈的民族心理需求召唤下,武侠小说迅速风靡,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等作家崭露头角。在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小说+电影”模式日益成熟之后,武侠神怪小说的大量拥趸都天然地成为同类型电影的潜在观众群体,尤其是武侠神怪元素在当时西方影片中非常罕见。在中国电影讲中国故事的强烈内驱下,1924年符舜南导演《侠义少年》成为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次试水,只可惜打斗多为群戏,场面调度混乱,“似嫌胡闹”[14]。1925年号称“空前”的武侠言情片《劫后缘》上映,在武打戏方面虽有进步,但叙事内核过于简单空洞。直到1927年史东山执导的《王氏四侠》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电影和武打动作、侠义精神的有机结合。影片化拍摄群戏乱斗为对单体动作表演的准确捕捉,辅以宏大的布景,“旨说‘革命的起因、‘人生的真义,非常明了,更切合现代思潮,助长民众的勇气和坚决心,大大的有益于中国。”[15]正因此,影片收获业界的一致好评,被盛赞为“这才算一张片子”[16],开创了中国武侠神怪片相对成功可行的范式。之后,截选改编自《江湖奇侠传》的《火烧红莲寺》以“接顶”法、演员表演与动画形象相融合等特技摄影技术制作出“剑光斗法”、空中飞行分身斗技等场景,令向恺然瑰丽的想象力結晶被具象化地复现演绎,引起万人空巷的观影狂潮,正式开启武侠神怪片泛滥的时代。从1928到1931年,武侠神怪片产量高达250余部。在1931年7月23日,19集的《火烧红莲寺》被全部禁止放映后,中国武侠神怪片的制作狂潮戛然而止。但武侠神怪片始终是中国独创的电影类型之一,蕴含着“于现实生活之范围外,另辟一种境界,使人耳目一新”[17]的审美意义,是中华文化中玄奇美学与尚武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典型电影类型诞生,如以《阎瑞生》《张欣生》为代表的侦探片、以《西厢记》《梅妃》为代表的历史古装片、以《雄媳妇》《济公活佛》为代表的滑稽喜剧片等。
总而言之,“正如约翰·福特之于西部片、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之于悬念片一样”[18],中国早期电影人也将个人的作者印记深深地烙印在电影类型分化之上。于是从晚清起就开始创作社会伦理和黑幕小说的“通俗盟主”包天笑多做社会伦理片;有笑话三千在手的“文坛笑匠”徐卓呆专注于喜剧片;武侠小说创作颇丰的“武侠圣手”顾明道改编武侠神怪片;长期编撰哀情小说的“紫罗兰主人”周瘦鹃擅长于古装片和言情片;以翻译和写作侦探小说而盛名于世的“东方福尔摩斯”程小青为中国侦探片奠基等。事实上,鸳鸯蝴蝶派文人基本就是将自己专擅的小说题材平移至电影领域,在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进行电影化的改动,令其更好地适应电影媒介的艺术特性,在读者/观众的二重互动中实现早期中国电影类型美学观念的确立与分化。
二、传统类型范式的杂糅:多元面相的鸳鸯蝴蝶派电影
鸳鸯蝴蝶派是近代中国最为复杂的一个知识群体的概称,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因个体的身份认同与创作动机各有千秋,其文学话语实践不断变动,相应的电影创作也将新与旧、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元素集于一身,不单单是类型的、商业的,也同时并置着向内的个体精神表达、文化哲理思考与向外的伦理道德教化、艺术形式探索。在古典小说叙事模式传统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现代性思潮,再经与新文学、左翼电影的纠葛、互动,鸳鸯蝴蝶派电影令经典的传奇叙事消解重生,确立中国的情节剧叙事模式。在“软硬之争”的“雅”“俗”对峙之间,杂糅传统类型元素,实现范式跃进,缔造中国电影叙事的丰富图景。
(一)传奇叙事的新生:“情节剧”传统的确立
虽然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实践在不断地发展丰富,但从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到20世纪40年代兴盛的“海派”,“其在情节叙事上的基本特征都表现为对‘曲折离奇的情节观的承袭和发展”[19]。追溯中国叙事艺术的发展史,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子书萌芽,在唐宋的文言短篇中迅速发展成熟,最终在明清的戏曲与章回巨制中走上顶峰的传奇叙事文脉,其“无奇不传”的题材选择与“曲折离奇”的情节编排技巧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取向,正因此,富有传奇叙事趣味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才广受大众欢迎。于是在这些鸳鸯蝴蝶派文人投身电影界后,“在继承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传统和模仿好莱坞电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初期无声电影,主要是靠离奇曲折的情节招徕观众的。”[20]据包天笑回忆,郑正秋邀请他做明星公司的编剧主任时提出的要求便是:“只要想好一个故事……情节最好是要离奇曲折一点,但也不脱离离合悲欢之旨罢了。”[21]对于发轫期的中国电影而言,对技术、艺术的认知都不成熟,那么一个离奇动人的故事便是剧作的首要关键。因此,“绝大部分早期的中国无声电影在剧作上都带有强烈的情节剧的色彩……这些影片的叙事大部分直叙人物的悲欢离合的遭遇和曲折坎坷的经历,情节通俗生动而富于跌宕起伏,并且叙事和人物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类型和模式,比较适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22]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久以来的“家庭-氏族”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和明清以来大量的以家族变迁反映时代历史的小说相同,中国的情节剧也被天然地限缩设置于家庭的框架内。早期电影导演们极其擅长用一个家庭的离合悲欢来折射个人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在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之间蕴藏伦理教化。郑正秋便是个中圣手,从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到第一部引起轰动的长片《孤儿救祖记》,再到巅峰之作《姊妹花》,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围绕家庭铺陈展开,将家庭情节剧电影的内涵外延呈现到了极致,这类“以家庭整合社会矛盾”的郑氏家庭情节剧直接“代表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片类型的基本形态”[23]。
在改编《玉梨魂》大获成功后,郑正秋和包天笑合作了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中国家庭情节剧典范的《空谷兰》。与其他小说改编电影不同,《空谷兰》的改编底本就是一本译作,包天笑“移其风俗人情于中国”[24],将之“改头换面,变成为中国故事”[25]。“空谷兰”这一题名也是就日文译名而转译,“取野之花之意也”[26]。在跨越三种语言的转译旅程后,包天笑“沿用中日两国共通的文学意象”[27],套入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在家庭宗族观念下增添平等、解放的个体自由新思想,消解文化壁垒,实现西方文本真正的“中国化”,令其深入读者内心。最后因《空谷兰》风行于世,“上海明星公司把它搬上银幕”[28]。就现存的详尽本事与字幕来看,《空谷兰》前后两部的叙事主要集中于纪兰荪和纫珠、柔云二女的婚姻纠葛之上。影片通过遵循最为经典的传奇叙事范式(设置正反二元对照的人物形象,以爱情与亲情为情感内核,通过多重误会和错过制造曲折离奇又能缝合照应的情节事件,传达善与恶、和解与报应的朴素道德观念),牵涉到当时中国的诸多侧面,尤其是“恋爱、婚姻、家庭组织、亲子之爱、教育”[29]等五大深层次社会问题,进而宣传进步思想,呼吁社会改革。之后,大量的鸳鸯蝴蝶派情节剧电影涌现,如《恨海》《孽冤镜》《梅花落》等,中国早期电影迎来“一个创作主潮”[30]期。可以说,正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改编与创作令传统的传奇叙事在电影这一新兴媒介上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尤其是他们对“曲折离奇”情节的矢志追求,不仅确立了早期中国电影类型叙事中的“情节剧”传统,还令影片具有大量不同的类型元素,有意识地实现类型杂糅,对之后的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乃至于新时期电影均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二)类型叙事的“狂欢”:重思“孤岛”电影
鸳鸯蝴蝶派引发的商业类型片创作热潮在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初兴的十年中尤为凸显,甚至可以说奠定早期电影形态,促成“中国现代电影发生”[31]。随着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运动兴起,郑正秋等电影界的中坚力量纷纷转投左翼电影实践,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的影响力日薄西山,即使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对“商业电影”进行大型讨论的“软硬之争”事件中,鸳鸯蝴蝶派也近乎销声匿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电影创作虽然较之前产量大减,却依旧持续产出。从1931年始,姚苏凤为天一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陆续编剧了《歌场春色》《残春》《妇道》《夜会》等十余部影片,近乎同时,张恨水的部分作品也被断断续续地改编,如《银汉双星》《似水流年》等。只是这些创作无论是主题表达还是类型叙事基本停留在旧的模式框架内,没能杂糅更多可行的类型元素,突破言情与社会伦理类型融合的上限,在增强“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基础上实现类型叙事的范式跃进。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进入“孤岛”时期后,大约从1939年至1941年,徐卓呆、程小青与范烟桥等纷纷重回电影创作领域,先后为国华影片公司、华美影片公司、金星影片公司编撰30余部剧本,同时顾明道、秦瘦鸥的经典作品及张恨水、刘若云等名家佳作也纷纷被改编,掀起第二次鸳鸯蝴蝶派电影的创作高潮。
“孤岛”时期的上海虽仅剩租界区的方寸之地,但电影生产却如火如荼,从新华影业公司的小成本影片《飞来福》和《乞丐千金》开始,将近四年的时日里,“共有20余家制片公司摄制了近250部故事片”[32],创造了堪称“奇观”的商业电影盛景。虽后世评论多将其定义为“畸形繁荣”,但中国电影类型叙事获得了深化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之中鸳鸯蝴蝶派文人又出力甚多,乃至于“臭名昭著”的“双包案”影片《三笑》《碧玉簪》《孟丽君》都和他们休戚相关。虽然因为制作周期短,又大量取材于稗官野史类的民间故事,导致影片大多内容庸俗,镜头语言粗糙,但多重类型元素的杂交嫁接却也提升了影片的可看性。如同取材自“唐伯虎点秋香”民间传说的历史古装片,艺华影业公司出品的《三笑》就在通俗的古装片类型基础上增添歌唱元素,而与之打擂台的国华影片公司出品、范烟桥编剧的《三笑》则加入“近乎胡闹的滑稽穿插”,虽然被时人认为都是“迎合了一般妇女与无知观众的心理”的“丙下片”[33],但其大胆的类型雜糅还是应予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徐卓呆各种类型的编剧尝试更是这场类型叙事狂欢中不可忽视的一抹亮色。1937年的电影《母亲的秘密》还是俗套的“旧式社会伦理+爱情”的家庭情节剧模式,1939年的《七重天》便以滑稽喜剧为主类型,以一栋七层公寓楼为空间,探长搜查少女丁玉芝为框架,穿针引线地勾连起七层住户的百态人生,以阴差阳错的巧合、恰到好处的误会等“离奇”的情节编排出大量笑料,同时杂糅侦探、爱情、社会伦理、歌唱等多重元素,增加影片的吸引力与受众面,令其揭露、讥讽社会形形色色丑态的悲辛底色更为深入人心,也正因此,时人盛赞:“在古装片的潮流中,能够再看到这种讽刺现实的作品,的确有推荐的价值。”[34]同年,徐卓呆开启了“李阿毛”系列,第一部《李阿毛与唐小姐》是典型的滑稽笑闹喜剧,甚至形制都和同期的“王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部《李阿毛与东方朔》便开始类型元素的复合,其以滑稽的方式讲述过时的父子不合社会伦理故事,且增添历史人物东方朔作为关键的情节推动力,虽然宣传的道理过于陈腐令人诟病,但其类型叙事实践还是颇为大胆;第三部《李阿毛与僵尸》的类型叙事就更为多样化,在一贯的滑稽喜剧底色上,设置潮流神怪元素,并布置相应的夜晚花园、棺材等恐怖场景,同时附加探查真相、寻宝、打跑土匪等侦探、武打情节,可谓流行类型元素的“大锅烩”。也正是这样包罗万象的类型“狂欢”式创作,以“李阿毛”系列为代表的“孤岛”喜剧片,“使得中国早期喜剧电影在混乱的大环境中建立起了属于自身的笑闹滑稽传统”[35],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传统源头,影响到后续“无厘头”等港式喜剧片的创作。总之,虽然“孤岛”时期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题材多以古装片和小说改编为主”[36],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但不乏具有类型叙事演进意义的上乘之作。
结语
总之,从新文学家的批判起,鸳鸯蝴蝶派便长期被视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37],无论是其小说还是电影作品都难登大雅之堂,无法获得公正的品评。然而其作为一种民国通俗文艺,既非单纯复古的“封建余孽”[38],也非自命的“保存国粹者”[39],更应被看作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思潮的中间产物,代表了都市“市民文化”的审美趣味与欲望诉求,是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民族叙事与商业娱乐话语的调和品。以当前的电影强国文化语境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电影沿袭与演进了古典小说叙事范式,进而生成商业化的电影类型观念,并创建考究的情节剧模式传统,实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这不仅深远地影响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形态,更对今天中国电影叙事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3.
[2]汪晖,余闻良.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127.
[3]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
[4]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M].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2:8-10.
[5]李少白.影史略榷——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321.
[6]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54.
[7]《古井重波记》的剧情[N].时事新报(上海),1923-4-23(12).
[8]《古井重波记》开映盛况[N].民国日报,1923-4-28(11).
[9]哀情影片《古井重波记》[ J ].上海(上海1925),1925(01):36.
[10]周瘦鹃.说伦理影片[ J ].儿孙福特刊,1926:29-32.
[11]周瘦鹊.《马介甫》琐话[ J ].《马介甫》特刊,1926.
[12]倚虹.评《风雨之夜》[ J ].上海画报,1926(64):1.
[13]王海洲.武侠片的文化踪迹[ J ].电影艺术,2017(05):26-32.
[14]青民.九月份新片之比较观[ J ].电影杂志,1924(5-6):2.
[15]华但妮.以王氏四侠卜中国电影之将来[ J ].电影月报,1928(01):70-71.
[16]梯维.看了王氏四侠以后[ J ].电影月报,1928(01):71.
[17]程小青.我之神怪影片观[ J ].上海(上海1925),1927(04):1-2.
[18]李道新.中国早期电影史:类型研究的引入与肯拓[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02):27-35.
[19]张巍.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创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139-140.
[20][22]钟大丰.中国元声电影剧作的发展和演变[M]//郑培为,刘桂清.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5,5-6.
[2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M].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95.
[23]杨远婴.郑正秋——社会伦理范式[ J ].当代电影,2004(02):27-28.
[24]范烟桥.中国小说史[M].苏州:苏州秋叶社,1927:294.
[2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上海:三联书店,2014:513.
[26]秋云.侨胞欢迎国产电影[N].申报,1926-10-14(18).
[27]陈凌虹.跨越三种语言的文本旅行——包天笑译《梅花落》[ J ].中国比较文学,2022(03):93-109.
[28]郑逸梅.芸编指痕[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285.
[29]郑正秋.摄《空谷兰》影片的动机(下)[ J ].明星特刊(07).
[30]陈国富.百年中国电影与江苏[M].北京:中國电影出版社,2005:3.
[31]李斌,曹燕宁.鸳鸯蝴蝶派与中国现代电影发生[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02):55-69,6-7.
[32]弘石.特殊的风景“孤岛”电影重读笔记[ J ].当代电影,1998(03):64-68.
[33]电影批评[ J ].电声(上海),1940(17):346.
[34]七重天[ J ].艺海周刊,1939(08):2.
[35]李道新.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喜剧片(上)[ 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101-105.
[36]张巍.“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情节剧观念的确立[ J ].当代电影,2006(02):69-75.
[37]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 J ].东方杂志,1933(03):17-18.
[38]阿英.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 J ].北斗,1932(02):348-358.
[39]西谛.杂谭(十二):新旧文学的调和[ J ].文学旬刊,192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