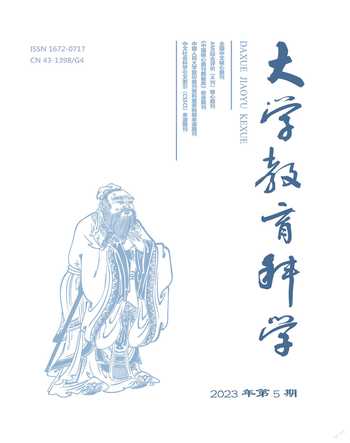论中国电影的自然审美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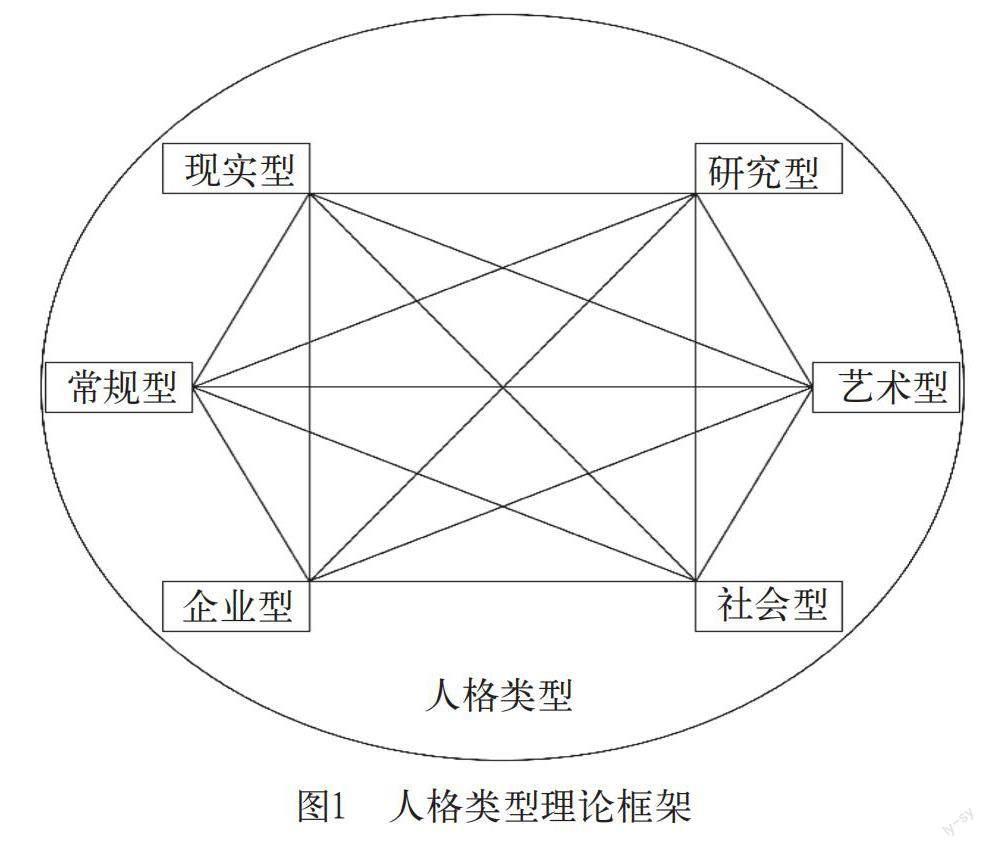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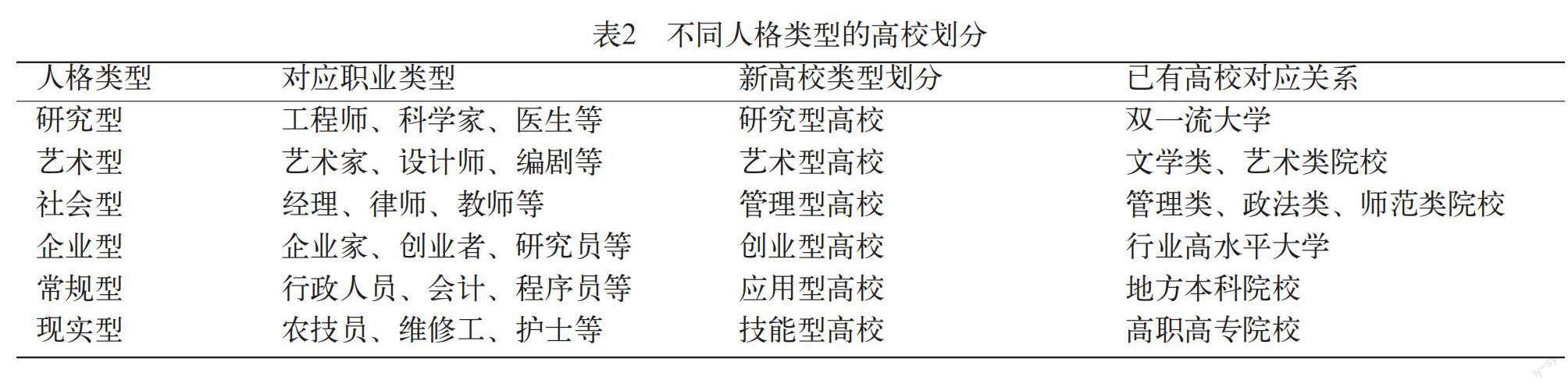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吕培铭,男,山西太原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艺术传统与中国电影叙事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价值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18)阶段性成果。
一、传统自然审美观与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建构
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化,如何以中國传统文艺美学的优质资源来熔铸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带有中国原创性的电影理论,成为紧迫的时代命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与审美意识的发展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在起源和发展上都与中国人的自然观念有极为密切的关系”[1]。无论是作为美学源流的儒释道思想、抑或是“意境”“意象”“心游”等审美范畴的生成均在不同程度地指向了自然何以为美的问题,其作为中国美学史“元范畴”[2]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些自然审美观念中还承载着中国独特的文化意识,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范式中,“自然”从未外化于人而存在,它从一开始便与作为宇宙生命本体的“道”相连结(老庄),这使其在审美之外又具有形而上的本体化色彩。其次,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然从不单是人们所利用、征服、改造的对象,它不仅能够使人获得精神上的亲近,道德上的满足,还能经由非功利的审美感受而进入美的世界,这是中西方审美观念的显著区别。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言:“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受,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3]
基于这样的审美事实,当人们试图以传统文艺资源切入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研究时,理应将“自然”作为一个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诞生于西方现代语境下的电影艺术,以逼真的光学透视见长,这就使其在表现自然景观时拥有得天独厚的媒介优势,它不仅能够全景式再现民族性的地域特色,还能够通过各种影像技术手段,对自然实现有意味的审美改造。随着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设的持续推进,关乎电影民族化相关话题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自然的传统审美经验及其话语建设却并未得到充分重视。[4]正因如此,以影像修辞手段来链接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在电影中建构具有民族色彩的自然审美观,不吝为完善中国电影民族理论的有力视角。
二、中国电影自然审美的思想取向
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三大源流,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念的生成。虽然三家的哲学观念千差万别,但在对自然美的关注问题上,却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当人们将儒释道所持的自然观与中国电影的影像修辞手段相结合后不难发现,它们所持的审美观照方法,恰好对应着中国电影三种截然不同的自然审美取向。
(一)儒家的“德性自然”:比物兴德,托物言志
儒家在进行自然审美活动时,倾向于把个人的道德理想向外物加以投射,形成源远流长的“比德”审美传统。所谓“比德”是指“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们的某种道德情操”[5],使自然具有人的感情色彩。在文学艺术中,比德传统最早可追随到《诗经》中,作品中以自然比物兴德的表现手法已初具规模;屈原《离骚》继承了这一传统,“香草”“鸷鸟”等自然物象浓墨重彩的刻画,实则也是表现了作者道德情感的对象化。理论层面,管仲较早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它在《管子·小问》中直接提出了“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的理论命题,形成了自然与道德关系的长久讨论。对“比德”审美观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孔子,《论语·雍也》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虽然这句话并未专指“比德”问题,但“智者”“仁者”的分类中却隐藏着个人精神品质对自然审美的决定性影响,这实际上是首次在美学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在形式结构上“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6]总的来说,虽然“比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原始色彩,但它却将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推进了一步,由此自然不再是神秘主义的巫术对象,它在与人的道德情感“同形同构”的过程中,开始成为“美”的象征。
在中国电影中,将自然景物与道德情感相“连缀”的比德手法随处可见。中国电影常通过自然物象的有机选择、配合以电影化的表现方式来塑造理想人格的“德性主体”。如创作于1931年的《一剪梅》中存在大量以“梅花”为主题的图案,它既作为一种视觉装饰元素,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和道德的象征;在《桃花泣血记》中,导演以“桃花”来类比琳姑坚毅淳朴的道德品格,当母亲在家中栽种桃花树时对幼小的琳姑说:“你将来做人做得好,它开的花必定鲜艳,若是不学好那末…”。长大成人后,当琳姑走投无路不得不用身体换取金钱时,路过桃花林时这句话又在耳边响起,实现了内心的救赎。
“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塑造了大量革命理想者的形象,自然景物的“比德”也成为烘托人物性格、讴歌人物精神成长的有力手段。在《青春之歌》中,影片开场便是一个长达2分多钟的“莲花”镜头,这个段落虽然与其后的故事空间无甚关联,但随着剧情推进不难发现,“莲花”正代表着林道静坚毅不拔、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品质;类似的例子在凌子风的《中华儿女》中也有所体现,在胡秀之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段落中,当胡秀之宣读完入党誓词后,导演紧接着给了四个连续的空镜头,它们分别是盛开的鲜花、壮丽的山河、巍峨的山峰、以及奔腾的流水。这些镜头不仅再现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同时也是情绪的激荡和意义的生产[7],它们一方面烘托渲染了神圣的政治氛围,同时也昭示着人物内心所经历的洗礼,颇具“托物言志”之感。
值得言说的是,虽然这种创作手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但毕竟不太符合电影艺术的表现规律。学者李玉华较早地注意到它在电影中的“滥觞”,作者在《诗与电影》一文中谈到:常见的情况是电影中主角的“牺牲”总会接一个“冬天古树”或“瀑布飞溅”的空镜头来表达崇高或哀悼、隆重的仪式总会加入一个“满簇鲜花”的特写来体现主角对美好的向往,这种类似于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显得我们的创作思路十分匮乏”。[8]据此,先进的电影工作者们开始注重以电影化的表现手段来建构情景关系,由此衍生出有关电影意象、意境等问题的研讨。徐昌霖、林年同、刘成汉等学者均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理论深度。
(二)老庄的“道法自然”:和谐共生,情景交融
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明确提出“自然”范畴的先哲,他以“自然”作为“道”之依存的逻辑前提,并借由“归根复命”“复归于婴儿”等返璞归真的思想,为中国“美在自然”审美传统做出了重大贡献。《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说的“道法自然”,并不是说在“道”之外还有一个“自然”可供模仿,其真意在于“道以自然为归,道的本性就是自然。”[9]这一说法在学者蒙培元的看法中也得到了呼应:“在老子看来,道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的。反过来说,‘自然不是别的,就是道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10]此后,庄子以一种“无我”的审美关注来面向自然,在天地宇宙的真实存在中亲证自由的喜悦,这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策略,为中国自然审美观念的飞跃开启了新的大门。
总的来说,顺应、尊重宇宙自然法则而善待万物,使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是老庄自然审美观的根本立场。具体在电影中,这种观念首先化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这成为诸多电影叙事的母题之一。一般认为,上映于2004年的《可可西里》标志着中国生态电影的正式确立。[11]表面上看,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民间护卫队与盗猎分子间的激烈博弈,这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叙事动力。从更深层来说,它所展现的是正是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导演陆川以纪实化的表现手法真实再现了人类残酷的杀戮场景,他让观众重审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傲慢,重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实现中国传统生态意识中“道”的回归。类似的观念在贾樟柯《三峡好人》中也有所体现,在国家快节奏的工业建设之下,人们将个人意志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使原本世代生活的土地变成了空洞的废墟,由此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逐渐分崩离析。导演正是通过魔幻现实的影像手法,对中国传统自然观念的失落表达了自己的叹惋。
从影像风格上来说,老庄的自然审美观在电影中还呈现为一种情景相融的美学风格,注重人与自然环境间的悠然和谐,这显然与西方主客二分的、危机性的自然景观相区别。如果说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立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哲学[12],那么中国电影在对蒙太奇技巧进行选择与取用时,则“更接近于普多夫金的连接组合而不是爱森斯坦的冲突与撞击”[13],这种注重人物与环境双向渗透的影像修辞方式,很难说没有受到老庄自然哲学观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说,老庄道家恰好成为孔门儒家的对立补充者,[14]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情景交融的美学智慧。自此中国电影在处理情景关系时逐渐摆脱了二者间的机械比附,并开始尝试将“意境”等观念纳入影像深层的自然旨趣当中,使自然与情感的关系变得愈发平等、融洽,如在《林家铺子》《巴山夜雨》《归心似箭》《城南旧事》《边城》《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中,人们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中国电影在人与自然的亲昵畅达中所呈现的诗情畫意,彰显着具有民族色彩的意境之美。
(三)禅宗的“心悟自然”:触目即真,色空之美
禅宗虽是传统佛学的一支,但究其实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现象哲学”[15],它的审美观念褪去了自然物象所有刻意人为的感情色彩,主张“物之存在的意义只在其自身”[16],这便是禅宗“触目即真”的美学智慧。禅者同样特别喜欢自然,他们认为自然万象皆为禅语,主张“悟道之机遍于十方世界”[17]。然而,在禅宗的智慧下,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念却发生悄然的改变,“它一改庄子和孔孟们人与自然的亲和与融溶关系,自然被心境化了”。[18]著名的“风吹幡动”公案便是此证,六祖慧能之所以能够将生活中的物理现象阐释为精神意识问题,其深层原因仍然是导源于一种“境随心转”的现象空观。类似的观念在禅宗“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公案中也有所体现,第三阶段看似是第一阶段的反复,但此时的山水却只是观者参悟的心相[19],它虽然保留了事物所有外在的感性细节,但此时认识与分析的视角已不复存在,客观物象开始从“我执”的牵绊中剥离而出,成为了观者某种心境的外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禅的自然审美经验彻底破除现象与本质的隔阂,任由自然景观在“青山自青山,白云即白云”的真实存在中自由舒展,这显然是一种迥异于传统儒道观念的全新美学思路。
具体在中国电影中,“禅”语境之下的“心性”自然摆脱了以往“情境相融的渲染与陪衬,也不再是蒙太奇思维中影像分切的技巧与修辞,其譬喻与联想的成分已然大幅度地减少了。”[20]以电影中常出现的月亮意象举例,如果说蔡楚生《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月亮的阴晴变化与主人公素芬的情感走向息息相关(赋比兴),那么《一轮明月》中的月亮则侧重于建构一种不可言宣的悟境。创作者并未以月亮来暗示男女的爱恨离别之情,而是通过一轮明月高悬空中来昭示一种神韵超远的氛围,使观者在静谧幽远的月色中收获禅意化的审美体悟。由此不难看出,“禅观”化的自然已经开始刻意与影像叙事拉开距离,通过感性细节的反复体认来彰显其自身的独特存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便是此例,该片以空镜头的方式展现了大量自然审美意象,虽然它们与叙事走向无甚关联,但却支撑起了全片审美意趣。导演在自然镜语和叙事内容的“背反”中呈现了一个圆满具足的生命世界,通过“触目即真”的呈现方式使“诗境”与“禅境”实现了内在的融合与统一。
同时,禅宗的“心性”智慧在电影中还呈现为一种趋向于“荒寒”的自然意趣,这是其“色空”观念所影响并决定的。禅宗的顿悟是无相的境界,声色五彩全部化为一种空的领悟,由此形成了精神意识的绝对冷寂,“荒寒”恰由此而来。朱良志认为,“冷寒为孤立虚空的禅境提供一种氛围,佛性真如总在这冷寒中展开。”[21]在《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冈仁波齐》《一轮明月》等作品中,那些“孤月”“寒雪”“冷水”“冰霜”“幽林”等荒寒意象的运用,其所展现的恰是一种禅意化的自然审美观。
三、中国电影自然审美的展呈方式
中国电影自然审美观念不仅与儒释道哲学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演化一脉相承。具体来说,“俯仰观察”“远望近察”的游观审美方式形塑中国电影横移化的镜头语言,展现了自然景观绵延流动的气韵之美。由《周易》“观物取象”所奠基的意象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国电影的造型风格,这使其逐渐在自然的“写实”与“写意”间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传统美学色彩的影像造型之路。在“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上,中国电影也常注重将影像表达比附于时序的更迭,以民族化的表现方式践行着“比情自然”的叙事旨趣,这些都是中国电影在传统美学滋养下所生成的独特审美观念。
(一)“游目自然”的镜语呈现
中国独特的自然审美方式很大程度是由中国传统审美视角的选择取用所决定的。西方绘画以模仿逼真为首要原则,画家常从固定的视点来观察对象,在二维平面上进行三维空间构造,由此形成“阴阳远近,不差锱黍”[22]的几何学光影造型。而华夏民族对天地万物的关照方式却与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诚如《易经》中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中国的自然审美从不以固定视角展开,多点移动的观察方式使我们的眼光在自然万象中开阖万里、徜徉流动,由此形成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23],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绘画从一开始便是“反透视法则”的,它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游目”“游观”的审美方式。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24]这里所说的“可游”指代的正是一种“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25]的“游观”视点。
在中国电影中,这种审美观察方式集中表现为一种横移化的长镜头效果。学者林年同先生曾将这种手卷式“动态连续镜头布局”[26]的方式称之为“镜游”,展现了中国电影对中国传统审美关照方式的赓续转化。历史地看,这种镜头处理方式在早期中国电影中便大量存在,如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认为,“中国古典绘画的空间意识和画面结构,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影像结构和镜语组成。”[27]据此作者考察了早期中国电影的镜头规律后发现,在郑正秋《姊妹花》等作品中,横移化的场面调度方式几乎覆盖了电影大部分的主要情节,在此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天堂春梦》《小城之春》等影片中,这种“平面延展和游动视点”[28]的视觉效果,得到进一步继承与发挥。郑君里在谈及电影《枯木逢春》的创作经历时,专门提到自然景物在这部分电影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9]在影片开场描写解放前夕的生活序幕时,导演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汲取灵感,创造了一个民族化影像段落:“坟堆、枯柳、死水潭,烟雾沉沉,似乎是瘴气到处弥漫;一家人被冲散的场面,镜头横移,前景不断变化,枯树枝,断壁颓垣一一从镜头面前移过,造成一定气氛。”[30]这种镜语呈现不仅将毛泽东的《送瘟神》进行了电影化表达,同时也形象地展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意境。近年来,“游”的自然审美方式在中国电影中的大量运用,如《云水谣》《长江图》《春江水暖》等等,这些均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在中国电影中所释放的巨大价值。
(二)“意象自然”的空间造型
中国古人在面向自然寻求美的感受时,绝不满足于机械客观的“传移模写”,而是充分發挥着审美主体的情感与想象,在积极的能动创造中完成“物”与“我”的亲善与融合。这种审美方式的结晶被称为“意象”。所谓“意象”是一种“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31],它虽然并未完全脱离客观事物本身,但已全然具有人的感性色彩,是勾连“写实”与“写意”的桥梁。这种方式最早可追溯至《周易》中,《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所说的“仰观俯察”,正是审美主体以情感为动力,向大千世界加以感悟和取舍的活动[32],换句话说,正是主观思维意识的有机参与下,才能使客观物象变为“人心营构之象”,进一步臻于审美的意义世界。
在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的建构中,诸多学者均注意到“意象”之于中国电影本体性的美学价值。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往往以时间性的叙事见长,其空间造型的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遭到忽视,这在源远流长的“影戏”传统中能够得到充分证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号召下,电影的空间造型意识被推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中国电影人开始逐渐摆脱传统“戏剧性”的依赖,深入挖掘电影造型功能的潜在价值。直到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这种造型表意的影像方式臻于顶峰,电影理论家罗艺军先生曾将第五代的造型方式称之为“意象造型”。所谓“意象造型”是一种“介乎具象造型与抽象造型之间,既不脱离物象的固有形态,又力图超越这种形态,以抒发审美主体对物象的主观感受和寄富审美主体的意绪为美学原则。”[33]它上承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精髓,下接现代性的电影表现方式,逐渐在“似”与“不似”、“写实”与“写意”间摸索出一条独具中国审美色彩的影像造型之路。
第五代导演们在进行“意象造型”的审美创造时均不约而同地将视角投向了自然,如《一个和八个》的主要场景均是外景,但全片几乎没有出现过象征生命的绿色,创作者正是在这种粗犷、荒凉的意象性景观中,表达了对帝国主义“三光”政策的批判;《黄土地》中占据画面四分之三的黄土地,在挤压、窒息的视觉造型中凸显着导演对农耕文明的批判与思考,张艺谋在《黄土地》的摄影阐述中专门提到了这种造型语言“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34]的视觉效果。无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吴子牛的《晚钟》等电影作品,意象化的自然景观同样是中国电影自然审美观的重要体现。
(三)“比情自然”的叙事旨趣
中国传统自然观念认为,外在客观自然界与人的生命活动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天道与人道的运行图式互为对照,由此形成“天人感应”的文化传统。这种观念可追溯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他借助易学对自然万象的细致观察,以阴阳五行观念推衍出天道与人道间的类比关系,建构出中国传统“天人和德”(《易传》)的宇宙本体观。在董仲舒看来,人如何效法、顺应天道的规律是人类存的首要问题,而自然界恰是“人事、天道之间的一种重要中介。”[35]据此,自然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成为沟通天人的枢纽。在美学领域,这种将自然“人情化”“感性化”的观念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比情”审美传统,它超越了“比德”在道德伦理层面的限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美学发展中人与自然间纯粹审美关系的生成。
这种自然与情感的关系在时序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阴阳交替,四时更迭与人性人心保持着某种同类和同构关系。”[36]遵循着这一审美轨迹,中国古代文人逐渐形成了“伤春悲秋”的传统。受此影响,中国电影在进行影像表达时,也尤其注重将情感比附于自然时序,以民族化的表现方式传达着“比情自然”的叙事旨趣。例如程步高的《春蚕》、顾长卫的《立春》、费穆的《小城之春》等电影作品均是以时令意象来奠定全片的审美基调。据《小城之春》的编剧李天济回忆,费穆正是在《蝶恋花》的反复吟咏之中找到了《小城之春》的情绪基础。虽然作为季节时序的“春”在片中基本属于“失语”的状态,它并未有机地参与到主体情节的建构当中,甚至导演对与季节相关的自然物象也并未做任何描写,但“春”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整部电影的幽怨气氛。导演正是在中国传统诗词的浸润下,以春天的伤感来比兴剧中玉纹佳偶难成、青春易逝的哀怨惆怅,传递出一股淡淡的感伤之情。
此外,秋天的萧索也常作为中国电影建构情节、传递情感的重要依据。从生命运行的自然规律来看,秋天是草木枯萎、生命由盛转衰的节点,它映射在人的精神心理当中,必然会带来一种感伤的情绪,这就为中国叙事传统的“悲秋”意识奠定了心理基础,电影《秋决》正是据此而创作的。虽然该片以“秋天行刑”为核心情节,但故事却始终传递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意识。影片结尾,当裴刚在一片肃杀的秋意中被押赴刑场时,女主人公莲儿已怀有他的骨肉,孕育的新生所意指的正是裴刚道德生命的重生与觉醒,导演正是在这种时序的感伤与生命的传递中,实现了对儒家伦理价值的确证与体认。
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中存在着深厚、绵延的自然审美传统,它不僅在中国美学史中举足轻重,同时也对中国人审美意识的生成具有深切影响。基于传统美学的分析视角来进一步厘清中国电影的自然审美观念,对当代中国电影民族性理论的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希望中国电影能够在“伦理化”“文化化”“奇观化”的创作趋势后,更多地将中国传统“自然化”的审美观念纳入影像当中[37],建构出与西方电影不同的审美思路,让自然重新成为当代人类的栖居之所,彰显“天人合一”的民族观念!
参考文献:
[1][15][18][19]张节末.禅宗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7,14,14,16.
[2]蔡鍾翔.美在自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1.
[3]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6.
[4]陈林侠.自然与当下中国电影的审美内涵及其叙述可能[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52-60.
[5]周均平.“比德”“比情”“畅神”——论汉代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和突破[ J ].文艺研究,2003(05):51-58.
[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泰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37.
[7]李镇.礼乐文化与中国电影美学[ J ].电影艺术,2021(02):17-25.
[8]李玉华.诗与电影——学习札记[ J ].中国电影,1957(01):43-44.
[9]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5.
[10]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
[11]张志庆,门晓璇.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电影的发展[ J ].当代电影,2021(02):153-158.
[12][苏联]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316.
[13]罗艺军.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16.
[14]李泽厚.华夏美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101.
[16]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
[17]皮朝纲.静默的美学[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124.
[20]王海洲,吕培铭.论中国电影的“禅意”旨趣与美学境界[ J ].东岳论丛,2023(06):70-74.
[21]朱良志.论中国画的荒寒境界[ J ].文艺研究,1997(04):135-148.
[22][2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7,129.
[24][25]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05:255.
[26]林年同.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有关古典美学问题的探讨[ J ].电影艺术,1985(03):35.
[27][28]倪震.探索的银幕[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85.
[29][30]郑君里.画外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167,167-168.
[31]蒋绍愚.唐宋诗词的意象和意境[ J ].文艺研究,2021(05):46-55.
[32]朱志荣.意象创构中的观物取象[ J ].文学评论,2022(02):41-49.
[33]罗艺军.第五代与电影意象造型[ J ].当代电影,2005(03):4-10.
[34]罗艺军.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663.
[35]崔锁江,白立强.董仲舒自然哲学的四重维度及其对天人感应论的调适[ J ].衡水学院学报,2022(06):53-59.
[36]樊波,常锋.论中国文化和文艺现象中的时间意识[ J ].艺术广角,1991(04):91.
[37]陈林侠.自然与当下中国电影的审美内涵及其叙述可能[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