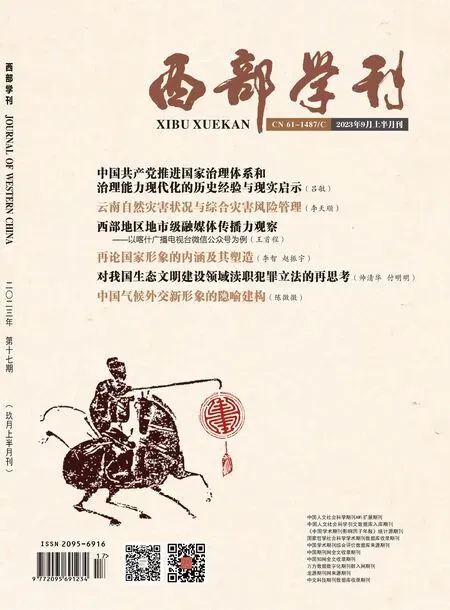再论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塑造
李 智 赵振宇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进入新世纪的二十余年来,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一直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从研究视角上看,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涵盖新闻传播学、商品广告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和后殖民主义等一系列理论视角。 从研究主题上看,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涉及国家形象的定位、设计、构建、传播以及国家形象修辞、战略等一系列问题。 就学科归属而言,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文化/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四大知识领域。 相应地,国家形象研究诉诸新闻传播学、市场营销学、文化/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范式。从总体上看,这些国家形象研究基本上对国家形象作出反映论、实体论和本质主义的理解[1]。 然而,关于国家形象的认识论、实体化和本质化的思维逻辑并不符合国家形象的存在和生成现实。 鉴于国家形象问题的复杂性与提升或改善国家形象上的现实困境,有必要反思和追问传统的国家形象观,对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予以再认识,确立起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惟其如此,方能找到塑造国家形象的新的有效路径。
一、存在论:超越国家形象的认识论理解
从传统学术上看,“国家形象”概念属于认识论范畴。 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最早于1956 年将现代国家形象界定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2]。此后,有西方学者进一步将国家形象理解为外部群体对某一国家形成的观念认知,譬如,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包含了人们对该国进行思考时认知(或想象)的总体属性[3]。 另有人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三维评价——目标兼容性(威胁或机遇)、相对权力大小、相对的文化地位所决定的综合印象[4]。
中国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上述界定,其中代表性的看法有:“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5]“国家形象是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对特定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政策、民族精神、国家行为、国务活动及其成果的总体评价和认定。”[6]归纳起来,无论是认知、想象还是评价、认定,都是认识活动——对客观实在的主观反映。 因而,国家形象就是人类认识的产物——是基于某一特定的对象即客观存在物(国家)的主观反映(映像或再现),或者说,是基于一国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国家(本体、实体)的客观存在或客观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然而,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国家形象观往往陷入一种很可能被经验事实所证伪的虚假逻辑:如果国家的客观存在(实在)好,那么国家形象就好;反之,如果国家的客观存在(实在)差,那么国家形象就差。 如果国家的客观存在(实在)发生改变(或变好或变坏),那么国家形象也会随之改变(或变好或变坏)。 而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形象现象和问题要复杂得多,其存在和变化并不完全遵循上述逻辑。 综观整个国际社会,一国的“实在”即综合国力或实力与该国的国家形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线性的因果关联性,更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相关的关系。 此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国家国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可能大不一样。 还有,一个国家的客观物质状貌/状况、社会体制及精神风貌的改变与其国家形象的变化之间也不存在同步性——或超前或滞后。 由此看出,关于国家形象的这种认识论——更准确地说,反映论的理解并不符合国家形象的存在和生成现实。
为了走出这种认识论或反映论逻辑与国家形象现实之间矛盾的困境,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国家形象。 其实,国家形象不是认识即反映或再现国家“本体”或“实在”本身的结果,否则,难以解释一国的国家形象为何会同该国本来的状况或样貌存在出入乃至于大相径庭。 国家的形象不是认识国家的产物,而是国家间(交往)实践的结果——国家形象建立在相关国家之间的国际交往即互动实践的基础之上。作为个体的人的集合体,国家“生存”或“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它是在与他国的国际交往实践中形成国家形象的。 如果一个国家脱离国际社会,不与他国展开国际交往而孤立存在,是不可能同他国建立起紧密的相互认同关系的,因而也获取不到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进而形不成自身在他国心目中的形象即自身的国家形象。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单单被他国外在静观或感性直观,乃至于被他国概念地本质把握,或者说,如果只是被认知——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那么,它是没法与他国形成相互承认、认同即身份认同关系的。 无论是国家之间相互的身份认同关系的构建,还是建基于国家之间身份认同关系之上的国家形象,都只能建立在国家间的国际交往实践之上。
对于一个处于国际社会中的个体国家来说,实践性是一种基本的存在规定性——国家是(交往)实践着的国家。 或者说,国际交往实践是国家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国家是以国际交往实践的方式而存在的。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国家的国际交往实践是国家的产物,倒不如说,国家是其国际交往实践的产物。换而言之,不是国家(的存在)规定其国际交往实践,而是国家的国际交往实践规定国家(的存在),或者说,国家(的存在)被其国际交往实践所规定——一个国家从事什么样的国际交往实践活动,这个国家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就是什么样的国家。 因而,“存在即实践”,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国际交往实践具有同一性,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其国际交往实践,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作为国家身份表征的国家形象只能建立在国家的国际交往实践——国家的“生存”(“存在”)——基础之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形象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而属于存在论的范畴。
二、关系论:超越国家形象的实体论理解
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意义都不是自身固有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意义系统内被赋予的。 换而言之,单纯的客观物质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有处于或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获得意义。 国家亦是如此,国家的意义是从国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获得的。 因此,作为国家的身份表征,国家形象是从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其意义,进而获得其存在的。 由此,严格地说,国家形象并不是国家自身具有的形象,而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关系)中的形象,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国家在他国或目标国/对象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甚而言之,国家形象是在国际体系中他国对该国的形象——他国关于该国的形象。 因而,准确地说,“国家形象”其实不是国家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国际形象(nation' s international image)。 鉴于国家形象并不是国家自身所拥有的形象,即不归属于国家自身、不为国家自身所有,国家形象就不是“物”或实物(无论是物质性的物,还是观念物;无论是“自然物”“自在物”,还是“为他物”或“自为物”),不是某种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或实体性存在,而只能是关系或关系性存在。 准确地说,国家形象形成于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一种国际社会关系,即一种在国际社会中与对象国或目标国交往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承认、相互认同即“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无论是积极地认同还是消极地认同的关系。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既不内生于国家自身的构建,也不外生于对象国或目标国的反映。 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先天预定或客观既定的、有待如其所是地(as it is)去反映、去传播的现成物即认识或传播的对象,也并非是一种自我定位、设计、构建和塑造的结果即自我建构物,而是一种国际社会中集体实践即跨国交往互动的产物即社会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物。 概而言之,国家形象所反映的不是一种独立自存的实体或实物,而是一种在国际社会中被“结构”出来的国家间相互身份认同关系。 正因“身份”不是实体(物),而是关系,作为身份表征的国家形象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因而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属于关系范畴。
由于国家身份建基于国家间即本国自我与作为他者的对象国之间的相互认同的关系之上,因而国家形象是基于双方国家相互身份认同而相互建构起来的。 可见,作为国家身份的表现,一国的国家形象存在于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之中,它是同他国相互依赖而非独立自在地存在着的,是(关系)结构性而非个体性地存在着的。 事实上,一国在从对象国那里获得国家形象的同时也界定并赋予了对象国的国家形象。 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都依赖于对象国而同对象国的国家形象对应、对等地“现身”的。 这就是国家形象的基本特性——(关系)结构性或相互依赖性。正是国家形象的(关系)结构性决定了国家形象存在的持续性(所谓“持存性”或超稳定性即惰性)及其转换的非自主性。
正因如此,国家形象及其改变不完全受制于一国单方面的主观意志和努力,不取决于作为主体的国家一方同意。 国家形象的形成需要经由主体国家和客体国家的共同“同意”(认同)而一致达成。 国家形象一旦确立,就不可以轻易改变或选择放弃。 进一步说,个体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彼此相互认同、相互依存程度或“密切”程度决定着个体身份的确定强度。 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不断交往互动(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互动)的过程中会以因果方式(即互动的开启和展开与共享观念的造就和生成之间互为因果)再现和强化彼此间业已共享的观念(shared ideas,无论是友好型还是敌对型观念),而观念共享程度或观念被结构化程度的加深则会增进相互认同的依赖关系,从而使彼此对对方国家身份的界定更为牢固,进而使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趋于固化。 譬如,冷战期间,伴随着军备竞赛这种消极互动的不断推进,无论是美苏之间互为敌人的形象,还是美英之间互为盟友的形象,都有一种固化的趋势。
三、过程主义:超越国家形象的本质主义理解
传统的国家形象观习惯于把国家形象理解为一种“现象”,进而不可遏制地去探求国家“现象”背后不直接显现或不可直观但却更基本、更本源、更实在的“本质”“本原”“实体”或“实在”即国家“本体”。 实际上,这种国家形象观预设了在“国家形象”背后有一个先行存在且相对稳定的、未被国际社会化的“国家”自身。 进而,它认为,国家形象根源于或建基于因而也从根本上取决于一种有着内在本质即自身固有属性的“实在”即国家的本然状态,因而确认了国家形象的客观实在性。 也就是说,这种国家形象观在确认作为客观实在的国家的本质性存在的同时,也确认了作为对客观实在的主观反映的国家形象的本质存在性。因而,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与之相对的是一种过程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这种过程主义的国家形象观认为,国家形象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 这是因为,国家形象不再被表象化地理解为“对客观实在的主观反映”,不再被理解为任何“物”——包括一般性的物(所谓“物质”)或实体性、对象性的物(对象物),而是被现象学般(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事情本身)地视为“物”之为“物”或“物”何以为“物”的依据——“物自身”或“事情本身”,或者说“存在”本身。 “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物),而是“存在”过程本身[7]。 概而言之,“存在”不是“物”,而是过程。 可见,在现象学观照下,作为“存在”本身的国家形象就不是任何现成物,而是“存在”即生成过程本身[8]。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形象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属于过程性范畴。
在反本质主义的视角观照下,世界不是一个聚合所有存在者的、终极而永恒的“存在者(being)”整体,而是一个去“存在”(to be)即自我生成(becoming)、变易的过程——整个世界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世界就是生成、变易过程本身。具体地说,世界不是一个如同容器般容纳各民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而使之共存于其中的自立自足、固定不变的“存在者”,而是基于各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国际社会中所有行为体之间的持续互动而处在不断生成过程中的“存在”(Being)本身——其中的民族国家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及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始终处于互动和互构的关系之中。 伴随着国家间的国际交往实践不断展开,作为国家身份表征的国家形象处于不断构建的过程中。 从整个国际关系的过程来看,国家间基于交往互动而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构成后,相关国家彼此在对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随之形成并确立,因为一个国家在对象国心目中的形象是由该国被对象国所界定的身份所规定的。 国家的国际交往过程决定了国家间相互身份认同的过程,进而决定了国家形象的生成过程。 国际交往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国家间相互认同关系的改变,进而带来国家身份的表征即国家形象的改变。 只要国际交往互动的过程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国家形象就始终处于不断“存在”(生成)的过程中。
四、国家间交往互动基础之上的国家形象塑造
在传统的国家形象观观照下,国家形象的塑造路径是:国家构建自我形象并把构建好的自我形象传播出去,以求给国际受众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形成合意的国家形象。 因此,传统的国家形象塑造逻辑是:(自我)构建(building,设计与包装)→(自我)传播(宣传)→(他者)反映(认知与评价)——一个国家通过对外传播把自塑的潜在形象转化为他塑的现实形象的过程。
然而,在新的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观照下,塑造作为国家身份表现的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单个国家的个体性问题,而是嵌入国际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体制、制度性的问题。 正因此,一国的国家形象并不受主体国家的主观塑造意愿支配,也不完全受控于主体国家自我构建和对外传播上的作为和努力,也就是说,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国家自身通过单方面努力作为或竭力宣示所能实现的。 只要一个国家与他国或国际社会身份认同的结构性关系没有发生改变,该国在对象国或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就不会改观。 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并未因为多年来中国对美传播的积极努力而发生根本性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因为中美两国间消极、敌对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中日关系亦是如此。
但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形象始终处于一个基于国际交往互动而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不可转换和改变的。 伴随着国家间互动及其模式的不断推进和变化(在良性与恶性之间转换),原初通过习得而业已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共有观念也会发生性质上的改变(在友好与敌对之间转换)。 在此基础上,国家间所建构的相互认同关系相应地调整(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转换),从而使彼此认定、界定的对方国家身份发生改变(在朋友或盟友、竞争对手与敌人之间转换),进而引发双方国家形象的对等变化(或趋于良好或趋于恶劣)。 这就是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体系结构转换进程中得再造的逻辑(机制)。 可见,若要重塑国家形象,就必须重构国家同他国或相关国家之间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 而要重构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关系,必先改造彼此共享的观念或知识。 最终,若要改造国家间共享的观念,又必先改造和优化彼此的交往互动模式。
那么,一个国家到底如何去改造和优化与目标国之间的交往互动模式,从微观单位即单个国家层面上讲,其必然的出路是,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为目标,积极调整国家的外交指向和重点,制定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民主性和人文性的外交政策,并且“单方面”不受干扰持之以恒地予以推行。 也就是说,要信奉和利用国家间观念和行为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①观念和行为的“互应逻辑”,是指观念和行为在人际间或群体间相互化和趋同化的一种运作机制。 在人际或群际交往时,双方会在互动和反馈中相互参照和学习,一方对另一方持有某种观念取向(或积极友好或消极敌对)或采取某种行为策略(或积极友好或消极敌对),对方会以同样的观念取向和行为策略予以回应。,打破恶性的互动循环,代之以良性互动循环,在交感互应中去“同化”(co-opt)对象国,从而在双方国家间建立起积极、友好的身份认同关系,进而彼此确立起在对方心目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当然,基于国家形象的结构性,一国国家形象的改善更寄望于通过双方和多方的共同努力,在宏观结构即世界体系的层面上促成国家间的交往互动对等化,并趋于良性化,进而实现全球互动模式的整体优化,最终成就全球积极“共识”(共有知识)和达成全球友好的集体身份的认同。 一个国家良好的全球形象终究建基于全球范围内的积极“共识”和全球命运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人类大家庭”成员身份之上。
五、结论
在认识论、实体论和本质主义思维逻辑支配下的传统国家形象观是成问题的,它对国家形象的存在和生成、变化缺乏充足的解释力。 这同时也决定了传统的国家形象观在国家形象塑造决策上的思想指导意义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其改善国家形象的政策建议有可能失效。 正因此,无论是基于学理上的探讨还是实践上的考量,破除反映论、实体性和本质化思维模式,超越对国家形象的认识论、实体论和本质主义理解,进而确立起存在论、关系论和过程主义的国家形象观显得极为必要。 惟有重新认识国家形象,确立起新的国家形象观,方能找到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新的有效路径。 新的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所规定的国家形象塑造机制表明:在战略决策上,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关键不在于国家的自我形象构建和对外传播(宣传),而在于相关国家间交往互动模式的改造和优化——因为国家形象的优劣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间的交往互动模式。 在此,就国家形象的塑造而言,外交(对外交往)要更重于内政(国家自身的建设);在策略操作上,鉴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从根本上建立在相关国家间交往互动之上,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在于国家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活动,而且,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要“从我做起”,主动调整行为策略,且持之以恒地贯彻对对象国或目标国的友好行为策略——在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上,国家的对外行动要胜于国家的对外宣传(所谓“行胜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