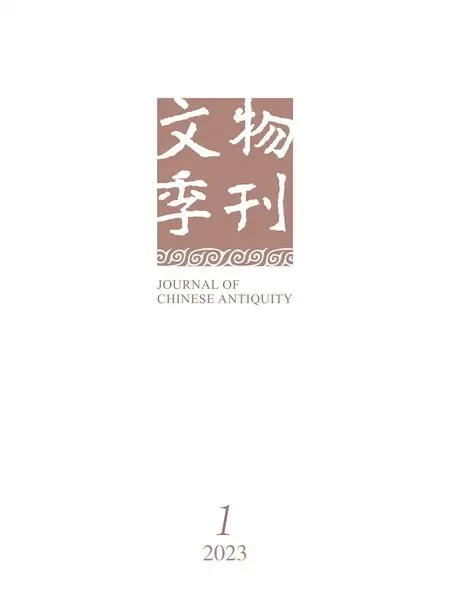新见北魏元泰墓志的士族化书写*
刘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中原文物》2019年第5 期刊发杨振威先生《洛阳新出北魏元泰墓志考释》一文,据此获悉新见元泰墓志之详情。杨先生把墓志铭同传世文献紧密结合,考证详审,提出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意见。笔者试在此基础上,围绕志主元泰皇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借助固定成型的制度平台,通过以小见大、类比关联的办法,管窥拓跋族群及北魏统治集团构造机理之一斑,展示中古北方士族化的历史成就与时代风貌。至于结论是否稳妥,还望方家斧正。拙作征引志文俱源自杨先生公布的拓片图版和简体释文[1],后续恕不再逐条标注出处。
承蒙杨先生提示,志主元泰正史有载。《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高阳王雍传》:“(高阳文穆王元雍)嫡子泰,字昌,颇有时誉。为中书侍郎,寻迁通直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太常卿。与雍同时遇害。追赠侍中、特进、骠骑大将军、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阳王,谥曰文孝。”[2]这段文字与其墓志颇多抵牾,然中古人物生平史、志互异现象司空见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唐长孺先生点校北朝四史早有明示:“《传》和《志》互见,未必《传》误。此类封爵、历官、名字、谥号等史、志不同的很多,凡不能断定史误者,今后不一一出校记。”[3]实际上,两者恰好互相补充,史、志各自的选材和修撰特点也就不言自明了。志文的一大贡献是交待了志主元泰的生卒年,他建义元年(528年)死于河阴之变,享年25 岁,则生于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该时段正是北魏洛阳政局由盛转衰、士族化浪潮风起云涌的紧要关头,唯有结合此特定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墓志士族化书写范式的成因,并有效提炼志文潜藏的宝贵信息。
一、志主元泰的出身等第
破解中古墓志的技术前提,一般要先弄清志主生前“体制内”的身份层级,最直接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测量志石的尺寸规格,因为遵照丧葬礼法,二者通常按特定比例搭配组合。这里引用一组北魏的数据以供参考:宰辅重臣魏尺三尺,约合80 厘米;一、二品官二尺四寸,约合66 厘米;三品官二尺,约合55 厘米;四品官一尺八寸,约合50 厘米;五品官一尺二寸,约合33 厘米;六品官一尺,约合30 厘米[4]。墓志尺寸本应匹配志主生前的最高职务,而在封闭固化的六朝士族制背景下,仕途巅峰往往为家世出身所左右,饱受种种限格、止法的羁绊。所以,志石的规制间接变成门第等级的缩影。将前述数据归并整合后发现,仅在士族阶层内部,门资一至三品的“膏腴”出身者,未来具备跨越三品公卿线的资格,志石就维持在二~三尺,即55~80 厘米之间;门资四、五品的“四姓”出身者,未来具备跨越五品大夫线的资格,志石就维持在一尺二寸~一尺八寸,即33~50 厘米之间。两者上下紧密衔接、泾渭分明,凸显门第社会流品之核心法则。就仕进资格乡品而言,彻底排斥寒门的士族上品或高品仅设一、二两品,刚好与之分别对应;超越此流品秩序的顶级至尊专称“超品”[5],地位非比寻常,另当别论。按此标准衡量,志石62 厘米见方的元泰无疑属于士族上流的“膏腴”群体[6]。这与其皇室宗亲的出身密切相连,史、志皆载:其父高阳王元雍官居丞相、位极人臣,祖父乃显祖献文帝,有皇孙王子之尊,自然端坐士族金字塔的尖顶,享受士族化运动最丰厚的红利。
还有个问题值得留意,墓志追溯元泰先世,不只局限于礼法规定的“祖之所自出”,即本房支系与帝系轴线交汇的第一节点献文帝,甚至远及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和实现北方统一的太武帝。志文曰:“烈祖重眸日角,应符定鼎;世祖乘乾得一,拓清宇宙。”这里的“烈祖”绝非单纯对远祖的美称,而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的旧庙号,后世赞颂其复国伟业,感觉开创功绩未得充分彰显,故孝文帝改革宗庙体系,以“太祖”置换“烈祖”[7],来论证拓跋入主中原的合理合法性。然而,不少宗室墓志仍沿用“烈祖”旧庙号,如元广、元维、元玕等志[8]。此乃传统习惯使然,或非笔者先前揣测那样是保守派抗拒新政之异常举动。“世祖”是太武帝唯一的庙号,始终没有变动。在献文以前诸帝里独叙此二帝,必定遵奉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四月颁布的诏旨:“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9]意即天子七庙序列中,二帝分列始祖之下的祧庙,神主百世不迁,故足可代表历代先君。这种突破常规的书法亦见新出北周拓跋迪墓志,文曰:“魏世祖太武皇帝之后也。帝族洪源,备书藏乎金匮;皇枝蕃屏,具载传于玉牒。高祖恭宗景穆皇帝。曾祖岱,太师、任城康王。祖澄,太师、录尚书、假黄钺、加九锡、任城文宣王。父顺,太傅、东阿文简公。”[10]同样把“祖之所自出”的端点向前延伸。此举并不具备礼制内涵,无非志主自我标榜、抬高身价的手段而已。
志主元泰贵为皇族毋庸置疑,然其在皇族内部的服纪位置尚待明辨。孝文帝移风易俗,旨在荡涤氏族遗俗对专制皇权的阻滞。首当其冲的举措是利用汉人的丧礼五服对拓跋族群实施深入、系统的家族化改造,并使之成为资源配置的尺度。于是,皇室成员根据与当朝皇帝的血缘关系被依次安置在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席位上,进而区分尊卑贵贱、亲疏远近。诚如台湾学者康乐先生所论,就是借助礼制的载体强行灌输华夏的纲常名教,最终实现由氏族直勤向王朝宗室角色意识的转换[11]。参照丧礼五服图,历经宣武、孝明两朝的元泰分别是前者的大功堂兄弟和后者的缌麻族伯叔父,俱在皇室服内至亲之列,显系优先分配利益的特权分子。
志主的等级地位还突出体现在墓志的题名结衔上。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用官阶权势衡量人生价值并为此盖棺定论。故正史、家传、谱牒、行状、碑志无不热衷堆砌官爵。志文结衔求全责备,素以数多量大、位望通显、类型多样为荣,大致有四种方式:赠官、赠官混搭最高官职、最高官职(往往也是临终官职)、生平全部官职。就等第而言,尤以前两种为尊。志文说元泰死后,“天子愍悼,策赠使持节、侍中、太尉公、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谥曰王”。志首题名曰:“魏故使持节、侍中、太尉公、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元公墓志铭。”显系以赠官结衔,属于最高等级。
附带谈下元泰赠官的史、志互异问题。正史本传同载侍中、太尉公、骠骑大将军、高阳王四项,多出特进,缺使持节,定州刺史写作武州刺史。主体内容相同,个别细节有异。若排除文本传抄讹误的可能,还有如下解释。河阴之变后政局诡谲,善后事宜应接不暇,尔朱荣广开恩赏,慷慨超赠[12],结果顿失章法,不仅职务叠床架屋,而且变动无常,致使史、志各有所本,分歧丛生。元泰的情况无独有偶,殉难者司空元钦的赠官,正史为“假黄钺、太师、太尉公”[13],墓志为“侍中、太师、太尉、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14],出入明显。比较而言,元泰“使持节”与元钦“假黄钺”都是赋予军事统帅权的仪式象征,本身并非正式编制的职官,结衔即便省略亦不为过。况且志文独载元泰临终的外镇委任:“俄迁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光州刺史,固辞不受。”尽管并未就任,但追赠方案必定据此设计,正史缺漏该环节的铺垫,难免抹杀赠官中“使持节”之存在。元泰所加“特进”,乃体现身份、地位和荣誉的散阶头衔,能使获得者达到“次于诸公”的班位[15]。他既已追授太尉公,又何必多此一举,故志文减省不录。至于刺史所任之州,起初可能是志文所载的“定州”,后为避让地位更高的元钦而改换“武州”,武州管辖北魏旧都平城外围的武周、车轮山,那里曾是明元帝的避难所,极具历史纪念意义,朝廷鉴于此予以平行置换。总之,史、志记录元泰赠官兼及新、旧版本,各有取舍的标准,二者在新材料出现前暂且并行不悖。
总括以上,根据志石的制式规格和志文题名结衔的方式,再结合史、志关于志主元泰的出身世系的文字记载,基本判明他无论在皇族还是统治集团内部均属上层精英人士。若将这种政治关系等位投射到士族语境下的社会场域,他无疑拥有冠族首望的桂冠,具体而言就是睥睨群伦的“膏腴”之上的超品层位。因为中古北方民族大融合归根结底是以胡汉上流阶级为导向的士族化,内徙胡人不是消极被动而是保持民族自尊的同化,尤其是宗室必须凌驾全体胡汉新贵之上,由此导出拓跋皇族士族化的时代命题[16]。明乎于此,方能理顺逻辑脉络,对志文进行贴近历史真实的诠释。
二、志主元泰的登仕起家
中古墓志仕途履历的书写无不以释褐起家为重头戏,因为它融汇了逝者几乎全部的身世等第信息,也预示着人生旅程的前景和政治生涯的走势。特别是起家官品的高低和职务的清浊属性往往与家世门第紧密挂钩,实则成为维护阀阅“流品”秩序的基石。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建构六朝贵族体制论格外重视起家问题,他说:“弄清楚九品官制的轮廓,就可以推测连接九品官制和中正乡品的是起家之制。在现实中规定贵族门第高下的,除此起家之制外,别无其他。”[17]所以,厘正起家与门第的对应关系至关紧要,志主元泰的身世直接决定起家,反过来又通过起家得以呈现。
墓志把元泰登仕起家摆在显要位置,文曰:“天子以宗戚俊乂,特加钦遇,乃引以内侍,除通直散骑常侍,虽释巾居此,而官人之举,未允佥望,转散骑常侍。”这里透露出如下信息:首先,元泰凭借皇室宗亲的身份被安排特殊的仕进途径。宫崎市定研究发现:“(晋代)宗室的官僚生涯有别于一般的贵族,特殊对待,大概处于中正的管辖范围之外,由宗正卿掌管,称为‘宗室选’……宗室的起家官职多为散骑常侍(三品),或者是各种校尉(四品),它是根据什么标准规定的,不得而知。不管哪一种,四品以上的官职是臣下绝对不可能获得的起家官,因此,宗室显然享受着特殊的待遇。”[18]晋制是北魏建政的蓝本,“宗室选”被照搬过来开辟皇族政治新局面[19]。从元泰的起家职务来看,他的确处于凌驾庶姓臣僚之上的高端层位,与晋代情形别无二致。其次,随着官僚队伍的膨胀,散骑常侍逐渐衍生出正员、通直和员外的区别,案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颁行之前品令,三者分列正二品下、正三品下、从三品上;太和廿三年(499年)颁行之后品令,三者分列从三品、正四品下、正五品上[20]。量级的绝对值虽有变化,但相对的效力值出入不大[21]。可见北魏“宗室选”的地位在晋制基础上又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宗室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再次,推敲志文可知,符合元泰身份的起家官应是散骑常侍,授通直散骑常侍则显略低,故迅即迁转正员予以纠正。说明北魏“宗室选”的层级区划更趋精致、细密,各档之间升降有序[22]。复次,据前引正史本传,元泰起家中书侍郎,迁通直散骑常侍。把志文明确记载的起家官当成首次迁转官,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晋品令中书侍郎位列五品,作为起家官固定搭配乡品一、二品的庶姓高门[23],但尚未达到超品“宗室选”的标准,所以正史记载可能有误。我们注意到,志文在起家环节后补充一句:“其在省闼,文义诰策,粲然可观。”众所周知,散骑常侍负责规谏顾问,草拟诏诰乃中书执掌。故此句暗示元泰以散骑常侍本职兼领中书侍郎,侍从之余兼管文书。且中书侍郎在太和前、后品令中分列正四品上、从四品上[24],与散骑常侍分别相距四阶和二阶,完全可由后者兼任。魏收修史所见履历残缺散乱,故简单地按品级高下排摆迁转顺序,却忽略了兼任的可能。
研判元泰的起家等级,还可从其他释褐通直散骑常侍者的集成分析中获得佐证。遍检史志,此类人物以宗室为主,如道武玄孙淮南王元显、武昌王元鉴,景穆玄孙中山王元叔仁,文成皇孙齐郡王元祐,献文皇孙赵郡王元谧、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琅琊县开国公元昶,献文曾孙赵郡王元毓[25]。梳理其身份特点,不难发现:首先,他们均为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的直系后裔,是正牌的王朝宗室,地位和待遇绝非道武以前诸帝后裔可比。其次,他们的父祖或本人享有王公重爵,在贵族阀阅序列中位居“膏腴”最顶层,即凌驾庶姓乡品的超品级别。元泰的家世出身与之如出一辙,通过此类横向比较,确证先前关于其门第等级的判断。
实际上,关于北魏散骑诸职起家的层级关系,宫崎市定早有论断:“起家的最高官职为散骑,散骑有散骑常侍(从三品)、通直散骑常侍(正四品下)、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都是正五品上)、通直散骑侍郎(从五品上)和员外散骑侍郎(正七品上)六种。其中,作为起家官一般是员外散骑侍郎……只有宗室或者准王室的近臣能够从五品以上(即通直散骑侍郎)起家,一般的臣下则多自六品以下,特别是七品以下起家。”[26]元泰身为皇孙王子,以通直散骑常侍起家应是朝廷规制使然。其地位略逊于散骑常侍起家的皇子亲王,但高于员外散骑常侍和诸侍郎起家的普通宗室,更是员外散骑侍郎起家的庶姓臣僚难望项背的。
三、志主元泰的升迁履历
墓志记录元泰的迁转历程较详:散骑常侍任上丧母丁忧守制,服阕后转任太常卿,俄迁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广州刺史,固辞不受。正史本传与之有所差异,仅记镇东将军、太常卿两项,未提坚辞外镇之事。综合二者推断,他守丧期满后先任太常卿,虽拒方镇之任,却接受镇东军号,以此在京赋闲,直至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殉难。这段履历尽管简短,但对了解北魏皇宗的发展境遇有一定帮助,解读其中奥秘的关键是北魏官员的仕进体制。
首先,丁忧是妨碍官员仕途的障碍之一,服阕启复能否保留原有职级至关紧要,同时也是衡量官员地位的有效办法。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极度推崇孝道,以驯化国人绝对顺从权威。为父母居丧期间的表现最能反映孝行,官员除国家特别需要夺情留用外,一律解除本兼各职归家守制25或27 个月,其间不准担任公职、不准宴饮娱乐、不准婚嫁社交,应当寝苫枕块、居于谅闇、素服弁带、极尽哀恸,凡此种种,付诸清议乡论,严加督促。如此一来,官员艰辛累积的资集自动清零,服阙复出只得重新开始,一般以低于原任的散衔过渡,待实职开缺后酌情递补,此举导致仕途停摆,对仕进前程冲击不小。当然,身份尊贵者不拘此例,或夺情留任,或官复原职,卓越者甚至委以重任。据此分析元泰,志文褒奖他的孝行:“太妃崔氏薨,寝苫食粥,率由导礼,婴号孺慕,感切行人。”俨然恪守名教的楷模,这种舆情反馈到朝廷,顺理成章地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复出所任官职乃执掌国家礼仪、领衔九卿的太常卿。此职晋令三品,太和前、后令分列从一品下和正三品[27]。品级、班位、清望度、效力值胜过原任散骑常侍自不待言,施展个性才华的舞台亦极大拓展。志文称:“位居九棘,秩亚三槐,敷赞九旒,兼司律礼。公乃搜求古文,广访儒学,必欲刊定钟吕,为一代准的。”标榜以制礼作乐、复兴文教为己任。排除其中溢美虚夸的成分,至少能够说明以元泰为代表的内徙胡人在汉化浪潮的洗礼下,文化水准、价值取向和气质面貌发生根本改观,他们挑战汉人士夫长久把持的礼学禁区,质疑权威的话语体系,敢于就尖端课题同知识精英一较高下。研究发现,北魏洛阳时代,愈来愈多的胡人出任太常卿,皇族又是其大宗,除元泰外,还有元寿安、元固、元端、元脩、元孝友、元恒、元顺、元修义、元瑞,约占总数的两成,超过胡汉任何家族,表明宗室既是汉化改革与民族融合的中坚,也是传承、捍卫华夏礼乐文明的主体[28]。元泰墓志堪称这一文化格局历史性转变的缩影,天潢贵胄的特殊身份赋予他无与伦比的发展前景,士族社会塑造人生归根结底靠阀阅门第。
其次,仕进顶点与家世出身紧密关联,据此逆推门第未尝不可。研究揭示,代表门第的乡品是对仕途前程的预示和承诺,它与仕进顶点的关系不是精确的定点对位,一品乡品并非都能攀升一品官位,二品乡品也未必具备担任二品官的潜质;而是概略式的区域对位,一品乡品准许跨越象征公卿的三品线,二品乡品准许跨越象征大夫的五品线。元泰的乡品是一品之上的超品,股肱宰辅乃理想预期,即便不能如愿,起码应跨越三品线,速度还要比一品乡品更快,不能像后者那般在资格临界线前徘徊迟延。元泰的仕宦顶点是镇东将军,晋令为三品,太和前、后令分列从一品下和从二品[29],距离宰辅尚有距离,假以时日还是有总揽朝纲可能的,怎奈河阴之变猝起,终结了预定的轨迹,坐至公卿的夙愿落空。值得注意的是,元泰从释褐起家到跨越三品线仅一步之遥,前举通直散骑常侍起家之宗室尽皆如此,照比异姓臣僚反复平调拉锯等待时机截然不同,而且这种质的跃升是在弱冠不久迅即完成的,皇族的特权性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洛阳新出北魏元泰墓志处处洋溢时代气息,其形制、书刻以及词藻文风无不彰显贵族气派。这里所说的“贵族”,不只是统治国家的政治权贵,还是社会文化场域的名门望族,融汇体制与社会的二元特性,即所谓门阀士族。它是汇聚曾祖以降三代官爵权势,主要通过婚嫁宦学之媒介,充分享受特权并形成显著、稳固的辨识特征,据此建构世袭、封闭、垄断、排他性的身份壁垒,凭借绵延不绝的传承积淀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安身立命,兼具自利性格和公益精神的家族群体或社会阶层,是中古独有的历史事物。元泰墓志恪守士族化书写范式,其贵族风范的流露是再正常不过的,毕竟北魏皇族作为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自然在士族化运动中独领风骚,成为引导时尚潮流的旗帜。志文有云:“公禀天地之英灵,挺自然之妙质,厥初怀抱,爰及志学,岐嶷韶亮,宽容都雅,擒文锦烂,谈谑泉涌,虽钟氏英童,曹家才子,语其先后,讵或前斯。”这种秀逸发于天生、门第合乎自然的陈词滥调是士族自我标榜的惯用套路[30],元泰墓志亦无法免俗。不过,它间接证明北魏皇族士族身份的自觉认同,是门阀化改革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而志文所载元泰简短的仕宦履历更是其身世信息的高度浓缩,连接起家、迁转诸节点,不难勾画出其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再将其置于仕进层级框架中衡量比较,便可比较准确地锁定他在阀阅序列中的位置。后世史家评论,优礼宗室者莫过元魏[31],由此获得真实、生动的注脚。事实证明,墓志等出土文献的研究,除了坚实的训诂考据外,也要结合具体的文化语境,紧密追踪时代发展的线索脉络,遵循古人固有的思维逻辑,才能有效发掘字里行间潜藏的深义,力争重返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