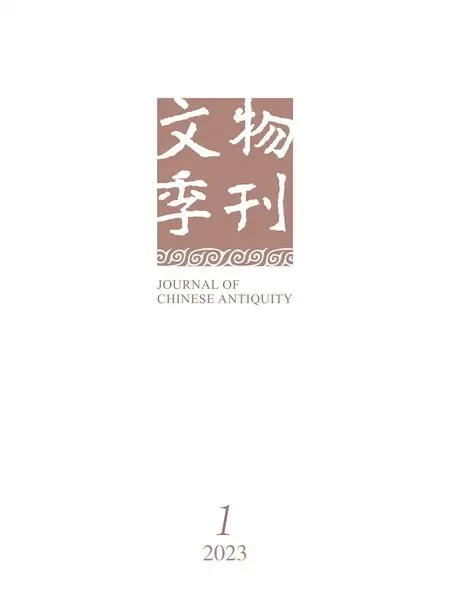垣曲北白鹅墓地族属及有关问题*
黄锦前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2020年4~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极为重要的新资料[1]。有关该墓地的国(族)属问题,随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所获铜器多有铭文,提供了一些殊为重要的信息,对两周考古及历史文化研究皆有重要作用,小文拟以铜器铭文为据,就有关问题谈一些初步认识。
一
该墓地发掘所获铜器铭文,目前公布和披露者主要有:
荐公?编钟(M1):荐公?作……。
荐公?鬲(M1):荐公?作器,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夺簋(M3:21、35)[2]:唯正月初吉,王在成周,庚午,格于太室,井叔内(入)佑夺,即位,王呼内史微册命夺曰:命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赐汝赤巿、銮旂,用事。夺拜䭫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命,用作朕皇祖中氏、朕文考釐孟宝尊簋,夺其万年眉寿永用,子子孙孙宝。
虢季甗(M3:10)[3]:虢季为匽姬媵甗,永宝用享。
匽太子簋(M5:12)[4]:匽太子作为行簋,用。
太保匽仲鼎(M5:20)[5]:太保匽仲作尊鼎,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用旂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太保匽仲鼎(M5:25)[6]:太保匽仲作为尊鼎,太保匽仲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匽仲太保鬲(M5:23)[7]:匽仲太保其作旅尊鬲,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毕鬲(M5:18)[8]:毕为其鼎鬲,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
太保匽仲盨(M5:8)[9]:太保匽仲作为宝盨,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之。
太保匽仲盘(M5:26)[10]:太保匽仲作盘,子子孙孙永宝用,华。
太保匽仲匜(M5:28)[11]:太保匽仲作尊匜,子子孙孙永宝用。
太师伯良父簋(M6):太师伯良父作为其宝簋,子子孙孙永用。。
太保匽仲盨(M6):太保匽仲为宝盨,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之。
仲大父簋(M6):仲大父作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华。
周射壶(M5:10、29)[12]:周射作尊壶,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中辛。。
发掘者认为,根据M3 出土铜簋铭文“朕皇祖中氏”和铜甗铭文“虢季为匽姬媵甗”,M6 出土铜盨铭文“太保匽仲”和铜簋铭文“仲大父”判断,墓地主人族属身份应当为“仲”和“匽”二者其一,后者尤为可能。该地很可能是一处王畿内的采邑,北白鹅墓地是一处两周之际位于成周王畿之内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有学者认为“匽”系南燕,或系北燕,发掘者据铜器铭文的“匽仲太保”认为其属召公奭之后的召氏家族。
据文献,周代燕分南、北,北燕是召公奭的封国,姬姓,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建都蓟(今北京城西南隅)。战国时为七雄之一,后为秦所灭。《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裴骃集解:“《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南燕姞姓,传为黄帝之后,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部。《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杜预注:“南燕国,今东郡燕县。”孔颖达疏:“燕有二国,一称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别之。《世本》:‘燕国,姞姓。’《地理志》:‘东郡燕县,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史记·秦本纪》:“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张守节正义:“燕,南燕也。”
据铜器风格特征、铭文内容及器物出土地点等看,此批器物应与燕国(北燕)无关,墓地族属更与燕国及燕人皆无涉。
二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仲大父簋[13]。敛口,鼓腹,圜底,兽首半环耳,圈足下连铸三兽面小足,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捉手内饰圆涡纹,盖面上部和器腹饰瓦沟纹,盖沿、器口下及圈足饰变形夔龙纹。铭作:
仲大父作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华。
与北白鹅M6 出土的仲大父簋同铭,应系同人之器,该簋应盗掘自北白鹅墓地。《铭三》定其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应为春秋早期器。
尤值得注意者,簋铭之末的徽记“华”,又见于M5 出土的太保匽仲盘铭文。M5、M6 关系密切,发掘者判定为一组夫妻合葬墓,应可信。太保匽仲盨在M5、M6 两座墓皆有出土。合观之,M6 出土仲大父簋的仲大父应即M5、M6 出土太保匽仲诸器的太保匽仲(或称“匽仲太保”),“仲”系氏或排行,“大父”系其字,“太保”系其所任职称。太保匽仲系华族氏之人。
《铭三》收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太保匽仲匜[14],铭作:
太保匽仲作荐匜,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用旂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铭文与北白鹅M5 出土的太保匽仲匜铭大同小异。
匜横截面成瓢形,长流槽上扬,腹微鼓,后有龙形鋬,龙口衔沿,竖耳鼓睛,四腿收束,短尾上卷,圜底下有夔龙形四扁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瓦沟纹。与北白鹅M5出土的太保匽仲匜形制、纹饰亦近同,唯后者口沿下饰重环纹。年代为春秋早期,《铭三》定为西周晚期,偏早。该匜应盗掘自北白鹅墓地。
合观M5 出土的太保匽仲鼎“太保匽仲作尊鼎,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用旂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毕鬲“毕为其鼎鬲,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及太保匽仲匜“太保匽仲作荐匜,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用旂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诸铭,可知太保匽仲与毕应为一人,“毕”系太保匽仲之名。
总之,太保匽仲系华族氏人,名“毕”,字“大父”,职任“太保”。
“华”作为徽记标识,屡见于铜器铭文,如:
中姞鬲[15]:中姞作羞鬲,华。
中义父鼎[16]:中义父作新客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华。
中义父盨[17]:中义父作旅盨,其永宝用,华。
中义父诸器系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中义父等与位于今晋西南垣曲一带的匽国系同族,华族铜器多出自周原地区,应系其族人在王朝为官之遗留。
1967年陕西长安新旺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逋盂[18]铭曰:
唯正月初吉,君在潦既宫,命逋使于遂土,其各姒司寮女寮:奚、微、华,天君使逋使沬,逋敢对扬,用作文祖己公尊盂,其宝用。
“华”应指华族。
合观周原和垣曲出土的华族铜器,可见周代华族的聚居地应在今晋西南一带垣曲附近。其入仕王朝者,在畿内应有封邑。
著名的大克鼎(善夫克鼎)[19]铭曰:
据铭文所反映的有关地名来看,“锡汝田于匽”的“匽”或即匽国在畿内之封邑,与邢、燕(北燕)等诸侯国在畿内皆有封邑相仿。由此也可见,匽在王朝是有一定实力的一方诸侯,北白鹅墓地发掘所见其墓葬及随葬品规模、等级和规格等对此也能予以印证。
“华”系族名,“匽”系其聚居地之名,即地名兼作国族名。类似情况在当时颇多,如周初芮国被封于今陕西扶风一带的殷商祈族故地,旂(祈)系芮都宫室宗庙所在,故铜器铭文中又常以旂(祈)代称芮,祈伯簋[20]、旂伯簋[21]“旂(祈)伯”即芮伯,叔友簋[22]、旂姬鬲[23]“旂姜几母”“旂姬”的“旂”皆系族氏名,系以地为氏[24]。又晋之先祖唐叔虞成王时始封于唐,曰“唐”,叔虞子燮父被徙封于晋(今山西曲沃),以在晋水改称“晋”。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魏,因魏惠王迁都大梁,又称梁。再如考古发现的两周时期的曾国,在古书中又称作“随”,“曾”“随”之称皆由其所封之地名而来[25]。
“匽”系地名兼作国族名,“华”系族名,综合有关铜器铭文看,太保匽仲、仲大父诸器的“仲”应系氏称,夺簋“用作朕皇祖中氏”,可证。仲氏之源起,或即夺之皇祖中氏。“太保匽仲”称谓系“职称+地(国族)+氏”,与“仲爯父太宰南申”(仲爯父簋[26])、“曾少宰黄仲酉”(曾少宰黄仲酉鼎、甗、簠、方壶、盘、匜等[27])等格式相若。“匽仲”称谓格式犹“曾季”(曾季卿事奂壶[28])、“楚季”(楚季苟盘[29]、楚季子钟[30])、“黄季”(黄季佗父戈[31])等。“仲大父”系常见的“氏+字”格式。
上述太保匽仲与中义父、中姞等同为华族人,中义父、中姞年代皆为西周晚期,夺簋年代为西周晚期,两相对照,中义父、中姞的“中”亦应系氏名,与太保匽仲一样,中义父、中姞亦系夺之皇祖中氏之后,姞姓,中氏。
太保匽仲据称谓看,所任应系王朝太保,例同司马南叔匜[32]的司马南叔于春秋早期在王朝任司马之职[33],否则应如“曾太保”(曾太保弁盨[34]、曾大保嘉簋[35]、曾太保发簠[36]、曾大保庆盆[37]、曾大保叔亟盆[38])、“蔡太师”(蔡太师䑂鼎[39])、“齐太宰”(齐大宰归父盘[40])等称“匽太保仲”而非“太保匽仲”。M5年代为春秋早期,则匽仲应于东迁后在今洛阳的东周王朝任太保,北白鹅墓地距成周洛阳仅80 千米,因而死后归葬于故国族,合情合理。
M3 出土的夺簋,子母口,口内敛,方唇,兽首衔环耳,短垂珥,鼓腹内收,微下垂,底近平,下接圈足附三扁支足。盖面隆起,喇叭形捉手。器外壁饰窃曲纹带、瓦楞纹、斜三角云纹、兽面纹。盖面近沿处饰一周窃曲纹带,靠捉手处饰两周瓦楞纹。据形制、纹饰及铭文可知,其年代应在西周晚期厉王前后。据铭文,王命夺“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所任系要职,夺应系地位很高的高级贵族。其后人中义父及太保匽仲亦于王朝世袭卿士,匽仲任太保,亦系显要职务。可见两周之世,匽在王朝势力不容小觑。
上述据文献,南燕系姞姓,也有学者认为西周时期南燕在晋西南一带,但据文献记载的南燕地望看,此匽应与南燕无涉。
《铭三》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太师伯良父簋[41],铭文与北白鹅M6 出土的太师伯良父簋相同,应系同人之器,该簋应盗掘自北白鹅墓地。簋敛口,鼓腹,圜底,兽首半环耳,圈足下连铸三兽面小足,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捉手内饰蜷曲夔龙纹,盖面上部和器腹饰瓦沟纹,盖沿、器口下及圈足饰变形兽体纹。《铭三》定其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应系春秋早期前段器。
簋铭“太师伯良父”,与太保匽仲一样,其所任应系王朝太师。铭末徽记符号“”表明其应非华族之人。同样徽记符号者,亦见于西周中期的师 鼎[42]、师趛鼎[43]、师趛鬲[44],可见有周一代,该国族之人常在王朝任师职。该簋出自北白鹅墓地,或系馈赠、赙赠等途径所致。
东周铜器铭文中屡见“匽氏”,如:
匽氏戟[45]:十四年,□平匽氏造□。平陆。
上郡守匽氏戈[46]:十四年,上郡守匽氏造,工㼽。洛都。博望。
匽氏钢刀[47]:十四年,上郡守匽造,丞□、司马巷、啬许□止、上但□,咸阳工。十四年,守匽氏造,内史□、□□□冉、邦工师庶、□敓啬、司马许□命左工工□、司寇公乘兄□□疪。
“匽氏”据上下文看应与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散氏”“原氏”(原氏仲簠[48])“吴氏”(吴氏季大鼎[49])“韩氏”(韩氏私官壶[50])等称谓相同,“匽”与“散”“原”一样,系族氏名。匽氏系上郡守,其地位应较高,结合匽氏戟的置用地点为平陆等信息来看,诸铭的匽氏很可能即匽国之后裔,系以地为氏。此批兵器系上郡监造,秦国上郡郡治在肤施县(今陕西绥德县),与垣曲相距很近,亦可佐证。
三
北白鹅墓地据目前发掘情况看,应系匽国高级贵族墓地,其年代跨越两周之时。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著录有一件近年私人收藏的匽伯鼎[51],铭作:
匽伯作齐(齍)鼎。
青铜器铭文中,燕国国君一般称“燕侯”“燕王”,《铭续》将“匽”读作“燕”,恐非。此鼎敛口窄沿,立耳,下腹倾垂,三柱足上粗下细。颈饰两道弦纹。据形制、纹饰特征及锈色看,应非燕国器物,而系晋西南一带所出。合观之,此鼎应系位于今晋西南的匽国之器,匽伯即匽国族君长。此鼎据形制、纹饰看年代应为西周中期前段,穆王前期器。应盗掘自晋西南一带西周中期匽国墓地。
《铭续》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匽鼎[52],铭作:
匽伯作宝鼎。
鼎侈口,尖唇,鼓腹,圜底,立耳,三柱足。颈饰分尾长鸟纹,以云雷纹填地。年代为西周中期,穆王前期器。据形制、纹饰及锈色看,应系晋西南一带盗掘出土。
铭文《铭续》释作“匽作宝鼎”,仔细观察,“匽”下应有字“白”即“伯”,应据改。鼎名亦应改作匽伯鼎。上述两件匽伯鼎的匽伯应系一人。由此可见,匽国在晋西南一带至迟自西周中期延续到春秋时期,源远流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传世的燕伯圣匜[53],铭作:
匜长流槽,腹较深,直口,龙形鋬,四兽形扁足。口沿饰变形兽体,腹饰瓦纹。此类形制、纹饰风格的器物,屡见于晋西南一带,而在北方的燕国则基本未见,该器也应系位于今晋西南一带的匽国之器,而非过去一般所认为的系北方燕国之器。匜之年代,过去一般定为西周晚期[54],据形制纹饰及铭文与有关器物及铭文对比来看,应以定为春秋早期为妥。匜铭“匽伯圣作匜,永用”,类似简质的辞例风格屡见于同时期晋西南一带及邻近地区的铜器铭文中,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虢季簋(M2001:95、67、146、86、94、75)[55]“虢季作旅簋,永宝用”、山西黎城西关墓地出土的楷侯宰吹壶(M8:7、12)[56]“楷(黎)侯宰吹作宝壶,永用”、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芮公父壶[57]“芮公父作造宝尊,永用”、陕西千阳崔家头出土的成周邦父壶盖[5“8]成周邦父作干仲姜宝壶,永用”,等等,亦可佐证。
“匽氏”“匽伯”等称谓,与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散氏”“散伯”称谓相类。
《铭三》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匽太子鬲[59],铭作:
匽太子作荐鬲,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
据北白鹅M5 出土的匽太子簋看,此鬲应盗掘自北白鹅墓地。“匽”《铭三》读作“燕”,不确。将其年代定为春秋晚期,偏晚,应系春秋早期。
匽太子与同时期铜器铭文中常见的“芮太子”(芮太子鼎[60]、鬲[61],芮太子白鼎[62]、鬲[63]、簠[64]、壶[65])、“虢太子”(虢太子元戈[66])、“上鄀太子”(上鄀太子平侯匜[67])、“黄太子”(黄太子伯克盘[68]、盆[69])等称谓相同,据此可以确定,匽应系与芮、虢、上鄀、黄等一样,系诸侯国。
《铭三》还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匽子盨[70]铭作:
匽子作旅盨,其子子孙永用为宝。
该器未公布器形图像,据铭文看年代应为春秋早期,而非西周晚期。该器据铭文字体及辞例格式等看亦应系匽国之器,《铭三》将“匽”读作“燕”,不确。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传世的匽公匜[71],铭作:
匽公作为姜乘盘匜,万年永宝用。
匜长流槽,兽首鋬,底下有四扁兽足。腹饰蟠虺纹,腿饰夔纹。年代为春秋早期。据器形、纹饰和铭文字体看,该匜或非北燕之器,过去一般皆将“匽”读作“燕”,或非。据匜铭,此匜系匽公为其夫人姜乘所作。据同时期与匽邻近的虢(虢姜鼎[72]、甗[73]、簋[74]、铺[75]、壶[76]、虢姜簋盖[77])、芮(仲姜鼎[78]、甗[79]、簋[80]、壶[81])、晋(晋姜鼎[82]、晋姜簋[83])等国皆与姜氏联姻的情况来看,匽与姜氏通婚,也合情合理。
四
北白鹅墓地所出虢季甗铭云“虢季为匽姬媵甗”,据铭文,此甗系虢季为其女出嫁匽国所作媵器。甗长方体,上甑下鬲分体铸造,子母口套合。甑外通体饰窃曲纹、波曲纹,云纹、重环纹。年代为春秋早期。春秋早期的虢国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及山西平陆一带[84],与位于今垣曲一带的匽国紧邻,故有婚姻往来。
传世有一件虢季匜[85],铭作:
虢季作中姬宝匜。
该器原藏潘祖荫,现下落不明。年代过去定为西周中期[86]。据铭文字体看显系春秋早期,应据改。结合北白鹅墓地所出虢季甗“虢季为匽姬媵甗”来看,匜铭与甗铭的“虢季”系同人,“中姬”即“匽姬”,“中”系其夫氏,“匽”系其夫之国族名,此匜亦系虢季为其女出嫁匽国所作媵器。
《铭三》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虢季子白鼎[87],铭作:
虢季子白作匽孟姬媵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对照可知,北白鹅墓地所出虢季甗“虢季为匽姬媵甗”的虢季实即虢季子白。据《铭三》介绍,该鼎2018年9月见于西安,应盗掘自北白鹅墓地。鼎侈口宽沿,敛腹圜底,腹较浅,高附耳,与口沿有两根横梁相连,底置三蹄足。颈饰窃曲纹,腹饰垂鳞纹。年代应系春秋初年,《铭三》定为西周晚期,应偏早。
传世有虢季子白盘[88]、虢宣公子白鼎[89]各一件: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虢宣公子白作尊鼎,用卲享于皇祖考,用旂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鼎平沿方唇,立耳,半球形腹,三蹄足。颈饰兽目交连纹,腹饰鳞纹,间隔以弦纹。盘圆角长方槽形,直口方唇,下腹收敛,平底下有四个矩形足,四壁各有龙首衔环耳一对。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波曲纹。其年代过去皆定为西周晚期,宣王时器。
其器主虢季子白与虢季子白鼎的虢季子白及北白鹅墓地出土虢季甗的虢季应系同人,盘之年代,最近有学者将其推迟至携王之时[90],亦非,应据改。
五
《诗·大雅·韩奕》: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毛传:“师,众也。”郑笺:“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陆德明《释文》:“溥音普。燕,于见反。注同。徐云:‘郑于显反。’王肃、孙毓并乌贤反,云:‘北燕国。’”孔颖达正义:“‘溥,大’,《释诂》文。燕礼所以安宾,故燕为安也。此言溥,犹《生民》之言‘诞’,故云大矣。为叹美之辞。韩城之言,为下而发,则韩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师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时,众民共筑而完之。据于时尚不毁坏,故言完也。”朱熹《诗集传》云燕系召公之国。韩系周宣王时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在今山西河津东北。西周、春秋间为晋所灭。《诗·大雅·韩奕序》:“《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毛传:“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
郑笺训“燕”为安,孔颖达正义云燕礼,与上下文皆不辞,系曲解经义。朱熹集传云燕系召公之国,燕与韩地隔玄远,于情理事实皆不合。可见诸家训释是有问题的。
《诗·大雅·崧高》: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毛传:“召伯,召公也。”郑笺:“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令往居谢,成法度于南邦。”孔颖达正义:“言亹亹然勉力于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继其故诸侯之事,令往作邑于谢之地,以统理南方之国,于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离背王室,当先营彼国,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营谢邑,以定申伯往居之处,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于南方之邦国。”“申伯之功,召伯是营”郑笺:“申伯居谢之事,召公营其位而作城郭及寝庙,定其人神所处。”正义:“此说往营谢邑讫而告王,言申伯居谢之事,乃召伯于是营其位。处于营之处有所作者,其是谢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寝庙。”
又史墙盘[91]、钟(3 式)[92]铭曰:
青幽高祖,在微灵处,雩武王既翦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命周公舍宇于周,俾处。
雩武王既翦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命周公舍宇以五十颂处。
即武王责令周公置房舍于周,以安置微氏家族。其立意与宣王命召伯营谢邑以安申伯近似。
又叔尊[93]、叔卣[94]:
侯曰:“叔!丕显朕文考鲁公,垂文遗功,不肆厥诲。余命汝自来诲鲁人,为余宫,有姝俱成,亦唯小羞。余既省,余既处,亡不好,不忤于朕诲。”
据上下文并结合文献所载宣王时使召伯营谢邑以定申伯及铜器铭文所见周初鲁国建都营邑之例等看,“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的“燕”很可能即匽国之“匽”,“师”毛传谓“众也”,《诗·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郑笺:“师,众也。”所谓“燕师所完”,即匽国民众(徒众)帮助韩侯建都营邑,与文献及金文所载召伯营谢邑以定申伯之国及叔助鲁侯建都营邑之事相若。宣王时匽国在今晋西南一带,与韩国相近,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亦皆吻合无间。
总之,北白鹅墓地的发掘,为一些铜器找到了确切的归属,使有关铜器铭文记载得以落实,也为订正部分铜器断代和古书训释的错误提供了重要依据。
六
综上所述,据铜器风格特征、铭文内容及器物出土地点等,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的匽与文献记载的南燕、北燕皆无涉。匽系位于今垣曲一带的国族,姞姓,在畿内有采邑,北白鹅墓地系匽国贵族墓地。东周兵器铭文中的“匽氏”或即其后裔,系以地为氏。
夺簋出自春秋早期匽国墓葬,应系墓主祖先的遗产。夺厉王时在王朝任要职,系高级贵族。其后人中义父及匽仲皆在王朝世袭卿士。太保匽仲与周原出土的中义父诸器的中义父同族,系华族之人,中氏,春秋早期在王朝任太保,死后归葬故国。两周之世,匽在王朝势力不容小觑。
匽国与位于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及山西平陆一带的虢国邻近,互有婚姻往来。北白鹅墓地所出虢季甗、虢季子白鼎的虢季(子白)与清末出土虢季子白盘的虢季子白系同人,盘之年代亦应系春秋初年。
近年盗掘出土的匽伯鼎、匽太子鬲、匽子盨及传世的燕伯圣匜、匽公匜等皆系匽国之器,而非过去一般所认为的系北方燕国之器。匽国在晋西南一带至迟自西周中期延续到春秋时期,源远流长。
据上下文并结合有关文献及铜器铭文记载,《诗·大雅·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的“燕”应即匽国之“匽”,所谓“燕师所完”,即匽国民众为韩侯营建都邑,与文献及金文所载召伯为申伯营谢邑及叔助鲁侯建都营邑之事相若。
北白鹅墓地时跨两周,地接两京(宗周与成周),所出铜器铭文等资料沟通了两周的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古代文明的瑰宝。该墓地所出资料,不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问题,更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或有争议的旧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可靠的证据,为两周历史考古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随着考古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还会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其价值和重要性也会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