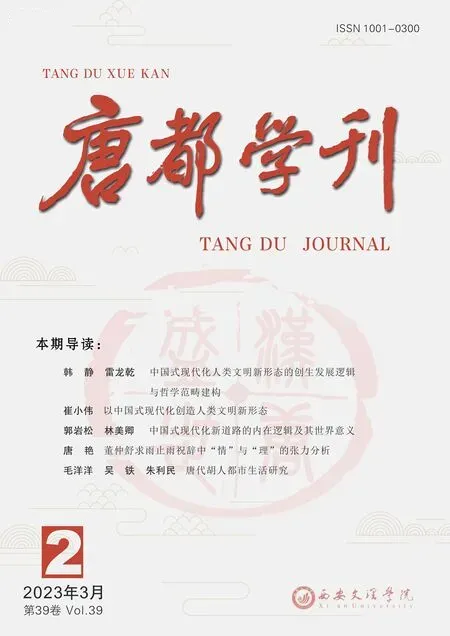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
——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李 睿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00)
一、对张载“合性与知觉”的不同解读
张载的心性论思想上承其构建的天道观,下启其工夫论,在其天人一贯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蒙·太和篇》有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7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来对“心”进行的界定,打破了当时以“知觉”为“心”的流行性见解,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具有创新意义[2]。但古往今来,诸多学者对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心性论论述提出异议。其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朱熹认为心自有知觉,并不需要“合性与知觉”才能有心,认为张载的“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之说,“大率有未莹处”[3]1432。在朱熹看来,心是统领性和情的,心中未动的天理(本体)即是性,心已动的对万物的感知(用)则是情,心则“包得已动未动”[3]93。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朱熹对张载的“天”“道”“性”“心”四句做了解读:
曰:“虚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无少欠阙,便是性;感动而动,便是情。横渠说的好,‘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此是总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说。”[3]94-95
这里朱熹不仅对“心”“性”“情”进行了三分,而且对张载的“天”“道”“性”“心”四句做了一个总分式的逻辑解读,认为“天”“道”与“性”“心”之间是总分的关系,“天”“道”是对“理”之规律性的总说,“性”“心”则是就人与物上具体的分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解说,都是以他自己的义理间架为基底,顺着自己的思想理路来诠释的,并不符合张载的原意。这里的关节点在于朱熹和张载二人对“性”的定义不同。在朱熹这里,“性”承接自程颐的“性即理”,即“性”是本体之“理”,是形上之实有。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道人生需落实于格物穷理的顺取之路。而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天”“道”“性”“心”是一以贯之的,体现了天人一贯的一个整体。张载所言的“性”上承自其天道观,有其本体义,同时“性”在下接人伦世界的时候,又有其道德义。在天人一贯的走向里,体现为人性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天地之性”是本然,“气质之性”是实然。这与“知觉”之“合”会有不同的效果,只有“天地之性”才能为“知觉”提供至善的道德本体支撑,故而由“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的“善反”之过程是应然,这一“善反”之进路,不仅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而且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由此可见,朱熹对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解读,并未全然符合张载之原意,所以朱熹此处对张载的批评并不成立。
牟宗三也认为张载的“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之说“亦不的当”[4]454,但与朱熹的批评不同。牟宗三认为性体中自有知觉,心并不需要“合性与知觉”才能成立,心其实是“性体寂感之神之灵知明觉或虚明照鉴”[4]456。牟宗三这里的解读,亦是以他自己的义理间架为基底,顺着自己的思想理路来诠释的,也不符合张载的原意。这里的关节点在于牟宗三和张载二人对“合”字的理解和运用的不同。牟宗三认为“合”用在此处是“不精熟之滞辞”[4]454,认为“知觉”本是“性体”发用流行之自然,“性体”之明觉自然的发用流行中,自能逆觉体征得“心”,无需多此“合”一举。这明显是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而以此来解读张载并不符合张载之本意。如上文所言,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天”“道”“性”“心”是一贯的,所以张载所言的“合”,无论是“合虚与气”还是“合性与知觉”,重在体现其中天人合一之一贯的动态,而且澄澈出人在这一动态之“合”中的主体能动性。牟宗三对张载此处的批判更多地是站在自身思想体系和概念逻辑中进行的,一方面不符合张载思想之原意,另一方面未看到张载“合性与知觉”之天人一贯思想背后的历史使命与现实关怀。
由上可见,诸多学者对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心性论论述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但这些学者基于自身理论来解读张载的思想具有局限性,并未看到张载“合性与知觉”之心性论思想在其“天”“道”“性”“心”整体思想体系中的天人一贯性,也未正视张载如此构建心性论思想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及其心性理论构建的思想史意义。笔者尝试通过分析朱熹和牟宗三对张载“合性与知觉”的不同解读,回归到张载的思想结构本身:厘清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心性论思想在其“天”“道”“性”“心”框架体系中天人一贯的理论进路;察觉张载“合性与知觉”的心性论思想构建中辟佛排老和重建道统的内因外缘;挺立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中的道德主体;定位张载心性论思想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影响。
二、张载“合性与知觉”提出的内因外缘
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心性论思想,出自其晚年思想成熟的理论著作《正蒙》中的“太和四句”:“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其心性论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但这个思想之所以会受到诸多学者的非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持批评观点的学者们是从自身理论视角出发,忽视了张载提出这个心性论思想时所面对的重建道统与辟佛排老的内因外缘。张载思想构建的原因就在于辟佛排老的历史使命,同时反省汉唐儒学之大蔽,这一点张载是充分自觉的,他通过对佛老体用殊绝的批判构建了自己的“太虚”本体,并通过本天道以立人道的进路,实现了与佛老“较是非曲直”的目标。
隋唐时期的儒家无论在宇宙本体论层面,还是在心性论层面都受到佛、道的冲击。士大夫往往于三教之间徘徊,形成一种“儒者无所不淫”于佛、道之学的局面。这里的关节点在于佛道二教对儒家进行了理论深度的非难,而汉唐儒学却难以抗衡。隋唐时期的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以创作代替了翻译,又成立了新的宗派,在隋唐时期佛教宗派林立,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等。这一阶段的佛教在义理发展与社会影响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高妙思辨的心性论给儒家和道家、道教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阶段佛教的发展与三教融合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以禅宗和华严宗为代表。禅宗是中国本土创立的佛教,舍弃了佛教理论中的繁冗,在继承竺道生的佛性论、顿悟说基础上以“顿悟见佛”的心性本体为主,兼采儒家性善论与道家自然主义,基本构建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华严宗的宗密(780—841)著有《华严原人论》,其中对儒、道两家进行了非难,并试图会通本末,以佛会通儒、道,以此来将儒、释、道会归一源。
《华严原人论》由斥执迷、斥偏浅、真显真源、会通本末四篇组成。其中斥执迷篇的主旨就是对儒、道两家元气说的非难。道家的宇宙生成观将万物的生成包括人的生成归之于自然虚无之道,宗密非难道家的这种生成观,认为如果依道家生成观来看,万物生化源于自然,那么岂不是“石应生草,草或生人”!儒家讲天命,“言贫富贵贱、贤愚善恶、吉凶祸福皆由天命者”,但现实往往呈现出福祸不一致的局面,那么该如何解释这德福不一致的现实人伦世界?[5]229宗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道家宇宙论和汉唐儒家宇宙论中的元气说中将道德心性与本体割裂两端的弊端[6]。仅仅以虚无之道为世界本原的话,并无法将人类社会与草木走兽相区分。宗密这一批判,也为儒道两家认清自己在宇宙论架构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方向[7]。不可否认的是,宗密对儒、道的批判目标是一种以佛为宗对儒、道的融贯,试图在儒、道和佛教内部各宗派的统摄下,直指“本觉真心”的心性本原。《华严原人论》本身除了是对儒、道的非难和对佛教其他宗派的判教以外,更是一种在统摄佛教内部各派基础上的三教合一趋向。宗密在《华严原人论序》明确提到:“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5]228也就是说虽然宗密是以佛之“本觉真心”的心性为世界之本源,但同时又认可三教不同的心性修养方法殊途而同归,皆以“惩恶劝善”为目的。所以宗密的思想也融贯了儒家的心性论学说和道家的“损之又损”“返本还源”的思维方式。
既然佛家的非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如何丰富儒家思想来与佛、道相抗衡在隋唐时期已经成为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隋唐时期的儒家学者已经开始有回应佛、道挑战的自觉,在心性论上表现为对佛教佛性论的批判与融会。隋唐儒家对佛教心性论有批判也有融摄。批判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以韩愈(768—824)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受到佛教的“祖统”影响,试图通过重建儒家“道统”来向先秦儒家心性论复归,并以此来批判佛教的心性论,想要达到与佛教相抗衡的目的。韩愈《原道》中提到:“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柯之死,不得其传焉。”[8]18韩愈在这里为儒家辨明正统,接续孔孟,试图重建“道统”。韩愈重建“道统”的努力就是对《大学》的提倡,将儒家“诚意”之“内圣之学”重新提升,拟与佛教心性论相抗衡。但因韩愈所承接的天道观仍然是汉唐以来的宇宙自然观,未完成从本体上挺立儒家道德心性的任务。所以并不能真正实现与佛教的抗衡。通过韩愈的努力,儒家学者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向先秦儒家的复归尚不足以与已经在宇宙论和心性论有所建树的佛、道相抗衡,于是儒家学者开始自觉的融摄佛、道,其中以李翱的援佛入儒为代表。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在继承孟子和《中庸》思想的基础上汲取了禅宗的思想。李翱援佛入儒而又能够坚持儒家立场的做法无疑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指引了方向,而且这一做法被宋明理学家所继承,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北宋时期的儒家由经学转出义理之学,并从义理之学中脱出理学。排斥佛、道以复兴儒学成为北宋时期儒家学者的普遍要求。批判的态度由激励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8]19逐渐转向“修其本以胜之”[9]。这为北宋理学家能够出入释老、返归“六经”并汲取佛、道所长以重构道统奠定了认识基础。北宋理学崛起初期正是在这种“三教合一”思潮的推动下,融摄了佛、道的宇宙本体论与心性修养论,构建起儒家的道德本体体系,用至善的道德本体将伦理社会与自然宇宙的生发圆融于儒家体系之中。
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面对着佛、道二教的挑战,张载之所以“出入佛老、返归‘六经’”,是担负着当时儒家学者重建道统的历史使命。张载有着本天道以立人道内在驱动力,可以说推天道以明人道是张载构建起天道观之后其思想的必然走向。张载直言佛老的缺失就在于其理论的“体用殊绝”“不知本天道为用”:
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梦幻,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1]8
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所从也。[1]26
虚空即气是体用相即,“有无”“隐显”“神化”“性命”是天道本体的自然发用流行,“本天道为用”“天性”必“范围天用”而落地于人生,就是天道一定是要落实于人道之中的,人道也一定能够推本于天。天道性命是相贯通的,这是张载以之批判佛老的理论基础。
张载为了重建“道统”“修其本以胜之”,在历史使命的推动下,自觉地在“天”“道”“性”“心”的天人一贯体系中来构建自己的思想心性论思想。王夫之曾盛赞张载心性论思想对异端的有力回应:“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通;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尽心知性,则存顺没宁,死而全归于太虚之本体,不以客感杂滞遗造化以疵类,圣学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异端之所可溷也。”[10]那么,张载究竟如何“合性与知觉”呢?重点在于其构建起了天道性命相互贯通的思想体系。
三、张载“合性与知觉”的“天”“道”“性”“心”之一贯
从能代表张载思想成熟的《正蒙》来看,其内容由天道到人道逐次展开,并且落之于天道性命之贯通上,用《正蒙》中的语句概括就是:“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且“天”→“道”→“性”→“心”逐次展开。也即是说,张载的“合性与知觉”是融合在其“天”“道”“性”“心”的天人一贯之体系中的。
在张载的思想中,构建了具有天道本体和道德本体双重含义的“太虚”本体。具体到张载天道观的构建来看,最关键的节点就是“太虚”本体之挺立。“太虚”本是出自《庄子》的表示宇宙空间的概念,张载在重新诠释《易传》和《中庸》的基础上对道家的“太虚”概念进行了改铸,将道家自然主义天道观与儒家生生的天道观进行了改铸性的融贯,通过对“太虚”与“气”关系的阐发,挺立起儒家的天道本体。“太虚”除了宇宙本体的蕴含外,还有道德本体之蕴含。这正依赖于张载思想体系中对“心”的挺立。
张载通过对“太虚”的天道本体义和道德本体义的并建,尤其是对道德本体的开显,打破了当时以“知觉”为“心”的流行性见解,把儒家心性的超越层面揭开,使当时儒家“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张载并没有沉醉在自己构建的形而上的本体系统中,而是非常自觉的进一步本天道以立人道,在此“合性与知觉”之天人一贯中践履心性工夫。“性”在张载的思想里,是建立在“合虚与气”的基础上的:“性”与“虚”之“合”为“天地之性”;“性”与“气”之“合”为“气质之性”。故而体现为人性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
“天地之性”是本然,“气质之性”是实然。只有“天地之性”才能为“知觉”提供至善的道德本体支撑,故而由“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的“善反”之过程是应然,这一“善反”之进路,通过对道德本体之挺立:不仅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而且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
从张载的思想展开总脉络“天→道→性→心”出发,可以看到张载思想立论的基础是对天道观的构建,但其构建天道观的目的绝不是要停留在对自然天道的认知层面,而是要由天道贯通到人道。
通过对“太虚”天道本体义和道德本体义的双层开显不难看出,张载“天→道→性→心”的思想进路正符合其本天道以立人道的进路。通过对“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进路的考察,“太虚”的两层含义已经明确,一个是天道本体,一个是道德本体。也正是因为“太虚”本身兼具两层含义,所以“天道”与“人道”得以一以贯之:“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1]63
从本天道以立人道的进路来看,张载建立了具有天道本体义和道德本体义的“太虚”本体,并根据“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逻辑展开自己的思想构建。
四、张载“合性与知觉”对道德主体的挺立
张载是顺着“天”→“道”→“性”→“心”的进路构建其思想的,在这个动态一贯的体系中,“性”之所以可以落实到人生,是通过“性”与“知觉”的“合”成的“心”来达成的:“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1]22这是张载在解读《论语》基础上的阐发。依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1]“道”之“弘”离不开“人”,正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先秦儒家对道德主体的挺立。但是随着汉唐时期儒家开始对“天”赋予神性,将“弘道”的可能性归结于“天”,在“天”的统筹下,人才能顺天而为,拥有“弘道”的权利和义务。这无疑剥夺了人“弘道”的道德主体性。这也正是汉唐儒学认为可以学圣人但却不可以至圣人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义理背景之下,张载需要打破汉儒的弊端,复归先秦儒家对人之道德主体性的挺立,于是张载在天人一贯的思想体系中强调“心”。所以张载提出“心能尽性”根源于“人能弘道”,而“心”之所以能够“尽性”就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的道德主体性的一贯,因此也就有人才能“检其心”,并可以通过“检其心”做修养工夫,从而达到“尽心则知性知天”的理想境地。因为这种“检其心”可以达到“不以见闻梏其心”,这时候已然是一种“尽性”的状态,这时候已经达到“圣人”“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境地。当然,这种“不以见闻梏其心”的“尽心”状态,是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挺立其道德主体,呈现出的不囿于“见闻之知”,而向“德性所知”靠近的工夫进路[1]24-25。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检其心”做修养工夫,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
“见闻之知”是人“心”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和遮蔽而形成的人最基本的对客观世界的表象认知,但这种认知层面尚不足以“合天心”,向外求的“知”不能完全“合天心”,因为“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能“合天心”的“知”是“内外合”的“知”。故而需要向内澄澈,澄澈出“心”之本然的“德性所知”。“德性所知”更为根本,向外所求的进路无法取得“德性所知”,所以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而“德性所知”只能靠人对道德主体性的觉知,要向内澄澈才能取得。张载通过对“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对比,将“心”的挺立,也即人的道德主体性落实于对“德性所知”的追寻。没有“德性所知”是无法“合天心”的。张载认为:“万物本一”,此“一”即“无所不感”的“太虚”本体,“人心”之内外合一的“所从来”正是源于“太虚”本体。“太虚”本体的重要功能是能够相感相合,又能够“合异”。天道万物之生成依赖于“太虚”与“气”的相感相合,而贯彻于天地万物生成的“太和”之“道”皆是以“太虚”为本体。无论是人性还是天性,无论是“性”还是“天道”,皆是由于“太虚”之神用与“气”相感相合而生,又须臾不离“太虚”之一贯之道[1]63。这里的“合”是在“太虚”本体影响下动态的双向运动,也就是说“太虚”本体是能够合“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见闻所知”能够通过经验认知获得,但“德性所知”是需要向内澄澈的,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止于闻见之狭”,所以对“德性所知”的强调显得更加迫切。对于如何践行和澄澈“德性所知”,张载将其落之于实践:“万物皆备于我”,张载将人的主体性凸显出来,人“心”可以通过“反身而诚”的工夫,与“太虚”本体契合,于是所作所为皆能从其心之“诚”,达至“乐”境[1]33。“心”之挺立正是依赖于道德本体之挺立。“心”与“太虚”的连结点即“诚”,张载的思想中对这种“反身而诚”的实践工夫有诸多诠释。“反身而诚”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
可见,“万物取足于太虚”,至一、至实的“太虚”是世间万物的本原,人也包含在世间万物之内。但人之所以在自然宇宙生化中最突出,最灵于万物,就在于其道德性。而人类道德之“诚”恰恰是蕴含于“太虚”之中的。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道德性,这是一种有着主体与天地参的理想走向。张载正是通过对“天”“道”“性”“心”的构建,并通过对“心”之道德本体“太虚”之“诚”的开显,将“太虚者天之实也”和“太虚者心之实也”连结,贯通天道与人道。当“合性与知觉”在天人一贯的体系中贯通,当人可以自觉践行道德主体性时,人之向上的道德追求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五、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历史定位
张载的心性论思想是有创见的,他提出的“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把心与知觉区分开,并在“性”与“知觉”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结构。而这一动态结构又是张载思想中“天”“道”“性”“心”动态一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心性论思想不仅契合其天人一贯的体系,而且接续先秦心性论思想中的超越性和一贯性,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用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随后的宋明理学中,心性论思想的发展正因为沿着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和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的不同,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从这一点看,张载的心性论思想具有非常深远的思想史意义。由此可见,朱熹以格物穷理的顺取之路解读张载的“合性与知觉”和牟宗三以逆觉体征之路解读张载的“合性与知觉”都因未证得张载心性思想之全貌而有其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