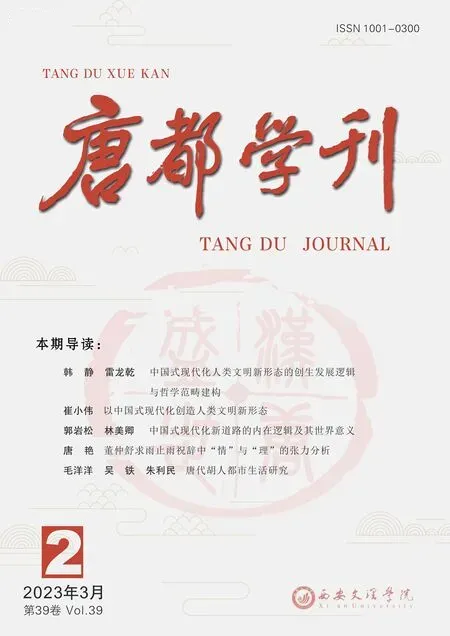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古代文论界在总结中国传统批评方法时,都无一例外地视“鉴赏感悟”法为其中最突出一种,这在不同教程和著作中均有反映(1)如蔡庚生主编《文学评论与鉴赏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方法”中总结为品第、感悟、评点、索引共计四种;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4页中,纳入“品第”批评中;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300页中,则将之纳入“印象传达和经验描述”中。。诚然,重视整体性的直觉印象、传达个人鲜明的审美感受和体悟,这是我国文学批评突出的民族特色,也是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所决定的。这在唐至清各个朝代的文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然而此方法真正发端并初步成熟,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先秦时期文学处于萌芽状态,文学尚未独立,批评话语依附在文史哲著作中,批评方法也处于寄生状态;两汉时期文学批评开始逐步弥漫,文论家将批评纳入经学的范围,被捆上“教化”的“战车”,无从全面发现文学的美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的审美意识空前觉醒,才真正在批评实践活动中广泛运用鉴赏感悟法,从而使文体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和难得的艺术美感。批评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我们透过批评文体,均可领略一斑。
批评是鉴赏的提高和升华。任何批评家必须首先是善于感受和品鉴作品的高明读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批评家必须有较强的艺术修养,具备过硬的艺术功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1]克罗齐《美学原理》也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平。”托尔斯泰则说:“要进行批评,可得把自己提高到理解被批评的作品之上。”这些至理感言,都揭示出批评家必须在感受、鉴别、判断、传达和创造诸方面富有功力,而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得到相当多批评家的普遍认同。如曹植就认为批评家必须首先擅长创作,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善于艺术感受方可评价作品(2)参见曹植《与杨德祖书》曰:“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就魏晋南北朝而言,鉴赏感悟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艺术感悟、审美体验与批评传达等方面。
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各种文论范畴、术语的提出,是基于批评家个人独特感受和领悟后的概括与提炼。这一时段批评家在批评时通常不从具体的分析和概括入手,而是偏重于主观的体会和含蓄蕴藉的表达,不是偏重于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是侧重于直觉的领会和体验,不是条分缕析地论证,而往往借助于形象的比喻。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力并非玄妙难测,而是“在人们的五官感觉上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审美感觉,更准确地说是在审美过程中对审美对象的感知、想象、知解等多种感觉的基础上综合而形成的审美经验的特殊能力。通常又称审美感受力,或审美鉴赏力。”[2]277-278批评家须具有相当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普列汉诺夫说:“只有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同极为发达的审美感觉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可以做艺术品的优秀批评家。”[3]可见,其“敏锐发达”之要求,说明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力必须远超普通读者之上,这是从事鉴赏批评、发现作品内涵的首要条件和必备前提。
(一)审美感受的类型方式
批评家运用此法是由整体直觉思维所决定的,通常采用主观的、直觉的、整体的、印象式的方式来获得对作品直接的认知。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处“思无邪”即是对《诗》三百全部作品整体的、综合的印象和感受,包括其思想内容、情感表达和语言音调等。此外,季札观乐时对《诗》中各部分的评价也是整体、主观性的印象。这种艺术感受方式在文学早期发展阶段广泛运用,尚与人们对文学性质、各种组成因素的认识程度有关。
但在秦汉之后这种批评方式逐渐蔓延开来,并渗透进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就值得思考了。若从渊源来说,它与古人最初整体性地、泛联系性地认识世界有关,也与中国古代以象观意、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分不开。并且从根本来说,这和艺术——不仅文学,而且任何其余类别——的美学特征及人们对美的认识、接受方式有关。艺术之美充满感性色彩,是需要读者发挥直觉去感受和领略的,需要热情、想象去身临其境地体验并拥抱,而非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肢解。具体就魏晋南北朝批评来说,批评家们往往很直接地道出许多作品的整体印象和直观感受。
1.直觉性
先秦时期孔门诗教之悟、老庄以“玄览”和“神遇”等论人与自然及社会之关系,都是直觉体认的认知方式。魏晋批评家常以敏锐的直觉来赏诗,陆云在书信中评析其兄诗作时曰:“云再拜:《祠堂赞》甚已尽美,不与昔同。既此不容多说。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见《吊少明》殊复胜前。《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汉功臣颂》甚美。恐《吊蔡君》故当为最。使云作文,好恶为当,又可成耳。”[4]67陆云完全凭借自身对陆机作品直接的艺术感受来进行评析,至于《吊少明》在哪些方面“殊复胜前”、《吊蔡君》为何“清妙不可言”、《汉功臣颂》“甚美”在何处。恐《吊蔡君》为何“故当为最”等等,都是批评家没有言也不会去言的,他只是道出自己阅读作品的最鲜明印象罢了,所论自然带有很大的直觉色彩。这在魏晋南北朝诗人、作家型批评家那里格外常见。
2.整体性
魏晋南北朝批评家传达艺术感受时绝不将作品肢解,不从作品的局部、细节上来把握,而表现为注重自然和谐,习惯整体赏玩和系统品味。表面看似乎省略了推论的过程和步骤,也不是由单一的语句、结构、思想、情感等总结而来,实则是直接的、整体的印象传达。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论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怯言其志。”[5]67阮籍诗给钟嵘的整体感受在于,它使人忘却胸中的龌龊和鄙吝,达到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境界,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是基于阮籍全部诗文的整体印象。此外,江佑诗歌的清秀圆润,其弟江祀诗歌的明媚华美,以及范缜等人的流畅明朗等,都是对不可分解的诗歌风格之欣赏。我们认为,正是直觉感受式的评析,才使中国文论许多范畴、命题、术语等因朦胧、模糊而具有多义性和丰富性。
3.模糊性
由于整体性地直觉感受注重质的把握而不做量的分析,对事物的描述不求精确明晰,不可避免地带有朦胧的色彩,使风格或范畴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这在擅长运用“设象喻理”,追求“神似”的批评家那里尤为明显,依靠意象的暗示来传达笼统的感觉。如曹丕以“气”论文,但“气”之所指为何,需据语境而定;而刘勰以“风骨”评文,也看似都运用了具象,然而其含义极其模糊(3)参见汪涌豪《风骨的意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无一定论。
(二)语言感受力的表现形态
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力必然首先从批评文本的语言入手。文学作品的语言讲究音乐美、情感美和结构美,以含蓄蕴藉和意味幽深见长,这尤其需要批评主体有良好的语感,包括对语言形式美、风格美、情感美、结构美、思想美等的敏锐感受和独特体验。
首先看形式美。就魏晋南北朝而言,批评家对语言的文采与质朴、对词语的选择、对秀句警句的运用等都十分敏感,批评时往往率先关注语言的形式美感。如钟嵘在《诗品》中论曰:“(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谢灵运诗)……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5]53钟嵘以极其欣赏的口吻感受出陆机诗文辞藻的宏富与华美,其表达的情致和色彩的描绘等都别具一格。他对谢灵运诗歌的名篇佳句和新辞丽句的感受也是十分到位的,谓其“学多才博,寓目辄书”,传达得也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此外对颜延之诗“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句一字,皆致意焉”的感受,对孝武诗“彫文织彩,过为精密”,对张翰、潘尼诗“虽不具美,而文彩高丽”的感受等,都堪称从形式入手感受诗作的典范。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也谈道:“……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简约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4]41也是从语言形式角度来感受扬雄、班固之辞赋作品的。他们的批评文字都显示出极强的形式感受力。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空前兴盛,名篇杰作层出不穷,秀句与警句的大量涌现直接导致“摘句”批评的产生。
批评家欣赏诗文中的秀句蔚然成风,他们从语言形式入手感受诗作也就毫不奇怪。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批评家以审美的眼光品玩、欣赏文学语言,其艺术感受力较之两汉批评家无疑是空前的进步与飞跃。
次看风格美。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对不同辞赋家与诗人的风格评析都是由感受入手的。如《诗品》中:“(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5]37“(刘琨诗)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5]87“(曹操诗)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5]131“(阮瑀、欧阳建等诗)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嵇微优矣。”[5]135钟嵘对古诗、李陵诗、刘琨诗、袁宏诗、曹操诗、阮瑀诗等之风格的归纳概括——如“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文多凄怆”“自有清拔之气”“鲜明紧健”“古直”“平典”等——都是一种整体性的感受,并没有详细分析是诗文的哪些因素导致这种风格的形成,也并不从作品的结构、形式、韵律及情感等方面入手寻找依据。这种整体性的印象概括是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的拿手绝活儿,它使批评文体少了些许的理性和分析,多了几分因整体印象而形成的朦胧之美和诗意气息。
再看音乐美与结构美。诗最初与乐、舞合为一家,古代文人写诗作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讲究韵律和节奏,注重结构、布局和剪裁等,视作品为活的有机生命体。批评家对音乐美和结构美的感受也是十分细腻的,如钟嵘《诗品》:“(张协诗)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才。词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5]59-60又如《颜氏家训·文章》:“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避讳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体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4]514显然钟嵘以比较法评论张协诗,是综合了形式美(词彩葱蒨、靡于太冲)、音乐美(音韵铿锵)和风格美(风流调达、文体华净)等多种艺术感受的。而颜之推同样地在对比中强烈感受出古今文章的不同,他综合感受了结构美(章句偶对)、形式美(缉缀疏朴,未为密致)和音乐美(音律谐靡、今之辞调)。应该说,批评家无论是对具体诗作还是时代文风的感受,都是十分到位的,从而为其精准的评析和自信的判断奠定了基础。
注重直观感受和切身体悟的批评方式经由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批评实践后,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批评家极力捕捉作品并通过其呈现因素所暗示出来的内在风神和整体韵味,发现诗文中朦胧飘忽的多层次情绪氛围和复杂意义,促使了后世“熟参”“妙悟”“韵味之至”等感受理论的产生,并使“意境”说在唐宋后不断得到升华。
我们认为,唐以后批评家对作品言外之意及多重韵味的感受和发现,对作品兴象风神、体格声调的开掘和探索,对作品直观印象和整体形貌的感受、体悟,对文本内在情趣、韵味的直接领会、把握和重视等,都是承续魏晋南北朝而来。
二、精准的审美判断力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审美判断力是指批评主体根据一定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对批评对象进行的价值评价之能力,它要求主体按照美的规律去对作品给予比较准确与客观的评价和鉴定,对作品在艺术或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所形成的特色及相应的地位及价值等进行客观的估价、评定与辨析。批评家必须具有鉴别和判断作品好坏、优劣、美丑、真伪的识见和能力,作为主体从事批评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古今中外文论家对此早有认识。
批评家的审美鉴别力和判断力通常体现在美感价值、认识价值和思想教育价值等几个层面。其中,对美感价值的感受、识别与评析是衡量其美感价值判断力的是核心维度。它要求批评家对作品艺术创造所达到的审美高度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程度进行判断。“美感判断力也就是判断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特点如何、魅力大小的能力。”[2]280结合中国传统文论发展研究的脉络及自身的民族特色来看,就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批评家的美感价值判断力可依次从滋味辨别力、对美学风格的品辨力、对作家作品性质内涵的辨别力来全面体现。
先看鉴别作品之“味”,体味文本的言外之意。中国文艺与“味”结缘历史悠久,唐宋以后不断讲究韵味、诗味、神韵等,而追溯其前则魏晋南北朝的钟嵘首倡“滋味”说,他就是凭借自身超人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品味力来品评中国上古历代五言诗之“滋味”。
在钟嵘明确提出“滋味”说之前,刘勰《文心雕龙》中已开始广泛地使用“味”字,明确地指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总术》中的“义味腾跃”、《附会》中的“道味相附”“统绪失宗,辞味必乱”,又如“余味”“遗味”“滋味”“深味”等,更是运用得非常普遍[7]264-265。并且,刘勰有时还用“玩”字来代替“味”(4)如《辨骚》篇中有“玩华不坠其实”、《熔裁》篇“虽玩其采,不倍领袖”、《知音》篇“书亦国华,玩绎方美”中的“玩”皆如是。,即对作品内涵的反复欣赏与品玩。无论是味还是玩,都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开始非常重视对作品外在文采及内在思想情感韵味的领悟和体悟,而他们的批评实践与其理论主张是相一致的,通观其批评著作,投入主体情感,细细辨析作品之味,是其批评的重要切入点。这充分表现在《诗品》之中:
(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5]33
(班婕妤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5]39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5]41
(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5]45
(陶潜诗)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5]97
5.2 观察出血与渗血 为防止膈神经移位术后伤口内积血引起感染和神经粘连而影响手术效果,通常放置负压引流。要观察引流液的色、质、量。如有异常及时通知医生处理。
类似以“味”品诗——而非两汉以政教和宗经论诗——的例子在《诗品》中随处可见,钟嵘评论诗人诗作充分立足于自己阅读文本时的最强烈和最鲜明感受,以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心动、产生阅读的陶冶与快感、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情感为基点。并且,我们从其言辞间可以看出他在进行“品味”时的那种思维和心灵的活跃状态,“一字千金!”“嗟乎!”这些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词语是味诗必然的接受反映。并且钟嵘在《诗品序》中极力反对过度用典和声律,推崇“自然英旨”,其味诗论与这一创作论相联系。钟嵘强调“吟咏情性”,诗作应自然而发,那么“对诗歌的欣赏自不必一字一句地推敲辨析,而只需反复诵读,深入体味,整体地、直观地加以把握”[7]266。当代学者刘明今曾从著述宗旨、文体形态等特征入手对《文心雕龙》与《诗品》进行了比较,发现钟嵘和刘勰在批评时都是“味”诗的高手,只不过前者品定优劣,据个人艺术旨趣,深入体味不同诗作之味,体现得更为突出和鲜明;而后者擅长“辨析章句”“考订格式”等,但仍以“味”诗为基础。
我们除了从批评文体中,可直接看出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以“味”品诗的审美判断外,还可从批评行文中看出他们对这种“味”诗法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实践。
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云:“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4]512意即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治国安邦,其“陶冶性灵,从容讽谏”是有滋味的,而品赏其中滋味,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他在评萧懿“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云:“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即是对萧作之“味”的涵泳品玩。这种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批评感受的抒发、批评情感的投入、批评作品的激赏等,都可以见出作品之“味”对批评家强烈的吸引力。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云:“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文隐深蔚,馀味曲包”;《情采》篇云“繁采寡情,味之必厌”。钟嵘《诗品》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5]11等等,都强调了对诗文之味的把玩和品悟。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云:“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可见谢灵运转向自然山水在于竭力追求平淡自然之风,其在赋体内容、表现方法和审美追求上的创新都力图使读者领悟作品的言外之意,从中获取微妙的意趣。而身兼作家和批评家的谢灵运也是这样实践的。钟嵘在《诗品》中同样表示出对作品之味,对文本言外之意的评析:“(宋光禄谢庄)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于王、袁,然兴属间长,良无鄙促也。”[5]154云“兴属间长”即表示对谢庄之诗言外之意的欣赏。可见,不论是刘勰、钟嵘还是谢灵运、颜之推,都在批评活动中践行其“味”诗观,将对诗味的辨析作为判定作品成就大小与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尺。
再看对“风格”的辨析和判定。诸如文体风格、作品风格、作家风格乃至时代风格等,魏晋南北朝批评家无不以其精准的鉴别作出准确的判定。如文体风格的辨析与判断一直为诸多批评家所关注,并在阐发与区分中不断走向明确和细密。如曹丕关于“四科八体”的划分首开魏晋文体批评的先河:“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4]14紧承其后陆机对文体的分类和相应的特征辨析概括得更为精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4]58显然,在建安年间曹丕凭借长期的阅读积累、创作实践及交友磨砺,以简洁的一字高度概括书论、诗赋等的整体特征,是极富批评眼光的。然而至陆机“诗缘情而绮靡”,则不仅分而论之,而且同时概括了诗抒情的内容(“缘情”)和美丽生动的言辞(“绮靡”)两个方面,相比曹丕提得更为全面和具体。这里笔者无意于区分二者审美判断力的高下,只是借此观管窥豹、洞幽烛微,对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的审美鉴别力有所领略。
又如对作家风格的判断和辨析。傅玄在《连珠》序中判断曰:“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宏利,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4]38四名作家均创作连珠体,然而批评家以比较和概括的方式将个中的特征、差异、优势及缺陷等辨析得一清二楚、一目了然,不能不佩服批评家高超的鉴别力。钟嵘在《诗品》中曰:“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5]144钟嵘将王济、孙绰、许询等人的风格特征(“贵道家之言”“善恬淡之词”)置入时代激变(“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爰洎江表,玄风尚备”)中审视,形成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的互动,也概括得较为准确、客观。而这是建立在长期把玩作品基础之上的。
再如对作品风格的判断。陆机在《遂志赋序》中简洁精当地评析了前人题材相近的赋作特征:“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陆机凭借自己的细心揣摩,并结合各自的身世性格等,精准地概括出张衡、蔡邕、张叔、班固四人四篇作品的显著特征,其审美鉴别判断力着实令人叹服。类似这样对具体文本的判定和概括、对比和辨析在魏晋南北朝批评家那里,完全变成了显微镜下的绝活儿,他们似乎融入了文本内部,进得书中,又出得书外,一切游刃有余。又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有论:“《幽通》精之整,《思玄》傅而赡,《玄表》拟之而不及。”[4]93批评家以“精”与“整”、“傅”与“瞻”、“拟之而不及”数字就对三篇作品进行了审美评析和价值定位,委实高明。
最后看对作家艺术成就、个性特征的发现和评析。魏晋南北朝批评家不仅对诗味、风格的判断与辨析十分敏感,而且对具体作家创作的独特性、艺术手法的性质定位等方面的把握也是十分高明的。如钟嵘《诗品》中论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5]39论左思诗:“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喻之致。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5]61钟嵘概括班婕妤“辞旨清捷,怨深文绮”,评析左思“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对二人创作个性及诗作风格作出了简练的审美鉴定。并且论左思时,不仅兼评其思想之美(“得讽喻之致”),而且在品第比较法中对左思诗文的整体性质与成就进行了定位:“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这样,钟嵘多侧面、多角度、多方法地对左思进行了判定,使批评显得立体化。同时,批评家对同一作家不同阶段的作品以及不同作家的相似作品等,也进行了鉴别和判断。除上文陆机对班固、蔡邕之赋的评析外,再看刘逵《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相如《子赋》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4]84显然,这是刘逵对汉代三名杰出赋家之作夸张失实之弊的批驳。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对作家作品不足、缺陷的判断固然都依照各自心目中的文学观,然而其对审美价值的判定还是较为公允和传神的。批评家充分肯定在他看来值得称赞和弘扬的成就,同时绝不容忍世俗眼光对杰作的低估和打压,绝不回避对作品自身所存在问题的揭露与剖析。如钟嵘《诗品》对张华创作的成就与特色进行了高度肯定(“其体华艳,……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尽管其声名甚高,但还是指出了其不足(“兴托不奇”“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批评家毫不客气地将之列入中品。而对于陶渊明判定其风格“文体省静,殆无长语”,尽管“世叹其质直”,然而钟嵘凭借自身的慧眼与发现,激赏其诗文,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竭力为之翻案。
可见,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对作家作品、风格特征、创作成就、作品价值等进行鉴定、辨析、判断时,是有着自身独特眼光和标准的,尽管少数地方遭后人非议(5)如后人质疑钟嵘列曹丕为下品,列陶渊明、陆机为中品等。这与南朝时期批评家的审美取向有关,不宜以今人眼光和标准来苛责钟嵘、刘勰等人。,但整体来看所下断语是较为公允、客观的,大体符合实际。
三、高超的批评传达力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批评家的敏锐感受力和精准判断力最终须转化为批评语言,以文体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批评家根据对象的特点并结合自身的批评动机与心理特征,采用相应的语言形式,将主体的感受、评价、鉴定等落实为批评文字的过程,谓之批评传达,它是批评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批评语言的运用、批评话语的营造、批评方法的调度以及批评体系的建构紧密相关。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开创性和深广度都是学界公认的,其批评文体的诗性特征,无论是骈赋体的美轮美奂,还是专著论文体的气势磅礴,抑或是表达方式的灵活多变,话语面貌的优美灵动,都逐渐为人所瞩目,并且这个时段批评文体是中国古代融诗性与谨严于一炉最为成熟也最为显赫的(6)当然若仔细分析中国任何一个时段的批评文体,都不乏诗性的灵动,方法的多变,或语言的优美,或体系的磅礴,但或者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者只是如湖面荡漾的波纹,毕竟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段那样成气候并具有开创性。。批评文体的文学性得益于批评家高超的批评传达力。这里选取批评家的艺术想象与符号转化、批评意境的营造等维度稍作透视。
(一)符号转换和艺术想象
批评家须具有很强的艺术推想力,即“通过体味作品的语言内涵,把语言符号转换或创造出新的体系及创作心理过程的推想能力”[2]278。这要求批评家必须要把文学语言描绘的形象还原或再度呈现出来,这是进入欣赏和批评的必备阶段。并且这种创造性想象不仅是形象的再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
身兼诗人、辞赋家的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积极活跃于文学舞台,广泛参与各种文学实践活动(含评论和创作),其批评文体从广义来讲是著书立言、进行创作的一种(7)这与该时段批评家的批评自觉并不矛盾,而其批评文体视为批评创造固然无争议。,因此批评家进行符号转换和艺术想象的能力相当发达。且看陆机《文赋》对极为抽象朦胧的构思过程所进行的形象化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4]57-58当构思活动开始时,平时书本或生活中积累的各种物象就纷至沓来,大脑思维处于高度活跃状态,批评家陆机如何把这种心物交融的微妙状态传达出来呢?他如何把自己多年创作过程中的这种深切体验变成读者可以感知的批评文字呢?创作时穷极宇宙、奔腾不定的想象力神通广大,主体对辞藻的选取、对形象的酝酿以及表达中的斟酌、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等等必然充满着痛苦、焦虑、比较甚至多次地反复,这个微妙的抽象过程似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对其把握是极富难度和挑战性的。然而陆机高超的艺术想象力——诸如以游鱼吞钩、飞鸟中箭、高空落地、辞别朝花、启开晚蕾等意象来形象描述——使其传达不仅形象而且生动,成为批评传达的神韵之笔。
且不说陆机开阔的发散思维,单是以依枝布叶、顺水寻源、虎起龙飞、树立叶满等想象就将以文传意、辞随意动的过程描述得栩栩如生,传达得入木三分。从陆机以多种形象来传达构思、布局、遣词等全部过程来看,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定善于将生活中所观察和体验乃至平时积累到的各种物象进行灵活的调度,善于天衣无缝、游刃有余地将之运用到批评实践活动中来。
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符号转化与艺术想象方面的开创,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明清历朝各代,也不乏富于奇特想象的批评家和擅长以丰富意象来进行批评传达的神来之笔。如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全部以具象和情景来展示二十四种诗歌意境(或与人格形象等),其想象之丰富与神奇,令人嗟叹。同样的,唐代皇甫谧的《谕业》篇论文[6]176,通篇采用意象,其想象之博之广已超过了袁昂《古今书评》之品评书法诗文者。意象批评在中晚唐时期已经趋于成熟,成为传统艺术批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宋代敖陶孙之《器之诗话》评论曹操等29位历代著名诗人,其独特比喻几乎成了意象的恢宏展览[8]15,将古代批评家的神奇想象推向极致。
然而,隋唐以后批评家以意象论文,在批评文体中自由展示想象的才华,除受自古以来“赋比兴”传统的孕育外,也多少受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寓想象于批评之中的启发与影响,或者说是承袭此阶段的批评方式而来,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魏晋南北朝文论家所显示出的高超批评传达力在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相比先秦两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与创造,相比后世则是一次批评方法的酝酿和哺育。
(二)“批评意境”的营造
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的高超传达力同时也表现在“批评意境”的创造上。竭力营造文学意境是无数作家创作的最高追求,是否具有意境之美因此成为衡量作品艺术价值高低与成就大小的重要尺度。而对于文学批评,同样也存着批评价值大小与批评美感强弱的问题,为何读者在欣赏大师的经典文本时所引发的审美感受、获得的认识水平、产生的联想思索等与寻常批评文本迥然有别?这与批评家是否精心营造“批评意境”有关。
何谓“批评意境”?从现代文艺学角度来看,它是“作品的意境、时代的背景和评论者的深刻感受这三者的有机结合的统一体”(8)参见阎纲《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61页;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284-285页,论及“批评意境”和批评家的“创造力”问题。。简易来说,真正杰出的批评必然同时融合了三个方面构筑起批评的立体空间而不是单向度的议论:一是对作品形象、思想、情感等深层蕴含的深入阐发;二是传统的“知人论世”,同时联系作家经历、情感、遭遇及社会环境、时代氛围等语境,真实地进入作家的创作语境而非剪断作品和主体、社会的“脐带”,以隔靴搔痒或纸上谈兵;三是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方可对作品发表与众不同的批评意见,从而形成独特的“这一个”。可见,批评意境紧密联系了作品—作家—社会—批评家四个维度。它是一种很高的艺术追求和批评志趣。而通常的批评并不要求对作家作品及时代社会全面涉及,但只要考虑到其中的二者,就堪称批评的经典。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竭力营造的批评意境,堪称后世之楷模,这才使其批评文体十分耐读,极富魅力。
如一代隐逸诗人陶渊明之地位在东晋南北朝虽然并不十分显赫,在刘勰、钟嵘、萧统、阳休之等众多批评家笔下,所论不一。且看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之评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哀。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4]471萧统突破常规地发现陶渊明诗文以酒寄托情怀,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深切理解其作品的内涵,并结合作者的生活处境(“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4]471)对其作品做出了公允、客观的解释,可谓知音之谈。同时直率地道出了批评家自身直观的印象和强烈的整体感受(“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4]471)。虽然所言“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并不尽然,却丝毫不影响这段批评文字所创生的批评意境,读来十分深刻。萧统不愧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读懂陶渊明诗作的杰出批评家,其选文和编集的眼光极为特别。
颜延之《五君咏》“对竹林七贤中五位作家的遭遇、处世、识鉴、风标、怀抱、情怀、辞章等进行了画龙点睛的品评”[4]183。他在以组诗来评论阮籍、嵇康、刘伶等诗人诗作,以寄托自己的悲愤情怀,他将所评人物放置到特定的生产环境中,并联系其遭际和性情来全方位地透视作家主体的心灵世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批评意境”。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诗作及序言[4]198-205,也同样创造了批评的意境。他在仿作中折射出自己的强烈感受和主观印象,体悟出不同作家的风格特征,揭示出各自的成就,其对作家风格的概括如论嵇康的“言志”、论阮籍的“咏怀”、论陆机的“羁宦”、论左思的“咏史”、论刘琨的“伤乱”等等,都是非常精准的评论。其以拟作揭示前代作家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表现出作者、批评家的识见,这在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自成一格。
(三)批评话语方式的折中性与灵活性
批评家所使用的语言表述也必须有利于传达主观感受和审美判断。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特别善于使用折中词来表达其思想,经常采用“A而B”或“C而不D”的话语模式。如傅玄在《连珠序》中论道:“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4]38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谈论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学观时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则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4]468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认为“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4]480批评家联通两个相反的方面,试图在A与B两极之间对诗人诗作作出鉴定和品评,比较中允地进行了定位,这种批评传达方式为魏晋众多批评家所钟爱。陆机在《遂志赋序》中评赋曰:“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4]62刘勰《辨骚》篇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4]284他们均以“而”字连接两者,既对作品风格进行整体性概括,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类似这种评论表述在魏晋文论中比比皆是。批评家试图调和矛盾或对立双方使之趋同,“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不可偏废”[9]。而这种批评方式运用得最娴熟者乃为集大成之刘勰,其《文心雕龙》中使用大量转折性连词而将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有机联系起来,诸如: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宗经》)
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
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熔裁》)
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
由此可见,刘勰论文时往往兼顾事物的两面而竭力避免片面性,他深谙文学批评通过参合、调剂而达到辩证、统一之道。学界曾分析过他对奇与正、华与实的论述,可供参考。刘勰评价《离骚》“熔铸经意”“自铸伟辞”,根据屈骚之特点并鉴于后人仿作之偏颇,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即作家在酌取新奇时不要失掉雅正,在修饰文辞时不要忽略内容,要求“奇”与“正”、“华”与“实”必须同时兼顾、不能偏废。因此,刘勰提出必须“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如果单纯偏爱一面,则势必“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
四、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文体的诗性品味之生成
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对作家作品敏锐的感受力、精准的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是探秘这一阶段鉴赏感悟批评方法的三个重要方面。而这些能力与方法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是在长期批评实践中逐步得到提升的。我们看来,这既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批评家的胆识和勇气,也与当时活跃的文坛氛围有关,更离不开批评家综合调度并灵活运用各种批评方法。清代文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提出“才、胆、识、力”作为创作主体结构的必备要素,这对于批评领域同样适用。其中的“识”即指识别、鉴定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主导着批评家判断的胆力和传达的才力等。在批评实践活动中,批评家对文坛新人之“识”,对写作风貌的“识”,对别一种艺术手法之“识”,对作品风格、价值及缺陷之“识”,对作家成就、地位及创新程度之“识”等,需一双慧眼。
魏晋南北朝批评家不仅有钟嵘、萧统那样的“识”,也有曹丕、裴子野那样的“胆”,更有陆机、刘勰那样批评传达的“才”与“力”。就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批评家发展之全面,在才、胆、识、力诸多方面可谓人才辈出,不仅有将领更有帅才,共同将中国文论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为何擅长此种批评?其成因何在?他们为何有如此高超的感受力、判断力和传达力?为何青睐并擅长鉴赏感悟式的批评方法?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与批评家在时代转型中眼光由教化、宗经向全面审美、品鉴转变有关。两汉批评家是以思想教育价值居上的,对文学现象的审美打量远退其次。而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更是审美全面走向自由的时代,是品鉴热情空前高涨的时代,无论是早期人物品藻中对个体性情、气质、个性、风貌的品评,还是后期对山水、田园等自然景观的欣赏、赞誉,都开发了士人的感受力,增强了其审美评判力。
其二,这与批评家往往同时兼为作家的双重身份有关。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各自的创作领域或者各领风骚,或者自成一格,如被评为“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曹植和诗风“古直”的曹丕,都是建安时期著名诗人,是当时文坛的领袖,是推动文学发展的组织者与号召者;而陆机的创作更是全面开花,辞赋、诗歌、各类公文等无不擅长,可谓“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在西晋名冠一时;即便是被章学诚誉为评论“专家”的刘勰和钟嵘也是双体并作的。而左思、沈约、徐陵等更是直接在序跋中以总结创作感受和经验的形式进行文学批评,而以诗歌体摹拟诗人风格并进行相关评论的沈约、颜延之、江淹等更是沟通创作和批评桥梁的使者;即便是史家萧子显、裴子野等也是擅长子书与史书写作的高手。总之,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的兼职性与两栖性打破了身份带来的壁垒,作家型批评家纷纷发挥创作时对外界自然景物的敏锐感受力和奇异想象力,纷纷畅谈他们在学习和借鉴前人或时人作品的体会和感悟,纷纷采用他们在阅读经典描摹作品时的典故事例等,从而使他们的批评不仅理论深刻,而且文体优美,富有浓郁的文学气息,读来赏心悦目,如饮醇酒。
其三,这还与批评家大量的阅读体验以及在实践活动中的艰辛积累与长期储备有关。批评家的评析力与创造力是自身素质的某种反映,更是带领读者走近作家的“引擎机”,是引导读者体悟作品深层蕴涵的“指南针”。建安曹家和南朝萧家皇室以其独尊的地位,引领了当时相当一批诗人型批评家,或者相互评论,或者彼此借鉴(切磋),或者写信商讨,或者共同选文……这些批评实践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批评主体的品评热情,对形成其批评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这一切,发生在创作觉醒、文坛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是难能可贵的,而秦汉与之相比,远没有这样的氛围,因此那时的批评自然显得单薄得多。设想如果没有树立徐干著《中论》那样不朽的志向,没有作为邺下文坛集团盟主的身份,没有与众多诗人辞赋家进行互评的资历,曹丕不可能写出《典论·论文》,也无法对建安七子逐一展开准确客观的评论;没有长期研读,分析不同诗作赋作的准备,没有对写作过程细腻的体会和打通创作与批评界域的本领,陆机的《文赋》不可能以如此奇特的想象来描述构思、剪裁、布局等全部的微妙过程;没有孤灯下览卷苦读数十年,没有对中国上古文、史、哲作品不断的揣摩和品味,就不可能成就一代巨著《文心雕龙》;没有对数千年诗歌发展史的了如指掌和众多诗人作品的精读,就没有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序》……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的感受力、判断力和传达力,既是每位批评家充分发挥各自优长的智慧结晶,更是他们在批评实践活动中磨砺和提高的必然结果。
魏晋南北朝采用此种批评方法对营造独特文体产生了哪些多元影响呢?这值得探究。鉴赏感悟型批评方法使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具有诗意的美感,充满浓郁的文学色彩,实现了创作与批评的融通和渗透。它融入思辨性和体系性批评中,与之共同构成中国文论的“双翼”。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方式开创了中国后世文论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在文体的体式方面不拘一格,随“体”拈来——体之性不同,则配合之法有异,有些批评文体特别适合鉴赏感悟法,如书信体、序跋体等;在文体结构方面随“性”适“意”,在文体语言的运用上极力讲究文采斐然。总之,使文体显示出很强的艺术性。
鉴赏感悟型批评方法使文体结构显示出简洁、凝练之美。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文体固然不乏“体大虑周”“思深意远”之煌煌巨制,诸如《抱朴子》《文章流别集、志、论》《文心雕龙》《诗品》和《文选》等一批专著体或子书体偏重于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而诸如序跋、书信、诗话体、赋体、论诗诗体等体式,更多地以鉴赏感悟方法写就,身兼作家或史学家的批评家,在文集之前或友朋往来或寄托哀思之间,直接写下创作的体验与感受,直接表达对作品的看法与意见,从而使批评文体简短而不冗长,用语凝练传神而不拖衣带水。或者一段话(阳休之《陶渊明集序》、陶渊明《闲情赋序》、颜延之《庭诰》、沈约《七贤论》、张融《戒子书》等),或者一首诗(沈约《伤王融》《伤谢朓》等),或者寥寥数行数语(荀勖的《文章叙录》、任昉《文章始》等),最长也不过一两千来字(如张融《门律自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裴子野《雕虫论》等),就表达出对作家作品的批评看法。批评家随性自然地谈创作、品作家、论文章,无意于建构宏富的理论体系,只需在简短的篇幅里概括作家的风貌、点出作品的滋味。虽然当今学者常拿西方式的批评文体来反观传统文论,认为“零散杂乱”“只言片语”是批评文体之弊,实则不然。在我看来,如果换个角度抱着理解而不是苛责的心态来看,这种文体样式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大力弘扬鉴赏感悟型批评方法并广泛运用息息相关。同时,只言片语、片言要句的凝练之美是当今文体无法比拟的,相对而言当今批评文体则日显其弊。我们认为,此种批评方法充分显示出古人驾驭汉字和语言的深厚功力。用形象化与诗意般的语言来传达批评思想,会给读者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
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传达对作家作品整体的感受和印象时,往往采用富有诗意的语言,优美灵动,读来颇富文学美感。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以比喻的方式极赞“风骨”运用带来的阳刚之美:“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段绝妙的批评文字美不胜收,以形象示“风骨”之内涵,就“风”“骨”各自的作用以及与文章的关系做了深刻的探讨与揭示,读来诗意盎然,文采斐然。
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相比两汉要有文采得多,这与批评家喜好形象化思维、擅长调动多种批评方法有关,而这也开启了后世谨严的理论内容常以感性的形式和诗意的语言来表达的优良传统。又如曹植在《前录自序》开篇即云:“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4]27以诗一般的语言道尽自己对优秀之作的整体感受,几乎和优美的创作语言别无二致。而这种诗意化的形象语言在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中比比皆是,极大地缓解了批评理论本身带来的冷静、理性与板滞,赋予文体特有的灵性。读者通常在美文中自然而然地接受批评,诚如刘勰在《知音》篇中所论:“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这既是批评家以鉴赏感悟之法评诗论文的体会,又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在后世读者群中的接受美学效应。
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批评体式众多,传承秦汉以来既有文体,又在论文体、骈体、赋体、诗话体等方面新创,因其浓郁的诗性特征而耐人寻味,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主体”角度入手考察,我们发现这与诸多文论家巧妙而高超地采用“鉴赏感悟”法有关。透过此阶段批评文体,我们能感受批评主体的别具匠心和批评智慧。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的诗性特征和文论家主体的批评方式及素养,都可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一面镜子,为当前文学批评提供重要的启迪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