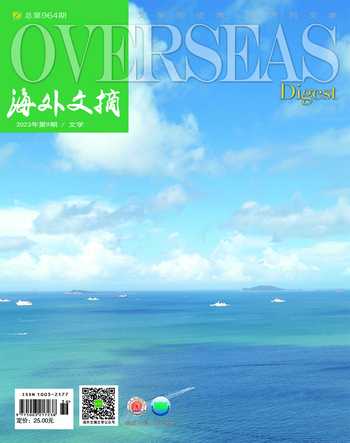樱桃红
李道立
谷雨至,樱桃红。
四月的微雨给榆树岭换了一层花色。油菜花、白菜花,还有桃花,都盛开过了。如今,樱桃红遍了榆岭花乡。
和谷雨一起从枝条的身体里冒出来的樱桃,穿越了静静的春天,颗颗晶莹剔透,滴滴落入湛蓝的乡村。一米多高的樱桃树,绿叶之间,看万盏星宿骤亮,偶尔有果农的一声轻轻咳嗽,“樱桃红了!”瞬间,我感到这姹紫嫣红的幻象被一层一层包围,闪现出一点点嫩绿、鹅黄、淡红、深红,且鲜亮而圆润,带着一抹光,欢快地抖动着微微的风,谁敢说,这不是樱桃的黄金岁月。
山坡与山坡之间,那闪闪的红色精灵,撑开绿色山林,果农更像绿海中的帆,推开春色,流动身影,一声声低空缭绕的回响,来来回回在滚烫的山间、田野、密林之中,像我儿时捉迷藏的岁月快速掠过。一群采摘者,沒有闪光,只有从容而低头的行走,只有行走的岔路。
出县城往北,在龙门的入口处,就是樱桃谷的大门口。在榆岭花乡,最前面的樱桃在荷塘之间,将目光对准一条傲慢的郑万高铁,一带绿谷分娩出整个春天迷人的身体。峡谷幽深,但深不过一片樱桃树的情谊。“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曾经偏处一隅的榆树岭,如今,竟成为南漳万亩樱桃的中心地带,一条日益繁忙的麻竹高速横穿而过。
宽阔平整的樱花大道拉近了山里与外界的距离,一到樱桃季,无论花季,还是桃季,车流不断、人流匆忙,不管忙闲,不管来去,都在证明美丽乡村的爱,都会把春天美好的时光投在这小小的樱桃之上。榆树岭,一带樱桃谷,连同一条腾空而起的高速,一条欲飞欲生的高铁,威风凛凛地守在山口,向过往的人们展示着它的生机与活力。
我家周围遍地是樱桃树,早出晚归,映入眼帘的是随山环绕、连天接地的果树,果木葱茏,花香四溢。在榆树岭,见面都是老乡,虽叫不出名,但都爱打招呼,一声“你好!”笑脸荡漾开来。出榆岭花乡小区,便是樱花大道,村里人大都在道路两边建起了漂亮的楼房。家家户户有山有田有桃园,大部分种植户通过樱桃实现了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随便路过一家,“你家樱桃在哪儿?”便会走出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或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顺手一指:“最红的那片,10 块钱1 人,随便摘。”你便能看见,曾经遥不可及的远山,就在眼前,连同被打理得规整有序的樱桃树,构成了一道道独特的樱桃山。我是在一个周日的上午,阳光初出,小心翼翼地进入一片樱桃林的,一簇簇亮晶晶的樱桃,或迎着朝阳、或垂头避阳、或攀于他树、或藏于沟边,那陷于天地的艳丽霎时把我融化了。摘樱桃不能心急,要一粒一粒地摘、一串一串地摘,还要把蒂带上,否则,摘下的樱桃很快失去光泽。一个小时后,便觉腰酸背痛,力不从心了,但收获却是满满的。晶莹、透亮的樱桃像一颗颗红珍珠,色泽光鲜,粉嫩饱满,令人心情舒畅,转眼忘却劳累。
摘樱桃不如吃樱桃。抓一把樱桃,两指衔蒂,送入口中,轻牙叩齿,轻舌一顶,肉核分离,吐籽另手,再送一粒,再吐一籽,桃肉慢咽,沁入脾脏,它们的去向,更多的时候是到了乡愁的地方。一边吃,一边想儿时的大山,一个孩子与仅有的几把樱桃的过往。小时候,樱桃稀少,父母偶尔从城里购回一两斤,便视若珍宝,而那时,吃樱桃很挠欠(很急),一把一把往嘴里送,来不及吐籽,吃过不少樱桃籽,大人们常开玩笑,来年从肚脐眼里要长出樱桃树来,吓得赶忙跑到茅房里。当然,这所有的源头,都要怪罪于樱桃太诱惑了。
樱桃熟,百果青。
人间四月,樱桃红遍。“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有了白居易的赞美,樱桃更是挠人。樱桃旺季不过两周,四月末,樱桃也熟透了,百果开始悄悄生出青色。枇杷、无花果,就连麦子,也开始慢慢生出青粒。被初夏的阳光渲染,青绿渐渐凸显,青涩的果子给人一种愉悦,越是这种青色,越是让人感觉到一种迫不及待。轻轻地喊一声,樱桃谷的路口就亮了。路边,一排排竹篮摆成一个水果大市场,各家各户置一把大雨伞,伞下果农或吃着早点、或叼支烟、或谈价、或叫卖,一篮里堆满樱桃,一篮里堆满桑葚,新鲜可人,娇嫩欲滴。在任意一亭伞前逗留,便传来一声吆喝:“樱桃,刚摘的——”声音像一篮篮樱桃,实在,饱满。
我目睹的不是樱桃的光鲜,而是光鲜背后的滋味,有时,劳动比生活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