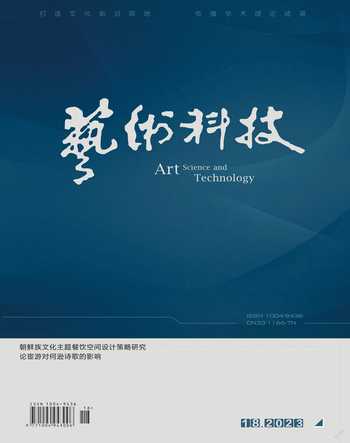回顾与展望:日韩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研究
宋熹瑞 许叶彤
摘要:1937年至194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控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成立,其表面上是一家以股份有限公司模式经营的大型电影公司,经济实力雄厚,经营规模庞大,涉及业务广泛,其中以电影制作为最,8年间完成千余部各语种、各类型电影,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推行侵略与殖民政策的超级宣传机器,对中国及东亚其他各地区人民的荼毒甚深,多国学者理应从多领域、多视角对其进行研究。然而,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相关的影片胶卷与档案文献在日本战败投降前夕被人为销毁,导致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一直徘徊不前,以个案与考证为主,尚未形成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相比之下,由于公司当事人的存在与语言的优势,日本与韩国在研究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呈现出阶段性与多元性的特点,可以为中国学界开展研究提供参考。鉴于此,文章在充分收集日韩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文献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全面细致考察日韩关于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研究成果,总结学术脉络与主要观点,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展望,以期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历史的话语权、解释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关键词: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日本;韩国;电影史
中图分类号:J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8-00-03
0 引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吉林省成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不仅在中国近代影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是了解近代东亚电影史的重要窗口[1]。在中國东北和朝鲜半岛同受日本殖民统治的背景下,“满映”制作的电影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这引起了日本与韩国学界的研究兴趣[2]。日本不仅有许多研究“满映”的论文与书籍[3],还有不少当事人回忆录与相关录像资料。在韩国,“满映”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全景式考察“满映”研究的变迁,综合学术研究、人物证言及文化作品等,对“满映”进行深入研究。
1 电影与帝国:日本的“满映”研究
二战至今,日本学界对“满映”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1 1950年至1972年:“满映”研究起步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对“满映”的研究资料以留用者与日本左翼电影人士的自传、评传、回忆录为主。所谓留用者,是指日本战败后中国共产党收编留用的部分“满映”人员,这些留用者在党的领导下编入改组后的东北电影公司[4]。相关资料有木村庄十二的《新中国》(1953)与《座谈会》(1954)、北川铁夫的《牧之光雄》(1958)、日本共产党人大塚有章的《未完的旅路》(1960—1961)、岩崎昶的《根岸宽一》(1969)。留用人员为中国电影制作提供技术指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共产党人大塚有章,因反对军国主义对外扩张被捕,被强征派到中国东北。1945年,他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尽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义务[5]。不过,部分日本战犯仍未反省“满映”的文化侵略罪行。伪满情报处长武藤富男在《满洲国的断面——甘粕正彦的生涯》(1956)中表达了对“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的哀悼和尊敬。事实上,甘粕正彦在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任“满映”第二任理事长,以“国策”电影推行殖民主义文化,并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殖民统治,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6]。
中日正式建交后,佐藤忠男在《映画史研究》(1972)卷头提出“调查‘满映电影”的呼吁。坪井与《满洲映画协会的回想》(1984)首次对“满映”业务内容、员工动向、作品概要、制作设备等方面进行分析[7]。以此为基础,佐藤忠男出版《电影与炮声》和《满洲映画协会》等专著。
1.2 1972年至1990年:“满映”研究系统化
1980年后,战败后归国的“满映”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回忆录、评传、自传等大量涌现,如小泉吾郎的《我的青春与满映》(1982)、小松泽甫的《持永只仁的足迹》(1985)、女演员李香兰(山口淑子)与藤原作弥合著的《李香兰——我的半生》(1987)[8]。这些书籍介绍了“满映”工作人员的生活经历、工作经历、思想情感等方面,为“满映”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视角。
除了上述文字资料,日本还制作了关于“满映”的影像《映像的证言·满洲映画协会》(日本东海电视台,1992)。该纪录片使用了俄国保存的“满映”胶片,日本学界以此展开了新的研究,制作录像带30卷《映像的证言·满洲的记录》(1994)。山口猛出版胶片图版书籍《“满洲”的记录——满映胶片下的满洲》(1995),《仿书月刊》出版《满洲映画协会特辑》(1998)。至此,日本学界形成了系统化的“满映”研究体系。
1.3 1990年至今:“满映”研究全面化
1990年前后,部分大学开设电影学讲座,“满映”相关文献的复印计划也相继出现。这些计划推动了“满映”研究的发展,并促成了“满映”研究大环境的形成。此阶段,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如影像学、建筑学、女性主义、符号文化研究等逐渐被应用到“满映”研究中。日本学界开始以交叉学科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对“满映”及其留用人员、演员、电影等展开研究。
“满映”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多围绕女演员李香兰(山口淑子)展开。中日混血的李香兰,是早期在好莱坞电影圈中崭露头角的亚洲女性。相关资料有四方田犬彦《日本的女优》(2000)、《李香兰与东亚》(2001),田中益三的《电影信使李香兰》(2000)、李香兰的第三本自传《活出李香兰》(2004)。
21世纪初,日本学界对中国政府留用的“满映”职员展开研究。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中日关系史学会编撰的《对新中国的贡献——用友情描绘战后史的一段》(2003),以及刘文兵的《满洲映画协会“启民映画”中满洲国表象分析》(2010)。
近年来,交叉学科的分析方式拓展了“满映”的研究思路。李敬淑的《关于战时下朝鲜·满洲电影人的越境活动之实证研究——以李台雨、李香兰为中心》(2017),讨论跨区域电影活动的实际情况。李润泽的《从映画杂志〈满洲映画〉中看明星表象》(2020),考察“满映”的明星选拔机制。张少博的《满洲映画再探求:围绕电影音乐中歌词含义》(2022),从歌词意义角度进行电影文本分析。林乐青的《满洲日本统治期建造物的现在:以满洲映画中中国东北地方建造物为中心》(2022),从建筑学角度出发,考察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建筑。竹峰义和的《日本殖民地下满洲与朝鲜制作的映画作品比较研究》(未见刊,2022),以电影制作为切入点,比较分析“满映”的“五族协和”和“内鲜一体”两种不同的制作方式。
2 电影与民族:韩国的“满映”研究
相比之下,韩国学界的“满映”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其研究方向较为多样,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向。
2.1 民族主义视角下的电影殖民
“满映”电影中“建设”和“民族”的概念植根于其所服务的傀儡政权,并成为宣传战略的一部分。韩国学者认为,“满映”电影表现出了韩国民族的伤痕意识形态与民族反抗精神。洪秀京的《“满洲国”思想与满洲映画协会:1937—1945》(2007)、安?洙的《满洲动作电影中模糊的民族主义》(2008)等研究,都探讨了电影所反映的韩国民族反抗意识和伤痛情绪。金大根的《满洲西部电影的话语分析》(2021)通过界定和分析台词和叙事结构,发现“满映”电影中存在“隐匿民族主义”。
2.2 电影管制政策下的“满映”创作
1937年,日本对伪满地区实施电影管制,出台了与电影相关的管制法——《映画法》[9]。目的在于通过拍摄特殊电影,创造“满洲”独立文化,建构所谓的“满洲”想象共同体。李俊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电影管制政策与满映》(2006)和《日帝的电影统制政策与满洲映画协会:以巡回映写为中心》(2008),前者分析以电影为幌子展開驯化中国民众的工作,后者重点介绍实行电影管制后,通过巡回放映活动将殖民观念深入东北偏远地区。姜泰雄的《满洲国故事片的诸相——以满洲映画协会的制作方向变化为中心》(2007),则以“满映”电影的剧情转变为切入点,考察施行管制政策对电影制作的影响。
2.3 作为“国家”宣传工具的“满映”
作为“国家”宣传工具的“满映”,其对伪满政权的作用备受关注。从洪秀京的论文可以看出,伪满政权亟须利用“满映”的“国家”宣传作用,增强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存在性。金丽实的《满洲映画协会的“启民映画”研究》(2013)揭示了“满映”站在所谓的“国家”层面宣传伪满兵役法方面的作用。综合来看,“满映”为伪满政权扮演了重要的“国家”宣传角色。
2.4 以“满映”为中心的日朝文化交流
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亚的控制地区,构建了以“满映”为中心的东亚电影网络,这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东亚电影网络——以满洲映画协会为中心》(李俊植,2007)中有所反映。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范围的扩大,电影网络由东北亚延伸到东南亚,电影宣传的核心也随之转移。金丽实的《满洲电影协会和朝鲜电影》(2011)回顾“满映”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电影交流[10]。
2.5 共产党接收的“满映”工作人员
日本战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满映”的工作人员和设施,1946年改组成东北电影制片厂。李炫贞的《中国共产党的满洲映画协会接收与东北电影制片厂保存的“满洲国”电影遗产》(2018)探讨了1945年至1953年留用人员对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影响。郑冬天的《与满洲电影制作结合的“民族像”——以李香兰和中国之夜为中心》(2022)着重考察“满映”女演员李香兰成为宣传活动主角的历史。
3 日韩“满映”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满映”的研究备受关注。然而,韩国和日本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和偏颇,需要针对性地加以改善。
韩国的研究偏向于从政治或种族角度批判“满映”的创造,忽视了其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一些学者将“满映”看作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延伸,忽视了其本质的多样性和文化价值。这些偏见会影响到协会的研究、资料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导致难以充分考虑电影作品本身的价值,无法明晰两个国家电影产业的异同。
日本较早开展“满映” 研究,也具有相对完整的体系。但由于日本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内容存在偏颇,其以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认为伪满洲国是在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而不是奴役中国人民。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较为主观,以20世纪80年代“满映”工作人员的自传、日记为主,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官方机构档案与多语种资料,研究深度和解释力度有限。
为了提高“满映”的研究深度和质量,亚洲各国需要加强资料的互通和横向联合,同时注重对“满映”的多样性和客观评价,避免从单一角度研究和评价其作品。
4 结语
“满映”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还可以探究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社会风貌、观念变迁等问题。应拓宽“满映”的研究视角,从电影史逐渐转向大众媒介史、文化史、社会史,从一国史转向区域史乃至全球史。同时要综合研究,以电影学与历史学方法为主转向综合艺术学、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从纵向史料梳理转向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纵横交错剖析电影与殖民、电影与战争等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获得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虞文俊,黄萃.生产·投资·扩张:“满洲映画协会”的再考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9):81-89.
[2] 虞文俊.日韩俄近代中国东北新闻史研究回顾[J].青年记者,2018(27):106-107.
[3] 池川玲子.“满洲映画协会”研究史整理与今后展望[J].形象与性别,2007(7):99-103.
[4] 木村庄十二.新中国[M].东京:东峰书房,1953:17-28.
[5] 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及其创始人:大塚有章[J].宋毅军,译.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3):154-155.
[6] 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6-218.
[7] 坪井与.满洲映画协会回想[J].映画史研究,1984(19):23.
[8] 山口猛.幻之电影满映:甘粕正彦与活动家群像[M].东京:平凡社,1989:1-2.
[9] 虞文俊,黄萃.宣传战的中枢:关东军宣传管理机构的制度建设与移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9):108-125.
[10] 金丽实.满洲电影协会与朝鲜电影[M].首尔:韩国影像资料院,2011:1-10.
作者简介:宋熹瑞(1998—),男,山东淄博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电影史。
许叶彤(2000—),女,安徽滁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
向:新闻史。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伪满洲国新闻统制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FXWB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