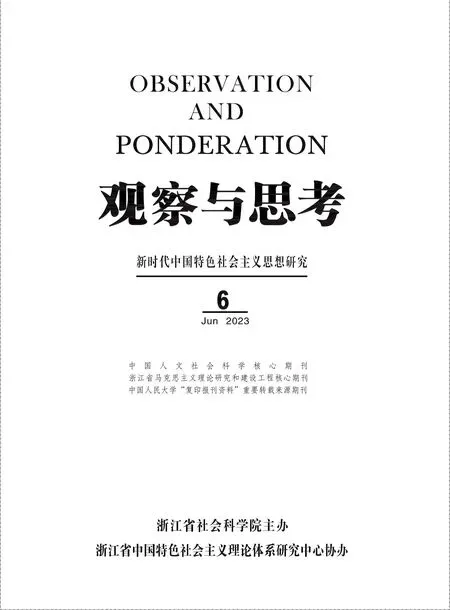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数字劳动的特征分析
刘 爽
提 要: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数字劳动这一蓬勃发展的新型劳动形态,广泛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数字劳动的特征分析是全面深入研究数字劳动的必要基础和关键前提。相较于传统劳动,数字劳动呈现出生产资料数字化、劳动产品非物质性、劳动空间网络化、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模糊化、劳动关系灵活性和不稳定化等鲜明特征。数字劳动的诸多显著变化,拓展着劳动的内涵与外延,重构着劳动正义原则,带来了一系列亟待回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深入分析。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相互联系的超级系统,使得借助程序软件使用计算机系统来生产的趋势势不可挡。网络生产价值链的大部分环节都产生了对数字劳动力的需求,新型数字劳动日益成为信息社会里的重要劳动方式。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20 页。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具有历史特性的数字劳动的探讨和反思,根本关乎着现实的人的发展。相较于传统产业劳动,数字劳动的劳动力队伍、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时间和空间、劳动形态、劳动组织形式、劳动过程的控制和管理方式、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等均发生了显著性改变,广泛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数字劳动的特征分析,是一个跨越哲学、政治经济学、实证社会科学的综合性问题。②参见魏小萍:《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数字劳动》,《社会科学报》2022 年4 月18 日。在充分吸收数字劳动相关研究①本文的数字劳动,是指互联网使用者主要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关键性劳动资料,以数字化信息为劳动对象,生产技术性软件和服务、数据商品、情感服务、能纳入数据收集分析交换网络的数据信息等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基础上,笔者重点分析了数字劳动的生产资料数字化、劳动产品非物质性、劳动空间网络化、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模糊化、劳动关系灵活化和不稳定性等典型特征及其带来的重大影响,以期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实践中重新理解劳动的概念,为全面系统推进数字劳动的研究提供必要基础。
一、生产资料数字化
撇开劳动的各种历史形式,任何劳动都是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的过程,数字劳动也不例外。基于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来考察数字劳动,是迅速把握其一般特征的重要切口,也能显示出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
相较于传统劳动对象以实物原材料为主,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表现为海量数据。对来源复杂、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的感知收集、清洗分析和提取传输并非是自动化过程,而要依赖于庞大复杂的劳动资料数字化体系。劳动资料常被认为是劳动者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它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也包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使其顺利进行的“对象条件”。有别于传统产业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数字劳动的劳动资料虽然也包括基础性硬件,但主要表现为诸如网络协议、大数据存储和分析、云计算、人机共生、虚拟现实等核心数字技术,以及作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等非物质存在方式。
马克思在论及劳动资料在历史中的位置时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0 页。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劳动资料数字化、智能化为起点的。由于资本的必然趋势要求“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75、780、775 页。。马克思表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后,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将是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算法模型、数字孪生等数字化劳动资料,本质上也属于自动的机器体系。一方面,包括智力劳动在内的生产过程日益自动化节约了劳动时间,增加了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无意地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将生产连续性、自动化和智能化发挥到极致,最大限度地代替着“无标签一般劳工”④[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409 页。的技能和力量。“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人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⑤[美]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2 页。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75、780、775 页。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不仅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使“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75、780、775 页。,使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而且决定了劳动力的概念不可能停留在体力和机械力属性的聚合上,不断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推动劳动力质量的变迁。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还革新了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形式,重构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网络技术的灵活性和互动性,突破了传统分工体系下的有组织的劳动力工厂雇佣模式,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化、劳动形式的多元化和劳动关系的灵活化。一方面,从内容上来说,大数据分析技术允许资本获取迄今为止难以获得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从形式上来看,算法管理和数字控制能够将相当异质的、分散的工人整合进“数字工厂”中,使众包工人、零工、临时工等灵活的按需劳动力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力转型的重要趋势。反过来,“规模庞大的全球劳动后备军的存在迫使世界工人的收入紧缩……越来越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弹性’”①[美]J.B.福斯特、R.W.麦克切斯尼、R.J.约恩纳:《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张慧鹏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 年第6 期。。
此外,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这些生产资料,已经开始在整个生产中担任中心角色。一方面,数字技术对市场需求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反馈,使得生产计划同消费需求进行频繁且迅速的交流,颠覆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相对“沉默”关系的福特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的盲目性。甚至,积累足够多的可提取数据可能使市场交易变得可知,使“商品的惊险的跳跃”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7 页。更易完成。因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降低了阻碍传统市场交换的成本,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交易,将市场逻辑扩展到新的领域。比如:它降低了查找信息以及订立、监督合同的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不确定性,并通过评级体系和保险机制产生信任;通过算法远程执行协调和管理任务等。
二、劳动产品非物质性
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被称为非物质劳动,它依赖于我们共同拥有的通信协作网络,关键特征是生产出交流、社会关系和合作。如果说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生活的手段,那么非物质生产创造的是社会生活本身。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劳动产品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社会关系、通信网络和生命形式时,劳动往往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经济生产蕴含着一种政治生产,或社会本身的生产,最终也是主体性的生产,是社会中新主体性的创造和再生产。
哈特和奈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为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提供巨大潜力的丰富论述,对于我们分析劳动产品非物质化的数字劳动,尤其是网络用户部分有意识地无酬劳动提供了重要视角。首先,相比于工厂劳动趋向于专业化和长期重复的、固定的、确定的活动,像网络众包、网络直播等形态的数字劳动需要灵活适应不确定的新环境、新要求,从而解决问题、创造关系、生产想法等。如果说工厂的物质劳动是无声的,倾向于形成沉默、被动的公众,那么,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数字劳动通常涉及语言、沟通和情感技能,与劳动主体的创造能力相联结。比如:网络直播的情感劳动可能在表演行为中实现了劳动主体自我满足与享受。其次,在诸如粉丝“打投”、网络字幕组翻译、自发地在数字平台生产原创内容等部分非物质形式的数字劳动中,劳动越来越具备自主负责协作的能力,“合作也完全内在于劳动本身”③[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 页。,而不是像以前劳动形式那样只受资本激发,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最后,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再受制于稀缺性的逻辑,其产品也不是排他性的。相反,关于观念、符码、感受、图像等非物质产品的使用、交流和传播会使产品本身得到强化和衍生,增进人们“对共同性平等和自由地共享”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94、106 页。。此外,非物质产品尤其是情感产品的生产使“妇女成为大量新兴职业的理想的劳动力蓄水池”②[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341 页。。哈特和奈格里甚至用“工作的女性化”来描述当下劳动性质的变化,强调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劳动灵活性得到提高,以及“那些与‘女性岗位’相关的传统特征,如感受、情绪和公关等,正成为所有劳动部门的核心”③[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94、106 页。。
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常常被批评“给人一种信息工作脱离自然和物质的印象”④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4,p252.。因此必须强调,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数字劳动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替代物质劳动。第一,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几乎总是与物质形式混合在一起。一方面,生产数据信息、情感服务、程序软件等非物质内容的数字劳动同其他一切劳动一样,要运用物质的身体和大脑。因为,“主要涉及身体力量或灵活性的工作与那些涉及思维敏捷性、专注性的工作往往是连续统一的”⑤姚建华主编:《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22 页。。另一方面,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离不开高度物质化的有形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结构的创造、网络增容、数据传输技术的优化迭代、稳定的数据存储介质等“贯穿整个价值链的大型垂直整合运营体制”⑥[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 页。,都要受到投资巨大的物理电信设施、专用接线器和路由器等的物质支持。并且,诸如程序软件等非物质产品常常作为技术元素加入物质产品生产中。第二,数字劳动不是在数量上替代,而是在质量上改变着物质劳动形式和场景。借用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数字劳动在今天的地位,等同于150 年前工业劳动的地位。就像当时所有形式的劳动和社会必须工业化一样,今天的劳动和社会正在走向信息化,智能化、沟通化、情感化的趋势。
三、劳动空间网络化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9 页。任何复杂的生产体系都需要有效率的空间结构。社会既定生产模式架构的特殊性质又形塑着空间。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空间突破工厂劳动严格的实体、区域限制,从物理现实延伸至无处不在的虚拟网络云端。第一,相比大工业生产的效率和合作要依赖于各种劳动要素的物理集聚和邻近,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不仅使劳动空间的规模与效率不再呈线性相关,而且使受地域限制的劳动力的跨区域、全球化合作成为可能。一方面,基于传感器、网络化设备和集成软件架构的算法管理,使今天的“数字工厂”拥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劳动者不必局限于面对面的封闭工厂或工业中心,在物流城市空间,众包平台,甚至移动终端,就可以完成数据信息的采集、提取、传输、储存,智能算法的优化迭代,网络服务器的维护,以及情感服务、创造用户生成内容等。这很大程度上实现着劳动者的工作场所的自主性,即对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和表现行使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不仅包括对自己当前工作任务的控制,还包括能够影响和形成自己所在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数字工厂能够将劳动过程的紧密组织,与灵活的劳动合同、随需应变的劳动力形式结合起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即便互相不熟悉,或者仅通过交换生产信息了解对方,也能有效地从遥远的地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流和隐形合作。比如:以“托克”、跨境客(Upwork)等为代表的线上众包劳动,通过网络劳动空间减少了生产过程受物理规模、地域距离等“外部限制”。从理论上讲,这可以使劳动者突破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边界,将劳动力出售给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买家,进行“技能套利”①Mark Graham,Isis Hjorth,Vili Lehdonvirta,“Digit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Impacts of Global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Gig Economy on Worker Livelihoods,” Transfer,Vol.23,No.2,2017,p142.。第二,网络空间中数据信息近乎无限制、无消耗、零边际成本的可复制性,各种数据产品或商品基于网络编码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便捷化的网络传输和云储存,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生产过程的认识。一方面,数字劳动不再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对生产时间节点严格限定,突破了商品堆积对储存空间的实体要求,压缩了数据商品流通中的时间与空间,将之前分别独立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复制成本极低的数据商品可能不经市场交换就被消费使用价值,使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流通体系难以维系。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里,虚拟的“流动空间”减少了资本增殖过程中的空间障碍,不仅缩短了资本在生产过程、领域的停留时间,而且缩短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周转时间的步伐,推动了资本的“灵活积累”。资本的本性要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9 页。。首先,相较于在工业化大生产的福特组织时代,资本还受制于一个具体的区域,必须按劳动合同与有限的劳动者打交道,生产链条的网络化将资本从固定地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劳动过程和工种此前的一系列现实限制,力求将新的劳动形式和新资源挪用至资本生产和流通中,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空间。相应地,劳动场所的网络化、全球分散和非中心化又引起了资本对劳动控制的中心化、隐匿化和广泛化。因为资本要随着新国际分工进行跨空间和跨生产环节的管理,就必须实现对劳动者更强的规训与控制。其次,相较于传统产业劳动通过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网络空间的交易时间以非人类的软件算法,如毫秒级的单位来测量,从而使生产和消费场所直接相通,在全球运输上用最少的延误和花费迅捷完成交易。也就是说,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高频率运转的网络化劳动空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从而加快了生产过程重复速度和数字劳动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速度。但是,当流通时间达到了归零的绝对速度,交换、货币和以交换与货币为基础的分工也就被否定了。没有交换,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资本也将不存在。
四、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模糊化
社会交往和劳动混在一起,工作与休闲之间没有明确界限,曾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而时间的线性测量,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成熟的工业社会都是以时间节约为标志,并在‘工作’和‘生活’间作清晰的区分。”③[英]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21 页。随着价值生产蔓延到更广泛的“数字工厂”中,劳动和生活、生产和消费、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导致商品化侵蚀和改变着人们几乎全部的交往关系。数字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不断消融,表现为劳动时间延伸进休闲时间,挤占“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63 页。。第一,对于被雇佣的数字技术工人来说,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是当前常态。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资本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会越多。第二,对于雇佣关系相对松散的平台劳动来说,一方面,大量碎片化的劳动时间与时刻等待劳动机会的休闲时间捆绑在一起。不同于传统产业劳动力相对稳定、有保障的职业,节奏规律地生产,以及固定的工作日,数字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增加。保障合同、固定日程的缺乏,使其在诸多非正式工作之间流动,摧毁其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区分,导致了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和发展空间贫困。另一方面,以计件工资为主的工资支付形式,使劳动者为了提高日工资会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如此一来,劳动者“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1、786 页。。第三,不同于工业模式下工人,几乎只在工厂几个小时就能生产出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可能在固定场所的固定时间段内完成,而是会延伸进生命时间的每时每刻。“当生产旨在解决一个难题、创造一种想法或一段关系时,劳动时间往往会扩展到整个生命时间。”③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Penguine,2004,p.111.这会让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的传统区分变得无意义。因为生活时间和生产时间完全重合了。如果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个人也会被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1 页。非物质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创造力,正是在劳动者自由组织自己的时间中生成。但是,劳动时间的不断增加、劳动关系的不稳定,使劳动者失去了对自由时间的掌控,从而也失去了生命创造力和潜在的生产力。
数字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重叠,还表现为休闲时间被纳入资本中“货币化”,日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运作中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无酬的产消劳动中得以鲜明呈现。一方面,货币化的逻辑取决于观众的注意力。网络用户基于休闲娱乐不固定地在网络上浏览商品、创造用户原创内容等产生的海量数据被平台无偿提取分析之后卖给广告商。广告商结合用户偏好、习惯和兴趣的详细资料,为其量身定制并精准投放个性化的内容,用以引导和预测用户消费模式。另一方面,玩工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信息和交流活动直接支持了财富积累。首先,玩工活动的程序化和工具化,以及出售虚拟商品换取真实货币这些行为,已经使其失去了作为纯粹休闲活动的设定。其次,无偿的游戏玩工的创造性极大地降低了游戏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费用,对于游戏产业资本增殖贡献巨大。马克思表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1、786 页。在免费的产消劳动中,“产消者”的部分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直接相通,部分休闲时间被隐蔽地转变为劳动时间,整体落入价值控制之中。产消劳动使资本有机会获得难以从正规劳动调动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对数字资本积累过程越来越重要。
产消劳动之所以很难从休闲活动中被辨认,很大程度上在于产消劳动和非劳动活动几乎采用同样能力,似乎没有付出“辛劳和麻烦”。在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被排除在生产之外。只有当工作结束,福特制工人才可以看报纸、去当地聚会中心对话、交谈。然而,在后福特制时代,由于“精神生活”也被纳入生产中,劳动和非劳动能力以相同的生产力形式诸如语言、社交、抽象思考等标识,①参见[意]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134-135 页。产消者的个性、本真性和激情充分地参与生产过程,劳动力与资本以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一种去异化与剥削之间的新的平衡,使得在闲暇时间自愿进行的、以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为主要体验的玩乐劳动很难得到承认。
五、劳动关系灵活性和不稳定化
相较于传统产业工人受限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有规律的生产线节奏和科层制管理,网络众包平台通常通过(半)自动化的算法管理,根据市场需求和可调用的高度分散且异质的劳动力(技术劳工和非技术劳工)来分配工作。平台劳动组织形式优化了劳动力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可跟踪性和碎片化,在为资本的弹性积累打开了新的劳动力蓄水池的同时,也正在割断雇佣劳动原有的稳定性、福利和支持的纽带。当资本寻求的不再是与劳动的长期契约,而是一种应急的、临时的合同关系,“资本尝试创造更多的‘灵活’的劳动安排,只不过是减少工人获得社会权利的一个掩饰”②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1 期。,劳动者将陷入普遍而持续的不安全状态,产生“不稳定化症候”③[法]皮埃尔·布迪厄:《遏制野火》,河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6 页。,缺乏有保障的合同、固定的日程、稳定的就业,沦为用后即弃的劳动力(disposable labor force)。正如卡斯特所言,“新技术所带来的弹性与适应性的急剧增加,使劳工的僵固性质与资本的移动能力对立起来。无情的压力迫使劳动必须尽可能地具有弹性。生产力与获利力都提高了,劳工却失去了制度性的保护,并且在一个变动不定的劳动市场里变得越来越依赖个人的谈判条件”④[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3 页。。
首先,与传统的临时劳务中介机构一样,众包平台是劳动关系和工作性质重构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制度化了后福特主义时代脆弱的劳动契约,迫使劳动者承担社会再生产的风险和责任。如果说临时工、零工以前还是一种例外,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大多数众包平台将零工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员工。零工与平台的合同关系被规定为一种商业关系,持续时间是完成其所接的平台任务所需的时间。根据平台的服务条款协议,独立合同工不享有正式员工所享有的福利,如:假期工资、病假、陪产假、保险或失业福利等。这些本属于传统雇主的相关责任,被转嫁给平台劳动者自身。
其次,一些标准化的和去技能化的平台任务通常按件支付,其工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边缘化的一种工资形式——计件工资。这一工资支付形式鼓励工人自发地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将资本家对工人的外部监管最小化。正如马克思所言,“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么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570 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矛盾冲突,转移到了工人自己身上。
最后,如果说在传统工业计件工作中,工作场所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还能使控制稍显复杂,因为车间工人可以联合起来,建立非正式的规则限制产出,从而影响劳动强度和报酬。那么,分散且异质的平台临时工很难团结起来,形成有效的反抗。一方面,流动的临时工人状况的杂多性使“过去以集中化的结构去自上而下组织工人的方式变得不再可能”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88 页。。并且,他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有着稳定的工作场所、道德行为规范、互惠和友爱的职业社区或劳工社群,不觉得当下的言论、行为、感觉会对弹性劳动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或约束。相反,不稳定的状态加剧着零工对其从事的工作的疏离感和工具感。对工作认同感的缺乏,使其行动和态度往往趋向于机会主义。另一方面,众包平台嵌入了许多隐形机制使权力关系尽可能向平台所有者倾斜。平台承诺给零工自主权,却又不肯放弃对其的控制权。比如:平台所有者对服务条款协议享有高度的单方面自由裁量权,保留随时修改服务协议的权利,削弱了零工对特定条例和规定的上诉能力;类似优步(Uber)的按需平台通过算法管理,不仅对服务提供者的绩效进行总体排名,创造同行的等级空间,使其竞争性而非合作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将质量控制和服务评价开放给平台客户,这些相关指标影响着平台零工的收入和连续就业,但算法系统的不透明,又只能使劳动者零碎地收集碎片化的信息,无法逃脱平台的隐形控制。如此一来,平台所有者通过诉诸算法“将他们的权威消解到一个公正的软件程序中”②Niels van Doorn,“Platform Labor:on the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Exploitation of Low-Income Service Work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Vol.20,No.6,2017,p903.,尽可能不直接与零工打交道,将其与零工的矛盾迁移到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消费者、甚至劳动者与技术的实践层面上,从而遮蔽他们对零工的监管和压迫,进一步削减不稳定阶级的对抗性力量。
结语
作为大数据时代蓬勃发展的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呈现出诸多显著的时代特征,不断拓展着劳动的内涵与外延,重构着劳动正义原则,挑战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带来了一系列争论激烈、亟待回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免费劳动”(free labor)③“免费劳动”是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网络文化:信息时代的政治学》(2004)一书提出的,包括“建设网站、完善软件包、阅读和应用软件组,以及创建虚拟空间”。这个概念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说的“产消劳动”、库克里奇和肖尔茨所说的“玩乐劳动”、达拉斯·斯迈兹所说的“受众劳动”都具有无酬劳动的相似指向,常被研究者界定为狭义的数字劳动。的价值来源问题,无法轻易测量出来的劳动时间是否还能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随着价值生产蔓延到更广泛的“社会工厂”④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工厂”,不仅指延伸至工厂与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价值攫取的数量上的扩大,而且指通过工人在生产循环中被动员起来的特有“精神”所实现的资本主义强化的质态。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否需要重新界定?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形式和逻辑发生了何种变化?非物质产品的所有权归属,数字劳工的“体面劳动”和权益保障等问题。此外,数字劳动也与特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生活的方式不可分离,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推动着现实的人的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深入分析。